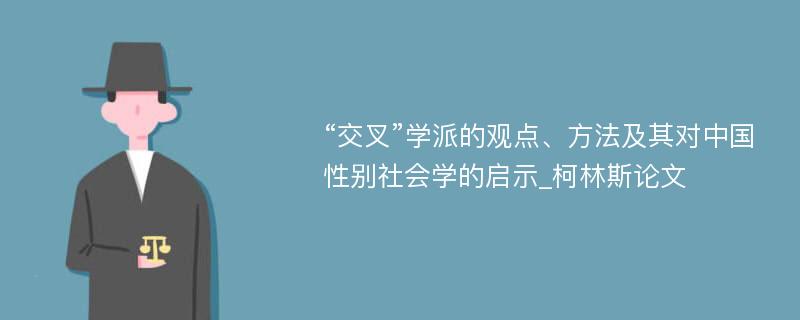
“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其对论文,启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黑人女权运动的崛起与“交叉性”流派的出现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研究是国外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范式,也是分析社会中性别现象的重要方法,但在国内使用的人并不多。本文希望通过追溯这一研究范式的起源,梳理其核心概念和基本方法,思考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在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权运动往往是相伴相生、互相推动的。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汇合交织,许多年轻的女性都参与到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运动中。一些黑人女性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投入到黑人社区的各种行动中,其中包括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奥迪·罗德(Audre Lorde),以及后来成为“交叉性”流派奠基人之一的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这些女性在积极投身黑人女权运动的同时,也发展了黑人女权主义思想(black feminism)。20世纪70年代,“康比河公社”建立,黑人女权主义者通过1977年著名“康比河公社宣言”(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向世界发声。这份声明的重要内容便是批判当时的女权运动更多地照顾白人女性的诉求而忽略黑人女性的需要(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1986)。黑人女权运动的兴起也影响了70年代之后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的知识生产。 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围绕着“社会性别”(gender)展开。但是,在黑人女权主义运动中崛起的学者批判社会性别的研究者将社会类别的一致性(homogenized social categories)看作非常自然(naturalization)的现象,认为类别内的所有人都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具有共同特征(Yuval-Davis,2006:199)。她们提出女性群体内部存在差异性,并认为对女性所遭受的社会压迫的讨论不应该仅限于社会性别领域。她们坚持认为,同一社会性别的群体即使存在一定的共同特征,但仍然会因为内部的阶级、种族、公民身份差异而缺乏一致性(Dill & Zambana,2009:1)。她们中的许多人在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中接纳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力图透过阶级、种族和性别三面棱镜来审视黑人女性身上所遭受的多重压迫,并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来改善黑人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在她们的推动下,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许多女权主义者都开始反思社会性别研究,转而关注女性内部的差异,包括年龄(Bradley,1996:105)、身体机能(disability)(Meekosha & Dowse,1997:49-72;Oliver,1995:100)、公民身份(citizenship)(Lentin,1999:75)和性向(sexuality)(Kitzinger,1987:22)。因此,黑人女权运动的崛起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社会性别理论与现实运动的碰撞中,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发展出同时关注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多元范畴的分析框架,为“交叉性”流派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如上所述,“交叉性”流派是在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互动中形成的。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出现的“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ies)问题也从另外一个方向推动了“交叉性”流派的形成。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环境运动等各种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蓬勃兴起的同时,不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探讨中都出现了身份政治的问题。在实践中,各种运动往往通过成员的某一个身份进行动员。但一个人往往拥有多个身份,在现实的运动中便出现了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同时,在理论解释中,一种身份往往被另一种身份所化约,这种还原论的倾向导致学者们在“哪个身份最为重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这些遍布实践和理论的争论不但没有推进原先的理论,反而在现实中分裂了各种社会团体。因此,如何解决身份政治的困境便成为这个时期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向前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黑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从不同身份“交叉”的角度出发来批判各种社会不平等、在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中建立连接的尝试,为女权主义者进一步发展理论和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启发。这也是90年代之后这一流派的概念、视角和方法逐渐被更多的女权主义者所接受的原因。 二、“交叉性”流派的主要观点 黑人女权运动的崛起、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都为“交叉性”流派的出现提供了土壤。20世纪80年代,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对女性主义提出了“所有女人都是白色的,而所有黑色的都是男人”的批判(Hooks,1981:100)。黑人女性主义者纷纷表示,女性主义理论以白人中产女性的立场为核心,忽略黑人女性的经历,要求女性主义理论更多地关注黑人女性身上所遭受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压迫(King,1988:42-43;Smith,2006:16)。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女性主义者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多重压迫(oppression)体系的相互作用,并尝试通过各种概念来描述类似的社会现象。其中以美国批判法学家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提出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传播最广。 80年代末,法学界内部已经出现了反种族歧视研究,法学家们开始质疑法律所谓的中立,认为种族偏见仍然存在于立法之中。女权主义者、法学家克伦肖强烈批判法律中缺乏对黑人女性权益的保护。她用交叉路口来比喻种族和性别歧视如何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并共同形塑黑人女性的生活经验(Crenshaw,1989:139)。她用这个概念来解释黑人女性作为“边缘性的女性群体”(marginalized women)如何受到各种歧视,而她们所遭受的歧视又如何遭到主流女性主义者的忽略(Crenshaw,1991:1241)。 20世纪90年代,柯林斯对“交叉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概念化,提出“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其他权力相互作用形成社会制度,而这些社会制度反过来建构出被这些特征所定义的群体”(Collins,1990:18;1998b:204-205)。她强调“交叉性”是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的连接点,既要考察宏观层面上种族、阶级和性别三种压迫体系如何交织在一起,也要考察微观层面上的个体和群体如何在这样相互交织的压迫体系中获得现存的社会地位(Collins,2000:18)。在柯林斯看来,交织在一起的不仅是个体或群体在微观层面上的主体建构和认同,同时还有宏观层面的制度形成过程。她在1990年出版的《黑人女权主义思想》(Black Feminist Thought)中提出了“支配矩阵”(matrix of domination)来描述结构性因素与个体间权力关系如何交织在一起,形成压迫。她将“支配矩阵”定义为“那些产生、发展并包含交叉性压迫的所有社会组织”(Collins,2000:228-229)。她认为“支配矩阵”的分析要结合个体或群体“情景化的立场”(situated standpoint)。所谓“情景化的立场”,指的是群体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形成的共同地位和在历史中共同遭受的不平等经历所促成的视角(Collins,1998b:204)。十年后,柯林斯又对“情景化的立场”进行了修正,认为原来对此概念的定义较侧重个体经验,比较狭隘,这个概念也应该指群体在历史中建构的集体视野(Collins,2012:19-20)。依照柯林斯的观点,对边缘群体的研究应该围绕在不平等制度中所遭受的经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视角来分析。 汉考克(Hancock,2007:64)也将“交叉性方法”(intersectional approach)与另外两种常用的方法——“单一方法”(unitary approach)和“多元方法”(multiple approach)进行了对比,指出“交叉性”方法存在六个方面的不同:首先,单一方法只分析一个范畴(category),多元方法和交叉性方法都分析一个以上的范畴。其次,单一方法认为进入分析的这个范畴是最重要的,而多元方法和交叉性方法认为每个范畴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只不过多元方法预设了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和次序,但交叉性方法则认为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和次序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三,单一方法和多元方法都认为范畴的概念化过程要么发生在个体层面,要么发生在制度层面,但不管如何都是静态的;而交叉性方法则认为范畴的概念化是一种个体和制度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第四,交叉性方法认为不同范畴在具体的情境下具有不同的相互作用,但单一方法和多元方法却认为不同范畴之间的组合是固定不变的。第五,单一方法的分析层次在个体层面或制度层面,多元方法可以同时分析个体和制度层面,而交叉性方法则分析个体和制度层面是如何整合的。第六,单一方法和多元方法要么进行经验研究,要么进行理论研究,并且通常倾向于使用一种方法,而交叉性方法通常可以将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并使用多重方式进行研究。 三、“交叉性”流派的基本方法 柯林斯之后,许多女权主义者纷纷将“交叉性”引入她们的研究之中,在方法上经过了从“范畴内”(intracategorial)到“范畴间”(intercategorical)分析,从“过程”(process)分析到“系统”(systematic)分析的变迁。 (一)从“范畴内”到“范畴间”分析 最开始,女权主义者只是将过去研究女性的方法与研究种族的方法相结合,这种方法被称为“范畴内交叉”(intracategorical intersectionality)。这种交叉性分析旨在分析女性群体或黑人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McCall,2005:1782)。范畴内交叉分析仍是将某一类的群体(女性、工人或黑人)作为关注焦点,然后将过去研究过的亚群体(白人女性、男性工人、黑人男性)作为参照类,寻找那些被忽略的其他亚群体(黑人女性、女性工人)的经验。在这种研究方法中,以往研究过的群体往往作为参照的标准,研究者通过个案研究将新群体的经验与之相对比(:McCall,2005:1783)。例如,过去研究男工,现在就开始研究女工(Freeman,2000),过去研究白人中产阶级,现在开始关注黑人中产阶级(Pattillo-McCoy,1999)。过去研究非洲裔的家政工,现在研究拉丁裔的家政工(Hondagneu-Sotelo,2001)。那些曾被忽略的群体的经验被逐渐添加进原有的范畴之中。但这种分析仍然局限在某一类别中,无法跨越不同范畴的边界。此外,不同范畴之间被认为是彼此分割或相互独立的,分析的过程缺乏不同范畴之间的联系。 为了超越某一特定的范畴,需要将所有的范畴联系起来分析。学者们开始思考如何进行“范畴间”的交叉分析。这种分析关注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McCall,2005:1785)。“将种族和性别的范畴视为‘固定点’(anchor point)”(Glenn,2002:14),研究这些范畴交织的地方。范畴交织之处也是不平等的汇集之处。各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也不再仅是研究某些群体的背景或情境因素,而是作为分析对象本身(McCall,2005:1786)。范畴间交叉分析不需要将分析仅限于某一群体内部的多元性,而是关注由多种范畴所规定的多元群体。这些群体是平行的,多种范畴成为分析这些群体的不同层面。这种范畴间的交叉分析并不认为范畴之间是割裂的,也不认为范畴是外在并作用于个体的,而是认为范畴之间是相互重叠的,而且在不同情境中,交叠具有不同的形态。 但是,达蒙仍然认为这种交叠的模型有过度僵化和简化之嫌,从而限制了“交叉性”分析本身(Dhamon,2011:230)。她从前辈柯林斯的“支配矩阵”中获得灵感,提出“意义生成矩阵”(matrix of meaningmaking)模型,该模型的特征包括:首先,强调范畴间相互作用的流动性和历史性,认为范畴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宏观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其次,它重视不同差异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这些相互作用之上的主体建构。第三,它超越了权力(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二元两分,认为控制差异程度和奖惩方式都能形塑模型的情境。 (二)从“过程”分析到“系统”分析 1.包含分析法(inclusion) “交叉性”研究最开始使用的是包含分析法。“交叉性”理论的鼻祖克伦肖和柯林斯都非常强调黑人女性群体的经验,她们在使用“交叉性”概念时,主张将黑人女性的声音带回主流的女性主义研究。使用这一方法的学者,要么通过个案研究展现被大众所忽略的黑人女性的遭遇(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三重压迫)以及这些遭遇带给她们的体验和感受;要么进行比较研究,将黑人女性的生活经验与白人中产阶级相对比,以强调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Moraga & Anzaldua,1984:144;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1986;Hooks,1981:55;Ladner,1973:5)。不管是个案研究还是比较研究,其共同特征是将被忽略的因素加到主效应中,将被忽略的人群纳入研究对象的队伍中,将边缘人群的经验加入到学科体系的知识之中。因此,包含分析法只是将新的女性群体的知识“添加”到既有女性主义理论之中,而不同范畴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被悬置了。这种方法很快就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批判: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添加”的方法仍然是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标准,并没有破除女性主义理论内部的知识等级(Brekhus,1998:34;Danby,2007:29),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种“包含”的方法其实是将不平等还原成“差异性”(difference),并没有深入讨论不平等背后的机制(Baca Zinn & Dill,1996:323)。 2.过程分析法(process-center model) 过程分析法不同于包含分析法,并不讨论性别、种族、阶级、公民身份等社会范畴对于不平等的独立作用,而是讨论这些范畴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包含分析法只是将阶级、种族等范畴添加到性别研究中,而过程分析法则重点分析这些社会范畴如何进行交互,将交叉过程置于中心。 那么,如何将各种范畴的交叉过程置于中心呢? 一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权力发生作用的具体情境(context)之中(Choo & Ferree,2010:133)。例如,关注“黑人女性”作为一个名词是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中建构起来并获得文化上的意义的,同时黑人女性是如何在各种权力的相互交织中形塑其主体性的。二是关注个体的身份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social location)是如何通过不同的情境形成的。身份形成过程是动态分析的重点。三是进行比较研究(McCall,2005:1790),尤其是比较不同情境下个体身份的变化。四是着眼于权力关系的分析。过程分析认为身份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权力关系的作用过程,通过剖析身份是如何在权力关系中建构出来的,来揭示背后的不平等。 因此,过程分析法在社会建构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身份在具体情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来展示权力关系的错综复杂和彼此交织。但是这种分析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不同社会范畴的建构往往属于不同的分析层次,因此很难将微观层次的性别范畴、中观层次的种族范畴以及宏观层次的阶级范畴放在一个过程中分析(Choo & Ferree,2010:134)。 其次,使用过程分析的学者们为了更好地掌握“交叉性”,通常将注意力集中在交叉权力体系中的个体身份建构过程,但是过于倾向个体的身份叙事可能导致很多研究越来越远离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问题的批判,也使研究者忽略制度性的因素在形成社会不平等中的作用,从而了避开了对各种社会不平等的回应(Collins,2009:ix)。 这些反思都将过程分析中所强调的身份建构置于争议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局限于身份建构的分析非常危险,容易将研究引向一种自恋而肤浅的个体叙事(Grzanka,2014:71)。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讨论身份认同和主体性是有意义的,但对身份认同的分析不应该脱离压迫体系,并非所有的身份都应该纳入分析框架中,需要关注的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的身份”(inequality-based identities)(Grzanka,2014:68)。在这些学者看来,身份并不是社会不平等形成的基础,而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Grzanka,2014:68)。在研究中,既不能排斥讨论身份认同,也不能仅限于讨论它本身而忽略它背后宏大的社会图景(Cho et al.,2013:797)。 学者们呼吁用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来解决过程分析容易陷入身份陷阱的问题。这种方法旨在破除原先在身份和不平等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将身份和社会结构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中。系统性分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3.系统分析法(systematic model) 提出系统性分析的学者认为,过程的重要性并不应该高于制度(Weldon,2008)。通过分析不平等的制度如何影响不同层次的社会过程,可以将不同层次的社会范畴纳入一个框架内分析。这些学者感兴趣的并不是建立某种身份的社会过程,而是影响这些社会过程的复杂系统。这个复杂系统在很多学者的分析中被默认为由性别、种族和阶级关系所建构的政治经济体系(Peterson,2005:499)。交叉性的系统性分析旨在剖析这些复杂的系统如何将性别、种族等因素嵌入到所有权、劳动力的商品化和资源的分配等社会过程中(Choo & Ferree,2010:135)。例如,考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下,少数族裔女性获得什么样的工作,从而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存在什么样的权力关系之中,以及建立什么样的身份认同。为了进行交叉性的系统分析,许多学者使用了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这些学者将社会视为通过历史过程建构的多个有边界的系统,每个系统之间相互独立,但又彼此影响(Choo & Ferree,2010:136)。这些系统具有相对稳定性,在路径依赖的情况下能影响系统内个体的社会地位和行动,但它们也非常脆弱,受到系统内任何一个因素的影响都可能发生变迁(Walby,2009:11)。因此,历史制度主义方法一方面将不同层次的社会过程和身份建构与更为宏大的制度勾连起来,另一方面也为行动者改变社会不平等提供可能。在系统性分析方法中,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制度变迁出发,来讨论社会不平等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罗丽莎(Lisa Lowe)对于美国移民法案变迁的分析展现了亚洲移民在美国的地位如何受到法案的影响,而亚洲移民如何在回应这些排斥性方案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文化(Lowe,2014:10-16)。雷迪批判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有色人种中的同性恋者排斥在国家福利之外,同时还不断通过各种项目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之中(Reddy,2014:22-31)。戴维斯也批判里根政府以来美国推行的福利削减政策将许多黑人女性推向社会的边缘(Davis,2014:73-79)。莫汉蒂等学者则分析了在排他性的移民制度以及不平等的福利制度之下移民的身份困惑、挣扎和反抗(Mohanty,2014:79-85;Sengupta,2014:86-91)。交叉性的系统分析法通过在相互交织的不平等制度与个体的多重身份间建立联系,打破了过程分析中结构和主体性对立的局面。 四、“交叉性”流派的内部矛盾、局限与进一步发展 虽然经过上述观点的发展和方法的变迁,但“交叉性”作为一个流派还不够成熟,它内部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张力,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挑战。 首先,“交叉性”流派在定义的问题上存在困境(Collins,2012:22;2015:2)。许多研究者都声称自己使用的是“交叉性”研究,但每个研究者对“交叉性”的理解不同,使用的方式也不同。一些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理论,一些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启发性概念,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它作为一种分析策略(Davis,2008:68)。对于社会不平等的比喻也从经典的交叉口转变为“差异的坐标轴”(axes of difference)(Yuval-Davis,2006)或“动态过程”(dynamic process)(Staunas,2003)。在纳什看来,研究者如果将“交叉性”作为一种理论,尚需加强它的解释力,即如何更好地使用“交叉性”来解释现实中权力的相互交织及其塑造主体性的具体机制(Nash,2008:13-14)。海瑟·比伯则认为“交叉性”更多的是一种帮助学者进行分析的方法论(Hesse-Biber,2007:1-24)。对于如何使用这一方法,学者之间并没有定论。学者们想当然地将“交叉性”运用于经验研究之中,但在方法论上缺乏讨论,“交叉性已经成为性别研究的主要范式,但我们却很少讨论如何对交叉性进行研究”(McCall,2005:1771)。虽然一些学者提出了从范畴内到范畴间分析(McCall,2005:1775-1785),从过程分析到系统分析的可能性(Choo & Ferree,2010:134-136),但另一些学者仍然批评“交叉性”过于开放,定义模糊不清,呼吁发展出更加清晰、具体和稳定的方法(Davis,2008:69;Jordan-Zachery,2007:254;Nash,2008:15)。不过,麦考尔和克伦肖并不认为定义模糊是主要问题,“与其讨论交叉性是什么,还不如讨论交叉性在做什么”(Cho et al.,2013:794)。她们认为即使没有清晰的定义,“交叉性”仍然能够培养一种“分析的敏感性”(analytic sensibility),即让研究者采用一种交叉的方式来思考异同问题以及它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Cho et al.,2013:785-810)。这些争议的背后是“交叉性”的定义困境——到底应该在学科内来定义“交叉性”,还是跨越学科的边界来拓展“交叉性”,或是以完全颠覆传统的学科知识生产方式来对待“交叉性”(Collins,2009:xii)?如果在学科内对“交叉性”进行清晰的定义,可能会导致其过于狭隘,难以发展,但如果跨越各种边界让每个学者依照自己的理解来随意使用,又可能导致这个词过于泛滥,失去它的意义(Collins,2015:2)。柯林斯最新的文章中尝试为“交叉性”的定义困境寻找出路,她认为“种族形成理论”(racial formation theory)为解决“交叉性”定义困境提供了可能(Collins,2015:4)。考虑到“交叉性”流派是从一系列的批评种族理论中诞生的,种族形成理论能够帮助“交叉性”流派通过历史、动态的种族建构视角将宏观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和微观的文化表征联系起来(Collins,2015:4-5)。这样既重视宏大的社会过程,也不会忽略个体的行动,还可能跳出定义之争。柯林斯认为,立足于种族形成理论,“交叉性”流派可以朝三个方向努力:一是从知识形成的角度来审视什么样的命题、概念和内容会被纳入该流派;二是从分析策略的角度来思考如何使用“交叉性”来剖析各种社会现象、制度、问题;三是从批判实践的角度来探索如何将该流派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追求社会正义的实践中。柯林斯提出的解决方案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但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交叉性”的定义困境,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其次,“交叉性”流派内部在“身份”问题上充满矛盾。对于该流派来说,身份是充满争议的概念之一(Grzanka,2014:67)。一些学者批判“交叉性”理论“还没有在身份或主体性(subject)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看法,就着力于描绘二者如何形成”(Carbado,2013:815)。正如上文所述,对于身份及其形成过程的关注是“交叉性”流派中过程分析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如何进行身份的研究却存在不同的意见。希尔兹批判许多心理学研究将身份操作化为自我形象(self-image)和自尊(self-esteem),在进行交叉性研究时只重视比较群体的差异性,或者通过列联表的方式来计算不同差异对于个体的独立或交互作用,完全不考虑差异形成背后的不平等起源,对理解和改变压迫体系毫无作用,反而会强化某些刻板印象(Shields,2014:92-97)。另外一些学者强调个体叙事,将身份的研究付诸对于知识谱系的探究和语言的考古挖掘(Cole,2009:561)。他们受到福柯和德里达的影响,开始质疑现代性的基础,包括现代理论的哲学基础,以及学科的各种概念和类别。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原先的各种范畴(种族、性别、阶级)以及范畴内部的二元两分(白人/黑人、男性/女性、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受到挑战,不平等本身也面临解构(Davis,2008:71)。在范畴不存在的情况下,范畴之间的交叉也变得流动和不稳定了(Staunas,2003;Lykke,2005;Knudsen,2006)。这部分学者受到了流派内部的强烈批评。反对者认为身份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将重点转移到对个体经验的凸显,过于强调个体的特殊性,脱离现实经验,对改变边缘性女性的无权地位、推动社会变革毫无帮助(McCall,2005:1777)。反对者们都坚持认为,如果将“交叉性”理论导向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方向,就会背离“交叉性”理论提出的初衷(Varela,2003:29)。柯林斯等“交叉性”流派的前辈将“交叉性”作为女性主义者反对种族歧视的武器提出来的时候,就表明了自己对女性主义后现代转向的担忧和批判。在她看来,后现代主义放弃对宏大社会结构的关注,转向个体化、去情景化的叙事,会导致人们感到无力摆脱不平等,从而陷入对霸权的同意(Collins,2014:49-54)。她认为个体反抗是无法改变压迫的(Collins,2014)。虽然从个人故事出发更容易掌握“交叉性”,对个体身份叙事的研究也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个体的经验和身份如何在交叉的权力体系中建构起来,但对于个体身份叙事的偏向会导致许多研究越来越远离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批判,也逐渐拒绝对社会不平等制度的回应(Collins,2009:ix)。包括柯林斯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关注和讨论身份认同性、主体性很有意义,但局限于身份建构的分析则非常危险(Grzanka,2014:68)。身份的讨论应该放在更加宏大的社会图景中,打破身份和结构的二元对立来处理(Cho et al.,2013:797)。这也是流派内的学者后来转向系统性分析的原因。但即便如此,普尔仍批判交叉性流派的学者总是试图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将不同的身份切割出来分析,但纷繁复杂和彼此交织的身份在现实中并不是那么容易分离,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交叉性”流派在身份问题上的张力(Puar,2014:336-337)。 第三,作为在美国的黑人女权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批判理论,“交叉性”理论是否适用于对第三世界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交叉性”流派内部也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柯林斯在2010年的时候提到,她也逐渐将目光望向跨越国家的各种社会生活(Collins,2010:8)。她认为“交叉性”的范畴也可以同时扩展到“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民族、性倾向、年龄、能力和国家”各个方面(Collins,2010:8)。而在现实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权主义者也确实将“交叉性”流派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作为反抗殖民主义的工具(Mehrotra,2010:417)。除了反抗殖民主义之外,亚洲一些国家的女权主义者也通过“交叉性”的方法来研究本国女性移民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并进行了各种实践(Choo,2012:42-43)。但一些学者也意识到在第三世界发展“交叉性”流派可能会遇到困境。首先,当西方女权主义者借助“交叉性”的棱镜去看待第三世界女性的生活世界时,很容易将其视为受害者,一味强调对其的保护,而非倾听且与她们一起讨论,从而忽略第三世界女性的能动性和声音(Grzanka,2014:196)。如果西方的女权主义者拒绝在交叉分析中思考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问题,那么当她们使用交叉分析处理第三世界女性的问题时,可能会形成知识上的殖民主义。此外,许多学者也批判西方女权主义者在思考第三世界的交叉问题时忽略“国家”在形成差异和不平等中的作用(Mohanty,2014)。她们认为“交叉性”流派应该更多地将国家、边界和移民纳入其研究框架中(Patil,2013:863)。但是如何将这些要素纳入“交叉性”的研究框架?学者们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巨大挑战。全球化加大了移民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而这些移民可能在流出地是优势群体,但在流入地是弱势群体(Purkayastha,2012:59-60)。这种双重身份也加大了“交叉性”流派进行跨国分析的难度。 不过,尽管“交叉性”流派存在以上种种局限,它仍然被许多国家的女权主义者所接受。21世纪初,它也被引入欧洲世界,在德国、瑞典被用于指导女性福利政策的制定(Kerner,2012:203;Weber,2015:22;Solanke,2009:732)。虽然存在争议,但“交叉性”流派也在逐渐被引入第三世界国家。在实践领域,“交叉性”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被引入社会工作领域,成为指导实践的重要理论(Mattsson,2014:8;Mehrotra,2010:417;Murphy et al.,2009)。除此之外,“交叉性”也在近几年被逐渐引入立法领域,用于指导相关法律的制定(Solanke,2009:723;Grabham et al.,2009)。在今后的发展中,“交叉性”理论可能会与实践结合得愈发紧密。 此外,一些学者也开始探索如何在“交叉性”流派中纳入空间的视角(Anzaldúa,2014:106-109;Boyd,2014:110-118;Pattillo,2014:119-125)。空间的使用和占有背后隐藏着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权力关系,空间的分布也为人们的社会互动提供了可能,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空间是“交叉性”分析的新工具或媒介(Grzanka,2014:99-101)。还有一些学者则开始思考如何用“交叉性”的视角来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实践(Grzanka,2014:259)。可能涉及的议题包括性别和种族相关的生物医学理论的产生过程(Somerville,2014:266)、慢性病和流行病在不同阶级和种族的分布(Shim,2014:273),以及互联网所建构的虚拟世界内的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Daniels,2014:281)。 五、“交叉性”流派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如果说“交叉性”流派的概念和方法将被或已被引入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那么,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它对中国的性别社会学是否存在意义?能提供什么启发?在中国运用此研究方式需要注意哪些关键因素? (一)“交叉性”流派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研究的启发 1.审视中国女性内部的社会分化 “交叉性”流派对女性内部差异以及形成这种差异的宏观社会过程的关注,为我们审视中国剧烈社会变迁下女性内部的社会分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社会结构重新整合。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人们之间的差异逐渐被转化为社会不平等。社会性别之间的分化并没有因为市场的推动而减少,反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而加深。男女同等待遇的计划经济政治的消失,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逐渐边缘化(蒋永萍,2003:15;王天夫等,2008:37),劳动力市场上男女工资收入差异扩大(李春玲、李实,2008:94),女性越发被隔离在某些职业之外(蔡禾、吴小平,2005:71;吴愈晓、吴晓刚,2009:88;李春玲,2009:13),女性从事的职业逐渐贬值。在性别分化加剧的同时,女性内部的阶层分化也逐渐凸显。一部分精英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了更高等级的地位,拥有更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资本;另一部分中产阶级女性无法像精英女性一样拥有令人羡慕的资源,但仍拥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和体面的工作;最后还有位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她们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从事廉价和艰苦的劳动,挣扎在社会边缘(佟新,2010:13-15)。此外,女性内部的城乡分化也与阶层分化发生了重叠。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农村女性往往处于社会阶层的底端,与城市的中产女性和精英女性在生活经验和利益诉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如何面对剧烈社会变迁下中国女性内部的这些社会分化?社会性别范式在解释今天的社会现象时已经展露了它的局限性。不管在经验研究还是实践中,将中国女性作为整体一块来对待无疑会限制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发展。研究者需要引入和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来回应女性内部的这些社会分化。“交叉性”流派所提供的视角和方法提供了一种可能,让研究者通过社会性别、阶层和城乡等多个范畴来审视中国女性内部社会分化的微观表征及其背后的宏观过程。艾米·汉瑟在《服务遭遇》(Service Encounters)(Hanser,2008)中分析了市场经济时期服务业女性在身体、年龄和城乡上的差异是如何转化为女性内部的阶层分化的。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自己使用的是“交叉性”的方法,但其关注社会性别和阶层相互转化的视角无疑有利于分析女性内部分化的机制以及背后的结构性影响因素。而在反思和批判女性作为同质性“整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性”理论,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中国女性内部分化背后的社会机制。 2.重塑中国性别理论和实践的互动 美国的社会性别理论是在第二波女权运动浪潮推动下形成的,而“交叉性”流派则是在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交织中诞生的。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一直贯穿着这些理论的推进。但是在中国,性别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呈现出不同的路径。清末中国女权主义思潮发轫初期,自由主义女权和无政府女权等多种西方女权思潮被陆续引入中国(宋少鹏,2016:71)。这些多元的思潮经过革命的排斥、洗涤和纳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论。该理论从革命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前30年,甚至到改革开放初期,都对中国的各种妇女解放项目和实践具有深刻影响。其中,妇联作为实践的主体,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大量妇女解放的工作。但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始终存在阶级与性别的张力。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性别的话语都放在阶级的话语之后,性别的问题被化约为阶级的问题。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整个社会逐渐从阶级话语中挣脱出来。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后,许多妇联干部和女性学者吸收了社会性别理论,却意外地衍生出一种脱离了阶层、年龄、地域和民族的抽象的“女性”概念。这个抽象的概念被裹挟在一些“女性味”的话语中,当面临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对妇女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剧烈冲击时,失去了对抗的力量,转而被商业所利用(王政,2005:89)。虽然近20年来,在社会性别理论的指导下,体制内(妇联)和体制外(非政治组织)发起了许多实践项目,但由于抽象概念的阻碍,很多项目难以回应社会剧烈变迁下出现的新问题(包括上文所提到的女性内部的阶层分化),导致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虽然新一代的研究者试图从西方女权主义思想中寻找帮助,但引入的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并没有为此带来太大的改观。二者对个体叙事和个体反抗的强调甚至让人们忽略了宏观的社会不平等。 “交叉性”流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发轫于对抽象而同质的女性概念的批判,并且在与实践的互动中发展起来。通过“交叉”的视角,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论中性别和阶级的关系,将其作为一种嵌套而非对抗、替代或化约的关系来处理。同样,实践中,“交叉”的视角帮助我们介入群体不同层面的具体生活,从不同方向来共同推动社会不平等的改变。借助“交叉”的视角和方法,我们可以挖掘本土的理论传统和实践资源,重塑中国性别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互动。 3.寻回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声音 剧烈的社会变迁不仅带来女性的社会分化,使女性内部出现了精英女性、中产女性、农村女性、女大学生、打工妹、下岗女工等多个群体,还形成了残疾妇女、单亲贫困母亲、(男/女)同性恋等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几十年来,虽然学术和媒体的讨论仍主要集中在女性精英和中产女性所关心的问题上,但许多研究者已经将目光投向底层女性。在劳动社会学领域,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将性别与阶级的双重视角糅合在一起。李静君和何明洁批判劳动过程理论中的“阶级优先”预设,提出资本在工作场所中往往借用女性的身份来实现控制。在《性别与华南的奇迹》(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中,李静君发现两地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结构导致了香港分厂和深圳分厂内部管理策略的差异。劳动力短缺使得香港工厂通过温情的方式来打造“工人妈妈”(matron worker)的身份,从而让女工自觉地工作;同时,供过于求的内地劳动力市场则使深圳的工厂能够通过规训、惩罚和乡缘控制等方式来制造出驯服的“未婚女工”(maiden worker)(Lee,1998)。何明洁的研究也同样强调资本对于不同女性身份的利用。在她的《劳动与姐妹分化》中,餐馆通过女性不同的身体特征和年龄来实施对她们的控制(何明洁,2009)。但由于两位学者的研究起点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框架,分析主要集中在工作场所等中观层次,缺少对于劳动控制背后的社会和政治经济不平等的批判。此外,劳动过程理论往往被认为缺少挑战政治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对结构的强调导致学者忽略女性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也使得改变这些女性命运的可能性显得很渺茫。另外一些学者曾在自己的研究中尝试探索底层女性的能动性。潘毅的《中国女工》将20世纪90年代打工妹的性别和阶级经验的交错放置在改革进程中宏观的社会过程下考察。在她的研究中,资本借用女性的地域身份对女工实施控制,使女工形成了被称为“打工妹”的破碎而多元的身份(潘毅,2007)。在她的笔下,被剥夺话语权的打工妹只能通过“梦魇”这一身体的反抗来发声(潘毅,2007)。严海蓉则通过家政工的故事来分析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如何通过“素质”的话语来打造出渴望“自我发展”的女性主体(Yan,2008)。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两位作者所强调的能动性都是非常个体化的。在潘毅那里,个体化的能动性通过一种身体的反抗表现出来,而严海蓉笔下破碎流动的主体根本没有改变她自身命运的可能。 这些学者都在努力寻回底层的声音,但这些声音还非常微弱。为了更好地改变底层女性所遭受的社会不平等,我们需要和这些女性一起去寻找甚至创造出更有力的声音。具体可以从两方面来努力:一是更多的研究者从性别、阶层和城乡等多个层面关注底层女性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经验,二是借用“交叉性”流派的方法将她们集体而非个体的声音发出来。在交叉性流派中,由“支配矩阵”和“压迫轴线”等基础概念发展而来的系统性分析通常会结合“情景化的立场”,即柯林斯所强调的群体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形成的共同地位和在历史中共同遭受的不平等经历来分析群体的遭遇,同时思考改变群体命运的可能性。这在中国语境中,对许多被忽视的边缘群体(如残疾妇女、单亲贫困母亲、男/女同性恋等)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交叉性”流派运用于中国社会环境中的局限 虽然“交叉性”对于研究者审视中国女性内部的社会分化、重塑中国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探寻底层和边缘人群的声音都具有启发性,但作为发端于美国黑人女权运动的理论,并不能直接套用到我国的经验研究和实践中。研究者将其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可能会遭遇若干挑战,试分析如下。 首先,对于这样一个在第一世界国家发展起来的理论,能否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上文第四部分已经有所论述。在中国,国家在形塑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各种身份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罗丽莎通过考察一个工厂里三代女工的性别和阶级身份,发现不同时期的女工身上都烙着国家在推动现代化项目的印记(罗丽莎,2006),而贺萧对农村女性感知性别和农民身份的研究中也发现,国家在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Hershatter,2011)。因此,在中国通过“交叉性”视角和方法来考察女性在性别、阶层、地域和民族等多方面经验的相互交织,一定要考虑国家推动的宏观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与美国显然不同。“交叉性”理论形成于美国的社会运动中,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公民社会”式的“国家—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与社会是界限明晰的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并且二者间存在对立。但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却并不是如此清晰,关系也并非截然对立。因此,当我们引入“交叉性”的视角和方法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理论所预设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不适用于中国。“交叉性”流派所提及的造成各种社会不平等相互交织的系统,也并不一定能与中国的现实契合。此外,黑人女权运动更多地将“交叉性”理论用于指导自下而上的运动,但在中国现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要进行任何改变社会不平等的实践,都不能无视强大的国家力量。 其次,“交叉性”流派是美国黑人女性在回应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内部矛盾的斗争中形成的。在对付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一双头怪时,它是非常有利的武器。但在中国使用的时候,则会受到中国不同的历史路径的限制。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什么?对于形塑女性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发挥了什么作用?不同群体的女性身份是如何嵌入“官”与“民”、“公”与“私”之间的矛盾的?这些身份与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各种项目和群众运动存在什么关系?当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以后,原先的矛盾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和新时期的矛盾又出现了什么样的结合?对于不同的女性群体又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研究者在吸收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方式时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引入“交叉性”流派将遇到的挑战。此外,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后,社会中萌生的力量要么被吸纳到制度中,要么被排斥和压制,使得改变社会不平等的实践都呈现出一种“去政治化”的状态,这和“交叉性”流派在美国黑人女权运动中扮演的政治性角色存在一定差异。 最后,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与美国不同。在流动已成为社会重要特征的今天,将“交叉性”视角和方法运用于分析中国移民(包括移民海外的华侨以及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都会遇到第四部分所提到的双重身份的困境。 (三)“交叉性”流派在中国可能的发展方向 尽管“交叉性”流派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挑战,但是研究者只有在了解西方理论边界的基础上进行吸纳、重整和创新,才能在理论和现实的碰撞中推进中国性别社会学的研究。因此中国的研究者仍然可以立足于本国的现实,尝试在以下方面进行一些拓展。 1.时空的交叉性 如上所述,研究者使用“交叉性”分析进行中国研究时既要关注国家的重要角色,又要注意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矛盾变迁,同时还要关注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那么如何把这些因素整合进“交叉性”的分析框架之中?过去我们进行性别社会学研究通常进行的是截面的和静态的社会分析,但是我们会发现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的作用并不相同,而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也在不同时期发生了变化。性别社会学研究必须追踪这些变化,进行动态的研究。加入历史的维度非常重要,中国的性别研究已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社会史作品,空间的视角也在慢慢引入中国的性别研究,但将二者的交叉当成一个坐标系来考察中国性别现象的研究还较为少见。那么,如何在“交叉性”研究中加入时空的维度?老工人聚集区的迁移以及城中村的形成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性别、阶层和市民身份的交叉问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尝试进行时空性交叉研究的机会。 2.跨界的交叉性 王政曾经提出“越界实践”的概念,认为越界“不仅是自我完善,更是改造社会,这样的实践不可能仅是一种个体行动”(王政,2005:3)。她在书中提到的“界”更多指的是中美两国及其文化的界限,但本文尝试探讨的“交叉性”分析在中国的跨界实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跨越学科的界限,不同学科背景的中国女性主义者从不同角度切入,通过互相补充和配合来深化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例如在上文提到的将历史学、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时空研究,此外还包括人口学、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共同合作开展的老人健康的性别、阶级和地域差异研究,以及运用法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知识的各种反家暴和反性骚扰项目。二是跨越研究者和行动者之间的界限。正如上文所述,“交叉性”为重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可能。但重塑能否达成,还要看能否跨越研究和行动的边界。只有研究和行动的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推动“交叉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三是跨越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之间的界限。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并不是西方的二元对立关系。妇联在改变性别不平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但若要在妇女的解放事业上走得更远,以妇联为代表的官方力量还需要在“交叉性”视角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性别与阶层之间的关系,并且回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发动群众力量的传统,积极与民间力量对话和合作。只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良好结合,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才能向前推进。标签:柯林斯论文; 美国女权运动论文; 交叉分析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黑人文化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群体心理学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女权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