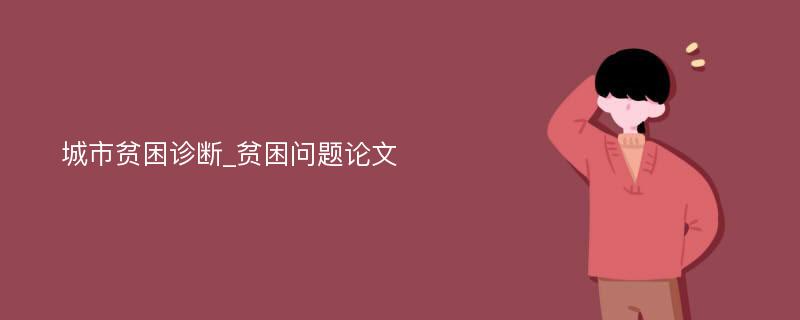
城市贫困问题的诊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的机会和手段这样一种生活状况。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市中实行普遍就业制度、基本均等的工资收入制度以及粮油供应的价格补贴制度,城市里基本不存在突出的贫困问题。但是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中启动了破产失业机制;企业职工的工资不再由国家统一确定,完全由企业根据自身的经济效益自行确定;粮油价格全面放开,短时间内涨了10倍。因此,失业者、提前下岗者、亏损企业的职工等等,开始沦为城市中的贫困者。对于这种新情况,笔者拟作一些较为粗浅的研究和阐述。
一、城市贫困的现状描述与宏观预警
据国家统计局最近抽选的全国550个县市、15 万户居民家庭的生活资料的测算结论,1993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贫困标准为人均年收入1130元人民币;困难标准为人均年收入1355元人民币。 目前我国城镇约有370万户、1200万人口处于上述贫困状态。值得一提的是,按四口之家年收入14763美元的贫困线计,美国的穷人在1993年已增至3930万人, 占美国人口的15.1%。发达的市场国家尚且如此,更何况正处于体制转轨中的中国(美国的人口数只相当于中国的1/4)。[1]
据河南省统计局城市调查队发布的测算资料,1995年河南省城市贫困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1343元,仅相当于城市居民平均水平的35%左右。由于收入微薄,赚的钱主要用来糊口,食品支出达60%以上,但仍然量少质差。城市贫困家庭人均消费的肉类、家禽、瓜果、鲜奶等,总起来说,比城市人口的平均水平低将近一半。其中,肉类的消费量比一般城市人口少40%;鱼和鸡少50%,鲜奶少65%。调查表明,1995年城市贫困人口在脂肪、蛋白质、热量三种主要营养中,除了脂肪尚能达到正常健康需要外,其他两种,都达不到国家所认可的正常生理需要的最低极限标准。由于贫困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二不得不用于购买食物,日常的穿着和使用方面的消费就自然地处于很低的水平。在穿衣方面,大体比平均水平低60%以上,许多贫困人家在耐用消费品方面,仍处在“老三件”阶段。唯有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比平均水平高出52%。
城市贫困人口在刚才所提到的那些食品的消费上,不仅比一般城市居民要低得多,并且自己和自己相比,还有个逐年下降的趋势。同时,遇到了入不敷出的难题。从全国来看,1995年和1990年相比,城市居民的猪肉消费下降3.7%;牛羊肉下降19.1%;鲜奶减少6%;甚至连蔬菜也要压缩消费,1995年和1990年相比也减少了16%,另从全国来看,平均每个城市贫困人口的支出大于收入的缺口近几年来是不断扩大的:1991年人均为60元;1992年人均100元;1993年人均124元;1994 年人均161元;1995年人均181元。[2]
社会学家通过对1992年黑龙江全省1200户城市居民家庭中10%最低收入户的抽样调查资料分析表明,目前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较低,生活质量较差,尚处在较为贫困状态。恩格尔系数是国际通用反映居民生活贫富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表明,最低收入家庭月人均用于食品支出额为38.63元,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为56.28%,高于全省平均比重6.36个百分点,比最高收入家庭高8.39个百分点。按恩格尔定律规定,恩格尔系数高于50%则为处在较贫困状况,因此成了目前黑龙江全省城市居民奔向小康的一大难题。
调查表明,我国城市最低收入家庭每人月均消费性支出为68.71 元,比黑龙江全省的114.83元低40.17%, 只及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消费的38.41%,这部分家庭不仅消费量处在低水平线上, 而且消费结构质量也差,从几种日常主要商品的消费不难看出,低收入家庭消费与黑龙江全省及高收入家庭均存在明显差异。首先是食品,最低收入家庭月人均支出38.63元,比黑龙江全省平均水平57.32元低32.61%, 只及最高收入家庭中人均水平的45.09%。最低收入家庭中肉禽、鲜蛋、水产品、 鲜菜的人均消费量分别比全省平均消费量低32.63%、27.5%、45.05%、10.76%。其次为衣着商品,最低收入家庭月人均支出为10.79元,全年人均购买服装2.47件,分别比黑龙江全省低50.05%和47%, 只及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消费的35.84%和42%。质地差异也很大, 如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消费鲜菜的混合平均价为每公斤0.49元,成衣每件24.67元, 全省平均鲜菜每公斤0.62元,成衣每件30.94元, 最高收入家庭每公斤鲜菜混合平均价则是0.66元,成衣每件35.5元。调查表明,低收入家庭日常消费吃的也是廉价商品多,穿用档次低。在耐用品中,低收入家庭彩电、冰箱等现代化电器拥有量少,其百户拥有量分别为43.6台和11.4台,与黑龙江全省平均拥有63台和29台比,分别少19.4台和17.6台,仅为全省所拥有量的69.2%和39.3%。[3]
另据调查,上海市区还有26万贫困户和82万多贫困人口,仅浦东就有8.258万人人均实际每月生活费收入为135.09元。[4]据有关媒体透露,南京市有6万多名月收入100元左右的特困职工;鞍山市职工家庭人均收入不足70元的有16220户。 据国家有关部门对全国五大城市的联合调查表明,在这些现代大都市里,尚有9%左右的贫困者。[5]
可以预料,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尤其是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相当一个时期里,中国城镇中的贫困人口将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而不断扩大。所以,诺贝尔经济学资金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莱因在前不久的一次在华研讨会上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在更均匀的地域范围内展开,以使整个人口都能获得改革带来的物质利益。”[6]他同时指出,在亚洲其他地方的某些国家,长期不公平的分配减慢了经济的发展,甚至使经济产生倒退。因此,为了获得迅速的发展,政策制订者应对经济利益在大部分人中间的平等分配给予充分的重视,否则政治家们可能要面临国内的不稳定。克莱因的观点对我们不无启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出现和增多,表明我国城镇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了显著分化,引起这种分化的有过渡性因素,也有持续性因素;有个人自致性因素,也有体制因素;持续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研究表明,城镇低收入群体的一些社会特征(包括心理和社会行为)有逐渐凝固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案例表明,在低收入群体布局分散、群体特征不明显的大城市,家庭成员参与城市社会活动所特有的身分单一和活动多向两种特点使家庭消费下降的弹性很小,家庭成员极难接受降低生活水平这一事实,在业贫困者作为家庭经济支柱难以通过家庭认同和群体认同来宣泄或者转移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因此,大城市在业贫困者从常态到越轨行为,其越轨行为从隐蔽性到突发性,从家庭认同到社会认同之间的三个转变往往缺少过渡,而现有的社会指标监测对于发现和界定这类转变也缺乏敏感,这不利于大城市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城市贫困的原因分析
城市贫困,不仅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是世界范围内长期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世界银行在70年代初根据一个严格的贫困定义,估计大约有9亿人口是绝对贫困的,其中有2亿在城镇。如果把绝对贫困定义为:“收入在不够负担营养上适当饮食及非食品的必须项目之下”,联合国最近关于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估计指出,1985年,(不包括中国在内)这些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字也达到11.5亿,其中3 亿多一点是城市贫困人口(UN,1989)。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拉丁美洲,据“拉美人口统计中心”(celado)1983年的研究,大都市有40%的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之下,到本世纪末,这个数字估计可达2/3。[7]
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市贫困问题,根源于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社会分配的不公正、政策的失误以及不利的国际因素的影响。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不利。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工业制成品价格不断上涨,使发展中国家严重受损。加上债务负担过重,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趋于减少,特别是西方以人权“民主化”等条件处理双边经贸关系,单方面的经济制裁、贸易配额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层出不穷,也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出现的原因,一是亏损和双停企业的效益下降,二是前段时期物价持续上涨造成职工生活困难,三是失业和提前下岗者遇到的生活贫困。
目前亏损和双停企业主要集中的行业是:纺织、轻工、森工、煤炭、军工,这5个行业的职工多属低收入群体, 他们的收入仅是高收入行业职工收入的1/2到1/8。近年来,减发工资、拖欠工资和离退休费的现象相当严重。据对23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1994年末, 城镇职工中有291万人被减发工资,有204万人被停发工资;离退休人员中有64万人被减发退休金,有51万人被停发退休金。1995年亏损企业和困难职工数量继续增加。据26个省级劳动部门的调查,截至1995年底,共有破产、停产、半停产企业约4.1万户,涉及职工665万人,其中被减停发工资的职工有479万人,减发和停发工资总额105.7亿元;破产、停产、半停产企业的离退休人员有163万人,其中不能正常领取离退休金的近70万人, 减发和停发离退休金总额为7.88亿元。困难程度较严重的地区有东北三省、河南、江西、陕西、山西、贵州等省。有的企业连续4 个月没开工资,造成50%的职工家庭没钱买粮。而那些远离城市的煤炭、军工、森工常常是一家几代人在同一企业工作,拖欠工资对这类职工家庭影响更大。[8]
根据对9个省1994 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来源”的数据分析,国有企业和集体职工工资占生活费收入的比重平均值为0.788042,[9]可见职工工资(主要是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对于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至关重要。由于长期拖欠工资,部分职工的原有积蓄已经花光。据某省的部门调查,停产企业中有20%的职工靠亲友接济,34%职工靠变卖家产和节衣缩食度日,一些职工家中断菜断粮现象时有发生。双职工、多职工在不开工资企业的职工家庭尤为困难。有的特困职工因生活无法维持而吃野菜、讨饭、捡破烂、卖血、卖淫,甚至自杀,境遇凄惨。因特困企业交不起统筹费,统筹部门采取“差额回拨”,不足部分由企业自补,因而提高离退休费标准难以落实,调查的集体企业中只有7%落实了国发(1994)9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调整企业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的通知》的规定。全国有5 %的离退休职工只发部分或停发退休金。[10]
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短缺社会的特殊阶层和职业阶层的物质占有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必然结果。发生在通货膨胀背景下的物质占有差别所导致的消极的社会后果之一,便是“在高水平的消费中,需求得到低水平的满足”。即使消费在增长,但是,一般的家庭的主要看法是“情况正在变坏”;这是因为,在高水平的通货膨胀下,相关的大部分家庭本期收入中的消费支出绝对地增加了。社会学家的调查更具实证性,它告诉人们,前段时期物价的持续上涨,已造成部分职工生活水平的下降。1994年由于我国生活费指数上升了24%,使31%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下降。1995年虽然物价涨幅有所遏制, 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比例仍然继续扩大到38.5%,据重庆市总工会1995年11月份的抽样调查,该市按必需品法口径计算出来的月人均消费额为196.67元,而困难企业职工家庭人均月生活费收入只有111.47元。在被调查的困难企业职工家庭中,62.06 %入不敷出。职工人均工资虽有增长,但一是只涨档案工资的“空调”;二是地区不平衡,1994年职工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500元, 最低的吉林省仅为174.47元,新疆职工月人均收入在300 元以上的只占职工总数的1.8%;三是各种收费、摊派都有较大增长。 三种因素综合作用使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少数职工生活呈现绝对贫困化。调查表明,1994年有的煤矿80%的职工没买秋菜,进入冬季无钱买煤,室内温度仅在5℃;由于企业拖欠工资,职工交不起房租费,一些租房户职工被房主逐出。1995年9月末统计,青海省有2万名职工人均月生活费在70元以下,其中8000人在45元以下,无钱买取暖煤,无法储存冬菜,有的连基本口粮也无能力购买。1994年北京居民人均收入为6500元,户均收入为17000元,但是该年在北京市民人均生活费月收入不足100 元的相当部分职工家庭中,已经出现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出门”,无法进行体面社会交往的案例。[11]
导致城市贫困的另一个原因是失业。失业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而我国失业现象又具有其特殊性。 除了政府公布的1994年城镇2.9%的失业率外,大量存在的是城镇隐蔽失业现象。隐蔽失业,是指虽有职业但就业不充分、低效率就业的非公开失业;具体地说,是指有劳动意愿并且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未能与岗位在数量或质量上实行充分有效的结合而处于部分闲置状态的现象。我国的隐蔽失业现象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的冗余劳动力。我国目前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约1.1亿人,约有隐蔽失业人员3000多万人, 隐蔽失业率为30%。基本根据是:(1 )近来几千家国有企业在比较规范的股份制改造中,平均约有30%至40%的职工被“分离”出来;(2 )据估计国有企业中资不抵债的企业约占10%左右,这些企业的人数约有800万;(3)国家科委的一份有关500余家国有企业调查表明,其有效工时仅占制度工时的40%至60%,即是说,这些国有企业至少有40%的隐蔽失业者。[12]调查表明,目前失业者和提前下岗者的家庭,尤其是人口多而就业者少的家庭,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另据社会学者的研究,在大都市,低收入群体相对比较分散,而且多是企业的内部分化,这样的低收入家庭为了维护个人尊严,甚至仅仅为了子女而需要保持在社会交往中的形象,往往掩饰自己生活状态的穷困,几乎没有形成群体行为和群体意识;而失业者和提前下岗职工的家庭,由于生活状态相同而集中,已经具有了群体意识,[13]为了改变贫困状况,也出现了内部认同和组织群体行为的征兆。这种状况对社区秩序、社会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值得重视。
三、城市反贫战略的构建
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最为重视、研究最多、对策与措施搞得最频、然而收效不甚大的问题之一是贫困问题。一般地说,克服贫困现象的难度极大,而缓解贫困严重度则是可能的。城市贫困问题也不例外。
近年来,各地区分别制定了自己的有关城市扶贫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最低工资标准。1995年这一标准郑州为163元, 县级市要低一些;二是居民生活补助标准。郑州每人每月50元,洛阳、新乡这样的地级市45元,县级市35元。还有些城市的规定更具体,如青岛规定,从1996年起,凡具有本市城市户口的居民, 家庭月人均收入不到96元者,每月由民政部门用现金补齐到96元,并享受每月36元的粮油特供,就是说,这36元的粮食和食油是可以不拿钱的。武汉市也采用了类似的办法,将贫困家庭的人均收入补齐到120元。[14]上海、福州、 大连、厦门等地也已有初步方案出台并实施,广州、深圳等城市也在积极酝酿。例如:1994年上海确定的贫困线标准是147元,另加一些实物,是由民政部门与劳动部门共同制定的。[15]不过,各地虽然有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但是普遍缺少明确限定责任边界的、有能力的保障供给主体和有效率的实施机制。据1995年初广州市调查,只有65%的企业能够执行市里制定的贫困职工困难补助标准,实际上有56.5%的困难职工不能得到正常补助。1995年全国90%的城市仍然由企业或者企业主管单位承担职工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线,就调查的各城市而言,保障有标准而标准实施无保障的情况并不罕见。[16]职工的工资应该由企业来发,而不能让政府负责,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明确的。政府最低工资政策,是对工人阶级的关怀,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权力,但支付最低工资的却应该是企业单位。生活费补助和最低工资不同,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对居民的生活补助不是企业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可见,落实政府的扶贫政策,需要寄希望于深化改革,寄希望于通过改革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寄希望于改革中建立新的城镇低收入职工的社会保障体制。
继续抑制通货膨胀是缓解城市贫困问题的另一个对策。有人认为,改革过程中,通货膨胀为加速改革步伐提供了一个契机,也有人认为通货膨胀给改革带来了根本的危险。今天看来,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从各国经验看,在通货膨胀危机爆发的初期,物价的上涨速度明显低于货币发行量的增长,此时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暂时的刺激,形成虚假的“通货膨胀景气”,但紧接着就会出现加速的物价上涨,货币需求大增,居民开始恐慌,抢购风潮席卷而来,失控的通货膨胀严重扭曲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关系,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使改革的成果化为乌有,甚至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在改革过程中,要尽应有的努力慢慢降低通货膨胀的水平(这一办法同通货紧缩主张有很大区别,它强调的不是急刹车,而是“慢慢降低”)。这时,只有一种行为应该在经济政策中受到重视,那就是令人满意地降低物价上涨型通货膨胀的水准和缩小短缺的规模。当然,这里讨论的前提是在改革进程中已经受到短缺膨胀的困扰。通货膨胀的加剧要求给予工薪阶层以适当的工资物价补贴,但是,改革进程中不允许有任何传统因素干扰经济的市场化,它要通过反补贴使价格结构趋于合理。这种“反补贴”,在波兰第二阶段经济改革中曾威胁到其占支配地位的工资物价政策。在1982年到1987年的6 年时间里,波兰为了改善扭曲的价格结构,在改革过程中实施反补贴政策,物价上涨了近5倍,而价格结构并没有取得比以前更好的均衡, 与之相联系的工资和其他收入的结构甚至比变革之前变得更不合理,改革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废除补贴,而在于取得新的经济均衡,工资和物价政策以及经济和财政的措施的执行都应该服从这一目标。要达到均衡,通过降低通货膨胀率比提高膨胀率要容易得多,其适当的要求是同时降低所有经济人的货币收入率,更进一步,调节货币供给增长率,使之与国民收入的变化真正同步。
当维持渐进式地降低通货膨胀和减少短缺时,对不能激发起效率的有关价格和补贴进行更广泛的变革和限制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这些变革和限制要求具有很大差别和非常严格的货币信用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治上的考虑,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不能在纯粹经济条件下解决。因为,一个新的管理体系的成功引入不是决定于它的经济吸引力或基于理性的推导,而是取决于真实政治力量对其兴趣的存在。不过,应该强调,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必要大幅度地削减补贴从而对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在商品价格弹性非常低或者是我们寻求的消费品已趋于饱和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这时应该引导人们去储蓄。因为基本需求是没有弹性的,而且家庭预算要考虑某项开支是否重要。所以,在高档消费品使用技术条件缺乏或选择没有余地之中存在着大量的储蓄潜力。
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再一个措施是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机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促进功能”,从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和我国现实的失业压力出发,适当扩大失业规模在所难免。1996—2000 年间可以考虑将政府宏观控制的失业规模由现在的3%扩大为4%。加上提前退休,近期内占总数12 %左右的职工可以剥离出企业,这将实质性地改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再就业工程的进展。另一方面,要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安全功能”,适当提高失业救济的发放标准和替代率。目前各地失业救济标准仍然是1993年制订的。这两年一方面物价涨幅较大,另一方面工资总额增幅较大,提高失业救济的替代率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建议将各地失业救济金发放标准统一规范在上年所在城市最低生活费标准(或民政部门社会救济标准)的120%至所在城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80%之间。在这个幅度内,由各地政府制订具体的发放标准和政策,原则上应根据失业人员工龄长短划分为5年以下、5—10年、10—15年、15—20年、20年以上等档次,工龄越长,失业救济越多。
注释:
[1][6]以上数据和资料转引自伍大荣:“贫富差距的动态思考”,《社会》,1995年第10期。
[2][14]以上数据转引自陈相成:“不容忽视的城市贫困现象”,《经济经纬》,1997年第2期。
[3]以上数据转引自郑文彬:“低收入家庭生活步履维艰”, 《活力》,1993年第6期。
[4]以上数据转引自袁华音:“浦东新区贫困问题与社会保障”,《社会》,1994年第3期。
[5][15]以上数据转引自王立新、万辉:“城市扶贫路千条”,《社会》,1995年第11期。
[7]以上数据转引自艾吉特·辛格:“城市化、 贫困和就业:第三世界的大都市”,原载于英国《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第11卷,1992年。彭本荣译。转载于《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1期。
[8][10][11][16]以上数据和资料转引自樊平:“中国城镇的低收入群体:对城镇在业贫困者的社会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9]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 第266页。
[12]以上数据转引自李明:“我国隐蔽失业问题分析及对策”,《学习与实践》,1996年第1期。
[13]江流、陆学艺、单天伦:《1994年~199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35页。
标签:贫困问题论文; 物价水平论文; 标准工资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