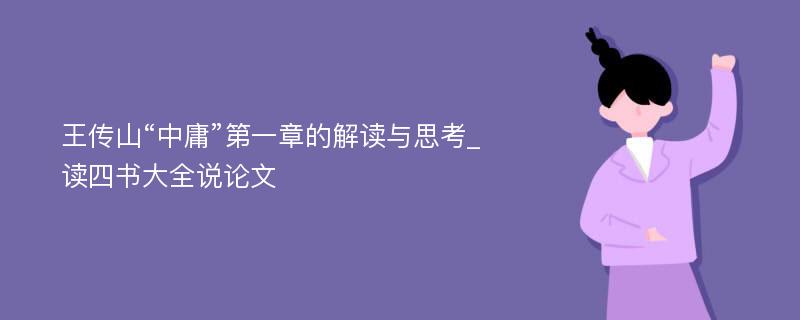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庸论文,思想论文,王船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6-0641-11
关于船山对《大学》特别是其对“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心性学理解,我在另一篇论文中已经作了细致的分析。众所周知,道学的心性——功夫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学》和《中庸》二者共为基础。《大学》和《中庸》不仅为道学提供了基本的心性范畴和功夫范畴,也成为道学心性哲学和功夫理论的核心经典。朱子早年的心性功夫受《中庸》(中和)影响较大,中年以后其学则以大学功夫(格物)为主(注:自然,这只是笼统言之,朱子中年以后至晚年,其功夫论中亦重视《中庸》的戒慎恐惧等。),宋代道学也因此转变。朱子以后的道学发展,无论心学理学,多在《大学》功夫的框架中以各自的诠释向不同条目发展,如阳明主致知,淮南主格物,蕺山主诚意等。但《中庸》的范畴与节目仍与《大学》条目结合一起受到重视,尤其是“慎独”之说贯穿《大学》《中庸》二书,所以阳明仍注重戒慎恐惧的问题,蕺山以诚意与慎独并提,船山亦是如此。本文即是在对船山《大学》思想研究基础之上,以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中庸》首章的诠释为主,对其《中庸》心性学进行的一些基本分析。
一、“中”之诸义
《读四书大全说》的中庸部分涉及到《四书大全》中的《中庸章句序》、《读中庸法》、《中庸章句大全》、《中庸或问》,我们的关注则集中于船山围绕《中庸》本文、章句、或问的首章讨论所发生的思考,这是因为传统上对中庸的研究无不重视其首章,也是因为“中”、“和”、“道”、“性”、“已发”、“未发”的原始讨论都在此章,心性功夫的讨论多集中于此。
在朱子学的《中庸》解释中,认为“中”字按其在文本中的脉络,可区别为不同的意义,并为此区别也建立了各种不同的对比性表达。如朱子言:“名篇本是取时中之中,然所以能时中者,盖有那未发之中在。所以先说未发之中,然后说君子而时中”[1](第325页)。朱子弟子陈北溪说:“中和之中,是专主未发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义:有在心之中,有在物之中”[1](第325页)。这里就出现了时中之中、未发之中、中和之中、在心之中、在物之中这些不同的概念。
这种分别早在北宋道学已经提及。如伊川对“中庸”的界定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第326页)。与伊川以“不偏不倚”定义中不同,程张门人吕大临则以“无过不及”定义中(注:吕大临说:“圣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则过与不及皆非道也。”但他也说:“不倚不谓中,不杂之谓和。”此处引文见《中庸辑略》,载《四库全书》第1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61、566页。)。朱子后来同时吸收了这两种说法,认为中有两种基本意义,不偏不倚之中是作为心体的中,无过不及之中是作为行为的中,前者是体,后者是用(注:朱子释中之义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见《四书大全》,第325页。)。程门苏季明曾问伊川:“中之道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同否?”伊川曰:“非也,喜怒哀乐未发是言在中之义。只一个中字,用处不同”(注:引自《中庸辑略》,见《四库全书》第198册,第567页。)。此是把“中之道”与“未发之中”加以分别。朱子后来说:“在中是言在里面的道理,未动时恰好处,或发时不偏于喜则偏于怒,不得谓之在中矣”(注:《中庸或问》论名篇之义小注,见《四书大全》,第545页。)。在中就是指这个“中”不是表现于外在行为的中,而指在心性里面而言。
朱子在《中庸或问》中乃说:“中一名而有二义,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说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谓在中之义,未发之前、无所偏倚之名也。无过不及者,程子所谓中之道也,见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盖不偏不倚,犹立而不见四旁,心之体,地之中也。无过不及,犹行而不先不后,理之当,事之中也。故于未发之大本则取不偏不倚之名,于已发而时中,则取无过不及之义,语固各有当也”(注:此答或问者之疑“名篇之义,程子专以不偏为言,吕氏专以无过不及为说,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见《四库大全》,第545页。)。在朱子学的理解中,时中之中是用,是在事之中,是无过不及之中。而未发之中是体,是在心之中,是不偏不倚之中。换言之,时中之中是已发之中,中和之中是未发之中。《大全》引新安陈氏云:“不偏不倚,未发之中,以心说者也,中之体也。无过不及,时中之中,以事论者也,中之用也”[1](第325页)。
在《或问》中朱子藉问者之口曰:“此篇首章先名中和之义,此章乃及中庸之说,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何哉”?朱子云:“中和之中其义虽精,而中庸之中实兼体用;及其所谓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则比之中和,其所该者尤广”[1](第549页)。朱子以为,中庸的中既不仅是未发之中,也不仅是已发之中,而是兼含二种意义。
总结起来,《中庸》作为篇名,此“中庸”一词的“中”即是所谓“中庸之中”;《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此“中”即所谓“未发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此中节之“中”即所谓“在事之中”;“君子而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此“中”即所谓“时中之中”。朱子最后将这些有关“中”的说法都容纳在一个体用系统之中,在这个系统中:“中庸之中”是兼动静体用而言的,它包涵“中和之中”与“时中之中”两方面,在这两方面当中,“中和之中”是体,“时中之中”是用。“中和之中”又可称“未发之中”、“在中之义”、“不偏不倚之中”、“在心之中”;“时中之中”又可称“中节之中(已发之和)”、“中之道”、“无过不及之中”、“在事之中”。就“中”与“和”而言,这里的“中”是指未发之中,“和”则属于已发,故中与和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
二、中和皆体
在接下来的“名篇大旨”中,船山兼取朱子《章句》和《或问》加以讨论,名篇的问题即《礼记》中此篇何以命名为“中庸”,在朱子学传统中,这同时涉及到“中”的概念在《中庸》文本中的不同用法,以及“中”与“和”的概念分别与体用关系,已如上述。船山对《中庸》题名以及“中”之义异议不大,但他着重就中和体用的问题提出异议。
船山认为:“其专以中和之中为体则可,而专以时中之中为用则所未安”[2](第60页)。就是说,朱子学派认为中和之中是体,船山认为是对的;但朱子学认为时中之中是用,船山是不赞成的,他主张时中之中也是体,故说:“但言体,其为必有用者可知(小注:言未发必有发);而但言用,则不足以见体(小注:时中之中,何者为体耶?)。时中之中,非但用也。中,体也;时而措之,然后其为用也。喜怒哀乐之未发,体也;发而皆中节,亦不得谓之非体也。所以然者,喜自有喜之体,怒自有怒之体,哀乐自有哀乐之体;喜而赏,怒而刑,哀而丧,乐而乐,则用也。虽然,赏亦自有赏之体,刑亦自有刑之体,丧亦自有丧之体,乐亦自有乐之体,是亦终不离乎体也。……中皆体也,时措之喜怒哀乐之间而用之于民者,则用也。以此知凡言中者,皆体而非用矣”[2](第60页)。观船山之意,他的第一句话是认为,当我们指称某物为体时,我们会肯定此体必有其用(的一面);可是,当我们指称某物为用时,我们却往往不能确定其是否有体或其体为何,以至会否认此用同时亦是体。从这样的哲学观点来看,船山说“时中之中非但用也”似乎认为朱子学派以时中之中为用的看法,在某一意义上并无不可;但应当承认时中之中也同时是体,也就是说,时中之中既是用,也是体。因此,不仅时中之中是用也是体,其它所有朱子学派认为是用的“中”都同时也是体。可是,照船山后面的说法,他又认为,被朱子学派区别为体用的各种“中”其实都是体,不是用,这就是所谓“中皆体也”、“凡言中者,皆体而非用矣”。看来船山的说法不严格,应当加一“但”字,他应该说“凡言中者皆体,非但用也”。
船山又说:“未发者未有用,而已发者固然其有体。则中和之和,统乎一中以有体,不但中为体而和非体也。时中之中,兼和为言。和固为体,时中之中不但为用也明矣”[2](第60页)。第一句说“未发者未有用”,即中尚未发为用,但未发必有发,不必担心未发作为体而没有用。这与上面一段开始所说一致。最后一句“时中之中不但为用”,也就是上面说过的“时中之中非但用也”。值得分析的是中间几句,船山说“已发者固然其有体”,但朱子学派也认为已发有体,体即未发,未发之中是已发之和的体,已发之和是未发之中的用。船山显然与朱子的想法不同,船山的主张是“和”也(就)是体,因此,那些传统朱子学规定为已发的范畴,如表示情感合度的“中和之和”,与表示行为合度的“时中之中”,船山认为都是体。可见船山所说的“有体”不是另外有一个某物作为和的体,“固然其有体”与“统乎一中以有体”都是指自己即是体,所以他不赞成未发之中是体、中和之和非体的说法。
可见,在船山的看法里,不仅被朱子归于“体”的一系列范畴(如“中和之中”、“未发之中”、“在中之义”、“不偏不倚之中”、“在心之中”)是体,被朱子归于“用”的一系列范畴(“时中之中”“中节之中”“已发之和”、“中之道”、“无过不及之中”、“在事之中”)也是体。简言之,比起朱子,船山更强调已发为体、和即是体、时中即体(注:以《四书训义》及《正蒙注》观之,船山晚年似不再用“时中为体、和亦是体”之说。)。
不过,这样一来,也显示出船山的体用观念与朱子的体用观念不同。朱子是以内在之根据为体,以外发之表现为用。而就此处所说,船山则规定凡可以被措之于民的东西都是体,措之于民用的实践则是用。因此,喜怒未发是体,喜怒发而中节也是体。为什么说喜怒发而中节也是体呢?因为,在船山看来,喜有喜之体,怒有怒之体,观船山之意,是以自体为体,即喜的情感本身便是喜的体,怒的情感本身便是怒的体,而把喜怒措之于政治实践,这是用。所以就未发可以发为已发而言,未发是体;就已发的喜怒情感可以发为刑赏之实践而言,喜怒亦是体。可见船山是在一个“发”的系列中来确定体用的:如果甲可发为乙,则甲为体;如果乙又可以发为丙,则乙亦为体(注:根据此理,如果甲可发为乙,则甲为体,乙即用;而乙又可发为丙,则此时乙为体,而丙为用。但船山为突出对朱子代辩论,故未将此理清楚说明。)。如此类推,而此中的“发”可以具有多种意义。
以上是就上引船山对朱子的体用说的异议而作的分析。以下再就首章中船山的其它的体用讨论进一步加以分析。船山说:“中无往而不为体。未发而不偏不倚,全体之体,犹人四体而共名为一体也。发而无过不及,犹人四体而各名一体也,固不得以分而效之为用者之为非体也”[2](第61页)。这里的辩论有些特异。第一句“中无往而不为体”即上面所说的“中皆为体”,不必再论。未发之中是体,已发之中也是体,这也是前面讲过的。比较特别的是这里提出,未发之中的体,与已发之中的体,可视为全体和分体之别。这是什么意思呢?自然,从全体和部分的方面看,未发是喜怒哀乐一切情感之未发,而已发则不可能七情同时发作,或喜或怒,只是一部分的感情表现出来。但已发与未发毕竟层次不同,船山的这种比喻既不能证明已发与未发是同一层次上的全体和部分间的关系,也不能说明何以发而无过不及也是“体”(与用相对)。
船山又说:“以实求之,中者体也,庸者用也。未发之中,不偏不倚以为体;而君子之存养乃至圣人之敦化,胥用也。已发之中,无过不及以为体;而君子之省察乃至圣人之川流,胥用也”[2](第61页)。这是说,“未发之中”以不偏不倚为规定,是体;而由未发之中引发出来的存养实践,是用。“已发之中”以无过不及为规定,而由已发之中引发出来的省察实践,是用。可见,船山以来,有关《中庸》所提出的各种“中”,都是体,而每一“中”所引发、所对应、所见诸的实践都是用。比如,在朱子学传统中的规定,与未发相对应的修养是“存养”,与已发相对应的修养是“省察”,船山认为存养是“未发之中”对应的用,省察是“已发之中”对应的用。在这个意义上的体用观念与朱子所讲的中和体用的体用观念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船山的这种讲法其实并不见得构成对朱子的真正批评。这里也可以看出,船山的讨论中其实也是接受了朱子学很多的假设和规定的。
船山接着说:“未发未有用,而君子则自有其不显笃恭之用。已发既成乎用,而天理则固有其察上察下之体。中为体,故曰建中,曰执中,曰时中,曰用中;浑然在中者,大而万理万化在焉,小而一事一物亦莫不在焉。庸为用,则中之流行于喜怒哀乐之中,为之节文,为之等杀,皆庸也”[2](第61页)。未发是体,此状态下体未发为用,但与未发相对应的存养功夫就是君子之用,在这个意义上,未发不待发作而亦有其用。已发是用,用之中似不见体,但已发的省察功夫达到的中节就是体。因此,中作为体,可以说无处不在。在用的问题上船山似乎有矛盾,因为他在前面说过,“中皆体也,时措之喜怒哀乐之间而用之于民,则用也”,这是用。而这里说,中之体流行于喜怒哀乐之中,为之节文,皆用也。问题是中之体流行于喜怒为之节文,如果这便是喜怒之中节,而船山前面曾主张中节之中也是体,怎么在这里说为用了呢?也许,这里的节文等杀应当解释为礼的实践,也就是说中之体流行于喜怒哀乐而发为礼的实践,这是用。
《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性、道、教三者的关系上,船山说:“性、道,中也;教,庸也。‘修道之谓教’,是庸皆用中而用乎体。用中为庸而即以体为用”。他认为性与道是中,也就是体;而教是从性、道发出的实践,所以是用。他更在一般意义上面提出,用就是“用中”、“用乎体”,也叫做“以体为用”。可见,船山所说的用,是指对于体的运用、实践。所以他还说:“夫手足体也,持行用也。浅而言之,可云但言手足而未有持行之用;其可云方在持行,手足遂名为用而不名为体乎?夫唯中之为义专就体而言,而中之为用,则不得不以庸字显之”[2](第62页)。以手足为体,持行为用,合于上面所说的船山的体用观(注:船山此种体用观,以实体与其运用分别体用,又可见其所说:“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以者用也,即用刺阴阳五行之体也。犹言人以目视,以耳听,以手持,以足行,以心思也。”见《读四书大全说》,第69页。)。照此种体用观,船山以为,当手足未动,未有持行之用时,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说手足是体。同理,未发之中未发为用时,不妨碍我们说未发是体。但当手足在持行时,难道手足就只是用而不是体了吗?以此推之,当已发之时,难道时中之中就只是用而不是体了吗?这也就是船山在前面反复强调的“未发者未有用,而已发者固然其有体”(注:关于船山的体用论,此节所说皆就中庸首章而言,其所涉及者非本体论。涉及本体论的体用论,可参看曾昭旭的分析:“个体非是形上本体所作用的对象(若然则体用分为两截矣),而直是本体之一端而可直通于全体者。于是个体乃真亦有其超越无限之尊严,且直是就其有限之存在而立其无限尊严。……于是个体亦可直称为体。”其又云:“本体之现端为一一定体,……而一一定体又全具本体之创造性而亦起用者,非一一僵死之物也。……总之是两体回环相抱。”见《王船山哲学》,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第345、347页。)。
船山强调用,他说:“《中庸》一部书,大纲在用上说。即有言体者,亦用之体也。乃至言天,亦言天之用;即言天体,亦天用之体。大率圣贤言天,必不舍用,与后儒所谓‘太虚’者不同。若未有用之体,则不可言‘诚者天之道’矣。舍此化育流行之外,别问窅窅空空之太虚,虽未有妄,而亦无所谓诚”(注:《王船山哲学》,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第138页。按船山此处对横渠太虚说尚有微辞,值得注意,然其晚年则归本横渠之学。)。“用之体”即上面所说“用乎体”“以体为用”,总之不离用言体,船山甚至认为《中庸》主要是讲用,讲实践。这些思想可以看作其诠释《中庸》首章中和体用说的天道论基础。
三、未发为性
现在来讨论关于“未发”的问题。自宋代道学程伊川与其门人讨论《中庸》“未发”之义以后,经过杨时、李侗至朱子,“未发之义”成为道学中庸诠释的焦点。船山面对朱子学派的诠释传统,也承认“未发”问题的意义和重要性。他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儒者第一难透底关。此不可以私智索,而亦不可执前人之一言遂谓其然”[2](第79页)。这既可见其受到朱子学的影响,也显示出船山强调独立思考的性格。
船山反对以未发之心为中。他说:“今详诸大儒之言,为同为异,盖不一矣。其说之必不可从者,则谓但未喜未怒未哀未乐而即谓之中也。夫喜怒哀乐之发,必因乎可喜可怒可哀可乐,乃天人终日之间,其值夫无可喜乐、无可哀怒之境,而因以不喜不怒不哀不乐者多矣,此其皆谓之中乎”[2](第79页)?这是说喜怒哀乐的感情是由可喜怒哀乐之事所引起,而人在生活中多处于没有可喜怒哀乐之事刺激的状态,故人的内心状态,大多数时间中是属于不喜不怒不哀不乐的状态,可是我们能说这些不喜不怒不哀不乐的状态都是《中庸》看作为“天下之大本”的“中”吗?船山断然表示他不赞成把这些不喜不怒的状态都视为中的看法。这种对朱子学未发论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这样的看法在船山以前如阳明学中也提出过。另外,船山在这里并未说明其理据,比如,假设船山认为不喜不怒时仍有意念,故不得为中,则自伊川起,至朱子,已经将所谓“未发”规定为“思虑未萌”。
船山又在概念上提出“中”与“空”的问题,中非是空,不可以空证中;中不是无善无恶,无善无恶不可谓之中:“夫中者,以不偏不倚而言也,今曰但不为恶而已固无偏倚,则虽不可名之为偏倚,而亦何所据以为不偏不倚哉?如一室之中空虚无物,以无物故,则亦无有偏倚者。乃既无物矣,抑将何者不偏不倚耶?必置一物于中庭,而后可谓之不偏于东西,不倚于楹壁。审此,则但无恶而固无善,但莫之偏而固无不偏,但莫之倚而固无不倚,必不可谓之中,审矣”[2](第80页)。船山认为“无所偏倚”与“不偏不倚”是不同的,不能用无所偏倚证明不偏不倚。朱子本来说过:“喜怒哀乐未发,如处室中,东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于一方,只在中间,所谓中也”[1](第344页)。船山的批评应当主要是表达对朱子此说的不满,但也可以说包涵了对阳明学的批评。
船山又指出:“曰在中者,对在外而言也。曰里面者,对表而言也。缘此上文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而非云‘一念不起’,则明有一喜怒哀乐,而特未发耳。后之所发者,皆全具于内而无缺,是故曰在中。即喜怒哀乐未发之云,而未及释夫‘谓之中’也;若子思之本旨,则谓此在中者‘谓之中’也。……未发之中,体在中而未现,则于己而喻其不偏不倚耳,天下固莫之见也。未发之中,诚也,实有之而不妄也。时中之中,形也,诚则形,而实有者随所着以为体也”[2](第80页)。这是说,中庸所说的未发,并不是指一念未起的意识状态。所谓“后之所发者,皆全具于内而无缺”即指潜在的喜怒哀乐,故未发其实是指喜怒哀乐的内在根源和根据,而一切已发的喜怒哀乐都是此根源的外发和表现。这个隐而未发的根源,船山认为就是二程所说的“在中”。
在这一点上,船山的讨论也显示出存有论的面向。从存有论来说,未发时此中体作为“在中”,内在于心而为体(所谓体在中而未现);已发之后,此中体表现为“时中之中”,随事随物以为体(注:我一向不喜欢用“中体”这类概念,而此处已无可回避。中体即作为本体的中。)。如果用《大学》的讲法,未发是“诚于中”,已发是“形于外”;用《中庸》二十三章“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的讲法,未发之中是“诚”,虽然隐而未发,但实有不妄;时中之中是“诚则形”,是内在实有不妄者形著于外,此时此实有者与物为体,即前所谓“已发之中,无过不及以为体”。所以,从存有论说,“以在天而言,则中之为理,流行而无不在”。
船山进而指出,这个“在中”,即是理,即是性:“盖吾性中固有此必喜必怒必哀必乐之理,以效健顺五常之能,而为情之所由生。则‘浑然在中’者,充塞两间,而不仅供一节之用也,斯以谓之中也”[2](第81页)。“故延平之自为学与其为教,皆于未发之前体验所谓中者。乃其所心得而名之,则亦不过曰性善而已。善者中之实体,而性者未发之藏也。若延平终日危坐以体验之,亦其用力之际,专心致志,以求吾所性之善。其专静有如此尔,非以危坐终日、不起一念为可以存吾中也”[2](第81页)。“不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便唤作中,乃此性之未发为情者,其德中也”[2](第84页)。可见,最终船山认为“中”是性中固有之理,是情之所生的根源与根据,而且这个“中”充塞天地,具有本体的意义。他还称赞李延平,认为延平所谓体验未发之中,即是体验性善,他还肯定“善者中之实体,而性者未发之藏”,意思是善为中的本质,而所谓未发即是指性。所以,不能说不喜不怒就是中,而应当说“中”是性未发为情的德性状态的一种表达。这一来,船山几乎回到了朱子的说法“中为性之德”“中所以状性之德”(注:皆见《四书大全》朱注及小注,第344页。)。
宋儒吕大临主张“中即性也”,伊川批评说:“中即性也’,此语极未安。中也者,所以状性之体段(若谓性有体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又说:“若只以中为性,则中与性不合;子若对以中者性之德,却为近之”(注:皆见《中庸辑略》,《四库全书》第198册,第566页。)。朱子之说即来源于此。又宋儒胡五峰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发展道学的中庸诠释,朱子早年也曾受其影响。而船山的上述讲法,以未发为性,以未发之中为性善,以中为性之德,都合于宋代道学的讲法。
自然,质疑喜怒未发便是中,而把未发归于性,明代王学即已如此。事实上,朱子讲未发有二义,一为心有未发已发,二为性未发情已发,后者可见于《中庸章句》所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1](第343页)。
朱子《中庸或问》亦云“盖天命之性,万理具焉。喜怒哀乐,各有攸当。方其未发,浑然在中,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及其发而皆得其当,无所乖戾,故谓之和。谓之中者,所以状性之德,道之体也;以其天地万物之理无所不该,故曰天下之大本。谓之和者,所以着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所共由,故曰天下之达道”[1](第583页)。可见在未发的问题上,船山的看法与朱子的《中庸》诠释是相近的。
四、戒惧慎独
“慎独”之说,《大学》、《中庸》都有表达。《大学》传文释诚意章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首章:“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我们在讨论船山的《大学》诠释的论文中之所以没有涉及关于“慎独”的问题,意即留待《中庸》中一并加以讨论。
按朱子《大学章句》释“君子必慎其独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者,故必谨于此以审其几焉。……虽幽独之中,而其善恶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也”[1](第80,87页)。可见朱子把“慎独”的“独”解释为“己所独知”的知觉状态和境况(注:按朱子所谓“独知之地”,此“地”字《大全》载新安陈氏曰:“地,即处也。此独字指心所独知而言,非指身所独居而言。”见《四书大全》,第81页。),而以“慎”为谨慎地审察善恶之几。
《中庸》首章第二句有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朱子《中庸章句》释其中慎独之义:“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1](第339页)。朱子在《中庸》中对慎独的解释和其《大学》中所解释是一致的。朱子认为,“戒慎”讲“慎”,“慎独”也讲“慎”,但“不睹不闻”与“独”有别。简言之,“独者,人之所不睹不闻也”;“其所不睹不闻者,己之所不睹不闻也”。就是说,戒慎恐惧的“不睹不闻”是指自己无所闻无所见,也就是“未发”。而“独”是指自己的内心别人无所闻见,别人虽然不睹不闻,但自己的心有自我意识,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种独知已属已发。也因此,朱子将“戒慎”与“慎独”的功夫加以分别,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为未发时的功夫,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为已发时的功夫。
船山在其读《大学》说中提出:“但当未有意时,其将来之善几恶几,不可预为拟制,而务于从容涵养,不可急迫迫地逼教出好意出来,及其意已发而可知之后,不可强为补饰,以涉于小人之揜着,故待己所及知,抑仅己所独知之时而加之慎”[2](第19页)。从这里可以看出船山对慎独的看法。在他看来,“独”即是“己所及知抑仅己所独知之时”。这个说法吸收了朱子之说即人所不知不睹不闻、而己所独知。但“及知”是提出显示船山的提法也包涵有自己的主张。船山之意以为,独属于意,属于意之已发;而且独所代表的意,只是自己刚刚知觉而别人完全不能知觉的意识状态。这个主张,其实就是以“独”指意念之初发将发之几。至于“慎”字,船山认为“慎字不可作防字解,乃缜密详谨之意”[2](第19页)。又说:“若夫慎之云者,临其所事,拣夫不善而执夫善之谓也”[2](第47页)。船山把独解释为意之几,这种对几的强调的讲法应当说是对朱子学慎独说的进一步展开。(注:《四书大全》之《大学章句大全》载新安陈氏发挥朱子说曰:“己所独知,乃念头初萌动,善恶诚伪所由分之几微处,必审察于此”;云峰胡氏云:“独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见《四书大全》,第81、84页。)。
船山认为独是已发,这与朱子相同。但船山明确提出独即意,这就与船山自己心性学重视诚意有关了。船山说:“慎独为诚意扣紧功夫,而非诚意之全恃乎此,及人所共知之后,遂无所用其力也”[1](第20页)。在他看来,从意来说,意之已发分为“己所独知”和“人所共知”两个阶段或部分,诚意是指两个部分全体都要慎之而严,慎独则专指“己所独知”的这前一个部分。故慎独属于诚意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如果把慎独当成诚意功夫的全体,那么在人所共知的阶段就无功夫可言了。
船山说:“《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谓君子自知也,此(《大学》)言‘十目’‘十手’,亦言诚意者之自知其意。如一物于此,十目视之而无所遁,十手指之而无所匿,其为理为欲,显见在中,纤毫不昧,正可以施慎之功”[1](第20页)。这也是说《中庸》的慎独之独是君子自知而他人不知的状态,这个状态属于意,而自知就是自知其意;船山强调这与《大学》讲诚意的自知其意的状态相同。由于独属于意之已发的状态,故船山又指出,这种状态下,自己内心之意念,为理为欲,自己都了然不昧,这种状态正好采用慎独的功夫。
船山说:“《礼记》凡三言慎独,独则意之先几,善恶之未审者也。”明确说明独属于意,是意的“先几”阶段,即意之初发初动初萌,此时意的善恶尚待分辨。船山强调,慎独是诚意功夫的一部分,慎的对象只能是意,而不能是心(注:此处的心指正心之心,有关船山关于正心之心的观念可参看我的《道学视野下的船山心性学:以船山的〈大学〉诠释为中心》一文,《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因为明德之心虚灵不昧,有善无恶,而“慎”的功夫是在善恶混杂之中“拣其不善以孤保其善”[1](第47页)。船山以此来说明何以《大学》传在诚意的部分提出慎独:“传独于诚意言慎者,以意缘事有,以意临事,则亦以心临意也。若夫心固不可言慎矣。是以意在省察,而心唯存养。省察故不可不慎,而存养则无待于慎,以心之未缘物而之于恶也”[2](第47页)。慎独是“拣其不善而执其善”,这属于省察,故慎独属于意之省察,也就是说,慎独是意的省察功夫(注:船山对慎,还有一说法:“慎者,慎之于正而不使有辟也。慎于正而不使有辟者,好恶也,君子以内严于意,而外修其身也。”这是解释《大学》“君子先生乎德”。)。
船山精于易学,往往以易论《中庸》,如:“‘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泰道也;所谓‘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所以配天德也。‘慎其独’,复道也;所谓‘不远复,无祗悔’,‘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所以见天心也”[2](第71页)。船山用泰卦九二爻辞解释《中庸》的戒慎恐惧,未明其意。按传统解释泰九二爻辞,是指用心弘大,包容不遗,但不知船山何以以此比喻戒慎恐惧。按《周易内传》论泰九二爻辞有云“乃不偏倚而尚于中道”[3](第114页),船山或以此喻未发之中的不偏不倚。至于复卦,应当是用“有不善未尝不知”解释“独”,以比喻“独知”。无论如何,这个讲法可以看出船山也是把戒慎恐惧与慎独分开来看的。
朱子《中庸章句》解释戒慎恐惧为:“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不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1](第336页)。船山的解说是:“君子则以方动之际,耳目乘权,而物欲交引;则毫厘未克,而人欲滋长,以卒胜夫天理。乃或虽明知之,犹复为之。故于此尤致其慎焉,然后不欺其素,而存养者乃以向于动而弗失也。“有不善未尝不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之谓也。“知之未尝复为”,慎独之谓也。使非存养之已豫,安能早觉于隐微哉”[2](第74页)?方动之际就是意之先几,意之动则有善有恶,所谓恶即人欲之萌。此时若不能辨别理欲,则人欲将会滋长而最终胜过天理;或者虽独知意动于不善,却仍行之,则成乎不善之行。所以人须在意念方动之际,用“慎”的功夫,使意念不自欺于素正之心(注:船山此处所说的“素”,即其《大学》说所谓“素正之心”,可参看拙文《道学视野下的船山心性学——以船山对〈大学章句大全〉的评论为中心》。)。不过,船山所谓“然后不欺其素,而存养者乃以向于动而弗失也”,此种说法似乎将慎独属“存养”,而不象前面属之“省察”,有不协调处。其实船山是指,存养是未发功夫,是慎独以前功夫;正是由于善作功夫者在意念发动之前有存养的功夫,所以才能在意念方动之际行之以慎独的功夫,使在意念发动的状态得以弗失。如果不是素有未发功夫的存养,就不可能在意念初动时察觉善恶之几。船山认为《易传》“有不善未尝不知”,就是莫见莫显的独知,这是慎独的前提;“知之未尝复为”,就是慎独,亦即慎独的过程及结果。
由此,船山认为《中庸》首章的主旨是:“盖所谓中庸者,天下事物之理而措诸日用者也。若然,则君子亦将于事物求中,而日用自可施行”[2](第65页)。“中”代表天下之理,“庸”是将理措之于日常实践,而“中庸”就是要人在日常事物里面求理。“故中庸一篇,无不缘本乎德而以成乎道,则以中之为德,本天德;而庸之为道,成王道。天德、王道一以贯之,是以天命之性不离乎一动一静之间,而喜怒哀乐之本乎性、见乎情者,可以通天地万物之理。如其不然,则君子之存养为无用,而省察为无体,判然二致,将何以合一而成位育之功哉”[2](第62页)?存养为静中涵养性体功夫,但若无省察,则为无用;省察是动时审察功夫,若无存养为基础,则为无体。
船山又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自知自觉于‘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者之胸中。即此见天理流行,方动不昧,而性中不昧之真体,率之而道在焉,特不能为失性者言尔。则喜怒哀乐之节,粲然具于君子之动几,亦犹夫未发之中,贯彻纯全于至静之地。而特以静则善恶无几,而普遍不差,不以人之邪正为道之有无,天命之所以不息也;动则人事乘权,而昏迷易起,故此待存养之有功,而后知显见之具足,率性之道所以繇不行而不明也。一章首尾,大义微言,相为互发者如此。章句之立义精矣”[2](第45页)。“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出于《礼记》的《孔子闲居》,可理解为欲念未动未起时清醒的意识状态。自知自觉此清醒状态,就是《中庸》所说的莫见莫显的独知,故自知自觉即是独知,独知即自知自觉自审其意念之动的善恶。这个方动而不昧的意识状态,就是天理流行的表现,亦由此可见性之本体。因此这个“独”(动几)可以说是喜怒哀乐发而中节的根源。“未发之中”是发而中节的更深的根源,虽然未发时为静,此时意念未动,善恶无几,但“未发之中”在至静之中恒在不息。此时不能用慎独的功夫,必须用存养;只有经过长久的存养功夫,才能保证人在意念初动时有充足完全的独知去审辨之,而中和的大用才能成立。
所以,船山认为“慎独”是以“存养”为其基础的,“《大学》言慎独,为正心之君子言也。《中庸》言慎独,为存养之君子言也。唯欲正其心,而后人所不及知之地,己固有以知善而知恶。唯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而后隐者知其见,微者知其显。……以明夫未尝有存养之功者,人所不及知之地已固昏然,而莫辨其善恶之所终,则虽欲慎而有所不能也”[2](第73-74页)。即有长久的存养为基础,隐微的独知才能辨知善恶如白日之明显;如果没有日常存养的功夫,所谓独知已昏昏然不能辨善恶,这种状态下“慎”的功夫也就无所用了。船山还主张,慎独在《大学》系统中是指“正心”,慎独在《中庸》系统中是指存养。船山以存养、慎独二分,认为存养是慎独的基础,并认为这个思想就是《中庸》首章的大义,这些都与朱子学的解释一致。船山在其读《中庸》说中,还屡次使用“圣贤心学”、“心学”的概念,这些地方都可见他所受道学心性-功夫论的影响。
五、余论:《笺解》与《训义》
船山作《读四书大全说》之后,又曾作《四书笺解》和《四书训义》,其《四书训义》之成已在其六十岁之后(注:据许冠三《船山学术思想生命年谱》,《四书训义》始作于61岁,以船山作书之速推之,应可在一年中完成。许说参见其《王船山的致知论》,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余论即略论此二书关于《中庸》首章的解说。
《四书笺解》云:“修道者不可但于事为上求合于道,必静存以体天理不息之诚,动察以谨天理流行之机也”[4](第124页)。这是明确指出,《中庸》所谓“修道”并不是只要人们达到时中之中(在事之中),而是强调静存动察的修养功夫。其中天理不息及流行的说法,与前述《读四书大全说》的“静则善恶无几,天命之所以不息也”、“自知自觉于,即此见天理流行,方动不昧,”(原文稍长,以上二句是概引)相近,也与“未发之中,不偏不倚以为体;而君子之存养乃至圣人之敦化,胥用也。已发之中,无过不及以为体;而君子之省察乃至圣人之川流,胥用也”是一致的。
前引读书说中有云“未发之中,体在中而未现,则于己而喻其不偏不倚耳,天下固莫之见也。”《四书笺解》云“性不因形声之有无而不存于心也”[4](第126页),可谓前者的注脚。前节曾引船山说:“唯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而后隐者知其见,微者知其显”,《四书笺解》有云“见显只是是非分明”[4](第126页),以此可以解释前句为:只有戒慎恐惧于不睹不闻作为基础,独知时才能是非分明。可见《四书笺解》的一些疏释对读书说是有益的补充。
关于《中庸》首章喜怒哀乐一段,《四书笺解》谈到中和的区分:“盖言此性之存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者,则所谓中也;此性之发而为情,能皆中节者,则所谓和也”[4](第127页)。又云:“喜怒哀乐二节,言性情本有中和之德,以具众理应万事,故能存养省察以致之,则其功效有周徧乎天地万物之大用也”[4](第126页)。这是说,中与和是指性与情而言,而性情皆统于心(心统性情);心具中和之德以应万事,所以能由存养以致中,由省察以致和;人的致中和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成就,还可以促进宇宙的和谐发育。
《四书笺解》也提到“未发”与“不睹不闻”的区别,他说:“喜怒哀乐之未发,与不睹不闻不同。不睹不闻以事物未接言,未发以己之所以应物者未出而加一物言。彼所言者,道之常存于心;此所言者,德之可被于物也”[4](第127页)。我们记得,朱子认为“其所不睹不闻者,己之所不睹不闻也”。船山把不睹不闻解释为事物未接于己(故对物无所睹闻),这与朱子一致,与读书说有所不同。至于以“未发以己之所以应物者未出而加一物言”解未发,是说自己并未发出以加被于物。最后两句如果用以解说“不睹不闻”与“未发”的区别,更不如用来解说“中”与“和”的区别,即未发之“中”是指道之常存于心,已发之“和”是指德之可被于物。船山在这里的解释似不周全。
《四书训义》全录朱子章句集注,而在每章后以“训义”为题,综合阐述船山对此章的解说,层次递进而成系统。这与读书说随句落笔,处处加评,即每章之义亦散漫不明的特点不同(注:曾昭旭谓“船山书大率为注疏体,往往随文衍义,因几立说;由是精义散见,漫无所统”,参看其《王船山的哲学》,第3页。另需指出,《四书笺解》与《四书训义》似兼为学子应举用,与《读四书大全说》形成、整理自己思想的札记不同。《四书笺解》、《四书训义》对朱子批评甚少,这也可能是个原因,但船山晚年思想越来越趋向道学,应是事实。)。
《四书训义》对《中庸》首章宗旨的理解是:圣人之学,以性善论为基础,而充分力行存养和省察的功夫;存养以治内,省察以发外,内外合一之德称为中庸。道出于人性,人性出于天,天以理气化生万物的过程为天道;气生万物,人为最灵,形具而理在其中;人心能知此理,人力能行此理,故人对此理的知觉认识与实践展开即是人道。“是人道者,即天分其一真无妄之天道以授之,而成乎所生之性者也”,船山用一“分”字,以说明人道的根源来自天道,而人道的使命就是完成人性。
关于首章的心性功夫,船山说:“是故君子之体道也,有所不睹者焉,形未着也,而性中之藏,天下之形悉在焉。君子于此而致其戒慎,所炯然内见者,万善之成象具在,不使有不善之形无故而妄为发见也。有所不闻者焉,声未起也,而性中之藏,天下之声悉在焉。君子于此而致其恐惧,所井然内闻者,万善之名言咸在,不使有不善之声无端而妄相荧惑也。养其纯一于善成无杂之心体,然后虽声色杂役,而吾心之宁一有主者自若。斯乃以体天理于不息之常,而无须臾之离矣。此其静而存养者如此,盖以天与性不离于静中,而以此体天道而合道也”[5](第106页)。这是对于“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而加以解说。睹对形而言,闻对声而言,不睹不闻是指君子没有知觉到事物的形象,但此时事物的形象已经具备于人之性中。因此,君子在此时加戒慎恐惧的功夫,可以内见万善。何为内见万善,船山语焉未详,内见既为“见”,与睹的区别何在?而内闻者,则似乎已非未发。无论如何,船山认为静时要用此戒慎恐惧的存养功夫,以帮助养成纯善无杂的心体,这个心体在有睹有闻时可以成为心的主宰。这个功夫属于静而存养,即意念未动时加以涵养。
关于慎独,《四书训义》说:“及其一念之动也,是天理之所发见也,而人欲亦于此而乘之;是吾性之见端也,而情亦于此而感焉。君子既常存养,以灼见此理于未动之先矣,则念之所发,或善或恶,有自知之审者。故其动也,在幽隐之际,未尝有是非之昭著也,而所趋之途自此而大分,莫见于此矣。其动也,亦起念之微,未尝有得失之大辨也。故君子知此人所不及知、己所独知之际为体道之枢机,而必慎焉,使几微之念必一如其静存所见之性天,而纯一于善焉。其动而省察又如此,盖以天与性昭见于动时,而以此尽道以事天也”[5](第107页)。船山此前多次用“动则人事乘权”“方动之际,耳目乘权”的说法,而在《四书训义》明确指出,“人欲乘权”是以“天理发见”为前提的。据船山看来,当人心由静转为动,必是因为一念之动,一念之动的原发之几,是天理发见,也是性的表现;人欲此时要乘天理发见之机而起来,于是情就发生了。在起念之微的时候,君子由于有静养的功夫作为基础,所以即使善恶分别很细微,但也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起念之微的内在变化,是人所不及知,而只有自己所独知,君子必须在此时用慎独的功夫,使得意念在几微之时便能一如静养之善。这个功夫属于“动而省察”,即意念发动而加以省察的功夫。
最后船山说:“惟吾性之为静为动皆涵天下之理,而道为体为用皆不离乎性情。……君子以其戒慎恐惧者存养于至静之中,而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人以为虚而无物者,君子以为实而可守;则存养之熟,而无一刻之不涵万理于一原,则心之正也,无有不正者矣。君子以慎独省察于方动之顷,而喜怒哀乐固然之节,存之于未起念之前而不紊者,达之于既起念之后而不违;则省察之密,而无一念之不通群情以各得,则气之顺也,无有不顺焉”[5](第108页)。这是说,静而未发之际,以戒慎来存养,这也是《大学》正心的功夫。动而起念之际,以慎独来省察,其效用可通被于群物。以“气顺”说致中和的效验,本于朱子《章句》和《或问》。
《四书训义》在《中庸》首章之末照录了朱子《章句》的首章结语:“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5](第109页)。船山照录这些讲法,表明他与道学如朱子学派的中庸解释基本一致,明显表示出船山的儒家立场和其所接受的道学影响,也证明船山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的确应作为整个宋明道学运动的一个部分(注:不过,照今本《船山全书》的《四书训义》字行之排,其中之《中庸》每章之末,船山都照录了朱子《章句》此章的结语;但船山本意是否如此,我觉得有些可疑。而《船山全书》的标点者对此似皆未觉察。也许朱子《章句》每章的结语不应列入“训义”之中,而与其他朱注皆以大字排出(今印《船山全书》朱注与训义字号同)。因未见船山原稿钞本,暂记于此。)。
考察船山《中庸》首章的诠释的结论,如同我们对他的《大学》说的分析的结论一样,即船山的《中庸》诠释是“接着”朱子学的诠释讲的,无论从话语、概念、问题意识乃至主要的功夫理论和立场,船山的思想、诠释都受到了朱子学的重要影响。同时,如在中和体用等问题上面,船山也提出了独特的看法,表现出他力图把道学的心性意义的实践扩展为包括政治、社会实践在内的一般实践,而这一立场反映了明清之际儒家学者的积极反思。
收稿日期:2002-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