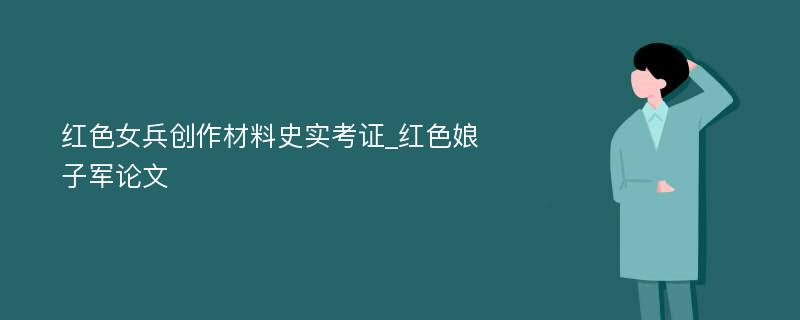
“红色娘子军”创作素材之史实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素材论文,红色娘子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红色娘子军”创作论争①过程中,报告文学作者刘文韶、电影文学作者梁信和琼剧编剧吴之分别对“红色娘子军”创作史料来源作了如下叙述:
有一天,我在翻阅一本油印的关于琼崖纵队战史的小册子时,偶然发现有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二十人。”全书仅有这一句话,其他再没什么别的内容记载②。
剧本所写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二师直属娘子军连”的历史,它以海南军区编写的《琼崖纵队军史》(初稿)为凭据。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完成初稿,一九五九年定稿发表于《上海文学》,一九六○年影片摄制工作最后完成,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全国首映③。
1958年,在准备庆祝建国10周年时,上级领导组织文艺界的人来搞创作,我就开始写琼剧《红色娘子军》。我曾在1954年写过琼崖纵队发展史,当时叫军史。后来据此创作出的琼剧《红色娘子军》④。
目前还没有材料能够考证出,记载“琼崖纵队发展”的史书系同一所指,但仍然可以初步确定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和琼剧剧本的书面叙事根据是“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女兵连”的相关记载。鉴于此点,本文定位于“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女兵连”史实考证,并不涉及“红色娘子军”其他创作素材研究⑤。
前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作战记录是这样描述1930年代的海南社会状况⑥:“琼崖社会早受资本帝国主义力量侵入,致城市洋货充斥,物价高涨,生活程度提高,因之农村生活亦受影响而高涨,使农村再不能自足自给,而日见破产崩溃。”“琼崖之经济状况从现时社会情形上观察,已陷于山穷水尽之境。”“而农村方面之农产品,除若干副产物或特产物可盈余运销外洋外,此琼崖之所以缺少构成经济之条件,而经济命脉寓于国外资本主义血搏之中者,其理明甚。”⑦洋货的充斥所造成自给自足经济的破产给当时社会增添了更多的动荡,岛内的海南人开始外出寻求各类生存机会。“故琼崖之人民,多因农村不能谋生,而纷移至南洋工商业发达之资本主义之殖民地,以图出卖劳力,易得酬资。”⑧不过,靠“闯南洋”(东南亚)赚钱的大多是些男人,而妇女大多留在家中支撑家业、养老携幼。男人们有了“衣锦还乡才能荣归故里”的理想之后,如果没有赚到足够多的钱,他们是不会轻易回家的,即便是回家那也犹如探亲之旅。在“出卖劳力,易得酬资”的海南人中,能够发财的毕竟是少数,因此他们不得不长年累月在外游荡,妇女则只能在家中盼望早日结束“守活寡”的日子。当然,“闯南洋”也有可能遭遇不测而客死他乡,如果这样的话,女人就要真正一辈子“守活寡”了。1930年代的海南,人们常常认为“守活寡”是“美德”,如果女人要主动提出改嫁,她们就会遭到公婆的反对以及社会群众的非议,总之像“改嫁”这样的行为好像不大受欢迎。电影《红色娘子军》中那个抱着木头“守活寡”的红莲形象,虽然说是虚构的,但绝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不过,善良而又勤劳的海南妇女⑨,她们的美德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好运:不少脱贫致富的男人很快在当地重新组建家庭。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态度大多是忍让顺从。海南文昌一位名叫邢增仪的女作家,她的一篇纪实性散文《文昌阿婆》就有这些一段描述:“我奶奶也是一个留守阿婆,她从怀上我父亲时就开始守活寡,同时固执地认为爷爷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而这一等就是50年——人的一生有多少个50年啊?爷爷在南洋活得很滋润,先后一娶再娶。在他七八十岁要落叶归根时才突然想起,哦,在海南文昌还有个结发妻子……”⑩
如果遇上婆媳关系紧张或邻里关系不和,妇女的生存境况就会更糟糕。《红色娘子军写真》书中是如下表述一名叫王运梅的女性从军原因:“参加娘子军之前,她曾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邻村的×××(名隐去)结婚。婚后一年,生了个女儿。在当时海南‘重男轻女’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她不仅遭公婆的白眼,还受丈夫的打骂。”(11)除此之外,该书还这样表述过1930年代海南女性的生活状态:“尤其是琼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一带的妇女,除了受‘四权’的枷锁束缚外,还受着公婆的打骂、丈夫离弃的痛苦,且要担负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她们在社会上受歧视,没有财产继承权,没有起名字的权利。”(12)
对海南社会状貌有所熟悉,并认真阅读1930年代海南妇女生活的相关记载,我们就可以发现:家庭冲突而不是阶级矛盾构成了女子从军最直接的原因。前工农红军琼崖独立二师师长冯白驹(13)在“文革”时期写的“反省”材料对“娘子军”有过这样一段介绍:“有些比男同志还坚强,丈夫反动作恶多端的,妻子带领革命同志去惩办;甚至丈夫熟睡时自己用刀子扎死丈夫,逃出来参加革命……”(14)从话语表述中隐约透露出当时社会的男女冲突。既然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至少一部分女性是由于家庭问题而投奔革命,这样的推论甚至可以在一份新华总社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内参寻找到佐证:“海南岛妇女参加革命的人,一般都是和家庭不和才出来参加革命的。”(15)
根据冯白驹在“文革”时期写的“反省”材料,“女子军”成立的时间是“一九三○年下半年”(16)这个时间可能有误。
1931年3月26日,适值全琼工农兵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乐会、万宁两县交界的加荣村举行闭幕式。在闭幕式上,乐会县赤色女子军连宣告成立。赤色女子军连仅有一排人数。连长是庞琼花,指导员是王玉文。(17)……1931年5月1日上午,红三团和乐会县苏维埃政府联合在乐会四区赤赤乡内园村的练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成立(18)。
1931年3月底,在六连岭下、万泉河边各乡村,张贴布告号召广大青年妇女参加红军,准备成立女子军特务连。(19)……1931年5月1日,就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当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地址在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今琼海市文市乡内园村)红色操场上(20)。
根据以上两份材料,可以确定“女子军特务连”正式成立时间应该是1931年5月1日,因为两份材料叙述无差异。至于在“女子军特务连”在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乐会县赤色女子军”“不属正规红军连队建制,是乐会县委和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的地方武装组织”。不过,就“女子军特务连”成立时的编制与总人数就存在一些分歧:
连以下编制实行三三制:全连编制三个排,每排编制3个班;每个班10名战士编制,全连各排编制共90名战士。连领导职数2人、指导员各1人,不设副职领导。连部工作人员编制8人,即传令兵、旗兵、号兵、庶务员、挑夫各1人,膳食员3人。全连指导员编制共100人。除了庶务员、挑夫、号兵3人为男同志外,其余的都是女同志。女子军特务连的排干部,一排长是冯增敏,二排长是庞学莲,三排长是黄敦英(21)。
经过严格的审查挑选,批准了90多名18至22岁的妇女参军。乐会县委调在共青团团委工作的庞琼花,任连长,特委派妇委主任王时香任指导员,全连103人。除了13岁的号兵符明,30岁的李××庶务长,30多岁的陈××运输员为男性外,全部是女兵。分三个排,一排长冯增敏,二排长庞学莲、三排长黄敦英(22)。
上述材料无法确定“女子军特务连”在成立时人数究竟是一百人还是一百零三人,但可以确定部队的编制及干部任命情况:“女子军特务连”隶属于“第二独立师第三团”(23),全连编制三个排,每排编制三个班;庞琼花任连长,王时香任指导员,冯增敏、庞学莲、黄敦英分别担任各排排长。成立之初的“女子军特务连”隶属于“第二独立师第三团”。1932年春“女子军特务连”的隶属发生了变化,原“女子军特务连”第一排和第三排调到师部驻地组建“第一团女子特务连第一连”;原“女子军特务连”第二排在新增一个排的基础上重建“第三团女子特务连第二连”(24)。
写标语、宣传、演出以及做群众工作应该是“女子军特务连”从事的主要工作,这一点在不同的“红色娘子军”史实记载中,并无多大出入,但在具体事件描述上则有不同,在《红色娘子军史》是这样表述的:“她们经常与农民一起劳动,农忙时帮助干农活,如犁田、插秧和割稻等。他们还在驻地办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读书。”(25)但在《红色娘子军写真》的表述就成了:“有时候,女兵们还要提着一桶桶石灰水,到村庄的墙上写标语。这就难住了娘子军的姑娘们了,因为连里只有王时香指导员识字。她便抓紧夜间教大家识字写字,每夜专教写一条标语。最难的是‘清匪反霸,土地还家’这条。‘霸’字最难写,但她们就用了几天时间,专门攻写这个‘霸’字。”(26)二者在评估“女子军特务连”的文化程度就存在相当差异。结合1930年代海南“重男轻女”观念,笔者认为后者更为可信,很可能是“女子军特务连”为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参加了“夜校”,而不是“办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读书。”
至于《红色娘子军史》、《红色娘子军写真》和《琼崖纵队史(送审稿)》等详尽叙述的“女子军特务连”从事的作战任务,笔者认为绝大多数应该属于协助而不是独立作战。如果要说“女子军特务连”在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也应该是就妇女参军的宣传效应与精神力量而言,理由如下:1、从人数上讲,“女子军特务连”在鼎盛时期,其编制人数应≤150人(27),且150人分别由红一团和红三团所辖,仅就“女子军特务连”而言绝对构不成这些书上所描述的战斗力;2、战争必然会导致人员伤亡,特别是在当时“女子军特务连”装备极其简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笔者查看死亡者名单时发现:“女子军特务连”十七位死难者中,有十名是在“马鞍岭殿后战”(28)中遇难,二名是被捕后被杀,只有为数不多的五名是在其他战斗中死亡;3、“女子军特务连”反复讲述并引以为骄傲的战役大多是协助战,如女兵协助红三团在一个叫沙帽岭的地方伏击了陈贵苑的民团武装,以及配合红三团通过佯攻加挖地道的方式火烧了文市炮楼。据说在一个叫文魁岭的地方女兵拼命还击了王兴志带领的民团武装发起的攻击,但女兵在这次还击中并无死亡案例,也就让人怀疑王兴志等人是否真有发起攻击的决心;4、原“女子军特务连”连干部的回忆,也无意中证明了笔者的这种假设。“女子军连的任务,主要是在苏维埃政府驻地放哨、看守犯人,到各个村庄宣传,多数在后方活动。”(29)
1932年春末改组形成的“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还执行了一项看守“犯人”的特殊任务。这些“犯人”除了“革命”的对象如地主、富农和当地官员之外,大多数从红三团内部“肃反”出来被称之为“AB团”“社会民主党”和“托派”的成员。“肃反”造成了革命内部的重大人员伤亡。“仅在丁狗园、狗埠大园、六盘园三个地方,被冤杀的革命者就达300多人。有一天竟有36人被杀死,埋在一个大坑内。全县被错杀的不下600人。”(30)甚至“女子军特务连”原连长庞琼花也成了“肃反”对象,她被隔离审问并投入监狱,不过她并没有被枪毙,成为为数不多的“肃反”幸存者之一(31)。没有证据表明“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执行了除看守任务之外的其他“肃反”任务,比如说枪毙“犯人”。作为女人,她们对“犯人”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据说她们是“边看守‘犯人’边流泪”,并秘密地向师部报告了这些“恶行”(32)。
1932年7月下旬,陈济棠派警卫旅旅长陈汉光率三个团一个特务营从海口港和澄迈东水港登陆,随后根据详尽确切的情报制定了严密的围剿红军计划。8月2日(33)凌晨,陈汉光带炮兵排亲自督战,兵分三路向独立师部(今琼海市烟塘镇平坦村)发起进攻。陈汉光部人数众多且武器精良,琼崖红军方面死伤甚多仍然不足以抵挡住陈汉光所率部队的猛烈进攻。至下午1时平坦村四面防守阵地均被击破,红一团只得借莽莽丛林撤退。8月5日至乌榄湾与合水湾一带,又遭到猛烈攻击。独立师师部只得继续向牛荫岭撤退,留下少数人员在马鞍岭构筑工事掩护,其中包括“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二班的八名战士(34),她们后来全部阵亡(这应该是“女子军特务连”自成立至解散过程最残酷的战斗)。连长冯增敏说她当天晚上从牛庵岭返回过马鞍岭战场,看到女兵们“个个身上沾满血迹,衣服被撕得稀烂”。(35)由于主力部队在战役中不断失利,师部在抵达母瑞山后便被逐步包围,不断受到围剿。完全可以想象在撤退过程跟随师部的那些女兵,她们的生活条件是何等艰苦。冯白驹后来在回忆录是这样回忆当年在母瑞山的生活情况的:“我们干部和武装同志一起,除身上一支枪和穿的一套衣服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吃的是地瓜和革命菜(是山上一种野生的东西,用清水煮起来,还可以吃,故我们把它命名叫革命菜),冬天季节,山上也非常寒冷,我们用香蕉叶做草席来睡,盖的也是香蕉叶,一年多一点时间,没有吃过一粒米,油、盐、肉等更不要说了。”(36)在电影《红色娘子军》的叙述中,她们在撤退过程中打了一场胜仗,而历史上的“女子军特务连”在当时的情况下完成一次成功狙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陈济棠等人编写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琼崖剿匪记》记载,警卫旅作战消耗最多的是进口机枪子弹(含轻机关枪和重机关枪),其次是驳壳枪、迫击炮和手榴弹;相比之下,记载所缴获的红军武器几乎全是步枪,并且品种繁多,但最多的是土制七九步枪,机关枪则是少得可怜的一挺。
在粮弹均缺和人员伤亡不断的情况下,政委冯国卿身亡,师长王文宇被俘。“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有相当一部分大员被冲散。“女子军特务连”的解体,有报道为“在大革命连连受挫时,为保存革命实力,红色娘子军连奉上级命令解散了。”(37)但诸如此类说法遭到了驳斥(38)。不管采用何种版本的说法,原“女子军特务连”的女兵们大多被俘。最先被捕也是最富戏剧性的当属原连长庞琼花,“她在当时被停职审查,与几百名受嫌疑的红军官兵一起,被关进设在母瑞山深处的红军监狱。名曰审查,其实是监督劳动。8月上旬,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兵临山下,他们才被宣布‘无罪释放’,予以遣散,从而走出自己人建造的牢房。由于红军队伍不收留,庞琼花打算回老家乐会四区岭下欧宅园村。但是还没有离开母瑞山境,她就被捕了。她后脚刚迈出共产党的监狱,前脚又被拖进了国民党的监狱。”(39)庞琼花、冯增敏、黄敦英、庞学莲等人被关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狱接受审讯,至少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被当做反面教材带到各地参加群众大会。在《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琼崖剿匪记》记载:“旅长均许改过自新,带赴各区开会,说明女子从匪之痛苦及绝望,听者信之,此种宣传,收效甚巨。”(40)据《红色娘子军史》所言,1933年底,她们被转移至府城监狱,1934年又被解押到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在感化院期间她们被要求诵读“总理遗嘱”,下地种菜或到生产毛巾等生活日用品的小工厂干活(41)。据说她们在狱中进行了抗争“放声臭骂国民党与陈汉光”、“砸坏了监房的木质工字窗”、“打碎了狱中用具陶瓷器皿”(42)。1937年12月底被关押的“女子军特务连”成员被释放(43)。从感化院释放的“女子军特务连”成员大多是重返故里,开始像她们的母亲那样嫁人生子,并主持家业。或许这是她们年轻时反抗的,至少也应该是不情愿顺从的道路,现在却不得不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具有典型意味的可能是原“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的指导员庞学莲,她是在从母瑞山突围的过程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出于被抓捕的恐惧,在他人的撮合下她很快嫁了当地一个牙医(44)。可能由于有人告密,婚后一个月“清乡队”来人把她抓走。她先后被关到阳江和府城监狱,最后送往感化院。从感化院回来的时候,她的丈夫已经另娶了一位妻子,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庞学莲出于无奈接受了这个事实(45),重新与丈夫一起过日子。在这个“一夫二妻”的家庭里,庞学莲生下了三个男孩,据说与丈夫相处得还不错。在一些历史记叙中,庞学莲与丈夫能够和睦相处是多么值得欣慰,但这通常会让那些善于思考的读者提出尖锐的质疑:如果有更多或更好的机会,庞学莲会不会并且应不应该选择其他的机会?在各类的史实记载中,都没有人提及过这个“一夫二妻”家庭中另外一个女人的感受,“如鱼在水”的感受恐怕只有这个女人自己才能体会到,要么,这可能是研究者应该避讳言及的。
前面提及的原“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从感化院回来后嫁给了乐会县国民政府一名叫王汉文的文书。与庞琼花同乡同宗的庞学莲说:“我也不知她怎么想的。当初父母为她选‘番客’,她都抗命,现在却嫁给人做二房……”(46)如果庞学莲想想自己不也是接受了“一夫二妻”残酷现实,她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在当时理想破灭的情况下,选择了活下去也同样是需要点勇气。日本占领阳江后,王汉文与庞琼花不愿到维持会任伪职,到会山区三洲乡加毫园的山上过隐居生活,日伪军队包围了加毫园,打死了王汉文。庞琼花长相甚佳,日寇将庞琼花带回阳江欲施强暴,庞琼花极力反抗并咬伤日寇手指,日寇恼羞成怒将庞琼花杀害(47)。不过,庞琼花并没有被解读成为一位女英雄,尽管她和她那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丈夫正是由于坚持民族气节而付出了生命。庞琼花一直是具有争议性的,理由是她在被俘后“被敌欺骗,讲些不利于革命的话”(48)这也是后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之所以要将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女主角由吴琼花改为吴清华的原因。
唯一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是冯增敏。她在1937年之后与未婚夫庞道方结婚,婚后还生有一女,丈夫庞道方在南洋谋生时被日本占领军杀害(49)。1945年她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工作,据说她为了革命工作还将女儿交由他人抚养,直到1950年以后才认领回来。另有人说她为了更好地完成革命工作而没有选择再婚。1950年后,她历任朝阳、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乐会县、琼海县妇联会主任等职。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作者刘文韶和琼剧《红色娘子军》的主笔吴之都明确地说过,他们在创作过程或者创作之后采访过冯增敏,估计当时请冯增敏讲述女子参军传奇故事人一定不少,尽管听故事目的各有各的不同。总之,她当时是一个“红人”,1960年她甚至参加了全国民兵大会,毛泽东送给她一支半自动步枪(50)。冯增敏做梦也没想到,在“文革”中她被揪出来受批斗,“造反派”称她为“叛徒”并开除了她的公职,让她回老家务农。当初她在部队落下的胃病,这时候正逐步恶化,更不幸的是她在放牛的时候,被斗架的牛当胸踢了一脚,而口吐鲜血。1971年的一天,冯增敏腹部剧痛(51),时逢大雨河水猛涨,无法过河及时就诊,五十八岁的她遂与世长辞。
“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指导员王时香释放后,嫁给了一位丧偶的国民政府联防队的中队长。“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连长”黄敦英则嫁给了一位国民政府区长(52)。1951以后,王时香的丈夫受到新政府的“镇压”;黄敦英的丈夫被执行枪决,因为他被指认为国民党特务。从1951年至1980年期间,王时香和黄敦英一直是“专政”的对象。当然,“文革”中她们受到更为残酷的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她们在被划分为“反革命家属”和“地主婆”的阶级成员之外,还有一个“叛徒”的指责。在《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琼崖剿匪记》一段描述成为“铁证”——“向本旅投诚的女匪伪女子军第一连指导员王时香、伪女子军模范队第二队长黄敦英……”(53)。以黄敦英尤甚,她可能是为“文革”中最为悲惨的原“女子军特务连”干部,黄敦英丈夫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三个未成年儿子和一位老母亲,这些全都由黄敦英一个人操劳,在“文革”中她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那些曾被指责为“反革命家属”和“地主婆”和“叛徒”的“女子军特务连”成员逐步得到“平反”,并开始“享受娘子军战士的政治待遇”(54)。“平反”姗姗来迟,相信她们的毅力可以使她们承受得起任何肉体上的折磨,但依照她们那样倔强的个性,又如何忍受得住种种不公和屈辱?“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在国民政府官员的眼中,她们是被感化的对象,接受着“仁慈和关爱”的施舍;在共产政府左派的眼中,她们是可恶的“叛徒”,理应接受着“镇压和批判”。她们早年因反对包办婚姻而参加革命,最后却不得不委曲求全;她们曾痛骂那些想让她们做“压寨夫人”的团丁,没料到也被迫做了人家的“二房”;她们年轻时打土豪、斗地主、镇压反革命,想不到人到中年也被当成“地主”和“反革命”来镇压。
“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历史的错位原本是一笔难得的财富,但是,如果她们的深重苦难被翻译为饶有兴味的传奇,那么就等同我们拒绝了这份历史遗产(55)。
注释:
①关于“红色娘子军”创作论争详情,请参看拙作《“红色娘子军”创作论争及其反思》,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②刘文韶:《我创作〈红色娘子军〉的历史回顾》,载《军事历史》2007年第3期。
③梁信:《勿将误传再误导——〈关于〈红色娘子军〉之缘起〉》,载《大众电影》2005年第4期。
④吴真、贺敏洁:《〈红色娘子军〉琼剧最早上演》,载《南方日报》2003年3月17日。
⑤“红色娘子军”创作素材显然包括但不限于“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女兵连”相关记载,具体而言则由于文学样式不同其创作素材存差异性,这是一个相当复杂且极具争议性的问题,故本文不将此作为关注范围。
⑥主要是就1930年代社会经济状况而言,旨在通过当时妇女生活状况考察妇女参军原因。
⑦⑧(40)陈济棠等人编写:《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琼崖剿匪记》,3、3-4、31,海南区档案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⑨由张开新等人编写的《红色娘子军史》有一段表述可以佐证:“为生计所迫,男人大多抛妻别子到南洋去打工,卖苦力;不出洋的也很少守在家里,他们或出海捕鱼,或上山垦殖,撇下女人在家撑着门面。家务农活,侍老育幼,养家糊口,里里外外,全靠女人操持。”除此之外,今日海口和三亚这样的大城市,仍然可以看到她们开三轮车接送游客、挑着担子卖热带水果,向游客兜售珍珠项贝壳等工艺品,这些妇女常常给外地人留下吃苦耐劳的深刻印象。
⑩详见邢增仪的散文集《海语》,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散文《文昌阿婆》后来还被改成同名电视剧。
(11)(12)(19)(20)(22)(26)(30)(32)朱逸辉等人编写:《红色娘子军写真》,102、3、8、9、9、15、27、27页,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0年版。
(13)冯白驹(1903-1973),海南琼山人。琼崖红军的创建人之一,海南解放后任海南行署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时受批斗。
(14)朱逸辉等人编写:《红色娘子军写真》,8页,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0年版。在《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一文的表述是:“有些比男同志还好,丈夫反动的带领我们打死他,甚至丈夫反动,在夜间和丈夫睡觉时,自己用刀子杀死丈夫,逃出来参加革命。”尽管有些出入,但主要意思并无差别。见中共海南区党委党史办公室编:《冯白驹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5)北京新华总社1957年1月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份《关于海南岛党内团结问题》内部参政。见冯子平:《风雨六十年》,259页,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0年版。
(16)冯子平:《风雨六十年》,421页,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0年版。
(17)(18)(25)(29)(35)(41)(42)张开新等人编写:《红色娘子军史》,14、12、35、67、60、47、46页,中共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2002年。
(21)张开新等人编写:《红色娘子军史》,16页,中共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2002年。名字有用同音字现象:庞学莲,有的文献资料中也写作庞学连;黄敦英,也有写作黄墩英。为方便阅读,本文无论自述还是引文均按庞学莲、黄敦英处理。
(23)关于“女子军特务连”的隶属关系同样存在出入,在《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琼崖剿匪记》的“伪组织系统表”中“女子军第一连”和“女子军第二连”直接隶属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司令部”,而非隶属于“独立师第一团”和“独立师第三团”。
(24)人事上也有所调整,一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时香,一排长卢赛香,二排长曹家英;二连长黄敦英、指导员庞学莲,一排长李昌香,二排长王振梅。
(27)1931年5月时人数≤103人,1932年春调整时扩充了一个排,根据一个排三个班,一个班十人计算,再加上勤杂人员等,扩充人数应≤40人,故“女子军特务连”总人数应该≤150人。
(28)“马鞍岭之战”是在遭陈汉光的国军部队追捕的情况下,在向牛庵岭撤退的过程中造成“女子军特务连”从成立至解体过程中最为惨重的伤亡,详见下文。
(31)运动相当残酷的,师长王文明的妻子邢学慧,曾是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她甚至不能在这次运动中保全自己的性命。
(33)特委正在准备在8月2日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从进攻时间上可以看出警卫旅的作战部署是十分周密的。
(34)此处采用的是《红色娘子军写真》一书的说法,在《红色娘子军史》一书的说法是二班十名战士全部阵亡。
(36)中共海南区党委党史办公室编:《冯白驹研究史料》,42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7)黄培岳:《〈红色娘子军〉幸存者的遭遇》,载《贵州文史天地》2000年第2期。
(38)朱逸辉等人编写的《红色娘子军写真》一书第116页:冯白驹在一次会议上也提及到个别人“存在悲观失望,动摇犹豫”和“贪生怕死”。
(39)张开新等人编写:《红色娘子军史》,42页,中共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2002年。《红色娘子军写真》一书的叙述是,庞琼花回家后躲在山中,因叛徒出卖被捕。详见该书96页。
(43)1937年12月中旬,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国共合作”使得这些“女子军特务连”干部被释放。
(44)《红色娘子军写真》一书说“在媒人的撮合下,嫁给了一位牙医”,而李高兰的《红色娘子军几位连级干部的坎坷人生》(载《老年人》2000年第12期)一文则是:“父母作主,把她许配给了阳江一个姓吴的穷人。”从《红色娘子军写真》所言庞学莲子女全部从事医学及其相关工作的描述看,前者似乎更可信。
(45)《红色娘子军写真》一书说“庞学莲是通情达理的女子,认为丈夫不是喜新厌旧,不是背叛妻子,而是出于无奈,便原谅了他,并跟他生了3个男孩儿。”而《红色娘子军几位连级干部的坎坷人生》一文则是:“庞学莲出狱回到海口,听到丈夫再婚的消息后非常失望。丈夫赶到她娘家看望,让她回家一起过日子,庞学莲谢绝了。之后,丈夫又一次次来看她,对庞学莲说:‘我现在的妻子也是穷苦出身,她钦佩你,也同情你的处境,是她叫我来请你回去的!’无奈之下,庞学莲只好接受现实。”
(46)据庞学莲所说,当年庞琼花从军是因为父母将女儿当做摇钱树,替女儿选“番客”。海南人把去南洋叫做“去番”,故称去南洋的人为“番客”,此处意为嫁个有钱人。
(47)当然,作为一个女人的解释又会有所不同。庞学莲说,“女人生靓了,有利有弊。”反“AB”团时庞琼花被投入监狱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那是因为漂亮有利;这次被日寇强暴,同样因她长相漂亮,不过这次对她个人来说却极为不利。庞学莲回忆此事,泪湿眼眶。详见《红色娘子军写真》一书第96页。
(48)冯白驹:《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见《冯白驹研究史料》,42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9)此处采用的是《红色娘子军写真》一书的说法,另有一说:“出狱不久,她嫁给了一名红军战士,怀孕后,丈夫在战场上牺牲。”详见李高兰:《红色娘子军几位连级干部的坎坷人生》,载《老年人》2000第12期。
(50)有的说是自动步枪,还有的说是小手枪,具体不详。
(51)据说是患急性肠梗阻。
(52)按照1930年代的海南习俗,女人到十五岁还没有确定对象,今后就很难嫁出去;到了二十岁再找婆家就比较麻烦;至于过了二十五岁,找到好婆家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她们毕竟扛过枪打过仗,身上少不了野性和反抗精神,普通人家不敢娶;为了生存下去,她们只好嫁给那些愿意娶她们的人,但这些人大多是“丧偶续弦”或是想“二房生子”的。
(53)在朱逸辉等人编写的《红色娘子军写真》和吴之的《溯流思源》(香港也仕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里,都试图列举各类证据来说明:“女子军特务连”中的某些人曾经背叛了革命,出卖了同志。历史相去甚远,包括本文在内的叙述都可能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尊重学术我们有必要考究历史事件的“真相”,但对于生活在那个不幸时代的老人,我们似乎不能过分苛求什么。
(54)在1992年10月的时候,海南一家公司给她们每人每月发放100元的生活费。《中国精神文明年鉴·1993-1994·海南》,第92页。据说现在政府已经发给她们每人每季度500元生活费,不清楚政府具体在什么时候开始生活费的发放,也不清楚这是否也是妇女主动争取的结果。
(55)笔者与文中所述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任何人员均无任何利益之关联。在水平能力范围之内笔者力求但不保证引用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出于学术研究目的本文引用了较多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笔者默认、同意、赞成、支持、拥护或反对引述中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