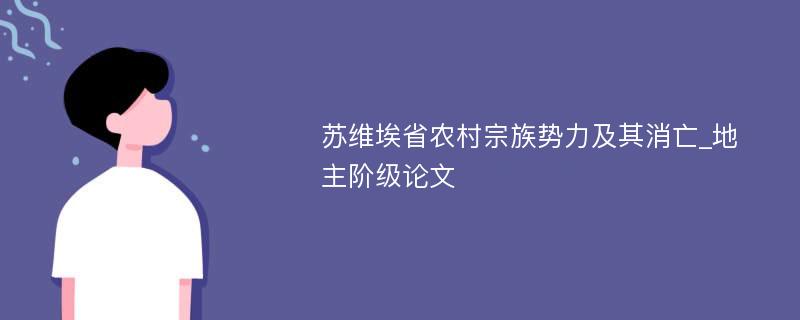
苏区农村的宗族势力及其消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宗族论文,势力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革命前宗族力量的活动和特点
宗放制度,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历史悠久,深固不易。社会成员大多聚族而居,交相并炽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是该制度衍生和寄托的社会基础;自然条件的艰苦、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以及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利用,则是该制度兴盛不衰的原因。近代以来,宗族制度历经太平天国革命和大革命的两次较大冲击,终因革命失败而仍然得以延续。例如,受大革命冲击最烈的湘东等地,宗族制度废驰,已达极点,但革命甫败,即由国民党“驻军刘军长竭力提倡,恢复旧规”。①因此,土地革命兴起,依然要遇上宗族制度的兴革这一社会问题。
土地革命大张旗鼓地冲击宗族制度和势力,其来有因。1928年,毛泽东调查井冈山根据地的湘东赣西几县后说,农村“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家族势力的广泛和强大,以致于使中共的“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毛泽东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毛泽东从一个很高的层次即农村中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高度,指出了“家族主义”的消极影响。
《申报》记者陈赓雅30年代初在江西万载县城郊所见,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宗族势力的繁盛和自大:“各姓氏之宗祠家庙,林立栉比,颇饶宗法社会之意识。……家族制度,亦较严密。各姓宗祠,计有三四十所,所用门联,多为‘皆以明伦,庙中何殊庠序;是亦为政,门内等若朝延’等口气。中以辛、宋、郭三氏宗祠规模最大,年可收租五六百石。”②这说明,农村的家族、村庄,远不仅是与政治无涉的自然单元,而是同封建的政治、经济密切相连的基层社会组织,它所公开流露的“为政”信息,是对封建权力的仿摹和追求。
宗族力量的凝聚和生发,一般说来需要四个条件:相当数量的公田公产;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组织力,与政权保持密切联系又为全族成员所信服的权威人士,亦即族长等宗族首领;能够组织全族活动的祠堂家庙;为全族共同遵守的族法家规。所有宗族都具有这些条件,但有强弱大小之别,那些族产雄厚、人多势众、门第显赫、家族成员在政权中曾居或现居高位者,被称为“望族”、“显族”、“大族”,与中小家族的地位大不一样,在地方上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地方政权往往也得看其脸色。滕代远巡视修水县后报告说,该县西乡以曹姓最多,欺压它姓“特别厉害”,西南乡以莫姓为最富最恶,每年收租数万石,“在该两姓的佃农特别受苦,愤恨之心亦特别激烈”。③这就是说,条件的强弱决定着宗族势力的大小,宗姓之间也不平等。
四个条件蕴含了宗族制度的性质、作用、经济来源及其与政权和社会的关系。据土地革命初期各地的调查,四者情况大略为:
族田族产:各地族田(山区还有山林)数目可观,赣闽湘鄂皖大都在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左右,高者如闽西长汀、湖北广济,占三分之一。土地和山林所出,是族产的基本来源。族田对佃户的剥削率与一般地主没有区别,本族为佃者租额亦不减轻,只可将租谷的一半折钱上交而得以多留点谷子自己食用,但也有要全部交谷者,佃户亦无可奈何。④族产的另一重要来源是高利贷。外族人借贷,利息很高,族内贫穷者借贷,则一般既能借到,利息也略低,如兴国富农放贷利息为2.4分,则宗族为2分,以表明对族人“还有些周济之意”,但宗族借贷“一样要抵押。公堂索债比富农还要厉害,期满利钱不清,牵牛赶猪,下田割禾,都做得出。⑤这说明,族田族产不仅是封建经济剥削的重要内容,也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满足无地少地的农民要求土地和免除受剥削之苦的愿望,势必触动作为宗族制度经济基础的族田族产。
宗族首领:这大体属地主乡绅一类人。他们大多因其财力、身份地位、处事威权或对家族的贡献成为宗族的核心人物。无论在何种基层行政体制中,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一村一族之内,分成数邻数闾或数甲数保,成员既为本族人,邻闾长或保甲长例多为宗族首领。保甲长的地位因宗族关系而巩固,宗族首领的权势亦因行政制度而强化,形成“保甲为经、宗族为纬”的社会格局。与此同时,他们又是族田族产的主有者,如寻乌县,“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而祠堂族产也“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⑥兴国公堂十分之六七为劣绅所持。乡绅一方面通过“把持公堂,从中剥削”变成地主;另一方面以占有族产为基础而大肆“行使其宗法社会之威权及统治”,严厉束缚族人的人身自由。江西省委报告说,乐平族姓农民均在文老闾(土豪劣绅)和武老闾(土劣保镖)统治下,“每个农民无论什么问题都要问过老闾”才可处置,包括回娘家的妹子“和哥哥所说的一切情形必须告诉文老闾”,⑦其苛严实难想象。因此,政权、族权最终在地主豪绅身上融汇交结,三位一体,所以族长也是彻底的反封建的社会革命的对象。
祠堂:祠堂又称家庙、宗庙,是宗族活动的中心,既是祭祀祖先也是处理、商议宗族事务的场所。祠堂之盛,万载已见一斑,其他地方也不逊色。陈奇涵说:赣南“氏族社会的传统习气浓厚,规模宏大的宗祠到处林立”。⑧规模之大,如兴国,“每个姓都有一至数个祠堂,一个祠堂可以驻一个连”;⑨建祠之好之精,如瑞金,“薄具资产者,即喜大建祠宇”,“庙宇壮丽,雕刻至精”。⑩宗祠多系祖传,但若兴建,大多需要族人集资,贫富均须分摊。宗祠的高大精致,与贫苦人家的矮房土屋,构成强烈对比。
族法家规:作为宗族行为规范的族法家规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后代仅谨遵承继而已,一般不多作增删。这种情况,由其所维护的宗族秩序与封建统治秩序的高度一致性所决定。如乐安流坑村董氏族规,主要内容为训诫族人听上命、供赋役、崇礼教、息竞争,以及严守“主仆良贱”名分,不许“僭越”,欠租抗主的仆佃得由主人或宗祠重加罚治。“刑罚不可废于国,鞭笞不可废于家”,“不损人而利己,不妒富而欺贫”,也是其它族规的共同内容。族规虽含很强的道德修养成分,旨意却是让族人在封建统治下安分守已,承认现实,“不非为”即不作有损封建秩序的事情。国家法律在农村往往有所疏漏,而族法家规则无处不在,违反不得,否则惩罚立至,轻者打板子、不准入祠堂和参加祭祀等活动,重者处以沉潭、活埋或死后不许葬入祖坟地。彭德怀少时仅因踢落一个鸦片烟盘,便差点被宗族溺死。族法家规对农民身心的桎梏和摧残,在某些方面甚至为政权功能所不及,其约束下层群众、维护封建统治这个根本点,与苏区推翻封建统治、解放贫苦农民的社会目标,极不相容。这也是湖北黄陂农民坚决反对“利用宗法思想制定族规、会规、禁条”的重要原因。
一个宗族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其活动和功能难以尽述。其中,有的不堪丑陋,对社会生产力破坏严重,也有的不无积极意义。仅挑一正一反两项活动再作分析。
宗族活动对社会、家庭和个人危害最大者之一是械斗。苏区屡有记载:“修水宗族观念特别浓厚,械斗最为利害;阳新氏族性极强悍,械斗之事时常发生”;广济豪绅鼓动宗族械斗,“有许多争坟山,争湖场,甚至为一些顶小的问题,牵联数十个村庄,械斗至数十百次,死人至数十人”;(11)瑞金民性旷悍,“尤好械斗,每斗则全村参加,伏尸流血,视为故常”。(12)地主利用家族关系组织土客籍民众的械斗,也是湘赣、湘鄂赣边界农村的重大社会问题。激起族人不惜流血送命者,是有形无形的宗族利益或名声,为此,甚至一语不合,一事不平,一鸡一犬、一草一木之微,由一家而牵动于一族,皆足以酿成绝大惨剧。械斗恶习,与社会进步显然背道而驰。
最能激发族人喜兴、自豪感和凝聚力的活动,是祭祀和表彰读书有成者。这种活动取用族产公费,场面惊人。瑞金“春夏宴集,大享族人,庖丁专司各族祭享及各族子弟毕业宴会者,竟多至二千余人,食具精粗皆备,极一时之盛”。(13)万载“春秋祭祀,阖族老幼,除无业者外,概得欢会聚餐,一日或于三日”,年高者饮寿酒和得“老命钱”,读书能猎取功名者则全族嘉奖不已,“一仍科举时代之旧规”。(14)这里,尚可领略尊敬长老、崇尚读书的民族遗风,确有其积极意义。这项活动很可能最受族人欢迎,因此,湘鄂西苏区初起时,群众最初反对没收祠田,“宗族的势力一时不能消灭”。(15)
二、社会变动中宗族力量的动向
当社会革命的大潮席卷而来之时,传统农村社会顿然感受到了它那深沉的份量。社会变革的政策和目标毫不含糊,它意味着,顺应也好,抗拒也罢,宗族制度和力量都不能再存在。因此,面对急风暴雨般的冲击,所有宗族力量,不论是大族还是小族,强宗或是弱支,都被推到了严峻的选择路口,或主动自觉、或身不由己、或半推半就地作出各自的抉择。
综合各种记载,面对社会变动,宗族力量呈现出响应、分化、中立和抗拒等四类动向:
积极响应、支持乃至参加社会变革的,主要是那些原先有优秀子弟在外读书,加入中共而后返乡组织农民、领导暴动的家族,即地方党领导人所在的家族,以及那些原来受到封建政权与大族压迫、排挤的家族,如各地的客籍家族和一些小家族。
陈毅1929年向中央的报告中专门提及,江西最早也是最好之一的革命根据地东固,是在吉安、南昌读书的学生入党后返乡,“利用家族关系”发动斗争创建的。在苏区斗争中牺牲了80多人的贺龙家族对创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作用,亦为人所共知。大体上,1928年前后南方各地迭连爆发的农民暴动,多为中共党员返乡利用家族力量秘密酝酿和发动。这是社会变动初期家族力量投入的特殊形式。这类家族,在社会变动中有领先之功,家族成员的态度有较高的一致性,行动也较为齐整和自觉,象东固,连族内的地主、富户也自动出钱为红军购买枪械,因而受到“同志的待遇”。
宗族的迎拒对革命的初期动员和力量的聚集不无影响,有时甚至成为革命力量能否在当地立脚的关键。肖华谈及兴国革命运动顺利发展之因时说,兴国的姓氏观念浓厚,肖、陈两姓很有势力,“这种姓氏关系,有效地掩护了革命势力的生长与发展,致使兴国县党的组织,一直没有遭到严重破坏”。陈正人对遂川西庄王姓家族的表现也一直念念不忘:大革命失败时全县仅剩的6支枪为他们所保存;土地革命刚起,他们又踊跃参加,并成了“出干部的地方”,遂川县乃至湘赣边界的不少干部都是西庄王姓人。这是一个表现卓越的家族。宗族投入革命,引起两个社会变化:一是这样的宗族力量已脱离其原来形态,而属于改造社会的政治力量的范畴,其斗争也就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上升为社会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抗争。二是它们立即受到旧秩序维护者的仇恨,如遂川王姓不少人遭到国民党的屠杀;皖西六安、霍山地区响应革命家族的“祠堂庙宇以及群众的住所被烧尽了”;由于客籍民众的革命,土籍地主便“利用家族关系组织反革命的武装,向客籍民众进攻。”这也说明,选择革命的宗族在当时敌我力量异势条件下,不但要有政治明见,而且要有非凡勇气。
宗族动向中最常见者是内部分化。这与前一种有相似之处,很难截然分开,但也有其自身特点。首先,促成分化的因素,大多为红军到达一地后对贫苦农民进行的宣传动员,而最厉害的武器是阶级分析方法。贫苦农民一旦明白宗族之内存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宗族力量的分化也就成为事实。其次,宗族内一般已有对立。如寻乌,原先便存在着贫苦族人要分公田而富裕族人反对的“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16)土地革命一来,要求分公田的族人自然立取拥护态度。又如瑞金,有的贫苦族人原先即对族内地主不满,以致有的甚至通过挑起械斗“而尽嫁祸于富室”。在社会变革中,这两种人是很难走到一起的。湖北光山大地主胡范成尽管威胁利诱其本族人(数千人)与革命抗争,由于“其本族中亦起分化”,实际跟随者仅数百人。因此,族长乡绅、豪强地主被杀、被管或外逃,而贫苦农民兴高采烈闹分田,成为苏区初期宗族力量分化的普遍现象。
也有保守中立者。据1931年8月15日《民国日报》记载,宁风洽坪村的谢姓家族,“士民守旧”。1928年朱毛红军动员各地设立农民协会,没收分配土地,竟被该姓视为有违祖宗礼教规仪的非分行为,合村之民不分老幼遂皆逃避而去。这种情况,从倾向上说,是不欢迎或者说反对社会变动的,他们满足于不惊不扰、用手臼打米吃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生活,一遇变故便惶恐万状,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既不想融入变动之中,也不想对变动犯难相抗。
另一种中立比较特殊。1927年秋冬,余江县康山等地利用宗族观念集合的8千余农民,倾向国民党却又“反对旧的土豪劣绅”,但对革命势力也不愿兵戎相见,与同样因宗族观念而纠合的该县大塘、崇州等处农民很不一样。这种情况十分少见,颇有代表性。
最后一种宗族动向是聚族反抗。反抗的形式多种多样,综之可举5种:一是积极配合国民党的反共,主动动用宗族力量参与清乡。永新县中洲村潭立官,1928年已年届74岁,尤“纠集族中子弟组织挨户团”加入清乡,“积极参加反共”,每有捕获辄予杀害,“不稍宽假”。(7)类似宗族,对社会变动尤其是其领导者共产党人,持至恨至狂态度。他们虽不敢独力相抗,一旦有所倚靠便肆无忌惮。
二是不待国民党行动,即主动集合族众扑灭暴动,进攻革命,仇杀民众。于都农民暴动时,刘国瞿等利用宗族关系动员禾丰和上龙田刘姓千余人反扑,将暴动领导者张文焕等及邻近房屋焚毁一尽,这次暴动也很快失败。类似者也发生在湖北阳新等地。阳新豪绅地主甚至自动将家财散给族人,以笼络人心,“团结氏族民众”进攻革命力量,以致形成严重的赤白对立。
三是集众抵抗红军。此种方式在反抗者中较为普遍,也有点规模。1930年8月,赣东北红军李新汉部在波阳八齐,曾遭到方、蔡等宗族力量的顽强抵抗。“八齐农民,素称强悍,”乡长方恒发、乡绅方轫升、蔡品辉等复对其施以军事训练。红军来时,族众5千余人“以刀矛土枪土炮,实行对垒”,红军兵少力弱,不敌而去,一而再,再而三,竟到第三次才将抵抗克服,并将为首诸人镇压,(18)可见宗族力量声势之大。敢与军队抗衡者,还有鄂豫皖地区“最有力量的”地主武装──枪会,枪会的许多群众,便是“爹字辈的阔人老爷、户首族长们”召来的本族子弟。(19)
四是不准族人参加革命活动。湖北江陵张家场的张姓,是个大族,1929年鄂西民众大动员时,掌握族权的几个豪绅,“不许他们的族人加入农协”。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族权威严没有受到过冲击的家族。
五是结寨自保,用相顽抗。在所有抵抗中,以这种抵抗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以规模论,如湖南大庸西教乡大地主熊相熙家族,据寨上十个,拥枪数百支,成为桑植、大庸苏区之患。贺龙亲率大部红军于1928年8月围攻“熊族团防,以除后患”。结果攻寨凡7日,大小十余战,始将其击退。(20)这种攻守规模,较上述波阳八齐又甚。抵抗时间最长的要算赣南的土围子。被称为于都北部望族的赖村宋姓,以700多人据守土围长达四、五年之久。葛坳葛姓家族筑有围砦多所,小部红军来时,他们严约族中子弟力谋抗扑,且联络邻族共相抵御,与上下榭肖族、澄江谭族、赖村宋族等声气相通,直至组织国民党宁都、于都、兴国边陲联防办事处,与苏区长期为敌。这处土围,从1928年结寨固守,到1932年由红军主力功破,前后凡五年,其间有“血战百数十次”的记录。(21)从形式上说,这种配以现代武器(国民党军均曾援之以武器弹药)的聚族结寨,确实将自古以来宗族自守自卫的传统功能推到了极致;问题是,不辩社会变动的进步性质而一味死守既成宗族利益,这种自守自卫也就毫无意义。
综上所述,苏区社会变动中,宗族力量的态度和动向具有极高的相异性。它所表现的一般特点是:1.尽管土地革命的目标直指宗族制度,宗族力量却并非天然反对革命。2.宗族力量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主要决定于宗族的现实利益及其在乡村的地位,受到压迫或势单力孤的中小宗族包括客籍,变革现状的要求最强烈,容易首先响应革命。同时,宗族首领对社会变革认同的与否和深浅,也直接决定着宗族的行为。3.对社会变动持逆取向的宗族势力,力量分散,缺乏横向间的紧密联系,如于都葛姓虽曾联合邻族并被推为团总,“然遇时危事急之时,均让葛姓一族独当其难”,邻族不愿为结盟冒险犯难,结果葛姓还是势孤力单。因此,宗族势力不能形成巨大协调的足以阻挡或逆转社会变动的整体性力量。4.阶级观点成为引发贫富族人产生分化和斗争的原因,宗族首领由此而逐渐失去以往所拥有的完全控制权。这是一个真正属于20世纪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新变化,从根本上说,贫苦农民的觉醒和斗争,决定着宗族制度和宗族势力的命运。
三、宗族势力在苏区的消亡
严格地说,苏区不存在一个专门以宗族制度和势力为对象的革命运动。对宗族制度的革命,只是社会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与没收族产公田、打破家族主义、剥夺族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之类政策包含在推翻封建制度的整体大政方针中一样,苏区内的宗族制度和势力,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和农村新秩序的建立而消亡的。
1929年左右进行并很快完成的族田祠产的没收与分配,破灭了宗族势力依存的经济基础。如前所述,族田在农村全部土地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虽然族田祠产“表面上是一姓一族或者当地农民公有,实际上还是族长、会长、豪绅所垄断,利用来剥削农民”,所以,没收族田在绝大多数地方得到农民的拥护。族田的没收着眼点首先固然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增加可供分配的土地数量,但同时也意味着宗族活动经济来源、族长豪绅与族人经济联系的断绝,以及家族界限的打破。第一步,祠堂的财产田土一概没收,“不论某族某姓的了”;第二步,被没收的土地以乡而不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以“打破氏族地方封建关系”,是苏区的通行做法。
宗族活动的政治条件被瓦解,聚族相抗被清除。前者,主要是封建政权的被推翻使宗族势力失去依附和庇托,失却了上层联系和依托,宗族势力便成为孤鸿;苏区社会新规范的建立,使族法宗规不宣而废,宗族力量由是失去行为规范和制约;豪绅地主阶级的在社会巨变中,尤显零落之状,他们一部分逃到上海、武汉、南昌、长沙等大中城市,这部分人为数不少,仅吉安、赣州两城1930年便“陡然增加了十余万土劣地主”(22)及其家属,一部分罪恶较大者被处决,一部分则在苏区受到管制。三者之中没有宗族首领的统计,但必包括无疑。豪绅地主阶级的消灭,使宗族势力失去了核心人物,势成涣散而不能再行组织和运转。后者,举凡在苏区范围内不论以何种形式聚族相抗者,均先后被解除武装,遣散族众。那些在社会革命最初的冲击波中顽强地留存下来并筑成坚固寨围的宗族据点,也在苏区1931年开始进行的肃清“土围子”行动中相继被击破。到1932年2月,仅江西苏区即消灭这样的土围石寨200余处,占总数的95%。也就是说,盘踞围寨的抵抗势力已基本上被肃清。前述于都赖村、葛坳、杨梅头等族寨被攻开时,族首或击毙或自杀或被捉,而占守寨人数三分之二的贫苦族人(如赖村达500余人)则被“解放”和安置。族寨的被击破,可以说是宗族势力作为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最后消亡。
宗族力量的转化和贫苦农民的动员,是宗族势力消亡的重要表征。投入革命的家族可以说是对宗族力量的自行摧毁,而表现出社会角色顺应进步潮流的革命转化。由本族革命者先行导引的整族变动,是革命转化的形式之一;红军深入农村的宣传动员引发的广大族人的觉醒,则是更普遍的转化形式。这种转化,使广大群众脱离旧的宗族生活轨道而热烈投身社会变革,少数群众反复、反外族不反本族地主、家族主义等现象固然迅速消失,一度陷入以姓氏族长名义组织的地主武装的族人也很快觉悟而倒戈相向。因此,苏区群众自动“毁灭祠堂庙宇的神龛佛像匾额对联”,将家里供着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取下,换上马克思及革命先烈像与革命标语。(23)他们的转化使宗族力量失去了社会基础。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极端行为,而增加了动员的困难。有的不做宣传即贸然“去毁庙堂、打菩萨、掘祖坟、焚宗谱,激起群众反感”;有的仅因掌握族权的少数豪绅地主反动,便误认为整族整姓尽皆反动而予以打击,鄂西江陵曾因此导致张姓500余人怒而联合敌军入苏区烧杀,并影响王姓彭姓群众反水。这说明,即便是进步的社会变动,也要把握适度,失当行为往往达不到预期目的而招致负影响。
原先作为宗族活动场所的祠堂也换了新主人。祠堂都成了苏区中央、省、县、区、乡各级政府的办公场所或文化娱乐之地。在瑞金县保留的85处中央机关和著名领导人的旧址旧居中,仅宗祠即达27座,占三分之一,其中最有名的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地,便是座落在叶坪的谢氏大宗祠。宗祠作用的转换,也是宗族势力消亡的一个标志。
最后,宗族的一些功能尤其是有益的功能被取代和以新的形式得到接传。它最为强调的家族利益被阶级利益取代,以家族出人头地为追求的族团目标被阶级解放的社会目标取代,宗族调解功能为乡村政权与贫农团、妇女会等组织取代,互助救济功能为乡村政权与生产合作社、拥军优属委员会、互济会等取代,经济活动功能(主要指物品的交易与交换)被乡村政权和供销、消费、金融合作社等取代,奖惩与治安功能被乡村政权取代,等等。这样,农村社会生活便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新的轨道上运转,它同时表明,农村社会的新的结构形态已经铺就,而宗族制度丧失了它的位置。
苏区内宗族制度和势力的消亡是彻底的、不妥协的社会革命的结果,反映了中共改造农村社会的构想和努力。从社会进步的观点看,这场社会变动富有积极的成果和意义。首先,改变了农村几千年迁延不变的社会结构,清除了农村社会生活中腐朽、消极、落后的内容,它所构成的对部分封建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无疑值得称道。其次,解除了农民在宗族内的封建人身束缚,提倡并实践了村姓之间、家庭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社会平等,以往世家子弟通过门第血缘关系进入上层社会或权力中心的优势被打破,下层群众拥有了发挥创造性的广泛机会。再次,通过对宗族制度的消解和新的社会机制的架建,实现了农民群众与国家政权的高度结合,从社会体制上保障了农民群众对乡间事务的关心和参与,这对于组合社会主体性力量和实现既定社会目标,大有裨益。
当然,也应见及,将宗族权力和功能大部收归政权,既有益也有害:大益在便于与民众协调,避免因失调引发的负面后果;大害在加重了政权的负担,有误导政权纠缠于琐细事务的可能,从而设下招怨的隐忧。另一方面,宗族势力的消亡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以强制性的变革行动换来的,因而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巩固性,宗法观念的肃清自然无从谈起,宗族势力的消亡也非一劳永逸,国民党攻占苏区后宗族势力立即复兴的事实,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消除宗族势力尤其是宗法观念,是个长久的社会任务。上述两个问题,都不是历史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者提出的,因此,不应苛求。
注释:
①②(14)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1933年。
③《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
④⑥(16)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
⑤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10月。
⑥《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28年4月15日。
⑧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中央苏区》,第1页。
⑨肖华:《兴国革命斗争与“少共国际师”》,《回忆中央苏区》第392页。
⑩(12)(13)渔叔:《瑞金匪祸记》,1934年12月。
(11)《鄂东巡视员曹大骏的报告》,1929年8月31日。
(15)《万涛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8月11日。
(17)《剿匪阵亡及殉难忠烈事略》,1935年4月。
(18)姜伯彰等编:《波阳匪祸史》,江西省档案馆存。
(19)《黄安工作报告》,1927年12月4日。
(20)《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10日。
(21)《于都葛坳澄江赖村三保卫团抗匪记》,1935年1月。
(22)(23)《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
标签:地主阶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