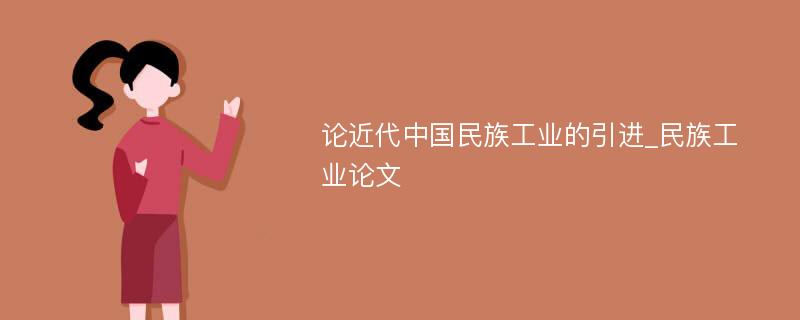
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对外引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中国论文,民族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充分认识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优质原材料、生产技术、专业人才等〔1〕, 提高民族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缩短近代化的探索时间,变晚起步之劣势为高起点之优势,及早实现进口替代,提高国产化水平,这是一条较为便捷、有效的途径,也是后发展国家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对外引进在懵懂中起步,在探索中前行,不断走向理性,并进而寻求进口替代,逐步实现国产化,走过了一段曲折艰难的历程。
一、在懵懂中起步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使一些有识之士在震惊之余,开始开眼看世界,承认自己落后,西方先进,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呼声,这可看作是近代中国关于对外引进的最早表述。但在学什么、怎么学以及怎样引进、引进什么的问题上,中国经历了由表及里,由幼稚、盲目到逐渐成熟、理性的历程。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 标志着中国工业化的开端。 从70年代开始,私人民族资本主义也在缫丝业等行业中出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放松对私人资本的限制,民族私人资本企业开始获得较大发展。但是,当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在中华大地破土而出时,中国的近代民族机器制造工业却尚未诞生,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机器厂——发昌机器厂迟至1866年才创立,而业务却是修理外轮。以后相继设立的民族机器厂也完全局限于外国轮船修理业务。 据统计, 从1866 ~1885年,上海设立的民族机器厂共有9家,全部是船舶修造厂,1890 年前后,有少数民族机器厂转而部分地依托于本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个别企业开始尝试轧花、缫丝机的仿造,但所制造的仅是简单、小型的机器,在整个民族工业生产领域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因此,近代民族工业发端时期并没有自己的国有设备可资利用,一发轫便与对外引进天然地联系在一起,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必须也只能从对外引进开始。在民族工业早期,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私人资本企业创办所需的设备完全从国外引进。江南制造局设备来源一为容宏赴美采购的机器,一为购入虹口美商旗记铁厂;福州船政局设备主要订造于法国和英国;其它国家资本企业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兰州织呢局、华盛纺织总厂、湖北纺纱局、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工厂、上海织布局、萍乡煤矿等,私人资本企业裕源纱厂、公益纱厂、业勤纱厂、埠丰面粉厂、华兴面粉厂、公和永缫丝厂、宁波通久源轧花厂等,所用设备无不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丹麦、比利时、意大利等国进口。〔2 〕随着洋务企业的广泛设立和民族私人资本企业的兴办,进口设备呈逐年上升趋势,上海口岸《海关册》1878年开始对机器进口单独立项,1886年全国进口开始分列机器项目。1889~1893年全国机器进口值平均每年达60余万关平两;1895年甲午战争后,外国人被允许在华设厂,民族资本也掀起设厂浪潮,机器进口更大量增加,1895~1899年平均每年达200余万关平两, 这一时期成为中国近代设备进口的高潮时期。设备之外,工业生产所用的原料特别是须经科学方法提炼加工的原材料,也只能依靠对外引进,如洋务军工企业制造军火所需的熟铁、青铅、紫铅、海墨等购自英、奥等国,毛纺织厂染色用颜料向德国进口。在民族工业发展早期,由于创办的企业不多,涉及的工业领域有限,因此原料进口的数量、品种并不多。
初涉近代工业,毫无办厂经验,兴办企业所必须的技术、管理人才也等于零。洋务派奏设广方言馆、新式学堂,遣送幼童出洋留学,开了近代教育之滥觞。但人才的培养非一蹴而就,须假以时日,在这段真空时期,举凡略通西文或与西方有过交往之人,均在洋务企业网罗之列,如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宏1863年被曾国藩委派赴美采购机器,驻外使臣刘端芬、薛福成等为洋务企业订购机器、招募洋匠,从事生丝出口贸易的胡雪岩受左宗棠之托,为兰州织呢局购办机器等等。买办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更被洋务企业畀以重任,肩负经营管理之责,但他们毕竟没有受过近代工业文明的熏陶和专业培训,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未明究理,根本难当此责。因此,早期工业企业不得不雇用外籍人员,“事当创始,不能不于洋人中之熟悉机器者暂为雇觅数人,令中国人等从事学习,务使该洋人各将优娴之艺,授以规矩,传其秘窍。该学习人等若能劳身苦思,究其精微,逐渐推求,久之即可自动制作。在我可收临阵无穷之用,在彼不致有临时挟持之虞”〔3〕,实现“始者师而法之, 继者则比而齐之,终者驾而上之”的目标。对为什么要雇佣洋人,张之洞坦言:“事属创举,中国工匠未经习练,一有差池,贻误非小,故必多雇洋匠,借资引导”,开平煤矿主持人也认为“煤铁两宗开采工程浩大,且深藏地下,苟非机器势难得乎,但用机器开采,必须用精于机器之人,今延定西国矿师、煤师,熔铁管机器等,分别总管名目,到工导引”〔4〕,可见, “借资引导”是当时民族工业企业聘用外人的一种共识。江南制造局1865~1905年间共雇佣洋人22名,除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三人从事翻译工作外,其中有11人先后担任了总监工、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督办顾问等要职,福州船政局前后任用的法国人超过40名,天津机器局雇佣英人2名,兰州织呢局创办时雇有德国机匠13 名,汉阳铁厂官办时期共有洋员40余人,大生纱厂、公和永丝厂、宁波通久源纱厂、和丰纱厂等也都聘有洋人。洋人往往大权独揽,兰州织呢局“在名义上左宗棠任命赖长主持局务,其实局务完全操纵在德国人石德洛未、福克、李德、满德、米海厘等手里,由他们来包办”〔5〕; 上海织布局“厂房建筑、机器配置及其安装运用,自惟美国工程师丹福之计划与传授是赖”〔6〕; 公和永丝厂创办以意大利人麦登斯为工程师指导全厂厂务;大生纱厂“一切技术和管理事务唯洋工程师之命是从,所有工厂机器物件的添置,全归洋工程师开单”〔7〕。毫无疑问, 广泛聘用洋人而且十分依赖洋人,是早期民族工业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
工业化初期,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刚刚开始,又严重缺乏近代科技人才,因此往往无法直接引进,只能假手他人,这是早期对外引进的特点之一。外国公使、洋枪队成员、海关税务司、洋行等充当了中国早期对外引进的中介人,天津机器局委托丹麦领事馆的英国人密妥士办理购买机器、招募洋匠事宜,福州船政局则由江汉关税务司事法国人日意格全权操办;私人企业由于没有这层官方关系,机器设备几乎都通过洋行订购。假手他人的间接引进与雇佣洋人负责技术指导和生产管理一样,如果所托非人,则不免被欺诈,但也可以避免因自身缺乏近代科技知识和办厂经验所引起的种种不良后果,其中利弊不可片面论之。不过,无论如何,创办企业过程中的重要决策总得由自己来完成,洋务派官僚既对近代科技知识懵懂无知,又往往意气用事,幼稚、盲目便成为早期对外引进的又一鲜明特点。江南制造局创办时盘买的美商铁厂以修造轮船为主,留聘的8名洋匠“向以修造轮船为长技”, 而江南制造局却是以生产军火为主,引进的设备、人员与生产要求相去甚远,李鸿章原希望“立时兴造”,但事与愿违,工作迟迟不得进展,“经营数月,糜费巨万,总未得手”,制造枪炮“皆系手挫而成,似与打造无异……费工、费钱、费时”,产品质量可想而知,“该局所造之炮,殊极陋劣……无裨实用……实则世界各国当时已复用生铁炮者”,李鸿章也直觉地感到“料外国造洋枪法与器,必不如是之蠢且费”〔8〕。 鉴于江南制造局设备和人员的强项在造船,1867年曾国藩拨出专款改造轮船,次年即造成一船,以后所造船只的马力和吨位不断提高,1885年造出了钢板船,但这并未引起当局者的重视,1885年后停造轮船。兰州织呢局系左宗棠创办,他根本不懂原料应与机器性能相匹配的道理,向德国买来的机器仅适合纺细羊毛,而兰州附近所产的羊毛比较粗硬,德国技师为使原料强就机器性能,使用大批人员挑拣细毛,据载40人每天只能拣到两磅细毛,100斤羊毛中只有十分之一能织上等呢, 余下的只有部分可织粗呢和毡毯,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由于合适的原料取给有限,因此设备的利用率仅三分之一,大量设备闲置。兰州织呢局资金供应本来紧张,依靠官府拨款维持生计,以极宝贵的钱购买大量闲置设备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盲目引进的结果。兰州织呢局产量低,质量差,销售困难,1882年底,德国人合同期满回国,因事先没有教会接手的技工,1883年便因锅炉爆炸而停工,诚如张之洞所说“费银百余万两……巨款尽付东流”〔9〕。洋务企业中对外引进幼稚、 盲目最具代表的当推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他在铁矿、煤矿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就贸然向国外订购设备,当承造的英国工厂要求将铁砂、煤焦等寄样化验,以便确定“炼何种之钢”、“配何种之炉”,并郑重提醒张之洞“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对此置之不理,竟大言:“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一份可也”。英方据其酸法炼铁配置了两个大炉,这种炉不能去磷,而大冶铁矿恰恰含磷过多,后来,汉阳铁厂费尽周折制造出铁轨,经化验含磷过多,容易脆裂,“万不能用”。20世纪初李维格携带大冶矿石、萍乡煤焦及所制产品赴英化验,才终于明白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设备性能与原料属性南辕北辙。幼稚、盲目的引进,使汉阳铁厂付出了“糜去十余年之光阴,耗尽千余万两之成本”的沉重代价,1894年铁厂被迫停炉,1896年招商承办。〔10〕与洋务官办企业相比较,民族私人企业则认真谨慎,更多地表现出实业家的素质,但限于资金力量、专业知识和办厂经验,对外引进在起步初期也同样存在种种问题,如裕源、裕晋等棉纱企业,引进的机芯属于国外淘汰的旧机,部件破损,整体不配套,“每万锭纺机中,梳棉机之配合不足,以致梳棉功效不佳,影响成纱产品俱巨”〔11〕,等等。
如果说20世纪以前,对外引进是在懵懂中起步,那么20世纪以后则是在前行中走向理性。
二、逐渐走向理性
世纪之交,中华民族一方面经历了一系列巨创,另一方面又不甘屈服,努力抗争,民族主义思想勃兴,振兴实业成为一种时代浪潮,民族工业蓬勃兴起。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引进逐渐走向理性。
经过生产实践,企业家们普遍感到企业产品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设备老化,从而影响产品的质量,也影响了产量、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痛定思痛,引进新式或较新式设备逐渐成为民族企业家的共识。这方面感触颇深的是荣宗敬、荣德生,他们在茂新面粉厂初创时期,由于资金不足,购入的是石磨而非新式钢磨,所磨制的面粉销路呆滞,产品积压严重。1909年,他们果断决定,向往来钱庄借贷,拆去石磨,订购美国最新式粉机,改造茂新面粉厂,1910年初,新机安装完毕,生产能力增加3倍半,年产量增加了9倍,产品质量大为提高,销路转旺,伴随着生产效率和产量的大幅度提高,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逐渐在同行业中崭露头角。荣家兄弟尝到甜头,引进先进设备成为他们后来创办一系列面粉、棉纺织企业的一条惯例和一大法宝,新建企业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即便是租办、收购旧厂,也把更新改造技术设备放在首位,从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恒丰纱厂在饱尝设备陈旧之苦后,至聂云台经营时期开始大力采用新式设备,改蒸汽机为电力马达,拆去不合用的37寸旧钢丝车,买进20台40寸新型钢丝车,又将15000锭细纱车的罗拉、车头、钢领等换新。 经此技术改革,该厂不仅生产成本减低而且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至1915年,16支纱每天每锭产量由原来的0.5磅提高到0.9磅左右,棉纱品质也有很大改进,16支云鹤牌棉纱,成为上海纱布交易所的标准纱,棉布的产量也由每台每天1匹增加到2匹左右,企业整体效益大为改观,为该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紧紧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的创立者宋裴卿,在创办企业对外引进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经历。他看到英国“蜜蜂牌”“学士牌”毛线在市场十分畅销,遂拟仿制,从英国进口了一部纺制毛线的纺机,由于不谙毛纺技术,不期购进的是一部已淘汰的粗纺机,纺出的毛线没有弹力,根本无人问津。他于是资送其弟宋宇涵出国专攻毛纺技术,学成回国后即被委派出国购买机器,经过多方比较,宋宇涵以较低的价格从英国购买了两套性能尚佳、式样尚新的机器,安装试车一举成功,纺出100号、200号等四股、六股绒线,取得了价廉、优质之效。以后东亚始终把追求技术进步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抵羊”牌毛线能很快在竞争激烈的毛线市场站稳脚跟,并走向全国。
这一时期对外引进的渐趋成熟,还表现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采购,许多企业纷纷绕过洋行这一中间环节,走出国门,直接在国际市场购置机器。上海水泥厂对通过洋行购买还是出国订购,非常谨慎,董事会专门召开会议,反复讨论,最后一致认为“派人往外洋订购机器,是有种种利益”,为稳妥起见,采取两步棋的策略,“一面派马工程师及刘宝余先生出洋(德国)采办,先行开帐寄申,一面由公司派股东中熟识机器者,向各洋行探价开帐,同时股东会开议,决其取舍”〔12〕,最后经过价格、质量等方面的综合权衡,决定在德国直接向厂家订购。上海水泥厂的行为,表明以往引进设备依赖洋行的状况大为改观,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大大增强。
针对性强,目的明确,成效显著,是这一时期对外引进走向理性最集中的体现。中华煤球第一厂的成功创办颇能说明问题。当时上海居民还是用木柴稻草作燃料,煤球市场潜力很大,适有法商找刘鸿生解决煤屑过剩问题,刘鸿生除一部分用来制造水泥外,决定创办机制煤球厂。他邀请曾在汉阳铁厂担任工程师的同学黄锡恩参与筹备,派他赴日参观学习并购买机器。在赴日之前,黄先用煤屑和粘土试制煤球成功,但对能否用机器批量生产仍不敢盲目决断,于是把煤屑和粘土也带往日本,试制成功后才订购机器。由于原料与机器性能符合,投产后一举成功,“出品精良”,“销路大为畅旺”。〔13〕除了引进原料注意针对性外,引进人才也强调针对性。大中华橡胶厂薛福基拟办厂制造胶鞋,为从日本引进专业技术人员,特在日本登报公开招聘,通过与众多应聘者的广泛接触,最后决定在熬油、涂油这两个影响胶鞋质量的关键性技术环节引进外员,选中日本著名技师藤芳藏为技术顾问。结果,大中华所产的胶鞋不粘不裂不脱,鞋面光洁,完全可与日地钤牌胶鞋相媲美。
全方位引进是这一时期对外引进的一个鲜明特点。当时是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的时代,不仅传统行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新兴行业更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如化工、橡胶、卷烟、仪表、电灯制造等等,因此,对外引进不再局限于少数传统行业,而出现于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追求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成为企业家们努力奋斗的共同目标;先进的机器设备、优质的原材料、合理的生产工艺、科学的管理方法、有用的技术人才等等,都成了对外引进的内容。这一方面意味着工业化程度的深入和对外引进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进口仰赖程度的加剧。如西药制造业,在20年代以前,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进口外国原料、半成品加工合成。机器设备进自外国自不必说,五洲厂的双放式甘油蒸发装置是德国产品,片子机是美国出品,旋转式过滤机是瑞典货;中法厂的“三K牌”乳化机由德国制造,胶囊机产自美国;新亚厂的蒸馏机、磨粉机、制片机则从日本进口。制药用的原料,甚至淀粉等辅助材料,也都依赖进口,五洲厂所用的各种酸、钙、钠、钾等都是美国原料,柠檬酸亚铁是英国原料;中法厂的次亚磷酸钠、锌氧粉来自英国,淀粉酶购自美国;新亚厂进口的原料更达24种之多,进口国家有英、美、日、瑞士等。对当时制药工业现状,有人曾痛心地戏称:“中国药品原料,除黄浦江的水是国产品外,其余全部都是进口的”〔14〕。橡胶业的情形也与制药业相类似。据统计,上海橡胶业所用的27种原料,除原煤一项外,其余26种完全或主要依赖进口,直到30年代以后才有个别种类碳酸镁实现自给。但仰赖进口,提高了生产成本,而且进货时间、数量、质量也难以保证,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因此随着中国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国产化便成为一种时代要求,对外引进也在20年代后期进入新阶段。
三、对外引进与进口替代相互促进
近代中国的对外引进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跃上了新台阶,进入了对外引进与进口替代二者并举、相互促进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的对外引进十分强调引进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追求“价廉、优质、高效”的引进效果。典型的例子当首推1928年吴蕴初筹办天原化工厂。他首先向欧美有关化工设备的生产厂家发出一系列函电,询问设备价格、生产性能等,鉴于资金有限,最后以较低价格购进法国在越南开设的远东电化厂的全套设备,并聘该厂原总工程师白努尔(班纳)为工程师,负责设备安装、试车、试产及指导生产。厂方与之签订为期三年的合同,对其权利、义务、待遇、目标作了详细规定,合同第一条规定班纳的职责:“(一)将天原厂所用之机械及一切笼罩装置安妥;(二)制出烧碱、盐酸及漂白粉;(三)将工作上之一切效率及一切出品之纯粹度较准,使安全适合于标准数,此项标准数另行明细规定。”第八条规定班纳必须保证天原厂在一定期限内顺利出货,并严格规定了产品合格率、废品率以及电流效率、钠氯损失率、盐酸比重等各项技术指标。第九条规定“班纳于同时或以后自愿在上海区域内不再受中国人或外国人之委托担任同样之工作”。天原厂付给班钠上海通用银元一万元,分五期支付:合同签订日付两千元,机械完全装妥后付两千元,出货后付两千元,产品检验合格率达标后付两千元,最后“再照料工作两个月,俟一切妥帖再付最后之两千元”〔15〕。于此,天原厂在人才引进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明、成熟,洋务派“在我可收临阵无穷之用,在彼不致有临时挟制之虞”的良好愿望至此才得到了真正实现。1930年9月天原厂设备安装竣工,试产一举成功,经过调试改进, 产量质量稳中见升,1930年11月10日正式开工。天原厂的创建被公认为“一次成功的引进活动”。吴蕴初后来创办“天利”、“天盛”,对外引进也都非常成功。这使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对外引进水平在总体上有了显著提高。
对原材料的引进,这一时期也更趋成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重考虑进口原料与机器性能、产品品种相适应。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许多企业为了取得竞争优势,纷纷引进新式设备,开发新品种,如棉纺织业向以纺低支纱为主,织布也以粗布居多,我国的细纱、细布市场几乎全为英、日产品所独霸,日货尤多,利润很高,市场需求也大。为适应产品向高、细化发展,问津高档品市场,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申新纱厂、统益纱厂等民族棉纺织企业,纷纷引进细纱机、细织布机,从事高支纱的纺制,但国棉纤维短、弹性差,不适宜纺支数较高的棉纱,纺42支以上细纱必需使用优质外棉。由此,民族纺织企业并不一味坚持使用国棉,而果断地引进外棉,以使原料、机器、产品相一致,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30年代开始,民族棉纺企业使用外棉比重急剧上升,如永安纺织印染公司1928年国棉比重尚占88.74%,1930~1933年外棉比重急升至半数左右,1931年国棉仅占36.86 %,外棉高达60%以上。永安纺织印染公司生产的32支以上细支纱,不仅行销国内,还远销国外,与日本细纱相竞争。二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原料供求变动信息,大量购进优质价廉的外国原料,弥补国内生产不足。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内连年内战,许多农民纷纷弃耕避乱,1931年又遇特大洪灾,国内棉花大量减产,但国际市场棉花连年丰收,供应充足,“美棉、印棉……(国际)产量加增,于是执货者竞向市场贬价求售”,价格大跌特跌,1931年美棉每磅价格由“美金一角六分跌至六分,跌风之猛,突破从前记录”〔16〕。受此影响,中国棉花价格亦由每担45两跌至30两,但与美棉、印棉相比,仍属昂贵,于是各纱厂均大量购进低价美棉。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为“花贵纱贱”所困扰,制约了民族棉纺业的发展,而大量进口低价优质外棉,一度改变了花纱比价逆差,棉纺业随之出现短暂繁荣。利用国际供求变化,通过对外引进调节国内供应短缺,表明民族工业进入国际原料市场的能力大为提高。
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后,民族工业企业一方面在对外引进中越来越成熟,另一方面也逐渐认识到对外引进对后工业化国家虽然是必须的,但也有很多不利因素,如进口设备和原材料常常需时长久,缓不济急,甚至断档,生产往往难以正常进行;进口设备和原材料一般都价格昂贵,还要支付巨额运费、保险费和关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等等。对近代企业家们来说,实现国产化和进口替代,不仅仅是为了摆脱依赖,而且事涉民族利益,关系到民族工业全面健康的发展。企业家们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身到国产化的努力中,谱写了一曲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辉篇章。近代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最能说明这一时期设备国产化的情况。棉纺织设备国产化的努力,起步于20年代初,1921年中国铁工厂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家自制纺织机器工厂的诞生。1922年中国铁工厂正式开工,首先仿造日本最新式丰田自动织布机取得成功。继而又成功地制造出锭子、钢领圈、罗拉等纺织机主要零件,以前这些零件完全依赖进口,因磨损快,需要量大,而外货供应时常脱节。中国铁工厂建厂的宗旨,就是要结束中国纺织业被人卡住脖子的历史。惜开工之时,中国棉纺业正逢不景气时期,各厂都在收缩投资,铁工厂始因缺乏资金,继因产品缺乏出路随之陷入困境。20年代国产棉纺织设备,还只是零部件,至30年代大隆机器厂完成整套棉纺机器的制造,才标志着中国纺织机械制造出现质的飞跃。大隆创办于1902年,创办人严裕棠十分懂得企业发展离不开人才,除了向社会广泛延揽外,还先后把几个儿子送往美、日、德等国专攻纺织机械制造,20、30年代陆续回国。大隆能最先走向纺织机器专业生产并完成整套纺纺织机的制造,并不是偶然的。在制造整套纺织机以前,大隆试制过引擎、小农具,继而又成功地仿制了部分纺织机,由于国人迷信外货,轻视国货,产品无法打开销路,1925年租办苏纶纱厂,铁、棉联营,既为产品找到了出路,又为整套纺织机的制造奠定了基础。大隆接收苏纶纱厂后,并没有向国外订购新机,所有整修及所需机器均由大隆承担,出口天官牌纱,质地优良,成为上海交易所从事期货交易的筹码。严家接办的其他亏损厂如仁德、豫丰等依靠大隆的技术力量,也取得了经营成功。30年代随着严家子弟尤其是机械制造专家严庆龄学成回国,大隆的事业步入了一个新的里程。严庆龄主政大隆后,大事技术革新,工艺改革,至1937年终于成功地制造了整套棉纺机器,共有纺织厂用的各种机件50种之多。整套机器曾在上海市政府成立10周年纪念工业展览会上展出并作现场操作。大隆出品优良,逐步在用户中树立了声誉。1935年江阴利用纺织公司在致大隆的信中写道:“前向贵厂订购400 锭之大隆式大牵伸精纱机,自承装置完竣运转以来,历时已逾10月,其成绩优良,堪称国货机器中之翘楚。至于各部分机构之准确,车面之平衡,齿轮走声之低微,均与舶来品无分轩轾。且自开纺以来,所纺细纱条干均匀,生产量20支纱,每锭平均可出1.2磅以上……”〔17〕。抗战时期,大隆迁往租界, 改名泰利。上海棉纺织业在抗战时期一度畸形繁荣,纱布价格步步上升,对棉纺机器需求迫切,而外货进口困难,不得不求之于国货,泰利是当时唯一有能力制造整套纺机且技术水平最高的企业,因而产销两旺。从1937~1949年大隆(泰利)共生产了14万整套棉纺织机器。另外,实力雄厚的纺织厂也纷纷生产零件和部分纺织机,如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从1930年起开始制造纺机零件,后来逐步自制拼线车、筒子车,1936年向德国订购了一批精密的新型工作母机,准备着手制造全套纺织机器,装备工厂,扩展企业,曾制成精纺纱锭1万枚和梳棉机的大辊筒等, 不意太平洋战争爆发,从德国进口的精密母机和其他大部分主要机器被日人劫掠,自制全套纺织机器的计划从此成为泡影。
以上是设备国产化状况。原料国产化也在30年代大步发展,最能反映时代特征,也最令人钦敬的是国际前沿科学——基本化学工业原料酸碱的国产化进程。20世纪被喻为化学工业的时代,酸碱更被喻为工业之母,举凡玻璃、造纸、染料、有机合成、食品等都离不开它们作原料。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国内酸碱生产尚无人问津,必须仰赖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亚交通梗阻,进口渠道不畅,国内纯碱供应奇缺,碱价贵如黄金,独霸我国碱业销售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大获暴利。因洋碱供应短缺,致使我国上海、天津等一流通商口岸因买不到纯碱,许多工厂纷纷倒闭。目睹这种状况,早在东京留学时曾“摄像立誓”工业救国的范旭东,决心负起中国“化学先导”的使命,继创办久大精盐厂后,联合一批志同道合者于1919年在溏沽荒滩开始破土兴建永利碱厂。碱业制造是一项投资多、技术高、风险大的尖端产业,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制碱技术为苏尔维法,因碱业利润极高,又关系国计民生,欧美各国对制碱工艺实行严密技术封锁和垄断,不许外人参观,主要机器设备均由各碱厂自制,严禁流入市场。在对外引进技术、设备此路不通的情况下,范旭东和一代化学英才侯德榜以及陈调甫、孙学悟、李烛尘等,凭着拳拳爱国之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期间遇到了资金短缺、社会舆论攻击、外国公使作梗、试产失败等一系列的挫折,但他们以顽强的毅力,经过整整8 年的不懈奋斗, 终于取得了成功, 1926年6月29日,永利碱厂洁白的“红三角”纯碱终于问世,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1家用苏尔维法制碱的国家。永利碱厂也是世界上罕有的用海盐为原料的制碱工厂。海盐盐分低、苦卤芒硝成分甚高,与饱和的矿盐盐卤不能相提并论,一经氨化即生沉淀,堵塞管口,无法生产,永利碱厂技术人员通过反复探索,排除障碍,所出纯碱含炭酸钠99%,硫化钠不到0.001~0.002%,不溶化质含量仅0.02~0.04%,盐分低于0.6~0.8%,与“欧美用矿盐制者,绝无分别”。当年8月,在美国庆祝建国150周年费城万国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获金质奖, 被博览会评定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红三角”牌碱,从此享誉世界,洋碱霸占中国市场的时代结束了。“红三角”纯碱以优异的质量主动迎战卜内门公司碱的挑战,并在日本市场打垮“峨眉”牌。1932年又生产出烧碱、洁碱。永利的三碱(纯碱、烧碱、洁碱)大量用于国内民食和医药、造纸、染色、玻璃、肥皂、人造纤维等工业,中国第一座制碱工厂以雄伟英姿屹立于世界化学工业之林。1933年,范旭东这样写道:“我们在世界秘密中寻出一条路线,受尽工业技术上折磨和世界托拉斯的压迫与引诱,差辛还没有屈服。现在每年进口的洋碱由一百万担减至四十八万担了。”〔18〕这表明一半多的碱市场已由国产货所占领。但是,中国化学工业还缺少另一翼——酸。对于中国制酸工业,英、德都想染指,范旭东以百倍的勇气和努力,从外国人手中争回了中国化学工业的另一只翅膀。当时久大、永利事业正蒸蒸日上,创办硫酸铵厂,范旭东等于抢来一副沉重的苦担子往肩上放。他曾对陈调甫等人语重心长地说:“(把硫酸铵厂)从虎口夺回来,就国家全局上说,这当然是有重大意义,而就永利本身来说,简直可说是自讨苦吃。此时万一我们应付不得法,便可根本动摇。这并非危言耸听,有事实摆在眼前。在铵厂未出货以前,每年38.5万的利息和一切开支,都要这每天100 多吨的纯碱担负,这是已经成了铁案的。出货之后,还有外货倾销的压迫,不知要经过多少时候的奋斗,才能克服了。此外,筹备时期的一切负担,都要靠碱厂开支,在最近期中没有遇到外货倾销或意外打击就罢,否则就够头痛的。诸如此类,说不胜说,我们大家须要十分觉悟。”〔19〕经过艰苦的筹建工作,1937年2月5日,投资庞大、设备精良、工艺先进,称为“远东第一”的永利硫酸铵厂正式投产,生产出第一批硫酸铵,揭开了中国化学工业史上崭新的一页。其后,硫酸、硫酸铵、硝酸、液体阿摩尼亚等化工基本原料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望着这些产品,范旭东激动不已,自豪地说:“中国化工的另一只翅膀又生产出来,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不再受基本原料恐慌的限制了。”〔20〕
这一时期在人才方面也出现了替代引进现象,由国外引进转为招揽国内人才和注重企业自身培养。宁波通久源纺织厂1911年已“专用华人,自为经营”,努力摆脱对洋人的依赖。进入30年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不再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如天原化工厂1932年法国人班纳合同期满,从此不再使用外国人;上海水泥厂“技术事项向雇德工程师主管”,1931年德工程师汉谋解雇后,不再聘用外国人,而致力于“厂内人员之培养,与国内专才之罗致”,“洗往日专赖外人之弊”〔21〕,另聘电技工程师彭开煦和化学工程师徐宗涑主持技术工作,1936年董事会决定资派化验师丁继光赴德学习最新水泥制造技术,为期两年,学满回厂;信谊制药厂在德籍俄人霞飞博士1937年回国后,即转聘国内英才,留德药学教授潘正涛、留法化学博士林世瑾、医药博士毛守白、留美药学博士兰春霖等,先后被礼聘到厂主持原料、制剂生产和研制新产品,信谊制药厂还每年与各高等院校联系,要求保送优秀毕业生来厂工作,并资送青年技术骨干到法国深造;民族橡胶工业普遍聘用日本技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橡胶工业同业公会向全体同业发出五项倡议,其中第三条即是解雇日本技师,正泰、义生等橡胶厂纷纷登报声明,解雇日本技师,这既是抗日斗争的需要,也是人才替代引进的结果。
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外引进越来越强调引进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大大增强,无论设备的进口还是原料的采购,都能够实现廉价、优质、高效的引进质量和引进效益,能够实现设备、原料、产品三者之间性能配套,对引进的外国技术人员的管理也日趋成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民族企业也出现了消化引进、进口替代的趋势,民族企业家们以强烈的爱国热情进行了艰苦而顽强的国产化努力,大隆机器厂全套纺织机器的生产,永利碱厂和永利硫酸铵厂的建立以及碱、酸的出口,天原化工厂、上海水泥厂等一大批民族企业的弃用外人、专用华人,都表明民族工业在设备、原料、人才等方面的国产化能力大大提高,企业的发展进入了相对自主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近代民族工业的对外引进自民族工业发轫开始,贯穿于整个近代工业化过程,各个工业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在设备、原料、技术、人才等方面进行着对外引进,它们的起步和发展都离不开对外引进。19世纪60年代对外引进在懵懂中起步,但多盲目性、被动性和幼稚性,付出巨大的代价。20世纪以后,逐渐走向理性,开始追求引进设备的先进性,注意设备与原料之间性能的适应性,引进质量明显提高。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后,对外引进更为合理和科学,成效更为显著,同时,也出现进口替代趋势,国产化程度大大提高,对外引进与进口替代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外引进是后发展国家的必由之路,没有对外引进,就不可能有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对外引进对中国利用世界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人才,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等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外引进是以振兴民族工业为目标的国产化运动走向纵深的支点,借助对外引进,中国民族产品占领了一定的国内市场,挤占了部分国际市场,尤其在中、低档商品市场,民族产品取外货而代之,少数企业产品甚至问津高档品市场,与外货展开激烈的角逐,并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设备、原料、人才等不可能全部建立在对外引进的基础上,过分依赖进口,必然影响到民族工业独立自主、全面健康的持续发展,所以,随着对外引进的深入和发展,应该努力寻求进口替代,逐步实现国产化。如何提高对外引进的质量和效益,正确处理对外引进和进口替代的关系,这是后发展国家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回顾近代民族工业对外引进的历程,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
注释:
〔1〕由于经营管理经验、生产模式等弹性较大, 本文着重探讨的是设备、原料、人才的引进。
〔2〕具体参阅《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61年10 月第1版,第3辑:《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2版。
〔3〕〔4〕《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183、375页。
〔5〕《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49页。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1版,第527页。
〔7〕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中国政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8〕《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43~45页。
〔9〕《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 第24页。
〔10〕以上均引自《洋务运动》(八),第526~528页。
〔11〕《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283页。
〔12〕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13〕同上书,第223~235页。
〔14〕《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15〕上海市档案馆编:《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6页。
〔16〕《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中华书局1964年3月第1版, 第158~159页。
〔1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大隆机器厂的发生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页。
〔18〕《化工先导范旭东》,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11页。
〔19〕《范旭东传》,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168页。
〔20〕《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46页。
〔21〕《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89~90页。
标签:民族工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