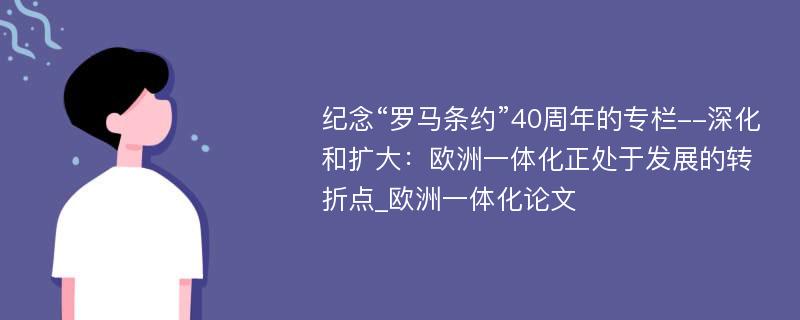
纪念罗马条约40周年专栏——深化与扩大:欧洲一体化处于发展的转折关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论文,欧洲论文,条约论文,关头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迎接1997年3月25日罗马条约签字四十周年之际,欧洲一体化正在攀登一个新的发展的巅峰:一方面,马约的生效与欧洲联盟的建立将欧洲一体化进程深化到了建设经济联盟与政治联盟的新阶段;另一方面,欧盟已着手规划它的另一次扩大,审议一大批中、东、南欧国家的加入申请。到下一世纪之初,其成员有可能增加至二十几个或甚至更多的国家。然而此深化与扩大进程也对欧洲一体化提出了一些极其严峻的挑战,欧盟当前不仅面临着如何实现上述宏伟目标的艰巨任务、还面临着调整欧洲一体化内部关系和改革欧盟体制以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要求的问题。欧盟在后一方面的动向虽说不如前一方面那样令人注目,而且常被单一货币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事务所掩盖,但或许是我们分析判断欧盟这次深化扩大过程乃至欧洲一体化发展趋势所必须予以挖掘的。本文拟就其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篇章的念头,一则引起国内同仁对此的讨论,二则纪念四十年前那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一、这次深化过程涉及到成员国向欧盟大范围让渡职能与权限,从而意味着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间的重新平衡。
就其本质而言,国家间的一体化可以认为是由群体(一体化组织)行为逐步取代个体(国家)行为的过程。因此,一体化的每一步进展必然意味着职能与权限由个体向群体的让渡和集中,阻断这种让渡和集中,也就阻断了一体化进程,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上,这个让渡和集中过程尽管相当艰难和曲折,但它的总体趋势应该说是十分明显的:从巴黎条约到罗马条约,继而到欧洲单一文件和到马约、欧洲一体化每前进一步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伴随着这种让渡和集中。而且应该说这是在符合成员国基本利益前提下,由各国自愿作出的让渡,欧洲一体化之所以继续存在和发展,现有成员国愿意留在其内并有不少国家在申请加入进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欧洲一体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体现了各成员国的基本利益,或者说它可以实现成员国单独所不能实现的利益。
在此前提下,一体化结构内和一体化过程中,由于个体间具体条件的不同和发展状况不一致,群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个体间又必然存在利益差异,反映为群体并不能完全满足(有时甚至还会排斥)个体的个别或特殊利益,而且在群体中又必然存在个体间利益与负担的分配不均。因此,在群体利益尚不足以完全包容和涵盖个体利益的情况下,各成员国显然还有凭借和伸张国家主权来维护本国利益的需要与倾向。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之间的这种争夺,同样表现得十分强烈,矛盾还不时激化为冲突,酿成其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欧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跃,经贸联盟计划将强化经济政策的协调、制订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实现成员国国民经济间的高度聚合,并最终以欧盟的单一货币取代各成员国的货币。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及开展民政与司法事务合作,更将一体化活动延伸到了非经济领域,触及国家主权中最为核心和敏感的一些部位。由于涉及到如此大范围的职能与权限让渡,在马约谈判中,如何维持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间的平衡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而争论的结果是两个妥协和折衷。
首先,在将经贸联盟确定为法定目标的同时,马约在罗马条约中写入了限定欧共体职能与权限的“辅从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共同体应在本条约赋予它的权力与指派予它的目标的限度内行事。
在不属于其专管的方面,共同体应根据辅从原则行动,即只有在和仅限于下述情况下:所拟行动的目标非成员国所能充分实现,且由于所拟行动的规模或影响,因此而最好由共同体来实现。
共同体的任何行动,均不得超越实现本条约目标所必需的程序。”(第38条)
对这个据说起自基督教教义的原则,已有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论述,欧盟委员会也专门发表了一份通讯,对它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见《欧洲共同体通报》1992年第12期)。概括起来,该原则包含了三层意义:第一款是对共同体行动的一般限定,可称之为“授权”原则,即共同体行动必须符合条约的授权并只是为了实现条约规定的目标;第二款是对共同体扩权的限定,可称为“必要”原则,即共同体向专管范围外拓展其行动必须满足其中规定的两个条件;第三款是对共同体扩权幅度与程度的限定,或可称为“强度”原则,即任何扩权仅以实现条约目标所需为限。此原则冠冕堂皇的目的是如马约第A条所说,“决策的作出应尽可能地贴近其公民”,而实际目的无非是要对欧共体的扩权制订一个标准,换句话说是要限制“布鲁塞尔怪物”对成员国主权无止无休的蚕食。
其次,在建立欧盟并将欧洲一体化活动向非经济领域大范围拓展的同时,马约在欧盟的体制上否决了更具“联邦”性质的“树形”结构,而选择了主要是“政府间”性质的“柱形”结构。这一结构的欧盟“屋顶”下,新拓展的两个一体化领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民政与司法事务合作——形成了相对独立于欧共体(经货联盟)事务的两根“支柱”,并配置了主要是“政府间”的决策与运行机制。这种选择表明,在不得已向欧盟让渡职能与权限的同时,成员国力图对这些职能与权限的行使加以严格控制,以维持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间的某种平衡。
作为交换的筹码,“辅从原则”与“柱形结构”可以说是成员国加在超国家权力头上的“紧箍咒”或“笼头”,而且是以限制发展和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由于欧共体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实现马约的既定目标而不是进一步拓展活动领域,辅从原则的作用与影响还没有充分展示的机会,但欧盟三年来的运转足已证明“柱形”结构是极其笨拙和低效的;它人为地将一体化活动在体制上割裂了开来,显然背离了建立欧盟这样一个总体结构的初衷。为此,在1996年3月开始的新一轮政府间会议的内外,有众多呼声主张将第二,第三“支柱”并入第一“支柱”,即对欧盟的各个领域实施委员会动议——理事会(在欧洲议会参与下)决策委员会执行的单一体制。
这种合并自然有助于增进欧洲一体化的整体性和总体性,并可以改善欧盟的决策效率,但它带有的政治含义恐怕是不少成员国还难以接受的。首先,这将意味着大大加强委员会与欧洲议会之类超国家机构的外交与安全、司法与民政等事务上的职能与权限,从而进一步消弱成员国对这些事务的控制权。其次,这还意味着欧盟迈出走向联邦体制的决定性一步。
欧洲一体结构内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间的平衡是个难摆的“宴席”:一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但一些成员国既要分享一体化的好处,却又不肯放弃本国的权力;二是“杯羹难分”,超国家权力的扩大必然意味着成员国权力的缩小;三是“众口难调”,参与的国家愈多,覆盖的利益愈广,平衡妥协的余地愈小。
在更深层次上分析,欧盟与成员国间在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上的争夺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迫使欧盟国家必须继续加强它们间的一体化。以联合的力量来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80年代后期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表明了这种发展态势。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间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发展的绝对不平衡又使得伸张国家利益与维护民族个性的民族主义不仅没有退缩,反而随着一体化的深入而表现得更加顽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两个同样明显的趋势看似相悖,却是对立统一,但迹象表明此矛盾的发展已接近临界点:一方面,欧盟经济一体化进展到目前的地步,成员国政府调节本国经济的职能已相当有限,而经货联盟的建成意味着经济决策将最终将由布鲁塞尔或其它什么地方来作出;另一方面,面对经济一体化的这种深层次发展以及冷战后时期欧洲局势的变化,形成一种能进行政治与安全决策的政治一体化结构,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已是势在必行。因此,如果成员国间无法在国家主权让渡问题上达成必要的共识并找一种能较好平衡这两种权力的新结构,马约目标的实现和这次深化与扩大过程的完成将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说得更严重些,欧洲一体化还可能因此止步不前,或甚至走向其反面。
二、实现这次深化与扩大过程还需对欧盟的决策机制、机构间的权力分配和相互关系作出必要的调整
作为整个欧盟体制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的欧共体体制,是在50年代为了在6国间实现一些有限的一体化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它是当时条件下六国妥协的产物,带有先天的不足,集中反映为决策效率低下和缺乏民主,在而后的年月中,这一体制虽经多次调整,但包括1986年的单一欧洲法令和1992年的马约,都只是修修补补,未能使它脱胎换骨却反而使这两大弊端更加积重难返,而如前面所述,马约的“柱形”结构还增添了欧盟决策政出多门的新问题和使总体效率更其低下的必然结果。因此,无论是已经老化的欧共体体制还是尚未定型的欧盟体制,都无法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挑战,必须进行重大的调整,而马约之所以特别规定要在1996年召开另一次政府间会议讨论机构体制改革,正是为了解决当时已经见到但无法了断的这个问题。
从技术上来看,欧共体决策效率低下是由于立法程序的繁复,但其根子在于成员国利益上的差异。同一项立法对不同的成员国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与负担,从而在理事会中引起分歧乃至冲突,并可能因某个成员国的异议或否决而搁浅。罗马条约为理事会决策制订了一种以特定多数议决的程序,并对此程度的实施范围作了十分明确的限定,其意就在于加速立法过程,但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即便在可以多数议决的场合,理事会仍习惯于尽可能地协商一致而避免强行表决。在欧共体这样的结构中采取这样做法的苦衷是不难理解的,它可以避免成员国间因过渡对立而造成分裂,但其代价是延缓了决策。为加速立法过程,委员会在起草提案时就得为平衡成员国间的利益煞费苦心,它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习惯做法是将好几项提案“绑”在一起成为必须同时通过的“揽子”计划,使各成员国在其中既有所得又有所失,得失至少能相抵,易于相互达成妥协。但如果说这个办法在利益差异较小的6国间还行之有效,在第一次扩大后已日显勉强,在将来利益差别悬殊的三十几个成员国间就根本行不通了。
如何提高欧共体决策效率是欧盟机构体制改革的中心课题,但从政府间会议台上台下的讨论来看,良策无多。现有的建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理事会内更多地使用特定多数议决程序,逐步达到凡属欧共体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均由特定多数或简单多数议决;二是控制委员会成员的人数,不使它随成员国增多而不断膨胀,保持其集体负责机构所必需的精干。这两个方面或许是维持欧共体决策最低程度有效性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前者是单一欧洲文件与马约已开始的一个渐进过程,这次可望有所继续,但恐怕还远达不到前面所说的地步。后者是下一次扩大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否则一个包括三十多来名成员的委员会将意味着瘫痪,但问题是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不愿改变委员会现时的组成办法,其他建议包括改变理事会主席的轮流坐庄的办法以增强它的能动作用,以及理事会在授权时给委员会更大的机动性以加速决策的贯彻等。
但正如前面已提到的那样,欧盟决策效率低下的症结并不在于它实施采取何种议事程序或甚至采取何种决策机制,而在于成员国间利益上的差异。为维护本国利益不至受损,各国首先是不愿轻易地让渡国家主权,不得已作出让渡时,则力图地从体制、机制与程序等方面对此权力的行使施加限制和控制,追溯欧共体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欧洲一体化的每个深化过程都伴随着权力重心从超国家机构向政府间机构的转移,从巴黎条约到罗马条约是委员会权力相对于高级机构的大大削弱,以及权力中心向理事会倾斜,关税同盟与共同农业政策方面运转前,经由欧洲理事会的特定多数议决程序和规定理事会与委员会间的关系准则,1966年的“卢森堡妥协”进一步削弱和限制了超国家权力的行使。70年代初期“欧洲政治合作”的引入和70年代后期“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则干脆采取了在欧共体体制外另立山头的做法,马约“柱形”结构的形成,也可以说是这一趋势的延续。所以,效率实在是欧洲一体化结构内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之争的牺牲品,是个解不开的死结。
欧共体一直背着“官僚政治”的恶名,其决策缺乏透明度和民主监督更使一向标榜民主的欧共体如芒刺在背。欧共体“民主赤字”的症结之一在于其唯一民选的机构欧洲议会并不具有议会通常享有的立法权,经单一欧洲法令的“合作程度”到马约的“共同决定”,欧洲议会目前所拥有的基本上还只是在一些经严格限定的事务上参与立法的权力,主要是与理事会不能就一立法提案取得一致时,可在—“调解委员会”内参与修改委员会提案,以及最终否决某些提案。随着一体化活动领域的不断延伸和职能的不断扩张,这种不民主显然会拉开欧洲一体化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加剧它业已相当严重的信用危机。欧共体另一个常受到指责的不民主现象是理事会决策的封闭性和不受任何监督,作为欧共体的主要决策机构,理事会是成员国政府间进行讨价还价和幕后交易的场所,其议事从来是关起门来进行的,而且除成文决议外,一切都秘而不宣,人们往往只能从决议的字里行间或各国政府事后的表态中揣度讨论的情况。在马约的“柱形”结构中,理事会作为各“支柱”决策机制中心环节和“支柱”间联系环节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这种不民主状况自然引起更大的关注。
在这次政府间会议上,扩大欧洲议会的权限,特别是赋予它立法和加强它的监督权,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并必须有所进展,但问题是欧洲议会的权力能扩大到何种地步呢?顺理成章的是给它以立法动议权,但这意味着侵削委员会的独占权力;委员会一向力主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然而一旦动到自己头上它就不见得会乐意了。再者,成员国似乎也不大会同意。一则各国政府对欧洲议会的评价普遍不高,认为它的言论与行动均显得轻浮而不负责(或许是因为它无责可负),担心给它权力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会进一步降低决策效率,二则在欧盟与成员国间,民主是个“零和博奕”:扩大欧盟一级的民主必然意味着削弱国家一级的民主。因此,如若不能找到一种可包容或缓解此矛盾的安排,则不但欧盟的“民主赤字”无法还清,两级民主机构间的冲突反而会加深和激化。另一方面,完全开放理事会议事,将成员国间的讨价还价暴露于众,只能有损于各国之间的关系。因此,理事会议事的开放恐怕也将是有限的,这次改革如能做到公开最初的辩论及最终的表决那就是很大的进步。
在欧盟的体制问题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50年代形式的那一套机构与机制已很难适应90年代后期欧盟的情况,更不用说预期中的扩大了。马约虽然为欧盟确定了一系列中近期目标,但没有能为它配置保证实现这些目标的体制与机制,而将此任务留给了这次政府间会议。从讨论情况来看,由于成员国间立场上的差异实在太大,迄今进展甚微,在欧盟这样的结构中,进度和标准从来是就低不就高,得过且过。因此对这次政府间会议所能达成的改革,也不宜期望过高。
三、实现这次深化与扩大过程还要求寻找一种既能保持欧洲一体化整体性,又能照顾成员国间差异性的组织形态与发展途径
这里所谓的“整体性”意指保存欧洲一体化的整体结构并维持大致间同步的进程,而“差异性”则是要顾及成员国对一体化的不同承受能力和接受程度。这是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扩大进程出现并逐渐突出起来的一对矛盾。70年代初欧共体由6国扩大为9国后,成员国间对一体化接受程度出现明显差距,表现为欧共体决策常常因为要容纳众多不同利益而变得更其困难,以及多数国家深化一体化进程的要求每每被个别国家的否决所阻断。为此,人们开始探索能适应此差距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当时曾出现了将成员国按不同条件或愿望组合成核心与外围的“双层共同体”(Two-Tier Community)主张,70年人后期着手第二次扩大时,大约是预见到欧共体内南与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势必增加决策难度和阻碍一体化的深化发展,又陆续出现了“双速欧洲”(Two-Speed Europe)、“可变几何欧洲”(Variable-Geometry Europe)、“差异欧洲”(Differentiated Europe)等设想。“双速欧洲”及其变体“多速欧洲”(Multi-Europe)认为欧洲一体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一定强求单一或同一速度,可以让具备条件和有此愿望的国家先行一步,而让其它国家在条件成熟后再跟进。“可变几何欧洲”主张在欧洲一体化的总体结构内,可以存在不同的组合和参与方式。“差异欧洲”则将上述两种构想结合了起来,建议视情况与条件许可,采取多样化的一体化组织形式和发展速度。虽说后来人们常将欧洲货币体系及尤里卡计划等引证为对此类设想的尝试。事实是它们严格地说还只是有关成员国间在欧共体结构外的多边安排,大约是因为担心接受此类安排意味着差异的体制化,从而危及欧洲“团结”,欧共体机构内虽有众多讨论,但官方舆论始终未正式首肯它们为可供选择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马约是欧洲一体化内部与外部局势发展的产物,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偶然性,但不管怎么说它都是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最为雄心勃勃的一次深化过程。由于它意味着一体化活动领域的大大拓宽和一体化程度的大大加深,成员国间在客观承受能力和主观接受程度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如果继续以往的做法,强求每个成员国接受全部目标而且大家齐步前进,马约首先不可能得到通过,通过了也难以得到贯彻。为实现所需的发展又照顾到个别成员国具体情况,马约不得不作出让步,在实施经货联盟第三阶段,“欧洲社会宪章”、共同防务政策、司法与民政事务合作等一系列较为敏感的方面,给某些成员国在参与程度和参与时间上某种选择的自由,从而在事实上接受了“差异欧洲”。
欧盟预期中的再次扩大,使得寻找一体化发展新模式变得更其迫切。这次扩大涉及接纳一大批中、东、南欧国家,它们与欧盟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结构、历史文化传统上的差别均将远超过现有成员国间。将所有这些国家绑在一起前进,可想象到的结果只能是“胖”的拖瘦,“瘦”的拖死,不要说马约的既定目标实现不了,连现有成果都恐怕难保。为此,引入和推行“差异欧洲”之类模式,已是舍我其谁的唯一选择了。
马约接受“差异欧洲”模式是对欧洲一体化结构内发展不平衡的承认,或许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国家之间因不同历史渊源和发展道路形成的不同民族个性、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生活习俗,这些差异不但不能抹杀甚至还得刻意维护和保护;它们的衍化是个长期的自然过程,强制趋同只能适得其反,成员国间还存在着发展差距和政策差异,并必然地反映为对一体化的不同承受能力和不同接受程度;这种差异只能通过有关各方自愿和自觉的调整努力,在发展过程中寻求缩小和消除。无视由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差异而强求一致或强行推进一体化,而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反而激化冲突并造成事实上的不一致和停顿。这种情况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它的历史危机也几乎都是这样发生的。
但另一方面,“差异欧洲”终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它带有很大的风险和难度。它的风险在于很难保证不同的组合和不同的速度不会长期化、扩大化和固定化,从而造成欧洲一体化最终在结构与体制上的分裂。这种风险又大大增加了寻找可行方案的难度,任何方案的可行与否首先将取决与它能否控制差异的“度”,使不同的组合继续保持在同一总体结构内,使不同的速度不至于将差距拉开到无法弥合的地步,如果不能明确界定此“度”,并找到能有效控制此“度”的措施,则“差异欧洲”很可能衍变成为任凭成员国各取所需的“菜单式欧洲”(Europe a la carte),久而久之使欧盟沦为图有虚名的空壳。此类方案的可行与否还将取决于能否被成员国所接受,特别是被“外围”或“后进”国家所接受,使它们不致产生失落感并具有跟进和动力。一种主张“差异欧洲”的观点认为,只要欧洲一体化结构能保持一个有高度凝聚力的核心,则成员国间即使拉开些距离或速度亦无伤大局。他们引证英国从拒绝参加到要求加入的转化为例,认为其间的关键就在于当时6国间的“团结”。从欧洲一体化的扩大历程来看,此观点不无道理。这样的一个核心确系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同样表明,维持6国团结的代价有时可以是很昂贵的;榜样的力量也不是万能的,还需有一定的措施和必要的投入来拖动“后进”跟上队伍,此外,现在的和进一步扩大后的欧盟与当时的6国欧共体已不可能同日而语,核心所需拖动的恐怕已超出它的力量范围。探索发展新模式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全新课题,“差异欧洲”与“多速欧洲”究竟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蹊径还是陷井,恐怕只能由实践和时间来证明。由于这事关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命运,欧盟在作抉择时必然十分小心谨慎,一条基本原则似乎是尽可能避免在体制上分成“核心”与“外围”。
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极其粗浅地从三个方面论及欧盟这次深化扩大过程对欧洲一体化内部关系的深刻影响(它所涉及的显然还包括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及欧洲一体化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也许仅此就可毫不夸张地说,世纪之交的欧洲一体化正处在一场空前深刻的变革或者说危机之中,这些关系的调整维系着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包括这次深化与扩大进程本身的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