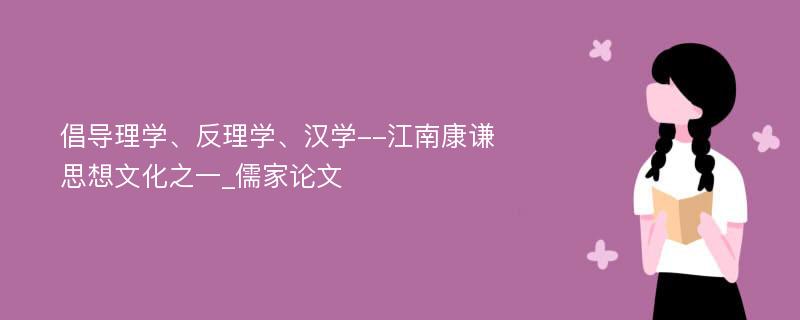
崇理学与反理学及汉学——康乾江南思想文化概略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理学论文,概略论文,江南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乾盛世,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各种文化思潮发展势头迅猛,撞击激烈;统治思想之钳制亦空前严密。这些特点于江南地区,表现得最为集中突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因此在盛世江南经济、文化发达的大背景下,产生各种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亦是地域思想文化之花结出的硕果。
一、崇理学与反理学
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与正统思想,自南宋以来,统治者皆视之为控制黎民思想的工具。有明一代,理学甚盛,故理学被称为“宋明理学”。明代前期二程与朱熹之地位极高,除孔孟之外,无与伦比。陈鼎云:“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广而大之,令儒臣辑五经四书及《性理全书》,颁布天下。”(注:《高攀龙传》,见《东林列传》卷二。)统治者对程朱理学之推崇可谓不遗余力。然理学自身亦并非铁板一块,早在朱熹倡导客观唯心主义理学观之时,即有陆九渊创立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观,与朱熹相抗衡。待到明代中叶,又有王阳明承“心学”之遗绪而发扬之,倡言“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观点,一时成为显学,程朱理学则盛极而衰。但陆、王心学于明末亦因其“空谈误国”而走向衰微。
清初战乱平息之后,统治者开始重视文治。在面临采用何种思想工具以巩固封建统治的选择时,乃钟情于程朱理学。如清圣祖康熙“夙好程朱,深谈性理,虽宿儒耆学,莫能窥测。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享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非后世所能及也”(注:昭梿:《啸亭杂录》。)。康熙帝对朱熹的地位如此抬高,对理学经典如此传播,关键在于他认为“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注:《清圣祖圣训》卷十二。),而且“非此(按:指《朱子全书》)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一家”(注:《御纂朱子全书》序。),即把朱子理学视为治国治民的万灵丹方。逮至乾隆帝同样极力崇尚程朱理学。因为御史谢济世注《四书》,多与朱子不合,且有诋毁朱子之语,乾隆帝即为之龙颜大怒,上谕云:
朕闻谢济世将伊所著经书,刻刊传播,多系自逞臆见,肆诋程朱。从来读书学道之人,贵乎躬行实践,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辨别异同。况古人著述既多,岂无一二可以指摘之处?以后人而议论前人,无论所见未必即当,即云当矣,试问于己之身心,有何益哉?我圣祖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而谢济世辈倡为异说,互相标榜。恐无知之人,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风之义,且足为人心学术之羞……尔等可寄信与湖广总督孙嘉淦,将谢世济书中,有显与程朱牴牾,或标榜他人之书,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注:《东华录》卷四。)
乾隆帝为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对批评程朱理学的思想言论严加制裁,则从反面说明了程朱理学乃统治阶级控制“人心”的法宝。
盛世最高统治者之尊崇理学,得到了一批所谓“理学名臣”的支持,他们推波助澜,更使程朱理学显“中兴”之势。
康熙朝初期有后升为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汤斌。此人师从理学家孙奇逢。孙奇逢的哲学思想是调停程朱、陆王两派。汤氏受其影响,于康熙八年(1669)与同道立志学会,建绘川学院,“所讲以身心性命纲常伦理为主,其书以四书、五经、孝经、小学,濂、洛、关、闽、金溪、河东、姚江诸大儒语录及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书为主”(注:《志学会约》,《汤文正公全集》。)。虽然他不废姚江王阳明心学,但其思想实乃以程朱派为主。汤氏门徒甚多,广有影响。
此外官至礼部尚书的“理学名臣”李光地,则只是崇奉程朱理学,“以濂、洛、关、闽为门径,以六经、四子为依归”(注:杨明时:《文贞李公光地墓碣》,《碑传集》卷十三。),著有《大学古本说》《中庸章段》《朱子礼纂》等理学研究著作,此人品格卑劣,曾贪功卖友(陈梦雷),属于“伪道学家”。他之崇理学乃是逢迎上意,曾吹捧“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自朱子以来至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无其殆将复起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注: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十三。)为康熙倡导程朱理学大吹喇叭。
康熙中后期至雍正初期则有被雍正帝称为“礼乐名臣”、官至雍正朝礼部尚书的张伯行。此人为官清廉,人品亦刚正不阿,是真理学家。张有《道学源流》《濂洛关闽集解》《伊洛渊源录》《性理正宗》等理学著作。张伯行独尊程朱之学,故抨击陆王心学,称“陆王之学不熄,程朱之学不明”(注:《张清恪公年谱》卷下,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于程朱理学思想,他尤其标举“主敬”观,所谓“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道莫大于体仁,学莫先于主敬”(注:唐鉴:《张孝先生》,《国朝学案小识》卷二。)。张伯行关心教育,在多处建立书院,并亲自讲学,对于程朱理学之宣传不遗余力。张伯行雍正三年(1725)二月十六日逝世前,在遗疏中还吁请雍正崇尚“正学”即理学,可见其于理学崇奉之至。
但是盛世的理学名臣并未对理学进行实质性的理论开拓发展,只是老调重弹而已,因此清代并未出现真正理学哲学的繁荣,亦未崛起卓有建树的理学大师。程朱理学与陆王理学发展到清代都已是明日黄花,表面的热闹掩盖不住内容的苍白空虚。清代毕竟是汉学的时代。
清代哲学真正具有见解的思想却是反理学的理论。
清代反理学思想并不自康乾盛世始,早在清代三大儒的著作中既已开反理学之先声。如顾炎武既对即阳明学派之讲“良知”,言心性,清谈误国,予以批判,谓“世之君子,苦博学明善之难,而乐夫一超顿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注:《答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六。),又抨击程朱理学,称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注:《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大力倡导经世致用,反对“口耳之学”(注:《亭林全集·与任钧衡》云:“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脱理实际,闭门修养。但顾氏于程朱理学的批评锋并不锐利,只“略加诽诋,亭林即自谦为‘僭’,不敢如其诽諆阳明之大胆敢言”(注:陈登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61页,东方出版中心1989年版。)。王夫之主张元气本体论,认为宇宙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物质实体,否定虚无之说,旨在“辟佛老而正人心”(注:《正蒙注·太和篇》。),此乃针对理学唯心之论而发。他批评陆王“屈圣人之言以附会之,说愈淫矣”(注:《正蒙注·神化篇》。),与佛教本质无异;又批“朱子之说反近于释氏灭尽之言,而与圣人之言异”(注:《正蒙注·神化篇》。)。在人性论上,王夫之标举“天理即在人欲中”,“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注:《读通鉴论》卷二十。),以批驳朱子“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黄宗羲哲学思想亦认为宇宙乃物质元气所充塞,而“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注:《薛敬轩学案》,《明儒学案》卷七。),为此批判程朱“理在气先”说,称“世儒分理气为二,而求理于气之先,遂坠佛氏障中”(注:《王南塘学案》,《明儒学案》卷二。)。三大儒多认识到程朱理学与佛老的唯心本质相同,可谓直捣黄龙之评。
但是真正对康熙朝理学泛滥进行拨乱反正,作出全面而激烈的批判的是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颜元堪称是清代反理学的重镇。
颜元年轻时先信奉陆王心学,后因读《性理大全》,又崇尚程朱理学。但他从康熙七年(1668)34岁为养祖母刘氏守丧期间开始发现“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侵淫,非正务也”(注: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崇理学思想已发生转变。康熙十二年(1673)39岁养祖父朱翁卒,他由河北蠡县养祖父家回到出生地河北博野县北杨村,继续参加农业劳动, 生产实践使他重视实用实行。 康熙三十年(1691)57岁南游中州,结交河南各地儒士,对程朱理学之为害有更深刻的认识,正如其所述:“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下士,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注:《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又称“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对程朱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
颜元批判理学,采用的是打鬼借助钟馗之法,即借圣人与孔孟之名攻击程朱,或曰将程朱之学置于孔孟之学的对立面,以剥去其“正统思想”的伪装。他指出程朱“与尧舜、周孔判然两家”,“孔孟、程朱判然两途”,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孟孔”。(注:《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这一批评方法自有其时代局限,但亦不必苛求。后来袁枚批判程朱理学亦同样采用了这一方法。
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本质上都是空谈心性、脱理实际的唯心主义哲学。颜元则继承了清初大儒经世致用的思想,又“尝躬耕畎亩之中,卖药开封之市”(注:《存学编》卷一。),身体力行,故针锋相对地倡导实学实行。钟陵《习斋言行录”卷下列颜元之论云:
今世之儒,非兼农圃,则必风鉴医人,否则无以为生。盖由汉、宋诸儒,误人于章句,复苦于帖括取士,而吾儒之道之业之术尽亡矣。若古之谋道者,则有礼、乐、射、御、书、数等业,可以了生。又见孔子委吏,简兮硕人,王良掌乘可见,后儒既无其业,而又大言道德,鄙小德而不为,真如僧道之不务生理者矣。在颜元心目中,真儒决非坐而论道、空谈道德心性,而不务生理的“僧道”之类,而是懂得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人,是具有经邦济世之实学的人。因此他批评程朱理学“以主敬致知为宗旨,以静坐读书为功夫,以讲论性命、天人为授受,以释经注传纂集书史为事业”,陆王心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去善去恶为格物,无事则闭目静坐,遇事则知行合一”。宋明理学只知“静坐”闭门思过,脱离实践,于世事无补,故颜元指斥理学“分毫无益于社稷民生,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注:《存性编》卷一。),一言以蔽之,空洞无用,从而揭出了理学的致命伤。
程朱理学还鼓吹“理在气先”、理是第一性的唯心“天理”观。颜元则坚持认为“理气融为一片”,理气不能割裂,“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注:《存性编》卷一。)气与理之间则以物质的气为根本,此乃唯物的理气观。
在人性论问题上,程朱理学基于其理气二元论,分人性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前者禀于天理,故善,后者禀于气质,故恶,因此要“存天理,去人欲”,以获得“善”。理善气恶说是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理论的根基。颜元持论与之截然相反。他既然主张理气合一,故认为“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注:《存性编》卷一。),气质是人的根本,而善恶是从属于气质的第二性的道德问题。他还强调,气质本善,并不恶,故反驳气恶说云:
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鸟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注:《存性编》卷一。)既然气质非恶,那么为何有些人却称气恶呢?此乃“引蔽习染”(注:《存性编》卷一。)所致,是后天环境影响造成的。颜元还认为,如果人的气质真是先天即恶的,则“未免不使人去其本无而使人憎其本有”(注:《存学编》卷一。),即将使人放纵所谓恶的先天本性,并视恶为合理的存在。这显然是荒谬的。当然,颜元以孟子的性善说批程朱的性恶说,仍未跳出唯心观的窠臼。
程朱理学家为抬高理学的地位,又大力宣扬“道统”之说。朱熹《中庸章句叙》说:“盖自上古圣人,继天立地,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注:《朱子文集》卷七六。)《信州州学大成殿》又记云:“熹惟国家稽古命祀,而礼先圣先师于学宫,盖将以明夫道之有统,使天下之学者,知皆有所响往而几及之。”(注:《朱子文集》卷八。)他显然是以承接“自尧舜以至于孔孟”,“自孟子以至于周、程”(注:《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堂记》,《朱子文集》卷八。)之道统自命,后人亦称“道统之传,终归朱子”(注:华希闳:《白鹿洞讲学录序》卷首。)。颜元对宋儒道统之说大不以为然。他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指出理学之所谓“道”,并非孔孟之道。理学的主张实际上属于释道之道。朱熹虽曾辩解云:“儒、释之间,盖有所谓毫厘之差者。”(注:黄宗羲:《明道学案》,《宋元学案》卷十三。)实际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二程之学亦出入佛老,“返求之六经而后得之”(注:《跋胡文定诗》,《朱子文集》卷八一。),本与老释有不解之缘。如理学之静坐修养说,以及禁欲观,与佛学教义本无二致。颜元正是以此为突破口,进攻“道统”之壁垒的:
……赵氏运中,纷纷跻孔子庙廷者,皆修辑注解之士,犹然章句也,皆高坐讲话之人,犹然清谈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气质本有恶。其与老氏以礼义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等为六贼者,相去几何也?故仆妄论宋儒:谓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则可;谓之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注:《习斋纪余》卷三。)此论将宋儒理学与周礼之儒学“正派”截然分开,道破其“集汉、晋释、道之大成”的唯心本质,从根本上否定了其所自诩的得道统之地位。
颜元继承者李塨哲学思想与其师笙馨相应,亦标举理气一元论,提出“气外无理”(注:《恽民族谱序》,《恕谷后集》卷二。),认为物质的气是首要的,理含于气中,此乃唯物的观点。又认为“理见于事”(注:《论语传注问》。),理表现在世事中。为此批判宋明理学空谈性理的唯心、无用论:
自宋有道学一派,列教曰“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诚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谈性天,捕风捉影,纂章句语录,而于兵农、礼乐、官职、地理、人事、沿革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文,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注:《论语传注问》。)李塨显然亦是从“用”即经世致用的立场出发,抨击理学之脱离实践、于世事无补的空洞说教。进而,他反对宋儒之“静坐”说,赞同颜元观点,主张“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注:冯辰:《恕谷年谱》卷二。袁枚:《宋儒论》,《小仓山序文集》卷十九,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颜、李虽然不是江南人,但对江南的反理学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故不能不论及。其后袁枚就公开站在颜李学派一边,赞同“我朝有颜、李者”对理学“侃侃然议之”即对理学的批判。其哲学思想乃是对颜李学派的继承与发扬。
乾隆时期江南反理学的骁将则为徽州府休宁县人戴震。他于自然宇宙观上提出“古人言道,恒该理气”说,“道”作为宇宙的本体,即包括物质性的气以及气之运动规律“理”,(注:戴震:《绪言》前言。)故又称“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注:《孟子字义疏证·天道》前言。)。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有理则有气”(注:《程氏粹言》卷二。),“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注:《朱子语类》卷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等本末倒置的唯心观,而且在道与理、气的关系上较颜、李有更全面的认识。
戴震反理学的主要贡献,是反对程朱将理学与封建政治、伦理挂钩,作为封建等级制度的桎梏。如理学鼓吹君臣之理、父子之理,以维护封建专治统治。戴氏认为“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矣”(注:《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古人所谓“理”,一是“明其区分”,如“肌理”、“腠理”、“文理”,是区分不同事物的概念;二是“以我之情洁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意谓合乎人情亦是“依乎天理”。而程朱之理乃“心之意见”(注:《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是一种主观心性,并不合乎客观与人情,以这种“理”来评判是非曲折,则要祸国殃民。
程朱理学最蛊惑人心的是倡导“存天理,去人欲”的伦理观,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视“天理”即“无欲”为真正的人性(注:朱熹云:“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见《朱子语类》卷十三。),而视“人欲”为罪恶的渊薮。这种理欲之分,“造成忍而残杀之具”(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旨在扼杀人的基本的物质与生理欲望,显然是一种僧侣主义、禁欲主义。戴震则针锋相对,指出人欲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它包括“声色嗅味”等饮食男女、穿衣吃饭的需求,是人用以营养“血气”而生存的必需条件,所以人欲非恶。相反,人欲只要合乎自然之道即为善,亦即是“理”,所谓“理者存于欲者也”(注:《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以此,反观程朱之“理”,就是残杀人性乃至人之肉体的工具: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注:《与某书》,《东原集》卷八,经韵楼本。)这是清代反理学的哲学家声讨程朱理学最犀利、最深刻的檄文,理学的本质被揭露无遗。
袁枚对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伦理观亦有类似批判,或许言词不如戴氏激烈,但精神并无二致。
二、汉学盛行与反汉学
理学发展至清代已是强驽之末,如江藩所说,理学“逮及明时,讲席遍天下,而东南尤甚,至本朝,其风衰矣”(注:《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清朝学术主潮或曰“清学”之出发点,乃“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清学取理学地位而代之。梁启超概括清学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治学方法,“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称‘汉学’”(注:《清代学术概论》第56页。)。而汉学之发祥地正在江南。
前述曾论及清初大儒黄宗羲、顾炎武发反理学先声,其实此二人亦开汉学之风气。江藩认为:“黄氏辟图书之谬,知《尚书》古文之伪;顾氏审古韵之微,补《左传》杜注之遗。能为举世不为之时,谓非毫杰之士耶?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二君实启之。”(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故将黄、顾二人附于《国朝汉学师承记》册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语,显然欲以“经学”即后之所谓“汉学”取代理学。黄宋羲云“南宋以后讲学家空谈性命,不论训诂,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所谓“论训诂”、“宗汉儒”与其所谓“以六经为根柢”(注: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二。)同义,即宗汉学。此外清初胡渭、阎若璩等皆为汉学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
汉学之真正确立主导地位而至兴盛,乃在乾嘉时期,期间形成了所谓乾嘉学派。最著名的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与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包括惠栋以及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皖派包括戴震以及乡里弟子金榜、程瑶、凌廷堪、胡匡衷、胡培翚、胡春乔等,以及京师弟子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此外京师权要纪昀、王昶、毕沅、阮元等亦倾心戴震。(注:参见《清代学术概论》第5页。 )阵容甚是强大,非理学家可比拟。
江藩称:“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注:《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惠氏为儒学世家。惠栋祖父周惕、父士奇皆宗经学,有此家学,惠栋更发扬光大之。惠栋自幼即博览经、史、诸子、百家。学问该恰,尤善校勘,精审典籍,于古书之真伪,滆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1750)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尹继善、黄廷桂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语。年五十后,专心经术,著有《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明堂大道录》《故尚书考》《后汉书补注》等,学术成果颇丰。钱大昕誉之为“先生所得尤深”,在汉儒之上。(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惠栋的治学重在考证,以复古为宗旨,其《九经古义·首述》所谓“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故梁启超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注:《清代学术概论》第29页。)惠氏于汉经师之古训尊奉如经,有盲从之嫌,故王引之批评惠栋“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注:《焦氏丛书》卷首手札。),堪称一针见血之论。惠氏崇汉学却不废宋学,惠士奇曾手书“六经尊服、郑,百法效程、朱”之联(注:《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上。),惠栋正是遵从此旨,因此惠氏吴派之汉学受到当朝统治阶级的青睐,广有影响,亦是理所当然的。
皖派戴震自幼即有怀疑精神,当塾师授之以《大学章句》右经一章,问其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曰:“此子朱子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曰:“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不能答。(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此种疑古精神与惠栎之从古意识自不可同日而语,实乃真正的清学时代精神,他论学云:
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注:《答郑用牧书》,《东原集》。)“不以人蔽己”,则“志存闻道,必空诸依傍”,对“汉儒训诂”亦要承认其“有师承”,要认识到其“有时亦傅会”,(注:见《与某书》,《东原集》。)不可不辨。“不以己自蔽”,则要“不知为不知”,于所见要“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可“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注:《与姚姬传书》,《东原集》。)则又表现出实事求是,追求“真知”的精神。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戴震之倡汉学,是以反理学为旨归的。其《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即已超出考证学范围而兼论义理,唐鉴称“先生本训诂家,欲讳其不知义理,特著《孟子字义疏证》以诋程朱”(注:《国朝学案小识》。),尽管语带讥讽,对此不以为然,但“诋程朱”则道出本质。可惜这部戴震自负为“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注:《东原集》卷首段玉裁序引。)的杰作却不为世所重。但其思想代表了时代进步的思潮,难能可贵。
戴震后学中与戴并称的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清学成绩亦甚卓著。如段氏之《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念孙之《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引之之《经义述闻》《经义释词》等,皆为清代学术之代表作,颇有见解,阮元评曰:“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注:《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115页。)
汉学之兴盛,甚至影响及诗坛,如经学家翁方纲等以考据为诗,连作诗亦如同训诂,而遭到袁枚的批判。由此可见,汉学之蔚成风气,非同一般。
汉学盛极而衰,于道咸之后终于走向衰落,既有其时代原因,亦有其自身原因。其实汉学于启蒙期与全盛期即已暴露出自身致命伤。但作为学术主潮,汉学在乾嘉以前很少遭到非议。具有反潮流精神对汉学进行批判的有识之士,可谓凤毛麟角。
但有识之士毕竟还有。批判汉学考据的学者首推颜元,他既反理学,又反汉学,陈登原称其“非特宋明以来之理学而反之,即当时新兴之考据学,亦一举而反之。颜学之所以其后不昌者在是,颜学之所以资人兴仰者,亦是欤”(注:《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115页。)。 颜元之反汉学考据,乃基于其主张“实”与“习”及“有用”的实践观。在颜元看来,无论理学还是汉学都是“只以多读书为博学,是第一义已误,又何暇计问思辨行也”(注:《存学编》卷一。),是“纸墨之功多”、“习行之精力少也”(注:《习斋年谱》卷下。)。因此他不满汉学启蒙者顾炎武之“手不舍书”,黄宗羲之“乘夜丹铅”,恶其“玩物”而“丧行”(注:见《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第118页。)。 他进而认为“汉之滥觞,宋之理学,皆伪儒也,必不得已,宁使汉儒行世,犹虚七而实三”(注:《习斋纪余》卷九。),所谓“伪儒”即“口头见道,笔头见道”(注:锺陵:《习斋纪余·叙》。),满足于寻章摘句之学,仍脱离实际,为痛误苍生之原。颜元弟子李塨同样既反理学,亦反汉学,称“汉儒之于圣学,驿使也;宋儒,使改换公文者也”(注:《颜氏学记》卷七。),“驿使”谓其于学只是传递而不能启用也。又称“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注:《颜氏学记》卷七。),与其师桴鼓相应。
颜学尽管“其后不昌”,但并未完全中绝。袁枚之反理学,固然是承继颜学;其反汉学,亦未尝不承继颜学。与颜元相比,袁枚在汉学全盛之时仍公开反潮流、反汉学,其胆识更加非凡。
顺便应提及的是反汉学者还有桐城派。如姚鼐屡为文诋汉学破碎,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恶、戴所学,不遗余力。(注:《清代学术概论》第61~62页。)尽管切中了汉学若干弊端,但其出发点是为程朱理学辩护,为已衰落的程朱理学张目,宗旨与颜、李、袁截然不同。
应该承认,汉学考据在古籍的校注和辨伪,佚书的辑佚,旧史的考证改写和补充等等方面,确实成绩巨大,亦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它是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学人“避触时忌,聊以自藏”(注:《清代学术概论》第64页。)的结果。汉学终于逐渐远离经世致用的正轨,而对其进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标签: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理学论文; 清代学术概论论文; 国朝汉学师承记论文; 读书论文; 孟子论文; 国学论文; 程朱理学论文; 人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