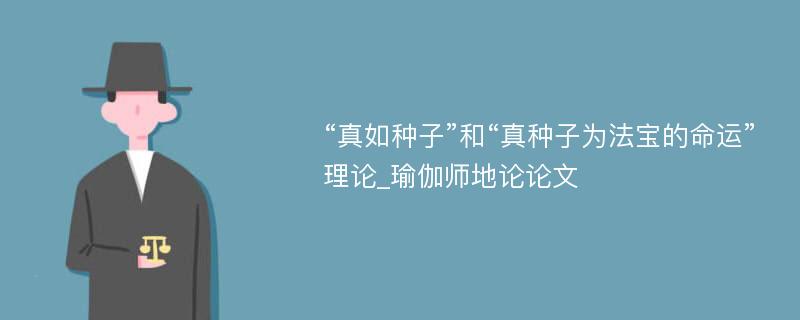
法宝的“真如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如论文,种子论文,法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912(2008)-01-0052-09
佛教追求的目标是超脱烦恼、获得觉悟、成就涅槃,而觉悟的原因或根据何在,是佛教思想家一直关心的问题。唐代的玄奘译出瑜伽行派的重要著作《瑜伽师地论》和《成唯识论》之后,“种子”说成为解释觉悟的原因和根据的重要理论范式。不变众生因为具有获得觉悟、成就涅槃的种子,所以通过修行就可以最终超脱种种烦恼,证得佛果。但“种子”概念在上述两部著作中的说法和内涵又是不一致的,具体地说,《瑜伽师地论》中的“种子”称为“真如所缘缘种子”,而《成唯识论》中的“种子”则称为“法尔无漏种子”。这两部著作被翻译出来的当时,围绕这两种“种子”的性质等问题,在坚持唯识学派立场的慧沼(650—714)与受到《涅槃经》等影响的法宝(627—705)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本文拟以法宝对“真如所缘缘种子”与“法尔无漏种子”的解释为中心,对法宝的佛性思想及其在佛性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做一探讨。
一、“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
在佛教中,“种子”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杂阿含》等经典①。根据这些经典的说法,众生的身口意行为所造成的业力就像“种子”,可以带来种种善恶的果报。在大乘瑜伽行派经典中,种子说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表述诸法存在的根据和发生原因的概念。其中,表述诸法存在根据的“种子”(bīja)即真如,又称为“种性”(gotra)、“界”(dhātu)、“性”(prakrti)等,如《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的“种子”说即指诸法的“基体”②。而表述诸法发生原因的“种子”则主要表达烦恼“种子”。如《菩萨地持经》“真实义品”中,“自性”被视为现在世的现象存在生起的根源,而“自性”之所以能够生起一切现象,在于存在概念分别③。而在《瑜伽师地论》的“摄抉择分中五识身相应地意地之二”中则形成了作为“种子”的“遍计自性妄执习气”的概念[1](589)。
“遍计自性妄执习气”的概念与原始佛教以来作为善恶一切法根据的“种子”说,在内涵上已经是大异其趣了。也就是说,“种子”由中性的概念变为否定性的概念。它被规定为源于对本质的执著的残留习气,这意味着它成为解释一切染污法或世间法的缘起的概念范式。而出世间法因为其常住性、普遍性和清净性,与“种子”的生灭性、各别性和染污性直接矛盾,用“种子”概念说明出世间法的根源就遇到了困难。正是为了解决出世间法的存在根据或发生根源问题,《瑜伽师地论》提出了“真如所缘缘种子”说:
复次我当略说安立种子。云何略说安立种子。谓于阿赖耶识中。一切诸法遍计自性妄执习气。是名安立种子。然此习气是实物有。是世俗有。望彼诸法不可定说异不异相。犹如真如。即此亦名遍行麁重。问若此习气摄一切种子。复名遍行麁重者。诸出世间法从何种子生。若言麁重自性种子为种子生。不应道理。答诸出世间法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非彼习气积集种子所生。[1](589)
即作为“遍计自性妄执习气”的“种子”虽然解决了作为“实物有”、“世俗有”的世间诸法的发生根源,但出世间法因为与世间法在性质上根本不同,所以从逻辑上讲,出世间法不应该由“习气积集种子”所生。《瑜伽师地论》提出出世间法的根源应该是“真如所缘缘种子”。所缘缘,即它既是所缘(认识的对象),同时又是所缘得以发起的根据,真如作为一切万法的真理和存在根据,被称为所缘缘。
但这一汉语复合词可以有两种读法,即A:作为真如、所缘缘的种子;B:以真如为所缘缘的种子。两种解读的区别在于,前者把真如直接理解为种子,而后者则仅仅把真如视为种子产生的“所缘缘”。那么,《瑜伽师地论》提出的“真如所缘缘种子”的内涵是A还是B呢④?
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美国的山部能宜教授主张A说,即真如=所缘缘=种子。其主要理由为,在《瑜伽师地论》的上述引用文之下,还有以下问答:
问:若非习气积集种子所生者,何因缘故,建立三种般涅槃、法种性差别补特伽罗,及建立不般涅槃法种性补特伽罗?所以者何?一切皆有真如所缘缘故。
答:由有障无障差别故。若于通达真如所缘缘中。有毕竟障种子者。建立为不般涅槃法种性补特伽罗。若不尔者。建立为般涅槃法种性补特伽罗。[1](589上)
据此,山部教授认为文中出现的“真如所缘缘”与上文出现的“真如所缘缘种子”从上下文的语气看,应该是指同一个概念,即都是指“真如所缘缘种子”,而既然后文中明确提出“一切皆有真如所缘缘”,那就意味着一切皆有“真如所缘缘种子”。这种普遍存在于一切众生的“种子”只能是真如。从而得出结论:真如=所缘缘=种子⑤。
但对于这段问答,松本史郎教授则做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即“真如所缘缘”与上文出现的“真如所缘缘种子”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真如所缘缘”即真如=所缘缘,是一切众生皆有的,而“真如所缘缘种子”作为“通达真如所缘缘”,即对于真如这一所缘缘的认识则只存在于特定众生之中,具体地说即只存在于有种性者之中。那些具有“毕竟障种子”者则没有“真如所缘缘种子”。松本史郎由此得出结论:真如=所缘缘≠种子。
如果单纯从《瑜伽师地论》汉语译文的逻辑分析,“真如所缘缘”与“真如所缘缘种子”确实意义不同,而且从整段文字看,正是为了说明二者的不同,《瑜伽师地论》才导入了“障”的概念,即因为有“毕竟障”的存在,所以有些众生虽有“真如所缘缘”,而无“真如所缘缘种子”,因而不能般涅槃。从这个意义上说,松本史郎的结论更具有合理性。
实际上,根据中国法相宗思想家对《瑜伽师地论》的注释可知,在印度,关于“真如所缘缘种子”的内涵和性质本来就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说法。例如,中国法相宗的实际创始人窥基法师在《瑜伽师地论略纂》中云:
又由决择分世第一法。缘真如教法为所缘故。以此为因缘种子。生见道智。即说世第一法。名真如所缘缘种子。以缘教法影像真如。修习为缘故。言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此是胜军论师义。即以此文故。言一切皆从新熏成。护月释云。其自身中本有无漏种。由在解脱分等位中缘教法故。名真如所缘缘。当于此时旧种遂增。由本有种故。得入解脱分位。又入见道时。由前已习缘真如观。今得成熟。缘着真如。真如即是所缘缘。本有无漏之种。乃能生此现行智果。由缘真如为境。种方生现行故。言真如所缘缘种子生。[2](184中-185上)
可见,在胜军和护月之间,围绕着“真如所缘缘种子”是“本有”还是“新熏”存在着分歧。即胜军认为以真如、教法为所缘缘(认识对象)新产生的种子(见道智之种)为“真如所缘缘种子”;而护月则认为以真如为所缘缘、本有的无漏种子现行而形成无漏之果时,此本有无漏的种子称为“真如所缘缘种子”。
按照瑜伽行派的说法,真如作为无为法是凝然不动的,所以胜军所说的“从新熏成”者,是产生“见道智”的“种子”,而非真如。而护月的本有说,也是指“本有无漏之种”,而非真如。所以无论是胜军的新熏说还是护月的本有说,都认为真如是“所缘缘”而非直接形成出世间法的“亲因缘”。
另外,在《瑜伽师地论》的“摄抉择分”中的“菩萨地”,有“真如唯所缘缘摄”[3](697下),即在因缘、增上缘、等无间缘和所缘缘等四缘中,真如是而且仅仅是“所缘缘”。《瑜伽师地论》还有“真如非因”[3](698中)的说法。由此可见,《瑜伽师地论》明确否定了真如作为能生的因缘种子的可能性。“真如所缘缘种子”,至少在《瑜伽师地论》中应该理解为以真如为所缘缘的种子(tathatā=ālambana-pratyaya≠bīja),而不能理解为真如即所缘缘即种子。
但《瑜伽师地论》与其他许多大乘佛教的著作一样,是一部由不同时期完成的诸多部分构成的合集,所以各部分之间并不总是有严格的逻辑一贯性。如在“菩萨地”中,虽然明确肯定“真如非因”,但在论述“十因”说时,在讲“种子”是缘起(杂染法)的牵引因、生起因时,同样讲到种性是清净法的牵引因和生起因,中间没有进行任何区分[3](747下23-24)。而且,在《瑜伽师地论》第八十卷论述“转依”部分,有“此转依,真如清净所显,真如种性,真如种子,真如集成”[4](747下)。这里的“真如种子”就其字面含义来说,可以解释为“真如=种子”。由于这段话提供了真如与种子之间关系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所以它成为“一乘”论者以真如解释种子的重要经典依据,也成为与“三乘”论者争论的焦点之一⑥。
二、法宝对“真如所缘缘种子”的理解
1.“真如种子”与“真如所缘缘种子”
首先,对于《瑜伽师地论》的“诸出世间法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生。非彼习气积集种子所生”,法宝从真如缘起的立场做了诠释:
此同《大般若》云,真如虽生诸法,真如不生。又云,一切圣者戒定智品,从此性生。亦同《华严经》“清净甚深智,如来性中生”。[5]
在这里,法宝将真如与“真如所缘缘种子”等同,将诸出世间法从真如所缘缘种子直接理解为真如生诸法。法宝将“真如所缘缘种子”与出世间法的关系,置换为真如与诸法的关系,故意淡化了瑜伽行派的论说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种子”。本来,在《瑜伽师地论》中,真如并不直接与出世间法发生关系,而是作为所缘缘间接地参与出世间的生起,其关系可以表述为真如……种子→出世间法。而法宝的解释则简化为真如=种子→出世间法。
这从视真如为凝然不动的存在、否定真如为万法生起因的瑜伽行派的立场⑦看,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故慧沼在《能显中边慧日论》中反驳法宝云:
既说真如名为法性,即是法身,何能令生。又云:
此说真如出诸法者,为增上缘。非亲因缘出生诸法。然如不生,是增上缘生。若一如生万德,何有定异因。[6](426中)
即作为无始无终、无染无净的无为法的真如,只能作为诸法生起的增上缘,而不能成为“亲因缘”。真如与诸法的关系是“所依”与“能依”的关系,而非生成论意义上的“所成”与“能成”的关系。用《决定藏论》的说法⑧,真如只能是诸法的“依因”,即存在的根据,而非作为生起根源的“生因”。如果把真如视为诸法的“生因”,就会遇到一因生多果的问题。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真如=种子”说会受到瑜伽行派的诟病,法宝进一步引用《涅槃经》和《瑜伽师地论》的说法作为经证,论证己说的合理性:
若以是真如故不得名种子,何故涅槃经说第一义空为种子邪。又瑜伽论等云,种及界性,名异体同。因何许是,佛性不许邪。[5](395)
《涅槃经》中确实提到佛性为“第一义空”⑨,也提到“佛性种子”⑩之说,但并没有直接提到“第一义空”为“种子”。不过《涅槃经》从“第一义空”的立场出发理解、诠释佛性和种子的意趣,是与法宝的“真如种子”说有相通之处的。即都从“本性”的立场出发论证佛智、佛果的根源,而不是单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界定“种子”以及“种子”与佛果的关系。这也是《瑜伽师地论》将“种子”与“界”、“性”等视为同一层次的概念的主旨相通。
但应该注意的是,法宝与批判者慧沼等的不同,除了对“种子”概念的界定相异之外,关于“种子(真如)”与诸法关系的理解也完全不同。具体地说,法宝虽然讲真如生诸法,但这里所说的“生”,并不是瑜伽行派所说的“种子”生诸法之“生”。“真如生诸法”,是说真如是诸法存在的根据,是一切诸法的所缘缘、增上缘。真如并非如“种子”般直接作为诸法生起的“亲因缘”。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真如虽生诸法,真如不生”。说到底,真如生诸法,只是为了说明真如与诸法之间依存关系的一种方便说法,或者说一种譬喻。这里的“生”是一种虚指,而非实指。如果认为法宝所说的真如之“生”等同于“种子”之“生”,就是对法宝的一种误读或误解(11)。
2.关于“法尔无漏种子”
与《瑜伽师地论》的“真如所缘缘种子”相类似的概念,是《成唯识论》的“法尔无漏种子”概念。在瑜伽行派的思想体系中,真如是一切存在的根据,而“种子”则是生起诸法的直接原因。如何把二者统一起来,特别是将出世间诸法的“因缘”与“所缘缘”统一起来,成为唯识学派的重要课题。
《成唯识论》卷二在对印度的“分别论者”(心性本净说)进行批判时云,“心”如果是空理(真如)则无作用,如果是心本身则是有漏法,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不可能成为觉悟的原因。其结论为“由此应信,有诸有情无始时来,有无漏种,不由熏习,法尔成就”[7](08下-09上)。可见,瑜伽行派提出“无漏种子”说是与对“心性本净”说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成唯识论》卷二在解释《瑜伽师地论》的“地狱成就三无漏根”时云:
又瑜伽说地狱成就三无漏根。是种非现。又从无始辗转传来法尔所得本性住性。由此等证无漏种子,法尔本有,不从熏生。[7](08中)
《成唯识论》此处的“无漏种子,法尔本有”成为中国法相宗的“法尔无漏种子”和“本有无漏种子”的出处和依据。这里的“法尔”是自然、不假作为之义,即无始无终、天然本具,与“本有”是同一内涵。《成唯识论》又云“依障建立种性差别者,意显无漏种子有无”、“故由无漏种子有无,障有可断不可断义”[7](08下)等。可见,《成唯识论》提出“无漏种子”的概念,是为了说明真如的遍在性与众生五性差别之间的矛盾。即虽然众生皆依真如而存在,皆由于无漏种子的有无,众生的烦恼障和所知障有可断有不可断,所以众生才有五性差别。
“无漏种子”作为连接真如与出世间法的中介概念,与“真如所缘缘种子”的内涵几乎相同。它具有两方面内涵:其一是无漏性,因而可以成为出世间法的种子;其二是“本有”或“法尔本有”,因而不是新熏而成。
如前所述,在胜军和护月之间,围绕着“真如所缘缘种子”是本有还是新熏,存在着分歧。在《成唯识论》中,二者得到更清晰的表述,本有说被规定为“一切种子皆本性有,不从熏生。由熏习力,但可增长”;而新熏说则为“种子皆熏故生。所熏能熏俱无始有。故诸种子无始成就。种子既是习气异名,习气必由熏习而有”[7](08上-08下)。新熏说主张无漏种子由闻熏习而生,种性差别决定于二障(烦恼障·所知障)的有无,从这一立场出发,不承认“本有无漏种子”的存在。
如上所述,《瑜伽师地论》的“真如所缘缘种子”
在解释真如与种子的关系方面,存在着模糊空间。《成唯识论》提出“无漏种子”的概念或许是为了消除这种模糊性和歧义性。但如果按照“本有说”的说法,此种子也属于“本性”所有,仍然存在着“有为法”的种子如何存在于“无为法”的本性中的问题。所以法宝反对本有说,其主张与“熏习说”相接近。如在“六初无漏因”中,在引用了《摄论》、《释论》和《涅槃经》之后云:
佛教即是后得智相,以无漏教。此闻熏习,与有漏相违。渐令前前有漏渐灭,于后后念无漏渐生,非有漏中有无漏性。[5](461-463)
即作为无漏法的后得智是由“闻熏习”而得,是逐渐增长而生,非于有漏法中本有无漏种子。
法宝又云:
待闻熏习以为因缘,圣道方生。无一经说有漏之中别有有为无漏,以为因缘,生其圣道。[5](476-477)
如上所述,法宝以“真如种子”解释“真如所缘缘种子”,实际上是否定了唯识学派从“缘真如所得智”的角度把握“种子”的范式,将“种子”义消解、吸纳到了真如概念中。这意味着将“种子”生诸法的发生学的问题归结成了真如生诸法的存在论问题。但,如此以来,真如与诸出世间法之间就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就难以说明诸出世间法如何发生,以及真如这一平等法为什么会表现出诸种差别法来。
法宝于是采纳《摄大乘论》等提出的“闻熏习”的概念,试图对“种子”说进行改造,提出一套佛智发生学的新范式。即真如与出世间法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逻辑问题,不能靠概念作中介,由真如直接推导出出世间法。由真如到佛智、佛果的过程是一个佛教实践即“闻熏习”的过程。无论引入“真如所缘缘种子”还是“法尔无漏种子”,都不能解决作为无为法的真如如何生起有为法的问题,唯有依靠“闻熏习”的修行实践,有漏才会渐灭、无漏才会渐增。在进入见道位,真如自然表现为佛智、佛果。
由此出发,法宝强调三乘的差异不是“本性”中存在的差异,而是由后天的行为所决定的(12)。法宝还对“法尔本有种子”做了新的阐释:
由此,久远先习种子,对其近习者亦可名为本有种子,然非法尔。[5](461-463)
即相对于当下由“闻熏习”得到的种子,过去久远以来熏习而得的种子,可以暂且称为“本有”,但这种“本有”并不是“本性”中所具有之义,而是指在时间序列中居前而已,它仍然是有为法,是需要“闻熏习”而得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宝虽然有条件地肯定“本有”概念,但却明确反对“法尔”概念。这样,在法宝这里,“本有种子”就不是“本性”具有的无漏种子,而是从久远以来通过“闻熏习”的实践得到的清净种子。
三、“真如所缘缘种子”与法宝的佛性说
法宝对“真如所缘缘种子”的解说,是与其佛性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真如所缘缘种子”说是瑜伽行派提出的探讨成佛的根据和过程的理论范式,那么法宝对这一概念的再解释,就彰显了法宝佛性说的理论特质。
1.“本性”与“客性”
佛性一般指成佛的根据和可能性,自从《涅槃经》译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几乎成为佛教界的共有理念。但“皆有佛性”只是一种理论的假设,它不能说明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现实中众生在境界上会有种种差别,甚至还存在似乎没有任何成佛希望的极恶众生。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佛教提出了诸如“本性住性”·“习所成种性”(13)、“性种性”·“习种性”[8](888中)、“理佛性”·“行佛性”、“本性”·“客性”等范畴,力图在理论上解决这一矛盾。即众生普遍具有的只是“本性住种性”(“性种性”)、“理佛性”和“本性”,而众生在现实中的种种差别源于修行善法所得不同。
法宝最为服膺的《菩萨善戒经》在论述“本性”、“客性”概念时云:
云何名性。性有二种。一者本性。二者客性。言本性者,阴界六入,次第相续,无始无终,法性自尔,是名本性。言客性者,谓所修集一切善法得菩萨性,是名客性。[9](962下)
“本性”即众生本来具有的佛性,一切众生平等具有;而“客性”则非众生本来具有,而是后天闻熏习而产生。法宝对“有为无漏种子”的判释,就是从“本性”俱有的立场出发的。
准此理教,善戒经等本性即是真如,平等而有,无别有为无漏种子、众生有无不同。声闻地中,以远,客性与本合说。随转理门,就其客性,说本性有无。以六种无性之相非决定故。善戒经以其本性,与客合说。[5](310-313)
在法宝看来,“本性”即真如,平等存在于一切众生之中。在真如的层面上,对众生来说不存在“有为无漏种子”的问题。在经论之中虽然也说到“本性”有无,但这是就“客性”而说“本性”,因为只有“客性”才有有无问题,“本性”是一切皆有的。
应该注意的是,法宝在这里否定的“有为无漏种子”,即作为“有为法”的“无漏种子”。而法宝自己主张的“真如种子”(包括后面提到的“无漏智种子”)则是“无为法”种子。《成唯识论》在论及作为“有为法”的种子时曾从六个方面界定“种子”,此即“种子六义”(14)。另外,作为熏习种子的所熏,也有四义(15)。法宝估计到反对者会以“种子六义”等反驳他的“真如种子”,故从“本性”和“客性”的不同,对两种“种子”做了区分:
若以违种子六义刹那灭等故,不说名种者,法尔种子亦不是与能熏相应熏成,何得名种。故知,六义种子,唯说有为,四义所熏,唯说客性,非本性也。[5](399-400)
在法宝看来,与能熏相应所熏成的“种子”是有生有灭、有始有终的“有为法”,属于修习所得的“客性”,而真如等“种子”则属于“无为法”,属于先天本具、遍在一切的“本性”。既然瑜伽行派也不排斥“法尔种子”的概念,自然也应该理解“真如种子”等概念。
2.一切皆有佛性与五性差别
《瑜伽师地论》虽然提出了“真如所缘缘种子”说,似乎解决了所谓出世间法的生起问题,但仍然存在“真如所缘缘”皆有而五性差别的问题。《瑜伽师地论》提出烦恼障、所知障的二障说,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问:若非习气积集种子所生者,何因缘故,建立三种般涅槃法、种性差别补特伽罗,及建立不般涅槃法种性补特伽罗?所以者何?一切皆有真如所缘缘故。
答:由有障无障差别故。若于通达真如所缘缘中,有毕竟障种子者,建立为不般涅槃法种性补特伽罗。若不尔者,建立为般涅槃法种性补特伽罗。若有毕竟所知障种子布在所依、非烦恼障种子者,于彼一分建立声闻种性补特伽罗,一分建立独觉种性补特伽罗。若不尔者,建立如来种性补特伽罗。是故无过。[1](589上-中)
依照《瑜伽师地论》的说法,有性、无性的差别源于众生所具有的障碍种子。如果这种障碍种子永远存在,那就是无涅槃种性,反之则是有涅槃种性。而在声闻、独觉、如来五性中,声闻、独觉源于永远存在的所知障种子,而如来则是消除了所知障种子者。如此一来,众生皆有“真如所缘缘”就与五性差别的存在不相矛盾。
对《瑜伽师地论》的说法,《成唯识论》认为众生种性的差别固然是由于障碍种子的有无,而障碍种子的有无又决定于“无漏智种子”的有无。这样,《成唯识论》将二障的有无问题转换成了“无漏智种子”的有无问题。即有此“无漏智种子”则二障可断,没有此无漏智种子则二障不可断。
对于这种解释,法宝表达了不同的立场:
此释违文瑜伽。若障种有无由智种者,即真如所缘缘一切有故,即是智种一切有。智种一切有故,即合障种一切可断。因何障种有断不可断也。[5](405-407)
在法宝看来,因为“真如所缘缘”即是真如,而真如即是无漏智种子,所以真如一切皆有,就意味着无漏智种子一切皆有。而无漏智种子一切皆有,则说明众生皆可断除二障种子。
可见,法宝与瑜伽学派的分歧,仍然在于如何理解和界定“真如所缘缘”。瑜伽学派将它界定为有为法的无漏种子,所以随众生的根器不同,此无漏种子有无不同。而法宝以真如界定“真如所缘缘”和“无漏智种子”,主张真如=“真如所缘缘”=“无漏智种子”。从这一立场出发,“真如所缘缘”和“无漏智种子”就被视为无为法,无生无灭,遍在一切众生之中。因为众生皆有“无漏智种子”,结论当然就是众生皆可断除烦恼、所知二障,皆可得般涅槃。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宝作为一乘论者的立场。
四、结论
讨论佛果的根据和缘由,可以有两条路径:一是从“本性”的立场出发,探讨其终极的存在依据,这就是“真如”说;二是从“客性”的立场出发,探讨其发生的机理和过程,这就是“种子”说。从“本性”的立场出发,因为“真如”的遍在性,会导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结论;而从“客性”的立场出发,由于众生现实的烦恼障和所知障的存在,则五性各别说成为当然的结论。
在肯定“真如”作为“本性”佛性的立场上,法宝和慧沼等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慧沼等对法宝以“真如种子”解释“真如所缘缘种子”的批判,更多是因为没有注意到法宝“真如种子”的“种子”的譬喻用法,没有注意到法宝所说的“真如生诸法”的“生”是“真如不生”。而法宝明确否定“法尔无漏种子”,并不是否定瑜伽行派的“种子”说本身,而是法宝欲将此“种子”严格界定为由熏习产生的“客性”佛性。法宝并不是如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只是站在“一切皆有”的立场反对“五性各别”,而是主张通过对佛性的“本性”、“客性”的严格区分,从不同的范式出发理解“一切皆有”和“五性各别”。法宝之所以不赞成“真如所缘缘种子”和“无漏种子”这两个概念,在于这两个概念模糊了佛性的“本性”和“客性”的界限。这种混淆表现在佛教的修行实践上,则容易把五性的差别归于众生“法尔本有种子”的有无,进而将这种差别固定化。
法宝做出这种判释,与当时佛教界的状况以及法宝本身的佛性论立场分不开。玄奘将瑜伽行派的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以后,人们意识到这一崭新的论说与旧有经论的说法之间存在着相互抵牾、甚至相互矛盾之处。特别是在此之前译出的《涅槃经》提出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理念已经成为佛教界的主流理念,而瑜伽行派则认为三乘佛性有别,甚至有一类众生(一阐提)没有佛性,这就对旧说提出了巨大挑战。于是那些熟悉旧有经论、又有机会接触到玄奘新说者,或者对新说提出质疑,或者试图去会通二者(16)。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瑜伽行派的佛性说逐渐与中国本土的佛性说合流,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
法宝虽然参与了玄奘的译场,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但在参与玄奘的译经活动之前,法宝就已经是著名的学者,特别是对《涅槃经》有深入研究,曾著《涅槃经疏》,服膺《涅槃经》一佛乘的基本立场。法宝的这种立场使得他在面对和接受瑜伽行派的思想时,不是无批判地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鉴别,有所取舍,这与玄奘、窥基等的立场是有很大差异的。法宝对《瑜伽师地论》“真如所缘缘种子”的解释,一方面在“客性”的立场上肯定“五性各别”说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本性”的立场确定了《涅槃经》一系“一切皆有”的正当性。并力图通过“闻熏习”的修行实践将两种看似对立的命题统一起来。
但由于“种子”一词已经在瑜伽行派获得清晰的界定,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公共概念,所以法宝对“种子”的再定义,特别是“真如种子”的说法具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在理论争论中,如果争论双方在基本概念上不能首先达成共识,就可能造成聋子对话,使争论偏离问题的实质。法宝的佛性论不断受到诟病的原因,既有批判者对他的立论的误解,也有他本人对“种子”等概念界定上的模糊。但法宝面对作为显学的唯识学的炽盛,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吸收改造新的唯识学的要素,从新的角度论证一佛乘的合理性,显示出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
注释:
①如《别译杂阿含经》卷三“譬如下种子,随种得果报。汝今种苦子,后必还自受”。《大正藏》卷2、388下。
②《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一“问,此种性名有何差别。答,或名种子,或名为界,或名为性,是名差别”。《大正藏》卷30、395下。
③《菩萨地持经》卷一“有性者,建立施设假名自性。久远已来世间计着,一切忆想虚妄根本。所谓是色是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地水火风色声香味触法乃至涅槃。如是世间假名有自性法,是名为有”。《大正藏》卷30、893上。
④据日裔美国印度学者山部能宜的研究,“真如所缘缘种子”的梵文原文应为tathatālambanapratyayabīja。这一复合词,从梵文文法上看,也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即A:作为真如、所缘缘的种子(tathatā=ālambana-pratyaya=bīja)以及B:以真如为所縁縁的种子(tathatā=ālambanapratyaya≠bīja。见山部能宜“真如所縁縁種子につぃこ”《日本の仏教と文化-北畠典生教授還歴記念集》、永田文昌堂1990版63-87页。
⑤见山部能宜“真如所縁縁種子にっぃこ”,同上。另,德国的施密特豪森教授也持此说。
⑥日本的源信(942-1017)在《一乘要诀》中云:“问。沼公难云,若即真如为种能生,应但云从真如种子生出世法。何须云真如缘缘种子生(已上)。此义云何。答。第八十只云真如种性,真如种子(云云)”。源信以《瑜伽师地论》第八十卷的“真如种子”为经证,反驳慧沼对法宝“真如种子”说的批判。《大正藏》卷74、365下。
⑦“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谓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即是湛然不虚妄义”。
⑧“阿摩罗识,作圣道依因,不作生因”。《大正藏》卷30、1020中。
⑨“师子吼品”云“佛性者名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智慧”。
⑩“我身即有佛性种子。若说无我。凡夫当谓一切佛法悉无有我。智者应当分别无我假名不实”。《大正藏》卷12、651上。
(11)这种误解不仅存在于慧沼等法宝同时代的思想家之中,也存在于现代的大多数研究者之中。如常盘大定在《佛性》中云“法宝的解释,虽然在一乘家中颇有权威,公平来看,却有以一乘家义裁剪文意、强以真如为种子之感”。《佛性》515-516。末木文美士亦云“法宝将‘真如所缘缘种子’理解为真如自体可以作为种子而作用”。《平安初期佛教研究》,第798页。
(12)“准此经文(《密严经》)故知,三乘种性因十业有”,《一乘佛性究竟论》卷4、339。
(13)“云何种性,谓略有二种。一本性住种性,二习所成种性”。《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大正藏》卷30、478下。
(14)“然種子羲略有六種。一刹那滅。……二果俱有。……三恒随轉。……四性决定。……五待緣。……六引自果”。《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09中。
(15)“何等名為所熏四羲。一堅住性。……二無記性。……三可熏性。……四與能熏共和合性”。同上。
(16)日本最澄的《法华秀句》记载,在法宝之前,就有沙门灵润,造“一卷章”,从十四个方面分析了玄奘新译经典的教义与旧经论之间的区别。《传教大师全集》卷3、154页。
(17)《宋高僧传》卷四“释法宝亦三藏奘法师学法之弟子也”。《大正藏》卷50、727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