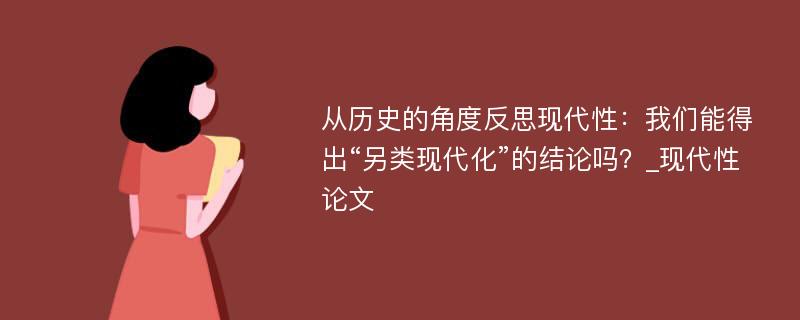
从历史角度反思现代性:能得到“另类现代性”的结论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结论论文,角度论文,另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149-04
我将以亚洲各社会为例,从历史角度来提出对诸种“另类现代性”的批判。我以为,“另类现代性”这个思想的意义在于挑战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性概念,但随着近年来这个词在学术和政治圈中逐渐流行,它也面临批判。下文第一部分就要揭示个中原因。而造成这一术语流行的圜局、使它前所未有地受关注的圜局,也对现代性及其历史带来至关紧要的新问题,为何如此?我会随后论及。
我认为,“现代性”这个概念足够包容新近彰显的历史复杂性,但我们以前理解的“现代性”概念要实现这一包容,就需要重新加以改造。在它前面加上一个形容词“另类的”,有着重要的反霸权意图。但它忽视了一点:尽管这些新的“另类”是对全球霸权加以重塑后的产物,但依旧陷于早期现代性的霸权假设之中。同样,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它也侧重于研究和解释非常政治化和概念化的现代性后果。为了伸张这些领域中有着持续的文化身份,现代性的历史化往往伴随着昭示“他性”的历史的具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其历史意义是与本次旨在于跨区域互动的“全球性交换关系”讨论会的其他指导原则相背离的。①这样,用一个形容词来肯定现代,就分散了人们对现代史基本问题的注意力。相反,现在需要的是把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不一定非得抛弃,而是加以重新思考,以便切合我们对其历史和现状的不断变动的理解。
诸种“另类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基本问题在于,与这些另类相对的“现代性”是什么不清楚,或者如卫腊富(Ralph Weber)在最近的一次讨论中所说的,“现代性”是什么东西的“现代性”?[1]最近的用法常把诸种“现代性”这个思想理解为文化,且最显著的用法是用来指各个非西方社会,也就是声称这些社会特定的文化遗产需要不同于欧美的现代性道路,而在此以前唯有后者提供了现代性的各种标准。对“现代性”的这个“文化转向”需要加以更为严格而批判性的审查,甚于其倡导者或者其批判者所进行的审查。其倡导者对当代文化有一个差异崇拜的倾向,而其批判者则因其抽去现代性的一切实质内容而简单地消解这个转向。诸种“另类现代性”与有亲缘关系的诸种“复合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概念一样,不过是现代性中另一危机的症状:这就是伴随其全球化而来的危机。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术语是否有助于理解这个危机,或竟提供更为模糊和难于捉摸的解释?这不仅是抽象的知识路径,而且也是深刻的政治路径和意识形态路径。
我认为“另类现代性”的思想是不证自明的,但在细微的意义上,即现代化尚未导致这些社会复制那个本身即是一个虚构抽象(an imaginary abstraction)的西方模式,则需要论证。另一方面,对“另类现代性”的各种诉求,就其不能探讨现代性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在差异持续之外还有何他性卷涉其中而言,它们即便不是空洞的,也是非常成问题的。相反,对另类现代性的诉求,其意义在别处:此即断言不同社会有定义现代性的权力。欧美的傲慢在于认定现代化必须遵从西化的路子,因此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一问题现在是以折射文化诉求式的诸种“另类现代性”来表达,为什么这些诉求大受欢迎而成为全球性话语的一部分,包括早先声称独占现代性的那些社会在内皆是如此。塑造现代性以及我们对其复杂性加以理解的,乃是另类性诉求之具有这样的力量,而远不是有关文化差异的模棱两可的证据,和文化差异可能对现代性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无论不同社会之间有着何种变动不居的差异,我们都需要解释我们现在和过去在理解差异和对待差异的态度上的各种差异。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各种文化标准,而且要考虑转变全球性权力的配置。这一转变既与现代性的过去有关,也与其现状和将来有关。
单就积累学术证据来说,要说明最近对现代性种种问题的重新表述都会很难。我认为问题刚好相反: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发生转型后,也要求有一个恰适的历史来解释转型后的认知。这一认知曾经引导我们重新发现新的证据,或者让我们熟知的东西重新充满活力。为了从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霸权中拯救现代性,我们要欢迎这一做法,但它并非没有陷阱。诸种“另类现代性”这一思想只要依旧系于现代民族和文明范畴,便会具有各种反霸权的意涵,也开启了史学狭隘主义之路,带着自身的霸权意涵,鼓励其他中心主义。注意到这个困境是书写过去的前提,这样会避免早先的各种霸权和压力,以专注于为全球性身份政治提供服务。这需要重新思考过去,不只是把过去当作某种现代政治身份的源泉,而且是把过去当作各种探讨人类身份问题的源泉。
一、诸种另类现代性
随着全球化上升为历史研究和解释的范式,诸种“另类现代性”思想广为流行。其启示显然是当代才有的,因为是现代性的全球化为挑战欧洲中心版本的现代化提供了力量。现代化越是作为带着逻辑普适性和欲求普适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获得全球认可,似乎对其基本的历史假设的抗拒就越大,因为这一假设认为,现代性是欧洲历史的独特产物,它一经产生,就毫无例外地为所有社会的未来指明了道路。“另类现代性”挑战这一欧美中心主义目的论,认为有其他的现代性轨迹。用杜波依斯出色的辩证术语来说,这个现代性“双重意识”大概可以说成是全球现代性的条件,现代性正在展开新的阶段,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同时通过号召差异特别是文化差异而导向碎片化。
“另类现代性”的各个概念前提至少是在表面上相对直接。首先,确认现代性是一个有着普世诉求的全球存在,没有这一点要谈“另类性”就几无意义。用某本该主题文集的编辑的话说,“用‘另类现代性’来思考,就是承认现代性是无法避免的,就是阻止思考终结现代性……现在,现代性无处不在。”[2]我们可以加上一句,“无处不在”也意味着一无所在,因此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但不仅于此。
其次,现代性在各地皆意味着同一个事或展示相同的特征,“另类性”是针对于此而出现的。但这并非来自其无处不在的特征。现代性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圜局中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这些圜局把现代性同化或“翻译”到该圜局中,并因其影响而发生转变。也正是在现代性的本质之中,因其对持续变迁的承诺而无尽地从过去、现在和将来产生出新的现代性。用卫雷蒙(Raymond Williams)所说的文化变迁术语来说,现代性的宰制因残余和突现之持续地交互作用而成为可能,也因此受其制约。[3]“另类”这一形容词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原初的欧美模式相参照的,但也易于用来指过去和现在的其他的现代性。由此,欧美模式可能不再作为标准来衡量现代性,而仅仅是作为“另类”之一。这是查迪皮(Dipesh Chakrabarty)常为人所引用的“把欧洲省级化”[4]这个术语所指涉的意涵。
第三点随之而来。现代性是与不同的文化实践协调一致的。这可能如其经常意味的那样,现代性是“无文化的”,可以用于不同的文化遗产。如蒲卡乐(Carl Pletsch)30年前提出的那样,这就是现代化话语,把现代化看作是从传统(文化)走向由科技理性所统治的现代性,并因此意味着无文化。②这曾在南半球国家(the Global South)以现代性作为“技术”的工具化处理方式中得到回应,中国坚持区分“体”(substance)和“用”(function),以前者指本土价值,后者指现代性实践,也呼应了这一点。③这也同样并经常意味着虽然有一个现代性文化,但它在所有时候都是复杂文化环境的一部分。不是现代性文化驱使其竞争者消失,而是在不同文化的互动之中产生出新的文化现代性。这曾经是后殖民批判主义者坚持把“杂交”(hybridization)作为文化过程,以及坚持其亲缘性观念文化翻译或“翻译的文化”时的一个共同主题。[5]也正是杂交这个概念使拉布诺(Bruno Latour)提出了“我们从未曾现代”的论断。[6]
这个术语的三个意涵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明显,而当代各个社会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也很明显,所以上述这一切都可能是再明显不过。随着现代性在全球纵横交错,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出复杂的互动,上述这些就是现代性的意涵。
它们在什么意义上是另类的?对谁来说那是另类的?很明显,诸种“另类现代性”在走向差异的意愿之外可能意味着什么?其空间所指和时段所指为何?这一思想为何走向意识前沿?什么时候走向意识前沿?这些都得到广泛的关注,穿越了那些发展的分水岭,并采取了文化转向。如果我们为差异问题引入一个伦理的维度,这些问题就会更为复杂:所有的差异都是人们所想要的吗?在缺乏作为普世原则、能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范式的情况下,由谁来做出决定?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主要困境,正如在各个社会中乃至全球政治最高层中许多争争吵吵所显现的那样。
从分析的角度来说,一个基本的问题涉及“另类现代性”中时空指涉的模糊性,这一模糊性来自于其作为一个概念而进行的广泛而不同的展布。这些展布从坚实的“文化特殊性和植根于该地点”对现代性的解读,到将现代性高度抽象地等同于各民族和文明空间。④从纵列来看,这些用法提示我们,就现代性的空间性来说,在“另类”之中有“另类”,这一提示也受到标识现代性历史特征的冲突所支持。现代性空间,即其社会性、文化性乃至政治性空间,更进一步因各种矛盾而千疮百孔,因地方的、国家的、文明的和全球性的对现代性的不同诉求而冲突,也因不同阶级观念、性别观念、族群观念、城乡区隔观念等而导致的不同社会空间的冲突,已经明显是千疮百孔了。
诸种“另类现代性”的空间如此,其时间也差不多。这里的辩论展现出很宽广的寻求他性的理由:从遭遇现代性时他性的历史性出现,到断言各种蔑视历史的文化之间存在类似永恒目的论的差异。用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来说,历史辩论似乎是最普通的辩论:他性乃是特定历史圜局中现代性过程的产物。这个辩论是反对现代化话语中传统和现代性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这个话语把现代性看作是功能整合的整体,把二者的关系看作是零和(zero-sum)关系。⑤在极端上,这个辩论抓住了土著空间里的现代性,它只有在服务于传统时才能得到理解。在一部199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政治学训练出身的土耳其现任外交部长认为,各伊斯兰社会有必要实行另类现代性,因为他们的各种文化在目的论上就不同于欧美的那些社会。这一辩论的极端版本曾由中国人表达过,他们似乎相信中国性(Chineseness)是基因禀赋的。⑥这些差异也明显造就了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以及对于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问题的不同取径,它们处于非常当代的现代性矛盾之源。最明显的,乃是自由派或左派多元文化主义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安置到文化政治议程中的“文明的冲突”这两个矛盾之源。另一方面,就它们给予文化持续性(以及其极端文化主义)的分量而言,我们很容易把它们与从政治和社会认知角度出发去寻找的诸种另类现代性区分开来。后者从1980年代以来遭受严重倒退,尽管依旧没有从极端性思维阵营中消失。例子之一即哈迪(Hardt)和纳格李(Negri)所提议的“改造—现代性”(alter-modernity)概念,这个概念在大众进行全球性斗争,反对各个地方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反民主政治时,强调各个人类主体的文化翻新。[7]
时间性问题尚有另一个维度,与批判地评价“另类现代性”诉求有关。未来可能是留给现代性更不用说诸种另类现代性去处理的,但有关诸种“另类现代性”的话语极少涉及未来。它提示的各种另类未来是反对现代化话语之目的论的,这与其同时重新肯定全球性相违。其对未来提出的文化和历史诉求,遭受到与现代性自身一样的不稳定性。在当前世界以各种文化和民族混合日益强化为特征的情况下,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我们时代所理解的差异可能会重新塑造,并造就新的团结和区隔。“另类现代性”的各种空间将安置在哪里呢?其他性本质又会是什么?我们可以就现状和过去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出诸种“另类现代性”的人更接近于他们与之另类的人,还是更接近于他们认为有着同样文化身份的国民或同一文明的人?很显然,就我们所关注的和有关历史与现代性观念的知识取向方面而言,尽管我们与会的各位来自不同的民族和知识背景,但所分享的文化空间,即远比上一代历史学家们所分享的要一致得多。
现代性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即是寄居于其上的瞬时性(transiency),对我来说,另类现代性这一思想也遭受同样的瞬时性。因此,另类现代性最好理解为现代性的产物,这现代性自身仍然易于产生各种新的现代性,其他性最重要的来自于与过去一直被当作是普适现代性模式的想象性欧美现代性模式有着明确的不同。各种欧美现代性也是历史性的,也没有提供单一模式,尤其是当我们超越正式的体制而去看日常文化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另类现代性话语对各种另类现代性之相互关系也缄默不语。用这些另类现代性术语来认知的这个世界,有多少种另类现代性呢?它们之间关系的本质又是什么?另类现代性这个思想常常把我们带回到全球组织的现有构型中去,特别是民族—国家的构型中去。民族—国家是其看好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单位,更不用说是文化的所在单位了。如果它成功地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观念,对它所期待的未来之路线远无助益,而很可能是各种新霸权行将就世。有趣的是,所有这些另类现代性共同的一点,是欧美各个社会全球化了的霸权现代性,而在现代性将民族—国家正式作为人类普适的政治组织形式之外,这些另类现代性殊少有提示。人们假定现代性所正式化的民族—国家,“其自身内部有一个机制去衡量文化差异,并将赋予这些差异以道德意义。”[8]即便是以文明的名义提出诉求时,情形依旧如此。正如以伊斯兰遗产为诉求的各个社会中民族和普世共同体之间的矛盾雄辩地揭示的那样,这些现代性诉求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眼光和民族追求的调制。
各社会之间的差异一直很明显,各社会过去为实现现代性时,这种差异导致成功的程度有不同,也正是这种差异成了把这些社会放在进化序列上不同位置的标准。这种情况对于努力发现相对于现代性的另类路径来说,也同样存在。这个术语或可能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各地与现代性相距的想法,则如同现代性自身的历史一样古老,尽管在土著或外国学者所写的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中心论进化史学中,这个想法常常因其“保守性”而遭到消解或边缘化。⑦正如中国的例子表明的那样,绝大多数社会最初对现代性的技术感兴趣是为了保卫本土价值,而这个态度从没有消失过。就我所注意到的例子来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把现代化当作是西方化而是当作“当代化”(contemporanization),这个意涵也恰好是“现代的”这个词的一个基本意思。“现代的”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指的是最近,新的,和与时俱进的(up-to-date),以区别于古代。⑧创造一个当代的但属于本土的“新文化”,一直是绝大多数社会从遭遇现代性以来就普遍存在的考虑。另一方面,各种另类方案并非总是以文化的术语来体现,这在上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但也在许多对立运动的抱负中最为明显不过。须知这些运动都致力于寻找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类方案。
实际上,无尽地生产另类方案乃是现代性的一个定义性特征。用人类学家顾家客(Jack Goody)的话说,“现代就像当代,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并不代表某个分期或风格,只有在飞逝和模棱两可的意义上才代表分期或风格。”[9]现代性是否适合或值得作为一个分期的概念,是颇为争讼不休的议题。我下面还会论及。此处只需要提出这点即可:“另类现代性”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思想,不止是因为它肯定了现代性,而且还因为它为现代性提供了另类方案的抱负。诸种“另类现代性”从各文化中抽取作为差异的证据,但这些文化自身在许多情况下皆是现代性的产物,我们认知古代是根据现代性的要求,正如政治空间既是他性空间也是根据现代性的要求。如王爱华(Aihwa Ong)所说,“另类现代性”中的另类“表明现代性的各种类型是(1)由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间、其人口和全球资本之间不同的关系束所构成;(2)被那些占据‘西方’知识并重新以关涉自己国家的真理方式来呈现西方知识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们所建构”。[10]
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诸种“另类现代性”诉求的根基中找到对上述这些论断的支持。有趣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绝大多数讨论中不在场的中心,或可能是刻意为之。我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最近的一部著作中引用一长段来说明:
在当前“现代性”各种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怎么能把它们的产物即信息革命和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与其可憎的古老类型区隔开去,而不必使它们卷涉于追问严肃的政治和经济这些系统性后现代性概念不可避免的问题?答案很简单:谈论各种“另类的”或“替代的”现代性……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有一种现代性,这与标准的或霸权性盎格鲁—撒克逊现代性模式不同。任何你不喜欢的后者的东西,比如不喜欢它使你陷身的贱民处境,都可以通过自信的和“文化的”观念来将其抹去,并提出自己的不同的现代性……现代性唯一让人满意的语义学意义在于它与资本主义的关联。[11]
在这个意义上,“另类现代性”与一般意义上的后殖民批判相似:它们之间不止是偶然而暂时的亲缘关系。后殖民批判替代了早先基于新殖民观念的批判,把批判的重点从资本主义转向殖民主义,把批判的主题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批判。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比詹明信所说的要有问题得多,因为资本主义也难免受文化的调制。但依旧有必要探寻是否有可能探讨现代性而不用涉及资本主义,或者相反。⑨“另类现代性”话语因没有系统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性(诸种)文化的关系而有所不足,特别是其作为话语出现这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所引起的全球关注是与资本的全球化相伴随的。这个话语本身并不新颖。如我刚才所说,欧美之外(甚至有可能在欧美之内)的现代性话语一直在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靠近现代化不是追随“西方”的足迹,而是因其承诺强化特殊性诉求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基础。如果这个话语在我们时代获得过广泛关注,那是因为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提出,这个话语要求我们把最大的关注给予那些因在全球资本方面的成功而显著起来的社会。
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经济政治权力等原因而重要,而经济政治权力与各种话语权并非无涉。在不即时显明的理由上,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很重要:资本主义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塑造过现代性,自身也担负着其各种文化环境的标志。如果资本主义像现代性一样诉求其文化环境的独特性,一如今日经常呼吁的那样,那么欧洲的资本主义就与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没有差别。资本主义和各种欧美现代性的历史纠葛,意味着只要这些现代性曾经受到过资本主义的塑造和推动,那么,曾经提供环境让资本主义上升为全球霸权的欧美各社会,它们的各种文化遗产就为资本主义所承载。小看资本主义和各种欧美文化之间的这一关系是错误推理的一个根本原因,正如当代中国领导人乃至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所提出的,可以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而将各种所谓的“西方”价值排除在外:这些“西方”价值一直把诸种“另类现代性”的国家工程,和抑制文化与政治另类方案相结合,因为文化与政治另类方案要求从既有权威结构中获得自治并反对既有权威结构。⑩资本主义并非“免受文化影响的”(culture-free)。它呈现自身的文化,并可以从一个社会传输到另一个社会,但它也可以是传输自身社会的文化遗产的工具。
换句话说,资本的全球化也表明塑造过其发展的欧美各个社会的价值的全球化。寻求诸种“另类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与全球资本主义企业的各种文化现实发生冲突。它们甚至可能代表对这些冲突造成的各种问题的回应,特别是围绕若干处于竞争中的中心资本出现极化的全球场景中,起作用的那些价值出现繁殖。竞争是足够激烈的。不过我们需要注意,这些来自不同历史遗产和经验的价值相互竞争,以声称诸种“另类现代性”自身是相当现代的,因为它们现在从各个地方得到成功应用,而这些目标与当初刺激它们起源时的社会和政治理念是相违的。一个出众的但绝非唯一的例子,是儒家与资本主义的联姻导致资本主义在东亚各社会得以发展。这些社会甚至比欧美各社会还要热衷于“发展”,而这个“发展”正是诞生于它们曾反对的欧美现代性中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这个媒介,它们也传播到世界各地,欧美价值成为全球价值储备库中的一部分,即便在其孕育下土著价值重新绽放而挑战它们。(11)
诸种“另类现代性”这个词最显著的是用来与民族和文明相参照,表示在其边界之内的文化一致性,而这又是与同时在现代性圜局之中诉求“文化复杂性”相违的。文化一致性假设可以用于国家、社会中的霸权群体,或者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而它们自身则讽刺性地是它们寻求加以利用的现代性的产物。这些假设与全球针对现代性提出无所不在的异议相冲突,包括该思想的诞生地。如果现代性确实是“无所不在的”,那么与现代性的冲突就不限于民族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者限于具体化的东西方观念,而恰恰是全球各社会的组成部分。对这些政治空间化的强调,模糊了它们内部对现代性的前景有着深刻的不一致意见,而这又包括意识形态导向和政治权力等问题。诸种“另类现代性”只是指社会中不同群体对现代性的不同应对,但这些社会并没有类似的利益或文化倾向。同样重要的是,特别是我们今天,随着人口流动、商品流动和各种文化实践活动拓展、扭曲和撕碎文明和民族,文明和民族的准确边界在哪里?
现代性的矛盾,以及搜寻另类的努力,乃是现代性历史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可能见证的是现代性矛盾的普遍化,这不是现代性和传统的冲突,而是诸种“另类现代性”为竞争霸权和优势的冲突。如果用诸种“另类现代性”这个词去理解现代性的历史性,那么它就是无可争议的。如我们所知,它们代表的是现代性的深远发展并入了新的社会和文化空间,而不是与现代性相断裂。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见证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各种模式之间的竞争,但所有的模式都属于现代性。这个现代性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有赖于竞争的结果,但不可能的是,基于目前的证据,现代性会游离于资本之外。无论如何,其新的组成部分要求承认它们的存在,过去一如当前,为其投下新的曙光,为其设定新的权力结构,使之与其前一阶段区别开来。
二、作为历史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历史,这是我在别处所说的全球现代性的条件。我将全球现代性区别于前一个阶段,即一般所说的现代性阶段,而现在把它说成欧洲现代性更合适,它显示的是欧洲和美国两个世纪的全球霸权模式。(12)欧洲现代性是世界各地诸种社会遭遇现代性的一种伪装,这种遭遇所采取的形式与欧美文化和政治实践不可区隔,所以现代的东西和西方的东西之间少有区别。所以难免会出现抗拒,强调在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做出区别,接受其中一个,而抗拒另一个。这种对欧洲/美国文化特定内容的抗拒,就好比是对异国入侵威胁到要剥夺当地身份的那种霸权的抗拒。这种抗拒采取若干形式:从保守型的复兴传统,到解放者在新的民族国家的世界里寻求自治,到社会主义者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等。但在最后一种形式中,其他的抗拒形式都认可“西方”现代性是优先的,要求各地从过去的各种遗产中转变出来,以沿着现代性的道路前进。
这种态度在大众意识中,在“西方”或西方以外的地方,发生多大的变化却值得怀疑。不过,稍微看一下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就足以说明这种变化在全球文化政治中是相当重要的,正如“另类现代性”这一观念已经表明的那样。许多国家对先前瓦解自己保守主义的欧洲现代性采取替代方案,这一做法已经走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前沿,包括欧洲和北美,以保证自己有人听,即便是那些对他们采取模棱两可态度的国家,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政权。(13)在全球政治的层次上,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话语有不同的构成成分,而否认这些意识形态具有同期性,是不再可能的了。在确认各种文化遗产都占据同样的时间和空间以后,区分先进与落后的做法已经消退。这样,除了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层次以外,人们越来越难以提出一个进步的标准。而科技和经济发展层次的进步标准则愈加醒目地确定,现代性作为所有社会的共同属性,指的就是科技和经济的进步。差不多为众所确认的是,我们都住在现代性之中,但对现代性却有不同的体验。欧洲现代性的遗产随处可见,各种自治现代性主张的遗产也是如此。在新出现的国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和土耳其,出现了多发展模式或范型多样性的诉求,本土价值的复兴,承诺可以克服欧洲现代性的问题,克服把欧美带向不可避免的衰退的欧洲现代性。有时我们难以克服这种印象,即欧美的支持者(cheerleaders),比上述社会中敏锐关注这种对立的知识分子,更热衷于这些诉求。
为了协调现代性的欧美起源和当代对现代性的挑战所作的努力带来了紧张,在把现代性从欧洲中心主义中拯救出来的努力中清晰可见这种紧张,包括呼吁“另类现代性”,如上面引用的高迪立(Dilip Gaonkar)的话中已经表明的那样。我再引用已经提到的那一段:
若干世纪以前相对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西方和西方以外诞生的现代性,现在已经遍布全球。它不是突然到来的,而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到来,经历了漫长的时段。现代性是通过接触来唤醒的,通过商业来传播的,由帝国所管理,带着殖民的痕迹,受到民族主义的推动,而现在则逐渐由全球媒体、移民和资本所操控。现代性总是在乌托邦修辞所伴随的机会主义碎片中,持续地“到来和出现”。现在它不再单是从西方来,尽管西方依旧是全球现代性的结算库(Clearinghouse)。[12]
艾森斯塔德在他编辑的影响深远的文集《多样现代性》中表述过同样的观点。他说,世界各地的社会已经“发展出独特的现代动力和解释模式,原来西方的现代性工程不过是它们的关键的并常常是模棱两可的参照点。在非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许多运动表达出了强烈的反西方乃至反现代的主题,尽管这一切都是独特的现代性。”[13]
如果现代性的后果是有问题的,那它的起源也是有问题的。现代性如此明显的繁荣,以及对欧洲现代性带来的欧洲中心论进行挑战,已经提出诸多问题,涉及现代性的结构,这些问题的影响在革新派史学中随处清晰可见,不仅涉及历史学家,而且还关涉学科的边界。世界史志显然受益于这一潮流,并首当其冲表明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探索自重新考虑他人参与制作欧洲现代性开始,拓展到纵贯非洲—欧洲—亚洲的各种社会同样的现象。这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明显。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这些社会在“早期现代”时期的重要进步,使它们在19世纪之交如果没有超越欧洲的话,也是与欧洲平起平坐的。因为他们有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支持,带着极大的景仰之心看待如明清时代这样的社会。(14)对这些政治体系的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结论。(15)沿着这些路子,在方法论上出现了一个转向,即从研究单个社会转向研究超地方的进程,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的“全球交换关系”或“比较方法”(这两者需要区别开来)。早些时候会把西方欧洲和北美看作是现代性和世界史的缔造者,而在新的史学中则是在有史以来多样的政治和文化空间发散出来世界历史进程的产物而已。麦威廉(William H.McNeill)以一个先锋史学家的口吻,来描述他最近从欧洲中心叙事向世界叙事的转变:“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区分在不同层次上存在的网络的复杂性:在当地村落或狩猎群的层次上,在包括不同职业群体的单个城市层次上,每一层次都有自身的多样网络;较为单薄的长距离网络将城市群链接为文明,把文明链接为欧亚大都市和美洲大都市,直到他们在1500年以后成为一个单一的、相当紧凑的、世界性的都市网络。”(16)
在这些质疑现代性即欧洲现代性的问题中,还是有一些保留。从历史上来说,单就这些思想出现的地点是欧洲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提出了概念性的问题。欧洲现代性的制作过程包含了许多涉及非洲—欧洲—亚洲乃至以外地区的历史潮流,他们交织在一起。现代性并不是从基督教中抽取出来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产物,不是欧洲中心主义偏好的选择。现代性出现于这一宽广的全球语境中的非洲—欧洲—亚洲的一个角落,如果把这一全球语境看作是现代性的史前史,或者把这一全球语境看作是整合到现代性当中成为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即便是它出现的地点也会体制性地和在文化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吗?
持续地把现代性等同于欧洲现代性这一做法倾向于前一个方案,导致人们偏好使用“早期现代性”来描述这一形塑时期。(17)这个用法将早期现代从其现代性与产生的地域联系中脱开,从而寻求避免这一术语的目的论色彩,赋予它一种超越地域的范围,使之包括诸多社会,从非洲—欧洲—亚洲一端的日本,到另一端的奥托曼帝国,认定他们都经历了“早期现代”,但只有一个最终会满足现代性的标准。这个用法因为在重新解释早期现代时,遮遮掩掩地重新表述了早期所做的传统和现代的区分,而遭受批判,尽管比起早期的文明话语,甚至是比这一话语的“传统的发明”版本,这一术语极大地为各种传统赋予了更多的动力,它仍然遭受批判。类似的,那些更倾向于经济学的研究,也绝不让人满意。其观点让人想起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目的论去发现“资本主义萌芽”。结果,这个话语将欧美现代性限制在工业社会的出现上而减缩了欧美现代性,一方面,侧重从横跨大陆的互动中产生出特别的欧洲现代性的那些文化和社会特点,诸如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科学知识的利用等,所有这些都是工业现代性的前提;另一方面,这一话语没有认识到其他参与到早期现代的社会依旧禁锢于其中,不必然是因为他们没能转向现代性,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构成,使得他们没有沿着参与制作了欧洲现代性的欧洲社会(无论如何包括了该地区的所有社会,更无须说那个无形地误导人的实体概念“西方”)同样的轨道前行。(18)
我认为,探讨这些概念问题并坚决打破早期把现代等同于欧洲现代这种做法的一个方法,是简单地以颠覆现代性在构成和展开时空间的重要性这种方式,把现代这个术语投射到“早期现代性”这个时期。蒙古征服后出现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系,取代了早先的朝贡国家,重塑了非洲—欧洲—亚洲的空间,这提出了一个新的大陆互动地图,要求在商业互动中采用新的内部组织和超越当地组织的方式,直到把这些社会沿着都市网络串联起来。正如沃尔夫30年前所说:
1400年代,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存在内在联系。各个自认为文化上与众不同的群体却是通过亲属制度和仪式性联盟而连接起来的。国家扩张将其他人群并入到更包容的政治结构之中,精英群体互相继承,控制农业人口,建立了新的政治和象征秩序。贸易形成了自东亚穿越撒哈拉沙漠到黎凡特(Levant,地中海东部区域——译注),从东非到东南亚半岛的网络。(19)
我把这个时期称为“非—欧—亚现代性”,其标志是能够在远西(不是远东)产生欧洲现代性的横跨大陆的力量。但它采取不同的形式和轨迹,以与当地政治和社会特点相一致。在现代性的这个阶段和早期阶段有一些共鸣,尽管在共同性的强度方面,以及在“网络”隐喻缺乏冲突方面,其语境非常不同。全球现代性的世界比“非—欧—亚现代性”的世界整合要更为紧密,但由于同样的原因,它提供的另类性比现代性起源所提供的“另类性”要少。
我希望以上与“欧洲现代性”的对比应该已经足够表明,使用“现代”于这一时期,不是要拓展欧美霸权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而是在我们从当代要求非霸权思维的视角去处理现代性的历史问题和概念问题时,要把这些另类的可能性放在议程上考虑。重新分配现代性的空间,以把它从布劳特(Blaut)所说的“渠道历史”中拯救出来,把注意力从任何有关现代性的特定实质定义转向现代性得以产生的关系,把现代性看作时代性,回向它的语义学起源。我的意图不是要剥夺现代性的内容,而是要颠覆这一内容积累的复杂性和历史性,因为现代性是在展开的过程中得以发明和再发明的。[14]
我们也需要注意对立意义上的一个困境,并使这个术语的运用合法化。可以讨论的是,批判欧洲现代性,肯定当地过去传统,已经造成滑向另类的中心主义,在全球文化政治中这种另类的中心主义具有肥沃的土壤:所有的过去都已经被民族化,并如查巴塔(Partha Chatterjee)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所说的,被东方化。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质疑“另类现代性”概念的重要理由。(20)把这些社会配置到由跨社会互动所界定的空间,是把过去历史化的一个途径,以抵消民族或文明目的论的非历史的历史倾向。历史地理解现代性,不止是要解构欧美对过去的诉求,而且要对所有证明这些诉求都是现代性产物的诉求去中心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超越现代性的藩篱来思考现代性。
三、如何处理现代性
这些历史解释的问题是现代性的历史化,换句话说,是现代性概念自身的问题。如果现代性是时空中众多扩展力量的产物,在不同的地点采取不同的轨迹,随时都在实践中遇到抗拒而发生转变,并在最后为民族和文明的历史轨迹的主张所克服,那它作为全球性转换型力量,其意义是什么?或许更为基本的是,使它成为一个分期概念或特定空间区隔的定义性特征是什么?更加不可操控的是,它带到不同民族那里的意义是什么?在它诞生地欧洲,现代这个术语不过就是指最近的,与古代相对,在用来指历史形成和时代性的意义之前,这个词已经有漫长的历史。(21)在我熟悉的非西方语境中,这个术语也简单地翻译为“当今”或“当代”,与这个词的起源以及在欧美的用法相当一致,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与现代性与众不同的特征即无尽的变迁相当一致。这些用法表明了什么?如果现代性确实有特定的内容的话,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都被赋予了比它应该具有的历史意义更多的东西。反过来说,要说现代性是改变全球的过程,其结果是在不同地方产生不同的内容,这么说也很容易。因此,难以用任何特定内容比如制度或文化来界定现代性。
有的学者确曾认为应该把这个概念降格为一个历史范畴。本杰里(Jerry Bentley)曾经对他所描述的现代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22)在欧洲和现代性有着紧密关联的情况下,一个彻底的反欧洲中心主义也要求降低现代性的价值,这确实很有道理。我注意到,人类学家顾家客揭穿了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一些最基本特征诸如个体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等是一种创新的口号,他或许比任何人都走得更远。(23)现代性的界限,无疑是很模糊的和漏洞百出的,从想象的长时段视角来看尤其如此,如研究印度莫卧儿(Mughal)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穆哈班(Harbans Mukhia)在一次现代性讨论会中提出的那样。他道出内心的疑惑:五百年后现代性会是什么样?用麦考尼(Robert and William McNeill)等所做的比喻来说,仅仅是“鸟”眼所及、时空交错的“人类网络”中的织线吗?还是查迪皮从宽广的生物学视角所提出的那样,是一个类似变迁序列中的一个飞速变迁的时期而已?或者是诸如柯大伟(David Christian)这样的历史学家在著作中提出的大写历史的更大图景?(24)
特点或许是当代的,但对问题的意识却难说新鲜。钢汉斯(Hans Ulrich Gumbrecht)在提及一个世纪以前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时写道:
斯宾格勒意识到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十字路口,且越来越意识到欧洲“局部小世界”之外不同步的历史发展,这导致他抛弃了传统的历史分期方法,即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分期法,简直是微不足道而又枯燥无味。正是其前辈提出的“现代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到文艺复兴,再到十九世纪初”,在斯宾格勒看来,要表达历史的发展简直是白搭。他认为,只有从一开始就把历史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呈现才可能。(25)
至于现代性是世界史的定义性轴向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绕开,因为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问题重重。其根本的特征是崇拜变迁和追求新鲜,所以没有清晰的办法来界定其特征。它顶多是西欧各社会对自身的看法,到17世纪西欧人开始把他们自己看作是超越祖先、超越其他民族的划时代提升,因此要与过去和其余地方决裂。(26)这个术语带着孕育它的地方的特征,以及该地所设定的全球霸权。它的空间边界切割和穿越了各社会,与其时间界限一样成问题。此外,也还有其他的方法来组织过去,比如通过个体和家庭的视角,通过地域比如都市与乡村的视角,通过国家、区域和大陆的视角来组织。他们肯定产生了不同的过去,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延续和变迁类型,而不是现代性所说的时空总体化想法:即与过去断裂,把所有的当代性屈列于历史时间之中,展布这些诉求,以落后社会和进步社会或传统与现代来划界,而这些边界则成为征服世界和殖民的合法理据。(27)
近来,在各后殖民社会及现代性产生地,现代性因消除了人们的主体性以及文化实践,以及创造出了否定精神世界和宗教世界的世俗世界,受到人们的攻击。(28)用查巴塔的话说,现代性还剩的,就是假如“通过追溯西方政治制度的历史谱系,我们业已建立了西方现代性的历史纯粹偶然性,没有理由要求在世界其他地区复制该制度的结构。”[15]这种挑战进一步质疑作为欧洲现代性产物的、并根据其特权来重新组织过去的历史时间。目前,历史屈从于从文化视角进行的批判。这一批判质疑以时间归之于历史时间的做法,并从文化的角度指出,思考尚未失效的过去有不同的方式,不管这些方式有多边缘。(29)把现代性从曾是其绝对基石的历史意识中剥离开去,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把它丢弃到瞬时性的大海之中,把它作为诸多随机漂浮的可能故事而已,如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哈伦与故事海》中的小说所做的那样。
不过,冲向现代性乃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动力。但现代性之所以有价值,恰恰是被看作是那些导致其无情和无法探索可持续真理的原因:现代性就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和技术。应该在别处寻求精神抚慰,转向宗教或者被现代性压抑的那些文化遗产,是它们威胁要消除身份的消费世界,提供给人们以身份。但人们很容易忽视这些另类的抚慰源泉已经在新的历史圜局中获得新的意义,包括政治商品化和文化商品化。我们探讨的那些问题,是它们以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语言提出来的,这就是现代性语言。历史时间已经成为瞬时性,其他的瞬时性通过这个瞬时性得以折射,有关另类瞬时性的知识和确认另类瞬时性并没有阻止我们继续在历史时间里写作。全球化世界令各地方世界黯然失色,差异意识一直伴随着它,而我们的各种话语一直带着强烈的差异意识,深深地嵌刻于对全球化世界的关注之中。现代性带着它所生产的一切恐惧,在全球议程上放入许多人渴望的价值——有时尽管是与现代性自身深深对立的价值。
我们也必须考虑这一点:如果我们放弃现代性观念,我们必须承受在知识上和政治上将失去的东西。这些概述有例外,但我想在普通的层面上,它们的有效性是为我们当代各种问题所支撑的。这些问题前所未有地呈现为全球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各个社会当中得到广泛复制,表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实践是普遍化的,穿越了它的许多文化具象(avatars)。换句话说,尽管过去三个世纪中它有着各种问题,已经成为不仅是造就它的欧洲人的意识,也成了全世界的意识:寻求另类性就表明了这一点。如果现代性抗拒固定的定义,或者抗拒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它无论如何还是提供了一个叙事,使得自从蒙古帝国以来一直在建构中的世界的成败得失有点意义。蒙古帝国带来了一种非欧亚的感觉,从而连接早前人们已知的穿越欧洲、非洲和亚洲的那些区域空间。这个感觉随后为穿越非欧亚各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所全球化,并得到拓展,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漂洋过海,尽管其态势一直不稳定,其幅度也有差异。苏步拉(Subrahmanyan)曾建议我们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历史的全球性和并接现象。”[16](强调是原文即有的)(30)沿着这些路线所做的分析让人们关注许多层面的互动,以及它们不同的时间性,现代性会从这里得到繁衍,也表明其在历史中的展开。是这些互动界定了孕育现代性的全球性之空间,这就要求新的时间感来解释这些空间的差异。
这是世界史承担的任务,而世界史本身就是这种时间意义上的产物。让人惊讶的是,蒙古人发挥过重要作用,将此前尽管有若干世纪的联系但依旧分离的许多世界聚拢起来,在他们的指导之下,穿越大陆世界之感首先诞生于平凡的伊斯兰世界。哈马丹(Rashid-al-Din Hamadani,1247-1318)的百科全书《编年纲要》(Compendium of Chronicles)不过是一个纲要。它把各个社会聚拢起来,却让它们的历史分开,也没有试图从这些历史之中造就出一个我们所理解的穿越大陆的历史。无论如何它的重要性在于其体例采用比较编排,表明对它们的空间关系有了新的关注。(31)是那些互动使得第一部非欧亚历史纲要成为可能,这些互动也繁衍(并继续繁衍)出我们称为现代性的总体性,以及它所包含和繁衍的许多差异,但逐渐服从于总体性的需求。现代性繁育了另类性,也把它们的范围限制于现代性的视野之内。
“大图景”(big-picture)式的视角带来了一套不同的伦理和史志学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对突破现代性的局限特别重要,同时又不否定现代性本身的意义。其最基本的意义是伦理上的:这将我们和我们的事业置于一种视野之中,这种视野让我们保持谦卑,让我们克服如自然是人类有待征服的自然那种傲慢。很难说未来会怎么样,但未来并不乐观。以自然作为现代性的见证(如最近玻利维亚所作的)这种做法,指出了一种了解现代性问题的新思路,指出我们在资本所控制的全球视野之外,尚有拓展空间视野的必要。相应地,宇宙时间考虑了历史时间,并指出,如果我们想要在一再缩短的未来之外,拓展历史时间的话,就有必要修正我们有关变化和发展的观念。在这视野中,过去并没有过时,因为那就是过去,而现代性的那些工具也许不足以克服现代性的各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过去也许就是知识的储备,也是想象未来的依据。诚然,根据过去几十年的文化和政治逆转来看,历史并没有成为过去。
因此,所需要的不是由全球文化政治所驱动的诸种“另类现代性”,而是针对全球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性之各种另类方案,去重新构想全球过去和全球未来,以此作为人类事业之中,尽管有各种人性差异但还能自觉的源泉,而不是作为狭隘身份的源泉。(32)这也显然是现代性的产物,任何严肃的努力需要以此为起点,以超越全球现代性——这个全球现代性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是与自身相违的。现代性的时空惯习限制了各种宇宙观。不管科学不科学,宇宙视角可能是克服这些世界观局限的前提,但宇宙瞬时性会把生活于历史时间和空间中的各种问题模糊化,所以只有当宇宙视角避免把人类的活动压缩到宇宙瞬时性之中时,这一前提才成立。以宇宙时间来重新想象人性依旧要与历史时间打交道;历史时间尽管有各种想象局限,但依旧是身份得以形成和世界得以认知的瞬时性;历史时间受困于进步和发展,其时间逐渐以消费和异地安置的速率来衡量。即便是宇宙时间揭示现代性是一个幻象,它也依旧是持续塑造人类意识和行动的幻象。
我想,克服这个幻象是重写现代性史学的基本工作。我们居于现代性之中,我们的世界是现代性创造的世界,我们也是通过它来看的世界,我们的瞬时性是由历史时间决定的。宇宙视角可以揭示各种在时空范围内受到限制的范畴是稍纵即逝的。但其合理性存在于它贡献给解决现代性议题的视角,为此,历史时间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起点:揭示现代性的历史性,揭示创造现代性的各种力量,揭示其诸多现已全球性的问题,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则为解决所有问题铺了路的问题。现代性可能是我们各种问题的源泉,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起点。在诉求各种“另类”方案中恢复失去的各种身份很重要,只要它能作为解决共同问题的资源,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宽广的问题。
[译者简介]陈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注释:
①本文的初稿是作者在2012年4月27-29日韩国首尔召开的亚洲世界史学者协会第二届年会上所作的基调发言。
②Carl Pletsch,The Three Worlds,or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Labor,Circa 1950-1975,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No.23(October 1981),pp.565-590.有关作者所说的现代性的“文化”对“非文化”(acultural)理论,参见Charles Taylor,Two Theories of Modernity,in Dilip P.Gaonkar(ed),Alternative Modernitie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72-196.
③帝国总督张之洞在19世纪晚期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似乎从来没有在中国思想者当中失去其吸引力,尽管过去一百年时间里有了许多变动。有关的讨论和批判,见Joseph R.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Vol.I,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59-78.
④有关“植根于该地点”(site-based),见Gaonkar,Alternative Modernities,p.15.也参见该文集中,Dipesh Chakrabarty,Tejaswini Niranjana 和Michael Hanchard等各自围绕劳工议题、妇女议题和非洲人流散议题的那些文章。关于把现代性等同于各民族和文明,可以在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刊Daedalus、由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编辑的特刊《复合现代性》(129.1,2000年冬季卷)的文章中找到。在使用概念时的这些差异部分是因为文化研究者和社会科学之间不同的研究癖好所致。把“另类”和文明“经典地”等同起来的,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思想。所有给予这个思想的批判,都在反映从土耳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亚洲观点。
⑤Sudipta Kaviraj,An Outline of a Revisionist Theory of Modernity,Archives of European Sociology,XLVI,3(2005),pp.497- 526,和Partha Chatterjee,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Studies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查巴塔的著作采取卡福饶贾(Kaviraj)的理论框架,我认为,因为他对“发展序列理论”的偏好胜于现代性的历史性,所以这个理论框架不适合,因为“序列”表示的是确定“现代性组成元素”的可能性,对其定义来说可能已经充分。从这个讨论中我们不清楚卡福饶贾为什么依次用“对称/序列”二分而不是用一开篇就使用的“结构/历史”二分来构拟他的论点。
⑥Ahmet Davutoglu,Alternative Paradigms:The Impact of Islamic and Western Weltanshauungs on Political Theory(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4),p.195.作者把“伊斯兰范式”描述为“绝对是西方的另类”。潘霖(Lynn Pan)在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Tokyo:Kodansha International,1994),267页中提到,新加坡华人似乎相信“华人特性的某个原初核心或不可更改的本质,相信这个本质是华人基因与生俱来的。”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从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中国人那里也听说过类似的话。
⑦见收入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特刊(4.2;2006)中的文章4.2(2006),Beyond Hegemony?——Europe and the Politics of Non -Western Elites,1900-1930,以及Cemil Aydin,The Politics of Anti-Westernism in Asia: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 Pan-Islamic and Pan-Asian Though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⑧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and,Ziya Gokalp,Turk'culugun Esaslari(Principles of Turkism),ed.By Mehmet Kaplan(Istanbul:Ministry of National Education,1990).有意思的是,当代中国对过去的刻画,如历史博物馆中的新的历史展览,其鸦片战争时期以前被当作“现代”(modern,作者用汉语拼音注明包括近代和现代——译注)或“半封建半殖民”,现在则当做是“复兴”,而在此以前的历史则降低为“古代”。
⑨现代主义在文化上范围要比作为概念或现象的现代性要局限得多,但即便是现代主义也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城市化和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文化后果(特别是反基督教文化)紧密纠缠在一起。葛彼得(Peter Gay)写道,“现代主义的温床来自于那些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广泛的繁荣.”Peter Gay,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From Baudelaire to Beckett and Beyond(NY:W.W.Norton&Co.,2008),p.18.有关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的经典讨论,可以参见薄玛协(Marshall Berman)的论述。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New York:Penguin Books,1982).安赔礼(Perry Anderson)对此有一个批判性讨论。Perry Anderson,Modernity and 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144(March/April 1984),pp.96-113.
⑩亚洲的诸种“另类现代性”如果不是1980年代晚期兴盛一时的批判“西方”式民主话语的直接产物,也是其转世,常常相反地提供建立在亲属价值之上的各种威权型另类政治方案。两名土耳其学者在讨论土耳其另类观点诸种“另类现代性”时说,“它们都把全球化看成是土耳其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不断变迁本性的内在元素,强有力地支持土耳其整合为欧盟的完全成员,强调为土耳其经济增长而生产的重要性;但就它们的民主话语、复式主义和自由来说,则有不同。这种差异体现于同时提升公民权和个体性的普遍话语,以及提升有机团结群体内各成员的文化/道德身份。这意味着自由贸易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表达,与土耳其经济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是‘共存’的”。E.Fuat Keyman and Berrin Koyuncu,Globalization,Alternative Moderniti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urke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2.1(February 2005),pp.105-128,p.124.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即社群主义尽管有自己的文化甚至宗教纽带,但表达的是不限于任何单一文化的政治观。
(11)有关这些议题的讨论,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见Arif Dirlik,Culture and History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Modernity(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11).
(12)Arif Dirlik,Global Modernity:Modernity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Boulder,CO:Paradigm Publishers,2006).对下文所论及的这些议题的精心讨论,参见Arif Dirlik,Revisioning Modernity:Modernity in Eurasian Perspectives,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12.3(June 2011),pp.284-305.我的进路体现的是人们所说的“亚洲作为方法”,回溯到1940 年代日本思想家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的一篇文章“亚洲作为方法”(“Asia as Method”)。最近的一些讨论中屡屡提及,最有名的是陈光兴(Kuan-hsing Chen)的Kuan-hsing Chen,Asia as Method:Toward Deimperialization(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以及汪辉(Wang Hui)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A Genealogical Analysis,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8.1(2007),pp.1-33.竹内对现代性深有影响的讨论,见其文集What Is Modernity? Writings of Takeuchi Yoshimi,ed.and tr.by Richard F.Calichm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对汪辉著作中使用“欧洲”和“亚洲”的批评,见Ralph Weber,On Wang Hui's Re-Imagination of Europe and Asia,Europa Regional,17.4(2009),pp.221-227.我愿用“欧亚”(Eurasia)来取代“亚洲”,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不仅更准确,而且还希望避免用大陆块的一部分来替代另一部分。
(13)比如可以参见China Perspectives 期刊德里克所编2011 年第1 期特刊中的文章:China Perspectives,No.1(2011),The National Learning Revival,ed.By Arif Dirlik.
(14)这里我指的是这些著作: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8);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以及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the European Experience(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它们几乎同时面世,并迅速在期待其结论的知识圈中获得深远影响。
(15)参见这一特刊中的文章:Daedalus,Vol.127,No.3(Summer 1998),“Early Modernities,”“Introduction” by S.N.Eisenstadt and Wolfgang Schluchter.这一期特刊与上一条脚注中提及的著作是同一时间出版;这也揭示这一议题在“现代性”(m's.)之外,用汉语“现代”(xiandai,意指当前、从此、现代)和“未来”(weilai)来重新包装。
(16)William H.McNeill,Leaving Western Civ Behind,Liberal Education,97:3/4(Summer/Fall 2011):pp.40-47.这里指的是Robert McNeill and William H.McNeill,The Human Web: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New York:W.W.Norton,2003).
(17)见Daedalus 刊Early Modernities,特别是由艾森斯塔德和舒世特(Schluchter)所写的文章,以及魏鹏(Bjorn Wittrock)的讨论;有关用“早期现代性”来指欧亚状况的更令人信服的例子,见John F.Richards,Early Modern India and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8.2(1997):pp.197-209.
(18)比如可以参见Timur Kuran,The Long Divergence: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库兰(Kuran)像其他研究资本主义史的学者如布罗博(Robert Brenner)和上面引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强调西北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其社会和政治因素具有重要性,这是奥托曼帝国所缺乏的。(我们可以补充说,这也是其他地方比如明代中国所缺乏的)这个观点很受欢迎。另一方面,作者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似,也带着目的论倾向来考察这些“缺乏”,认为是对发展的障碍,而不是另类的历史轨迹。后者是少数人的观点,影响了Joseph Levenson 的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ample of Asia,1300-1600(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7)。这部著作记录了标题中所表明的各种“另类”方案。有关布罗博,见Merchants and Revolution:Commercial Change,Political Conflict,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1550-1653(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布罗博当下的关注是英国革命,但他的研究,重要的在于展示了有组织的商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他和其他资本主义史学者的侧重点不同,比如Giovanni Arrighi,Fernand Braudel和Immanuel Wallerstein.
(19)Eric 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Berkeley,CA:Univerity of Caliornia Press,1982),p.71.蒙古人对欧亚的启示在这些发展中究竟起到哪部分作用依旧是有疑问的。沃尔夫(Wolf)在美洲看到的类似潮流与蒙古人显然没有任何关系。贝克威思(Beckwith)在其最近的中亚研究中,拒绝把蒙古征服看作是一个“转折点”,尽管他确认“他们成功地把欧亚的许多部分带入到一个商业区域,并为参与其商业的那些人造就了令人难以置信数量的财富。”Christopher I.Beckwith,Empires of the Silk Road: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ity Press,2009),p.183.中亚也是奥托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萨法维(Safavid)帝国等的发源地,它们在16 世纪早期造就了一个“没有中心的欧亚”。有关这些变迁的研究,侧重于中国东南关键港口泉州(即马可波罗的Zaitun)的,见Wang Mingming,Empire and Local Worlds:A Chinese Model of Long-ter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Walnut Creek,CA:Left Coast Press,2009),chap.6.欧亚意识在欧洲一直存在,而在东亚随着蒙古帝国的消失而逐渐消失,如郑和在15 世纪早期昙花一现的远征以及所谓的朝鲜世界地图有趣的命运所证明的那样。相似的,16世纪早期明代耶稣会士地图中引入的“亚洲”这个词,直到19世纪欧洲地理学重新引进为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印象。而朝鲜地图可能是源于阿拉伯,并在朝鲜时期(1392-1897——译注)和宋明中国时期流行。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3: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Cambridge,UK:Can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pp.554-556; Gary Ledyard,Cartography in Korea,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II,Book 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235-345(fn.31 for the Korean world map),以及刘迎胜和杨晓春编《〈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10年)。可以认为,在东亚没有欧洲的那种贸易和传教(也因此没有教育)社会支持者,没有这些群体所要求的政治打击,也没有在当前视野之外扩展的利益。欧洲在新的欧亚空间意识中发现的不过是异域情趣或短暂即逝的利益。有关政治、商业和地图制作的关系,参见Jerry Brotton,Trading Territories:Mapping the Early Modern World(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有关莫卧儿印度以统治者为中心对“全球”的回应,见Sumathi Ramaswamy,Conceit of the Globe in Mughal Visual Practic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49.4(2007),pp.751-782.
(20)Partha Chatterjee,Nationalist Thought in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Chaps.1-2.我倾向于这一卷的第一版,因为后来版本把标题中的问号去掉了。
(21)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Modernism,Avant-Garde,Decadence,Kitsch,Postmodern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3-14.“现代”欧洲的“现代性”历史之复杂和矛盾,钢汉斯(Hans Ulrich Gumbrecht)以一篇简短但却富有启发的文章讨论过,Gumbrecht,A History of the Concept“Modern”,in Hans Ulrich Gumbrecht,Making Sense in Life and Literature,tr.by Glen Burns,(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2),pp.79-110.特别重要的是,钢汉斯提出,人们对“现代性”的反应是不同的,当这个概念从一个知识分子圜局(比如法国)到另一个(比如德国),就获得了新的维度。当前这些知识分子圜局在范围上来说是全球性的,在越来越共同的话语中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另类”方案。
(22)Jerry H.Bentley,Beyond Modernocentrism:Toward Fresh Visions of the Global Past,in Victor H.Mair(ed),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pp.17-29.在最近的世界史中,人们有意避免把现代性看成是与过去的断裂,比如Jane Burbank 和Frederick Cooper,Empires in World History: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以及Beckwith,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23)Jack Goody,Renaissances:The One or the Man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The Theft of Histor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s.7 and 9; and,Capitalism and Modernity:The Great Debate(Cambridge,UK; Polity Press,2004).感谢何纳迦(Najaf Heider)提醒我不要忘记顾家客的著作。
(24)Robert McNeill and William H.McNeill,The Human Web: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op.cit.; Dipesh Chakrabarty,The Climate of History,Critical Inquiry,35.2(Winter 2009):pp.197-222;David Christian,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最初出版于2005 年。
(25)Gumbrecht,A History of the Concept“Modern”,p.107.有意思的是,在对“西方的衰落”的关注潮中,对斯宾格勒的关注应该上升到台面上来说。“西方的衰落”也代表了当前的现实。
(26)这是詹明信提出的观点。他说,“现代性的比喻‘可以看成是’自我指涉的,如果不是行动性的话,因为它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类型的出现,与此前的脆弱形式决然分裂,在此意义上,它是自我存在的标志,指涉自我的符号,其形式就是其内容。那么‘现代性’作为一个比喻,就是现代性的符号。”Fredric Jameson,A Singular Modernity: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London:Verso,2002.p.34.他补充说:“‘现代性’的比喻总是以某种方式重写,强有力地替代先前的叙事模式。实际上,当我们接触到最近的思想和作品时,肯定某种‘现代性’时,一般都包括重写现代性自身的各种叙事;这些叙事已经存在,并成为传统智慧。”(pp.35-36)詹明信在这里所说的话,也可以看成是对诸种“另类现代性”所说的话:后者无疑包含于其中。卜汉斯(Hans Blumenberg)也说过类似的话:“现时代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把自身看作是纪元(epoch)的时代,由此就同时创造了其他纪元。”引自Sven Trakulhun,Ralph Weber(ed),Modernities:Concepts,Temporalities,and Sites in Asia and Europe(即将面世).p.1.
(27)这个问题在这个文集中得到广泛讨论: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tr.by Keith Tribe(Cambridge,MA:MIT Press,1985),以及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Timing History,Spacing Concepts,tr.by Samuel Presner 等(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柯瑞哈(Reinhart Koselleck)写道:“历史的历史化和其推进性阐述首先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体验真正的历史暂时性方面,历史和进步都有共同的特征。”Futures Past,p.143.
(28)Taylor,Two Theories of Modernity,作者在其著作中曾详加阐述现代性的宗教问题,最著名的著作即是A Secular Ag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29)南阿希(Ashis Nandy)在为另类文明遗产辩护时表现出最前卫的历史批判。见History's Forgotten Doubles,History and Theory,34.2(1995),pp.44-60.更为广泛的是从土著视角进行的历史批判。有关讨论见Linda Tuhiwai Smith,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London:Zed Books,1999),esp.chap.1.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倡导将历史“文化化”与将文化历史化方面最为著名。见Apologies to Thucydides:Understanding History as Culture and Vice Vers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钢汉斯认为在欧洲现代性之内,到20 世纪早期为止,“通过确定现代性的起源而为当前设定一个界限,从现在起这种做法似乎不可能了,因为各种历史变迁序列加速,以及确认存在着复式的异质性历史变迁。”见Gumprecht,A History of the Concept“Modern”,p.101.
(30)协调历史和概念(或结构和分期)方面的混杂,见柯瑞哈的讨论,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chap.10,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ty.
(31)有关伊斯兰帝国,参见Michael Adas(ed),Islamic and European Expansion:The Forging of a Global Order(Philadelphia,P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3).顾家客曾在Renaissances:The One or the Many?中提出这一时期有一个跨欧亚发酵。有关《纲要》中对中国部分的讨论,可见王一丹《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
(32)有关“人性”概念(不止是感情)出现的讨论,见Bruce Mazlish,The Idea of Humanity in a Global Era(New York,NY:Palgrave Macmillan,2008).
标签:现代性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欧美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