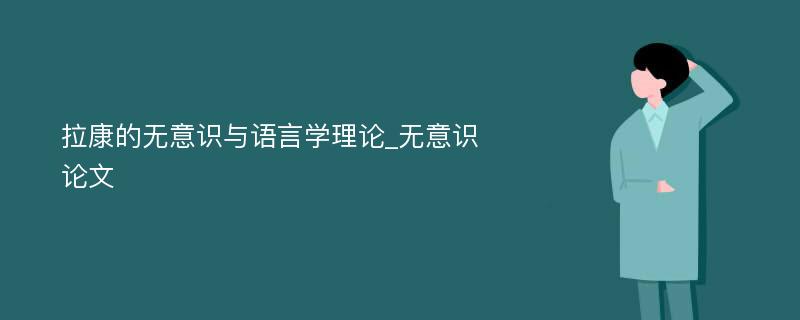
拉康的无意识与语言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在继承和创新方面已经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相当的不同,那么,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0),却在众人纷纷背离弗洛伊德原则之时,呼唤“回到弗洛伊德”。
拉康作为一位震撼了二十世纪学术界的著名思想家,在学术思想的多方面都有所拓进。他反对英美新弗洛伊德主义从外部即社会文化方面来阐释弗洛伊德,同时,他也反对荣格那种心理化倾向和集体无意识化的神秘倾向,认为这些观点使弗洛伊德的学说平庸无奇地“精神病化”了。
拉康与其他法国结构主义者重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尤其是无意识理论不同之处在于,他一以贯之地把精神分析学作为结构主义研究的对象,并强调要借助于结构语言学的模式,用科学的术语对“无意识”加以描述,从而使其纳入现代人文科学的领域。
拉康对心理分析学说的理论倾向性作了重大的再思考。他的一生是不断地创立学派,又不断地背离自己的学派的一生。他那种独立不羁、极富个性、喜好论战的学术风格,使他的学术生涯成为与其曾经隶属过的所有学会和团体粗暴决裂的历程。他的著作充满了玄虚的概念和极富抽象色彩的言述方式,具有一种相当晦涩的文风,藉此反抗那种把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日常语言分析的做法,并与纯粹运用于心理医疗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划清了界限。因此,拉康理论出现以后,获得了相当一部分追随者,受到作家、电影评论家、女权论者、哲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广泛注意和重视。拉康作为一位主要的结构主义乃至是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活跃于当代思想舞台。
一般认为,拉康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主要是从精神病学逐渐走向精神分析学时期,其代表作是1932年发表的博士论文《论偏执狂病态心理及其与人格的关系》,以及1936年他首次提出的“主体形成阶段”学说,即“镜像阶段”理论。中期是发表著名的讲演——《罗马讲演》并形成了自己精神分析学派的时期,其代表作是《言语和言语活动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这为其未来的思想学术方向勾划了大致轮廓。当然,他在1953年还倡导“回到弗洛伊德去”的学术意向,并向公众开放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拉康研究班”的讲演。晚期是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决裂而进入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时期。这一时期,他逐渐从精神分析学上升到结构主义理论,甚至最终上升到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如关于人类主体的思想、关于能指的优先地位的主体观念,关于欲望需求的本质的探讨,甚至还提出关于后启蒙运动( Post-Enlightenment),从现代语言学、哲学、 人类学等更广泛的思想维度转向了结构主义的哲学,并为自己新的文化话语寻求新的语汇。他在后期与萨特的“他者”(Other)这一概念展开论战,并与梅·庞蒂就 “肉体”(the Body)概念展开争论。晚期, 他还将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译成法语,并十分喜爱海德格尔关于语言、诗歌和真理的观点。这些思想倾向使得他在关于文本解读和叙事抑制的意义揭示方面具有不俗的见解,并影响了阿尔都塞、福科、德里达的思想。
一 无意识话语与主体理论
“无意识”是精神分析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无论是弗洛伊德、荣格、还是拉康,都对无意识理论进行过认真地分析。当然,弗洛伊德强调的是“个体无意识”,荣格强调的是“集体无意识”,拉康则将语言导入无意识中,强调“无意识作为主体的语言生成和主体的生成”,包括镜像阶段、主体的想象、象征和现实的三个层次。拉康在《形成“我”的功能的镜像阶段》一文中(注:J.Lacan,Ecrits:A Selection.trans.by Alan Sheridan,New York :W.W.Norton and Company Inc.1977.pp.1-7.),强调并不是无意识产生语言,而是语言产生无意识,人这一主体是在婴儿时期通过对外在的“他者”的接受而逐渐认识自我的。
1 镜像阶段
所谓镜像阶段,指人的心理形成过程中的主体分化阶段。拉康根据幼儿心理学的研究指出,婴儿入世时本是一个“未分化的”、“非主体的”存在物,此时无物无我,混沌一片。“婴儿的经验是一种混乱,是一种形状不定的一团”(注:J.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trans.by Alan Sheridan,London,1977.p.177.)。从他六个月到十八个月期间才达到生存史上第一个重要转折点——“镜像阶段”。这一期间婴儿首次在镜中看见了自己的形象并“认出了自己”,发现自己的肢体原来为一个整体。他认出了镜子中的自己,感到欢喜, 紧偎着在镜子面前抱着他的大人。 (注:J.Lacan,The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p.2.) 这是主体形成的开始,在此时期以前,世界好比是个母体,婴儿尚不能使自己同母体分开。拉康认为,婴儿在镜像前的自我认识就是“自我”的首次出现,这个过程他称之为“首次同化”,即婴儿与镜像的“合一”。“首次同化”也就是第一次的“自我异化”,因为此时发生了自我与镜中之我的对立,原始的“我”似乎被分裂了。当婴儿企图触摸镜像时发现它并不存在,这种发现了作为整体的自己的像而“像”又不存在,这个内在的矛盾就是“自我”的异化。大人形象与其他婴儿具有和婴儿镜像相同的功能,婴儿可以从他们的形象中比拟出自己在世界中这唯一的其他存在物组成了“双边关系”。拉康把这一关系归结为“母子双边关系”,因为母亲是此时婴儿世界唯一重要的“他者”。
镜像阶段虽然展开了主体形成的前景,却并未使“主体”真正出现,因为此时婴儿在镜像中看到的是与母亲在一起的形象,自己只是与镜中之我的“合一”,他还不能和这个“他者”分开,或者说“意识”虽然分解为自身的“像”,却未能与其保持认知上的间距,彼此之间还存在着无中介的对立。因而婴儿此时所找到的自己,还只是一个幻象或想象。
拉康将“俄狄浦斯情结时期”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母子双边关系期,此时父亲还未介入,孩子在这一阶段与母亲直接相对,想成为她的“一切”,即成为母亲欲望的欲望,因而就是想去与母同化。
在第二阶段,父亲开始介入,从此开始了三边关系,孩子遭遇了异己的父法。在镜像阶段就形成“想象界”。然而,形象既是“想象界”,同时也是“象征界”,因为在这里,婴儿已经开始接触外在的语言和异己的文化习惯。在“象征界”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从镜像阶段向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过渡。在这个阶段,婴儿开始服从由“父亲”带来的现实生活之“法”。“父亲的真正职能是把欲望和法结合起来。”“俄狄浦斯”是孩子通过意识到自己、他者和世界并逐渐使本身“人化”或“主体化”的时期。可以说,由非主体向主体的伸展,孩子开始意识到他在成长并与社会、文化、语言相协调。俄狄浦斯情结中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因素:法、楷模和许诺。父亲所代表的社会言语就是“法”,“法”是精神的疏离性和承诺性之间的一种协调。从此,孩子完成了与父亲的“第二次同化”。
在第三阶段,孩子开始与父亲同化,牺牲了自己的真实欲望,而完成了建立合法主体的过程。这时候,孩子由于接受了父亲的权威而在家庭的坐标中获得了自我的名字与位置。名字与位置就是主体性的原初的“能指”,于是,克服与母同化而与父同化,并开始进入语言秩序,随着自我主体的生成,就从自然状态进入到文化秩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主体”只有在幼儿进入社会和文化时才会逐渐实现。这一重要的转换过程是与语言的出现分不开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语言象征结构是先已存在的,当自我进入其中之后将“按该秩序的结构成型”,即“主体将被俄狄浦斯情结和语言结构模塑”。
镜像期是第一次认同,而理想之我则是第二次认同,主体借以在幻觉中预想自己力量成熟的那种身体形式,这种身体形式是构成性的,人将自身外投于一个对象之上,而这又包含了将“我”与这个对象维系在一起的种种幻觉。拉康认为,镜像期的作用是一种“心像”功能的一个例证,因为这种功能力图在有机体与实在之间、在内心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关系, 所以这种发展被体验为一种时间的辩证法(注:J.Lacan,Ecrits:A Selection.trans.by Alan Sheridan,p.3-5.),它使个体的形成进入历史生成过程之中,使“自我”能与社会中的复杂文化境遇结合在一起。
总体上说,拉康的“镜像理论”将主体心理结构的形成与社会文化结构与语言象征结构结合起来,从而引伸出主体三层结构(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理论,对“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有重要推进,对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主体心理的构成及其运动方式,作家作品中的心理文化意蕴的把握都具有新的启迪。
2 想象·象征·现实
拉康的“主体理论”中,关于想象、象征和现实三个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1960年,拉康自称为结构主义者之后,对想象、象征、现实这三个术语先后排列次序同以前有些差异。在1953年的讲演中,他将三者排列为象征、想象与现实,而在1974到1975年的讲演中,却排列为现实、象征与想象。学界对此争论不已,但是就拉康理论的真实意图而言,我以为,排列为想象、象征、现实三者递进关系,可能较为合适。
“主体心理结构”,是指主体的心理构成及其层次结构。“主体”是拉康学说中最具哲学意义而又最玄虚的概念。在他看来,自我与主体之间存在着区别:自我不是主体,自我与人、与显像、与功能的距离比意识或主体本位更近。自我位于想象界一侧,而主体则位于象征界一侧。自我是主体的想象的同化场所。拉康所说的“主体”,是指个体的言语、语言的等价物。主体是在精神分析治疗是提供给精神分析学家的文本。主体的和行为的一般结构,存在于“象征界”与之相联系的语言中。话语的象征功能具有一种主体间的社会文化的因素,它对心理“想象”层次所造成的人的主体性而言是重要的。
拉康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把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层,而是把主体心理分为三个层面,即“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想象界”是人的个体生活、人的主观性。它是现实界的前驱行动的结果,是在主体在个体史的生成基础上形成的。
“想象界”这个词包含了“映象”与“想象”双重含义,也包括与躯体、感情、动作、意志等种种直觉经验有关的幻想之物。它是一个欲望、想象与幻想的世界,是主体构成中的基本层次之一,是一种个别化与个体化的秩序,因而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想象界”不受现实原则的支配,作为欲望的主体,在“想象界”出现并自己创造着自己的“自我”。因此,在“想象界”水平上的个性自我设计是虚幻的。“想象界”具有的“幻想功能”使人在不现实中与幻想相整合。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我”,并未形成真正的主体,而是预先地设定它。“想象界”不受现实原则的支配,然而也不是自由无边的幻想。“想象界”与“象征界”有着紧密的联系。
拉康把“象征界”说成是一种秩序,是支配着个体的生命活动的规律,这使它很像弗洛伊德的“超我”。然而,与“超我”不同,拉康的“象征界”不实行强制,“象征界”同语言相联系,并通过语言同整个现有的文化体系相联系。语言把人的主观性注入普遍事物的领域,个体依靠象征界接触文化环境,同“他者”建立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客体化,开始作为主体存在。幼儿只有进入象征界才成为主体,才由自然人变成文化人。象征界的作用就是人的社会性与文化性的实现,以及人的性与侵略本能的规范化。
“实在界”永远“在这里”,永远在现在。“实在界”似可类同于弗洛伊德的“需要”范畴,具有“本我”的意味。实在界是语言对它起作用的东西, 或者是“语言达到范围之外的东西”(注:J.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pp.1-7.)“实在界”不是指客观现实界,而是指主观现实界,它是“欲望”的渊薮。
拉康的“主体层次”,虽然各属不同的逻辑类型,但想象界与象征界却包含于实在界之内。这三个层次具有使主体与他者和世界发生联系的功能,其中任何一个层次内秩序的改变都将影响其他两个层次。经过拉康的转换,“主体”不再是弗洛伊德的所谓本我、自我、超我的心理层次迭加,不再是认知过程的基础或本源,而只不过是各种心理功能之一,是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组成的系统。它并非与生俱来,也不必然存在。主体的存在取决于象征层功能的正常发挥。
因此,拉康的主体心理结构就是对主体的性质所作的结构分析。他把“能指”看作意识言语,而把“所指”看作无意识过程,进而断言无意识操纵着主体的言语表征,而且是绕过“我思”功能来操纵的。拉康纠正了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无意识在语言生效之前已经存在的说法,而强调无意识是与语言同时产生的,当语言与欲望配合不好之时,无意识便浮现出来,并由于话语的存在而强加给主体,因为,话语主体要使主体通过“能指的狭窄之路”(注:J.Lacan,Ecrits:A Selection.trans.by Alan Sheridan,New york,1977,pp.1-7.)。
在梳理了三者各自复杂的内涵以后,我们还必须了解这三者间的关系。简言之,这三者是从现实到想象,从想象到象征的梯级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由较窄的视野到更为广阔视野的视域推进。因为,拉康自己说过,这是人类现实性的三大阶段,而现实只是作为想象与象征的前提和界限而存在,因为,“在现实面前,词语被迫终止”。可以说,正是这三者构成了人的活生生的心理结构模式。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主体”即无意识主体,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抽象,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把主体与自我的区分过分地夸大,并将之对立起来,会导致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
3 问题与争论
拉康的“无意识话语”和“主体理论”,已经在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理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上进了一步,而具有自己的文化语言的特点。但是,拉康无意识主体理论,却受到了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诺曼·N·霍兰德的严重批评。
霍兰德在《后现代精神分析》一书的《拉康理论的弊病》中,对拉康理论进行了清理。首先,他认为,拉康的镜像阶段说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镜像阶段的阐释中,拉康并没有提出任何实在的论据,而仅仅是一种假设。拉康只是在文中论述了1903年以来儿童发育方面的一种状况,提到了一位哲学家马克·鲍德温的一本书,却未提及书名。霍兰德根据自己的观察,发现婴儿从六个月到十八个月的照镜行为,并非像拉康所称的那样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过程。婴儿从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整个阶段中,无一例外的都是对自己的镜像感兴趣并做出反应的。
霍兰德记述了布鲁克斯—根恩和米切尔·路易斯做的一项实验,他们趁一个婴儿不注意将口红涂在他的鼻尖上。当孩子照镜子并看到这处红点时,如果他摸摸自己的鼻子,那就证明他知道镜中的映像就是他自己的形象。这一研究显示,“孩子要到十五个月而不是在此之前,才开始对镜像等同于自己。那时他们才开始表现出自我意识的行为,比如在镜子面前摆了种种姿势,而不是拉康所说的喜气洋洋。简而言之,在十五个月之前,没有一个孩子能通过口红测试,而到了二十四个月时,所有正常孩子都通过了口红测试。这与拉康所描绘的图画截然不同,等到孩子能够认出镜中映像就是自己时,大部分孩子已经开始使用语言了。当孩子们辨认出自己的镜像时,他们显得紧张而局促不安,而不是像拉康所称的喜气洋洋(注:诺曼·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版,第196页。)。
我以为,霍兰德对拉康的这一纠正,是具有对话意义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拉康的镜像理论毫无意义。拉康也许在医学实证上有些疏漏,但是他提出这一理论的目的并非是说是十八个月的孩子还是二十四个月的孩子才能辨认自己,相反,他意在强调一种“非主体”向“主体”的生成,而且不断生成的活生生的主体性,时间的某些误差并不会导致理论的倾覆。就此而言,拉康的理论并没有失效。
进一步说,拉康的根本目的在于,将语言学研究引进心理分析理论。他强调,所有的自我形象,包括组成自我(ego )的那些形象基本上都是幻想性的。他通过这种镜像阶段想说明的是想象的自居作用,而且可以从中辨认出一种象征的自居作用。就此,他认为纽约学派把强化的“自我”作为心理分析的中心目标时,已经不可挽回地混淆了主格的“我”(I)和宾格的“我”(me), 从而也就混淆了想象的自居作用与象征的自居作用。所以,不可否认的是,想象和象征的区别的确是拉康镜像阶段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其主体学说的关键。我认为,从这个层面看,霍兰德的批评有些以偏概全的味道。
二 无意识的语言结构
拉康在1953年秋在罗马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罗马讲演》的文章,此文发表后有两种英译,一种被译为《自我的语言:精神分析中的语言的功能》,另一种译为《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范围》。这篇文章主要是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加以修正,进而提出这样一个公式,即:能指/所指(S/s)的对照。这样,能指和所指作为两种不同秩序的位置,就被一道抵制意指的屏障隔离开来。(注:J.Lacan,Ecrits:A Selection .1977.p.149.)于是,在拉康的公式中,能指和所指不再是索绪尔所说的像一张纸的两面那样可以彼此依存,相反,能指和所指的纽带已经被切断,它们成为独立的存在。所以,能指必须以意指的名义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滑动的所指”和“飘浮的能指”,“能指”什么也不表征,它只是自由地飘浮。
那么,这种“滑动的所指”和“飘浮的能指”说明了什么呢?拉康认为,他的“能指”就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意识,“所指”就是无意识,而无意识是语言的总体结构。所以,精神分析就是通过“能指”对无意识作出修辞性解释。
1 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
拉康指出,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也就是说,无意识本身的探讨必须从结构语言学的层次进行,而不能简单地从生物学的层面进行。因为说到底,无意识是隐藏在意识层背后的东西,只有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无意识,才具有一种内视语言的意义结构。事实上,弗洛伊德早已发现这种内视语言的结构,他是通过“梦”、“玩笑”中所说的“凝缩”(condensation)和“易位”(displacement),就可以用“隐喻”(metaphor)和“换喻”(metonymy)的转移来描述。而拉康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无意识像语言学中的隐喻和换喻一样,其形式方式应该参照“语境”(context),运用语言的规则来解读其中的含义。如果说,“能指”是意识,“所指”是无意识;“能指”是外显的梦,“所指”是内隐的梦;“能指”是症状,“所指”是欲望,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专门意义的“能指链条”。
拉康强调自己的精神分析学与美国精神心理学不同,因为精神分析学是研究能指的结合方式,研究一个句子中意指背后词义的词,并构造能指链条,而所有这些能指链条都是以无意识为基础的。只有通过能指与所指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才可能发现语言结构与无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就这个意义上说,无意识存在于意识话语的空白处,无意识内视于意识话语或本文,无意识是另一种文字系统,它在意识话语的空隙之间穿行,可以透过意识话语洞察无意识本身。当然,无意识除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它可以通过隐喻和换喻的象征来加以表达,从而对弗洛伊德有关梦的解释进行重新描述和阐释。
2 无意识作为他者的话语
拉康将无意识定义为话语,甚至看作“他者”的话语。这一命题是拉康的主体与无意识理论的关键。
无意识集中在心理结构的上层(想象界、象征界),它不是生物的需要,而是某种文化化和社会化的东西。无意识并非是无序的或不可控制的,而是有序的,具有文化性质的话语结构。拉康不仅看到了无意识结构的核心内容即移位与压缩机制,而且从语言学角度重新加以描述。认为在“症状”、“梦”、“动作倒错”与“笑话”中有同态结构。在它们之间有同样的“压缩”与“移位”的结构法则在起作用。这些无意识法则与语言中形成意义的法则是相同的。所谓语言学法则即隐喻与换喻的法则。隐喻用一能指代替被抑制的另一能指,换喻则使一能指代表另一能指。这样,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就意味着它们彼此以“空白”隔开的诸成分是彼此相连的。这些“空白”同实际的语词一样具有同样重要的功能。无意识的工作是映射“意义链”,这些意义链可能是不合现实逻辑的,是意义暂时隐在状态的存在序列。
在拉康那里,“他者”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他者”不仅指其他的人,而且也指仿佛由主体角度体现到的语言秩序。语言秩序既创造了贯通个人的文化,又创造了主体的无意识。“他者”是一个陌生的场所,而所有语言都诞生于此。“独立的主体”是不存在的。人向“他者”屈服,人的每一行为,包括最利他的行为,最终都来自要求被“他者”承认和自我承认的愿望。拉康为了不使“主体”概念孤立,而使其与“他者”共存,甚至为了破坏传统的主体概念扩张而采用了“他者”概念,并用“主体与他者”的辩证依存来颠覆主体的同一性。拉康一反笛卡尔的命题“我思故我在”,而说:“我思处我不在,我不在处我思。”
“话语”在拉康那里,只是指语言的话语的某种分词或某种结构机制,这种机制遍布于心理结构的所有层次,使一切层次的比较或从一个层次相邻一个层次的过渡成为可能。话语是某种一般分解原则,它既先于语言的各种形式主义,也先于实现这些形式主义的言语功能。言语实践是语词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条件,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处在前符号、前概念、前语言、前心理的层次上。拉康认为,心理、文化、语言三者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话语原则、文字书写,也就是以个体心理的东西和社会文化的东西为中介的形式形成机制,是一种空间,在此空间中,思想的表达方式在本体论上植根于存在,而躯体的生命则是由原初结构而充满活力。
拉康将语言与对象割裂开来,因为,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现实性完全被归结为人为的无意识结构的话语流露。将无意识语言化,使拉康能够利用语言学中通用的专门科学方法。然而,既然无意识被说成是研究任何问题的起始原则,所以这种方法也应当被绝对化了,其结构就必然走向语言中心主义。夸大无意识、无人称语言结构的意义,使拉康学说成为结构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体系和先验论成分聚集的焦点。
不难看到,拉康提出的“无意识作为他者的话语”的根本意义在于,他力求在人文知识体系中实现一场话语体系的根本变革。如今,这一理论对哲学、美学、文学的影响日益深远,并成为现代文艺“欲望分析”的重要范畴。
3 欲望的分析
拉康是把“欲望”的问题放到他思考的中心地位,尤其他后期的哲学更是如此,当然,众多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对“欲望”问题都比较关注,使得这一问题言人人殊。
“欲望”是与“需求”相区别的概念,因为“需要”总是对一个特殊对象的需要,而“欲望”是与匮乏相联系的,即欲望是超越了需要层面而产生出来的。欲望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产生,主体的欲望是对他人的欲望,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欲望便成了主体和个人形成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拉康认为,“欲望具有干扰和震动的力量”。(注: J.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p.68.)虽然欲望支配一个人,但是又能自我逃避能指系统的严密逻辑。
无意识是语言赋予欲望以结构的结果,语词没有把握住能指的实质,因为被命名的只是表面上的命名,欲望能够给予能指以意义。但意义只为主体所感,所以无意识是一种呈现,是对未被指认的欲望的呈现。拉康强调,婴儿对身外的母亲的认同受到了阻碍,因为他这种母子“双边结构”注定要被一种父母子“三边结构”所取代。孩子从父亲身上的“法”认识到还存在着一种更广阔的家庭与社会的网络,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只有当孩子承认父亲所象征的戒律或禁令时,他才抑制了自己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就是无意识。
拉康著作中,有一个关键的术语就代表了父亲这种性别符号即菲勒斯(phallus),指一种性别的含义。 拉康从语言方面重写了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言述。正是由于父亲的介入,孩子被抛入了“后结构主义式的焦虑”之中。他无穷趋近欲望,却不能满足欲望,而这种欲望受到外在的戒律,被压缩凝聚成为无意识。因此,他在接受外在语言和文化结构的同时,从想象界转入到拉康所说的象征性的秩序。于是从一个能指转向另一个能指的可能性是没有终结的欲望运动,所有的欲望都肇因于匮乏,欲望不断蠕动,以求获得匮乏的满足。
人们的语言正是依靠这种匮乏而产生作用。因为,符号所表示的恰好是真实对象的进入,而词语仅仅因为他者的进入或拒斥才具有意义张力。所以拉康说,进入语言就等于变成了欲望的牺牲品,语言被挖空而成为欲望之物,在欲望中语言遭到分裂。沉入语言就等于脱离了拉康所说的真实世界,而永远无法接近这个领域。所以,人们只能用一些替换物来代替另一些替换物,用一些隐喻来代表另一些隐喻,这样,使自我在想象和虚构中得以完成。
那么,有没有一种超验的意义或客体来支撑这种无穷尽的欲望的焦渴呢?拉康认为有,这就是菲勒斯本身,即一种超验能指。他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指示器,是把我们分离出想象态,置于象征秩序中的那个预定的符号而已。
可以说,无意识就是那些遭受到“抑制”的欲望。其所以成为无意识,就是因为孩童时代学会了语言。拉康就此指出,学习语言就是暴力,抑制和异化的开端,而人要进入社会,领到社会通行的语言的身份证,他就必须学会自己的名字而自我命名,这就是异化的开端。因为,我认识到除去我的种种欲望之外,我也仅仅是一个符号,是众多人中一个对象,是他们所说的“你”,这样一切都成了语言的空洞的能指形式。
进一层看,“比喻”就是以一个能指代替另一个能指,“转喻”则是通过连接性来表达意义;比喻是欲望的症状,这一症状在一个比喻性的结构中取代了欲望,而转喻就是欲望的显现,因为后来所有的欲望都是对最初欲望连接性的替代,每一个欲望之间都有连接的关系。接康就此进一步引伸说,现代艺术中具有的神经分裂,恰好就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比喻性或转喻性都消失了,是表意链(能指与所指)的彻底崩溃,留下的只是一连串的能指。这就是一种沉醉于现实中的感觉,把现实的一切都看成是破碎的、零散化的能指系统。这就是现代或后现代式的、当下精神分裂的欲望和欲望的坠落。
4 分析与批评
对拉康上述的无意识的语言结构,霍兰德同样做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首先,拉康竟然毫无批判地依靠索绪尔的能指所指语言观,而今天的语言学家已不再使用已经过时的索绪尔的模型了,这样用语言来理解无意识的过程,只能使无意识理论更加晦涩神秘。霍兰德认为,拉康唯一的重要性在于,他使法兰西意识到了精神分析。其次,他还强调拉康弊病的另一方面,即他的心理语言学。因为在拉康将索绪尔语言学的“心理学化”过程中,“犯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错误”,他将语言实体转化为心理实体是“能指和所指”,并将能指等同于所指,而将索绪尔的所指等于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索绪尔放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那条杠杆,被拉康等同于弗洛伊德的抑制。这样,“拉康把全部心理决定论都化作单一的语言过程,能指与指称另一能指。他竟然让现代语言学怀疑其存在的这一过程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注:诺曼·N ·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第191页。)霍兰德指出, 当拉康试图从心理学方面证实索绪尔的语言形式模型时,拉康是将自己的思想建立在自我经营的语言之上,那会使他的思想深深陷入反心理分析的泥淖之中,所以,拉康是一个完全反心理分析者,是一个行为主义者。
我以为,霍兰德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英美的语言分析病理学派的角度出发,对拉康所做的攻击,却并不具有完全的说服力。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杰姆逊的说法比较公允。杰姆逊认为,拉康转进了一种语言学现象中,他把恋母情结指定为主体对“父亲的名字”的发现,换言之,它包含在想象关系朝一种特殊形象的转换中,这是实在的双亲转换为一种新的恶意的父亲角色,这种父亲是以母亲占有者和以法律地位出现的。所以,无意识通过无非是获得语言的压抑而产生出来的东西,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交际环境中,就被拉康重新阐释过了。因此,杰姆逊认为,“主体的移置和无意识重新定义为语言,欲望的地形学和类型学及其具体化——这就是‘接康主义’的梗概”(注:刘小枫、王岳川、弥维礼主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257页。)。
可以说,杰姆逊对拉康既有对其理论偏激之处不满的地方,同时也对他理论的建树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当然,拉康的理论仅仅是提出了我们习焉不察的问题,他对无意识理论的全新的揭示,已然超越了弗洛伊德理论视界,它对语言的话语结构的洞悉,欲望的深入分析,无疑是有着知识增长和学术推进功效的。
三 文本阅读与叙事抑制
文本的解读是与叙事的抑制紧密相关。在民间故事和神话里,对“凝视”做了很好的符号学解释。凝视即转换整个系统的功能作用来窥视。拉康认为,在视觉经验中,凝视表现在视线和无意识欲望的轨迹的交汇点上,凝视在主体恰恰就是被无意识的话语所察看的人,因此,凝视超出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转换,超越替代而起的作用。(注:J.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p.78.)
将其精神分析学理论运用于“文本”分析上,使拉康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文本中词语本身只存在有意识的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能指和所指具有一种上下文的语境关系。(注:J.Lacan,Ecrits:ASelection.trans.by Alan Sheridan.New York.1977,p.163.)拉康提出“隐喻性替代”的说法,即无意识话语反过来将意识置于能指系统中,换位或位移叙述的无意识的欲望的位移,也就是说,叙述具有位移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这是在文艺作品系统位移活动中确立的法则。
对文本阅读的阐释的新颖之处,可能要数拉康对爱伦·坡的《被窃的信》所作的阐释了。爱伦·坡所叙述的故事框架是非常简单:王后刚收到一封密信,国王突然回来,王后匆忙之间只好把信堂而皇之地放在桌子上,希望这样反而不致引起疑心。恰好这时大臣到来,他巧妙地在王后眼皮下偷走了这封信,在原处放了另一封信。由于国王在场,王后无计可施,只好后来找警察总长去找回这封信。警察总长仔细搜查了大臣的住宅,但未能找到那封信,只好去请教业余侦探杜品(Dupin)。杜品只身造访大臣的住宅并轻而易举地拿到信。杜品分析能力超人,推论大臣也会像王后一样,不会将信藏匿起来而只会放在明处,因为放在明处恰好是最好的隐藏方法。这样,杜品发现信随便插在壁炉架上挂着的袋里,等大臣的注意力被引开时偷走信,又在原处放了一封相似的信。
拉康认为,这个故事揭示出一种“结构的重复”。在这种结构中,首先是发生在王宫中大臣偷窃信,而第二场发生在大臣家,杜品又偷了信,所以这是对第一场的重复。他指出,其中有两个场面,第一个他称为主要场面, 引起了全部故事。 (注:J.Lacan,"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Yale French Studies 48,1976,p.41.)在第一个场面有三个窥视(凝视者)者。即第一位(国王)的窥察没有见到什么;第二位(王后)的窥察知道国王没有发现而自以为保住了秘密;第三位(大臣)的窥察知道国王的茫然和王后的焦急,于是大臣拿走了王后收到的信,在原处放了一封空白的信。(注:J.Lacan,"Seminaron 'The Purloined Letter'".Yale French Studies 48,p.44.)那么,其中,第二场是第一场的重复,这两场显示出“三种窥察(凝视)”:第一种窥察是见而无所见的窥察,也就是国王的看和警长的看,他们对明处的和暗处都视而不见;第二种窥察是看到第一种看所看不到的,但是自己又被隐藏的秘密欺骗的一瞥,这是王后和大臣的窥察;第三种是前两种窥察都应该是隐蔽的东西,都让这一种窥察看到了,就是杜品。
拉康就此展开分析说,在“场景重复”中,“主体间的位移”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也就是说,那封信(letter)一词构成了双关语,在小说中字面义是“信”,而它的隐喻义是一种结构体系中的“能指”。这是一种精神分析的寓言,被窃的信成为代替无意识的隐喻。于是,那封不知内容的信,作为一个纯粹的能指,控制了主体群的行动意向。那个纯粹的能指,在主体中构成的微妙关系促使主体间的不断“位移”。所以国王和警长视而不见,是因为他们处在“能指的极限的位置”。而王后和大臣被双边关系所迷惑,在其中他们虽然看见,但由于处身其间而又不能完全看见,所以仍然具有盲点。只有第三个视点——杜品的位置才是全知全视的位置。但是,拉康马上就进行了补充,并对弗洛伊德主义加以理论的修正,认为杜品处于一个分析者的位置,也不应该是知道一切的主体。(注:J.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of Psychoanalysis,p.230.)他认为,杜品也应该隐入圈套之中,因为没有留下一封空白的信,以此报复大臣。杜品也偷了这封信,向大臣表明自己也暂时得到大臣所希望的控制王后的力量。这个故事作为主体的位移,使拉康感兴趣的是“欲望的结构”。这个结构要求挑出一些人,把他们置于三角形的位置上,在这种位置上不断地替换人物,表示出“结构的重复”。当人物活动的时候,信也移动到另一位置,所以,小说要说明的是:能指的传递在无意识的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所以谁也不知道信的内容或发信的人。
这事实上意指存在着三类不同的文本阅读者,一是像国王和警长那样对文本一无所知的阅读者,他们只能读表面的含义:二是像大臣和王后那样可以在文本中看到他们所能够看到的部分明显和隐在的意义;三是杜品这样的最高的解读,他可以打乱篇章的限制,而使欲望在篇章中重新定向,这种无意识使语言重新具有了活力。所以无意识在其结构里会显示出创造力,他是可以发现更多的意义的超文本阅读。
拉康以爱伦·坡的《被窃的信件》为例来说明这样一种观点:在作品中有着当事人所不知道的内容的信件(能指)成为行为的原因。因此,主体不是全知表述的主体,它是被事件或话语决定的说话的主体。由此拉康得出结论:人只是会说话的主体,人的本质在于,人只是会说话。这种非主体性的“主体理论”,在“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具有重要影响,直接影响到现代作家及其创作心态和人物心理结构分析。
拉康对文学解释和批评划了三层界限,即有限的阅读、两面性的阅读和全方位的阅读。他所称赞的正好是第三种——全方位的阅读。因为,对拉康式的精神分析批评家来说,这种阅读强调的不是擅用作者的意义,而是读者将作者的意义化归为己有,作全方位的阐释。因而,这第三个位置是意义分解者的位置,也是读者的最佳位置,能产生一种“革新的阅读法”。
但这种阅读法,在德里达看来却是“一种真理的供应者”。德里达说拉康把能指理想化,给了能指其本身没有的实质性,而且过分地将地将“信”看成是一种“性”(欲望)的主要能指,从而对文本施加暴力而犯了“性中心论”的错误。对此,霍兰德在《找回〈被窃的信〉:作为个人交流活动的阅读》中也认为,爱伦·坡的故事其实就是把信反过来,把隐秘重要的内部反出来,使它显得无关紧要。他同意德里达对拉康的批评,认为拉康所分析的最后是一种“无”,但是这种“无”本身就是一种“有”,因为,怀疑本身就是一种对怀疑的信仰。霍兰德深不以为然地认为,拉康把视角的变动重复和变化,变成了一种信条、一种方法,被他的信徒们机械地运用。
尽管对拉康的那种文艺的批评有多种意见,但我认为,拉康强调“无意识的欲望结构”是一种“重复的结构”,而且这一结构经常使能指失去意义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新意的。同时,拉康将他的精神分析阅读法施于文学作品,推进了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拓展了思维空间。他从弗洛伊德式的“泛性主义”作品分析中走出来,而使自己的文本分析具有当代文化和语言学的色彩。我想,其功当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