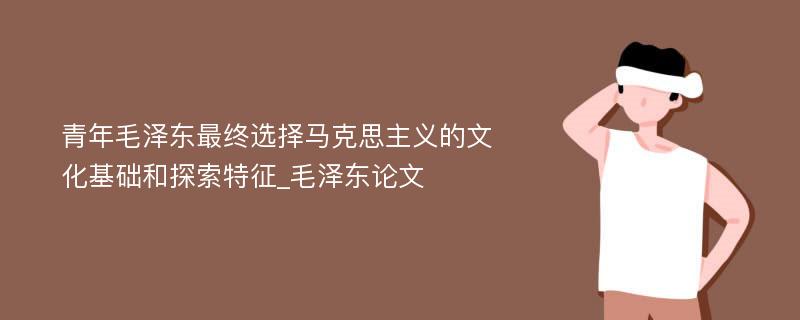
青年毛泽东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与探索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青年论文,基础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3)02-0085-09
一、时代潮流的激荡与湖湘文化的哺育
从1840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开始,随着帝国主义用洋枪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开始了备受侵略与欺侮的悲惨历程。这既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来侵略者的血与火的斗争历程,也是中西文化开始碰撞、冲突并不断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从魏源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历史步伐。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实干家与组织者,在中国所掀起的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以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而黯然落幕。中国新一代青年志士沉痛反思中国甲午战败的原因与教训,深刻认识到:花费巨大的洋务运动只是学习了西方文化器物层面的东西,而没有学习与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文明。于是,一场以改革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旧制度,建立民主新制度的政治改革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
在这场中西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中国社会大变革中,先进的中国人尤其是其中的湖南人之所以能够及时而敏锐地看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问题——政治制度,这与湖湘文化已经达到的认识高度是密不可分的。从中国近代“冲决网罗、思想解放的伟大先驱”谭嗣同的思想来看,他在进行清王朝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运动时,就提出了十分激进的民主变革要求,对封建君主制及其精神支柱“三纲五常”进行了猛烈攻击。这与他首先继承了王船山“纯是兴民权之微旨”,又吸收了“法人之改民主”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中西先进文化在谭嗣同身上交汇融合的集中反映。为了创立一套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的指导思想,谭嗣同以“精探性天之大原”[1]P49的探索精神,决心融合中西文化,包括吸收印度佛教的思想精华,创立了一个“仁以通为第一义”[1]P29的“仁学”体系,提出与西方列强及东方日本全面“通商”、“通学”、“通政”、“通教”,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通商富国”、“实业强国”、“科学兴国”、“变法救国”思想,并以鲜血与生命践行了他的救国理想,开创了流血救国、暴力斗争的思想传统。谭嗣同的亲密战友唐才常,进一步发挥了谭嗣同“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提出“欲开二千年来之民智,必自尊新始;欲新智学以存于鹰瞵虎视之秋,必自融中西隔膜之见始”。[2]P33为此,唐才常更系统地提出了“通商以富国”、“通学以新民”、“通法以维权”、“通使以建交”、“通政以改制”、“通种以保族”、“通教以促大同”等一整套“新吾中国”的主张。作为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民主革命的过渡人物,唐才常及其战友们以杀身成仁、血溅荒丘的英勇壮举,宣告了改良主义运动的破产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至20世纪初,中国大地出现了新的曙光。“古称山国”的南方内陆省份湖南又一次走在中国社会新变革的最前列。在迎接新世纪的最初春雷声中,先进的湖南人一方面更强烈地表现出“救中国自湖南始”的湖湘精神,这是由中国内生的先进文化——湖湘文化所培育出来的强大民族自信心、聪明智慧、英雄气概与精神力量的生动体现;另一方面则表现出更积极更虚心更全面更深入地向西方学习,从政治文明、社会制度层面来改革中国封建旧制度的英勇实践。这首先表现在杨毓麟于1902年冬写的《新湖南》和杨度于1903年10月写的《湖南少年歌》。杨毓麟在《新湖南》中高度赞美了王船山所开创的湖南“特别独立之根性”,以及魏源、郭嵩焘大胆学习西方的开放精神,尤其是热情讴歌了“直接船山之精神”、“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3]P35谭嗣同;同时亦更深入全面地介绍了西欧霍布士、陆克(洛克)、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与“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大胆地喊出了“以吾湖南为古巴,以吾湖南为比利时,以吾湖南为瑞士”,“欲新中国必新湖南”的革命呐喊。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则以清新激昂、脍炙人口的诗歌唱出了“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4]P95的千古名句。在他们擂响的春雷战鼓声中,湖南走出了一位伟大的“实行的革命家”黄兴,他怀着“建设共和新事业,铲除世界最强权”[5]P277的坚定信念,无私无畏地协助革命领袖孙中山创建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同盟会,勇敢地走在革命武装斗争的最前线,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与满清王朝进行“武器的批判”,生死百战,万难不屈,为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制度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与热血。这位“实行的革命家”黄兴也作了理论上的新探索。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民主建国思想、高扬民权的人民“主人论”与反对官僚主义的官员“公仆论”,以及一整套“政党政治”与“依法治国”论,还表现了对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与价值取向的最初追求。黄兴的亲密战友宋教仁,则以西方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为蓝本,为中国设计了一整套“三权分立”、“多党政争”、“政党内阁”的民主共和新宪政的新蓝图。正当他满怀信心地为实现自己的政治设计而奔走呼号时,却被袁世凯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使中国仿效西方议会选举民主政治的最初尝试遭到重创。中国由此而走向越来越激进的暴力革命与武装斗争道路。以“黄、蔡邦之模范”[6]P490而闻名于世的湖南另一位民主革命英雄蔡锷,不仅在辛亥革命中以光复云南之功有力地配合与支援了武昌首义,独具卓见地揭露了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多次表示了“长驱北指,直捣虏廷”、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决心;而且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公开暴露之后,义无反顾地在云南揭举“反袁护国”的义旗,以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坚决击败了袁世凯的军事反扑,为全国反袁斗争的蓬勃展开作出了榜样,赢得了时间,终于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而一命呜呼。蔡锷也以“再造共和”之功而彪炳史册。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青年军事家,蔡锷在军事理论上的新贡献就是他不仅充分吸收了欧美、日本的近代化军事理论与实战技术,也继承与改造了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特别是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新的反侵略战争的军事战略思想,从而丰富与发展了我国近代军事理论宝库。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与封建帝制,但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依然饱受帝国主义的压榨与欺侮,在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深渊中呻吟。在辛亥革命之后的1913年从西欧留学归国的杨昌济,目睹国内“政争汹汹,仅免破裂,人心风俗不见涤荡振刷焕然一新之气象,而转有道德腐败一落千丈之势”,对辛亥革命及中国近80年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与总结,认为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机器制造和政治制度,更要学习其精神文明——“精神之科学”,这就涉及整个国民思想的根本改造问题。他说:“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7]P200为此,杨昌济提出应首先改造中国的哲学、伦理学,创立一个新的哲学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最高指导思想,从根本上改造全体国民的思想。这比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同类见解,至少早一两年。杨昌济还认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只是中国向西方单向引进,也应有中国向西方输出的问题,这是一个双向互动、交流融合的过程。为此,杨昌济首次提出了“合东西两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主张:“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自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7]P202-203他还极其精辟地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民族精神,“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拆卸之则死矣。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7]P199这就充分说明,学习与引进外国的先进文化,必须与中国的国情实际相结合,不能不加分析地“全体移植”、盲目照搬。这一见解,在当时可说是空谷足音,卓见独具!这说明,经过近八十年“西学东渐”,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经验积累已达到了一个新的理性认识高度,即: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是双向交流、融合互益、共同提高的过程;学习西方不是盲目的“全体移植”、“全盘西化”,而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具体分析,善因善革,取舍何宜,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人在如何处理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上的最精辟的见解。
正是在杨昌济的直接教育与熏陶下,未来中国革命的领路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豪迈地提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6]P86青年毛泽东同样把人心风俗、思想道德的改造问题提到最高地位,进一步发挥了其师杨昌济的思想改造论,他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6]P86毛泽东后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抱负于此已见端倪。
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比较、选择、英勇斗争的过程,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8]P796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与发扬前人思想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最终从西方先进文化中“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从而为中国革命指引出一条走向胜利的正确的道路。这一最终的历史抉择是怎样作出的?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最终决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从中国近百年争取民族解放、社会变革斗争经验教训总结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而毛泽东则是作出这一伟大历史抉择的代表者。在成千成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尽管每个人作出这一选择的具体经历各有不同,但却像百川归大海一样投入到这一历史洪流之中,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舍生忘死地奋斗,这其中必然有其内在的历史规律在起着作用。我们从其代表人物毛泽东的思想探索经历的剖析中,即可看到当时大多数先进中国人的这一历史抉择的必然性!
二、青年毛泽东的知识构成与求学特点
正像生物的个体发育重演生物的系统发育一样,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历程也浓缩、凝聚、重演并集中反映了近百年先进中国人的思想探索历程。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早年所受的教育是旧式的私塾教育,读的是“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也曾同情和敬仰过旧式农民起义的英雄——一个叫彭铁匠的哥老会首领。后来又读过洋务派、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初步了解到中国所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在湘乡东山学堂,毛泽东开始接触西方的“新学”,特别是知道了“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崇拜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9]P113。1911年初,毛泽东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常常阅读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开始受到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写了一篇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文章,提出由孙中山“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9]P115。那时他虽然还不知道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梁与革命派孙、黄的思想差别,却在奋勇追随着不断更新的时代步伐。当辛亥革命爆发之后,19岁的毛泽东勇敢地投入了这一革命洪流,毅然地参加湖南革命军,而且是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这期间,他从《湘江日报》和江亢虎的一些著作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9]P117。在“南北议和”之后,毛泽东从军队退伍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精读了一位国文教员借给他的《御批通览辑览》,从中深受启发,其对知识的巨大需求量,使他感到“还不如自学更好”。于是,他在校6个月之后就退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自学了半年。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还读了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的著作,以及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神话故事。[9]P120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在20岁以前已经打下了颇为深厚的国学与西学基础,接触了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以及《忠精传》、《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通俗小说(在韶山少年时代所读),也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代思潮的激荡与熏陶,并初次参加了辛亥革命实践的锻炼。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启迪、教育方面,他在韶山的少年时代就已经读到有关美国革命的文章,对“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的历史向往之至;并在一部《世界英杰传》里,“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9]P114。可以说,毛泽东知识形成的基础阶段,就具有中西合璧(即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启蒙)、知行合一(参加实践)、与时俱进(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同步)的显著特点。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从此,毛泽东在其恩师、学贯中西的海内大儒杨昌济的直接指导下,对中西文化特别是哲学、伦理学、历史学作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认真研读,时间长达五年半之久。在这里,毛泽东认真阅读了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的著作,及《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楚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他认真阅读了杨昌济翻译编纂的《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哲学上各种理论之略述》、《西洋伦理学史之摘录》以及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伦理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受到西方从古希腊哲学、法国启蒙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系统熏陶,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洛克,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德国古典哲学家休谟、康德、费希特、叔本华、尼采、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上百位西方大哲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与了解。特别是汇集杨昌济几十年研究心得,融合中西文化精华,培养“圣贤豪杰之特质”的《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等课堂讲授与课外辅导,更是给毛泽东以终身受益的巨大启迪,为毛泽东未来平治天下打下了深厚的“预备功夫”。在这期间,毛泽东作为《新青年》的热情读者,也受到陈独秀思想解放、科学与民主的时代新思潮的激烈鼓荡,以更加成熟、自觉的战斗精神投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湖南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如果说1911年18岁的毛泽东是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满腔爱国热情投入辛亥革命,那么,这时的毛泽东则是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6]P390的主人翁的自觉精神投入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斗。
在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中,在过去数十年“西学东渐”的基础上,西方五花八门的新思潮进一步潮水般地涌入中国,正如毛泽东在1919年7月所指出:“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6]P364-365“于此可知世界思潮改变之速势力之大矣。”[6]P365-366这主要是因为: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空前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弊端与痼疾,有如“霹雳一声,石破天惊。举世滔天之祸,全欧陆沉之忧”,“若待爆之火山,若奇幻之魔窟,风云万变,光怪陆离”[10]P921,极大地震醒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我们曾经热烈向往与学习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原来也不过如此,它们并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极乐世界”,同样充满着贫富对立,剥削与压迫,灾难与战争!特别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惨痛经历,使先进的中国人越来越看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与丑恶嘴脸。这就使他们对原来追求与信奉的为资本主义降生而鸣锣开道、大喊大叫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说,如“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等,产生了怀疑;而对产生于19世纪的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旨归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包括刚刚诞生不久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介绍给中国人。早在20世纪之初,杨毓麟、陈天华、黄兴、宋教仁等杰出的民主革命家,他们在为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而浴血苦斗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看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与侵略伎俩,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目标。而且他们也已经初步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与社会弊端,对西方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热情的宣传与介绍。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甚至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刚刚举起中国民主革命大旗的时候,就幻想同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从而实现赶上和超过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宏伟战略目标。孙中山于1905年10月20日《〈民报〉发刊词》中指出:“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赌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环视欧美,彼且膛乎后也。”[11]P76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刚从国外回到上海,就约见了宣传社会主义的江亢虎,鼓励和支持他建立中国社会党,争取在中国能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早在1911年参加湖南革命新军时,就已经在长沙《湘江日报》和江亢虎的小册子中读到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只是当时先进中国人的主要精力还在为完成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目标而奋斗,社会主义还只是作为一种“学理”被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所探讨。
三、在不断探索、试验、比较中作出的最终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空前震撼和动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与流派中喷薄而出,放射出其不可战胜的真理的光芒。中国于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邃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6]P292这种思想解放的范围涉及各个领域:“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6]P393这种思想解放的力量如排山倒海、势不可挡:“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了中国任何时代。”[12]P697-698。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西方各种新思潮再次如潮水般涌入中国,除了“科学与民主”这一近百年学习西方的主旋律、主潮流,随着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弊端与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各种揭露与批判资本主义的新思潮、新学说、新理论表现了更浓厚的兴趣。一时间,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如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改良主义等各种学说,纷纷登陆神州,如百花怒放,争奇斗艳,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早在20世纪初就已被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等先进的中国人介绍到中国来了,但它只是作为社会主义各流派中的一种被介绍到中国,尚未引起人们高度重视,更未引入实践领域。只是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它所卷起的惊天动地的狂飙巨浪才开始从北方涌进了古老的神州大地。
在西方各种各样的学说、理论中,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这是中国人民长达半个多世纪奋斗、摸索、比较、选择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是“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才最终决定“以俄为师”,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并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其最终革命目标。那么,毛泽东则在1918年夏至1920年底,经历了两年多的艰巨探索,就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仰,成为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毛泽东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就能作出这样的思想抉择,真是超乎寻常的艰难。如果从他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开始,他的思想探索历程可说是浓缩了中国近80多年的思想探索与历史变革进程。他少年时代熟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及曾国藩等人的著作,可算是经历了洋务派的思想熏陶;后来又热烈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熟读过他们的著作,可算是重历了改良派的思想探索历程;刚刚进入青年,就勇敢地投入孙中山、黄兴所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受到民主革命的战斗洗礼,随后又如饥似渴地自学了严复翻译的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可以说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系统哺育。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毛泽东所主编的《湘江评论》被时人评为“眼光远大”、“魄力充足”、“议论精湛”、“内容完备”、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刊物之一。可以说,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毛泽东都认真地学习过,研究过,反复比较过,有的还真诚实践过。例如,1918年夏刚从湖南一师毕业,毛泽东就曾想试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工读主义”,计划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在岳麓山创立一个“新村”,“名之曰工读同志会”,建立起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人读书、共同劳动、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新社会”。1919年毛泽东在北京参加了王光祈创办的“工读互助团”的活动,这年4月回长沙后又再提此议,并在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了《学生之工作》,公布了他建立新村的具体设想。1920年春夏期间,毛泽东还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只是到了这时,他才感到“工读团殊无把握”,而决定另找新路。
对胡适所鼓吹的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毛泽东也曾受过其影响,并想在湖南建立“问题研究会”,起草过《问题研究会章程》,其中列举了“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国语问题”、“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等大问题达71个之多,加上大问题之下的分问题则有数百个之多。毛泽东不仅与胡适有过直接交往,他所创办的自修大学,就是“胡适之先生造的”[6]P475;而且在1920年10月杜威、罗素、蔡元培等人来湘讲演期间,他还担任过记录员,直接聆听了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改良主义的演说。
正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受到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这时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9]P125。也可以说这时他还在学习、摸索、比较、选择的过程中。可见,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在其初露峥嵘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尽管热情讴歌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欢呼“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6]P390。但他在介绍马克思与克鲁泡特金这两派学说时,更倾向主张温和改良的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他认为马克思是主张“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指资本家——引者)拼命的倒担”;而另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6]P341。可见,这时空想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还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据上风。
但是,深受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与“重行践履”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8]P125。他在1919年领导湖南新文化运动、鼓吹思想解放的同时,又发动了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政治斗争;在驱逐张敬尧之后,又发起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热情地希望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政治原则,实现湖南的民主自治。他为此先后写了10多篇鼓吹“湖南自治”的文章,提出了“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6]P690的具体方案,并希望通过湖南自治的榜样,“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6]P531。“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借助人民“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而上台的谭延闿、赵恒惕之流,尽管他们标榜自己站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派一边,却连这种温和的民主改良主张都不能接受,反过来对毛泽东发起的民主自治运动进行压制。这使毛泽东通过议会民主道路改造中国的理想彻底破灭。他在1920年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说:“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6]篇48这表明,毛泽东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已经彻底失望,迫切希望寻找、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来救中国。他对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30年的改良维新与革命运动作了这样的初步总结:“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易辙。”[6]P553此前不久,毛泽东曾把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作过比较,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宜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他在这年9月5日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说:“但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今译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我的先生杨怀中说:‘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四千年来一直到现在的老办法,结果得了一个‘没有中国’。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6]P507-508这说明,毛泽东此时对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已有相当了解,但尚未下最后决心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仍在满腔热情地从事湖南自治运动,鼓吹美国的“们罗主义”,幻想把湖南建成“东方之瑞士”[6]P680。可见,毛泽东当时追求与践行的主要还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与原则。只是在1920年11月底,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之后,毛泽东深受打击,痛定思痛,才深感“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结果均归失败”,自己所精心筹划与热情参与的湖南“自治运动”亦宣告破产,“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辟道路的首要之举,就是“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趋赴”[6]P554。这又回到毛泽东在1917年所主张的“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当时作为学生的毛泽东还处在探索的起步阶段,只是朦胧地以孔子的“大同”理想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大同者,吾人之鹄也。”[6]P89经过3年多否定之否定的思想探索历程,毛泽东又重新树立起“大同”理想:“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础。”[6]P560只是这时的“大同”理想,已不是中国老祖宗孔子的空想的“大同”理想,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毛泽东在1920年11月出的《新民学会通信集》中明确指出:“驱张”和“自治”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只是我们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6]P571据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他在1920年读了“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9]P131这是毛泽东在时隔十多年之后的回忆,可能记忆并不十分准确。据近些年国内党史专家的考证,以上所提三本书,国内分别于1920年8月、10月和1921年1月才出版[13]P87-90,毛泽东不可能在1920年夏天就读到这几本书。根据我们从毛泽东当年所写的大量文章与书信,以及他所从事的革命实践这两个方面考察,认为他是在1920年冬才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最终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最有说服力的根据是:当1920年底在法国的新民学会的会员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产生的两条道路、两种方法之争时,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蔡和森的走俄国式暴力革命道路的主张。当时以蔡和森为代表的主张是:“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式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以肖子昇、李和笙(即李维汉,又名罗迈)为代表的主张是:“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对这两种主张,毛泽东表示:“我对子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14]P4-5他进一步联系这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在长沙演讲所主张的用教育的方法和平地实现共产主义,同样认为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资本家不仅掌握着金钱,也控制着一切教育机关与社会资源,而且有政府、军队、警察、法律等国家机器对之进行强力保护,“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14J]P5毛泽东进一步对前此接触过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一次清算。他说:“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4]P8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4]P5-6不久,即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进一步表示:“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4]P15这既是毛泽东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思想探索的理论总结,也是他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的亲身实践中所得出的切身体会!是青年毛泽东最初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得出的科学认识,所树立的坚定政治信仰。如果说在1920年7月,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还在研究、考察之中,认为“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6]P154。那么时隔数月之后,此时的毛泽东已完全赞同蔡和森主张“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及蔡和森所概括的革命公式:“俄社会革命出发点=惟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15]P154这表明,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已经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已经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这不仅是以毛泽东与蔡和森为代表的湖南新民学会一批先进青年的抉择,也是当时中国一批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周恩来、赵世炎、恽代英、苏兆征、彭湃、张太雷、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抉择。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16]P1514正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苦斗,终于彻底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取得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开始一往无前地迈向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标签: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杨昌济论文; 谭嗣同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思想史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