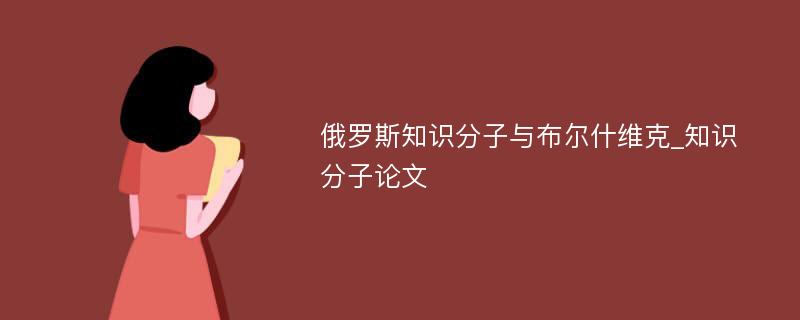
俄罗斯知识分子与布尔什维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尔什维克论文,俄罗斯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6)04—0078—(05)
一、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性
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比较独立的精神性团体与俄罗斯的历史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应该起始于1836年恰达耶夫在《望远镜》上发表的《哲学书信》。这篇文章激烈抨击了俄国历史传统的腐朽和农奴制的可耻,并以悲凉的沉重的笔调发出了“高贵的失望的呐喊”:“我们不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我们属于这样的民族:它不能成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1](P35—36) 对自己祖国的历史传统持如此极端悲愤的否定批判态度,既是西方现代性冲击后内心强烈的震撼和极度的失望的反应,又是典型的俄罗斯的方式。因为“只有经过这种强烈的自我否定,才能获得俄罗斯的自我意识”,才能为俄罗斯的伟大未来提供可能的保证。[1](P36) 在恰达耶夫浓郁的悲观主义气氛中,实际上始终贯穿着对未来的信念和企盼:“我深深地希望:我们将要解决社会制度的大部分问题,我们将使旧社会中产生的大部分思想走到尽头,我们将回答人类所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11](P37) 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晰地看到他内心深处那种对俄罗斯神圣使命的坚信和对尘世的上帝之国的追求及圣灵的新时代的期待。一方面秉承西方现代化普世性的观念,一方面是对俄罗斯特殊性的洞察以及深怀俄罗斯独有的弥赛亚思想。用赫尔岑的话来说,俄国思想史实质上就是从这封书信开始,后来根据对这封书信的态度确立自己立场的不只是一代俄国知识分子。[2](P4) 可以说,这种关系以后一直困扰着近现代俄国的知识分子:俄国向何处去?俄罗斯现代化究竟是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东方式的道路?究竟以革命方式还是以改良方式改造社会?俄国历史发展的落后、政治的专制、人民的极端苦难,这究竟是谁之罪?俄罗斯有没有前途?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这个俄罗斯式的命题(或者说恰达耶夫命题)无论对哪个时代哪个派别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甚至今天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个命题将贯穿俄国现代化进程始终并一直左右着这一进程的取向。
俄罗斯文化结构的内在矛盾和民族特性的深刻印迹以及西方现代文明的涌入,使得俄罗斯知识分子自出生就备受东西方张力的折磨,这内外两种基本因素的交互作用模塑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充满悖论的文化特性和极性分裂的精神气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既有强烈的“弥赛亚”救世情怀,又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精神。俄罗斯救世情怀源自于东正教,它强调俄罗斯作为“第三罗马”具有天神所赋的拯救斯拉夫乃至整个世界的伟大使命。俄国历代革命者都强调“俄国革命”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和对世界的普遍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又能看到他们对宗教的无情抨击和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精神。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列宁、托洛茨基等革命者身上都非常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双重性。
第二,既有强烈的人民崇拜精神,又有深深的精英统治思想。这种人民崇拜和精英统治交织的思想在革命民主主义、民粹主义甚至部分布尔什维克那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三,科学理性主义和反智传统奇特结合。俄国知识分子急切渴望用科学理性来改变俄罗斯的野蛮和愚昧。但是,俄罗斯人民整体的落后使知识分子陷于深深的孤立之中。这种孤立感又生发出一种变态的情绪,即认为自己有文化是一种罪孽,由此反对文化并竭力掩饰自己有文化及知识分子的身份。其实,这种反智传统是人民崇拜精神的一种变态反映。
第四,一方面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和道德优越感,另一方面又有高尚的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
第五,一方面能很快吸取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深陷俄罗斯旧文化传统泥淖,表现在思想上理论上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但在实际生活和具体操作上往往表现出专断独行,也需要制造神话和宗教式的崇拜,并习惯于采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方法。
最后,是对人民的强烈的终极关怀与根本无视其实际生活利益的矛盾交织。
俄国当代著名的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曾非常深刻地揭示过这种特质的根源。他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就其思想渊源而言,是从一种独特的宗教式的源泉中汲取营养的,他们可以与上帝同在,也可以反对上帝,但是不能没有上帝,就连无神论者亦如此。[3](P28) 18世纪反教会思想潮流、19世纪革命运动包括激进的虚无主义运动甚至20世纪俄国革命运动,似乎都只有从这一独特的源泉出发才能理解。所以,俄国知识分子能够把英法科学主义特别是法国的建构理性主义和德国的浪漫主义都一股脑儿吸收进自己这个消化功能并不好或不可能一下子消化的机器里。这样,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俄国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与基督教千禧年的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弥赛亚意识一致的东西就变得不难理解了。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激进倾向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中得益颇多,其实更多得益于基督教的启示主义传统。这个集基督教的启示主义、第三罗马说和西方建构理性主义特别是雅各宾主义的救世主义传统,一直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最强音。尽管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柔弱的新宗教运动也偶有回声,但从未盖过前者激昂的交响。
如果说西欧知识分子的激进同样也为专制极权留下空间如雅各宾主义等,但它始终存在一个与之抗衡的力量即保守自由主义。然而这种自由主义在俄国就没有真正存在过,这与俄国没有市民社会有关。后来即使形成一定规模的自由主义,也是处于两难的境地:“一边是‘改革的’专制政权(沙皇领导下斯托雷平政府推出的强行改革——引者注),一边是‘复旧的’‘民主运动’(对解散村社的抵抗——引者注),一边是不公正的‘自由’,一边是反自由的‘公正’”。因此,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的无所作为,与其说是出于苏联官方史学所称的‘软弱性’,毋宁说更多地出于斯托雷平改革中自由主义者所处的尴尬境地。”[4](P243)况且, 当时正值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更使自由主义立场不得不模糊。所以,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足够的道义力量来唤起民族的成熟和理智。俄国充斥的要么是激进的要么就是专制的情愫,而激进的最后又往往走向专制。
二、从知识精英到政党精英
从历史发展视阈来看,政党是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产物。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是现代化演进的自然结果,那么,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政党则通常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出现,政党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与其说是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造成的民族生存危机”,但无论怎样,没有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现代政党政治。[6](P19) 俄国政党和其他落后国家政党一样,是引领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需要的产物,体现为孙中山先生所言的“以党建国”的历史特征。[6](P191)
自彼得以后,俄罗斯经历的每一次现代化诉求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这种由沙皇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改革,其动力源不是来自自身物质发展和社会全体成员的共识,而是西方原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世界性扩张带来的民族危机、民族失败以及伴随改革而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引发的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分裂促成的。这一系列体制内的改革,不但没有改变原来极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不但没有消弭民族危机和改革导致的严重的社会分裂后遗症,促成社会转型成功,相反使应该受到抑止的旧势力在每一次改革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则成为一次高于一次的改革成本的承担者。这种现代化诉求的改革实践实际上完全把现代化所要求的时空连续统一性和特殊与普遍的整体统一性人为地分割、取舍开来,“使整体性现代化与特殊化传统性异质同构,双向异化,劣性组合,扭曲社会转型的健康正道,使社会深陷转型泥淖。”[7](P7)
产生于这种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与自己的祖国既恨又爱的无法割舍的关系,而历次沙皇专制体制内的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和俄罗斯完全缺乏西方式的市民社会的现实,又规约了他们在俄罗斯社会变迁中将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极其重要但又极为艰巨的使命:推进俄国现代化、实现俄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这种超强烈的使命感既是俄国的福又是俄国的祸,俄国后来的辉煌与灾难都与此有关。在如何推进俄国现代化的问题上,俄罗斯知识分子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道路。根据他们的思想,开始有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分(19世纪40年代前后至60年代),后来产生了民粹派(后分温和民粹派和革命民粹派)、自由派(有保守和激进之分)等并形成了不少秘密组织和团体(19世纪60、70年代至90年代),如“土地和自由社”(后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劳动解放社”等。但是,知识分子在俄国人群中所占比例极小,他们的声音因无法通过正常的公开的渠道传播而在社会上影响很弱,更何况,由于知识分子自身就像曼海姆所说的是一个“漂浮的”阶层,没有完整的阶级基础,与其要承担的重任不相吻合。俄罗斯知识分子既然自视为俄国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那么,他们就不仅仅要为俄国现代化提供思想动力,更需要在实践层面上作出直接的行动。于是,知识分子就要寻找阶级力量的依托,他们的政治纲领必须是代表他们所依托的阶级的利益的。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一些秘密组织或团体已经意识到并开始作出行动,如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劳动解放社”强调无产阶级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这些秘密组织或团体的组织化及其发起的一系列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政党行为的前奏。
当然,俄国知识分子组织化倾向并不表示就一定能产生政党组织。作为“最有表达力的现代政治组织形式”的政党,[8](P14) 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倾向进而走向政党是有条件的,这里不妨借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观点:“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有仔细考查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长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9](P33) 俄国在现代化开启后直至20世纪前后,其现代化进程屡屡受挫,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和行为日益激进,“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日趋膨胀,政治活动专业化的要求也愈益强烈。俄国现代化进程尽管不断遭遇扭曲和变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现代政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如文化条件、组织条件和传媒条件等,这种伴随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要求和条件“使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倾向明晰为政党倾向”。[10](P109)
再者,19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政党政治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已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西方工人阶级也利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政党政治所蕴涵的政治文化意义与政治实践方式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示范作用:他们“急切地在组织化的基础上寻找一个具有利益聚合功能的组织,一个新的大众动员工具,一个政治活动的专业化机构,一个具有政治权力取向的组织。”[10](P111) 他们急切地希望采用西方政党政治的方式或行动,使得知识群体能够通过参与政治实践、主导政治实践来改变俄国的命运。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相继出现了各种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如立宪民主党,它基本上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派人员组成。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产生到发展都是在沙皇专制羽翼下而生成了一幅畸形的骨架,处于一个尴尬两难的地位,导致它始终没有能够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成为主角,它只能是“陛下的反对党”;社会革命党,其前身就是代表村社农民、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主张农民社会主义或通过村社社会主义走现代化道路的民粹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接受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君主党,主要由皇公贵族和大地主阶级以及与专制体制紧紧联系的旧的习惯势力、狂热的宗教分子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组成,吸取了不少斯拉夫派的观点,反对资本主义民主,更反对社会主义,等等。组建这些政党和参与政党的早期活动都是由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承担的,知识分子成为俄国政党政治中最为活跃和影响最大的力量。这些知识精英转化为政党精英,他们为了维护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制订了纲领、战略方针和策略措施,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几乎多数时间是在秘密的条件下(除了君主党)展开活动。由于俄国资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够在力量上和道义上独立承担起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使命,这个历史重任开始是由几个革命党共同承担。而当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以后,所成立的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临时政府并没有显示出能够带领俄国人民摆脱战争、消除贫困、激起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及改善人民生活和实现社会平等及公正的能力,而这一切“成了一场新的革命的强大的促进因素”。[11](P240) 代表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布尔什维克综合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要求(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并将它们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联系在一起,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从革命的党成为执政的党,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从颠覆旧制度旧文化的先锋变成建构新制度新文化的创作者。
三、从“剧作者”到“剧中人物”
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虽然接受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但他们毕竟都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或抹去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特质深刻地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对历史的基本看法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包括他们对西方乃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同样不可避免带着这种矛盾的双重的态度来接受和解读。这种影响,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深入了解俄罗斯的国情而不盲目地照搬西方和教条式地信奉经典,塑造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政权。但也正是这种影响,使得这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越来越强化了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和俄罗斯知识分子那种充满悖论极性的特质,越来越把由特殊性带来的成功和胜利视为绝对的普遍的真理,逐渐偏离了他们革命的初衷、革命的目的,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期,对党内集中制的强调、对无产阶级纯洁性的重视和对社会主义文化与以往一切文化的区别等等都达到了绝对化的地步。所以,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上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出现了召回派和取消派,出现无产阶级文化派和马哈伊斯基主义,产生了取消一切党派的决议和后来如此激烈的党内斗争以及这种残酷的斗争方式。这些都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这种极性悖论特征有极大关系。
尽管少数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特别是列宁晚年深刻的文化自省和文化批判,重新解读根源于西方现代文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出了“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感慨,[2](P773) 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落后的国家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社会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对社会主义看法的“根本改变”,并没有成为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共识。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坚持列宁的通过新经济政策和文化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力量”严重缺失,主宰布尔什维克的仍然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充满悖论的传统精神。一方面,他们在思想理论上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又往往违背辩证唯物主义,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当作白纸上能够画上最美丽的蓝图一样简单。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思想与其说来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构想,不如说更多的来之于他们自己的想象和憧憬。列宁自下而上、通过利用市场这样一个温和的渐进的道路使他们那种救世主式的情愫和精英统治观念无法释怀,更与他们激进冒险以期通过强制性方式而不善于耐心寻找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解决矛盾的习惯格格不入。于是,列宁去世后不久新经济政策就被宣布结束,便成了非常自然的事;布尔什维克最后选择走向了一条不同于列宁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自上而下的仰仗无产阶级专政、依靠军事化、集中化的行政命令手段来强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路径,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了的。可以说,这是与马克思社会主义相背的、很像被马克思痛斥过的那种“粗陋的”、“虚假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本质上是已经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再版。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企图把一切都抓在自己的手中,甚至包括原来一切顺利进行,而且一直仅由社会力量管理而无官方干预的事务”,因为布尔什维克几乎认为,“就连小草也不能在阳光下自由生长,必须由‘政委’和他们的部下采取措施帮助它们生长”;[13](P240) 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把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把权力知识人自己,都交付给了中央委员会最后其实是交付给了一个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独裁者”。[14](P100) 这种由布尔什维克权力知识人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模式,最终成为迫害布尔什维克知识人的工具,布尔什维克权力知识人最终由这种社会主义的建构者变成丧失自己独立思想的附庸甚至受害者。布尔什维克是这段历史的创作者,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剧本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16](P147) 深受剧情的安排和摆布。这一切,表明俄罗斯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特征在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身上浸润是如此的浓厚,更表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不断进行自身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的极其重要性。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俄罗斯历史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