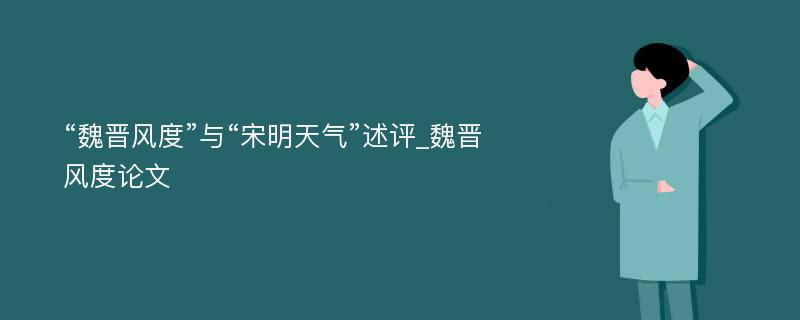
评“魏晋风度”与“宋明气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风度论文,气象论文,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作者对李泽厚、冯友兰关于“魏晋风度”、“宋明气象”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士阶层的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这一观点提出反驳。认为“魏晋风度”反映的是魏晋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封建专制制度扭曲了灵魂的士阶层的各种劣根性;“宋明气象”是江河日下的后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济欲之具”。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决不能嫁接于宋明理学的枯木朽株之上,也不应是“魏晋风度”和“宋明气象”的结合。
In this manuscript,the author contradicts the views held by Li Zehouand Feng Youlan that the"Stylish Way of Life in the Wei and JinDynasties"and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of Moralist in the Song and MingDynasties"represent the Lofty spiritual aloftn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intelligentsia.The "Stylish Way of Lif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the author argues,betrays the dark side of the distorted souls of theintellectuals who dragged out an existence in the feudalist despotismof the time,whereas the "Atmosphere of moralist in the Song and MingDynasties"gives the means to filled their lust of the ruling class inthe declining feudalist society.Both of them cannot betransplanted,separately or in their unity,in the current value grown out ofmodernization.
魏晋玄学的人生观是门阀士族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政策的产物。
1981年3月,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盛赞“带有玄学意味的魏晋风度”,宣称:(魏晋玄学)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觉醒”。同年7月,冯友兰致函李泽厚,对其为魏晋玄学“平反”大加赞赏,提出还要为道学“平反”、肯定宋明道学的“气象”(《中国哲学》第9辑第390页)。次年,李泽厚发表《宋明理学片论》,赞美宋明理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在李泽厚和冯友兰看来,无论是“魏晋风度”还是“宋明气象”,都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士阶层的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
“魏晋风度”和“宋明气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玄学家和道学家所代表的“精神境界”是不是那么庄严、崇高、伟大而值得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效法?反映这种“精神境界”的魏晋玄学和宋明道学作为“圣人君人南面之术”在学理上有什么内在联系,从而使得李泽厚在为前者翻案以后还一定要为后者翻案?对于这些问题,不能不认真地加以辨析。
魏晋玄学及其“风度”得以风行,反映了特权阶级的生活情趣和对经济政治特权的追求,而不是李泽厚所说的“人的觉醒”和蔑视功名利禄等“理想人格”。
一、魏晋风度:“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
透过魏晋名士玄之又玄、经虚涉旷的清谈,深探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知其世而论其人,就可发现,玄学和玄学家所代表的魏晋风度,从总体上可概括为三句话:以清谈服食为干禄之具;以玄远通脱为偷生之术;以任诞放达为享乐之方。这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被专制制度扭曲了灵魂的士阶层的种种劣根性。
以对农奴实行超经济强制之奴役的地主庄园为经济基础的门阀士族,自汉末以来,始终是以争取政治特权来保护和扩大其经济特权作为其“修齐治平”之宗旨的;同时,魏晋时期政局及社会之动荡不安,又使这一享有经济和政治特权的阶级(或阶层)在人生追求和观念形态上具有了与两汉经生之追求和经学意识形态不同的色彩。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虽然享有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中正制所规定的政治特权,但士族子弟仍要靠担任“中正”的门阀官僚给他们所定的品级来决定其占有土地和农奴数目之多寡,这就必须迎合当政的士族领袖关于“九品教化法”的标准。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来看,无论是曹魏集团还是司马氏集团,都采取了援道入儒的意识形态政策:一方面,坚持儒家传统,用“官、禄、德”诱使读书人当“佐主成化”的朝廷之士;另一方面,又鼓励在官禄德之争中持老庄的退让态度、“节虽离世而德合于主,行虽诡朝而功同于政”的山林之士,目的是塑造一批任职时“不谴是非”、同流合污,退隐后养尊处优、夷神委命的“贤才”或“君子”。从玄学家的人生观来看,动荡的社会和政局固然使他们对于“人生无常”的感叹格外强烈,但现实政治的需要和追求享乐的欲望却要求他们在“有”与“无”、“生”与“死”、“情”与“理”、“善”与“恶”、“名教”与“自然”、朝廷与山林之间找到平衡点,于是而有“体有而拟无”、“有情而无累”的“圣人之德”,有“有累而存理”、“缘有弊而用”的“君子之情”,有“在有无之间”、“不欲异于时”的所谓“朝隐”,有“入其俗,从其俗”、“若有意,若无意”的“容迹”与“寄通”,还有既“奉时恭默”、“安亲保荣”而又“永啸长吟,颐性养寿”的“与时浮沉”。所有这一切,正是魏晋玄学及其“风度”得以产生和风行的原因。它反映的是特权阶级的生活情趣和对于经济政治特权的追求,而不是李泽厚所说的“人的觉醒”和蔑视功名利禄等有限性的身外之物而追求精神的无限性的“理想人格”。
始倡玄风的正是主持九品中正制之实施的门阀士族领袖、吏部尚书何晏,王弼、夏侯玄为之推波助澜,史称“正始玄风”或“正始之音”。何晏这位执掌士子升迁之权的当政者既倡导玄学,士族子弟们自然趋之若鹜;何、王、夏侯三位“正始名士”因怕死而率先服药,“竹林七贤”紧跟其后,于是具有服“五石散”之经济条件的门阀士族子弟也群起效法。“风度”是服药的结果——这是精研古籍且通医道的鲁迅的卓越见解。“潇洒飘逸”:这是因为服药后皮肉发烧,怕磨破皮肤,所以只能宽衣缓带、脚踩木屐;为了发散药性,所以只能披头散发、衣带飘飘、木屐作响地外出“行散”。“扪虱而谈”:这是因为服药者穿旧衣更为舒适,要使旧衣耐久就不能常洗,因而衣内多虱。药性发作,“双眸朗朗如岩下电”;脱了衣服,“濯濯如春月柳”;喝醉了,“傀俄如玉山之将崩”;……如此等等,全都与服药纵饮有关。这一切,不是李泽厚所说的“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恰恰相反,对于身居高位的士族官僚和以此来争“上品”的士族子弟来说,这是腐朽生活方式的表现。正因为清谈和“风度”皆为干禄之具,所以士族名士们根本不可能做到“以无为本”,从而十分典型地反映着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颜氏家训·勉学》斥魏晋名士“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确实是有根据的。“正始名士”三人中,除王弼因病早死外,何晏、夏侯玄皆因与司马氏集团争权夺利被杀。但尽管官场如此险恶,名士们还是孜孜于利禄之追求。
在魏晋时期门阀士族统治集团充满血腥味的窝里斗中,玄学以其通脱玄远的“风度”发挥着其作为保命和偷生之术的功能。
封建专制制度靠使臣民恐惧的原则来维系,不敢要求获得“免于恐惧之自由”权利的名士们遂以其通脱玄远的“风度”来作为苟且偷生之术。“竹林七贤”中除了嵇康以外,都是拒斥崇高的。司马昭惧怕士人们有豪杰气概的真崇高,所以杀嵇康以恐吓士人;但司马昭又深愔,无论是礼法之士的伪崇高,还是风流名士们的拒斥崇高,对于维护其专制统治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他既需要那些被阮籍戏称为“褌中之虱”的伪崇高的礼法之士来为其正名分,也需要像阮籍那样的拒斥崇高的“褌外之虱”来为其收人心。所以司马昭屡屡盛赞阮籍“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把阮籍树为在专制淫威下“戒慎恐惧”、“奉时处默”的典范。即使是嵇康,有时也不免佩服阮籍的这套修养功夫,自云“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于“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人,如王戎、山涛、向秀、阮咸,官都当得很大,但都是尸位素餐,以玄远通脱自保。后来的名士们,如王衍之辈,虽然身居宰辅之位,但都以谈玄周旋于那互相之间如同寇仇的晋代诸王之间,以为保全性命和禄位之计。
儒家强调等级名分的“天理”,为门阀士族的经济政治特权提供了保障。只有通过考察“宋明气象”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才能对其作出真切的解释。
带有玄学意味的任诞放达的“风度”更是魏晋名士们的享乐之方。打开《三国志·魏书》、《晋书》,就可看到那时门阀士族的生活是何等糜烂!除了门阀士族地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之外,援道入儒的玄学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导致这种糜烂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儒家强调等级名分的“天理”,为门阀士族的经济政治特权提供了保障,儒家礼教中本来就有对于不同等级的人的生活标准的不同规定,有统治阶级的男子可以妻妾婢女成群而女子只能从一而终的双重两性道德,所以玄学家乐广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但另一方面,儒家礼教的一些规定又确实不利于门阀士族太放纵,如居丧期间不能饮酒食肉近女色,平时对妻妾婢女以外的女人也要讲男女之大防等等,这就需要用道家思想来补充儒学之不足。于是就有阮籍出来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声称“礼岂是为我辈设”,这种说法既反映了门阀士族地主以特权者自居的普遍心态,同时也为他们在必要时不遵礼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为“以孝治天下”的最高统治者所默许。名士周顗当着一大群名士的面要与另一名士的爱妾作爱,“露其丑秽,颜无炸色”(邓粲《晋纪》);“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沈约《宋书·五行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名士们的性放纵也与“服药”有关。我不知道李泽厚有没有读到上述“名士风流”的史料,难道这一切也是值得歌颂的风度,像他赞扬魏晋风度时所说的“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动人心的意绪情感”吗?
正统道学家标榜的“以德抗位”的“德”,不过是将特权阶层的私利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其实质是以“公义”“道德”的美名来维护特权阶层的特殊利益。
善哉叶适之言:“世之悦好(庄子)者有四: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虑,奸邪者济其欲。”(《冰心文集》)
善哉钱钟书之言:“魏晋士夫奔竞利禄而坦语‘玄虚’,玩忽职司而高谈‘清净’,……岂非道亦有盗欤?……王(弼)何(晏)乃盗道窃国之伦。”(《管锥编》第1134页)
二、宋明气象:“义理之悦,刍豢寓焉”
所谓“宋明气象”,同样要从它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来解释。以标榜道德伦理至上的正统道学家为代表的“宋明气象”,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假借大义以文其奸私的所谓“以德抗位”,神化“天理”以安享福泽的所谓“终极关怀”,推行恶俗以理杀人的所谓“伦理自觉”。什么“与天地合其德”,什么“孔颜乐处”,什么“天理人欲之辨”、“王霸义利之辨”等等、等等,无不是江河日下的后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济欲之具”。
首先,周程张朱等正统道学家所标榜的“以德抗位”,其实是假借大义以文其奸私。
北宋王朝以不到全国人口1%却占有全国土地70%官绅豪右兼并之家即大地主阶级为其统治基础,以“不抑兼并”、“不立田制”、免税免役等政策赋予其特权、助长其势力,而政府的繁重赋敛则是主要从农民缴纳给中小地主的地租中提取的,这不仅严重激化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更激化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反映到政治上层建筑中,就形成了中小地主阶级改革派(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大地主阶级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的激烈斗争。新党与旧党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保护官绅豪右大地主阶级的经济特权,而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就是要抑制官绅豪右的经济特权。这使得旧党无不咬牙切齿。缺乏道学“气象”的旧党士大夫坦直地谴责“王介甫小丈夫也,……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夺富民之利”(苏轼《诗病五事》);而富于道学气象的儒家“大丈夫”则打出了堂皇的“道德”旗号:程颢说新法是“以邪干正”,致使“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宋史》卷427);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介甫(王安石)之学害了后生学者”(《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张载亦从道德上批评王安石缺乏“与人为善”之意,“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宋史》卷427),如此等等。而旧党首领之所以欣赏道学家,就在于二程、张载的理欲之辨、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等等,都是与“荆公新学”相对抗的意识形态。然而,纵然是善于假借大义的道学家也不免要露出马脚,如程颢说新法“以贱陵贵”(《宋史》卷427),张载说“天理流行”的三代之治是使“富者不失其富”(《经学理窟》)。
宋室南渡以后,朱熹面对力主富国强兵恢复中原的浙东永康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流行、朝中主战派势力时有抬头的形势,也一再上书批评皇帝不能“正心诚意”、不能用“君子”却用“小人”、不能摒却功利,强调“王霸义利之辨”即“君子小人之辨”,亦大有“以德抗位”的气概;同时又借总结历史为名,谴责王安石“学术不正”、“骋私意,饰奸言,以为违众自用,剥民兴利”、“肆情反理”、“败国殄民”,把北宋亡国之祸归罪于王安石变法(《书两陈谏议谴墨》),目的是为了不让改革派、主战派重走王安石之路。后来尊崇程朱学说的元王朝编撰的《宋史》,遵循程朱的思路,将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人物章惇等列入《奸臣传》,章惇“奸”在何处?《宋史》对章惇一生的性行作了一段总评:“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宋史》卷471)明明是不肯任人唯亲的美德,却说成是“穷凶稔恶”。
正统道学家所标榜的所谓“与天地合其德”的终极关怀,
实际上是通过神化封建等级秩序之“天理”安享其富贵福泽。
清初学者颜元批评周程张朱等“有宋一代人物识趣卑庸”(《习斋记余》卷六),对明代道学家亦多微词,虽不为无见,但却没有说到根本上,假借大义以文其奸私——不仅是阶级的私利而且是个人的奸私——才是本质。程颐在旧党得势后当了崇正殿说书,马上就结党营私,与此他官大的蜀派旧党大臣苏轼争权夺利。程颐还亲自出马谴责蜀派大臣不关心“龙体”、乃至皇帝患疮疹多日还不知道去问候。由此激起蜀派大臣的愤怒,纷起揭露“程某之奸”(苏轼语),说他“污下险巧,素无乡行,……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谏议大夫孔文仲语)。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洛蜀党论》一文中,更揭露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摭语言文字之失以陷人于罪”的卑劣行径。至于朱熹为陷害同僚而对官妓施以酷刑逼供、明代大儒薛瑄为保富贵而不肯对将遭惨杀的民族英雄于谦伸一援手、王阳明被其夫人“枚数其平生奸私事”等等,都是学者们熟知的掌故。
其次,正统道学家所标榜的所谓“与天地合其德”的终极关怀,实际上是通过神化封建等级秩序之“天理”来安享富贵福泽。这一观点可以冯友兰、李泽厚最为称道的张载《西铭》、程颢《秋日偶成》等反映“宋明气象”的代表作来加以论证。
李泽厚所推崇的正统道学家的“伦理自觉”,实际上是强制推行恶俗、以理杀人的封建伦理异化。
《西铭》在宋明道学中确是具有纲领性的,它反映了儒家以“天地君亲师”为内容的“终极关怀”。《西铭》先讲“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把封建伦理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次讲“君”,认为皇帝秉受天命犹如宗法制中唯一有继承权的“宗子”,将帝王神化;再次讲“亲”:要畏天自保以敬亲,乐天不忧以孝亲;接着讲“师”:“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使人们都成为颖考叔那样的天之孝子;最后,强调人生的贫富贵贱都是天的良法美意:“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人活着就要顺事封建伦理之“天”,死而后已。只要认真读一读这篇“纲领”,就可以看出李泽厚所说的“与天地合德与万物同体的伦理学主体性”,“属伦理而又超伦理、准审美而又超审美的精神境界”,原来是怎么一回事。至于所谓“贫贱忧戚,玉汝于成”则是向被剥削者说教,而周程张朱这些“富贵”者们是不妨心安理得地享受其“福泽”的。
与其说玄学家是新道家,毋宁说他们是开始援道入儒的新儒家;至少可以把魏晋玄学看作是援道入儒而建立新儒学的尝试。
程颢的《秋日偶成》诗,是李泽厚乐于引用并以此论证“不怕艰苦而充满生意”的“本体论境界”的重要例证。所谓“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云云。程家世代为官,是地方上的官绅豪右兼并之家,何来贫贱,何来所谓“不怕艰苦”?而正是在那安享福泽的生活中,方感“道通天地”,对所谓上天给予的“厚吾生”的富贵福泽无限感激;至于“富贵不淫”,可用他既狎妓侑酒、又声称“心中无妓”来作注解。
第三,李泽厚所推崇的正统道学家的“伦理自觉”,实际上是强制推行恶俗、以理杀人的封建伦理异化。
体现玄学理念的“魏晋风度”维护并强化了儒家关于社会伦理道德教化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李泽厚说:“宋明理学强调在实践行动中而不是在思辨中来实现这个普遍规律(‘理’)。这种实现又必须是高度自觉的,即具有自我意识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在追求伦理学上的‘自律’,而反对‘他律’。”在这里,封建统治秩序被说成是科学的宇宙观意义上的普遍规律,强迫人遵守的吃人的礼教被冠以“自我意识”、“反对他律”的美名。诚然,礼教作为防民之术,封建统治者及其代言人总是要人严格以之“自律”的。然而,真正的科学的宇宙观意义上的“普遍规律”何在?清醒的而不是迷信和盲从的“自我意识”何在?发自人的至性至情的自律性的道德何在?正因为这一切在封建礼教中都不存在,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只能用残忍的手段来实行“他律”。张载和朱熹都有十分明确地主张恢复上古三代的肉刑来使“天理流行”的言论。肉刑包括墨(脸上刺字)、劓(割鼻)、剕(剁足)、宫(男阉割女幽闭)、大辟等五种,其中至少劓、剕、宫等三种是在宋代以前很久就已被废除了的。只是由于道学家提倡,这些肉刑在官绅豪右之家的私刑中还存在,尤其是施于女子的宫刑(幽闭),比施于男子的更残忍(见王夫之《识少录》及褚人获《坚瓠集》续集卷四)。以这些残忍的刑罚来维护礼教,难道是主张“自律”而反对“他律”吗?朱熹在漳州做官时还以法令的形式来强制妇女缠足,此后又重申程颐关于“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之义,导致强迫妇女缠足及殉死成为风俗,这难道也是主张“自律”而反对“他律”吗?事实是,只有实行严酷的“他律”,才能维护礼教所规定的皇帝的特权、官僚的特权、父系家长的特权和双重两性道德。
善哉陶望龄之言:“嗜欲难忍,又假理以通之;然则理者,尤济欲之具而害物之首也!”(《歇庵集》卷12)
善哉钱钟书之言:“本诸欲,信理之心始坚;依乎理,偿欲之心得放。……大欲所存,大道生焉;义理之悦,刍豢寓焉。声色货利之耽,游情凶杀之癖,莫不可究厥道源,纳诸理窟,缘饰之以学说,振振有词。”(《管锥编》第1133-1134页)这些话,真是揭露道学气象的绝妙好辞!
三、从“魏晋风度”到“宋明气象”:援道入儒的持续开展
为什么在为“魏晋风度”翻案以后就一定要为“宋明气象”翻案?除了前面所述魏晋名士“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与宋明道学家“义理之悦,刍豢寓焉”在“精神境界”上的相通之处外,在学理上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这又是一个不能不认真探讨的问题。
首先,关于魏晋玄学的学派属性。魏晋玄学究竟是属于儒家还是属于道家?提出这个问题,正如问宋明道学究竟是儒学还是禅学,或者,是儒教还是道教?冯友兰称魏晋玄学为新道家,称宋明道学为新儒家;李泽厚亦将魏晋玄学归入老庄类,将宋明道学归入儒家。我以为这种观点有双重标准之嫌。依我看,正如不能以很多人称宋明新儒学为“禅学”或“道学”就判定其为佛教或道教一样,也不能以前人说魏晋玄学家“祖尚老庄”、“不遵礼法”等等来判定其属于道家。如果判定是否是儒家只有一个标准,即是否在本质上维护特权人治的等级名分伦理道德,那么,与其说玄学是老庄学说之复兴,毋宁说玄学是儒道合流的开始;与其说玄学家是新道家,毋宁说他们是开始援道入儒的新儒家;至少可以把魏晋玄学看作是援道入儒而建立新儒学的尝试。
第一,玄学家尊孔甚于尊老庄,其立言宗旨是以道家的本体论来弥补儒学之不足。冯友兰自己也承认,魏晋玄学家“仍然认为孔子是最大的圣人”,认为孔子“比老子、庄子更伟大”(《中国哲学简史》第254、255页)。但他认为玄学家是援儒入道而非援道入儒。事实恰好相反,玄学家代表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以道家学说作为齐家治国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精于考据的乾嘉大儒钱大昕曾指出:“平叔(何晏)奏疏,有大儒之风;平叔之《论语》、辅嗣(王弼)之《易》,未尝援儒以入庄老。”(《潜研堂文集》卷二)他这话是有根据的,试看《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所载何晏上少帝曹芳的奏折,其中所讲的“修齐治平”的道理,全然是儒家《大学》的口吻。
判断是否是儒家只有一个标准,即是否在本质上维护特权人治的等级名份的伦理道德玄学家仍然具有从当时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来确定个体价值的儒家特征,而没有象庄子那样力主摆脱人际关系来寻求个体价值。
第二,体现玄学理念的“魏晋风度”维护并强化了儒家关于社会伦理道德教化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明代学者杨慎指出:“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一曰尊严家讳也,二曰矜尚门第也,三曰慎重婚姻也,四曰区别流品也,五曰主持清议也。”(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条引杨慎语)尊严家讳是儒家提倡的“孝”之极致。矜尚门第,体现着儒家之所谓门第高即意味着德高望重的精神,所谓“为政之要,不获罪于巨室”、“侯之门、仁义存”是也。慎重婚姻是儒家的礼教所特别强调的,因为婚姻在儒家看来乃是风化之本原,只是魏晋时代的婚姻对门第的要求极为讲究而已。区别流品,将士人分为九品,一品为“德行”,二品为言语、政事、文学,都是承续着儒家“孔门四科”及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而九品之区别,用何晏王弼的话来说叫做“贤愚有别,尊卑有序”,也体现着儒家名教的精神。至于主持清议,更是儒家“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的表现,虽不及东汉党锢之士,但仍在继续维护名教,这从王弼批评“不复应物”、裴頠“崇有”、乐广讲“名教中自有乐地”、王羲之颂扬儒家先王德行等等都可看出。这一切,至少都说明,玄学家仍然具有从当时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来确定个体价值的儒家特征,而没有象庄子那样力主摆脱人际关系来寻求个体价值。
“《庄子》向郭义”标志着援道入儒的新儒学初始形态的形成。
第三,即使是历来被看作“非圣无法”的嵇康、“背礼叛教”的阮籍,本质上也是维护儒家的纲常名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本是嵇康用以讽刺借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之名行篡位窃国之实的司马昭集团的一句话,这恰恰是他作为魏国宗亲和中散大夫坚持“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伦理的表现。嵇阮都讲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但与此同时嵇康又强调“审贵贱以通物情”(《释私论》)、阮籍强调“守尊卑之制”(《通易论》),都不肯放弃名教。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就曾指出:“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关于嵇康太相信礼教,鲁迅举其《家诫》为证。至于阮籍,我倒想补充一句:只要看载于《晋书》卷二《文帝纪》中那篇由阮籍起草、“司空郑冲率群臣”为司马昭劝进的宏文,就可发现,阮籍“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也是一个借崇奉礼教以自利的人。
宋明道学与魏晋玄学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是魏晋玄学援道入儒的的持续开展。
从何晏王弼到嵇康阮籍再到向秀郭象,魏晋玄学进入了第三期的发展。所谓“《庄子》向郭义”,更以“明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序》)为宗旨。如果说,魏晋玄学作为援道入儒的新儒学的初始形态,在何晏王弼的阶段儒与道尚且貌合神离,在嵇康阮籍的阶段是外道内儒的话,那么,在“《庄子》向郭义”中二者已是水乳交融而标志着儒道合流的新儒学初始形态的完成。
其次,宋明道学与魏晋玄学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是魏晋玄学援道入儒的持续开展。宋明道学继承了魏晋玄学“圣人体无”、“圣人有情而无累”、“名教中自有乐地”的基本精神,加以发挥,使之成为既援道入儒而又融摄禅学的新儒学的精致形态。所谓“圣人”之学,无论这“圣人”是指作为“素王”的孔子,还是作为对帝王的尊称,都具有“君人南面之术”的意义,所以玄学一变而为道学,是十分自然的。试看宋明道学家如何发挥魏晋玄学的“圣人君人南面之术”:
王弼的“圣人体无”的本体论命题和关于名教出于自然的论述,通过宋儒“无极而太极”、“体用一源”、“理一分殊”的演绎,而成为至高无上的封建伦理本体。其微妙区别仅在于:前者说名教出于本体,后者说名教就是本体。后者比前者更具有至上性和强制性。
王弼讲“圣人有情而无累”,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正因为圣人“神明茂”,通乎本体,所以能“应物而无累于物”(何劭《王弼传》)。宋儒对王弼的这一观点加以发挥:“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而圣人则能做到“廓然而大公”,“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因为圣人之情乃是“天理”的体现,所以能不为情累(《明道文集》卷三)。从“圣人有情而无累”到“圣人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全都具有将宗法社会的尊长推崇为“天理”之化身的意义。区别仅在于:后者认为圣人之情欲是“公”,凡人之情欲是“私”;圣人之情是“天理”,凡人之情是“人欲”,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方面是在更为巧妙地为统治者的纵欲辩护,另一方面又是对人民大众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无情扼杀。
至于乐广的“名教中自有乐地”的命题,更为宋儒所格外看重,由此进而探讨“孔颜所乐何事”;同时又按照其赋予自然以道德伦理属性的做法,使“孔颜之乐”成为体现名教之自然的本体论境界。这一“精神境界”既体现在张载《西铭》和二程语录中,更为朱熹的《论语注》所大加发挥。而如此一发挥,玄学中“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也就完全化解,无论贫富贵贱,只要安分守己,就有“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气象”。乐广的本意不过是说“名教”已经为门阀士族提供了足够的享乐特权,经宋儒一发挥,又外加要老百姓体验其“贫贱忧戚”之“乐”了。冯友兰要李泽厚为道学“平反”,说“由玄学一转语,便是道学”,确实没有说错。
面对“五四”以来新文化人对吃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李泽厚不能不承认宋明理学的“巨大现实祸害”,但他却充分肯定宋明理学在“纯理论上的成就和特点”。这种说法是如此不可思议:一种那么“庄严伟大”、那么“富于人情味”、从而“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主体性”的哲学竟然会造成“巨大的现实祸害”!如本文所分析,宋明理学之所以造成巨大的现实祸害,其实正在于其“纯理论上”的谬误:把封建名教神化为至高无上的宇宙伦理本体,以特权阶级的私利冒充“廓然而大公”的普遍规律,以作为特权阶级“忍而残杀之具”的“天理”冒充人的道德自律的主体性。至于李泽厚说宋明理学造就了文天祥和谭嗣同等志士仁人,更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臆说:谁不知道文天祥和谭嗣同都是反理学的思想家呢?由此可见,那种“从旧的中发现新的”的现代新儒学的一贯做法,只能是纯主观的牵强附会;而经过变革“从旧的中发展出新的”,才是尊重历史前进运动的辩证法(参见胡绳《理性与自由》第14页,华夏书店1949年12月第3版)。因此,如果要从整个人类和整个民族之前途的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决不能嫁接于宋明理学的枯木朽株之上,也不能是“魏晋风度”和“宋明气象”之结合,而应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之历史发展作具体而深刻的研究揭示,使现代人的精神境界建立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所揭示的普遍规律与作为社会实践之主体的现实的人之清醒的自我意识二者之结合的基础上,建立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实践所确立的关于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上。
宋明理学之所以造成巨大的现实祸害,其实正在于其“纯理论上”的谬误:把封建名教神化为至高无上的宇宙伦理本体,以特权阶级的私利冒充“廓然而大公”的普遍规律,以作为特权阶级“忍而残杀之具”的“天理”冒充人的道德自律的主体性。士之无耻,乃国之大耻,愿中国知识分子从“魏晋风度”与“宋明气象”的污淖中振拔奋起。
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盲目推崇“魏晋风度”和“宋明气象”者大有人在,在现行体制中自觉践履“魏晋风度”和“宋明气象”者更不乏其人,后者正是鲁迅所痛斥的那种对于“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的手法十分精通者,且这些人还熟谙“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日下的实利又何损哉?”(《十四年的“读经”》)这些“知识分子”是特别适应旧的中国国情的一群。官场和学术界的腐败现象,除了体制的原因外,正是此类人所造成。士之无耻,乃国之大耻,这是中国社会的大不幸!笔者愿再次重申自1988年以来屡次申述的观点:“必须首先启中国知识分子之蒙!”愿中国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从“魏晋风度”与“宋明气象”的污淖中振拔奋起,从此改弦易辙,勿自欺,勿欺人;勿欺世,勿盗名;勿歌颂升平,勿粉饰黑暗;勿受“官、禄、德”之诱而失其节操;卓然独立,诚实无伪,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做人,则中华幸甚,人民幸甚!
标签:魏晋风度论文; 儒家论文; 门阀士族论文; 魏晋论文; 魏晋风流论文; 门阀制度论文; 玄学论文; 宋史论文; 李泽厚论文; 西铭论文; 国学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名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