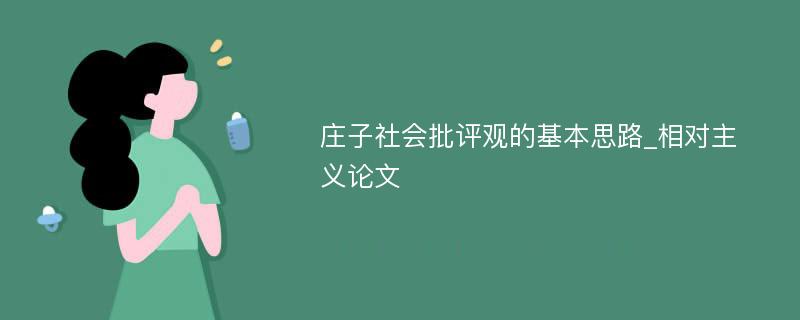
简论庄子社会批判观的基本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基本思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社会批判传统的奠基人和不祧之祖,庄子对专制君主、仁义道德乃至于整个人类文明的终极理性拷问,构成了他卓立不群的理论风格。这三方面的批判,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递进关系的逻辑序列:政治批判→道德批判→文明批判。本文的任务并不在于揭示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旨在剖解庄子完成以上三大社会批判所分别依循的基本心路。这就是:(1 )相对主义对绝对主义或独断论的权力话语结构的颠覆;(2 )自然“天放”的人性论对仁义道德理性秩序的感性抗争;(3)“无为”主义自然观对一切文明社会形态的根本拒斥。
一、相对主义自由意志对君主专制主义独断“逻辑”的内在消解
在某种意义上,正如没有尼采和爱因斯坦便没有20世纪西方世界波澜壮阔的相对主义思想运动一样,没有庄子也就不会有中国人在生活形态上的相对主义传统。从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广阔视域看,庄子思想的相对主义内涵都极为丰富,难以简单概括。限于学养和篇幅,本文拟将其复杂的哲学语义转述为如下若干层次:
一、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庄子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庄子·齐物论》以下引文凡引于《庄子》只注篇名)“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秋水》)这里,庄子指出,当我们说到“成”“毁”、“大”“小”时,我们总是自立为标准,而自然存在的世界并没有这个标准。于是,人为的度量衡作为“人”所约定的一个缺乏内在根据的标准、工具,也就只有相对的意义。既然我们赖以存在的自然存在的世界是相对的,当我们拿了这工具性的标准作为尺度时,它不应被价值化、绝对化。也就是说,当我们说什么是什么(或怎么样)时,我们是内在地设置了一个标准,而真正的存在世界没有这个标准,所以我们对任何事物只能说:相对于什么来说,它是什么样(或怎么样)的。
二、在价值论层面上,庄子认为,如果外在的物理实在没有一个绝对的时空参照系,这就在存在论层面上取消了“价值”存在的客观根据。无论人多么地需要一个“心灵的以太”来支撑脆弱的人生,人类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冰冷的世界。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秋水》)有没有一个特殊的人格,由于他具备有某种得自于“神明”的特殊性,从而使他有资格来为别人乃至全社会,设定一个价值标准呢?没有。这里,庄子很清醒地认识到:价值是一个属于人的领域。如果假设一个超越一切的“道”,那它对人的价值评价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如果让人(或物)自己为自己立法,他(它)便趋向于自保的本能,“自贵而相贱”。从世俗层面上看,一个人的价值不能靠自己来确定。
第三,认识论层面。庄子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是最难说清的。因为在庄子那里,“认识”,这个困扰西方哲学界几百年的大问题,本质上是不存在的。他不认为人可以自外于自然,“自立为主体”而进行所谓的“认识”,不相信人可以“真”的认识世界,并从而取得“知”,人只能在“心斋”“坐忘”等不大能说得清的沉思默想式的经验性活动中,来和大自然那奇妙的统一性(“道”)进行某种神秘的沟通。因此,庄子在认识论层面的相对主义,就是我们从前两个层面的中间,硬性拉扯出来的一个作为当代人不得不追问的问题。因为在庄子看来,既然世界的存在是相对的,而每个人的价值尺度又不可避免地是相对的,关于“知识”,就不会有一个真实与否、正确与否的标准,因而也只能是相对的。
以上就是庄子相对主义的三层内涵,即“齐万物”(存在层)、“等贵贱”(价值层)、“和是非”(认识层)。从这样的相对主义出发,任何真理的独断论倾向都会受到无情的消解,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专制政治垄断真理解释权的独断论。(请注意,在西语中, 与相对主义[relativism]相对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一词,同时即具有专制主义之意。)
一切社会法则所具有的规定性特征,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主观化的。它的客观性需要一个程序化的民主方式来确定、来保障。中国古代圣贤说了那么多“民本”的话,其实都未曾填补这一逻辑上的缺环。根据这种逻辑,把任何一种理念(如儒家传统)绝对化,使之作为专制君主独断统治的理论基础,这在庄子看来,本身就不合法。
儒家思想多为一些非逻辑的类比、附会,比如“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来自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而“君臣如父子”更是基于儒家“孝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的由血缘推出政治的动物原则。
这种“逻辑”强迫人们把王道政治这个神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实体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和思维模式,而不是相反,从人的幸福中推衍出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既然“君”和“师”是上天为民而设,哪一个个人有可能拒绝它呢?这种王道与天道的统一,政权和教权的混然不分,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就表现为暴力和教化的交互为用,连体互补。它一旦作为一个整体被观念地接受下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就只能从“孝”的自然伦理的必然中来体验“忠”的实惠和神秘。现实的专制君主不仅是“仰古以治今”(司马迁语)的历史承续者,而且是受命于天的神意传达者。在这种神秘的无法也无须论证的“统一”中,君主的统治被绝对化为一个无边的实体。
庄子断然否认了儒家对现实政治的这种想当然式的合理化程式。他勇敢地祭起了自然之道的大旗,用彻底的相对主义观念,对这种神学政治的独断性展开了无情的消解和批判。
在庄子看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自然“天道”是一种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的“公道”,而不仅仅是“王”的“道”。在“无所不在”(《知北游》)的“天道”中,“王”,没有先天的优越性。每个人都在“道”的面前获得了一份“德”,因而他们是平等的。庄子尖刻地嘲讽各个伦理—政治派别的“各为其所欲”“以自为方”,说他们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批评他们是“皆以其有为不可加”(均见《天下》)的独断论者。这种独断倾向就是在为专制君主作帮凶,就是为虎作伥。如果各家各派都能放弃自己的主观成见,以开放的心灵,宽容的态度去理解一下他人他派的观点,尊重他人他派的权利,平等对话,在辩谈过程中突显那昭昭的“天道”,就有可能进入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广义协变”的社会状态。
庄子这种充满怀疑精神的相对主义哲学,作为批判君主专制的理论根据,对后世两千多年人们反对“立六经以为准”(稽康语),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王夫之语),批判“天下之大害”的专制君王那“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黄宗羲语)的无道和无耻,都有着巨大的理论上的滋养作用。
但是,庄子对专制君主的批判,虽然可以说是在卢梭式的自然状态中达到了自由平等的境界,却未曾在“枢始得其环中”(《齐物论》)的相对主义旋转中为自己找到理论的“定轴”,从而为人类找到“心灵的以太”。也就是说,庄子看到了运动变化,却没有找到“超出各个运动环节之外”的“运动本身的固定之点。”(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9页)结果是, 在他残忍地剥蚀消解儒家的历史理性的同时,却又拒绝逻辑地推演自己的先验理性。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文化局面:独断、专制的历史理性被消解、被剥去了神圣的光环和合法性的硬壳,却又通过相对主义绕过了希腊式的悍然自立为主体的知性觉醒,绕过了人之所以为人所必然具备的自由的根据、平等的条件等命题,走向一种“齐物”的沉冥,“坐忘”的玄思;最终在“真知”中“逍遥”,在逍遥中“去知”,进入了一种既超功利又超价值的原生命精神状态。
结果是,儒家以“孝”为本的、伸向社会中的“血缘”触角,非但未被最终消解,反倒是为它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背景。“齐民”在“宗法”中整合,宗法在社会中推衍,从“家”社会中“蒸发”出了“国”,而国家往往就冒领了“天下”。于是,专制君主的神圣、合法性受到了儒家“王道”和道家“天道”的双重保证,社会之网在自然之网中不是被消解后重组,而是在消解中得到胶塑和叠加。
二、自然天放的人性论对仁义道德理性王国的感性抗争
从文武周公开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向社会推展的“家”天下“礼治秩序”,若从自然法的角度来考察,它实际承担着某种契约性社会功能。“周礼”作为约束人行为的一套行为规范,曾经取代殷商文明,使社会渡过了两三个世纪的平静岁月。周平王东迁后,历史进入了霸权迭兴的时代,霸权对秩序的破坏引发人们的思考。“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的孔子在用“仁”把“周礼”软化后,安放在人们心中的同时,却不断强调人对“血缘”关系的无法超越性。“人从哪里来”之类的追问在孔子这里是一个极为理性也极为简单的回答:爹娘生的。人既然是父母所生,“三年方免于父母之怀”,那么作为“回报”,你就要为父母的不幸亡故“服丧”,就要在父母生前不但从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精神生活上尽可能让他们享受人生的幸福和欢乐。一句话一个字:“孝”。孔夫子的理论核心是“仁”,而“仁”是根源于“孝”的。弟子们在整理他的语录编撰《论语》时开宗明义,录了一句“学而时习之”接着就讲“孝为仁之本”,这不是偶然的。“夫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矣,达乎天地。”(《礼记》)至于怎么个“达”法——至少,孔子从来不回答这类问题。当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当他说“敬鬼神而远之”的时候,他就把人类哲学追问的亘古情思推给了我们这里要说的庄子。这里我们不讨论庄子关于“人”的追问,只看他对孔子这种由“孝”而“忠”,由“家”到“国”,由“血缘”到“社会”等一系列等距离类比式的理论跳跃所展开的激烈攻击:
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
这是宋国太宰和庄子的一段对话,见于《庄子·天运篇》。庄子在此显然是有感而发的愤激之言,却“一语打破后墙”(金岳霖语)。是啊!如果整个的儒家学说都是以“孝”为基础(“仁之本”)的,那么,这也是动物界普遍遵循的原则。人“来源”于父母之爱,是父母爱情的结晶,虎狼又何尝不是?
如果在“孝”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仁义道德具有强烈的动物性色彩,那么,它对真正的人性(“性命之情”)就只能是一种损毁和贬抑。《庄子·骈拇》曰:“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岐;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噫!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也就是说,在庄子这里,人的自然的生命状态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价值意义,任何关于社会的规范、原则,都必须依是否有利于人的这种存在状态作为它“合法性”的唯一根据。因为人得之于自然之道的生命状态,自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凫不曾为腿短而难堪,鹤也不曾为腿长而不便,“凫胫”的短不能否定“鹤胫”的长,而“鹤胫”的长也同样不能否定“凫胫”的短,它们都自然合“德”,自会成就它本然已然的“道德之正”。儒家以“血缘”为基础的仁义道德,作为社会规范,说穿了,无非是想做一些“截长续短”的整顿工作,庄子说这是多余的。
与儒家的这种社会理性不同,庄子的人性论建构在经验层面上,表现为对人性的分层理解和独特叠加。在庄子这里,人性是被放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区别对待的。在物质层面上,庄子是一个拉美特利主义者:“人是机器”,主张人的“情欲固寡”。他认为“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逍遥游》),对物质生活中的人来说,五升之饭足矣;即使你南面为君,你能鲸吸海水,栖尽寒枝吗?
在精神层面,庄子对人的思维能力表现出最为狂放的艺术想象,他完全达到了恩格斯所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27页)。因此, 他可以像全智全能的“上帝”一样,在“无待”的神秘领域中进行“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逍遥”(《庄子·逍遥游》)。
把这两个方面叠加在一起,就是庄子的自然天放的人性论。庄子完全经验主义地说:“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盗跖》)怎么样满足人的这种需求呢?庄子由此开始慢慢离开他经验的大地,展开了他巨大的“垂天之云”般的想象的翅膀。首先,他认为“天下有常然”(《骈拇》),天下的这种恒常不变的性质表现在人性上就是“彼民有常性”,而这种建立在“常性”基础上的需求,通过人们“织而衣,耕而食”的劳动是可以得到满足的,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仁义”的框锢。在这种自由的本然生命状态下,人们可以说是进入了“同德”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类接受了一种难以接受的“依靠自身的存在”(马克思语)的“存在”状态,“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均见《马蹄》),既不需要神灵的福佑,更不需要社会假“父母”保护之名的禁锢。这样,庄子“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山木》),过上了一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
一种恬然本真的状态,一种混然的原始自由和平等,就这样没有社会约束(“义”、“礼”)地被建构、被设定为一种天真烂漫的本然生命价值,对儒家的道德伦理构成了彻底的否定。
三、用“无为”自然观否定文明本身
庄子的“无为”自然观,作为对大自然最高权威的无条件承认和服从,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通常被理解为人在大自然面前所应该保持的受动涵容的心态,即承认自然律与人类之间,是了无关涉的。他说:“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天道》)按李约瑟的说法,这是任何科学思想得以发展的第一个必要前提。
当庄子终于用受动涵容的自然观来否定文明本身时,他是用一种科学式的冷峻来审视人类文明,用一种高悬的价值理想,来对现实生活进行必要的批判。
正是人类自己的思想能力,把自己推进到历史之中而不是停留在“时间”中。但庄子在进行他深刻哲思的同时,却早熟性地意识到:一种不顾及人类个体自由、幸福的社会“治理”和历史“进步”,乃至于人类的自以为“知”的心态,都可能是十分有害的。他通过自己的反省能力达到了让自然“自省”的境界,就好像黑格尔让绝对精神旋转起来一样。黑格尔把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异化,而现实社会是对终极目标的异化。庄子却把人类一切文明进步,理解为对自然界有秩序和谐的“大美”(《知北游》)的异化。对自然的异化也就是对人的自然天放的人性的异化,对人类应有的生命本然状态的异化,说到底,是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异化。于是文明不仅无功,而且罪该万死。
那么,怎么办呢?庄子在《缮性》中写道: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返其性情而复其初。
古代的人就那么糊里糊涂地活着,恬静无欲,淡然无极但却是幸福地活着。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知识,但他们懂得那“‘一’与‘言’为二”(《齐物论》)的文明与自然相分裂的可怕,在“至一”中享受着道体的温暖和透明。后来,糟了。出了一个个的英雄人物,他们“离道以善,险德以行”,比赛似地和幸福背“道”而驰,一天天离人的自然本性越来越远,日益受“心”(也就是人的思维能力)的支配。结果,越用心越觉得知识不够用,只得日益想出更多的花花点子,越陷越深,终于来到了今天再也拔不出脚来的沼泽地,再也“无以返其性情而复其初”了。
还有办法吗?在庄子那里,似乎还有。那就是逆历史回溯,回到“古之人”那里,在历史的零度状态处,就是“道”的故乡,“德”的家园。
现在,包括两千多年后我们现在的现在,我们觉得自己“进步”了,我们为此而沾沾自喜,浅薄地为自己有了汽车,住上了洋房而得意洋洋,但在庄子那里,这勿宁说是一场灾难的开始。《庚桑楚》中庄子曾以危言耸听的语调说:“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英国学者布赖恩·马吉曾指出:“从批判思想出现以来,连同苏格拉底学派,不断发展的文明传统一直与反文明倾向并驾齐驱(更贴切地或许可以说,在其内部运行)。这种反文明的倾向的传统相应地产生了朝某种如子宫般安全的前批判社会或部落社会回归的哲学,要么前进到某个乌托邦的哲学。由于此类反动的理想和乌托邦理想,都满足同样的需要,因此它们具有本质深刻的姻亲关系。”(《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庄子要对现实展开某种批判, 对现实的批判需要和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在历史的线轴上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拉向前,要么扯向后;或前或后,有距离就有超越,有超越才能构成批判的张力。但是,一旦回到了历史的零度状态,庄子就不再处于历史中,而只是处于自然的“时间”之中。
庄子这种“悖论”式的批判,和二百多年前法国的卢梭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许多论者把庄子和卢梭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怀念人类“童年的天堂”,就像我们憧憬共产主义理想。
回想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牛顿式”科学理性的肆虐,反思黑格尔以来辩证理性的狂傲,庄子那看似幼稚的理想和危言耸听,实际却是极为深刻的警告:任何人(包括在不管多么发展的历史时期的人类)都不可能穷尽真理,从而彻底控制自然(包括人本身的自然),因此,在任何当下的现实中,必须在相对中对未来开放,对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开放。“绝对真理论”有时就是神学目的论,就是象征人类愚顽的“洞穴偶像”(培根语),它的后果是用理想杀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认为,文明对于人类究竟是好是坏,并非一件可简单了断的事情。进步的同时,人类的美好天性在颓化,在上位者勾心斗角,“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齐物论》),下层民众身受奴役之苦,披枷带锁者道路接踵。人类创造文明,这创造却反过来成了人类的负担和压力,使人类丧失了美好的自然天性,于是乎人类自己在创造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摧毁。既然西绪福斯的“石头”终究要再一次地滚落下来,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推上去呢?这就是人类命中注定而庄子却无法忍受的悲剧。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开始回过头来反省自己能达到的界限。恩格斯早已指出过人类对大自然的每次胜利都将遭到自然的报复;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一再警告人们要注意“生态平衡”和“增长的极限”;马克思所说的“对象化转变为异化”等等都是这个意思。庄子认为,要获得人类的幸福,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自然中去。正像卢梭所呼吁的那样,只有在人类童年的天堂里,人的自然天性才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示:快乐、自由、平等。
庄子文明批判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科学性,而在于它高悬了人类自由理想的价值目标,从而对现实保持着某种永恒的批判姿态。人类一旦进入“历史”,进入有能力“循理(逻辑)而想”的状态,就进入了一种思想与现实的张力结构中。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结构,是任何一种社会要保持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一种在科学理性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文明,假如它是健康的,应该敢于并欣然接受任何价值理性的批判。反过来讲,一种需要借助某种神圣教条来保障,从而拒斥公共舆论批判的社会结构,决不会是任何类型的真正的科学结构,而只能是不可持续发展的非理性结构。
标签:相对主义论文; 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庄子论文; 社会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齐物论论文; 历史论文; 天道论文; 父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