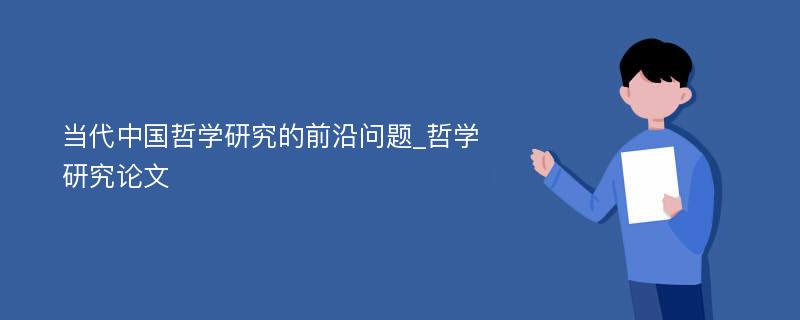
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跨入数字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小康型社会,时代和实践向我国哲学发展展示出新的平台和视野,要求哲学反思自身所面对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近十几年来,哲学的视野和哲学的问题域都世界化了,从原先的区域性的视野走向了全球性视野,从比较单纯的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跨文化比较,从对哲学体系和范畴研究的小框架走向了生动活泼的当代问题的研究。因此,反思我国哲学研究中的热点和前沿问题,既是我国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哲学思维方式的当代转向
1.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本质上是时代实践方式转向的体现。中国哲学界对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具有代表意义并揭示哲学内在特点的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包括哲学思维方式,正从静态的实体型思维方式转向动态的关系型思维方式。从哲学上看,实体型思维是“本体论思维”,它与几千年的“第一哲学”的传统密切相关,但传统的本体论思维实际上只是思维“什么存在着”或“存在是什么”,没有思考“存在怎样存在”、“存在怎样才是存在”,而深入到关系型思维,这就深化了原先的“存在”概念。如果说以前的本体论思维立足于单纯的“是什么”和“什么是”,那么现在的关系型思维则进入到“何为是”和“如何是”,即把“是”与“是的存在方式”结合在一起。
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哲学思维方式正在从现实性思维方式转向虚拟性思维方式。由于数字化,人类第一次拥有了两个真正的平台,即自然平台和数字平台,而数字平台的创立,使人类从现实性哲学、现实性的思维方式进入到虚拟性哲学、虚拟性实践和虚拟性思维方式。这里发生的最大转换在于,现实性哲学是把现实作为惟一的出发点,无论“是”“是什么”,“是”“如何是”,“是”都是现实的,人的思考都归结为对“是”的认识。在虚拟性哲学中,它的出发点是对“是”的超越,即不仅思维现实的可能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借助数字化的中介,人类可以对于现实的“不可能性”和“不存在性”进行思维,使原先的“是”的“不是”、“不可能”、“不存在”第一次成为人类的对象,从而导致了人类哲学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根本性转向。
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转向
第一,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回顾。
第二,对1978年以来哲学发展的回顾,发生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哲学研究方法的转向。
第三,对原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批判。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瞻望。对于进入到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提出了各种瞻望。
3.对中国传统哲学认识的转向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最近凸现出来的问题,本质上它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的哲学是否只有一个模式,即西方哲学的模式,符合西方哲学模式的就是哲学,而不符合的则不能称为哲学。这一问题随德里达在上海发表的“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意见而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百年回顾,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历史挑战,是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的历史性大反思。对这一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必然会导致两个结果:其一,深入对中国哲学传统特质的研究,寻找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元起点,也就是对中国哲学本身进行元哲学的思考和研究。换言之,在近代之后,我们放弃了中国哲学的传统,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而在我们走向21世纪的新时代,必须让中国哲学以自身的合法性走向世界。其二,当我们寻找到中国哲学的无可争议的哲学特质后,它同时也就是对西方哲学惟一合法性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否定。换言之,如果中国哲学也是哲学,那么,西方哲学就不能单独占有哲学这一形态,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种形态,只是由于历史的偏见和“西方中心论”的误读,把自己由一种哲学扩张为整个哲学。
二、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依据我国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哲学的前沿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对数字化时代的哲学思考,导致了虚拟哲学的产生,也形成对数码鸿沟以及数字化与人文精神的新思考。
虚拟问题与原有的哲学框架有着不同的特点,因为虚拟是用人化的形式来构建、合成和表达对象,虚拟若还只是停留在行为和语言符号范围内,那还是实践活动中的虚拟,一种代码形式的虚拟。在数字化时代,虚拟已经发展到用数字来合成对象;已经走出了语言符号的思维空间,成为一种真实的实践活动,这样的虚拟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哲学思维框架,是原有框架所无法概括的,所有这一切预示着数字化时代的哲学革命。
第二,对全球化的哲学思考,导致对全球平台上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国家和人的发展的全方位的新思考。
从哲学上看,所谓全球化,也就是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矛盾统一体,换言之,我们以前的活动的统一体是区域性的,而现在则产生了新的统一体。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矛盾的统一性与斗争性是不可分割的,新的世界性的人类活动平台,自然会有新的矛盾产生,在这里关键的是确立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达到共存、共赢。共存,就是我们共同存在于一个世界性的统一体和平台上;共赢,就是矛盾的各个方面如何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每一方都从其他各方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营养和因子,从而相互得到发展。共存、共赢是新的全球化时代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第三,对发展的哲学思考,特别是对全球问题的哲学思考,导致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产生,导致关于人类生存矛盾的新框架和新理念,导致从一种片面的“人类中心论”向“合理形态的人类中心论”的转向。
哲学历来是关注人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历来是哲学思考的重点。在21世纪,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它表征着人类由“人类中心论”进入到“生态中心论”,这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巨大转向。“人类中心论”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其核心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生态中心论”把人纳入到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中,人是这一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与这一系统的发展相同步。但在本质上,人只能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人永恒地只能从人出发,人不可能从“人类中心论”进入到“非人类中心论”,因此所谓“生态中心论”也就只能是一种“合理形态的人类中心论”。从一种片面的“人类中心论”进入到“合理形态的人类中心论”,这是人类在21世纪的世界观的变革。
第四,对当代科技革命的哲学思考,导致对一系列哲学热点和前沿问题的探索。
科技革命引发了一系列的哲学前沿问题,比如机器思维、克隆、基因、转基因、网络、暗物质、反物质以及一系列技术革命等,都成为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全面思考成为哲学的热点,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数字化和信息化,网络文化和网络伦理,基因和基因伦理,生态和生态文化,技术与人类的命运,世界跨文化比较,由全球化而形成的全球伦理和普世伦理,虚拟和虚拟政治、虚拟经济、虚拟创造,一些基本的物质现象如“黑洞”、“暗物质”,等等问题。
科技发展有一个方向问题,需要价值定向和人文关怀。因此,科技革命提出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技术与价值理念、自然与社会、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的发展等更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哲学思考的框架性转移。这也就是说,必须从全人类的发展、从全球性的存在的角度来重新思考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
第五,对人的发展的哲学思考,导致对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新思考,导致对人学理论的全面整理。
人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人类的活动由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现时代的信息文明,人的实践方式的变革对人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新的内容,诸如科技革命与人的自我认识,全球化与交往、价值观、人权的关系,市场经济与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可持续发展与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素质、人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与人性,社会变革与人的精神世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以人为本,道德建设与个人和集体、个性和社会性的关系,等等。
第六,对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思考,推进了对社会发展的哲学思索和研究,推进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使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三个代表”思想是一个整体,它表明共产党只有在“三个代表”的实践中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如果只代表先进生产力而不代表先进文化,那就没有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如果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没有超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只有把三者联系在一起,并落实到共产党人的行为实践中,使其成为行动着的思想,才能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引发了哲学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高潮,这是近几年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之一。
第七,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导致了我国应用哲学的繁荣。
在应用哲学中,比较引起人们关注的是:(1)各种具体哲学的产生,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行为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等的兴起和形成;(2)与各种具体哲学的兴起相关,如何使哲学的理念具体化到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行为中,如何使哲学与体制和行为规则层次结合起来,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也形成了新的热点;(3)哲学理论研究和表达的个性化,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它将会促成中国新的哲学和具有个人特色、个人思维方式的哲学家的产生,这是中国哲学走向成熟和发展的标志。
第八,立足当代实践,使原有的哲学研究普遍得到了深化。
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批学者首先提出并加以深化的,尔后实践唯物主义以及由实践唯物主义所主张的主体性原则、价值论推动了中国当代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把当代中国哲学推向了世界,因此,实践唯物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历史性、当代性的。在21世纪,实践唯物主义又引起了中国哲学界的广泛兴趣,主要在两个方面推进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一方面,对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继续深化研究;另一方面,从人的活动、生活、交往、生存等不同角度,对实践唯物主义加以开拓性的发展,从而对实践唯物主义有了更深刻的当代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