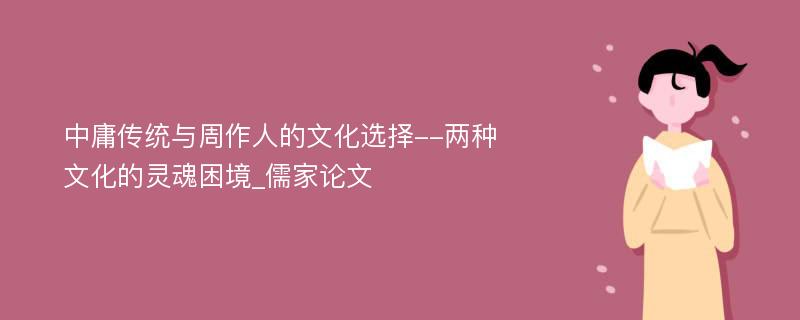
中庸传统与周作人的文化选择——两种文化之间的灵魂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两种论文,中庸论文,困境论文,灵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审视周作人,谁都避不开他从一个五四时期的文化先驱最后堕落为一个汉奸文人的人生历程。如何看待作为这一历程的依据的文化背景,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现有的从这一角度所进行的研究,至少可以说是薄弱的。本文试图从传统的儒家文化入手进入周作人的精神结构之中,以揭示和把握影响和推动周作人文化和人生选择的文化心理。
一
周作人曾宣称自己“赞美中庸”,但他却是“笑说”“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这里揭示着他思想中的某种矛盾,当我们理解了周作人式的“中庸”,也就知道了这“笑说”背后的意味是“偏用”中庸了。
周作人的确有一双独特的眼睛,他总是能够看出事物的“两端”,如人的兽性(人道以下)与神性(人力以上),平民与贵族,禁欲与纵欲,平和冲淡(出世)与焦躁积极(入世),绅士鬼与流氓鬼,叛徒与隐士等等,这大概也是一种“叩其两端”吧;于是他也总是将自己置于两端之中,试图“执两用中”。他在“叩其两端”的理论陈述中常常表现为从容自如、游刃有余。可在“执两用中”的人格实现中就显得捉襟见肘了,站在我们的角度上看,这后者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尴尬和困境。
“叩其两端”和“执两用中”是儒家的中庸思想。“中庸”在儒家文化里既是一个哲学范畴,也是一个伦理范畴,因而它既是一种世界观,又具有很强的人格意义,所以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注:《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注:《礼记·中庸》。)。中庸观念对周作人的思想方法来说,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他在看待各种问题时几乎都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如他所说:“生活之艺术即中庸。”(注:知堂《关于自己》。)“我们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执。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注:知堂《关于自己》。)他认为“微妙地混合取与舍二者”,就是一种“赞美中庸”的态度。(注:周作人:《瓜豆集·题记》。)
可以看出周作人的心愿是不倾向于事物的任何一端,在人的欲望上,是纵欲加禁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他要选择“过渡”位置,对待一切事物都要采取混合二者的中庸立场。
周作人的这种中庸态度,使他在现实的处境中常常陷入某种文化选择的矛盾之中,如在他的潜意识中,新世纪的文化重建主要是一种道德文化的重建,因而他做了一个不想做道学家的道学家,当他反观自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讨厌道学家,“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学家的缘故”(注:周作人:《雨天的书·序》。)。历史知识告诉我们,儒家文化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模式;西方文化的社会理想是以法制模式为代表。这表明作家在中西文化中自觉不自觉的做了选择。不仅如此,恐怕他的所谓“新的道德”,也是建立在儒家伦理精神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周作人后来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可以说已经讲得相当的明白了,他说:“我的道德观恐怕还当说是儒家的”(注:周作人:《自己的文章》。)。他的一生都是在这种中庸所带来的矛盾中挣扎着,他生活在一个社会思想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那突如其来的各种新鲜玩艺儿都曾触及过他。“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都令他兴奋,令他仰慕,对这一切他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就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注:周作人:《中山杂信》。)。这是周作人式的苦闷,他在各方面都想实现某种“调和”,但在实际上却常常是一个虚幻的梦。
在他的作品中这种困惑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就总的方面来说,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中,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周作人一直追求和希望他的作品能达到一个冲淡超脱的境界,但他好象并没有实现,不然,他就不会感慨自己做不好文章和“纯文学”(注:参见周作人:《苦口甘口·序》。),不会把自己的文章说成是“无用也无味的正经话”,是“儒家气”(注:参见周作人:《苦口甘口·序》。)。这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周作人始终说儒家的东西无用,可他却一直在明里引用,暗里流露和体现着儒家的文化传统。由此我们也该明白他曾说他童年学的那些儒家经典对他“毫无益处”的真正含义了。
周作人为什么总想超脱,写出来的文章自己读后又常觉是一些“有所为”的“说教集”呢?这里,一方面说明他对平和冲淡人生的向往,另一方面说明在他的灵魂中还有对民众的同情,对社会的关心,是一种入世的使命意识,一种“推己及人”的救世精神在支持着他的这一人格侧面。这种“有所为”无论在多大的意义上表明着作家为拯救民众、使全社会走出黑暗的努力,都透露着周作人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认识。如果是一个纯粹的个人本位主义者,我们就无法解释他的文学中的对社会、对历史的焦灼和积极,无法理解他的所谓“师爷气”所体现出来的对人间丑恶与不平的冷峻态度,我们只能用周作人式的“中庸”眼光来看待周作人,我们只能说周作人既是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个人本位主义者,又是一个心中藏有“修己安人”的儒家传统意识的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但我们必须看到,周作人思想中的儒家文化因素在他的“执其两端”的思考模式中,有时会表现出一种“误读”和扭曲,尽管对周作人而言,很难说全都是有意的。
二
周作人的所谓中庸主义有着尖锐的内在矛盾,使得他在文化选择和人生选择上犯了“价值尺度迷失”的错误。周作人的精神姿态一直是摇摆不定的,他虽在反传统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中国传统的整体性一元论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但他对待儒家的中庸思想时,却既有“执两用中”的愿望,又有多元主义谬误。周作人从五四时期就仿佛用儒家的中庸思想来认识人和社会人生,但他的“中庸”思想中缺少了儒家中庸思想的一种最重要的价值。
儒家的中庸思想的核心意义是孔子说的“中行”,孟子说的“中道”。孟子说:“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注:《孟子·尽心下》。)所谓“中道”,就是中正之道,“中”的价值目的在于“正”,即“中道,中正之大道也。”(注:东汉赵歧:《孟子注疏》。)“所谓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个恰好的道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注:朱熹:《答张敬夫》。)儒家文化的所谓“中”是“正道”,“庸”是“定理”,正如朱熹所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注:《中庸章句》。)
儒家的中庸思想认为事物都有对立统一的两端,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两端,要持“和而不同”的态度,即孔子所说的“叩其两端而竭焉。”(注:《论语·子罕》。)同时,事物的两端又可统一于“中”,“中”是正道,强调立身处事应时时合乎中道,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注:《礼记·中庸》。)因为事物都有其维持有序状态的准则,它的倾向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转向反面,所以孔子说“过犹不及”(注:《论语·先进》。)。表面看来,中庸之道具有较为广泛的实践性与操作性,但当人们真正将它作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时候,如欲实现既不“过”也未“不及”,却是十分困难的,也就是说,人们常常认为以中庸之道立身处事比较稳妥安全,实际上它的危险性仍然不小。周作人的中庸主张给他带来的多表现为某种困境。
儒家虽讲究中庸之道,但其思想的价值尺度是单一的,纯粹的,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只有寻找和奔向“中正”之道这个唯一的目标,即孟子所说的“君子返径而已矣”(注:《孟子·尽心下》。),才能实现君子人格,才算真正掌握了中庸之道。儒家所强调的是,在坚持中庸之道,面对各种事物时,都要以一个价值系统作为判别尺度,如孔子所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注:《孟子·尽心下》。)所以孔孟将那些心中没有原则,没有严格的价值尺度,随波逐流的人称为“乡愿”,而不认为这种人是坚持中庸之道的君子,相反将乡愿视为“德之贼”,即德行的损害者。
周作人说自己是“一个中庸主义者”,也承认自己“很有点象‘乡愿’”。而他对待各种事情和现象却不去加以区别和判断,并将此视为他对人生世事“宽容的理由”。(注:参见周作人:《〈谈虎集〉后记》。)
儒家的中庸之道有两个不可忽视的思想,一是正反、上下等方面的调和与互补;二是强调“中正”的价值尺度。儒家中庸之道的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也必须以“中庸”的思想方法来认识和把握,偏废任何一方都是一种危险的背叛。周作人主张对世间的各种事物、各种思想采取“于杂糅中见调合”(注:周作人:《药物集·谈俳文》。)的态度,主张在各种事物和思想理论面前不居一家之言,宽容共存。这些观点和主张,他自己虽说并没有子思的“那一部书”的背景,还是明显体现着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儒家思想是一种道德文化,价值意义是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和灵魂,价值判断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姿态,疏离了它的价值意义,偷换它对具体价值意义的本质规定性,都是对儒家文化的误解和扭曲。儒家以“恐其乱德”的基本动机坚决反对“乡愿”,就是强调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周作人的人生态度所缺少的,这正象他在描述自己的人生向往时所说的一样:“我们——只想缓缓地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地享受这些应得的苦与乐,至于路线如何,或者由西四牌楼往南,或是由东单牌楼往北,那有什么关系?”(注:周作人:《谈虎集·寻路的人》。)周作人正是以这样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来进行他的文化选择,因而周作人在“价值尺度”上恰恰与儒家的中庸之道出现了紧张。
他一方面将本来是具有同样内在价值的儒家的“仁”与“恕”对立起来,提出人生“有两种对外的态度,消极的是恕,积极的是仁。”(注:周作人:《逸语与论语》。)周作人将仁与恕分别开来,以为这样便可以取其“恕”作为他逃避现实的思想依据,但实际上儒家的仁和恕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儒家的仁与恕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孔子给恕下的定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卫灵公》。),就是要求人们以对己的态度来对待他人。朱熹对恕的解释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注:朱熹:《论语集注》。)。朱熹的门人陈淳对恕的理解是,“夫子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就一边说。其实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须要施于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达,人亦欲达。必推己之欲立、欲达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达之心,便是恕。”(注:陈淳:《北溪字义·忠恕》。)由此可见,恕的内在价值就是仁,从这个角度说,恕与仁的意义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恕为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仁的实践形式之一,不然,孔子为什么说“恕”“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注:《论语·雍也》。)呢?孟子说的“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注:《孟子·尽心上》。)的含义,不也是说勉励地推己及人地对待世事人生,是求仁的最佳途径吗?周作人所理解的恕只是没有儒家思想价值倾向的宽容,他虽然也将恕视为消极,但他所认同的却是消极的“恕”,而不是积极的仁,所以他说“似积极与消极大有高下,我却并不一定这样想。对于自救灵魂我不敢赞一辞,若是不惜用强硬手段要去救人家的灵魂,那大可不必,反不如去荷蒉植杖之无害于人。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于隐者的同情”(注:周作人:《〈论语〉小记》。)。这样一来,儒家的仁与恕在周作人那里,后者才成为适应时代的明智选择,而他所谓的“恕”又实际上是既不“推己”,也不“及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宽容主义。
与此相关,周作人在另一方面又等于将儒家的仁义、忠恕等道德价值加以空洞化,放弃了儒家的齐家治国主张所体现的强烈的爱族、爱国和爱群的基本意义,对各种事物近于无原则地加以调合,对各种观念和行为给以宽恕,如他在《关于宽恕》一文里以张良和韩信为例证,过分强调人生中的宽恕态度。如果说他在《日本的衣食住》、《怀东京》、《日本之再认识》等文章中所表达的日本生活的“舒适”、“有趣”,令人向往,把东京说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并使他颇多留恋等观点,在文化的视角上看,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可称为宽容的态度,那么,他在《留学的回忆》中,与日本侵略者唱同样的调子,把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为“兴亚”,在《中国的思想问题》里,将日本侵略者为其侵略行为辩护的“共存共荣”的宣传,说成是以仁为中心的中国思想的体现,是附和“人”的生存道德的行为等主张,就只是打着儒家的仁学思想和忠恕观念的旗号,而儒家文化的价值意义就完全被偷换掉了。可见周作人自己说他“很有点象‘乡愿’”,大概也是一种较为准确的自觉吧。
既然周作人的中庸主义是一种“价值尺度迷失”的人生态度,那么他最后的附逆投敌就较为容易在他的文化背景和精神结构上得到某些解释。
尽管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自称是中庸主义者,也在各种文化与人生场合里运用他所谓的中庸观念去对待世事人生,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与儒家文化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主义式的联系,而不是实质性的关系,因为周作人并没有对儒家文化的个性本质有实质性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周作人的“中庸主义”并非是一种实质性的儒家的中庸之道,在周作人精神结构里,中庸之道的符号意义处在更为显赫的位置。
三
1925年徐炳昶在给鲁迅的信中说中国人的根性是“惰性”,其表现形式一是“听从天命”;二是“中庸”。对此鲁迅讲得则更为准确和深刻,他说: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底,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有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注:鲁迅:《华盖集·通讯》。)
鲁迅这话并非一定是针对周作人而言,但“卑怯”却是周作人提倡“中庸”的主要背景,也就是说,周作人的中庸主义是他的卑怯的灵魂的外在表现之一。更为深刻的是,鲁迅所说的“卑怯”,作为国民劣根性,的确是困扰着周作人人生选择的阴暗动力。周作人对自己所具有的“以思想杀人”和“棒喝主义”的极端恐惧的心理是供认不讳的。(注:参见周作人:《〈谈虎集〉后记》。)对周作人来说,这种忧惧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心境,而是在五四时期就存在了,因而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能够感受到这种情感,如他的《苦茶庵打油诗》就充溢着这样的情绪,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忧生悯乱”。周作人多次谈起他的作品的价值主要是思想的价值,他始终想写些真正象文章的“文章”,但他还是写了些关心社会为人生的作品,那么在有“思想罪”的时代里,如何避免他所恐惧的事情的发生,如何作出自身的现实选择?周作人的思考是:
“我看,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不过,这如不是圣贤,只有做官的才能够,如上文所述,所以平常下级人民是不能仿效的。其次是有了烦闷去用方法消遣。抽大烟,讨姨太太,赌钱,住温泉场等,都是一种消遣法,但有些很要用钱,有些很要用力,寒士没有力量去做。我想了一天才算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闭户读书’。”(注:周作人:《闭户读书论》。)
是的,“闭户读书”也不失为乱世文人的一种人生选择,但这种选择是不是可以行得通,却是一个躲不过去的问题。周作人对此渐渐产生了一个误解,他认为他从五四以来,用自己的笔为社会启蒙和文学启蒙所做的努力都是为“别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人”的事,他觉得自己可以离开群体、超越现实。因而他痛恨自己过去对社会的热情和关心,这正象他自己所表述的那样:“我很惭愧老是那么热心,积极,又是在已经略略知道之后,难道相信天下真有‘奇迹’么?实实是大错而特错也。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注:周作人:《〈苦茶随笔〉后记》。)他认为个人可以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去生活,他把对社会的失望转化为某种逃避和旁观的现实选择,因而他决意去“闭户读书”。
那么,他既然要不问世事,关进小楼,来实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目的,又为什么要写专论此事的文章而公诸于世呢,这里我们大概还不能完全理解为他的诚实,当另有他意。我们从周作人的上文就可以看出他的心绪是烦乱的,愤懑的,他是在矛盾痛苦中作出的这种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呻吟,是自认失败的宣言。
华北沦陷后,北大教授的大多数都陆续地离开北平南下,这时的周作人对郭沫若等人的劝告无动于衷,将自己的宅所“苦雨斋”易名为“苦住斋”,表现出立志苦住北平的决心。他的心思显而易见,他再也不想管“人家鸟事”,不想参加救亡工作,而是想做一个现代的“都市隐士”。但周作人这个现代的“都市隐士”从一开始就在风雨飘摇中显得十分无力,没多久就不得不出山去为日本人做事了。这正应了鲁迅的论断,人不可能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生在阶级的时代不可能做超阶级的作家。
周作人的“中庸”是他的卑怯的灵魂的表现,而他那卑怯的灵魂又是以他的个人本位主义为基石的。
周作人从五四时期起就有个人本位主义倾向,他不承认有“无我的爱”,将那种“抹杀个人而高唱人类爱”的想法视为“太渺茫”。他所主张的“爱邻如己”,不过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推及于人类”的爱而已。(注:周作人:《文学的讨论一致日葵》。)
周作人对“生”的格外敬重,受到了西方个人本位主义的严重冲击和进化论的强者生存思想的扭曲,而转向了对个人生命的敬重,变成了一种个人主义的生命意识。
西方文化是一种求真的文化。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与上帝和真理相呼应的,那种唯我的人生原则在上帝和真理的召唤下可以达成一种超越,转化为某种宗教的情操和理性的献身精神。儒家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伦理文化,因而它是入世的、世俗的和务实的,它只有在仁学体系中才能形成某种人的高尚意志,只有将个人置于群体之中,并以敬重周围生命为其人格倾向,才能产生一种执着而无畏的人类意志。相反,这种道德哲学与个人主义的利己思想相融合时,它的必然结果只能是退隐,懦夫,奴颜媚骨。
一个以个人本位主义为其思想基础的人,在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选择中必然会表现出某种特殊的逻辑。周作人和鲁迅不同,他的精神结构缺少一种深层的道德支柱,而以外在功利化的社会理想为其灵魂的价值中心,因而,在社会现实积重难返,他一旦看不到社会在实际上的进步时,他的一切理想都变为颓废,一切希望都化作失望,于是认为自己为社会所做的努力都是一种无价值的牺牲。人们在失望的时候本来可有多种选择:持道德理想主义的人可能搁置外在功利,于是会出现两种选择,一是义无反顾地实现道德理想,完成道德人格,甚至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二是也可能暂时退隐,“独善其身”、伺机以待。那些以社会理想为其中心价值的人也有两种具体选择,一是在群体模式中的社会理想主义者因其并不在意某种社会理想的实现是否对自己有无回报,能够表现出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的献身精神;二是在个人本位主义模式中的社会理想主义者,一般是将自己的切身利益与其理想捆在一起,一旦为某种社会理想所付出的代价见不到回报,他便会自然将自己的选择转向有利于个人价值方面,这里当然包括作出能够获得个人利益的任何一种选择。周作人正是这最后一类人,他的社会理想破灭以后,他所关注的只是个人价值,而投靠强者是他获得个人价值的较好途径。
周作人在决定并苦住北平时,还希望别人将他看作苏武,而不要将他视为李陵,但对于“苏武”的渴望,仅仅是一种人格声誉的道德愿望,而他拒绝南下的目的却是为躲避与在当时不可一世的日本人作对,是惧怕为民族作出个人的牺牲,这才符合他对个人利益的渴求,与此相关,他没有做成苏武,投靠了日本人,使他自己酿成了毕生声誉的致命伤,虽也可说并非他的本意,但就其人生选择与精神结构的联系中来看,显然是十分合乎逻辑的。
在我们对周作人进行一番深入地研究和审视之后,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周作人的完整人格是由两个灵魂构成,一个站在他的人格结构的明眼处,以历史现实为背景,并参与历史现实选择,它的特征是个人本位主义的、没有坚定的价值信仰的中庸主义的卑怯的灵魂,它在历史现实中表现为一种患得患失、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背叛民族的人格姿态,因而这个灵魂显得颇为阴暗和丑陋;另一个站在他的人格结构的遥远的昏暗地带,它的特征是疾恶如仇、积极入世、具有儒家价值信仰和“知命”意识的灵魂,它常常被前台的那个灵魂挡在背后,虽也时而参与周作人在历史现实上的选择,但很少成为这种选择的主宰力量。它尽管一直处在后台的阴暗处,但它却比前者更为可爱,更易被人接受和认可。在情感上,周作人认同儒家文化传统所代表的中心价值,渴望成为诸葛孔明、陶渊明和苏武式的人格,但在意志和历史上,他却抵挡不了个人本位主义的生存忧患和死亡恐惧。可以说,周作人一生的痛苦都来自这两个灵魂的冲突,一生的失败都由于他在对各种文化的选择与融合、创造与转化上的严重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