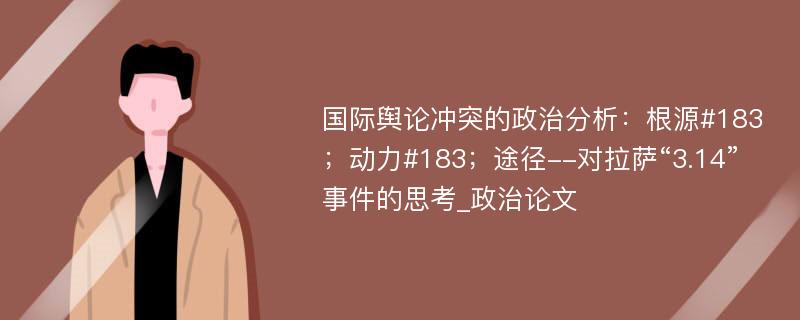
国际舆论冲突的政治学分析:根源#183;动力#183;途径——拉萨“3.14”事件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萨论文,政治学论文,根源论文,舆论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09 105X(2008)02-0054 07
一、引 言
2008年3月14日,在西藏拉萨发生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简称“3.14”事件,下同),18名群众遇害,多处商铺、学校遭到烧毁,造成经济损失2.8亿人民币。事件发生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政府高度关注,迅速采取措施维护社会治安,逮捕参与犯罪活动的不法分子,稳定生产生活秩序,拉萨局势趋于平静。
“3.14”事件之后,西方主流媒体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进行大篇幅的新闻报道,一边倒地支持所谓“西藏和平抗议运动”,谴责中国政府在事件过程中对藏民的“镇压”,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西藏人权,开展与达赖喇嘛的政治对话甚至允许西藏独立。引起注意的是,某些西方媒体采用歪曲事实、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伎俩,违反新闻报道客观、公正、中立的一般准则,带着强烈的主观偏见,以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妄加评论,加深西方民众对整个“3.14”事件和西藏现状的误解,形成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媒体舆论和民间舆论,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形象,给我国造成消极被动的国际舆论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民众、海外华人以及部分国际传媒对西方主流媒体的不实报道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击,揭露“3.14”事件真相的网站的建立、反CNN的爱国呼声、海外华人的游行和抗议成为另一股强大的国际舆论声势,同甚嚣尘上的藏独言论和反华舆论展开较量。藏独分子对奥运圣火传递的破坏行径作为事件的后续,亦在西方民间社会、政府、媒介与世界华人社会形成不同的解读、认知和民意。各种国际舆论彼此冲突、此消彼长,释放出大量国际政治信息,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学机理,遂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国际舆论是指民族国家在国际公共空间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所形成态度和意见的总和[1]。一般情况下,国际舆论表现为一种外交压力。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传播方式的变革,使得舆论更加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和突发性,一旦处理不好,就会迅速出现负面舆论,产生负面效应。因此,需要认清西方国家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了解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之间舆论冲突的根源所在和内在动力,明确化解国际舆论危机政策选择。结合拉萨“3.14”事件的国际新闻报道和更广义层次上的“西藏问题”,拟从国际舆论冲突的根源、动力、途径等几个侧面加以探讨。
二、国际舆论冲突的根源
当前的国际舆论冲突根植于深厚的、形态各异的文明土壤之中,是文明冲突和文化差异的重要表现形式;政治意识形态的隔阂与敌视为民族国家之间舆论冲突的滋生提供了养料;文化、政治歧见导致长期对历史的误读与曲解,固化对问题的偏执看法,使“自我表述”在国际间也成为舆论冲突的因子。
(一)文明的偏见与误解
在国际政治学中,文明冲突论为认识国际舆论冲突的根源问题提供较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亨廷顿指出,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2]。按照亨氏观点,在当今世界的七大或者八大文明中,西方基督教文明具有普遍和狭隘的自负,认为自己是普世文明。由此,文明的差异偏见、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和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往往引起其他文明和非西方世界的反抗,形成相互摩擦、冲突的国际舆论声势。
西藏问题上爆发的国际舆论冲突,体现深层次文明的偏见和误解,是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误读西藏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产物。
1、西方世界对西藏和西藏文化的“香格里拉”情结。西方人对东方的神秘一直保持着强烈向往,西藏地处世界最大高原的深处、雪山环绕并由“活佛”统治,具有更为神秘的特色。从19世纪初叶开始,西藏在西方逐步获得了封闭领土的巨大名声,使热衷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为向往。西藏至今还未对西方完全撩起面纱,类似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构理想化的过程也始终没有完成。
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随着西方文明显露弊端,西方社会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变得迷茫,不少西方人希望从东方宗教的神秘主义中获得新的启示(如美国的英语佛学教学中心以翻番规模增长)②。而在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文明和宗教对他们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文明之一。因此,西方民众对西藏有着诗意的想象,认为那里就是梦幻般的香格里拉。
然而,西方却始终没有看到或者刻意回避与封建农奴制度统一共生的西藏文明和西藏政教合一社会的残酷性和压迫性,忽略西藏文明和宗教中漠视人权和残忍惩罚的因素。西方民众对事实裁减化地理解和认识,以符合他们对西藏文明整体性的美好认知。这种认知使得西方社会的非官方势力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反对,远比其官方态度更为激烈和普遍[3]。
2、西方世界对中华儒家文明的防范态度。问题的一方面是对西藏文明的诗意想象,另一方面则是对日益强大的中华儒家文明的紧张、误解和防范。在文明冲突论中,西方学者对结局的最终设计是中华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颇有“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味道。同时,在西方人的观点中,中华儒家文明与西藏文明是明确二分的,尽管内地和西藏都有佛教因素。西方世界一直怀疑中国政府对西藏文明采取压制、限制甚至灭绝的措施,其中包括控诉在中国统一和现代化进程中西藏文明的衰落,诬蔑中国剥夺藏人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猜测汉族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终消灭藏族等。西方社会以西藏文明的保护者和守护人自居。这样,产生了一个诡异的政治现象和文化景观,即与西藏文明相距甚远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反而要求与西藏文明密切联系的中国承担责任,保护藏族文化和西藏文明,并形成强大的民间舆论声势和态度,成为数十年来西方的定见。
(二)意识形态的隔阂与敌视
意识形态是一定团体中每个成员对周围世界以及团体本身的认知体系,反映了该团体的利益取向,为团体的集体行为提供了合理性辩护,同时也对个人行为提供一套约束。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之间易于相互理解、沟通和达成共识,意识形态体系相差甚远的国家、社会之间更容易产生隔阂、误解和敌视,沟通和理解的成本较高。由于民众的政治心理是意识形态存在的政治基础,而意识形态又影响着政治心理的形成。因此,在意识形态谱系中处于迥然不同位置的国家和社会之间更容易由于民众的政治心理、认知角度、思维定式等方面的差异产生相互敌视的社会舆论,民间的敌对情绪也更容易在意识形态的认识框架内激活和蔓延。
西方国家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西方民众的西藏观念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与中国数十年的意识形态隔阂与敌视。20世纪50年代,为了对付成立不久的“共产主义中国”,阻止“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美国情报部门加强对西藏的活动,妄图跨进中苏两国的后门。1959年策动西藏叛乱失败之后,西方国家对藏独势力给予军事、物资、政治和舆论上的支持,借此打击和牵制中国、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美国领头于1959年、1960年、1961年、和1965年把“西藏问题”列入联大议程,并于1961年和1965年通过了“西藏问题”反华提案。虽然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停止了对藏独武装分子的物质供应、经费支持和军事训练,但是,国内舆论对“共产党中国压制西藏自由独立”的反感一直没有消失,如影星李察·基尔通过电影《困顿》、《在西藏七年》宣传藏独思想,社会各界以演唱会、弘法会等活动所得的赠与收入支持“西藏流亡政府”。20世纪80年代之后,藏独势力在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为幌子攻击中国,游说、鼓吹西藏从“专制”、“暴力”的社会主义中国独立出去。在冷战思维的主导下,妄图分裂中国的西方势力和国际舆论使得达赖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今,达赖个人在西方被塑造成“坚忍”、“和平”的化身,成为一个神话,具有相当的号召力[4]50。这既与他长期以来坚持以宗教领袖身份进行“非暴力”的活动、保持“平易近人”有关,也与西方有人极力抬举他有关。达赖很懂得西方公众的心理和如何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他常常不讲西藏和政治,而讲“内心价值”、“道德”、“和解”、“静修”和“同情”,愈发使西方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他;同时,他利用西方民众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偏见,使其将中国认定为“黩武者”、“入侵者”和践踏人权的一方。
(三)历史的误读与曲解
在文明的误解与偏见、意识形态的隔阂与敌视的基础上,不同的国家和东西方社会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叙述历史,建构起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进而形成相异的甚至是矛盾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相联系,在与之相关的政治现实发生时从大众脑海里“提取”出来,激发国际冲突性的民间舆论。
“3.14”事件之后西方民间舆论发生强烈的反弹,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西方对历史上所谓“西藏问题”发生误读与曲解。这种错误的历史观被大众传媒塑造成既定的思想观念,在社会中沉淀下来,民众受到影响和熏陶,固化了对问题的偏执看法,形成了整体性的偏颇的社会舆论。同时,现有的社会舆论又进一步制约媒体的报道内容和价值取向,诱发了恶性循环。其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历史事件的描述与理解上:
1、“西藏的主权归属问题”。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5]。西方世界普通民众却往往不认可这种已经相当明确和清晰的史实,在他们的历史观中,西藏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政教合一的“国家”,只是数次地受到中国的“入侵”和“统治”,又数次地“摆脱统治”,其本身具有独立自主性。
2、“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和平解放是全国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藏人民推翻农奴制度,翻身做主人,迎接新生活的开端。但是,西方的学界、新闻界和民众从负面理解了这段历史。美国的主流媒体在描绘1950年西藏的和平解放时基本用“入侵”(invade)或“占领”(occupation)等贬义词汇[4]49。法国作家也写道:“神奇的西藏,受难的西藏,世纪末雪域遭遇的现实。1950年,中国入侵西藏,西藏遭受殖民统治。”③这些固定用语,在一遍一遍地加深读者的印象,也反映了西方社会主流思想和态度。
3、“1959年,西藏叛乱,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叛乱”。1959年的西藏叛乱是达赖集团策划领导的,受到美国情报机构煽动支持的分裂国家行为。人民解放军的及时平叛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和统一,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西藏农奴制改革的成果。西方却不认可这样的史实,他们通常将1959年的平暴说成“镇压”(repression)或“入侵”,其后形容中国政府和西藏文化关系的形容词则多半是“破坏”(destroy)[4]50。
4、“1989年,平定西藏叛乱”。1989年,少数藏独分子利用国际局势动荡的时机,妄图进行武装叛乱,谋求西藏独立,后被及时平定。此次平乱对维护祖国统一、维护西藏的安定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一小撮破坏祖国统一的分裂主义分子给予了有力的打击。而在西方人眼中,这一历史事件是藏族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和平抗争,却受到中国政府的“镇压”,暴露了中国“独裁、专制”的本质,应当予以强烈谴责。
三、国际舆论冲突的动力
国际舆论冲突的直接动因在于国家利益的冲突,经济政治利益之争往往外化为国际舆论冲突,并且以舆论战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机制和偏好会诱发舆论冲突并朝向激烈化程度发展。
(一)国家利益驱使是舆论冲突内动力
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一切国际政治行为都是围绕权力和安全的斗争。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原始动力,国家利益纷争是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或者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利益的情况下,政府会动员民间舆论支持,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声势和舆论环境,一方面打击对手,另一方面为后续的政策措施增加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样,对方国家也会以牙还牙,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报复,改变被动的国际舆论局面。20世纪80年代针对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美国国内出现迫切要求“修理日本”的社会舆论,为美国调整其对日经济政策并要求日本妥协营造了重要的舆论氛围④。这种调动、促使民间舆论和国际舆论的形成,向对手国家施压的手段,成为当前国际舆论冲突的滥觞。
“3.14”事件之后的舆论纷争和“西藏问题”的长期争议,实质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在现阶段则是中国日益强大崛起和西方国家不能容忍、无法正视中国崛起的冲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始终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方大国中国的崛起预示着国际政治中权势力量的转移和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世界不可逆转地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的全球霸权相对衰落,欧洲的领先地位也在动摇。中国崛起的巨大效应给西方世界强烈震撼,既有的“中国崩溃”思想被彻底颠覆,一个强大的中国成为不得不正视和接受的现实。同时,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能源、环境、贸易、安全等问题,以及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利益摩擦和纠纷却被恶意炒作和放大,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现实依据,充分体现其疑虑、防范中国的社会心理。“3.14”事件之后西方社会舆论对中国的批评与“中国威胁论”的逻辑如出一辙,其目的在于通过操纵“修理中国”的国际舆论为后续的政策出台张目,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满足本国民众情感宣泄的需要,达到阻碍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根本目的。近来,美国国会采取了一连串动作,对所谓“西藏问题”显示了格外的“热心”。佩洛西等议员频繁发表声援“藏独”讲话,呼吁抵制北京奥运,煽动民间舆论、国际舆论支持达赖和藏独分子。美国学者称,“佩洛西女士难以轻松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欧洲某些媒体则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台海局势缓和之后,“西藏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的唯一重要工具。可见,本次国际社会舆论冲突是被西方国家官方操纵和激化的,是为了满足自身国家利益的一项有计划、有目的的政治行动。
(二)西方媒体报道机制是舆论冲突的推动力
西方媒体一直以“看门狗”的角色自居,在社会上承担舆论监督的作用,制约政府的政策。媒体从业者嘴上说“我们只是告知”,实际上在发挥作用影响决策。媒体虽然常常以政府“对手”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却是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捍卫者,最担心政府违反规则并施加压力使之顺从“民意”。同时,西方媒体乐于挖掘社会的阴暗面,揭露不为人知的社会丑闻,除了新闻人的良知与责任使然之外,正所谓“人咬狗是新闻”的新闻报道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新闻的价值即在于吸引公众的眼球和注意力,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唯有如此,媒体的影响力和受众范围才能扩大,也才能得到更为丰厚的广告收入和经济效益。
西方媒体最为了解当地民间关注“西藏问题”、同情达赖和藏独势力的心理,西方民众的西藏心结和长期思想定势使得媒体不断迎合和满足民众的心理需要和对新闻信息的需求,通过其新闻报道,刻画出一个“神圣而又受难的西藏”;进而鼓励政府关注“西藏问题”,支持达赖和流亡藏人团体的要求,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下,政府是不可能置“民意”于不顾的,这些报道也构成了西方国家政府制定其西藏政策的重要舆论环境。“3.14”事件同时满足了西方媒介猎奇的行业特点,所谓“汉藏冲突”、“西藏局势动荡”和“侵犯藏民人权”等话题是他们极为感兴趣的,也是他们认为最能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内容。尤其是西方媒体一度不被允许进入西藏采访,更为整个事件添加了神秘的色彩,为西方媒体的炒作和渲染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此情况下,他们展开丰富的想象,运用各种手段和伎俩进行舆论操控,其中不乏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刻意裁剪、添油加醋等行为,居心不良,一望而知。正是西方媒体的如此操弄,密集的新闻报道和负面评论的出现,调动了西方社会的民间情绪,掀起西方社会的反华舆论和反华声浪,达到新闻舆论塑造社会舆论的目的。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和反华言论在中国和世界华人中间激起义愤和回应,形成声势浩大的“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西方歪曲报道”的爱国舆论和民间情绪,引发大规模国际舆论冲突。
四、国际舆论冲突的途径
当前国际舆论冲突主要表现为新闻舆论冲突和社会舆论冲突,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成为舆论冲突的平台和载体之外,互联网成为国际舆论冲突的新形式和途径。游行、示威、抗议等活动则以更加直接和行动化的方式表达民间舆论的不满情绪。“3.14”事件之后的国际舆论冲突具备了以上所有元素。
(一)新闻舆论冲突主要以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报道和评论形式出现
美国著名新闻学者李普曼指出,媒体营造的是拟态环境(又称虚拟环境或假环境),而不是真实的环境,它融入了人的主观意志和评价标准(这个标准很可能是偏离客观事实的)。由于专业性的选择、加工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的,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而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也就是说,媒体所营造的拟态环境虽然不是真实环境,却会对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实际的影响。根据西方学者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假设,在西方媒体那里,所谓的客观、公正是不存在的。对于西藏最近这些年发生的变化,包括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方面设施、条件的改善等,西方媒体不大会感兴趣,因为这不符合他们预设的框架,而西藏一旦出现麻烦,符合了这个框架的预期,他们就会高度关注,连篇累牍地报道,并以自己的解读去影响广大的受众,在受众的头脑中形成对西藏的刻板印象。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一提到西藏,西方受众就会产生很负面的联想,刻板印象已经形成[6]。
为了符合一贯的“刻板印象”,此次西方的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报道和评论“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移花接木,混淆视听”、“捕风捉影,制造谣言”,遭到我国主流媒体和部分有良知的国外媒体的揭露和批驳。比如,电视屏幕上明明展现的是我公安民警正在协助医护人员把受伤群众送上救护车,但解说词却说已经有数十人被(我公安武警)打伤、打死或者抓走。明明是在别的国家发生的警察正在驱赶一些闹事喇嘛的镜头,却被移植到这次拉萨事件的电视报道中,画外音还栽赃说是中国军警正在镇压抗议者。在同一天的电视报道中,有的西方媒体说伤亡人数达到了60多人,有的则说超过了80人,还有的说超过了100人,有的甚至说超过了300人。更为可笑、恶劣的是,这些报道都不指明信息来源,用的只是“据说”二字。
(二)互联网汇集整合越来越大的社会民意和能量,是新的舆论冲突平台和途径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突破了信息传播与扩散的时空界限,使互联网成为民间舆论形成和爱国声势集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在网络时代,更多的人拥有平等的信息解读权利和评价权利,并且能够借助互联网使相同的民意得到汇集和发展,使不同的舆论冲突在网络平台上交锋,激起全社会的更大关注,成为制造舆论关注热点的新形式。
“3.14”事件之后,西方媒体掀起对中国批评的浪潮,所谓“中国政府镇压西藏和平示威”的电视画面和图片密集出现,支持藏独一度成为西方的主流舆论。网络立即成为世界华人维护祖国统一,展现中国民意,反击反华言论的主战场之一。在YOUTUBE网站上,中国留学生制作的名为“西藏过去、现在、将来都属于中国一部分”的视频三天之内点击数超过120万次,各种语言的评论72000多条,引发了中西方关于西藏问题的大辩论。为了讽刺、揭露CNN等国外媒体对“3·14”事件的不实报道,我国网民自发建立英文反CNN网站,直接对外国公民进行宣传说明,进行反CNN网络签名,回应西方媒体偏见,在互联网上发出中国民间的正义之声,受到国外媒体和世界人民的关注。搜狐网上“抗议西方媒体造假、歪曲西藏事实”的栏目,得到超过1300万网民的点击同意[7],以虚拟的方式表达了义愤的声音和意见支持,发挥了汇集更大的民间舆论力量的作用。总之,互联网上的舆论冲突标志着国际舆论冲突的新动向,是各国政府考察民意和了解社会舆论的重要途径,极有可能引导今后国际舆论冲突的议题、焦点和方向。
(三)民间自发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将国际社会舆论冲突推向高潮
新闻舆论与社会舆论主要表现在新闻报道、思想观念和社会言论层面,具有软约束的性质。一旦国际舆论冲突以游行、示威、抗议等实际行动表现出来,则表明民间情绪已经按捺不住,需要以更加直接有力的肢体语言表现出来,是一种舆论冲突升级。
“3.14”事件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批评和歪曲报道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媒体的回应和民间舆论不满。之后,西方媒体不仅没有反省,反而变本加厉,美国CNN主播卡弗蒂发表严重辱华言论,导致中国反击西方舆论的升级。中国民间随后出现抵制法国货和家乐福超市的言论,在某些地区已经产生社会影响。海外华人在伦敦、洛杉矶等城市进行示威游行,抗议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和辱华言论,支持国家统一和北京奥运会,将本次国际舆论冲突推向高潮。同时,这种直接行动究竟是舆论冲突的最高形式和终结,还是新一轮国际冲突的开始,值得全世界关注。
五、结语:几点思考
拉萨“3.14”事件作为个案折射出国际舆论冲突的深层原因、历史背景、现实动力和交锋途径,为进一步思考涉藏国际舆论和营造国际舆论环境提供了视角和方法。
(一)深刻认识涉藏国际舆论冲突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1、长期性。国际舆论冲突根源于在文明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观分歧。因此,在中国与西方对西藏文明和相互之间存在误解和疑虑,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独特性,西方的西藏历史观已经定型、难以更改的情况下,西方世界尤其是民间舆论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有可能是相对固定和长期的。同样,这种西方偏见在中国国内造成的民间舆论反弹也将伴随西方的反华舆论长期存在,在特定的情势下还有可能被激化。
2、复杂性。除了文明、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差异之外,当前国际舆论冲突被赋予了更多的国家利益纷争的内涵,是国家之间利益、民意的博弈形式。中国的强大崛起,西方世界的心理失衡,中西方的利益摩擦都将增加舆论冲突的变数和复杂程度。西方打算利用何种时机“修理中国”,达赖集团和藏独势力将以何种形式成为西方牵制中国的棋子,以及在此过程中,西方媒介表现出来的煽动性都会导致事态向负面方向发展,引发更加强烈的中西方国际舆论冲突和对抗。
3、艰巨性。国际舆论冲突的复杂性决定了减缓和化解这种冲突的艰巨性。目前对中国而言,最为关键的制约性因素是国际传播和国际公关效果欠佳,新闻传媒仅仅在对内宣传上统一思想、调动民意,却没有完全发挥引导国际舆论向有利于我国方向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中国将面对西方国际传媒和西方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国际舆论冲突的负面影响也将相对严重地伤及中国,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和“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
(二)深刻认识国内、国际舆论因素对处理涉藏问题的建设性和牵制性
1、建设性。建设性主要是对国内统一民意和爱国舆论而言的。西方反华势力主导的国际舆论激起中国乃至华人世界舆论的反弹。这种反弹,有力地宣示了中国民众在“西藏问题”上的一致态度,可以有效地震慑反华势力和藏独分子,能够为中国政府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政府决策提供民意支持和积极的国内舆论氛围。
2、牵制性。一方面,国际舆论的对华误解乃至敌视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危及中国国家形象。在中国和西方关系中,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更多的摩擦和矛盾。尤其是西方国家政府的对华态度和涉藏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本国民意和社会舆论的制约,甚至被舆论所引导,给“西藏问题”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国内爱国舆论在特定的情势下可能会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膨胀,走向非理性的负面行动,不仅束缚政府的政策选择,而且引发更大范围的国际误解,成为国际冲突常态化和更为严重的国际危机的前兆。因此,在引导国内舆论时,我们必须坚持“理性爱国”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最大的爱国”[8]。
(三)深刻认识提升化解国际舆论危机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3.14”事件之后,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曾一度经受严峻考验。伴随着奥运会、世博会的开幕,中国将日益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任何国内事件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国际传媒效应,对国际舆论和国家形象带来诸多变数。因此,在国际舆论危机出现时如何合理应对、成功化解,已经成为当下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紧要问题。“3.14”事件至少给我国以下启示:
1、重视新闻报道,抢占制高点。加强“第一时间”信息的准确发布,坚决克服“报喜不报忧”、“家丑不可外扬”的新闻报道心态,完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健全政府新闻发布机制,严格把关,快速反应,“先发制人”。力争做到始终以第一时效引领舆论,用客观、公正、翔实的报道“先声夺人”,不让流言混淆视听,努力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
2、欢迎国外媒体,主动“请进来”。应该充分彰显大国自信和大国风范,以博大的胸襟和开放的心态对待各国媒体,放松对外国媒体的控制,主动敞开国门,欢迎甚至邀请世界各地的媒体进行客观公正的采访和报道。不能搞“闭关锁国”、“拒人千里”,否则会适得其反,使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猜疑、不安和消极评论,恶化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3、加强国际公关,积极“走出去”。要进行全方位、宽领域、高频度的国际公关活动,积极“走出去”。首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的外宣部门负责人及时出访与发生事件密切相关、对发生事件高度关注的国家,与各国领导政要沟通交流,解释说明,打消疑虑,防止外国反应失当,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对国家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其次,迅速开展大规模的公众外交活动。一方面,组织国内事件的亲历者、知情者出访国外,参与国际公关活动,发表演讲、接受国际传媒的采访和外国民众的询问,代表中国向全世界说明事件真相,反驳虚假言论,维护国家形象。另一方面,派出民间团体到国外访问交流,通过口头对口头、人际对人际、民间对民间的国际传播形式对国外民众的认知产生影响,增加在特定事件发生时刻对我国的理解与支持。
4、发动民间智慧,坚决反谣言。在突发事件的消极影响蔓延和国际舆论日益不利的情况下,有必要充分释放民间的爱国能量,调动民间智慧帮助国家摆脱困境。合理适度地发动民间声势回应错误国际舆论的压力,一方面可以增强国家应对危机的信心和政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给民间智慧和民间声音提供了施展的空间和平台,使其加入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制约消极国际舆论的影响。
5、依靠世界华人,努力树形象。国际上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反华舆论,应当充分发挥祖国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激发海外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拉近全球华人距离,团结和组织华人华侨力量,争取他们的声援与支持;利用他们对所在地社会文化、政府管理、媒体舆论等方面的了解和熟悉,反映华人声音,形成华人舆论,正面宣传中国,反击反华言论。
注释:
①参见令计划著《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载于《“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408页。
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教在美国的吸引力保持升温,对佛教的兴趣和佛教信徒也在增加。在西方,佛教是和达赖、西藏联系在一起的。
③转引自刘颖、郝亚明著《想象与对话:中法媒体报道下的西藏》,载于《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87页。
④参见《日美舆论战》(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作者近藤诚一的观点。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学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社会舆论论文; 美国媒体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西藏建设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新闻报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