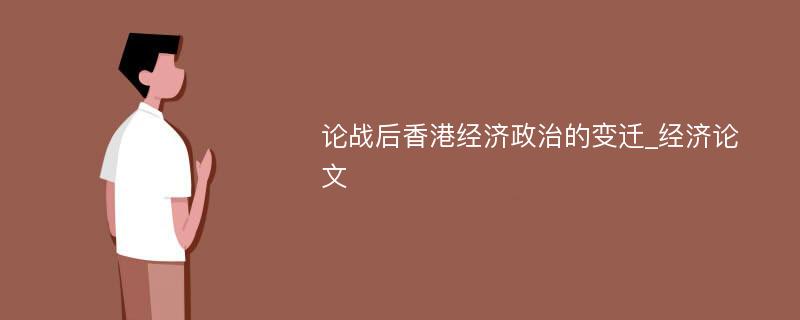
论战后香港经济与政治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香港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经过战后三十余年的建设,香港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至七十年代,香港进而成为世界性的出口加工、金融、贸易、航运、通讯服务和旅游娱乐中心。而经济领域的成就进而引发了社会政治方面一系列的变革,从华人政治力量的壮大到汉语成为官方用语、从分区民政署的成立到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的开张、从市政局议员的开放选举到廉政公署的严打重惩、从劳工立法到社会福利措施,传统的殖民政治体系与政策都发生了向现代方向的变迁。香港经济与政治联动发展的历史过程说明,一个社会最优先发展的应该是经济;当经济工业化多元化进展到一定程度,再逐步推进政治领域的改革,社会就会在平衡协调中求得整体的进步。
经过战后三十年的发展,香港经济从战争废墟上迅速恢复并成长起来。从六十年代开始,香港便逐渐成为亚太地区纺织、服装、塑胶花、玩具、手电筒等行业的加工制造出口中心。至七十年代,香港进而成为世界性的金融、贸易、航运、通讯服务和旅游娱乐中心。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政治方面的一系列联动,使传统的殖民体系发生了向现代方向的变化。本文拟从经济是社会政治基础这一视角对战后三十年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改良作一系统考察,以探讨香港经济起飞和社会政治变迁的轨迹。
一
香港在1842年开埠时只是一个荒凉的渔村,其后在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鼓励下,经过一百年的发展,香港经济逐渐发展兴旺起来,东方自由港城市的雏形已见端倪。但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相比,香港经济在二战之前也并无明显的超前。而且,它的经济此时主要建立在转口贸易之上,大多数的香港就业人口集中于船运及相关的商贸、服务、仓储、银行和保险行业。
二战中日军占领香港。在此期间,昔日以转口贸易为基石的经济遭到致命打击。与战争相关的制造业虽一度有所发展,但至战争结束也几乎全部残破。战争以及一百年的殖民地历史留给战后香港人的只是一个畸形而又伤痕累累的经济。
战后初期的香港,到处是一片贫穷破落的景象。居民普遍缺衣少穿,缺粮少柴,有60万居民在劫后的城市中游荡觅食,无家可归。[(1)]由战争和世界经济不景气带来的难民潮又使得香港的人口压力激增,1946年时香港有人口1,600,000人,1950年时已达2,360,000人。[(2)]人口压力造成的房屋紧张迫使成千上万的人在荒远的山坡上搭木屋居住,脏乱狭小,飘风漏雨,处境苦不堪言。
战争的阴影不久逐渐淡化。数年之间香港就恢复了原来的转口港地位,1950年的对外贸易额又超过了战前水平。贸易额每年增长30—48%。1951年,全港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4.33亿港元。但其整体经济依然十分脆弱,转口贸易占据了绝对的比重,1951年的转口贸易额占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80%以上。而制造工业毫无生气,1950年香港人口达到236万人,可整个香港却只有1,500家小工厂,雇工人数不到8万人。全港生产总值只有15亿港元多一点,平均每人只有750港元左右。[(3)]这些小工厂又主要集中于原材料和初加工行业。1949年向美国出口的价值2.34亿港元的商品中,超过50%的商品是猪鬃、皮革、菜子油、钨、针织品和橡胶鞋。[(4)]香港显然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工业化社会。它只是世界商品流程中一个生意兴隆的中转货栈而已。香港政府发表的商业指南对此也不无自嘲地写道,香港“似乎对分发财富比对生产财富更感兴趣”。[(5)]
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和西方国家实施的对华禁运使香港经济猝然陷入危机,转口贸易一落千丈。对内地的贸易额竟下跌了三分之二。1951年至1955年,中港贸易在香港出口市场上的位次从第一位下降到第五位。受此打击,与转口贸易相关的航运、银行、保险等行业均告疲软,商家倒闭之事日有所闻,失业人数骤增,社会秩序趋于不稳。香港遇到了它战后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道难关。
面对转口贸易的崩溃局面,香港及时调整经济策略,加速发展本埠工业。港人以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成衣等行业为先驱,充分运用来自上海等内地城市工商移民的资金和技术,增建新厂,扩建老厂,添置机器,积极生产适合欧美及东南亚各国销路的产品。此一调整在五十年代下半期就显示出它的最初成果。新兴工业区在港、九各地纷纷出现,工厂和雇工数急剧增加。工业产品的出口货值也成倍增加。1956年全港工业品出口总值达7.6亿元,与1949年的0.82亿元比较,增加9倍有余。[(6)]1959年香港政府发表对外贸易资料时,已将香港输出货物分别列为“产品输出”(Exports)和“转口输出(Reexports),其产品输出货值为22.82亿元,转口输出为9.96亿元,港产品输出已占全部出口额的70%。[(7)]这些数据表明转口贸易在香港经济中已占居次要地位,对外贸易的主轴是本埠工业产品外销。香港已经迈进了工业城市的门槛。
进入60年代后,香港工业化的趋势更加显著。1966年登记在册的工厂数和雇工数分别达到1万余家和42.4万人,1969年进而分别达到1.4万家和52.9万人。1969年的港产品出口货值是105亿元,与1959年的22.82亿元相比,十年间增加361%。[(8)]整个60年代,香港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3.6%。至60年代末,香港已经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纺织、服装、靴鞋、玩具、塑胶花、手电筒、搪瓷等产品的制造中心。
70年代初,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发达工业国家经济的长期衰退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出口为主导的香港经济在外部冲击下发生巨大波动。工业开工不足,大量产品积压,股票市场大泻,工商企业倒闭相继,香港遇到了它发展过程中又一个难关。
在市场困难面前,香港推行经济多元化方针,对经济结构再次进行重大调整。首先是实行工业产品多元化,以生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和高增加值的产品来应付欧美各国的市场保护主义。香港工业家在维持原有工业行业继续生产的同时,积极筹资或引进外资开拓家用电器、光学仪器、电动机械、化工及名目繁多的包括电子手表、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收音机和收录两用机在内的电子产品等新兴行业。在这些新兴行业的带动下,香港工业生产迅速摆脱困境,走向兴旺。1979年6月,全港工厂超过4万家,雇工87万人。港产品出口货值达559.12亿港元。[(9)]其中有些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已跃居世界前列,如港产手表在1978年的出口达到4,938.3万只,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一位。其次是发展多种经济部门,以经济基础的多元化来增强香港经济抵抗外部市场风险的能力。70年代下半期开始,第三产业中的金融、旅游、地产、批发、零售、海空航运、国际通讯等迅速扩展,并全面走向繁荣。全面繁荣的多元经济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财富。1977—1978年度香港财政收入超过100亿港元大关,达到102.32亿港元,至1980—1981年度更上升到214.28亿港元。[(10)]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战后香港工业化多元化经济的不断发展,工商资产阶级、劳工阶层、华人社会的整体力量都迅速壮大。尤其是华人社会的经济实力越来越成为香港经济的主导因素。早在1960年,华资就在香港工业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制衣业投资共1.3亿元,华人投资1亿元,占77%;织布业共有190家工厂,华人投资额占94%;针织业共有290家工厂,除有一家为英国人投资外,其余均为华资。[(11)]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华人已在多种经济领域显示其优势实力。1980年6月,英资香港置地有限公司宣布,以每股100港元(以股票及债券支付)的价格收购九龙货仓有限公司的股票3000万股,企图使置地公司拥有的九仓股权从原有的20%增加到49%,以便成为九仓的最大股东。华资寰球航运公司董事长包玉刚在海外闻讯,即刻回港,以每股105港元的现金收购九龙货仓公司的股票2000万股,使得包氏家族拥有的九仓股权从原来的30%增到49%,从而成为九仓的最大股东。在这场争夺战中包氏家族调动现金达21亿港元。[(12)]
经济的发展、经济力量的错动和换位在社会政治领域引起了联锁反应。拥有资本实力的工商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劳工阶层、步入经济中心的华人社会及其他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纷纷根据本集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所作出的贡献,要求相应的社会政治权利和待遇。他们或组织团体,或写书办报,或议坛抗争,或罢工示威,或游行请愿,向传统的殖民体制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虽然在英国宗主国的顽固干预下没能将旧的殖民体制彻底冲垮,但却逼使旧的政治体系及其政策向现代方向不断改良与调整。
二
香港的政治结构一直带有明显的殖民特征。依据香港立政的根本大法《英王制诰》(The Letters Patent)和《王室训令》(Royal Instructions),香港总督是英国女王在香港的代表,具有指导香港一切政务的权力。总督之下,设有行政局和立法局。行政局的职能是会审通过行政系统各司署提出的主要政策议案和法律草案,向总督提供制定政策的意见,并将已同意之法律草案提交立法局。立法局的职能是制定法律,审查准驳财政预算和监察行政机关的工作。不论是行政局还是立法局,其最后的决议必须经总督同意才能成为香港政府的政策或法律。除上述三个权力机构外,还有两个区域性的权力机构。一为市政局,专管港九地区环境、卫生、娱乐、房屋、市场、车牌执照发放等事务。它的成员由总督任命的官守议员和非官守议员组成。原则上市政局属于讨论和执行机构,它的建议须经行政局同意、总督批准方为有效;二为新界理民府,其职能几与传统中国的府县衙门相同,集新界地区行政、司法、税收等权力于一身。从1842年香港开埠至20世纪50年代,上述殖民结构几乎一层不变地被继承下来。
从50年代下半期开始,特别是60年代下半期以后,传统的殖民政治结构在强大的经济与社会压力下出现了危机,港英当局不得不对原有的政治体系和构成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一)成立分区民政署
在老式的殖民统治形式下,香港行政系统采取“功能部”分头工作的模式。这种模式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官与民距离过于遥远,官员解决问题时来去勿勿,浮光掠影,因而功效甚微。久而久之,市民们也没有兴趣向这些“走马灯官员”表述意见和要求;二是政府机构过于崇隆,市民觉得它森严可畏,不敢问津,结果是政府与公众天各一方,互相猜忌。在50年代以前,市民们为生计所迫,无遐考虑向当局反映意见。但5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市民越来越希望表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由于缺少渠道,怨气便越积越深,终于有1956年、1966年和1967年三次大的社会暴乱事件的发生。事后港英政府在1968年成立了与市民更贴近的政府机构分区民政署。全港共设有10个分区民政署。各分区民政署首长称为民政主任(City District Officer),其任期一般为3年,行政关系上隶属民政司。[(13)]分区民政署的办事处一般都设在街区路边楼下,便于本区居民随时造访,其门面也改采商店式大玻璃窗设计,减少官僚机构的森严性和不可捉摸性。自1968年开办以来,分区民政署的职能逐年扩展,概括而言有四大项,即收集民众意见和态度并报告政府、联络沟通地方团体及社区领袖、阐释政府方针政策、检查和协调各个部门包括市政事务署、社会福利署、教育司署、警务处及康乐体育事务处等机构在区内的工作。这些职能疏通和拓宽了公众与政府间的交流渠道,缩短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公众与政府的联系和互相了解,有利于化解民众对政府的怨恨之气,有利于政府集思广益做出合乎民意的决策。
(二)公务人员本地化
为了弥补殖民政府合法性不足的窘困,缓解华人社会的政治要求,港英当局改变过去重视招募外籍人员而忽视任用华人的传统,在各政府机构中更加注重吸纳华人。特别是在麦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任总督期间的70年代,华人进入政府和议政机构几成为潮流。在政府公务员系统,1952年,本地籍公务员有22,900人,海外籍公务员有1,063人,1968年,本地籍增加到71,057人,海外籍增加到1,879人,1980年本地籍再增加到124,950人,海外籍增加至3,064人。不到30年间,本地籍人员增长了5.46倍,海外籍人员只增长了2.28倍。以1980年公务员总人数统计,本地籍占97.61%,海外籍占2.39%。[(14)]如果以外籍人士占主要地位的高层政府官员统计,60年代后本地籍人士所占比重也逐年上升。以1980年与1960年相比,华人首长级官员从9.7%增加至30.2%;政务官级官员从9.7%增至49.0%;行政官级官员从50.3%增至93.7%;警察长及督察级从39.4%增至54.7%。平均计算,华人高层官员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27.3%增加至1980年的59.2%。[(15)]
(三)开放市政局议员选举
市政局是由原来的卫生局发展而来的,正式定名于1936年。在成立初期,其成员由港府官员和港督任命的非官守议员组成。其中的市政事务署长为当然主席,医务卫生署主管卫生事务之副署长为当然副主席,民政局、工务司、社会福利署长和徒置事务署长为当然议员。从1952年开始,增设民选议员。这一年市政局的议员总数是13人,当然官守议员、委任非官守议员和民选非官守议员的比例是5∶6∶2。其后,民选非官守议员逐年递增。1973年港府修改市政局条例,取消官守议员席位,使之成为全部由非官守议员组成的机构,委任议员与民选议员额各12人,主席与副主席由全体议员互选产生。[(16)]同年修订的市政局条例将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的资格条件均予放宽,凡在香港居住届满三年,年满21岁,达到一定的教育程度,或从事指定的职业、或财产达到一定标准,即使不懂英语也有资格参加选举。市政局议员开放选举,一方面为政府反对派特别是华人政府反对派和草根型地方人士利用议坛批评和监督政府提供了合法场所,如叶锡恩议员70年代就多次就政府政策对港府提出尖锐批评;另一方面为本地华人参与政治竞争提供了一条渠道。按习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一般都具有市政局议员经历。一旦市政局议员实行民选,接下来即便是立法局不实行民选,也意味着它的成员必须经过选民的第一道过滤。1973年和1977年,市政局的民选华人议员张有兴、胡鸿烈就是通过这一渠道进入立法局的。[(17)]
(四)成立与扩大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
从6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社会人士呼吁在常设政府机构之外设立一个“冤情大使”(Ombudsman),以专门接受市民对官员无能、拖延、歧视及舞弊情况投诉。在1969年12月的一次市政局会议上,14位市政局议员也一致投票赞成设立此一制度。在民间人士的压力下,港府虽然未设立冤情大使,但为了缓和压力,也不得不在1970年决定扩大1963年成立的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的职权,由政府高级公务员中调派一人,称为秘书长(Administrative Secetary)作为两局的常务行政负责人,正式设立市民投诉制度。任何针对政府部门或政策的投诉抗议都可前往该办事处投递。
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的设立特别是常务秘书长的设立,克服了非官守议员多为兼职因而无暇详细调查市民申诉的弊端。常务秘书长及其办事处征募的职员一方面代表非官守议员接见来访市民,接受投诉,一方面调查研究,为两局非官守议员进一步行动提供行政与文书协助。不论是秘书长,还是职员,他们都必须向非官守议员负责,并接受其指示和领导,不得拒绝接受任何市民的申诉。两局非官守议员则轮流当值,领导和监督日常运作。
(五)设立廉政专员公署
香港官场贪污受贿风气历来盛炽。而早期的香港总督对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总是讳莫如深,害怕对贪污的彻底调查“会使整个殖民机构丢尽脸面”。[(18)]这导致贪污受贿在二次大战之后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尤以警察机构“灾情最重”。
6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工商资本家、小商小贩、知识阶层及广大劳工对政府和警察贪污成风十分不满,抱怨谴责之声不绝于耳。香港殖民政府面对的政治压力徒然增升。总督麦理浩在任期间不得不授权立法局于1974年通过“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法案”,正式成立了独立于各部门之外的肃贪权力机构——廉政专员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or ICAC)。廉政公署在政府结构中占有特别的地位。其首长廉政专员直接向总督本人汇报工作,向总督负责。廉政公署全部职员自行招聘,毋须通过公务员铨选委员会。职员薪金高于其它部门同级公务人员,但若品行出现问题即刻遭到严惩。廉政公署对涉嫌贪污受贿者有不受限制的侦查权力,包括有权调查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文件、档案、日常事务及办公程序,有权对涉嫌人员进行搜查、逮捕、拘留和起诉。除此之外,廉政公署还兼有宣传反贪污法律、教育劝导官民和帮助机构与企业设计反贪污行政程序等权责。廉政公署在成立初期把工作重点放在与警察相关的案件上。从1974年2月到12月,在廉政公署收到的3189个关于贪污的举报中,有1443个是牵联到警察的。[(19)]廉署首先从葛柏大案下手。葛柏原为香港总警司。他利用职权严重贪污受贿,被判以4年监禁。随后,廉署乘胜追击,又连续查处了警司韩德、郑汉权、潭保利、箫统炎等大案要案,并把侦办范围进而扩展到整个政府部门。据统计,1974年除了与警察相关的30宗贪污案受到廉政公署的检控以外,还有75宗分别与监狱署、房屋署、海事处、市政事务处、消防事务处、人民入境事务处、劳工处、医务卫生处、运输署等机构有关的贪污案也受到廉政公署检控。[(20)]与这些案件相关的涉嫌官员或被判以监禁,或被没收财产和罚以重金,或被清理出政府机构。
三
与政治结构改良相一致,港英当局还对政府政策进行了调整。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以前,香港政府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一)提高汉语地位,使之成为官方语言
香港虽然是一个中国人占绝对多数的地方,汉语却长期不是法定的官方语言。对语言问题造成的政治隔阂、民族仇视及英籍官员的骄模跋扈贪赃枉法,港英当局早有察觉,但出于殖民主义的文化征服策略始终拒绝汉语的官方地位。1966年骚乱以后,港英政府这种顽固坚持英语正统地位的态度越来越遭到港人的非议。港督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迫于社会压力,表示要成立一个内部委员会来研究汉语与沟通问题。但该委员会却长时间拿不出研究结果。港督显然是想让语言问题不了了之。[(21)]
从香港经济发展和父辈经济奋斗中受益而又在政治生活中受阻的新生代华人大学生,对戴麟趾的消极态度最先提出挑战。他们或组织团体、或创办中文刊物、或演说抗议,对政府的语言政策大加挞伐,指出政府偏袒英语歧视汉语是一种“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和“对华人文化传统的侮辱”。[(22)]1967年11月,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学苑》提出,中文应与英文并列为官方语言。次年1月,崇基书院学生会举办座谈会,专门研讨中文列为官方语言问题。1970年3月,香港学生团体组成中文运动联席会。7月,香港17个学生团体和文化组织举办了“公开论坛”,疾呼采用中文为官方语言。10月,香港大学学生会通过决议,成立中文运动工作委员会,发动万人签名运动。专上学联也为此成立了特别研究小组。华人学生对汉语的呼唤运动得到了社区组织、中文刊物、市政局、立法局及一般民众的普遍支持。1970年10月,在立法局会议上,非官守议员也群起响应,提议政府将中文定为官方语文,并要求政府增加投入,加强对公务人员的汉语训练和增设会堂法庭等场所的同声翻译系统。1971年,以非官守议员为主的立法局财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停止过去对英文学校优惠津贴的不公平政策,实行中文与英文学校津贴均等化。在社会一致要求下,总督麦理浩终于在1974年颁布了《官方语言法案》,使汉语从此成了香港的正式官方语言。
尽管《官方语言法案》还保留了一些殖民主义的尾巴,如英文在法律条文方面有优越地位,但它无疑从文化根本上打破了英人对政府机构的垄断,改变了华人问政的天生语言劣势,为更多的华人进入政府和议政府机构打开了栅门。比如1974年以后,随着汉语官方语言地位的确立,市政局议员候选人的资格中取消了过去“必须精通英文”的规定。陪审员也不再限制在“必懂英语”的范围内。
(二)转变政府职能,关注社会福利事业
在二战以前甚至延至50年代,港英政府只是把香港当作英国在远东的一个军事和商业据点,最注重的是如何为宗主国谋求战略上和经济上利益,掠夺式的短期行为多于建设性的长期考虑。连后来的总督戴麟趾也承认在1953年以前香港没有什么可以真正称为社会政策的,香港的政策是集中力量为财富的积累创造条件,而不关心财富的二次分配。[(23)]1968年一个官方的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尽管香港在其它方面有了显著进展,在社会保障领域却以几乎完全没有发展而引人注意”。[(24)]
如果说在60年代以前抱有避难或移民心态的老一代香港人对港英政府有无社会福利政策并不太关注的话,那么,60年代以后与“经济奇迹”同时成长并把香港作为他们家乡的新一代香港人便再也不能忍受“只创造不分享”的社会现实,他们强烈地要求对经济发展的成果进行公平的再分配。为此,他们不断地集会、游行、请愿以至街头暴力对抗。这些都迫使港英政府重新审视它的社会政策。而经济的迅速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积累,也为香港当局改变社会政策提供了条件。1971年新任总督麦理浩在立法局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就着重表示,他在职期间有三件大事要优先办理,即房屋、教育和社会福利。[(25)]此后,社会福利计划按照总督的指令全面推行开来。
麦理浩上任以来至1980年,政府在房屋、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取得了相当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住房方面,1972年成立了由政府多个部门首长及12位非官守议员组成的职权更加广泛的房屋委员会,负责完成为150万人建筑公共房屋的任务。1976年又开始实行一项“居者有其屋”计划,将住房出售给现有的公房住户,并以此筹积更多的资金为那些需要租房的人再建新房。至1978年,已有200多万人——约占香港人口的46%——住在40万套由政府提供或补助的住房里。[(26)]在教育方面,1971年,政府公立小学已实现免费教育,得到政府津贴的民办学校也有20%的学生免收学费。在公立和受津贴的小学学生中,约有20%的学生每年可得到书费和文具费的补助。1974年发表了白皮书,1977年又发表了绿皮书,规划全港教育。1978年,港府建议对年龄在15岁以下的学生实现普及中等教育。次年,九年义务和免费教育正式实施。同时,增加对大学和技术教育的投入,为经济发展储备后劲。在社会福利方面,1971年在对接受援助的人进行收入考查的基础上开始提供现金津贴,这是香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政策。1972年接受现金津贴者的人数又比上年增加了60%,1973年又在72年基础上再增加11%。此外,政府对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不进行收入考查也予以直接补助。1977年起,凡是15岁到55岁的身体健康的失业人员也开始有资格申请公共援助,而在此以前只有失业人员的家属可以申请。至1978年,政府用于社会福利津贴的支出经过社会福利署的就比1973年增加了一倍。1979年还发表了一份内容广泛的白皮书《八十年代的社会福利》,提出了社会福利十年计划,这些都反映了港英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政策。
(三)加强劳工立法,使劳工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
在1953年以前,香港几乎没有劳动立法。1953年首次提出的工人赔偿条例,不仅所涉及的工人权益范围狭小,而且只适用于少数大工业企业。60%以上的劳动力完全得不到工时限制、假日和休息日的保护,也没有关于疾病津贴、最低工资、最长劳动时间及妇女分娩有薪假期的规定权利。在政府“只重经济不重权利”大政策庇护下,雇主几乎成为工业内部的无冕之王。他们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可以任意地扣减工人工资、增加劳动时间和强度,任意地解雇工人而不发给任何遣散工资。工人的工作条件不安全,工作权利无保障。
从60年代工业化开始,担当创造财富主力军的工人们纷纷组织和参加工会与雇主进行抗争。1968年全港有工会254个,会员117,920人,1978年则增加到工会326个和会员360,738人。[(27)]日益增多的工会和日益频繁的抗争活动终于引发了60年代到70年代香港政府劳工立法的高潮。1968年一年,港英政府推出的劳工立法就有33项。[(28)]
数目繁多的劳工立法从各个方面对劳工的权益提供了保护。雇主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待工人了。比如1968年颁布后来又不断修订的“雇佣条例”规定,雇主与雇员一定要建立契约关系。有契约关系的雇员,资方若欲解雇,必须提前一个月给予通知,否则要多付一个月工资。如果雇员连续工作超过5年,可以享有一笔长期服务金。再如“雇员赔偿条例”规定,如果雇员由于受雇及在雇佣期内发生意外而致受伤或染上职业病,则虽然雇员在意外发生时可能犯有错误或疏忽,雇主都须负赔偿责任。其它如“劳资关系条例”、“破产欠薪保障条例”、“职工会条例”、“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制造业方面工业培训条例”等立法,其中心也都是在于保护劳工的政治、经济、教育及人身权益。
总而言之,香港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虽然没有带给香港社会一个同样令世人瞩目的政治奇迹,却也引起了政治领域一连串的良性变化。从结构方面分区民政署的成立、公务人员的本地化、市政局民选议员的举办、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的开办及廉政公署的设立,到政策方面承认汉语为官方用语,注重社会民生福利和立法保障劳工权益,每一环节都标志着香港政治向现代民主方向的进步。香港经济与政治联动发展的历史过程说明,一个社会最优先发展的应该是经济;当经济工业化多元化进展到一定程度,再逐步推进政治领域的改革,社会就会在平衡协调中求得整体的进步。
注释:
(1)G.B.Endacott,Hong Kong Eclipse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art 3,Ch.3.
(2)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1,P.23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3)郑德良:《香港经济问题初探》第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增订本)。
(4)Commercial Guide to Hong Kong 1951 (Hong Kong: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1950)p.49.
(5)Commercial Guide to Hing Kong 1951 (Hong Kong: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1950)P.44.
(6)李宏:《香港大事记》,第106页。
(7)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Hong Kong:Department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1969)p.88.
(8)(10)(12)李宏:《香港大事记》,第129、144、150页。
(9)郑德良:《香港经济问题初探》,第13页。
(11)香港经济导报编:1961年《香港经济年鉴》,第43—50页。
(13)(14)(15)(16)诺曼.J.迈因纳斯著,伍秀珊等译:《香港的政府与政治》,第256、126、127、266页。
(17)史深良:《香港政制纵横谈》,第55—56页。
(18)Gene Gleason,Hong Kong P.219(New York,1962)
(19)Annual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for 1974,p.9(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20)《1976年香港年鉴》,“香港全貌,廉政公署”。
(21)Ian Scott,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p.111.
(22)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udents,A Review of Student Movements in Hong Kong (Wide Angle Publishing Co.,1983),p.14.
(23)(24)(25)(26)(27)乔·英格兰、约翰·里尔著,寿进文等译:《香港的劳资关系与法律》,第22、390、392、393、159页。
(28)李昌道等:《香港政制与法制》第120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