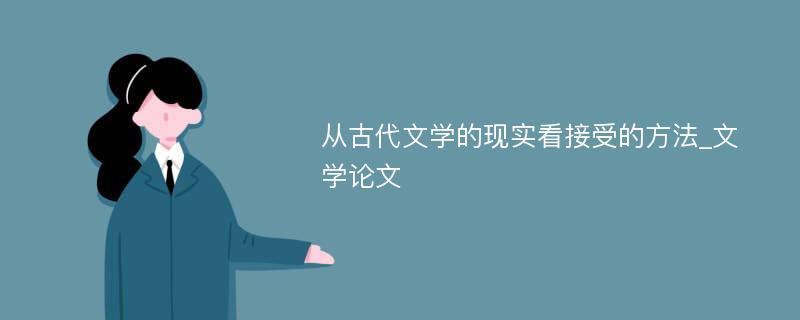
从古代文学实际寻找接受方法的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接受方法是本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颇为时兴的方法。
这种新兴的接受方法起源德国南部的康斯坦茨学派,旋即风行于欧美各国。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汉斯·罗伯特·尧斯和沃尔夫冈·伊塞尔,他们把文学文本看作读者接受的一个历史性的永恒的对象,研究了文学文本在接受过程中的关系,特别强调读者在文学创作过程和鉴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对我们研究受意者的途径很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
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文学鉴赏的实际,有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某些接受理论,以建构具有中国气派的接受方法的话语。
一、受意过程
接受理论认为,作者、文学文本、读者是一个动态的完整的文学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创作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作者赋予文本发挥某种功能的潜力;第二是接受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读者通过阅读实现这种潜力。把这个过程公式化则为:
作者←→文本←→读者
这个理论的出发点是作者而不是读者。尧斯所谓的要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伊塞尔所谓的要“暗含读者”,都是从作者的角度来阐释接受理论。由于视角不同,分析、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就不同。
现在我们要从语言的角度考察读者接受文学文本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过程,理所当然应把视线集中投射到读者身上,把读者视为整个受意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受意过程的公式应当颠倒为:
读者←→文本←→作者
而且,我们对这个过程的阐释也与一般接受理论不同。读者接受文本意义的整个过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只需经历由读者到文本,再由文本返回到读者这样一个小循环的过程。一般读者只从语言文字符号所指的层面上去接受文学文本的思想意义和教育意义,无需去揣摸作者的构思和创作意图。而对于那些从事文学史教学及研究的“高级读者”和“超级读者”,则不能就此止步。还必须继续前进,从文本深入到作者其人;再从作者其人返回到文本,从文本返回到读者,就是说,需要经过一个大循环的过程。下面侧重讨论这种大循环的受意过程。
这种大循环的受意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级叫顺向接受阶段,即沿着读者←→文本←→作者的方向被动地去接受文本之意。
这一阶段需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由读者到文本。文学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它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才能从文本的符号系列中显示出来。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就作为一种具有持续稳定性的艺术产品而存在,保证它的存在的是一系列经过作者人为地按一定密码组构的符号。读者首先要能识别基于不同表现形式的各种不同系列的符号,然后才能从具有众多审美规范的涨落系统的背景中将它具体化。“春风”一词,符号“所指”的意思是“春天的风”,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元日》),用的就是这个意思。而用在另一些诗句中,它的审美意蕴就丰富了。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欧阳修《戏答元珍》)。这些符号系列中的“春风”就不单纯指自然界中春天的风,而更主要是指朝庭中的暖风,指“皇恩”。而李白“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春思》),“春阿吹别苦,不遣柳条青”(《劳劳亭》)中的“春风”更不是指物,而是用拟人的手法渲染与情人或友人分别时的氛围。至于孟郊《登科后》中“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中的“春风”,已经与“得意”粘合为一个成语,表示考中进士后的喜悦;《说苑·贵德》中“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则用来比喻及时给人们教益。读者手捧文本一开始就要读懂语言符号系列中这些密码的意思,才能进入审美领域。
顺向接受的第二步是由文本到作者。有经验的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确实会考虑到“隐含的读者”的语言能力和审美能力,给读者留下一些可供思考和回味的空白和不确定的因素。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不能就文字理解文字,还需认真领会作者创作文本时的良苦用心。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一诗就有意给读者留下了不少空白。首先,诗中只有答语,没有问语,问的言词让读者去补充。其次,作者为什么要去寻隐者,与隐者的情义有多深也还需要作者去思考,再次,诗题是“不遇”,究竟“遇”到了没有呢?是继续寻觅,还是就此返回?还有,隐者是谁?是他人,还是作者自我人格的写照?这些问题需要了解作者的总体思想和创作意图才会得到中肯的答案。
大循环受意过程的第二阶段是逆向接受,是主动受意的阶段。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由作者回到文本。贾岛人在红尘、心在深山,以佛家的空无为本。他这次上山云游是为了求“兴”,“隐者”虽未寻到而与童子的一番对话足以“尽兴”,心灵上已与“隐者”相遇。在佛家看来万物皆空,只有自我的“心”才是实的。心中既已相遇,又何必再去寻觅什么。从作者笃信佛教的心境、情趣来阐释这首诗,就能把握它的真谛。
逆向接受除从作者总的思想倾向来理解文本外,还可以从作者创作文本时的境遇来加深对文本的认识。元和四年,柳宗元带领一些人游览了永州城外雄奇美丽的山光水色,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其中《钴汜潭西小丘记》,写他发现一座竹树青翠、石块奇突、山峰不凡的小山,主人标价四百,但卖不出去。作者把它买过来,捎加修理便呈现出清幽秀丽的真容。于是感慨说,以这座小丘秀丽的风景,若是生在长安,大家会争相购买,每天涨价千金也买不到:
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道乎?
如了解作者写这篇散文时的心境,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买了一座无人顾屑的小山会如此高兴。写此文的前几年,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而被贬为永州司马。五年来他继续遭到权贵的迫害,很多趋炎附势的亲友都远离了他,他坚信自己的主张和从事的改革是正义的,总有一天会被人们理解的。在这篇散文中,作者借被埋没的小丘来诉说自己的政治遭遇和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逆向接受的第二步是再从文本返回到读者。这时,读者对文本的符号所指,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文本的意图以及文本形象中的“多余思想”、“过剩题材”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因素,进行再创造,能动地接受文本客观存在的意义和意味。读者对文学文本主观能动地再创造,用逻辑语言付诸文字则是文艺批评,用艺术语言付诸文字便成了新的文学作品。我国古代,读者和作者之间不存在什么天堑。明代胡应麟说: “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僧尼)、羽客(道士)”(《诗薮》外编卷三)。
这些人既是读者同时也是作者。中国之所以被称为诗国,正因为人们既喜欢读诗也喜欢写诗。很多诗人就是在广泛阅读、欣赏前人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以取得突出的成就。其它文学形式亦然。金代董解元阅读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对文本“始乱之,终弃之”的主题大为不满,而对美丽、善良、多情的崔莺莺的悲剧命运则颇为同情,这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接受。后来他创作的剧本《西厢记诸宫调》就改变了“始乱终弃”的主题。元代王实甫阅读《董西厢》,觉得主题还不够鲜明,还应提到“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的高度来表现,于是便创作了大型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这就是读者对文本的二度创作,诉诸文学,便形成了文学的继承与革新。
从理论上说来,受意过程经过以上顺向接受和逆向接受两个阶段便完成了,而在实际受意过程特别是研究性的接受过程中则需要经历多次的反复循环才能完成受意任务。
二、受意方式
读者在受意过程中,对文学作品意义的接受方式很多,值得讨论的有以下几种:
(一)历史接受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文学作品从拥有第一个读者起就已成为历史,每个读者接受作品的意义都是一种历史性的接受。无论作品写的是过去的题材、现在题材、还是幻想中的未来题材,都是一定时代观念规范的反映。人们研读各个时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本质上都是在研读某种文学的历史,由此产生了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等学科。人们研读文学史上的作品大多习惯于用现存社会的思想、政治、道德、行为等规范系统去理解,去衡量;而另一些人坚持用文本产生时代的规范系统去研究、去品评。这两种接受方式,前者不尊重历史,后者不考虑现实。其结果不是将作品的意义拔高,就是将它的意义贬低。一部《论语》、一部《庄子》是中国儒、道两家经典的文学作品,几千年来,时而被人们捏扁,时而又被人们搓圆,都不是真正的历史接受的态度。
真正的历史性的接受,既要注意从传统中追寻文学文本意义中相对确定的因素,以使之回归;又要注意挖掘其意义中那些不确定的潜力,使其泛化到让当代人能够接受的程度。司马迁读《离骚》,就注意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和评论,他说:
屈平疾王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濯淖淤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爝然泥而不滓者也。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这样的评论既尊重历史又超越历史,把过去和现在的意义折射调和起来,古人今人皆可接受。
历史性的接受,有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作品的接受;也有同一时代不同阶层、不同观点的人对同一作品的接受。他们从作品中所接受的意义有的相同,有的则相左。同时西汉人阅读《离骚》,王逸的《离骚经序》与司马迁的观点一致,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则认为屈原写《离骚》是“扬才露己”,达不到个人的目的才“忿怼不容,沉江而死”。历史性的文本的接受研究,似乎可以任人接受,而其中相对稳定的意义则不能“脱缰式”地随意评说。
(二)比较接受
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和潜在的意义,读者通过不同文本的比较,能更好地认识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因而,这种接受方式越来越为阅读和研究文学史的人们重视,并广泛加以使用。
用比较的方式研读文学史,可以进行纵向比较,也可以进行横向比较。纵向比较接受,是从历史的纵切面上比较不同时期内容、题材相同或相反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陶渊明、王维、孟浩然、范成大都以反映农村题材,描写田园生活著称于世,都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而他们作品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不通过纵向比较;则很难作出公允的评论。两汉文学由于受儒家思想影响,耻于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农村风物,陶渊明破天荒地把田园生活作为审美对象。他的田园诗有躬耕劳作的真实感受,有探寻桃源的理想主义,有采菊东篱的隐士风度,作为田园诗的鼻祖是当之无愧的。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高士的闲情有余,而亲身的体验不足。如果陶潜称得上是田园中的主人的话,那王、孟不过是田园中匆匆来去的游客,但他们善于捕捉到田园中隐藏较深的蕴味。陶与王、孟的田园诗都有点飘飘然,而范成大的田园诗就比较贴近现实,比前人的同类诗多了几分泥土的气息和揭露剥削的内容。从审美价值看,王、盂的诗略高一筹,从政治意义看范成大的诗多得一分,他们从两个不同的侧面继承并发展了陶渊明的田园诗。
横向比较接受,是把某一作家的文本与同时代其它作家内容相近的文本作比较,以便更好地掌握其意义的特殊方面。陶渊明与谢灵运都活跃于东晋、刘宋交替之际,在诗歌题材的拓展上都具有开创性的功绩,都以崇尚自然美而著称于世并深深影响着后代山水田园诗人。但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看,陶诗胸次浩然,理想崇高,同黑暗官场决裂的态度比较坚决,是真心实意回到田园中去寻求人生的乐趣。因而同农人、渔樵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劳动的价值。而谢诗总是念念不忘政治权势,缺乏崇高的理想,往往借浪迹山水来掩饰“心存魏阙”的郁闷。表面似乎很清高,实际未免显得“浊低”。总的看来,谢诗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均不及陶诗。
比较接受可以在多方面进行,这里我们仅谈了在受意过程中的比较接受。
(三)审美接受
对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及作家的创作意图的接受,由于读者的动机、需求、效果不同,大体可分为一般的审美接受和高级的审美接受。
一般的审美接受,多以个体的形式出现。各个读者可根据自我的审美经验和趣味、感受、体验、理解文本的意义,无需过多顾及作者创作意图的初衷和社会群体意识的规范。《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何许人也,现难以稽考,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也不得而知,但并不影响人们对这部划时代的以日常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阅读和欣赏。小说写清河县生药铺老板西门庆勾结官府和社会上一些“不守本分的人”有恃无恐地为非作歹,与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荡妇纵欲乱淫,以至家败身亡的故事。人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把它做为一面镜子,了解明代中期上至朝庭太师,下至地痞流氓,中至各种市井人物的真实面貌和当时社会中各种黑暗污秽的情况;也可从民俗学、宗教学的角度,认识当时社会的各种风情习俗;还可从文学的角度分析各种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生动性;以及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当时白话小说的特点、日常口语、方言、成语、谚语、歇后语的运用,等等。阅读时,人们可以按各自不同的审美心理,不同的情感态度自由地接受。对西门庆,潘金莲等人所作所为的身世和悲剧结局,可以同情,可以批判,可以为戒,甚至可以效法。只要不把自己的感受和意见发表出来,不产生社会效果,都属于个人一般性的审美接受。
高级的审美接受,要受一定社会的审美标准和道德规范的制约,要考虑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客观的社会效果。明万历丁巳年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序》就是较早的对《金瓶梅》一书进行品评的高级审美接受的文章,《序》研究了《金瓶梅》的性质、作者的创作意图、社会效果及读者的情感态度:
《金瓶梅》,秽书也。……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戏中粗暴的男性角色,引者注),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
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善耳。”
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可也。
(明万历年间刊本《金瓶梅词话》
卷首,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这些研读性的评论,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我们现在的研读者,大多把《金瓶梅》看作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明代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充分地暴露了当时社会腐朽、丑恶的现象,但缺乏应有的批判。
研读《金瓶梅》可以从丑的对象中受到它的对立面——美的教益,这是古今评论者共识性的意见。
三 受意方法
受意者要想很好的接受文本文字符号背后深层的味外之旨和韵外之致,还须讲究受意的方法。受意的方法多种多样,有两种是值得研究的。
一种是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他认为,欣赏主体在接受文学文本的过程中应做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下》)。就是说,读者不要因为文学文本采用了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就影响自己对辞意的理解,也不要仅仅从文字符号的表层意思来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而要充分发挥欣赏主体自我的审美能力,调动感觉、情感、想象、理解等审美知觉的心理要素(“意”)去揣摩、体验(“逆”)作者的创作意图(“志”)。把作者外化了的心灵通过具体的艺术语言还原回去,这样才能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理解作品的思想意义。
“以意逆志”是以欣赏主体的“意”去“逆”(迎)作者和文本客观存在的“志”,这难免会带有主观主义。为了在进行艺术欣赏时尽可能减少主观成份,孟子又提出“知人论世”的弥补办法。他说: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万章下》)
这话本来是针对“士”的修养而言的,但已涉及到文学欣赏的方法。意思是说,要理解古人的“诗’、“书”,除“以意逆志”外,还要了解作者其人,了解作者创作文本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才能准确客观地把握作品的旨意。
“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有机结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辩证的受意方法。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那在什么地方呢?文章说:“在乎山水之间”,接着又说“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绕来绕去玩弄文字游戏,最后还是归结于酒。他不会喝酒,“少饮辄醉”,因心里高兴最后还是喝个晕头转向。他高兴的原因本来就是“醉翁之意”的所在。但作者并未正面指出,而又含糊其词地说:“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乐其乐”,诸家注本解释为“为游人的快乐而快乐”。把“其”解释为“游人”是不妥的,应解释为“他”,即作者自己,才是文章的所本。作者究竟高兴些什么呢?在文章中是难以捉摸的,如用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到文外去寻求,就比较容易理解“醉翁之意”的所在。写《醉翁亭记》的第二年,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一封信中说:
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之人不忽小官也。
这话道出了“醉翁之意”的真谛不在酒,也不在山水,而在“小邦为政”,一年就见成效。作者因积极参加范仲淹领导的革新运动,遭到保守势力的排斥被贬为滁州太守。自己的才能和报负在朝廷虽得不到施展和实现,而到滁州这个小地方短短一年多时间就“粗有所成”。这就是他“乐”的原因,而且在“乐”的后面还隐藏着难以言表的忿怨与不平。
另一种值得研究的受意方法是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不求甚解”,不能理解为读所有的“书”都只要“知其然”,不必“知其所以然”,而是说读书有几种读法,有的必须“求甚解”,必须穷追不舍,究其根源。而有的则不需要去“求甚解”,特别是读诗歌作品更是如此。正如明代谢榛所说:
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
(《四溟诗话》卷一)。
而一些论者未能洞晓“不求甚解”的妙用,对此颇有微词,不过是俗儒之见。俗儒解诗受意,一是只在片言只字上钻牛角尖。有的摘章寻句,傍征博引,东拉西扯、烦琐考证。文本中的一个字,一个词,竟用洋洋万言的巨大篇幅进行诠释,使人愈读愈不得其要领。有的主观臆断,断章取义,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苦心搜寻其年、其地之事,硬说某诗是为了某事而作,如说李白的《蜀道难》是“为严武入蜀而作”,杜甫的《兵车行》是为征吐蕃而作之类。有的人云亦云,胸无所得。这些学究、俗儒式的读书办法,怎能认识“不求甚解”之妙?
“不求甚解”的受意方法不拘泥于从字、词、句的小、处入手,而侧重从总本上的情、性、义、理去把握诗中所言的“志”。柳宗元《别弟宗》一诗云:
零落残红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后十二年,他的堂弟柳宗一来看望他,不久宗一便要离他赴江陵,他便写了这首赠别诗。诗篇借伤春写惜别,又借伤春惜别抒发遭贬后的危苦和隐恨。尾联两句的“梦”、“烟”二字把诗意引向空灵的境界,表达了难以言表的相思之苦和不平之意。如硬要说“梦中安能见烟”(《竹坡诗语》),未免就给人以吠日之消。柳宗元今后梦里到底和堂弟宗一在什么地方相逢,到底见到什么?大可不必去求“甚解”,今后也许他根本不会入梦,也许常在做白日梦,这些都无碍对诗意的理解。南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一词写他中秋之夜、泛舟洞庭,见到“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便“悠然心会”,感到“妙处难与君说”。他“心会”什么,“妙处”何在,无非是借以表示自己玉壶冰心,光明磊落的品格。若还要深求什么“甚解”,不被人讥之为迂腐的学究,就被人视之为说梦的痴人。
“好读书”与“不求甚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前提,是条件。没有“好读书”的基础,没有鉴赏文学作品的学、识、才、力,就不能真正掌握“不求甚解”的受意方法。这就是曹植所谓的“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与杨德祖书》),也就是刘勰所说的“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心雕龙·知音》)。不读书,又“不求甚解”的是庸人;“好读书”,而处处务求“甚解”则是迂儒。这两种人岂能与静节先生同日而语。
标签: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艺术论文; 金瓶梅论文; 文化论文; 春风论文; 隐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