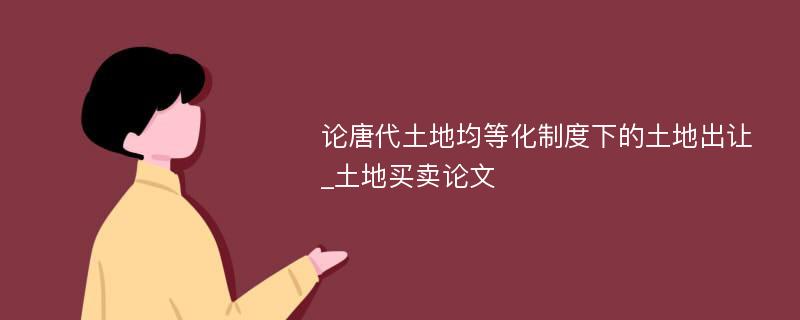
论唐代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田制论文,唐代论文,土地论文,买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前期均田制的破坏有着各方面的因素,其中土地买卖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认真研究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是了解唐代均田制变为庄园制,租庸调制变为两税法,府兵制变为募兵制的关键所在。
唐初均田制下土地买卖的存在
众所周知,均田制在北齐时就遭到很大的破坏,土地买卖的现象非常严重。隋文帝即位后,革除流弊,弥补缺漏,使均田制更加完善和进步,加上认真推广实施,使土地买卖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唐代均田制下土地买卖明显加剧,这从唐初均田令的规定中得到证明。《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载武德七年(624)均田令规定:“丁男、 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以所载百分之二十为世业田的比例计算,一个丁男占有二十亩世业田。当时,官吏的永业田比农民规定的数量为多。《通典》卷2 《田制下》载开元二十五年规定:“其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可知官吏的永业田最高达百顷,最低的数额也有六十亩,是一般丁男的3倍。
永业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政府的控制,不完全私有,但基本上还是私有的。武德七年(624)田令明确规定:“世业之田, 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就是说永业田在丁男身死后由其继承人接受,国家不再收回。这一规定,在开元二十五年(737 )田令中交待的更为明白,“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注:《通典》卷2, 《田制下》。)。这类土地国家是允许买卖的,如《唐律疏议》卷12《户婚律》云:“即应合卖者,谓永业田,家贫卖供葬。”也就是说农民在没有经济力量办理丧事的情况下,永业田可以卖掉。占受田80%的口分田虽然规定身死“则收入官,更以给人”(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但在特殊情况下国家也允许其买卖,“及口分田,买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狭乡乐迁就宽者,准令并许卖之”(注:《唐律疏议》卷12,《户婚律》。)。即口分田在四种情况下可以买卖,其一是买来用于充宅,其二是用于建造碾硙,其三是买来用于建造邸店,其四是从狭乡迁往宽乡者。由此看来,口分田虽然不象永业田一样为个人所有,但可以买卖的情况仅次于永业田。口分田和永业田的买卖规定尚且如此,其他土地的限制就更松了。如赐田、自买田等,“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注:《唐律疏议》卷12,《户婚律》。)。由此可知,在均田制下,土地买卖仍然是存在的。
除此还有不少其他情况下的土地买卖,事实上并没有受到政府的禁止。如《旧唐书》卷191《张憬藏传》云:“张憬藏,许州长社人。 少工相术,与袁天纲齐名。……左仆射刘仁轨微时,尝与乡人靖思贤各赍绢赠憬藏以问官禄。”张憬藏“固辞思贤之赠,曰:‘公当孤独客死。’”“思贤谓人曰:‘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岂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继而死,尽货田宅,寄死於所亲园内。”靖思贤是豪富之家,并非贫无可供葬者。看来,这类土地买卖是在均田令所规定条件之外的。又如《新唐书》卷112《员半千传》载:咸亨中, 员半千上书自陈:“臣家赀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五十石,闻陛下封神岳,举豪英,故鬻钱走京师。”实际上,员半千卖地是为了到京城求官,并不属于田令中规定的流移者,这说明唐初还存在着国家规定之外的土地买卖。这种情况虽然不十分普遍,但它作为均田制下土地买卖存在的一种形态却值得重视。
另外,在天灾人祸、战争破坏,以及剥削压迫苛重等情况下,百姓不得不把其土地卖掉,政府也不加禁止。例如武则天崇尚佛教,大兴土木,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贫弱者为了充劳役只好“卖舍贴田”。这种买卖土地的行为按规定来讲是不允许的,但事实却是如此。因为不卖舍贴田,百姓就无法完成烦重的徭役,官府只好允许他们在规定之外买卖土地了。还有武则天时期,由于突厥的不断入侵,战事频繁,徭役烦重,征调苛急,造成农民破产,“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可知,唐初在均田令规定之外,政府默许的土地买卖也是存在的。
唐中叶土地买卖的加剧
从唐中宗,经玄宗,到肃宗、代宗时期,均田制日益趋于破坏和崩溃,土地买卖比此前大为发展。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充足的证明。
第一、均田令所规定的买卖土地的条件比以前有所放宽。永业田在贞观、永徽时只有五品以上勋官和一般百姓“家贫卖供葬”及“狭乡乐迁就宽者”(注:《唐律疏议》卷12,《户婚律》。)可货卖,开元二十五年(737)田令又增补“流移者亦如之”(注:《通典》卷2,《田制下》。)。这里的“流移者”不包括乐迁就宽乡者,只包括未经政府批准的流亡人户。这样一来,永业田买卖的范围就比前放宽了。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早在武则天圣历年间,韦嗣立曾上奏指出:“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注:《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韦嗣立传》。)。这未免夸大,但至少可以证明当时人口逃亡的严重程度。唐玄宗开元时期,进士柳芳又云:“人逃役者,多浮寄于闾里,县收其名,谓之客户,杂居于人者,十一二矣。”(注:《全唐文》卷372, 柳芳《食货论》。)著名的宇文融括户就发生在此时,“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余万”(注:《新唐书》卷51,《食货志》。)。对这个数字当时虽有不同看法,指出由于州县希旨,往往以“编户为客”,但这八十万客户绝不全是原来的编户,其中必有部分是逃亡流移者。安史之乱以后,战争频繁,天下流移人户更加增多。如天宝十四载(755)天下有8 914 709户,至乾元三年(760),只有1 933 174 户(注:《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减少的户数竟达到6 981 535户。 逃亡户可以卖掉永业田,仅这一点,就可把均田制下的土地买卖加剧好多,不论在买卖的人次上还是在买卖土地的总量上都无疑远远超过从前。除以上永业田买卖条件被放宽外,开元二十五年(737)田令又规定: “所给五品以上永业田,皆不得狭乡受,任於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即买荫赐田充者虽狭乡亦听”(注:《通典》卷2, 《田制下》。)。这就是说,五品以上官在狭乡的永业田国家无地授与,由他们通过买荫赐田的渠道来解决。这些人不仅规定的永业田的数量多,而且皆是豪门权势之家,他们买卖土地也促进了这时期土地买卖的发展。另外,同样的规定,由于时代不同,也会对土地买卖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允许“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注:《通典》卷2, 《田制下》。)这一条,开元天宝时期产生的后果就比武德、贞观时期要大得多。因为唐初旧的门阀士族地主受南朝和隋朝政府的打击已经衰落,新贵族地主还没有羽毛丰满,他们虽然通过各种途径买卖土地,但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开元天宝时期却不同,此时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大官僚地主和大商人地主的势力已经膨胀起来,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他们会通过这一渠道无限制地购买土地。如财可敌国的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注:《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均田令规定下的土地买卖比以前大为发展。
第二,从事土地买卖的人比以前有所扩大。以前,从事土地买卖的大多数是官僚豪强和富商大贾,而这一时期进行土地买卖的人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普通百姓。皇亲国戚如杨贵妃姊虢国夫人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韦嗣立旧宅,想全部买得,便“谓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货,其价几何?’韦氏降阶曰:‘先人旧庐,所未忍舍。’语未毕,有工数百人,发东西厢,撤其瓦木。韦氏诸子乃率家僮挈其琴书,委於路中,而授韦氏隙地十数亩,其宅一无所酬”(注:《明皇杂录》下。)。官僚贵族买卖土地者如刑部尚书卢从愿,“占良田数百顷”(注:《新唐书》卷129,《卢从愿传》。)。 地方官吏买卖土地者,如东京留守李憕,“丰於产业”(注:《旧唐书》卷187 下,《李憕传》。)。一般官吏买卖土地者, 如宝应元年(762)四月敕指出:“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所以逃散,莫不由此。”(注:《册府元龟》卷495,《田制下》。)所谓殷富之家, 就是指一般的地主而言。如相州王叟,富有财,“积粟近至万斛,……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注:《太平广记》卷165, 王叟引《原化记》。)。王叟就是所讲的殷富之家。一般百姓买卖土地者也不是少数,与以前相比,更显得普遍。如天宝十四载(755 )八月制云:“天下诸郡逃户,有田宅产业,妄被人破除,并缘欠负租庸,先以亲邻买卖,及其归复,无所依投。”(注:《唐会要》卷85,《逃户》。)制言“妄被人破除”和“亲邻”虽然没指明身份地位,但大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因为在乡村者的亲邻一般是附近的农民,殷富之家固然不乏,但大都还是一般无权势地位的民庶。又如大历元年(766)十一月制云:“如百姓先货卖田宅尽者, 宜委本州县取逃死户田宅,量丁口充给”(注:《唐会要》卷85,《逃户》。)。这里把百姓买卖土地记载的就更为清楚了。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不仅是买卖土地的人员在扩大,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也成为土地买卖的主要代表之一,许多农民因赋役所迫而逃亡,官吏便将其田地货卖以充租庸。如乾元三年(760 )四月敕云:“逃户租庸,据帐征纳,或货卖田宅,或摊出邻人,展转诛求,为弊亦甚”(注:《唐会要》卷85,《逃户》。)。看来,地方官府货卖逃户田宅以充租税已成为平常之事了,国家虽然认识到为弊亦甚,但无法禁止。
第三,在土地买卖中买方和卖方发生了变化,是这一时期土地买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以前的土地买卖中,货卖土地者主要是贫苦农民或一般的地主官吏,购买者主要是官僚贵族和豪强大贾。但此时的土地买卖突破了原来买方和卖方的旧有框架,权贵殷富也有可能成为卖方,而贫弱百姓往往也会成为买方。如开元初,刑部尚书李日知方贵,诸子皆通婚名族,“后少子伊衡以妾为妻,鬻田宅,至兄弟讼阋,家法遂替云”(注:《新唐书》卷116, 《李日知传》。)。与其相反,贫弱百姓也有买地之举, 如宝应二年(763)九月敕曰:“客户若住经一年以上,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勒一切编附为百姓”(注:《唐会要》卷85,《籍帐》。)。所言客户,虽然包括客居他乡的商人地主、寄庄户等,但也有不少是流亡他乡的平民百姓,为了生存也尽力购买一块土地从事生产。这种情况说明在这一时期土地买卖已经开始向正常化的阶段过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展。
第四,在唐中宗至代宗这一时期,均田制下土地买卖的发展不仅反映在以上几个方面。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能得到反映。据敦煌文书所载唐高宗至唐代宗的户籍中可知,在天宝之前户籍上没有自买田的记载,而从天宝六载(747)以后,户籍中买田的记载明显多了起来。如斯坦因敦煌文书第3907号载唐玄宗天宝六载(747 )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户籍残卷(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附录,中华书局1979年。)载:户主郑思养,“一十二亩买田”。敦煌文书第514 号载唐代宗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残券载: 户主索思礼,“一十四亩买田”,等等。王仲荦先生认为这是合法的永业田和口分田的买卖,因为“买田记载在户籍帐上”(注: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第2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安史之乱以后,口分田和永业田的买卖事实上已不再受以前均田令规定的限制了,因为均田制已经崩溃,没有实际作用了;二是从户籍所载内容来看,所买之田可能是在田令规定额之外的土地买卖。如郑思养受田百亩,已有40亩永业田;索思礼已受2顷40亩,其中也有40 亩永业田。根据均田令百分之二十为永业的比例计算,以上诸户的永业田无一不符合规定。由此证明,户籍上的买田,很可能是永业田之外每户所买的私有土地,所以能写在户籍上,并得到政府的承认。这种土地买卖在唐玄宗以前极少见,反映了这一时期土地买卖的新发展。
均田制下存在土地买卖的原因
在均田制实施期间,土地买卖不仅一开始就存在,而且越来越发展。那么,为什么在均田制下会出现土地买卖?土地买卖又为何屡禁不止反而日益加剧?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均田制下土地买卖的出现和发展,首先与两种土地所有制形态并存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唐代政府是允许私有土地买卖的,而均田制本身恰恰包含着私有土地成份和容忍在其之外存在土地私有。
均田制本身所包容的私有土地,主要指永业田。永业田不用回收,世代继承,是属于农民的私有土地。丁男受田一顷,其中20亩为永业田,而且在受田时优先满足永业田的数额。即使按规定的比例计算,全国所受的公田,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变成私田,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数字。《通典》卷19《官数》载:“大唐(官数)一万八千八百五员,内官二千六百二十一,外郡县官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五。”这一数额虽然没有指明是开元时期的,但与唐玄宗时期的官数不会有多大出入。官吏永业田中除去最高一百顷不论,仅以“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计,此时官吏永业田额达90 000顷。若以最低一等“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计,永业田也有10 800顷。再加农民所受永业田,数量就更多了。
均田制本身还包容有园宅地。均田令规定:“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注:《通典》卷2, 《田制下》。)园宅地也是私有性质的土地,其理由之一,园宅地政府授与后不再收回,也和永业田一样由儿孙世代相继,除非是死绝户的园宅地国家才收为国有。相比之下,这种田比永业田更加稳固而不易变动,故在均田令还授制度中,从来没有见到回收园宅地的规定。其二,园宅地买卖不会受到政府的禁止,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所载,《高昌延寿十四年(唐贞观十一年)康保谦买园券》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园宅地可以买卖,即表明属于私有土地了。《通典》卷2 《田制下》云:“亲王出藩者,给地一顷作园。”其实不出藩的诸王和京官,园宅地也不会少,从他们所居住的府第规模来看占地是很广的。据《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所载,天宝十四载(755)有52 919 309口,园宅地总额多达17 639 769亩。汪篯先生曾考证:“唐政府掌握的约六百二十余万顷的田亩中,已经包括了大量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这约在一百八十万顷至二百三十万顷之间的隐匿田亩。”(注:《汪篯隋唐史论稿》第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天宝十四载(755),园宅地大约是总耕地面积的二十二分之一。 均田制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的私有土地。
均田制之外的私有土地还大量存在。一是官吏的赐田,最多者如裴寂,有“赐田千顷”(注:《新唐书》卷88,《裴寂传》。)。二是官吏的勋田。唐代的勋官皆有勋田,如武周圣历二年(694 )前后敦煌县勋荫田薄的记载(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附录,中华书局1979年。)就是明证。三是官僚地主的家传祖业。如唐高祖时下诏:“隋代公卿以下爰及民庶,身往江都,家口在此,不预义军者,所有田宅,并勿追收”(注:《唐大诏令集》卷114, 《隋代公卿不预义军者田宅并勿追收诏》。)。四是官僚地主和贵族权势所占有的土地。如高宗时,王方翼占田“数十顷”(注:《旧唐书》卷185 上,《王方翼传》。)。中宗时,太平公主“田园遍于近甸膏腴”(注:《旧唐书》卷183,《太平公主传》。)。唐玄宗时,宦官“甲舍、名园、上腴之田……半京畿”(注:《新唐书》卷207,《宦官传序》。)。李林甫, “田园水硙,利尽上腴”(注: 《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象这样广占田地的官僚地主多不胜举。他们在均田制规定之外的土地,完全是其私有土地。五是一般平民百姓的私有土地。如《唐律疏议》卷12《户婚律》就记载和解释了有关“盗耕公私田者”,“诸妄认公私田”,“诸在官侵夺私田者”的条文。所谓“公私田”讲的非常明确,“公田”是指政府所有的,如屯田、营田、职田等等,“私田”自然是指一般平民具有支配权和所有权的土地。唐律中所言的“私田”还指在国家授与的这些土地之外的私有土地。《通典》卷15《选举三·考绩》中云:“大唐考课之法,……其劝课农田,能使丰殖者,亦准见地为十分论。每加二分,各进考一等(原注:此谓永业口分之外,别能垦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劝课,以致减损者(原注:谓永业口分之外有荒废者),……每损一分,降考一等。若数处有功并应进考者,并听累加。”这类私田大多是农民开垦的荒废土地,不是政府授予的,所以划在政府所授土地之外,作为个人的私田来处理。《唐律疏议》中所云“私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类土地,因为永业田和口分田一般是不会荒废的。
由以上所述,充分证明了在均田制下存在着大量的私田,其中包括均田制本身的和外部的。在唐高祖至唐肃宗、代宗时期,执行的并不是单一土地制度,而是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两种成分并存,虽然私有土地成分不占主要地位,但却普遍存在和不断地发展壮大。均田制下土地买卖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唐代均田制下广大农民受田严重不足,是土地买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二。唐代从武德七年(624)开始实行均田制, 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农民受田不足就已出现。《册府元龟》卷105 《惠民》云:唐太宗“幸灵口,村落僵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这是贞观十八年(644)的事情,均田制推行才20年,就出现了受田不足的现象。 至武则天时期,农民受田不足的问题,更是每况愈下。《全唐文》卷196 狄仁杰《乞免民租疏》中讲到:“窃见彭泽地狭,山峻无田,百姓所营之田,一户不过十亩、五亩。”在均田制下农民无地的现象到唐睿宗时仍然存在,唐隆元年(710)七月十七日敕云:“其无田宅, 逃经三年以上不还者,不得更令邻保代出租课。”(注:敦煌出士S1344号文书,转引自唐长孺《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书两种跋》,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唐玄宗即位后,对农民受田不足的问题也未能很好的解决。
农民受田严重不足,但租庸调的征收却不是根据实际受地多少来决定,而是根据应受田数额来征收。租庸调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注:《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租庸调是按人头交纳,凡见一丁,就要缴纳二石粟,受地少的特别是未受田的农民不但承受不了政府摊派的赋税,而且正常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为了缓和这种状况,就不能不想办法来购买一些土地耕种。封建政府因无力解决农民的少地无地问题,也只好允许这种民间的土地买卖,并将其合法化登册入籍,给予法律上的承认。所以,受田不足不能不是均田制下土地买卖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均田制下土地买卖产生和发展的第三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均田制本身的缺陷。首先是这种土地制度是国有和私有两种成分的拼凑体,也就是说这种土地制度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所有制形态。虽然《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将均田表述为“均天下民田”, 但所给民田中就含有两种成分,即露田和桑田、园宅地。这种土地制度主要是北魏拓跋族把其民族传统制度和中原已形成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相融合造成的。众所周知,北魏拓跋族在形成国家以前,长期处于原始公社阶段,财产公有的思想特别严重。但拓跋族进入中原后,遇到的却不是他们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公有制环境,而是经过长期发展并定型了的私有制度。面对这种环境和制度,北魏统治者要想立足中原,就不能把其原来的制度全盘搬移过来,必须加以改革,吸收中原私有制成分,使其既与鲜卑拓跋族相适应,又与中原汉族地主相适应。由于均田制是拓跋族原有的公有制和进入中原后吸收汉族私有制结合而成的,所以制度中公有和私有成分共存并立。公有制成分即分给诸男夫的露田,私有成分即桑田。这种公、私并立的格局历代沿袭,唐代反映的形式是口分田和永业田。均田制中有私有土地成分存在,就必然会产生土地买卖的现象。所以,均田制存在的这一缺陷是无法杜绝土地买卖的。另一个缺陷是将解决土地荒芜问题作为制定制度的主导思想,也就是说制定均田制在当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推动垦荒。众所周知,北魏建国之前,北方是中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大分裂大混战时期,北方人口大量死亡和南迁,生产遭到破坏,劳动力受到摧残,土地严重荒芜。这就是北魏统一后面临的困难局面,特别是代北京畿附近,人少地旷的现象更为严重。为此,北魏统治者从四处大量迁移户口以充实这一地区,用计口授田的办法迫使农民大力垦荒。以后每个朝代开始时,由于国家掌握的无主荒田多,均田就推行得较好。但是这种带有很大局限性的土地制度一遇到荒田弃地少的时候就不好推行了,就必然会产生买卖土地的现象。可以说这是均田制不健全、不长久等缺陷所致。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在创建时就留下了土地可以买卖的缺口。如北魏太和九年(485 )制定的均田令中就明文规定桑田:“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注:《通典》卷1, 《田制上》。)。这样一来,就在均田制中留下了土地买卖的缺口,假使没有这样的规定的话,土地买卖是不会产生的,即使在均田制之外会出现土地买卖,那毕竟是违法的,而这种买卖却是合法的,政府承认的。北魏均田制在其以后历代继续推行时,土地买卖的缺口不但没有及时杜绝,反而越开越大。北齐时,除桑田可以买卖外,原来的公田也“悉从贸易”。北魏不许买卖的露田,此时也开始买卖了,故史言,“虽复不听卖买,卖买亦无重责”(注:《通典》卷2, 《田制下》。)。至唐代虽然职分田和公廨田等严禁买卖,但永业田仍然可以买卖,不但如此,而且把口分田的买卖进一步合法化。北齐时口分田从制度上讲还是不准买卖的,只是买卖无重责,而唐代均田令中正式规定可以买卖,而且买卖的条件和限制从唐初到唐开元天宝年间越来越宽。既然均田制允许土地买卖,那么在均田制下土地买卖的产生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综上所述,私有土地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带来土地买卖的存在和发展,农民普遍受田的严重不足只能通过自行买卖去解决,均田制允许土地买卖就更是如虎添翼了。在均田制下产生和促使土地买卖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上述三个方面为最根本的原因。
标签:土地买卖论文; 均田制论文; 唐朝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旧唐书论文; 通典论文; 唐律疏议论文; 新唐书论文; 唐会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