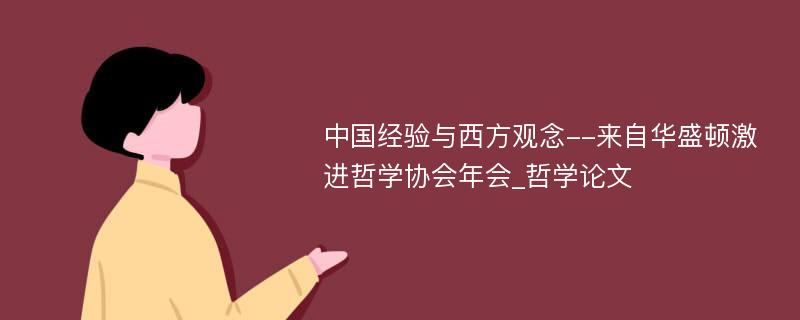
中国经验与西方概念——从激进哲学协会华盛顿年会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盛顿论文,激进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缘起
Z:过去我们讲到中国经验与西方概念之间有一条鸿沟,我看我们可以就此展开一场对话。不言而喻,我们三人的观点有同有异,对话的结果没有必要定于一论,不妨让讨论如其所是地保持其鲜活性与开放性。
W:中国经验与西方概念,这是个大题目。如何破题?J兄,你在美国先待了半年,据说与老美有深入的接触,中间又参加了一场很有意思的左派哲学大会,在会上得遇诸多左派健将,一定对此话题有不少感想,由你开头如何?
J:好,我先来抛块砖头。我从那次会议谈起。此会的确有意思。首先,会期是2004年11月4日至7日,美国总统大选尘埃刚刚落定,11月2日投票,11月3日出结果,此会11月4日开始。其次,会址选在首都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全美最著名的黑人大学,从此大学去白宫,步行不会超过一个半小时。最后是会议主题,干脆得很,“哲学反对帝国”,集中讨论伊拉克战争之后哲学应当如何应对帝国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等问题,实在大有意味。
W:“哲学反对帝国”?好!在当今这样一个强权即真理的时代,哲学确实不应当与帝国和平共处,否则无异于帝国之同谋。
Z:只是感觉他们似乎有点太迂腐了。帝国岂是哲学反对得了的?从根子上讲,帝国恐怕正是哲学的最高成就。以哲学反帝国,其结果完全可能是小骂大帮忙,或者干脆就是助纣为虐。
W:难道说西方哲学一路走下来,肯定要走进帝国状态?
Z:当然我们不必把一切罪恶都归咎于西方哲学。不过西方哲学中那种追求超越性、普遍性与形式化的理性主义传统与帝国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关联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否认。
激进哲学协会
W:此会是什么组织主办的,怎么矛头似乎直指白宫?
J:会议的主办者叫Radical Philosophy Association( RPA) ,“激进哲学协会”,这是一个对社会变迁进行哲学讨论的国际性非党派论坛。该协会脱胎于“美国哲学协会”中的激进哲学论坛,始创于1982年,是对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一统天下现象的一种反拨,试图把已经沦为分析技术的哲学恢复为对现实的批判。从事哲学研究而不批判现实,这在他们看来乃是哲学的耻辱。他们坚决反对哲学为当下非人的社会结构提供知识辩护。激进哲学协会大旗一树,立即有数支人马云集旗下,其中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和环境保护论,甚至还有现象学。
W:现象学居然也厕身其间,有意思,难道现象学本身包含着激进的政治含义?
J:这倒未必。一般地讲,现象学本身可保守可激进,但在美国这样一个分析哲学王国,现象学作为少数派难免受歧视,因而揭竿而起,倒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
W:那么,他们所谓的“激进哲学”究竟是什么意思?
J:“毫不留情地批判现存的一切”,这是他们最爱引用的马克思名言,也是他们对自身活动的定位。这种批判精神从过去几次会议主题也能略窥一二。1994年第一次全国会议之后,他们讨论的主题涉及一系列热点,诸如“从底层而来的全球化”、“21世纪激进哲学:向形成新政治文化及方向迈进”、“激进哲学与政治:开启一个新千年”、“行动主义,意识形态与激进哲学”等。这一次更干脆:“哲学反对帝国”,就在总统大选刚刚结束之后,就在首都华盛顿。
W:这不是存心要和小布什对着干吗?难道他们未卜先知,早在一年前确定会期会址时就预料到小布什会当选连任?
Z:这不大可能,即使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当选,他们仍然要讨论既定的主题。克里的当选并不会改变帝国强权之本质,能改变的只是表现形式而已。克里不是一再批评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干得不聪明吗?言下之意,他可以干得更聪明一些。
J:其实美国知识界中的绝大多数人,——多到99%,这是美国当代哲学大师罗蒂在上海说的,肯定有些夸张,但也不无根据,——不分左右,全都反对布什连任。
Z:布什太野蛮了。这种西部牛仔式的野蛮,在他们看来,并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更要命的是这种野蛮使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标榜的文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立马原形毕露,美国的软实力因此大打折扣。
J:但是美国的大资本与劳动阶层,尤其是美国南部诸州农民却不买知识界的账,非布什不选。去年感恩节时我曾在肯特基州一位牧师(其300多位教友全是当地山村农民)的家里当面问他投票给布什的理由,他脱口而答:Kerry is too liberal(克里太自由化了)。
W:大资本是因为贪婪与傲慢,劳动阶层则是因为短视与保守。
J:所以知识界很多人在大选后心情都非常难过。PBS一位著名女主持人更是难以自持,当众流下热泪,说是要移民加拿大。我刚到美国不久,伊利诺伊大学一位教授在课堂上与我就总统大选打赌,结果输给我5美元。这位老美在大选后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Life still goes on,anyway(不管怎么讲,生活还要继续)。其神情之沮丧,令人难忘。
基本理念
W: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有很多东西可谈,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讨论一次。现在还是回到“哲学反对帝国”这次会议上来。我想问的是,激进哲学协会的基本理念到底是什么?
J:激进哲学协会可谓两面作战,既反对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男权主义、同性恋憎恶( homophobia) 、环境污染、残疾人歧视以及一切其它形式的统治,又反对换汤不换药,防止有人以新式权威主义取代旧的统治形式。它的基本理念是要创建一个合作而非竞争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一切领域都由民主决策来治理。
Z:合作、非竞争、民主决策,这一切怎么听起来像是蒲鲁东。
J:哈哈。不过此鲁东非彼鲁东。至少它包含着当下西方人新的存在经验。
W:对他们的理念我们不必过多理会,对他们的活动我们却不得不关注。如果说帝国内部有什么他者,他们显然就是一个他者。这种他者或是叛逆或是同谋,需要格外小心。
Z:“哲学反对帝国”,这次会议的主题究竟何意?“哲学”不言而喻,“帝国”所指何谓?与前几年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一书有关吗?该书曾被人誉为“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
J:应当说没有直接关联。就我所知,在会上也无人提及此书。所谓“帝国”就是指当今之美国。激进哲学协会认为,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帝国时代,其标志是美国的帝国企图( imperial designs) 已经昭然若揭并且唾手可得。他们从几个方面来理解这一史无前例的帝国现象。首先,从经济上讲,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消耗大得惊人,比任何其它国家多得多,而它对外国市场的销售根本不足以覆盖这种消耗。美国在世界市场中的霸权位置,使它能够继续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展引擎”而起作用,美元也继续充当着主要的贮备货币。
其次,从政治和军事方面讲,军事平衡如此一边倒在世界史上比较罕见。“9·11”之后,美国居然声称,无论何时,无论针对何人,它都有道德权利发动所谓“先发制人”的战争。美国要么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世界组织,如世界货币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要么对它们不理不睬,假若它们有不同意见的话。它可以拒绝自己所反对的国际条约而不受任何惩罚,譬如有关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或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
最后,从文化上看,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其它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概莫能外。吃有麦当劳、肯德基,喝有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穿有牛仔裤、耐克衫,行有别克、福特,娱乐有好莱坞,解释世界事件有CNN,甚至自我认同也得以美国为标准。因此,激进哲学协会的结论是,美国像以前欧洲所有的帝国一样,已经按照一种不公平的种族契约( an unfair racial contract) 改组了整个世界,把少数人的利益建立在剥夺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在国际上如此,在国内也一样。
Z:确实,当今世界不按美国路子出牌,简直寸步难行。曹孟德当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美国现在可谓是挟“上帝”以令诸国。
J:作为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组织,激进哲学协会无意于像主流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界那样,或明或暗地为美利坚帝国提供道德证明。他们也不自欺欺人地相信,美国的霸权乃是权力政治这一非道德领域中最不坏的一种选择。他们对激进哲学家的界定特别明确:激进哲学家就是反对帝国的哲学家。
Z:有趣。看来,从哲学上无情地批判美利坚帝国现存的一切,这就是激进哲学协会的自我定位。
J:所以它致力于批判美利坚帝国的一切非人现状。种族主义、阶级剥削、男性统治、异性恋主义( heterosexism) 、正常主义( able-ism) (即残疾人歧视)和其它形式的统治,统统都在批判之列。另外,他们也关注现行全球秩序的生态意义,不仅要为当代人讲话,而且要为现在尚不能发言的未来子孙讲话。在激进哲学协会看来,一切剥夺、压迫与强制都必须批判。
Z:那么,他们如何看待革命,马克思所谓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他们主张革命吗?譬如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国的统治?
J:激进哲学协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会议与出版,尽管它也支持其它形式的解放斗争,譬如它号召人们反对美国政府对古巴的封锁,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往古巴开会;另外,它也号召人们反对死刑刑罚,但它从来不鼓吹暴力革命。激进哲学协会只是呼吁人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不主张以革命消灭现在的一切。它的目标是建构一种切实可行的秩序取代现行帝国,但此目标的实现不能通过革命。对激进哲学家而言,美利坚帝国对世界的统治固然可怕,但同样可怕的是以另一种形式的统治取而代之。必须消灭统治本身。这当然与整个20世纪苏联革命的兴衰给予他们的启示大有关联。他们害怕才出虎口,又陷狼窝。
W:在现行法律框架之下从事理论批判活动,这不是跪着造反吗?
Z:他们恐怕谈不上什么造反,只是帝国内部另一种声音而已。
J:他们不是要造反,他们只是要以理论批判的方式改变世界的现行秩序,以合作取代竞争,以民主取代专制。这与造反、革命相去甚远。谈到这里,有必要提醒一下,激进哲学协会只是一个供各方面左派人士发表自己观点的平台,其成员之间的政治观念可能相差很大,说到底,它并不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信仰的政治组织,尽管它于1996年在普度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会议上制订了一个章程。
追究Rawls的学术责任
W:现在来聊聊华盛顿会议,尤其是讲讲你自己在会上的所见所闻。
J:这次会议非常庞大,光是分组会就有60个之多。大部分是从学理上讨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非正当性,这其中对Rawls的正义理论以及《万民法》( The Law of Peoples) 多有非议。因为,虽然Rawls在《正义论》中为民主社会提供了一种较好的道德论证,但要命的是他并未把这种论证应用于国与国之间。在《万民法》中他建议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则的某些公理之上。但他设定了一个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道德等级制,却对这一等级制的道德恰当性不予置评。根据这一等级制,良好秩序的社会或自由的社会,比那些非法的社会或负担沉重的社会更令人向往。他认为一切民族都终将被商业和贸易吸引来遵守这些公理。在达到这样一种,用Rawls自己的话说,“实在的乌托邦”( a real utopia) 之前,良好秩序的自由社会必须管辖( police) 那些进步迟缓的社会。
Z:这不正是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之理论基础吗?消灭恐怖主义于国门之外只是保障美国国土安全的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替天行道,把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彰扬于全世界。目前布什的中东民主计划不正是以此为由吗?
J:确实如此。因此,会上有学者追究Rawls的学术责任,认为他难辞其咎。Rawls之所以让自由社会管辖世界,是因为他认为,在理论上自由社会不会自私自利,尽管在实践中自由社会难免苟且。但是他声称哲学家在这方面并不比外交政策实行者强多少。这就剥夺了哲学在此发言的权利。这一剥夺不仅使哲学对当代战争之正义性无法置喙,而且完全忽略了外交政策中的哲学维度。因此,哲学家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中所蕴含的哲学维度,按照Rawls的这番说辞,只能三缄其口。
W:这样一来,Rawls的确难逃为强权张目之批评了。如此批评Rawls,确实很有新意。那么,他们有没有什么正面主张?
J:有。“哲学地应对哲学所背书的政府暴力”,英语叫做Responding philosophically to philosophically endorsed government violence。哲学已经并且正在为政府暴行进行背书,这是哲学的耻辱。激进哲学必须从哲学上解构经过哲学合法性论证的政府暴力,还政府暴力以本来面目。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哲学家作为公共政策陈述者的记录令人难堪,正如布什二世的斯托劳斯式欺诈;要揭开此类现象之真面貌,Jonathan Glover 2001年出版的《人性》( Humanity) 一书可用。据说此书把20世纪政治暴力的基本理由驳得体无完肤:一切说辞只不过是要制造盲目的信仰与盲目的服从而已。在此书的基础上,人们能够把占领伊拉克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还原为资本家与其代理人之间的无耻勾结,一方资源饥渴,一方意识形态混乱。所以,有学者强调,单纯知道真理并不足以与非道德的军事主义抗衡,重要的是要与草根运动相结合。
Z:知易行难。知道真理距离实现真理相差何止千里。一部20世纪史就是一部真理之知与行的差距史。
巧遇美国老左Bertell Ollman
W:据说你在分组会上巧遇一位过去相识的老左派,他还赠给你一本近作?
J:是的。那是全美大名鼎鼎的Bertell Ollman,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2002年曾经到过我们学校,发表了一通有关中国现状的高论,我曾与他有过交流。这次他携新作《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 s Method) 来参加会议,有一个分组会专门评论此书,Ollman本人也到会作答。我对此公一向有兴趣,他若干年前就写过一本有关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书,叫做Alienation:Marx' s Concept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几十年来对马克思思想情有独钟,在美国学术界堪称是另类大师。他曾被Paul Sweezy,《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的编辑和“美国马克思学者”( America' s Marx scholars) 的主任,誉为“美国在辩证法和马克思方法方面的主要权威”。
Z:据说,《超越资本》一书的作者Michael Lebowitz对他的新作也颇有好评,认为是有关马克思辩证法最好的著作之一。
J:是的。此书其实是Ollman对自己有关马克思辩证法观点的一个总结。他围绕马克思内在关系哲学和马克思对抽象过程的使用这两个辩证法中很少为人研究的方面,重新组织了自己过去与现在的相关观点,把旧作中的相关部分亦收在其中,其目的是提供一种有关马克思方法的新视点,既具系统性、学术性,又具实用性。此书的重要性,用Ollman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仅澄清了马克思在不同理论发展时期中的真实思想,而且把马克思方法中的六大关键步骤一一道来,使读者能够把它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
Z:这很有意思。有机会一定要拜读一下此书。你当时到场了吗?
J:得知此公现身华盛顿会议,我焉有不到场之理?我感兴趣的除了这本书,更有他对当下中国形势的看法,因为这至少代表了美国左派对中国现状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我们作为中国学者不一定认同,但却不妨作为参考。因此,分组会一结束,我就上前与他打招呼,他很高兴,立马赠送给我一本《辩证法的舞蹈》,并且招呼在场的几位学者一起与我合影留念。
W:他对中国现状有什么高论?
J:我马上就要讲到这一点,因为后面大会上我还借他之名将了几位老美一军。
David Schweickert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J:大约是在11月5日下午,本次会议有一个集中的大会,专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的未来。大家就有关哲学在新型帝国时代的历史使命、人类可能的非资本主义前景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前途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在会上抛出的一个问题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三位发言人当场就在主席台上相互争论起来,弄得主持人最后只能在几次提醒无效之后,行使主持人的话筒权,强行中止了面红耳赤的争论,宣布会议结束。有趣的是,争论并未因此而平息,散会后大家又在台下“理论”起来。
W:你提了什么问题?
J:其实我所提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有意无意之中却触动了左派的软肋。刚才讲了,会议的专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的未来,三个发言人观点既相映成趣又针锋相对:一位发言人持极端悲观主义的态度,认为社会主义已经随着苏联东欧集团的崩溃解体而失去了任何可能的未来向度,换言之,苏东剧变乃是社会主义的墓志铭。
Z:社会主义已经盖棺定论,不可能咸鱼翻生了?
J:对。另一位则对少数现存的自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现状表示了深切的质疑,认为在所谓全球化的招牌掩护之下,资本主义至少已经渗入到这些国家的经济领域,而这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名存实亡。
W:这与第一位发言人的观点大同小异。
J:角度有所不同而已。第三位发言人最有意思。此公非等闲之辈,他是《反对资本主义》( Against Capitalism) 的作者David Schweickert,此书已有中译本,相识后他告诉我他还写了一本《资本主义之后》( After Capitalism) ,此书正在赶译中。这位老兄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对社会主义一往情深。
Z:有趣。社会主义在美国可是从来不入流,有人还专门写过一本什么书探讨为什么美国人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此人却逆流而上,有意思。
J:要知道他来自何处,芝加哥一所著名的神学大学,你会觉得更有意思。
Z: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本来就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嘛。
J:这当然不是Schweickert钟情社会主义的原因。在他眼里,美国社会非常无聊、异常枯燥,一切尽在资本的计算与操纵之中,早已丧失引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能力,资本主义已经穷尽了自己的可能性,只有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才能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W:那你到底提了一个什么问题?
J:我的问题很简单:即如何看待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以社会主义为立国之本的中国目前正在迅速市场化,加入WTO后在经济领域日益与国际资本接轨,在政治领域中国则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这一独特的“中国现象”应当如何理解?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在发言中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中国,似乎中国与社会主义无关。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我不得不将将他们的军。中国就是罗陀岛,就在这里跳吧。
Z:对,就让他们在中国大地上起舞。如果左派不敢正视现实,他们就永远不可能获得大地的力量。
J:我在提问时故意把Ollman 2002年在我们学校所作的断言——中国正走向资本主义——端了出来,因为当时此公就坐在我身边,拿来说事比较方便。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与台上的Schweickert是有名的思想对手,曾经出了一本好像叫《人类社会的未来——左派内部的争论》之类的论战集,两人在此书中有正面交锋。这是后来听Schweickert说的。我当时问三位发言人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如何评论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同意Ollman先生两年前所作的否定性断言。
W:你无意中把Ollman端出来,他们不要打架?
J: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俩尚未过招,三位发言人却在台上争论起来,看来“中国现象”确实很难消化。前两位的观点大同小异,即认为中国即使过去与社会主义有过瓜葛,而现在随着所谓的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的导入,也早已抛弃了什么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正在资本主义化,而且是正在坏资本主义化,这可以中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为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后果是大部分人的赤贫。
Z:Schweickert恐怕难以认同他们的观点吧?
J:不仅不认同,而且坚决反对。Schweickert坚决反对诸如此类的断言:什么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或正在资本主义化,或至少走在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恰恰相反,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在从事的一切才是人类希望之所在。社会主义并非只有或只能有苏东模式,并非只能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模式。正像资本主义有诸多形态一样,社会主义亦可有诸多形态。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恰恰是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我更新与发明创造,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整个世界陷入资本主义之际给人类保留了一线希望。
Z:看来,这位仁兄真是对资本主义绝望透顶了,一定要给人类找出一种新的生活可能性。那他对福山历史终结论肯定没有好感?
J:在他眼里,资本主义已经终结历史的福山式神喻只能说是右派的鼠目寸光与一厢情愿。他后来曾经盯着我的眼睛问我:资本主义可以经历诸多危机而起死回生,社会主义为何不能?资本主义凭什么剥夺社会主义试错的权利?此公对中国的热望令我感动不已。此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著恐怕会令不少口头马克思主义者汗颜。
W:他到过中国没有?
J:到过,到过两次。不过时间都很短,一次是在杭州,一次是在广州,都是参加学术会议,走马观花。在我回伊利诺伊大学之后,他给我发来了他的几篇论证社会主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最新文章。有一篇就是有关杭州会议的,另有一篇标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十条提纲”( Ten Theses on Marxism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里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观点。
W:什么观点?
J:其中一条提纲是说,我们现在能比马克思更清楚地发现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机制,至少是作为一个理想类型,这就是他所谓的“经济民主”。它将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企业由工人自治,投资由社会控制。还有一条提纲断言,向“经济民主”的过渡,无论是从资本主义过渡还是从现行社会主义过渡,都将是一个和平的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过去了,但社会主义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意思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结反而为他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敞开了道路。
W: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J: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最后的结论。他指出,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世纪则也许是中国的世纪。但是并非出于相同的原因,即中国不可能因为变成另一个比美国更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独步于21世纪。在他看来,如果中国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方面的大胆实践得以成功的话,那么21世纪将属于中国。但他又说,尽管这样一种未来是可能的,但却不一定必然到来,一种完全不同的未来也是可以想象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可能沦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认为,这样一种发展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悲剧,对人类来说也将是一个悲剧。
Z:中国当下实践之成败关乎人类未来之福祉,这听起来还是挺过瘾的。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聊聊他的观点,看看他如何立论。
中西思想交通问题
W:好。不妨把有关他的话题留给下次对话。不过,在结束这次对话之前,我们是不是听听你在会上会下的内心感受与感想。我觉得这也是挺难得的。
J:总的一个感觉是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人自己来思考。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西方形而上学的困境只有靠西方人自己来破。西方人,无论是对中国友好还是不友好,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始终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所操持的西方理论框架与中国人当下真切的生活经验之间有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们跨不过来,我们目前也跨不过去,因为我们也是在依照西方概念来解读自己的生活。这一点只要看看我们现在满口操持的词汇就一目了然了。可以看看有哪些词是舶来品,又有哪些词是祖传秘方;还可以看看在哪些祖传秘方中,又有哪些词已经完全或部分为舶来思想所化,成为“殖民文字”了。
W:其实,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经验也早已在某种程度上被“殖民”化了,因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侵蚀,西方概念已经成为中国经验的一大部分,甚至可以说,西方概念已经成为中国经验的主要部分。
Z:但是中国人毕竟尚未完全“西化”,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因此中国经验中仍然包含着许多中国文化传统。因此,每一次的西式解读其实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扭曲着中国经验,使之滑向不可言说的深渊,结果是集体失语。当下中国诸多危机与此不无关联。
W:怎么填平这条鸿沟,这恐怕是中国学界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否则我中华民族就不足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Z:自己的生存经验都说不清楚,自立就无从谈起了。中西思想交通问题是中国近代以来的“西化”运动的一个副产品,现在所谓“与国际接轨”更使这个问题空前突出。
J:中国人“西化”久矣,但中国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中国人。这一点是既令人沮丧又令人高兴的。当然,此中国人与彼中国人,譬如与1840年之前的大清子民,相去甚远了。时下之潮流是“与国际接轨”,这无可厚非,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一直在试图与国际接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学术、甚至纪元,方方面面一直如此。只是“国际”一词之所指时有不同而已:或指美欧,或指苏东;或指市场经济,或指命令经济。
Z:问题在于中国人有着自己悠久的文明传统。在与国际接轨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传统,甚至发扬光大自己的传统,这就成为一个纯粹中国性的问题。倘若中国是一蕞尔小国,习惯于仰其它文明之鼻息而存活,那倒也罢了,改换门庭即可。恰恰相反,中国人有着自己光辉的文明传统,垂数千年而不倒,环顾四海,令人自豪。
J:但是,这种自豪因为屡遭打击在1840年之后已经逐渐转化为一种“文化焦虑”,其核心情结在于如何迅速重振中华雄风。我们目前仍然生活在这种文化焦虑之中。这种焦虑不是单纯的经济成就或综合国力的提高就可以根除的。经济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优越。中华文明不兴,此焦虑难除。换言之,倘若不能在世界文明结构中做出与中华文化相称的独特贡献,中国人就不可能活得心安理得。这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使命感,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
Z:5000年养就的文化使命感,对应着一个半世纪的文化焦虑,这就是我们当下之历史境遇。
W:其实,这种文化焦虑之根基正是那根深蒂固的文化使命感。
J:所以,与国际接轨,不是要把自己从文化上连根拔起。在我们“接轨意识”日益明晰之今日,恰恰有必要强调文化自觉:“谁”与国际接轨,接轨之后成为“什么”?但愿我们中国人不要如此天真,以为接轨纯属技术性事务,不涉及文明冲突之大问题。
Z:我们现在的困境是:一方面不得不继续“西化”,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不得不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防止文明中断。
J:并不是说只要生理性的中国人还活着,中国文化之传统就永远不倒。倘若缺乏足够的文化自觉与实践,也许再过一、二个世纪,文化上的中国人就得到博物馆去找了,就像我们这次在美国各大博物馆中凭吊印第安文化一样。
W:不妙的是,当代中国人在现代性的裹胁之下,正在加快自己的现代化步伐,大干快上,根本来不及对当下所发生的一切进行反思,更不用说批判地评价了。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对中国经验与西方概念关系的思考,都有遭受“冬烘”之讥的危险。
Z:这不足为虑。思想家从来都是这样的命运。我们的任务是想清楚问题,并把问题呈现出来。
“容西易中”
J:我的几点基本想法是:第一,对中国当下生活经验的解读离不开西方范畴概念,因为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闭关锁国之中国。第二,纯粹西方概念不足以恰当地解读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经验,因为中国人毕竟还是中国人,其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还是与西方概念有着相当大的隔阂。第三,要填平这条鸿沟,必须对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有更加深切的体会。
W:那你如何理解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
J:我用“容”、“易”二字来形容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海纳百川之谓“容”,变通去执之谓“易”。因为能“容”,所以不断壮大;因为能“易”,所以生生不息。无庸讳言,中国人必须继续向西方学习,这既是生存之道,更是自我更新之契机。但在此学习过程中,中国人切切不可丧失自身的文化自觉与实践。未来的中国文化要想为世界文明新结构做出公认的贡献,就必须熔中西于一炉,铸造出属于自己因而属于全人类的新文化形态。这就要求当代中国人超越中西经验概念之樊篱,以实求名,而不是循名责实。
W:问题是如何超越?
J:关键是要在“容”、“易”二字上下功夫。有容乃大,变易而通,这样就既不会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又不会数典忘祖、自断命脉。当然这不是仅仅停留于纸上谈兵就可以做到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创造性实践。这种实践,从一个视角看,可以称之为“容西易中”,容纳西方新学,变易中国旧统。
W:“容西易中”,有意思。这与全盘西化有何区别?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又有何区别?
J:全盘西化是要挥刀自宫以便委身于人,“容西易中”则是以变求通而自我更新。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虽然貌似不同,却分享着相同的基本逻辑:即体用之分,或中学为体,或西学为体,而“容西易中”却要化解所谓体用之别。当代中国人没有必要纠缠于旧式的体用之争,关键在于能否创造出一种能够解读中国人当下生存经验的新思想、新概念。
W:但你这里还是有一个主体,即当代中国人。
J:这是自然,这个主体至少目前还化解不掉。谁叫我们现在所处之时代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化掉当代中国人这个主体,那是极其危险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性或有限性。老黑格尔有言:无人能够超越自己的时代,正像无人能拔着自己的头发而离开地球一样。我们不可能像上帝那样,无所不在。“容西易中”,说到底只是当代中国人面对现代性的威胁所做出的一种回应而已。换言之,“容西易中”虽然有意于破体用之别,却无意于去破中西之别。中西之别乃是当代中国人遭遇的先天性生存境地,不是想破就破的。当然,如果说有一天世界大同,暂且不论其是否可能,中西之别恐怕也要破。但这就不在我们的书中交待了。每一代人只能完成时代交待给他们的任务。
Z:容而易之,易而容之。看来,中国经验与西方概念之间要真正做到“容”、“易”二字并不容易。时间关系,今天就聊到这里,其它问题不妨留作下回分解。
标签:哲学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华盛顿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企业年会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