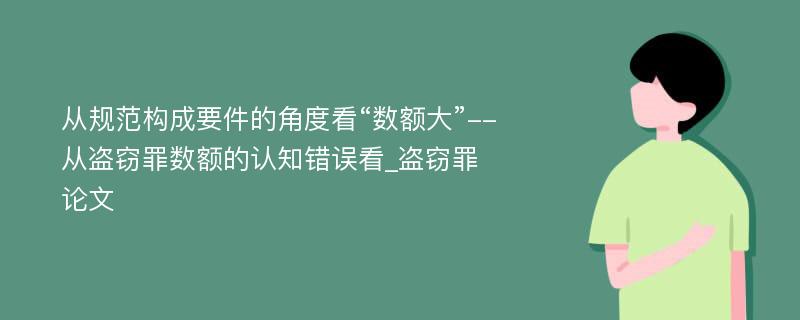
规范构成要件要素视野下的“数额较大”——以盗窃罪数额的认识错误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数额论文,盗窃罪论文,视角论文,要素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11)09-0043-08
实践中,人们的认识与刑法分则所设定的量化指标(如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并不完全一致,如何处理值得研究。正如储槐植教授所指出的,“我国刑事立法中,犯罪概念既定性又定量。它是我国传统治国经验‘法不责众’的现代模板,实际起着对刑法‘谦抑原则’的制度保障作用。但20年来的社会实践表明,刑事领域一些难解的重大问题均与犯罪概念定量因素密切相关”。① 由于各种原因,人们的认识能力各不相同,人们的主观认识与物品的实际价值之间存在不一致在所难免。笔者将以如下两个典型案例为研究视角。
案例一:天价葡萄案。② 2003年8月7日凌晨,北京海淀警方巡逻至香山门头村幼儿园门前时,发现4名男子抬着一个可疑的编织袋。盘查后,警方发现4名男子的编织袋中放着偷来的47斤葡萄。这些葡萄是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四人的馋嘴之举令其中的20余株试验链中断,损失巨大。北京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偷的葡萄进行估价,被偷葡萄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1220元。2004年4月,争议已久的估价问题经过检察院两次退补侦查后,“天价葡萄”最终按照葡萄的市场价格估算,经过北京市物价局认定,几个农民工偷吃的葡萄价值为376元。
案例二:卖淫女偷嫖客手表案。③ 2002年12月2日,被告人沈某某在某市某酒店与潘某某进行完卖淫活动准备离开时,乘潘不备,顺手将潘放在床头柜上的嫖资及一只“伯爵牌”18K黄金石圈满天星G2连带男装手表拿走,后藏匿于其租住的某市某区荷城甘泉街90号二楼的灶台内。事后潘某询问沈是否拿了他的手表,并对沈称:该表不值什么钱,但对自己的意义很大,如果沈退还,自己愿意送2000元给沈。在讯问中,沈某某一直不能准确说出所盗手表的牌号、型号等具体特征,并认为该表价值只有六七百元;拿走潘的手表是因为性交易中潘某行为粗暴,自己为了发泄不满。经某市某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手表价值人民币123879.84元。
一、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
(一)关于是否需要主观上认识到“数额较大”的理论之争
关于盗窃罪所要求的“数额较大”如何理解,是否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财物的价值达到“数额较大”,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第一是认识不必要说。这种观点认为,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客观处罚要件,只要求客观上达到了这一程度即可,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财物的价值是“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盗窃案件,由于行为人持概括的故意,因此,盗窃数额以被盗物品的实际数额计算,而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准确认识到财物的具体数额。刑法理论上亦有不少学者支持此观点。陈兴良教授指出,应将犯罪的数量因素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罪量要件。罪量要素之所以不能归入客观要件,除了因为在罪量要素中不单包括客观性要素而且还包括主观性要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客观要件是行为人认识的对象,因而对于判断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将罪量要素当作是客观要件,行为人对此没有认识就不能成立犯罪故意而属于犯罪过失,由此会对罪过形式的判断造成混乱。④ 而将数量作为独立的罪量要素,则只需客观达到,不需主观认识,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认识不必要说。
第二是认识必要说。这种观点认为,“数额较大”属于行为人主观故意的认识内容之内,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认识到,则应阻却故意的成立。如周光权教授指出:“行为人主观上并不知道盗窃的对象是科研实验品,因而对其包含的巨大价值并不明知,况且所盗葡萄、豆角价值也只能按当时当地的市场零售价的中等价格计算,而不能按投入的成本计算,因而不构成盗窃罪。”⑤ 还有学者认为,如“根据犯罪构成必须是主客观相一致的原理,当盗窃数额较大是盗窃罪客观方面不可缺少的要件时,行为人在主观方面也必须预见到要窃取的财物达到了数额较大,这样才能主客观相统一”。⑥
(二)犯罪故意的认识内容与“数额较大”
刑法理论上多数观点认为,对于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认识到,但问题是,对于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认识应达到何种程度,是否应对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全部内容都有所认识,如盗窃罪中,是否应对被盗财物的价值“数额较大”有所认识。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成立犯罪故意,必须认识、预见到关于该种犯罪构成的客观特征的一切情况。⑦ 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张明楷教授就此提出了“客观的超过要素”的概念,即认为存在不需要行为人认识到的犯罪客观方面,并以盗窃罪中的“多次盗窃”为例,认为盗窃罪客观方面的“多次”就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⑧ 首先,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适例,盗窃罪中的“多次”并不是具体盗窃犯罪的客观方面本身,它是立法者对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在次数上的法律评价,立法者的法律评价并不需要行为人认识到。行为人实施多次盗窃,实践中的处理是盗窃数额累计计算,而每一次盗窃数额仍然是要求行为人认识到的,“多次盗窃”这一客观要素之所以无须行为人主观认识,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客观要素并不是对行为(包括结果)的量定,而是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表征。⑨ 其次,尽管我国有部分学者赞成客观的超过要素说,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持反对态度。储槐植教授针对张明楷教授所提出的客观的超过要素提出了三点质疑:其一,论者一方面强调“客观的超过要素”不同于德日等国的“客观处罚条件”,但另一方面却又未能划清两者的界限;其二,论者要求行为人对“客观的超过要素”具有“预见可能性”,这种“预见可能性”实质上是属于“犯罪心态”中的认识因素;其三,“客观的超过要素”是否会导致“客观归罪”不无疑问。⑩ 再次,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各行为本身的所有客观方面,从责任主义的角度看,都应认识到或者有认识的可能性,至于立法者对客观行为再进行的评价如“多次”等,则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责任主义的实际机能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归责中的责任主义,即只有当行为人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具有主观责任时,其行为才能成立犯罪;其二是量刑中的责任主义,即刑罚的程度必须控制在责任的范围内,或者说,刑罚的程度不能超出责任的上限。(11)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此,责任主义应当贯彻得更为彻底。最后,即便是认为德日刑法学承认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有认识的客观的超过要素这一概念,但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要件,二者是同一意义上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即成立犯罪。而在德日刑法中是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行为必须符合构成要件、违法、有责,才能被认定为是犯罪,因此,即便在构成要件中主观上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数额较大”,也可以在违法性、有责性中要求认识到客观的超过要素。
不管是从实务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来看,故意的认识范畴都应涵括犯罪构成的所有客观方面,那么自然地,盗窃罪中的数额要素也应该被认识,即笔者赞成“认识必要说”,如果没有认识所盗物品的数额价值,可以阻却犯罪。
二、犯罪故意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
对于“数额较大”这一要素应达到何种认识程度,行为人是否认识到的评判标准是什么,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犯罪故意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之间的关系。
(一)记述(描述)的构成要件要素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概说
1.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
立法者以日常用语对客观事实作出一定的记述时,法官对于要素的对应物(客观事实)只需要进行事实判断的活动即可确定的要素,是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12) 对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虽有解释的必要,但在解释上基本不存在大的争议,在认定事实是否符合构成要件时,不需要法官的个人评价。如故意杀人罪中的“人”、拐卖妇女罪中的“妇女”等。对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只要行为人认识了要素本身,就能够理解其行为的意义,以故意杀人罪为例,行为人只要看见了“人”,并且朝着“人”开枪,就应该知道其行为会造成他人生命被侵害的危害结果,行为人就知道其行为性质。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中,法条所描述的事实,就是侵害法益的事实,不需要使用价值评价的概念。法官的判断重点是事实是否符合构成要件,而不是借助于其他规范评价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是否侵害法益。(13)
2.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及其种类
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是需要填充的构成要件要素,即法官仅仅根据刑法条文的表述还不能确定,只有进一步就具体的事实关系进行判断与评价才能确定的要素。这种判断与评价既可能是基于其他相应的法律法规、法官的自由裁量等法律因素,也可能需要基于道德、礼仪、交易习惯等法以外的规范。(14) 构成要件中的规范要素中不但要有确定的事实,而且以规范评价为必要部分。这种规范评价包括:法律评价,如“他人财物”;认识评价,如“虚假文书”;社会、文化评价,如“猥亵行为”、“侮辱”;伦理、道义评价,如“故意的”、“不法的”。(15) 关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分类,存在不同的观点。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法律的评价要素,即必须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出评价的要素,如《刑法》第277条中的“依法”,第425条中的“滥伐”,许多条文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二是经验法则的评价要素,即需要根据经验法则作出评价的要素,如《刑法》第114条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第116条中的“危险”等;三是社会的评价要素,如《刑法》中的“住宅”、“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淫秽物品”等。(16)
刑法中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等,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中的社会的评价性要素,它们是对危害行为或危害结果的评价和要求,不具有像危害行为、危害结果一样的实体性特征,但评价要素和事实要素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往往缺一不可。缺少了犯罪数额,危害行为、危害结果等事实要素就失去了规范意义。(17) 具体到盗窃罪,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中的社会的评价要素。不同人的认识可能不完全一致。“量的评价要素只是社会的评价要素的一部分,因为量的评价要素(如是否属于‘公然’、‘微薄的价值’等)也需要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评价”。(18) 行为人在盗窃罪中,既要认识财物本身的事实存在,也要认识财物的价值,两者同时存在,才能构成盗窃罪。
(二)对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程度
在故意犯罪中,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并不只是对外部行为的物理性质的认识,而是对行为的社会意义的认识。只有对行为的社会意义具有认识,才能说明行为人具有非难可能性。(19) 认识就意味着在感官上感觉到了描述性的构成行为情节,在思想上理解了规范的构成行为情节。在大多数构成行为情节中,两种认识的形式都是必要的,必须同时在感官上觉察其描述性的因素和在思想上理解其规范性的内容。例如,在销毁证件罪(《刑法》第274条第1款第1项)的故意中,就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行为人必须的确知道,自己是如何把一份书面文件连同旧报纸一起丢到火炉里去的;他还必须已经理解,这份书面文件不属于他所有,并且清楚,这份文件本来是应当在法律事务中作为证据的。只有在两者都具备时,才能形成故意。(20)
在描述性特征(即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中,这个公式是比较容易运用的。对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也仍然存在价值判断的成分,只是一般人的判断通常不会发生争议而已。行为人只要对客观事实有认识,通常就能理解行为的性质与意义。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要求主体认识到规范的含义,但不要求认识到精准的法律概念。对法律上是常人的行为人,不能要求具有与裁判官一样的严密的法的认识,通常只要明白了一般人所理解程度的社会意义就够了。(21) 例如,故意毁坏财物案件中,行为人将他人的戒指扔入大海,不要求其认识到其行为是法律专业术语的“毁坏”,只要求他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被害人无法再使用戒指即可。一般而言,行为人是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其行为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不存在疑问。即使行为人认为其行为不属于“毁坏”,这也属于对法律概念、术语的理解错误,这种错误为法律认识错误,不影响对其行为的定性。如果要求行为人认识刑法上的规范概念,则会不当缩小刑法的处罚范围,而且导致处罚的不公平。前田雅英教授指出:“作为刑法问题的‘非难’要素是以国民的一般规范意识为基础的,具有这样的认识就足够了。”(22) 行为人为了故意行为,必须“想象这个行为构成的意义”。(23)
(三)对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是否认识的评判标准
对于相当一部分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行为人认识到客观事实本身通常就能理解规范的含义。但对于需要经过社会法则判断的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人们的理解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对于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中的“淫秽物品”,不同主体的认识标准可能并不相同。但如果完全听任行为人对该问题的理解,将会导致行为人避重就轻,比如否认自己认识到物品的“淫秽性”。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判断,一般交由司法人员进行判断。“对于需要社会道德、文化以及社会经验认知评价的规范构成要件要素来说,法官诠释的标准与方法至关重要”。(24) 但如果完全听任法官的自由裁量,容易导致法官任意司法。“不应当存在完全由法官基于主观的裁量进行评价的构成要件要素,否则会导致法官的恣意判断”。(25) 再者,对于物品的规范意义,不同的法官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完全一致的,如果听任法官的判断,案件的处理就很可能缺乏确定性。法官对规范构成要件进行自由裁量的必要限制是,“即使某种价值判断介入到司法决定当中,那么它也并非作为法官的个人偏好而介入的。重要的是,支持这一结论的理由使得并且能够成为该法官所处的法律共同体当做合法的前提予以接受,或者说,这种价值判断对于其所适用的共同体具有某种意义”。(26)
判断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了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含义,应采取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评价标准。德国学者麦茨格尔在宾丁之后发展和完善的“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一直得到普遍承认和适用,即只要行为人所属的一般人能认识到规范的含义,就推定行为人能够认识其行为的规范含义。
三、对数额认识错误的处理
如前所述,“数额较大”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那么行为人在盗窃时对财物价值“数额较大”这一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错误如何处理呢?认识错误分为事实认识错误与法律认识错误,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错误当属事实认识错误,应按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来处理此问题。因为这种认识错误之下,行为人并非对其所实施的行为在法律上的定性产生错误认识,故不属于法律认识错误。这种认识错误是对所盗物品本身的价值产生了错误认识,物品的价值本身这一客观事实是犯罪对象本身的属性。正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盗窃罪的对象财物的认识错误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中的对象认识错误。关于对象错误,主流的观点是采取法定符合说,即只要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刑法的规定相符合就可以。就盗窃罪而言,刑法第264条就财物的价值区分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个量刑幅度,因此,行为人的认识只要与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相一致就可以肯定其认识与法律的规定一致,即使在更具体的数额上,行为人的认识与实际数额不一致,也不阻却行为人犯罪的故意性。笔者拟从如下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数额较大的认定
如何判定行为人对其盗窃的财物的价值是否数额较大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完全以行为人本人的认识为标准,根据“外行人平行评价标准”,应以一般人所认识到的标准为标准。只要其所属的领域的一般人能够认识到,原则上就推定其认识到财物的价值,除非其能提出相反的证明。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了财物数额较大,应结合行为人的生活阅历、文化背景,综合案件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确定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了其所盗窃的财物为数额较大,可以采取法律推定。我们原则上可以假定行为人是社会上的一般人,只要一般人能认识到的东西,行为人在一般情况下都可能认识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行为人是否明知所盗财物数额较大,除了根据证据能判断外,需要根据事实进行推定……一般来说,只要行为人并非盗窃明知是价值微薄的财物,根据行为的时间、地点、对象等因素,就可以推定行为人明知是数额较大的财物,而不致放纵盗窃犯罪”。(27) 如果行为人确实没有认识到财物价值达到“数额较大”,当然不能认为行为人有盗窃罪的故意,不能成立犯罪。但是只要行为人对财物数额的认识在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的幅度范围内,则不能阻却盗窃罪的成立,而不要求行为人精确地认识到所盗窃财物的数额。“因为要知道财物的准确数额,在有些情况下往往难以做到,有时专业人员经过反复审视、研究后还会认识不一,更何况有些盗窃对象在盗前还处于隐蔽状态,要求行为人知道其准确价值既有违情理,也不切实际”。(28) 对于其他类型的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如“淫秽物品”也是如此。(29)
案例1中的天价葡萄,普通农民工就其生活阅历、知识背景而言,不可能认识到所偷吃的葡萄价值数额较大,因此,其行为不宜以犯罪论处。但在以下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定罪:行为人在特定科研试验场所从事劳动,例如帮助进行试验或者从事该场所的劳务;曾经听人提起某科研场所试验品种的特殊性;某科研试验场所从外观上看,与一般的植物栽培场所有非常明显不同的外观或者警示标志等。(30) 但对于案例2,从案情的表述看,行为人不可能认识到手表的价值数额特别巨大。本案的判决书也指出:判断行为人是否对所盗物品价值存在重大认识错误,主要应从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及其行为前后的表现来综合分析。本案被告人沈某某出生于贫困山区,从没有见过此类手表,也不知道或者听说过有此类名贵手表;沈某某年龄不大,从偏远农村来到城市时间不长,其工作环境又是一普通发廊,接触外界人、事、物相当有限,基本上无从接触到戴有如此昂贵手表的人;案发地附近的市场上也没有此类名表出售,即使最好的商场内出售的最好的手表也不过千元左右。因此,以本案沈某某的出身、作案时的年龄、职业、见识、阅历等状况来看,其对所盗手表的实际价值没有明确的或概括的认识是有可信基础的。被害人将价值如此巨大的手表与几百元的嫖资随便放在一起,也有使对手表本来就缺乏认识的沈某某产生该表价值一般(而非巨大)的错误认识的客观条件。(31) 但她应该有可能认识到手表的价值“数额较大”,这也是行为人能够被定盗窃罪(但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原因。
(二)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之间的认识错误
我国刑法分则对许多犯罪行为采取了定量并且分阶段的模式,即对于具体犯罪不仅规定了犯罪既遂的标准,而且在犯罪既遂的标准之基础上,又根据社会危害性的不同,区分了不同的程度并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32) 对盗窃罪,根据其价值区分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这种数额上的区分,是对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及客观行为作用的对象提出了更精确化的处理。行为人盗窃他人财物,即使对所盗财物的数额有不正确的认识,但只要这种主客观的差别没有超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者“数额特别巨大”自身的幅度范围,就应当认定为主客观相符合,这里存在的错误就不具有刑法意义,对故意的成立不产生影响。(33) 但问题是,行为人认识到了其所盗窃财物的价值可能达到“数额较大”,但实际上财物的价值“数额特别巨大”(笔者称之为“低估”财物价值);抑或行为人认识到财物的价值有可能达到“数额特别巨大”,但被盗财物的价值仅是“数额较大”(笔者称之为“高估”财物价值)时,如何定罪与量刑,值得研究。
在低估财物价值的情形下,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只认识到了财物的价值“数额较大”,从责任主义的视角看,即使客观上财物的数额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也不能适用“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而只能适用“数额较大”的法定刑。当然,对于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给被害人造成了“数额特别巨大”的损失,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在高估财物价值的情形下,行为人主观上欲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认为被盗财物的价值“数额特别巨大”,但实际上被盗财物的价值仅是“数额较大”。对于这种高估物品价值的情形,主观上虽然有犯重罪的故意,但由于其行为针对的对象是轻罪的财物,即只有侵害“数额较大”财物的危险性,从客观主义的立场上看,只能成立轻罪,即盗窃罪的“数额较大”。但如果在此种高估财物价值的案件中,行为人客观上所针对的财物本身是具有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可能性,应认为是“数额特别巨大”的未遂。例如,行为人欲去某单位的财务处盗窃几十万元的款项,通常情形下该单位的财务处也有如此巨额款项,但行为人当天去盗窃时,巨额款项已于当天白天转至银行,行为人只得到了几千元。如果仅仅适用“数额较大”的法定刑,那么,行为人主观上超出数额较大的故意(行为人主观上是有盗窃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的故意)、客观上的行为有侵犯超出数额巨大的财物的危险性(行为人的该行为通常情形下有可能造成被害单位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被盗的可能性)将无法在量刑上得到体现。这种情形下应当适用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这一幅度的法定刑,但同时考虑到行为人实际所获取的财产只有“数额较大”,应认定为是“数额特别巨大”的未遂。或许有人会认为,既然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盗窃数额已经达到了“数额较大”,就不应认为是犯罪未遂。在这里笔者提倡犯罪既遂标准的层次性,即盗窃罪犯罪既遂的标准有“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个层次。其理由在于:犯罪既遂从客观存在到这一概念的专门提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在适用刑罚上与未完成形态的犯罪相区别,即根据犯罪进展程度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刑罚,以期更好地实现罪刑相适应。(34) 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但犯罪构成要件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内容,其是由具体的构成要件要素组成的,犯罪构成要件的齐备也就意味着构成要件要素的齐备。而我国刑法对于具体犯罪作了层次性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对构成要件要素作了具体的划分。例如,盗窃罪中的财产损失是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但刑法对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作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区分,既然构成要件的要素都作了层次性的划分,要贯彻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对于这些被立法作了层次性划分的犯罪而言,其犯罪既遂的标准当然基于层次性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标准。刑法分则对具体犯罪规定了完整的刑罚,只有达到犯罪既遂才能适用该完整化的刑罚,而没有达到该既遂状态,则应该结合刑法总则关于未完成形态犯罪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罚,这是犯罪既遂、未遂区分的最终目的,也是实现主客观相统一、罪刑相适应的必然要求。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刑法分则对于具体犯罪所规定的刑罚均是针对犯罪既遂这一完成形态的犯罪而言的。对于绝大多数犯罪,刑法针对该犯罪罪质的不同层次规定了两个以上的罪刑单位。每一个罪刑单位包含着一个相应的犯罪构成。处在第一个层次的罪刑单位所包含的犯罪构成是普通的犯罪构成,而处在第二个层次或更高层次的罪刑单位所包含的犯罪构成则属于派生的犯罪构成。派生的犯罪构成包括加重的犯罪构成和减轻的犯罪构成。(35) 因为刑法已经对派生罪的各个层次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刑罚,为了正确贯彻犯罪既遂、未遂在刑罚适用上的差异,就应当将犯罪既遂、未遂在刑罚适用上的区分贯彻到派生罪的各个层次之中。
注释:
①⑩ 储槐植、汪永乐:《再论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刘卉:《天价太空豆角案考问刑法基本理论》,《检察日报》2004年7月11日,理论版。
③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参考》(1999-2008),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④ 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立足于中国刑法的探讨》,《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号。
⑤(30) 周光权:《偷窃“天价”科研试验品行为的定性》,《法学》2004年第9期。
⑥ 董玉庭:《盗窃罪主观构成要件微探》,《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⑦ 赵秉志:《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239页。
⑧ 张明楷:《“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之提倡》,《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⑨ 王强、胡娜:《论主观罪过中的定量因素认识》,《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4期。
(11)(27) 张明楷:《论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法学》2004年第11期。
(12)(13)(16)(18)(19)(25) 张明楷:《犯罪构成体系与构成要件要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第191页,第197-198页,第195页,第213页,第195页。
(14) Mezger,Strafercht Allgenmeiner Teil,Ein Studienbuch,5.Aufl.,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1954,S.89.
(15) [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17)(33) 杨志国:《数额认识错误初论》,《时代法学》2007年第4期。
(20) [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21) [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22) [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23) Puppe GA 1990,153; dies.,NK,§ 16,Rn.51ff.
(24) 王昭振:《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司法诠释的标准与方法》,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3页。
(26) 焦宝乾:《法的发现与证立》,《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28) 朱孝清:《盗窃科研葡萄、豆角案定性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1期。
(29) 陈洪兵、麻侃:《由“淫秽性”谈规范构成要件要素认定的实体及程序路径》,《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D05年第4期。
(31)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参考》(1999-2008),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32) 徐光华:《犯罪既遂、未遂与我国刑法分则之规定》,《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34) 徐光华:《犯罪既遂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8页。
(35) 王志祥:《数额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法律科学》2007年第4期。
标签:盗窃罪论文; 法律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构成要件要素论文; 犯罪构成要件论文; 犯罪既遂论文; 犯罪主观方面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盗窃未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