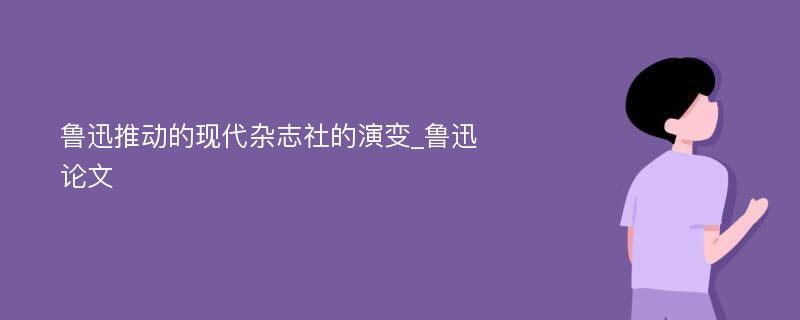
鲁迅推动下的现代杂志演进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历程论文,杂志论文,推动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2)03-0008-04
五四之后,中国的杂志出版逐渐向自由发行的方向萌芽,各种类型的新生杂志、报刊 的出现成为社会的一大盛景。胡适在1922年的估计是:五四以后,中国约有400种白话 文新刊出现。尤其是由进步知识分子群所共同策划、创办的期刊,则带有更为明显的思 想革新、批判和反抗的意味,这些期刊本身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鲁迅作为跨时代新文化主将,一生主编和参与编辑工作的报刊杂志约有20余种,他以 自己的亲和力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期刊发展的高潮,并承担了诸多工作,这一场文 化盛景的起落沉浮与他的生命历程息息关联。本文重点关注鲁迅作为杂志人的工作历程 以及在此中彰显的杂志出版理念。
始于《新生》的杂志创办理念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时常为《浙江潮》、《河南》杂志写作,并积极筹办《新 生》杂志,此后一生中他所从事的杂文写作、美术推广、国外优秀文学的翻译工作无不 始于《新生》的办刊理念。
许寿棠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 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 病根何在?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就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 事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 也求于逐渐解决或有所贡献。因此办杂志、译小说,主旨在此中。”“鲁迅的文艺运动 的计划是在于发刊杂志,这杂志的名称在从中国回东京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 名作《新生》……这本是同人杂志。”[1]P814“《新生》虽然没有办成,可是书面的 图案以及插画等等,记得是统统预备好了,一事不苛的;连它的西方译名,也不肯随俗 用现代外国语,而必须用拉丁文,曰:Vita Nuova。”[2]
《新生》经历了种种磨难,终于未能出世,他为筹办《新生》所收集的材料,演化成 其后的《摩罗诗力说》以及《域外小说集》。“《新生》的运动是孤立的,但是脉搏却 是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那时同盟会刊行……《民报》,……可是它只重政治和 学术,顾不到文艺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来负担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新 生》的介绍翻译方向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收集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 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1]P 829-830
《新生》虽然没有诞生,却是鲁迅杂志理念最具雏形的一次体现,同人意识、刊物主 旨以及刊物的美化、设计方面都被他在实际运作中加以特别强调,自我个性的张扬与推 介国外先进的文艺创作的热诚支持着他在思想荒原上前行。
5年后,《越铎日报》出世,身为名誉总编辑的鲁迅在其创刊号上激情洋溢地写道:“ 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 之精神”。虽然这仅仅是越社青年自办的一张地方性小报,但鲁迅寄予它以进步出版刊 物的信心和愿望:应具有开启社会精神革新的勇力、充当拥有社会监督人的权力,更应 是民众自由声音的讲坛。但现实的拒绝和实际工作的失利,终于使鲁迅意识到在当时的 中国,报纸和杂志实在是并无多大自由可言的,或者被同化,或者被剿灭。“但希望, 却是不能抹杀的”(《呐喊》自序)。从失败和痛苦中生长起来的忧患意识,逐渐转化为 《新青年》之中的现实主义。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呐喊·自序》)。 他努力使自己的创作符合整体的风格,“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 显出若干亮色。”(《自选集·自序》)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创作与办刊相协并进的文化革 新和思想革新的开创之路,也为同时代的诸多革命性刊物和社团文艺刊物的创办贡献了 自己的无限心力。
从《语丝》的自由文体到《莽原》的血与火焰
鲁迅从1918年加入《新青年》工作之中,经常应陈独秀的邀请去参加“商量怎样进行 《新青年》的集会”(《<守常全集>题记》)。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是新文学史的纪元,而《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一 系列的随感录,“具有缜密和雄辩的逻辑力量与高超的艺术水平,为五四后报刊上文艺 杂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
《新青年》仅是鲁迅的试刀之作,他并无很多实质性工作。当《新青年》的旗帜渐渐 黯淡下去时,“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新青年》的分裂已是迫在眼前。 针对胡适力主“不谈政治,专心于学术文艺”的办刊思想,鲁迅大力反对,“《新青年 》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所以任由它分裂”也不妨是件好事 [4]。如果失去了统一的杂志编辑思路,还不如由其分裂。鲁迅也并未如愿将自己的办 刊理想实现于《新青年》中,只“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里走来走去”,“ 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呐喊·自序》)而《新青年》终于于1922年休刊了。
《新青年》之后许多年,鲁迅一直在《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继续创作,直至 《语丝》的出现。《语丝》在孙伏园的大力提倡、鲁迅的积极响应下诞生。其创刊号虽 然仅印2000份,因读者争购,增印7次,共计1.5万份,发行全国,成为鲁迅在北京期间 抨击北洋军阀专制统治,批驳“甲寅派”和“现代评论派”的重要阵地。发刊词中如此 写道:“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枯燥,思想界太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 句话,所以创刊……作自由发表。……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 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个人的思想终是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 异。……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 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及文字美术和一般的思想的介绍与研究。”鲁 迅先后在其上撰发作品130多篇,“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 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我和<语丝>的始终》),是鲁迅于《语丝》的贡献, 而于《语丝》中纷呈出现的精悍杂文、幽默简练的小品文、言辞犀利的战斗檄文成为《 语丝》的一大特色,“《语丝》是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的。”(《语丝杂谈》)语丝文 体的出现以及鲁迅在其中确立的文字风格,不能不说是《语丝》迥别于其他杂志的一大 特色,“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1927年8月17日致川岛信) 。
但这样的一种刊物,就鲁迅看来,“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投稿者 ,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态度也过于暖味,只是籍由一个缘起而聚焦在一起形成的刊 物,“不特说不上战线的统一,就是说同人杂志,亦勉强了。”[1]P196终于丧失了“ 破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我和<语丝>的始 终》)。这种编辑战线的不统一,是《语丝》走向没落的最根本原因。
1925年,徐炳昶在给鲁迅的信中建议将《语丝》和他所主编的《猛进》与《现代评论 》“集合起来”,共同编辑出“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鲁迅完全反对,如若这样 ,难免就会出现一本不伦不类的中庸杂志,“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 于是乎可掬。”鲁迅真正想创办的是一个新型的小周刊,以做“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 ”;而至于杂志的同人性,“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联合战 线”(《华盖集·通讯二》)。
体现“小集团”、“联合战线”、主题鲜明的杂志《莽原》周刊终于于1925年4月24日 创刊,鲁迅亲自担任主编。“莽原”二字得自字典,刊头是由一位8岁的孩子随意写的 。《莽原》的内容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风格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 世,望彼将来”(《莽原周刊出版预告》)。
“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瞿秋白语)是对鲁迅此时工作的最佳评价。从 《语丝》的自由文体进化为包含着炽烈火焰的“文明评论”和“社会评论”的要求,是 鲁迅更为明确的办刊理念的体现,于此之时,他亦深切领悟到作为一本同人杂志所最需 要张显的个性魅力和自我立场,“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 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 ,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所谓‘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 仿佛有人’的人,不过这么一回事。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我和<语丝>的始 终》)
这些“意见并不尽同”的同人在杂志初创期是美好前景的潜力之源,他们驱策着鲁迅 和《莽原》共同的前行步伐。在1925年12月25日《国民新报副刊》的广告栏中,鲁迅亲 自为《莽原》的出版撰写广告:
“这本……周刊,想什么就说什么,能什么就做什么,笑和骂那边好,冷和热那样对 ,绅士和暴徒那边妥,创作和翻译那样那样贵,都满不在乎心里。”
鲁迅对《莽原》是充满希望的,但在1926年,他远赴厦门之后,莽原社内部发生的冲 突却使这本应该有着更长寿命的杂志草草收兵,不战而自亡。
1965年,刘易斯·克塞在考察19世纪和20世纪初盛行在欧美文化领域里的小型文艺杂 志时,如此界定:“小型文艺杂志……它的编辑总是对取得商业成功的念头存有戒心。 他们有着自我意识,只为先锋派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说话,也只向他们说话。”“小型 文艺杂志,以及同它们结合在一起的革新艺术家及作家的小团体和派别,起到了对那个 时代公认的观念进行攻击的矛头作用。虽然它们经常分裂成敌对的宗派和竞争的小团体 ,它们的编辑和作者却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上流社会的文化。没有这些多姿多彩、短命而 反正统和无所拘束的小型文艺杂志,各种反对潮流也不可能清晰地阐明它们的批评标准 。”[5]
《语丝》与《莽原》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的小型文艺杂志。它们受到了很多青年的欢迎 ,也广为流传。但刘易斯·克塞提到了它们的缺点,其生生灭灭种种缘由就在这“革新 ”和“派别”的个性上凸显了出来,或者是其批评性和革新性招致查禁之灾,这一点, 鲁迅也有清醒的认识,“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声称自 己不谈政治,但“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4]或者由于内部龃龉、理念不和, 小型编辑团体的易分性而终致消失。
当然,《语丝》和《莽原》及之前《新青年》的倒闭原因并不能由此论尽,当时的国 情决定了正是这些洋溢着革新精神和现实主义激情的杂志必须以此方式生存:编辑队伍 小型,更机动也更自由;创作群体为同人,语言立场更集中,个性也更鲜明。我们不难 看出,鲁迅一向赞成的散兵战、壕堑战风格在他的办刊思想中有较好的体现。
“同人”并不能尽展鲁迅于杂志中播扬新知识、更新国民性的理想,也许在实际操作 中,杂志受到“同人”意识的影响较重,但鲁迅也冀望杂志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1924 年4月鲁迅致李雾城信中言及:“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么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 ,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当《劳动文艺周刊》就是否要出版欢迎孙中山专号辩论时, 鲁迅说“因为一出专号,对于政治没有兴趣的人,他一定不要看,反而减少宣传力。” [1]P172先从外表上就要给人亲切之感,来引导那些陌生读者。越大量地吸引普通读者 ,就有可能越大量地将陌生人变成己方的朋友。在《文学杂志》第一期出版后,鲁迅给 王志之的信中说:“我以为我们的态度还是缓和些的好。其实有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 ,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 失,也姑且不要太求全,因为求全责备,则有些人便远避了,坏一点的就来迎合,作违 心之论,这样,就不但不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1]P36站定立场,心怀宽 容,才是一本杂志可以长期为之的办刊哲学。
具有“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的种种信念体现在《莽原》的出 版中,而它的自我颓败让鲁迅极为悲愤。此后他虽也有力于各种新兴刊物的出谋划策, 但于杂志编辑上的重点却转移到了翻译推广国外的先进文艺创作之上去,出现了其后的 《莽流》、《朝花》、《萌芽》及《译文》等刊。
热望《奔流》的《译文》时代
根据许广平女士的回忆,在上海期间,与鲁迅有关的杂志报刊就有50多种,鲁迅先生 最为费心的杂志就是《奔流》。
《奔流》于1928年在上海创刊,以介绍欧美及日本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目的是为了 能以正确的文艺理论纠正当时出现的左倾思潮,并愿与创造社的作家结成一条战线,共 同作战。如果说鲁迅之前于《语丝》、《莽原》中的工作能够充分体现其杂志运作理念 的话,那么于此时对《奔流》的工作,则更能全面地体现出他具体的编辑工作的风范。
《奔流》的印刷与纸张都比当时一般杂志要好,每期均有大量的精美插图,翻译者的 介绍紧跟译文之后,鲁迅为《奔流》所写的12篇《编校后记》对编辑主旨及时详尽的解 释,对读者起到了很强的引导作用。“目的无非是为了要把新鲜的血液灌输到旧中国去 ,希望从翻译里补充点新鲜力量。……同时,他也不排斥创作,白薇女士的《打出了幽 灵塔》的长诗,鲁迅就分期给予刊载,为读者与作者设想,这里,鲁迅是颇费一点心思 的。他曾说:‘这样长诗,要是编排得好,穿插得合适,才会有人看的。所以每期的编 排就很费斟酌’。”“他编书的脾气是很特殊的,不但封面喜欢更换,使得和书的内容 配合,如托尔斯泰专号,那封面就不但有书名,而且还加上照片。内容方面,也爱多加 插图,凡是他手编的书如《奔流》以及《译文》,都显现出这一特点。而插图之丰富, 编排之调和,间或在刊物中每篇文稿的前后插些寸来大小的图样,都是他的爱好。”[1 ]P1208
然而如此工作实在是“成本太大,老板们逐渐觉得为难了,也是事实。他自己却又没 有如许资本自办刊物,因之往往很有未展怀抱之感,这在鲁迅自己,是常引以为憾的。 ”[1]P722
1928年12月6日,鲁迅与柔石合编的《朝花》周刊在上海刊行,以“介绍东欧和北欧的 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扶植一些刚健质朴的文艺”(《为了忘却的纪念》)。封面由 鲁迅设计,刊头选用英国阿瑟·拉克哈姆的一幅画,“朝花”两个美术字也是由鲁迅所 写。但之后很多实际的编辑工作由柔石完成。
1930年1月1日,鲁迅与冯雪峰合编的《萌芽》月刊在上海刊行,创刊声明中说明其主 旨是“翻译,绍介,创作,评论”,鲁迅绘制的封面由“萌芽月刊”四个美术字组成( 第一卷第三期之后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之一)。
1930年5月3日,他在给李秉中的信中如此说道,“近来颇流行无产文学,出版物不以 此为旗帜,世间便以为落伍,而作者殊寥寥。销行颇多者,为《拓荒者》、《现代小说 》、《大众文艺》、《萌芽》,但禁止殆将不远。”鲁迅敏锐地察觉到由于无产文学的 盛行带来的现实出版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反革命文化围剿已然大肆猖獗,“禁期刊、 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作者是俄国的……也都在禁止之 列。”(《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鲁迅很少也很难有自由和空间进行切实的杂志编 务,直至1934年9月《译文》在上海创刊,才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杂志编辑工作。
鲁迅命名《译文》,主编了前3期。当时他已重病深居,停止了一切刊物编务,为了《 译文》他重出江湖,意义非同一般。《<译文>创刊号前记》中,鲁迅说:“原料没有限 制,从最古以至最近。门类也没固定:小说,戏剧,诗,散文,随笔,都要来一点。直 接从原文译,或者间接重译;本来觉得都行,只有一个条件:全是‘译文’。……不过 得这几个同好互相研究,印了出来给喜欢看译品的人们作为参考而已。”他与茅盾、黄 源商定要摆脱当时杂志16开本的模式,走32开本的形式,也得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译文》销售出奇地好,创刊号就重印了5次,这是他作为杂志编辑者最后的实际工作。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杂志发展史上有名的“短命”的“泡沫年代”。杂志读者急剧增 多,许多出版商都看好以杂志养书的前景,运作中杂志出版又比办报出书要简宜得多。 许多出版人将杂志看作一种消闲娱乐的阅读零食,更多的是由于知识分子派别林立导致 的“小派系”杂志的增多,更有看好杂志广告市场的商人开始在杂志上大力投放广告( 鲁迅辞职《语丝》与李小峰擅登广告招徕商人也不无关系)。杂志出版界一片喧嚣纷呈 景象,但由于国民党刊禁政策愈演愈烈,许多杂志都长命不了,尤以进步杂志所受压制 更甚。
鲁迅于此时改变以往“率性而言,凭心立论”的明确办刊宣言,杂志需要更有策略地 去斗争,1933年他在给太原榴花文艺社的信中说:“……必须查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 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时虚名,反致不能出版 。战斗当首先守住堡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当年鲁 迅在编辑《奔流》之时曾有批评“个人趣味”的言论,鲁迅在《编校后记》中反驳:“ 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驰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将 战斗性隐藏在趣味性之后,实是最符合斗争的需要。
鲁迅力求以进步、健康的杂志赐予读者,将读者尽量从思想麻醉品的休闲杂志中吸引 过来,如何在喧扰混乱的杂志市场中宣扬新文艺新思想,“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又 能躲开刊禁暗箭?他开始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着重引进西方优秀的先进文艺作品方面。鲁 迅在1935年9月29日致萧军信中强调:“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多看并没有 好处,其病根:一是对事物不太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好遗产。对于后一层,可见翻译 之不可缓。”
客观看来,《奔流》、《朝花》、《萌芽》及《译文》是一种经过了思索和战斗布局 后才诞生的杂志,较前之《语丝》与《莽原》的随意性,它们的主体意识、编辑技巧乃 至躲避报刊审查的本领都为之提高了。但由于时代特点,它们的刊行与编辑仍是小规模 操作,参与编辑是同人自不必说,主编承担了各种编辑事务,从约稿、寻找插图、编排 文章顺序到审校、付印、发行等杂务均得亲力亲为,杂志出版基本由主编与书店老板双 方进行对话,它们的前途与以往的那些杂志也不尽相同。于乱世之中承担了引领国人新 知的责任,本就万分艰辛,再加上层层禁制,外侵又临,每种刊物大都不能存在很长时 间,“七七事变”以后,很多进步杂志都受到国难的牵连而停刊了。但鲁迅负笈编撰的 辛苦实是不可忽视,他将杂志视为一种可供收藏和传扬的文化载体,自然要竭尽心力, 让之完美。
如果说《新青年》是引进西方思潮的启蒙,成为现代进步杂志的标版,那么鲁迅在之 后的数十年里的工作则是灌溉和培育,将现代杂志创办中的进步性、策略性以及编辑出 版形式都具体化和实践化了。就是以这些杂志为媒介,他奔波开创了中国新文化领域里 的新局面。
鲁迅一生与中国现代杂志的发展演进密切相关,除去由他亲自主编的杂志之外,他参 与出版的杂志更不胜枚举,《世界文化》月刊、《太白》半月刊的筹办,《北斗》的开 创,支持厦门大学的学生自办《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大力鼓励《美术杂志》的 出版,希望可以编辑出“浅显而且有趣”的“通俗的科学杂志”,以慰广大求知青年的 需要,努力提携新进的杂志编辑力量。他的这些辛勤的心力为中国早期的白话杂志发展 史添进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鲁迅去世前一年,他给王至之的信中如是说到:“投稿难,到了拉稿,则拉稿亦难, 两者都很苦,我就是立誓不做编辑者之一人。当投稿时,要看编辑者的脸色,但一做编 辑,又就要看投稿者,书坊老板,读者的脸色了。”在他热血激扬的生命历程里,他实 是体味了创办杂志中的无限艰辛和奔波的心力之苦。
“先生每编一种刊物,即留心发见投稿者中间可造之才,不惜奖掖备至,稍可录用, 无不从宽。其后投稿较多,或觉少进境,也许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以致为人不满。这怕 就是和青年来往难得持久之故吧。……投来的稿子,真是缤纷万状:有写了一次即不愿 复看一遍,叫先生细改的;有翻译而错误很多,不能登载,致怨尤的;有一稿油印多份 ,分投各刊的;有字甚小,模糊难辨的;自然还有不少稍加修改,即可采用的。……凡 是先生手编刊物,读者怕很少不满意的吧。”[1]P358-359鲁迅为中国早期杂志的发展 所贡献的思想张力与实践经验,实是后来的杂志人所能承继的最宝贵的遗产。
收稿日期:2002-07-05
注释:
①本文涉及鲁迅文章未注明详细出处的皆出自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鲁迅全集 》。
标签:鲁迅论文; 新青年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萌芽论文; 文艺论文; 译文论文; 语丝论文; 莽原论文; 朝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