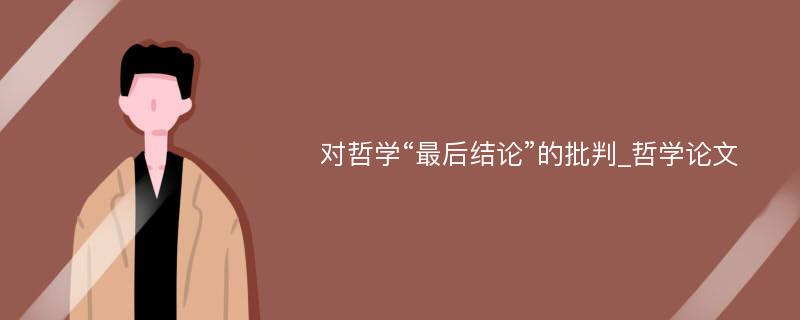
哲学“终结论”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 (1999)03—0046—(5)
自康德从独断主义迷梦中清醒过来之后,西方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批判”不仅成为一种哲学、一种方法、一种口号,甚至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批判精神孕育并造就了伟大的德国古典文化,同时又鼓励着现代人对这个包罗万象的庞大体系的不断反思。以尼采“一切价值之重估”为总特征的现代思潮走向了全面反传统的极端道路,引发了多层次多角度现代“主义”(isms)争奇斗妍的人文景观。“解构”不仅是某个流派的鹄的,而且是贯穿所有思潮的根本宗旨。解构运动的核心对象直指曾经是文化主宰的哲学,因为“哲学从关连着文化来讲,哲学就是指导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或智慧,也即指导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智慧。”(注: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页。 )故消解哲学的存在论意义即终结哲学就成了现代人扭转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但当我们面对由解构精神所带来的极端怀疑、虚无、绝决、冷漠使文化处于历史困境和现实裂变之中时,我们不禁要问:从批判到解构在何种程度上规定着我们的文化发展方向,即在何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如果不合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这种本源性的追问中,直接关涉到当今激变中不得不面对的冷静话题:如何对待传统。本文试图从时间上和内容上寻求解构运动理论根源上的合理性以及对我们现时代的意义。
一
解构思潮的秘密在于否弃形而上学,进而否弃哲学,最后将传统文化连“根”拔起而另谋出路。但现代“终结者”所宗主的康德黑格尔哲学并没有像他们那样简单地否弃形而上学。康德看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厄运,他认为形而上学成为“永无止境的纠纷战场”的原因在于它是人类理性本身提出的问题,但又超出了理性的能力范围之外、僭越知识而成二律背反。于是这种作为经验以外知识的形而上学成为不能由形而下知识来检验的“飘浮在上面的泡沫”。康德一方面承认旧形而上学的功绩,他说:“普通形而上学曾经在研究纯粹理智的概念方面有过用处,使这些概念通过分析而明确起来,并且通过说明解释而得到规定。”(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 年, 第184页。)但康德也看到“普通形而上学也就到此为止。 ”而且理性的整体性欲望还诱使它越出经验的领域,产生各种先验幻相。因此康德告别了“一般形而上学”,转而为真正可能的未来科学形而上学奠基。可见康德的批判并没有终止形而上学,他对普通学院形而上学的“造反”正是要建立一种“直到现在还从未作为科学而存在过”的形而上学,因为“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63页。 )康德坚信科学的形而上学“凭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法则”一定会到来。这是康德的伟大之处,也是启蒙精神的最高表现。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考察开了现代人整体上对形而上学猛烈攻击的先河。不同的是,康德“批判的本义应是论衡、衡量、抉择与料简的意思”(牟宗三语),是客观公正并富于建设性的,而现代人仅以消解为职志,放弃了更为宏大的理想,也就放弃了启蒙。
康德关于形而上学的伟大理想激励着历代哲学家为之不懈努力,最后黑格尔以某种“绝对”的思想方式和口吻宣布了这一时刻的到来。黑格尔发展了被康德视为不合法的辩证法,通过精神的内在发展和外化完成了世界的可理解性和理智直观的统一,达到绝对精神。至此哲学史宣告结束,黑格尔也因此被认为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终结”哲学的人。
但这种对黑格尔哲学的读解包含着极深的误解。黑格尔对哲学史的缜密研究中所建立起的强烈历史感与“终结”论所蕴含的历史断裂是格格不入的。黑格尔明确指出任何一种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每一种哲学都是世界精神递相连接的必然秩序中的一环。黑格尔哲学,从其根深蒂固的辩证法精神来说,既成某种结论——每一种哲学都会达到某个结论,同时又是哲学的新起点。从体系及其建构而言,应该也必定有个“终结”;作为某部哲学或哲学史的讲演来说,亦复如此。黑格尔说:“这就是当前的时代所达到的观点,而这一系列的精神形态就现在说来就算告一段落。至此这部哲学史也宣告结束。”(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四),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78页。 )黑格尔对终结一说有清醒的意识,他所终止的是哲学具体形态的一个段落,所结束的是他的“这部哲学史”。恩格斯早已看到了黑格尔的“终结”的性质,也为国内学者所逐渐认识到了。
此外,黑格尔倍受诟难的“绝对”观念被现代终结论者视为力证,而他本来所要表达的无非是康德所谓超越经验的无条件特性。具体地说,是指世界精神的艰巨探索在一定历史阶段上达到了本体意义上的终极法则:自由,“这是一切时代和一切哲学的要求。”(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四),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377页。 )这是黑格尔综揽思想历程的伟大成就,所以与其说是终结哲学,不如说是总结哲学。加达默尔公正客观地看到了黑格尔这个深沉而骄傲的宣言:“自那以后,历史就没有必要建立在新原则基础上了。自由的原则是无可怀疑和不可改变的。”(注:加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31页。)可以说,现代西方诸流派,包括旨在解构的后现代思潮,都不过是黑格尔设定的这个原则所做的各种具体工作,是“自由”追求琐屑且偏激的诸般表现,只不过他们并未意识到或者与黑格尔的理解不尽相同罢了。所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人们在谈论着形而上学的终结,谈论着我们所处的科学时代,甚至可以谈论着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的技术时代所特有的历史贫困。最终,黑格尔可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注:加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45—46页。)至于认为他的绝对精神包含了历史实际终点的观念,不过是那些过分热心的模仿者和另有理论需求的反对者要他承受的,黑格尔自己并没有这层愚狂的意思,他常常引用《新约》上的那句名言:“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已经站在门口了。”
形而上学仍然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在科学和常识联姻导致形而上学解体的时代,黑格尔仍然坚持“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它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注:黑格尔《逻辑学》(上),扬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2页。)当然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与康德的有所不同, 前者是体系的而后者是批判的、开创性的。黑格尔哲学还远不是康德所设想的科学形而上学的完成。至于康德的理想是否能够最终实现,目前我们尚不得而知,毕竟现代性是一项“末竟的工程”(哈贝马斯语),但重要的是,黑格尔接过了这个火炬。
黑格尔为包罗万象的各种知识寻求一种可公度可通约的企图,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时代科学精神的影响,更受到文艺复兴以来高扬的主体性精神的鼓励,而不顾自然研究本质上的暂时性及其与人文建构相似的不断超越自身的进展方式,所以注定了要遭到某种外在的失败。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庞大体系如此迅速的表面“崩溃”?我们认为只要从黑格尔苍白陈腐的学院气息中解脱出来,使之回到那最具特色的时代情境中去,并把他的思想放到生生不已的历史长河中去审视,就不存在所谓崩溃的问题了。作为哲学史的一环、作为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将从正反两方面受益于黑格尔哲学。就连海德格尔晚年也认为:“我曾再三反对过谈论黑格尔体系的崩溃。正在崩溃了的,也就是消沉了的,是继黑格尔而起的东西——包括尼采。”(注:转引自加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49页注释 3。)黑格尔哲学没有终结哲学,也没有被哲学所终结。
二
以德法为主的现代大陆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是以继承、改造和发展为目的的。客观上大陆现代哲学并不简单拒斥传统学说,而是在新的历史事实面前以更宽广的视域重新审视传统,力图在已经耗尽各种可能的传统道路外寻找“柳暗花明又一村”,寻求如禅宗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其基本表征便在于“重估”、“破执”、“解构”,但与其所批判的对象却有着非常深刻的关联。只不过这种关联十分含蓄遥远,因此哲学的重建工程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仍还停留在清理地基的早期阶段。人们远未能看到这项工程的结果,一切都似乎还处在晦暗之中。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存在的遗忘”,而在于遗忘了与传统的关联。
海德格尔被认为是现代解构思潮的主将,也是解构主义流派的直接理论先驱,他对哲学的态度决定性地影响着身后众多的思想家。海德格尔身处文化根基转换的宏伟历史浪潮之巅,秉承尼采、胡塞尔等人的批判成果,总结传统哲学的功过并尝试性地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由于受历史剧变、社会现实及德国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海德格尔的思想表现出彷徨、偏激与矛盾的特点。但在哲学的“终结”问题上,却极富新意与启谛。海德格尔明确提出终结哲学。他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是始于柏拉图对本真的希腊思想源头的降格所凝结成的一种遗忘了“存在”的学问,形而上学只思考作为存在物的存在,而没有进一步追问引导这一结论的更源初的亮光。传统哲学把形而上学看作是全部哲学(包括物理学)的“树根”(故称mata-physics),但遗忘了或没能进一步深究树根之能得以滋养的土壤,所以海氏认为传统哲学长期处于无根基状态。而且这种无根基状态还受到由希腊文化向罗马文化过渡中的翻译和阐释的加剧,结果导致当今的思想僵化、虚无主义、精神萎弱、技术统治等方面的现代问题。(注: See M.Heidegger:ThePrinciple of Reason,P113—129,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或“存在的真理”,才能解决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海德格尔后期以恸天之问言说着这一切,他相信,只有克服形而上学,才能给这深沉的“末世”带来一点生机,为澄明的真理扫除蔽障。但海氏所说的“去蔽”、“克服”不是消除形而上学,他认为只要人仍旧是有理性的动物,那就必然也是(从事)形而上学的动物。我们看到他对康德关于“形而上学属于人的天性”观点的赞同与一致,进而看到他在刺眼的“克服”言论中显现出对传统的另外一层“在场”。
海德格尔所说的“终结”,不是消极意义上的单纯中止、没有继续发展甚或颓败与无能。他说:“相反地,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Vollendung)。”(注: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9页。)紧接着,海德格尔进一步解释这种因完成而致的终结:所谓“完成”并不是指尽善尽美,并不是说哲学在终结处已经臻至完满之最高境界了。那么终结就是指达到一种“聚集”了各种可能性的“位置”,即指哲学孕育并滋养了科学,在科学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今天,哲学完成其历史使命而随诸神一起引退。这就是海德格尔的本意。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的存在史是人类历史上一段合理合法的历程。但随着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之可控制设置的胜利,哲学便宣告终结。但是人类的历史以及思想的历史并没有结束,所以现在面临的任务不再是营造与物理学同质的科学形而上学(Metaphysik),即“后物理学”,而是彻底转换思维视角,从根本上“超越”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走向uberphysik,即走向更本真更源初的“思”。可见海德格尔倡言的终结说不在于字面的常识性理解,更不同于解构主义的真正“误读”,而是喻示着“超越(überwindung)”,即包括着席卷、包括与克服(Ver-windung)在内的超越。
海德格尔把哲学当作一门封闭的旨在帮助人类渡过某个阶段的学科,一旦任务完成,自身也就退场。哲学学科退场的目的在于要把人类精神引向更有前途、更有澄明的“思”。思超越科学与玄学的二元背离,“它比理性化过程之势不可挡的狂乱和控制论的摄人心魄的魔力要清醒些……它超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分别之外。它比科学技术更清醒些,更清醒些因而也能作清醒的旁观。”(注: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5页。)这就是海德格尔批判传统、追问存在、终结哲学这一伟大构想的深刻用意。在哲学与思的比较中,他把传统哲学当作了小写的哲学,而把思看作永恒的大写的哲学。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与黑格尔极其相似,只是终结了已经进入历史的旧哲学,同时还以更大的热情召唤着新思想新哲学的到来,因为真正的哲学不会终结。他说:“那么,思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注: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6页。)从他更深的本义而言,即是说:思在,故哲学在。
透过学院气的思维方式和晦涩的术语,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是以极其矛盾和痛苦的心情来谈论哲学的终结问题。一方面,他把当今的精神危机归结到柏拉图式的传统形而上学之上,故走出传统的误区从而返朴归真以解决面前困境的前提就是首先要终结哲学。这是海德格尔思想中积极批判性的一面,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与其说他在批判传统,不如说他在批判现代思想的堕落。另一方面,在海德格尔的价值世界里,传统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纵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比起今天的混乱、虚无和萎弱状态,他又觉得传统哲学仍然是弥足珍惜的。在现代与传统的无奈选择中,他更青睐于后者——虽然他曾对此给予过最无情的批判,但那恰恰标识着他内心未曾言明的痛苦。比如就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表面上的分崩离析,他十分惋惜地说到:“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德国唯心主义的破产,而是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丧失其强大的生命力。结果不再能保持那一精神世界的伟大、宽广和原始性。”(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6页。)这是他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在他看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何尝不是已经开始丧失生命力,结果不再能保持传统哲学精神世界的伟大、宽广和原始性!
我们往往只看到海德格尔拆解传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的用意在某种程度上与康德的一致性:拆构(Destruktion)是为了察看地基、是为了克服和超越;更没有看到海德格尔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所作的痛苦抉择。海德格尔虽与康德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他并没有像康德所批判的那样“因噎废食”、“一劳永逸”放弃了对形而上学或真正哲学的研究与希望,只不过在他那里有着很不相同的面貌而已。这比起只为破坏而解构,故而无忌放言“终结”的解构主义思潮来,要高明且深刻得多。所以貌似具有批判特质的解构,实则是批判哲学的叛逆和倒退。
总之,海德格尔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而是以惋惜甚至悲哀的口吻来谈哲学的终结。与其说他在终结哲学,不如说他在奋力拒绝着诸神隐退后思想贫乏的技术时代的到来。诸神隐退象征着哲学被不幸地终结和思想的缺席。海德格尔亲历了历史的黑暗,目睹了无思的东西对人类的疯狂统治,他对此开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同时他又意识到他的四元世界结构(天空、大地、无限者、有限者)的无力无助以及他的救赎方案之实现的遥遥无期,他终于把痛苦交托给了“天命”以及“极不确定”、“尚付阙如”的世界文明的命运。海德格尔在积极抗争并指示着思进入澄明的自由之境的同时,告诫我们,如果照现在的状况发展下去,恐怕真的会“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了。所以海德格尔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要渡过当今的转折难关,解决愈来愈紧要的问题,恰恰不能终结哲学。
三
在近现代世界观的大动荡中,几乎所有流派的哲学家都企图用一种对哲学的科学特性的纯学术态度把它挽救到坚实的土地上,结果便如加达默尔所说“哲学因而就进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塘,或者搁浅在认识论的浅滩上,或者徘徊在逻辑学的死水中。”(注:加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6页。 )哲学的理论随着科学的胜利,即经验材料的不断累加,便再也无法把越来越多互不相容的材料组合为一个系统。哲学在这方面的功能消失了。作为时代决定性标志的科学之流行必然会终止哲学的经典作用,且哲学不同于科学、形而上学也无法成为“科学的”。但由此就以为哲学再无用处的终结论又显然把哲学的丰富内涵和它与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联系简单化了。而尔后对哲学给予的“致命打击”最多只能针对哲学中被简单化的那些方面。
纯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是人类精神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科学之于世界整体的“支离破碎”(熊十力语)限制了它无法从根本上承担起整个人类文化使命的重任。相反,单纯强调科学客观性的科学沙文主义已经给我们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科学与哲学共同起源于对世界的“惊异”(Wonder),共同回答着与人类切身相关的问题,不能以科学取代哲学(注:F.C.Copleston:The Function of Metaphysics,see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Metaphysics,P 34—43,Holt,Rinhart and Winston,1962.)。科学主义奉语言分析为万能并把它当作消解形而上学进而取消哲学的重要工具。但这种“哥白尼式革命”的“语言论转折”(Linguistic Turn )从根本上说亦不过是在形而上学内部发生的范型转换,即以语言论时代的语言本体替代认识论时代的理性本体,它不可能离开广义的形而上学的畛域。而且语言分析的力量和有效性范围也不是科学主义所想象的那样大,真正被语言所“误导”的恐怕不是他们所批判的形而上学,而是迷信于语言分析的科学主义自己。维特根期坦前后期的转变似乎就意味深长地喻示着科学主义的窘境,而他所谓“这贫困而黑暗的时代”产生的原因就在于现代人偏激地终结了本不应该也不可能终结的某种与时代命运休戚相关的东西。
哲学固然急待清理、固然需要不断的反思,却不能以摧毁代替转折。即使在正常的转折中也包藏着一种危险,正如施太格缪勒所指出的:“它会使人们把迄今为止的一切都看作是陈旧过时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引起思想上内在的放纵。”(注: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09页。 )处于现当代哲学内容急剧转折阶段的大多数思想家,尤其是那些以终结哲学为根本目的的人,或多或少都在放纵着思想。哲学的体系时代虽已成为过去,但哲学本身还没有结束,我们不能“为了历史而放逐思想”。人类的自然综合倾向仍然而且永远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用康德的理论来说,先验综合能力或统觉与人的形而上学倾向可以互证(注:人类不仅有生物本能,更有理性本能,后者为我们所不察。我们不仅要限制生物本能,更要限制理性本能,否则会产生先验幻想。而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即在不同的方面放任了理性本能,没能体会到康德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地盘的用意。M.霍克海默把这种现代现象叫做“理性的偏执狂”。)。所以说康德“即使在沉思存在的最深刻、最荫蔽的根据时,也仍在追求光明。”(卡西尔语)比较康德与后康德学说,难怪有人认为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降格和倒退中的。
就算被誉为“显得更为持中、冷静”的罗蒂新实用主义哲学也存在放纵和倒退的嫌疑。罗蒂把后神学时代取代神学而充当文化统治者角色的传统哲学称为大写的哲学,这种哲学随可公度性支撑的消失而消失,意即体系哲学或认识论哲学的终结。但他承认“教化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 )作为文化的一个门类与其他文化形式公平对话的权利依然存在,他认可“伟大的系统哲学家象伟大的科学家一样,是为千秋万代而营建”,同时也坦言“伟大的教化哲学家,是为他们自身的时代而摧毁。”(注: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322页。 )罗蒂披露了包括他自己“后哲学文化”在内的现代哲学的真正目的,并在终结说之外承认了(系统)哲学的永恒价值。罗蒂现象即是研究批判与解构关系极好的个案。其实教化也罢,批判也好,本身就离不开系统与建构。教化之被系统化、解构本身之被解构,本来就是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二律背反的主题。所以不管教化者、解构主义者的口号如何合理、目的如何善良,我们也无法剥离人类思想本性的自然倾向。即便要改造利用人类的思想成果,也大可不必为了多元化而牺牲整体性,更不必先去拼命否定它。至于后现代主义者以多元化的名义推行一种新的文化暴政,更会把我们引入歧途。
除去知识性质和哲学旨趣的变化之外,现代与传统在“哲学”的层面上完全同质。而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方略就是被批判者得以成立的基础。比如胡塞尔为克服自我意识的内在性与人对世界认识的超验性之间那种独断地设定的分离(这曾经被认为是认识论构造的基础)所提出的意向性理论,认为从命题表述与对可观察事态之间的经验一致性就可以假定世界的逻辑结构。再看康德及其后继者依靠形而上学观念把经验的a posterisori(后天)因素和理性的a priori (先天)因素提高到完美的统一,并把这种统一性作为一切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加以推演,人类就会得到真理。比较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在方法论上的深刻一致。而且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只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或维度更加提示了传统的生命力之所在以及与现代性之间的源流关系。他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现代哲学打碎了系统整体而在某些方面作些补充、在某些方面极度膨胀罢了。所以我们认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划分,仅仅具有年代学上的方便而已,就哲学的基本功能以及与人类的关系而言,不存在实质性区别。面对当今激进的反传统浪潮,再比较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理论异同,我们可以认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哲学还不够成熟,更谈不上“终结”的问题。
所谓哲学的终结,不过是现代人在文化困境和精神焦虑的驱使下对传统哲学的粗暴拒绝,也是一种现代精神生活、文化节奏中的简单化处理。不幸的是,这种粗暴和简单化是一种集体行为,或者说来自于一种集体的力量。所以哲学的终结问题才显得如此突兀和具有煽动性。殊不知我们的全部世界经验呈现为一个逐渐无拘无束、永无止境的过程,而对这些事物作出一种哲学说明的迫切需要也是一种永恒无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实现了我们每个人在思想中与自己的对话,而且也实现了我们大家都卷入并且会永远不停地卷入的那种对话,无论人们说哲学已经死亡,或者说哲学没有死亡。”(注:加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7页。)
收稿时间:1998—09—25
标签: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康德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家论文; 面向思的事情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