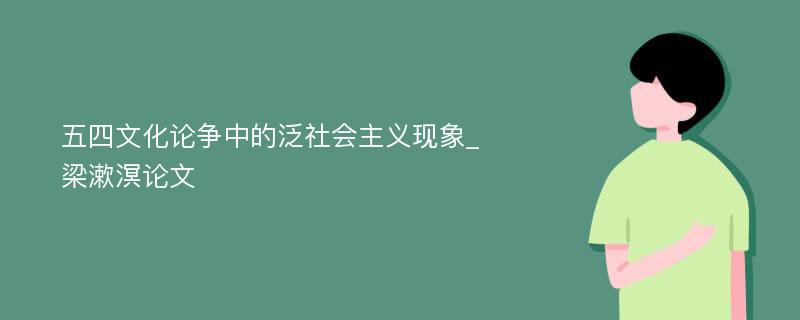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泛社会主义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东西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约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到1927年被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所代替,持续长达十余年,文章、论著发表千余。论争双方阵线分明,一为东方文化派,一为西方文化派。他们在东西文化何优何劣、差异何在、能否调和、东西方文化各自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如何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一为东方文化优,一为西方文化优;一为东西文化为性质之异,一为东西文化为程度之差;一为东西文化可以调和,一为东西文化如水火不能相容;一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一为西方文化有光明的前途,等等。然而,在激烈的对垒中,双方却在社会主义思想上达成暗中投合,对社会主义不约而同地给予了充分关注和赞许。
陈独秀是西方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动者。他虽然是五四时期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在五四运动以前却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中国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取而代之,为建立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然而,也就在这时他已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并给予了充分肯定。陈独秀写道:西方文化“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注: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1915年第1号。)。他还指出:虽然西方近代文明有缺点,造成了社会上的不平等,但又产生了“去此不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注: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1915年第1号。)。
此外,陈独秀在回击东方文化派“物质上应开西洋之新、道德上应复中国之旧”的观点时,也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的赞许。他说:如果提倡中国的旧道德,即使达到了“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也只是分裂的生活,利己的生活;去那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相爱互助全社会共同生活的思想,还远得很”。而西方的光明前途,就在于他们“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有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注: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卷1919年第1号。)。这里,陈独秀所说西方正在开发的东西,显然是指社会主义的新道德。
胡适是西方文化派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他对东方文化派提出的东方文明是精神(道德)的、西方文明是物质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包含物质的、精神的两方面;精神文明建筑在物质文明之上;西方的道德信条,在18世纪是自由、平等、博爱,在19世纪中叶以后就是社会主义。胡适还特别指出:19世纪以来,西方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资本主义下的苦痛渐渐明了,“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现在私有财产制虽然还存在,然而国家可以征收极重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财产久已不许完全私有了。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注:《现代评论》第4卷, 1926年第83期。)。
以上摘引,来自胡适在论争中的代表作《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篇文章发表于1926年7月,即这场论争就要结束的时候。 在此之前他与李大钊之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表明他是主张资本主义改良的。但这并不说明胡适反对社会主义这一文化现象本身,他只是认为当时的中国应该先进行资本主义而已。
胡适不仅称赞西方的社会主义,他还认为中国东汉时的王莽,实行了“土地国有”、“均产”、“废奴”、“设六筦”等社会主义政策,认为“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胡适替王莽鸣冤叫屈,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注:胡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读书杂志》1922年第1期。)
以上通过陈独秀、胡适的有关言论,可看到西方文化派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赞许。
《东方杂志》主笔杜亚泉,是东方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杜亚泉反对西方文化派把东西文化的不同视为程度之差,认为东西文化只是性质之异,中国虽然在经济上不如西方,在道德上却能“统摄人心”。因此,他认为东西文化应该调和。杜亚泉还预测: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的经济变动,“必趋向于社会主义”。何为社会主义呢?杜亚泉说:“西洋之社会主义,虽有种种差别,其和平中正者,实与吾人之经济目的无大异。孔子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主义所谓‘各取所须’(应为“需”——引者按)亦即均之意义。……实则社会主义,乃吾国所固有。”(注:伧父:《战后东西文明及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1917年第4号。)杜亚泉甚至建议国人:不要醉心欧化, 而要注意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应该“以现代文明为表,以未来文明为里。表面上为奋斗的个人主义,精神上为和平的社会主义”(注:伧父:《新旧思想之折衷》,《东方杂志》第16卷1919年第9号。),等等。
东方文化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梁漱溟,曾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从哲学的高度来谈论东西文化问题。梁漱溟断言: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对于此,他提出自己的哲学根据,并列举了许多西方文化正在向中国文化靠近的例子。其中,尤以社会主义的例子为多。梁漱溟指出:西方的经济是不合理的,现在正在要求改正,“这出来要求改正的便是所谓社会主义,西方的转变就萌发于此”(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第164—165页。)。他还说:“许多人总觉得他们都是空想……;然而无论如何,这改造要求是合理,那事实必归于合理而后己。”(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第164—165页。)梁漱溟还列举西方社会主义,有圣西门一派“宗教气味”的,马克思一派“科学气味”的,基尔特一派“哲学气味”的;并认为在基尔特主义的“协作共管”制度下,人们对物质生活“一定恬淡许多而且从容不迫,很象中国人从来的样子”(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第193页。), 等等。
以上就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泛社会主义现象。他们都不是专门在谈社会主义的,但对社会主义却谈了很多。社会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护身符,是他们各自所赞美的东方或西方文化的重要注脚。从而,这场论争在尖锐对立中却始终潜伏着不自觉的和谐。
二
社会主义能引起东西文化派双方的广泛注意,并得到他们共同的赞许或认可,并非偶然。如何对待社会主义这一文化现象,牵涉到人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文化基础。论争的东西文化两派,他们的西学知识可以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其中学基础也即他们的基本文化基础,却无可选择地出自同一个中国文化土壤。而这一文化土壤,经数千年孕育所形成的有关理想社会的知识以及道德主义价值观,就成了东西文化派双方都不自觉地关注并赞许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列宁说过,每一个民族文化里都有一些尽管还不太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虽然来自外国,但其一般内容如公有、均平、互助等,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文化自其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固本生元之时,就开始产生了诸如儒家的“均平”、“和谐”,道家的“小国寡民”,墨家的“兼爱”等社会理想。到了汉朝,有关社会理想方面的知识就更加蔚为可观了,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大同”社会理想,即《礼记·礼运篇》中所描述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女有分,男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自此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不断巩固,和《礼记》在诸经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礼运篇》中这一内容周全、文笔优美的“大同”理想,也就成了中国社会理想的经典,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文化人来说,“大同”理想也就成了他们文化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凡遇与“大同”相类者,对他们便极具亲和力,容易被认同,甚至会在新旧“大同”基础上,构筑和创造自己的“大同”。世道衰微之时,尤其是这样。近代中国人一接触西方“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教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时,就产生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五四时期东西文化派双方都对社会主义投以青睐,是与他们所共同具有的“大同”社会理想知识有关系的。只是这种关系由于当时正处于激烈对垒之时,表现形式更复杂一些。如陈独秀曾对《礼运》“大同”说出自孔子之口表示怀疑,并认为“即使《礼运》出于孔子,而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者,乃指唐、虞禅让而言,大同之于小康者,仅传贤、传子之不同,其为君主私相授受则一也”(注:陈独秀:《答吴又陵》,《新青年》第3卷1917年第5号。)。这话乍一看来,好像陈独秀对“大同”理想不屑一顾,其实这不过是陈独秀出于彻底反孔子学说的手法和态度上的表现而已。陈独秀除了否定其中他所认为的“君主私相授受”外,并没有对其他内容提出非议。而这些内容与他所极力推崇的西方正在“开发”的“公有”、“互助”、“利他”、“社会共同生活”有什么两样呢?这恰恰说明,正因为陈独秀早已熟悉并认可了“大同”理想,才认为它不应该出自他所极力反对的孔子之口。
另一个对“大同”说提出异议的是梁漱溟。在梁漱溟看来,孔子的所有言论都谐然一体,惟有“大同”说显得出格、不顺眼。他认为“大同”说不可能出自孔子,孔子所主张的是“不计较”、“恬淡”的生活,而“大同”里处处充满着“计较”,等等。梁漱溟甚至指责康有为以孔子之名写成《大同书》,是对孔子的亵渎,认为康有为根本就没有领会孔子的思想(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5—137页。)。其实,梁漱溟对“大同”持这种看法,除了表明他对孔子的人生观、社会理想有不同理解外,并不说明孔子的社会理想在他思想上没有烙印。梁漱溟所理解的孔子的理想社会是“不计较”、“恬淡”等,而他也正是以此来推测和赞美西方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
其他,如杜亚泉是以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之意,来寄希望于西方社会主义的。他曾说:“西洋经济界,若实行社会主义,则吾人怀抱数千年之目的,无手段以达之者,或将于此实现矣。”(注:伧父:《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1917年第4 号。)再如李大钊,则是以“人类一体”、“世界一体”、“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注: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第2卷1919年第2号。)等等,来向往未来的。在东西文化论争中,传统的“大同”理想与西方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在遥相呼应着。
比起“大同”理想,共同的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更是东西文化两派一致赞许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是儒家思想为主干的,而儒家又是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从而,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伦理道德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特别在伦理道德与政治、宗教、哲学的关系上,道德的重要地位更明显。如伦理学说和政治学说,在儒家的“先王之道”中,两者基本上是合二为一的,孟子所谓有“仁心”才有“仁政”,后儒所谓有“仁义”、“天理”才有“礼乐刑政”等。与伦理和政治的关系相反,中国伦理思想和宗教的关系并不密切。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除两汉曾有过“天人感应”说把宗教与道德相结合的现象外,伦理道德始终是与宗教分离的。人的内心情感,主要不是靠宗教而是靠道德来维系的。在伦理和哲学的关系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的由“人道”而及“天道”的思想。如董仲舒的有意志的人格神,程朱的“天理”,陆王的“吾心”,都是仁义礼智的集中表现。这种以伦理道德统贯一切的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就养成了一切以道德来衡量、以道德论取舍的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引进,对中国文化的道德主义是一个冲击,但还只是表面上的。辛亥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彻底铲除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但是,靠一两次思想运动,是难以摧毁人们下意识中的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何况新文化运动刚一开始,随之就出现了东西文化论争。于是,根深蒂固的道德主义,就不能不影响这场论争。
东方文化派之所以反对西方文化、坚守中国文化,就在于他们认为,西方道德沦丧,中国道德“犹能统摄人心”。道德是东方文化派在论争中进行攻、守的工具。发动新文化运动者陈独秀等,倒是以“进化论”为武器,试图除中国之旧布西方之新的。他们抓住了中国文化的要害伦理问题,所谓“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1919年第6号。),猛烈攻击儒家的纲常名教。但是,西方文化倡导者自身在论理方法上,除了笼统地批判中国固有的东西有悖于“进化公例”外,与东方文化派相比又有哪些新东西呢?他们同样在思想方法、价值观上摆脱不掉道德主义的束缚。陈独秀甚至认为,中国之危在于“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陈独秀还提出勤、俭、廉、法、诚、信六个字,把它们视为“救国之要道”(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1916年第2号。)。在思想方法上,西方文化派离道德主义的距离,并不比东方文化派远多少,何况来自对方的攻击又多是从道德角度来的,回击时也必然要从道德上来作文章,所喜所恶就难免蹈入道德主义的洞穴。
当时,李大钊曾对道德与物质的关系做过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说:“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道德的要求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注: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第2卷1919年第2号。)等等。但是,这种认识在当时还不占主导地位;而且李大钊的用意也旨在批判东方文化派的东西文化调和论,不重在从思想方法、价值观上扭转道德主义倾向,影响不大。
总之,一切从道德始又从道德终,这是东西方文化派双方的共同现象。从而,他们都频频提起“公有”、“均平”、“互助”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并在此意义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同怀赞许、期待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大同”理想没有讲明实现这一理想的物质前提,也没有论及实现这一理想的方法、途径,最终只是一种理想。以道德论取舍的道德主义,则明显地更是一种唯心主义。因此,受“大同”理想和道德主义的影响,东西文化派双方的社会主义关注和赞许,一方面是广泛的,另一方面就必然是空泛的。即他们均无作科学与空想之分,都仅是在泛泛而谈的各种社会主义所共有的均平、公有、互助等道德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关注和赞许,对现实社会的改造并无直接或实际的指导意义。然而,结合整个五四时期来看待这一现象,却不能不注意其客观作用,更不能忽视其内在的思想逻辑。
五四运动前后约10年左右的时间,之所以被称为五四时期,其重要内涵就在于,它是中国人自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重新考虑中国命运和决定中国路向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自此以后,中国就开始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行程。当然,这一结果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然而,俄国十月革命仅只是一个外因,真正使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因更重要,其思想背景更广阔,其认识历程也更复杂、曲折。从思想背景和认识历程看,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东西文化论争的展开、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等等,都是中国人重新探索中国路向的具体体现,也都是中国人一步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变动和认识过程。其中,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的社会主义思潮,它是中国人的意识倾向由原来的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环节。正是在社会主义思潮中,人们对俄国十月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原被视为社会主义之一种的马克思主义,也在这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以至于最终被接受。这一过程,就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段时间。
然而,社会主义思潮决非凭空而起。任何一种思潮,都是一种社会心理、意识倾向的变动,且都是经过一定的潜移默化过程才突然明显化的。社会主义思潮作为社会心理倾向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变动,也是这样。早在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以前,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这一鲜明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各种弊端的暴露、新文化运动展开后人们思想的大解放等等,已使人们对近代以来一直倾慕的西方资本主义逐渐产生怀疑,并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将视线向社会主义转移。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泛社会主义倾向,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心理变化。参与论争者无论是西方文化派,还是东方文化派,除去极少数顽固守旧分子外,应该说都是走在时代前列、欲为中国寻求最佳出路的先进分子,他们无意于专论社会主义,却都频频提起社会主义;他们激烈对垒,却又不约而同的赞许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早在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以前,有关国家出路问题的社会心理倾向,已开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移。
不仅仅如此。东西文化派双方大都是在社会舆论界具有视听影响的人物,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广泛关注和赞许,早于社会主义思潮,并持续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这对于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无疑具有舆论导向和气氛烘托之效。
当然,东西文化派双方能以异中有同,对社会主义同持赞许态度,是与他们共同的文化积淀分不开的,是同受“大同”理想和道德主义价值观影响的结果。因此,东西文化论争中泛社会主义倾向的客观作用,也就是“大同”理想及道德主义价值观的作用,即后者在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思想入口处,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国人接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诱。
由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和道德主义价值观,能使人们不自觉地受其影响而容易接近乃至接受马克思主义,它们是否也容易使人们不自觉地将其空想性带进马克思主义呢?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初期的一些事实看,它又是一个难以作否定性回答的问题。如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也就是在其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是要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甚至,直到大革命末期,瞿秋白还提出过直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次革命论”等等。这些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空想,在当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与经济基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物质前提与经济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之一。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或直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次革命论”,竟没有提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和经济条件问题。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还不能真正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把不自觉地以已有的思想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当成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继而又加运用得出了如上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这里所谓已有的思想,在形式上不能绝对说就是充满道德主义的“大同”理想,但在内容上,至少是与“大同”相类的、同出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东西。毕竟,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业经济社会化大生产下的产物。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在当时又仍然处于小农经济包围中的中国人,在短时间内匆匆接受、理解乃至应用马克思主义,是难以避免以自己现有的、最熟悉的东西来比附和理解的。这是一个思想规律,如同恩格斯所说,任何新的学说或思想,“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 页。)。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中国文化中的某些东西,既有积极的引荐、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妨碍人们真正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作用,这恐怕是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所始料不及的。而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泛社会主义及其客观作用,却分明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标签:梁漱溟论文; 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青年杂志论文; 大同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陈独秀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国学论文; 新青年论文; 东方杂志论文; 孔子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