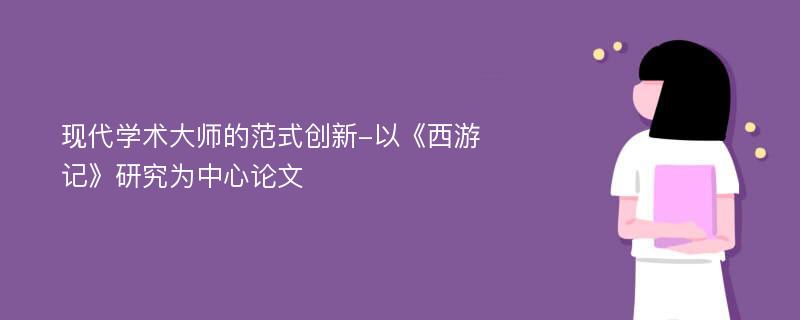
现代学术大师的范式创新——以《西游记》研究为中心
竺洪波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摘 要: 考察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轫期大师云集《西游记》论坛的学术景观和学术生态,重点评述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三人研究《西游记》的因缘、过程、成果和“范式”创立的学术贡献,并揭示大师们的学术理念、治学精神和学人品格对当下学界的启迪和昭示意义。
关键词: 中国现代学术;大师;《西游记》;学术范式创新
在20世纪初叶中国现代学术的发轫期,《西游记》研究是一块充满生机、成绩丰硕的领域。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大师云集,阵容蔚观,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胡适、鲁迅、陈独秀、陈垣、董作宾、俞平伯、傅惜华、徐旭生、郑振铎、赵景深、陈寅恪、孙楷第等学术大师纷纷参与(他们都撰有《西游记》研究论文,篇目略),其中王国维、胡适和陈寅恪三位大师最具代表性、典型性和影响力。从《西游记》作者考证、源流和版本梳理、文本阐释、人物和母题考稽到治学方法拓展、学科形态建构,大师们的卓越建树最终积淀为一系列宝贵的学术范式,从而一举完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范式创新。结合当下学术现状,考察昔日学术景观和学术生态,重温大师们的学术理念、治学精神和学人品格,更富有昭示意义,诚所谓“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未来以轨则”(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导生制”的实行,旨在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改变全凭教师讲解的枯燥方式,改变课堂上教师唱主角的方式,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发挥学生特长。
一、王国维:“外部研究”构筑基础
王国维是引领现代学术的“大师巨子”(陈寅恪语),在经史方面成就卓著,对现代《西游记》研究也有特殊贡献。尤其是重新发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整理《长春真人西游记》,以“外部研究”的范式功能构筑基础,对现代《西游记》研究有奠基、开辟之功。
(一) 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百回本《西游记》作为世代累积型巨著,最早的文学雏型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民国四年(1915),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发现佚去已久的《新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简称《诗话》)高山寺藏本,并旋即影印回国,经王氏校注后收入《吉石盦丛书》正式出版,国人始知佚本全貌。除却整理文献、拯救国故的价值,王国维此番发现的“附加值”——对《西游记》研究的价值未可觑视。
其一,推断《诗话》为“《西游演义》所本”。《西游记》有蓝本,但所本究为何物,历来多存歧见。或谓元明间杨景贤《西游记》杂剧,或谓明《永乐大典》所收《西游记》平话(今存有残文)。事实上,根据《西游记》的演化实际,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百回本《新刊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以前的各种“西游”文本都有可能成为其直接或间接的蓝本。王国维初见《诗话》高山寺藏本,立时认识到它作为《西游记》蓝本的意义。他在写于1915年的《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中,根据其写作时代和文字内容的特征,明确指认《诗话》“即《西游演义》所本”。同时历数自金院本《唐三藏》至元初吴昌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西游”作品的佚失情况,雀跃惊呼“南宋人所撰话本尚存,岂非人间稀有之秘笈乎!”
二是词汇准确性不够。因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某些词汇在西方国家和我国有明显区别,易出现翻译纰漏。如“莲花”,长久以来我国赋予莲花高雅、正直的文化内涵,而英语中莲花-lotus则意为慵懒、散漫,lotus eater表示“过着懒散生活的人”。
《诗话》之失而复得,找到了《西游记》最早的文学源头,王国维关于《西游记》蓝本的论断也成为学界定谳。鲁迅称《诗话》为“《西游记》的先声”,其状类似《大宋宣和遗事》是《水浒传》的先声一样[1]289。胡适则进一步认可:“这部书(《诗话》)确是《西游记》的祖宗[2]6”,它确定了后世《西游记》演化的文学性方向。
本项目在施工中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机械设备、材料拉运、建筑物构筑、砼拌合、设备加工、人员活动、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噪声、废水、废气、废渣、生活垃圾等,但由工程性质决定了三废污染较小,且随着施工结束而自动消失。本项目规定将所有治理河渠和保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装置、设备、监测手段和工程设施,均列为环保投资。经估算环境保护总投资为10.21万元。
从高职院校的角度来讲,学校应利用政策机制来积极营造创新氛围。比如采取组织导游比赛、旅游企业营销大赛等形式充分调动旅游专业学生的积极性,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比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创造能力。同时还可以鼓励大学生的创新项目,引导他们实时关注旅游行业发展状况,充分发挥其创新和创造能力,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水质管理:田间水层始终不能低于沟面。高温季节,适当灌水调水温,避免烫死泥鳅。若水质较差,选用水质改良剂和微生物制剂调水、改水。
其二,1932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应中文系代理主任刘文典之邀为招生考出试题,曾有求对子一题,给出的上联竟是“孙行者”。求对为题本已新颖,以说部《西游记》虚拟人物为题更是闻所未闻,一时引起议论纷纷。资料显示,陈寅恪拟定的下联(标准答案)为“胡适之”,周祖谟(今北大教授)、张政烺(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等人都答“胡适之”。可是当陈寅恪看到有人答出“祖冲之”时,不禁击节赞叹[11]58。这一神思奇想或许偶然,却也全在与《西游记》的冥冥因缘。
其二,论定《诗话》为“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关于《诗话》的文体意义,王国维指出:(《诗话》)三卷之书,共分十七节,亦后世分章回之祖。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其有词有话者,则谓之词话。章回小说后起于文言笔记体小说,但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最大宗。对于两者的递嬗演变,涉及中国小说发展规律,学界一度迷茫不解,学者所论吞吐。现在天赐奇书,《诗话》的文体特征一目了然:内容系玄奘取经,文字以故事为单元分节排列,每节附有标题,其间有诗有话(“话”即散文体故事),正与章回小说文体侔合。故逆向言之,《诗话》既为“后世分章回之祖”,则章回小说的源头在《诗话》无疑。章回小说“文备众体”(即包容诗、词、曲、赋等各类文体)的文体特征,也可从《诗话》找到相关的因子。这一“文学——学术之谜”的解决,完全基于王国维的发现和论述,也堪称《西游记》研究对中国小说学的一大贡献。
这一考证意义重大。首先是争鸣不断,异见迭出,俨然成为一个严谨的学术命题。鲁迅于20年代初率先提出异议,认为《诗话》是“元刊”。理由是时世“逮于元朝,张家或亦无恙,则此书或为元人撰。”[1]9730年代,郑振铎在《宋人话本》里依循王说定为宋刊;鲁迅又专门著文反驳,重申为元刊[3]176。时至今日,或曰宋(南宋)刊,或曰元刊,有人前推为北宋[4]413,更有人大幅推进断为“晚唐五代时寺院俗讲的底本”[5]。其次,王国维所作《诗话》版次的考证对《西游记》成书研究有直接关系。《西游记》从史实到小说有几近千年的演化史,但其文学形态的发生当在何处,机制如何,因文献所限,竟是无可论断。现在可知,无论是宋刊、元刊,抑或是“晚唐五代的俗讲话本”,《诗话》都早于元明时的《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和各种《西游记》简易小说,而衔接在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辩机执笔)和慧立、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部史传之后,成为由史传记载到文学创作的过渡形态,最早的“西游”文学作品,从而构成《西游记》的“先声”与“祖宗”,史传(以《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主)→《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平话→简易《西游记》小说→百回本长篇巨帙《西游记》这一完备的演化(阶段)排列得以确立。
据此,《诗话》是这一时期《西游记》研究最重要的文献发现,王国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1915年)是目前所见20世纪最早的《西游记》研究论文之一。
(二) 关于《长春真人西游记》
世本《西游记》问世时,作者佚名,“不知其何人所为”,后被误植至元初道祖邱处机(邱本作丘,因避孔子讳改)名下。究其缘由,是邱处机曾著有《长春真人西游记》(其弟子李志常执笔),备载其游历西域时所见道里风俗,凡二卷,藏于《道藏》中,惟两书同名,且邱著“世鲜传本”,故而后人不察,遂误为一书。清高宗乾隆六十年(1795),乾嘉学者钱大昕首度从苏州玄妙观《正统道藏》中抄出,真相始白于天下。
又及,胡适是现代学界领袖,除了学术成果丰硕,还善于擢拔后学,网罗俊才,故有“独为神州惜大儒”(陈寅恪语)的美誉。新红学殿军周汝昌,《水浒传》名家罗尔纲,都因胡适的赏识、培养而暴得高名。涉及《西游记》,则有胡适援手钢和泰,钢和泰“指引”胡适探寻孙悟空来源、首倡“印度佛经说”之事。
其一,厘清《西游记》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两书关系。20年代初期,鲁迅写成《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写成《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已初步论定《西游记》的作者为淮安儒生吴承恩,其中褫夺邱处机著作权的主要依据是钱大昕发现的道藏本《长春真人西游记》及其所写跋文,羽翼者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中的一则材料。然而,其时“邱作”说惯性巨大,《长春真人西游记》又属阳春白雪,藏匿深闺,知者甚少,小说《西游记》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两书混淆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王国维对《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整理和普及,在厘清两书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为鲁迅、胡适的《西游记》作者考证提供了佐证。
其二,为研究《西游记》与全真教之关系提供文献史料。《西游记》与邱处机无关,却与王重阳、邱处机的全真教有莫大关联。《西游记》虽叙佛教故事,但间有大量金丹术语,道家典籍,及全真七子诗篇,道教气场强烈,当是事实。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会通、交融,“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元来是一家”。作为传统文化载体,《西游记》的价值在于对中国主流文化的深度契合,其反映宋元以来道教主流全真教文化合情合理。《长春真人西游记》是全真教的原始典籍,也是《西游记》宗教文化研究,特别是《西游记》与全真教之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文献。从《西游记》学术史看,从柳存仁《全真教与小说〈西游记〉》到李安纲《苦海与极乐》,这些《西游记》宗教(全真教)研究的重要成果,都多得其襄助。全真教成为《西游记》研究的新领域,竟自王国维肇始,开垦之功,嘉惠后学,善莫大焉。
应予指出的是,无论是发现、研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还是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都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为现代《西游记》研究构筑基础,其学术“正能量”罗列如上。然而,因为没有直接深入《西游记》文本,长期以来,王国维《西游记》研究的范式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对《西游记》研究的意义可能为其“国学大师第一人”的声望所遮蔽。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范式)被历史遗漏,“遂成绝响”,在红学史上“极值得惋惜”[6]314。同样,王国维《西游记》研究“范式”的“被遗漏”,在《西游记》学术史上无疑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二、胡适:由痴迷到“发疯”
胡适痴迷古典小说,20世纪20年代集中考证小说名著,相继写成《〈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三国演义〉序》《〈镜花缘〉的引论》《〈儿女英雄传〉序》等考证文章,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构成现代学术史上的“考证性范式”,被学界誉为“善于给小说作考证的胡适之先生”。这种“痴迷”和“考证性范式”在《西游记》表现得尤其充分。
首先看其研究《西游记》的过程。胡适曾记述:
民国十年十二月中,我在百忙中做了一篇《西游记序》,当时搜集材料的时间甚少,故对于考证的方面很不能满足自己的期望。这一年之中,承许多朋友的帮助,添了一些材料;病中多闲暇,逐整理成一篇考证,先在《读书杂志》第六期上发表。当时又为篇幅所限,不能不删去一部分。这回《西游记》再版付印,我又把前做的《西游记序》和《考证》合并起来,成为这一篇。[2]6
成功的班主任平时不仅注意从观念上引导学生向真善美靠拢,从行为上引导学生积极向上,更会抓住时机,从心理上让学生感受到忙碌机械的学习生活中的友情、师生情,让他们的心理是暖的、软的,他们就会有归宿感,集体认同感,有信任感、幸福感。他们就会想让这个集体更好,并会为之全力付出,于是良好班风就会形成,也就间接省了班主任的很多工作。
这段话告诉我们:胡适的世纪雄文《〈西游记〉考证》实为渐次累积而成:先于1921年为上海亚东版新式校点本《西游记》写成《西游记序》,发表于《亚东图书馆馆刊》(1921年12月);紧接着于翌年在“病中多闲暇”之际,根据鲁迅、董作宾、钢和泰等人提供的新材料写成《〈西游记〉考证》,发表在当年《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6期;后来又于1923年乘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西游记》之际,把前述两文“合并起来”,遂成今日所见之长文《〈西游记〉考证》。该文收入《胡适文存》(四),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初版,又载于《读书杂志》民国二十年(1931年)。胡适考证《西游记》持续三年,年年修正,篇篇出新,乐此不疲,达到痴迷的境地。
胡适《西游记》研究的实绩,即“考证性范式”的具体贡献,如考定《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首倡《西游记》“游戏”说,推断孙悟空原型为印度神猴哈努曼,皆为前人未发之论,至今早已世人习知。特别是以如椽之笔横扫“谈禅”“证道”一类明清旧说,直接推动《西游记》研究的现代转型,其意义与推倒“旧红学”、创立“新红学”异曲同工,影响延绵不绝,学界至今奉为圭臬。而作为胡适《西游记》研究的特殊贡献,也是其“考证性范式”的补充,其亲自操刀改写“第八十一难”之事却鲜为人知,值得回味。关于兹事缘起,胡适有专文《〈西游记〉的八十一难》记载:
十年前我曾对鲁迅先生说起《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九十九回)未免太寒伧了,应该大大的改作,才衬得住一部大书。我虽有此心,终无此闲暇,所以十年过去了,这件改作《西游记》的事终未实现。前几天,偶然高兴,写了这一篇,把《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完全改作过了。[3]266
据该文文末所署时间为民国二十三年,即公元1934年,十年前即1924年,正是胡适写定《〈西游记〉考证》长文(1923年)不久。在持续三年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西游记》文本存在一些纰漏,为这部名著之微瑕,其中第九十九回所叙唐僧师徒求得真经返回东土途中,被通天河大白赖头鼋打入江中一难(第八十一难)太过谫陋粗糙,有凑“九九归真”之数的嫌疑,与前述八十难(包括清初汪澹漪增补之前四难)决不相配,因而在结构上虎头蛇尾,欠缺平衡。这一意见大约曾得到鲁迅的赞同。约十年后,他完成改作并应当时的《学文月刊》之邀公开发表。查该改作文本,胡适旨在弥补《西游记》结构“虎头蛇尾,欠缺平衡”的弊端,从“玉兔烧身”“扫(三兽翠堵波)塔入梦”“割肉布妖”等内容看还带有着力美化唐僧形象、强化作品佛教教义的主观意念。作为文学创作,其成败得失殊难定评[7]。然作为学术现象,这无疑是一段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佳话。从中也可看出胡适的学术兴趣和志向——对于《西游记》,由痴迷而“发疯”。
为了解本次强降水发生前大气中的水汽垂直分布和能量变化,以及高低层风场的配置情况,制作沿30.6°N的相对湿度RH、相当位温θe以及水平风场(u,v)的剖面(图3)。θe的垂直分布可以反映大气的对流性不稳定,当大气层中的θe随高度减小时,整层空气抬升后,大气层表现为整层位势的不稳定;反之,θe随高度增大时,整层空气抬升后,大气层能量将会变得更加稳定。
众所周知,胡适遍考章回小说,但都止于学术研究一途,即使是开创新红学的《〈红楼梦〉考证》也是如此。唯有《西游记》,既有反复考证(凡三次),又有创作,增改文本。胡适曾说过中国小说经典是“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小说研究是一番“大事业”,“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他从事小说考证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胡适自称为“发疯”——,或应景之需(如接受出版界的要求),而是满足自己的“两种老毛病”——“历史癖与考证癖”,像阎若璩、王念孙那样,采取乾嘉朴学考据、训诂等传统的治学方法,文史结合,文史互证,从事的是纯粹的学术活动[8]380。然而,其改作《西游记》第八十一难却是名副其实的“发疯”,不是什么“历史癖与考证癖”,而是创作癖。1920年8月,胡适撰《〈水浒传〉考证》怒斥金圣叹的评改“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言犹在耳,自己却欣欣然改作起《西游记》来,不是“发疯”是什么!
“目前的科研结果来说,统一还是认为生酮饮食只在短期内对于减肥有一定的帮助,但是长期的话,对身体健康肯定是有害无益的。”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副会长陆雅坤表示,在她的客户中如果有人提出生酮饮食的要求,她也会定制短期的低碳水饮食方案,时间最长不会超过三个月,“要在严格控制之下进行,还要配合运动,作息、饮食各方面的调整。”
作为“五四”新文学旗手,胡适以新诗见长,鲁迅因小说卓著,故而对这次属于小说创作的《西游记》改作的价值评估,胡适有自知之明,甚至缺乏自信。在改作写就之际,胡适自嘲称“伪书”,而后来亚东版《西游记》再版时,他也不愿意将这一改作插入到原本中去,致使所作之文备受冷落,几成绝版。在胡适文学生涯里,改作《西游记》第八十一难并非理性之举,扬短避长,其实堪比滑铁卢,但其中可看出他对《西游记》超乎寻常的痴迷。由痴迷而“发疯”,则令后人唏嘘、赞叹。这里的“痴迷”和“发疯”绝无贬义,因为其中正显示出胡适《西游记》研究的强大动因和恣肆汪洋的学术个性,他的卓越成绩和“范式”都由“发疯”催生,都是其学术个性使然。事实上,正是由于胡适的青睐,《西游记》研究在其时奇峰突起,有直逼“新红学”之势,成为现代小说研究的重要一翼。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开始整理蒙元史籍,择取文本即有邱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1925年亲手从道光《连筠簃丛书》杨尚文校本抄录,可见出其对该文本的重视。他利用辽金宋元明五正史以及《大唐西域记》《元朝秘史》《南村辍耕录》《西使记》等各类史籍文献,对书中元蒙人物、史实和西域地理、风俗详加注释、考订,又对原刊本所有讹误错失、衍乙脱漏之处进行了全面校勘,较之《连筠簃丛书》本堪为脱胎换骨,质量精益求精。至1927年,历时二年有余,数易其稿,《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定稿,由清华大学研究院正式出版。作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善本,其对《西游记》研究的贡献如下。
钢和泰(1877—1937),俄国贵族,著名汉学家,擅长梵文,早年只身徒步考察印度,对印度佛经产生兴趣,继而扩展至藏汉佛典。1916年来华研读梵藏汉佛经及回蒙文献,恰逢十月革命推翻帝俄,家破人亡,财产籍没,遂因生活困顿而滞留中国。胡适等学界名流及时援手,为其谋求教职,度厄解困,胡适甚至还为他的学术演讲充任翻译。期间两人论学频繁,切磋相契,钢和泰向胡适学习中国文化,胡适向钢和泰学习梵文,互多教益[9]。尤其是钢和泰精通梵藏汉佛经,对《西游记》传主玄奘大师所译佛经有深入考辨、专研,胡适研究《西游记》从钢和泰那里得到“指引”,并无奇怪。
在《〈西游记〉考证》中,胡适劈首说:“这一年中,承许多朋友的帮助,添了一些材料……遂整理成一篇考证。”据文献显示,这“许多朋友”主要是鲁迅、董作宾和钢和泰。关于孙悟空原型,胡适说:“因此,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罗摩衍那)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这就是《西游记》学术史上关于孙悟空来源两大对立学说之一的“印度佛经”说(另一是鲁迅“本土文化”说)。胡适援手钢和泰,钢和泰对胡适的《西游记》研究有启予之功,学界一向传为美谈。
三、陈寅恪:原型研究的渊源学意义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彻古今的匡世奇才,其文史著述“字字精金美玉”(吴宓语),凡登坛演讲,常有大牌教授入室旁听,故有“教授的教授”之令名。陈氏治学广博,精华在东方学和佛经考订,精通梵文、巴利文、突厥文、中波斯文等“珍稀——已死”语言,《西游记》论著不过是其“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专题研究的衍生品。然而究其对玄奘弟子的原型考稽,竟是开辟了《西游记》渊源学研究的新领域,成为现代学术中最具典范性和影响力的成果之一。
至20年代中期,陈寅恪展开“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课题研究,择取文本即有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并先后写成一组与《西游记》相关的论文:《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敦煌本维摩吉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考释序》等。其中以《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引文均出此文)最为重要。该文对《西游记》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录其大端如下。
在有压输水管道中,由于流速的剧烈变化和水流的惯性而引起一系列急骤的压力变化和密度变化,称为水锤。水柱分离是管流中出现空穴(空管段)时的一种水击现象[6-15]。
其一,1927年,陈寅恪任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课程,内含“佛学校勘——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其缘起即在“发现以前玄奘之翻译,错误很多,不如鸠摩罗什找几个懂他意思的中国人译得好。原因是玄奘都用意译,而鸠摩罗什于意译困难时则用音译。”(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著作》,台湾《传记文学》1970年16卷3期)。《西游记》记载玄奘取回真经三十五部,涉及佛经多达四十四种[10],必然引起他的注意。特别是《心经》因《西游记》而普及天下,陈寅恪更是专门著文《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校勘讹误。
其三,考定《诗话》为宋椠。王国维对《诗话》卷末(款一行)“中瓦子张家印”作了详尽考证。主要证据引自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关于宋代杭城瓦舍和书肆的记载。推断中瓦子为“宋临安府街名”“倡优剧场之所在”,张家印系“张官人经史子集籍铺”印章,则《诗话》为弥足珍贵之“宋椠”,其创作和成书在两宋间。
陈寅恪在“副业”收获杰出成绩并非偶然。《西游记》记叙唐玄奘西天取经故事,佛教徒尝有“《华严》别体”之誉,陈氏以印度东方文化和梵汉藏佛经为研究中心,即与《西游记》结下了不解之缘。兹有二事足见其对《西游记》怀有特殊的兴趣与机缘。
首先,考稽玄奘三徒原型,揭橥故事渊源及演变。《西游记》唐僧师徒四人,惟玄奘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两《唐书》本传和《高僧传》所记甚详,悟空、八戒、沙僧都属虚构,其原型和故事来源多有不明。陈寅恪从众多佛教经传中考出:(1) 《贤愚经》壹叁中顶生王升天争帝因缘故事与“闹天宫”故事雷同,印度史诗《罗摩延传》(今译《罗摩衍那》)中工巧猿造桥渡海神技与美猴王探险水帘洞、上天入地诸般故事相似。两者捏合,当是“《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故事之起源。”(2) 义净所译佛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叁所载牛卧苾刍惊犯宫女和天神化大猪故事,与猪八戒调戏嫦娥、化为猪身眸合,当为“《西游记》猪八戒高老庄招亲故事之起源。”(3)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壹描写莫贺延碛(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流沙景象必为《西游记》八百里流沙河之蓝本,“即《西游记》流沙河沙和尚之起源”。这三大考证结论除第三例胡适《〈西游记〉考证》已论及,为“世人习知”外,皆为陈寅恪首度在佛经中发现。
由上可知,陈寅恪的《西游记》原型考稽具有开创性,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后来,胡怀琛、赵景深、许郭立诚等人相继赓续这一研究,分别从印度佛经和敦煌变文中勾稽出许多《西游记》的人物和故事原型,致使《西游记》渊源学研究云集景从、新论迭出。
再次,探索、阐发佛经与小说的关系。陈寅恪不仅从佛经中勾稽《西游记》人物原型,总结其演变规律,还进一步将其上升为理论研究,探索佛经与小说的关系,揭示小说文体的佛教源头和嬗变机制。其中犹可注意者有二:其一,陈寅恪认为中国章回小说的文体生成存在多元源头,神话、文言笔记的影响为人注目,而佛经与小说的关系遭到忽视,“此为昔日吾国治文学史者所未尝留意者也”;其二,陈寅恪根据佛经与小说多方对读互勘,寻找到大量两者间的“对应点”,断定佛经的故事必然为小说吸纳,其形式——韵散互用之体——也必然为小说所沿袭。具体为:佛经中以散文体为主间夹诗歌者,蜕变为章回小说,以韵文体为主间夹散文或散韵合体者,则演为弹词、鼓书之类。总之,从佛经与小说的关系看,“益可推见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及其嬗变之流别”(陈寅恪:《敦煌本维摩吉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
其次,原型研究的渊源学意义。陈寅恪的原型研究具有自觉的渊源学追求。他说:“若能溯其本源,析其成分,则可以窥见时代之风气,批评作者之技能,于治小说文学史者傥亦一助欤?”运用佛经文献“溯其本源,析其成分”,或说“考其起源,究其流别”,概括了陈寅恪渊源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其“三重证据法”——倡导以“异族之故书”“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在小说研究中的具体表现。所以,对玄奘三弟子的溯源例证,其渊源学意义不限于人物自身孤立的考证,而是相应地代表着小说“故事演变之公例”,文学原型演变的普遍规律。要而言之表述为“三公例”。 一曰:仅就一故事之内容,而稍变易之,其事实成分殊简单,其演变程序为纵惯式(沙僧) 。二曰:虽仅就一故事之内容变易之,而其事实不似前者之简单,但其演变程序尚为纵惯式(猪八戒) 。三曰:有二故事,其内容本绝无关涉,以偶然之机会,混合为一。其事实成分,因之而复杂。其演变程序,则为横通式(孙悟空) 。三例由简而繁,囊括纵横两个流向,由个案追溯、分析总结小说“故事演变之公例”,也即原型演变的普遍规律。因为三例皆有事实印证,且考释翔实,不仅耳目一新,而且极富说服力。正是陈寅恪的独特视野和治学实绩,使其时的渊源学研究别开生面,直接推动了小说(文学)渊源学的形成。
四、结语:大师的当代启迪
当下,大师渐行渐远,成为世纪性的经典令人缅怀。结合当今学术环境和现状,昔日大师们的学术成果、治学精神和学人品格,更富有启迪和昭示的意义。
其一,开创“范式”,指引后世学术路径。所谓“范式”,指的是那些凝结卓越成绩,为后学导夫先路,提供线索和范本的治学模式,其意义在于以新颖的、带有根本性的原则和规则引发一个时代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变革。大师是人文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楷模,恪守“为学术而学术”,不受教条禁锢和世俗羁绊,故能摒弃旁骛和偏见,专注学问,发挥神思,抒发新知,创建学术范式。纵观《西游记》研究,硕果累累,“范式”繁富,成为现代学术一道绚烂风景。
王国维:外部研究——整理文献,构筑基础;胡适:考证——论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考辨史实;鲁迅:史论——与胡适共同论定作者,将《西游记》命名为“神魔小说”,实现文学史定位;郑振铎:演化——梳理故事演化轨迹,列定版本次序;孙楷第:版本目录学——搜寻珍稀古本,考定各版优劣,推定世本为《西游记》之最早版本;陈寅恪:渊源学——从梵汉藏佛经中考出《西游记》主要人物原型,推出小说“演化之公例”;赵景深:民俗学——揭示文本民俗文化传统;刘修业:作者研究——撰写吴承恩年谱、小传。
此外,袁圣时的神话学研究、汪浚的学术史研究,以及陈独秀的阶级论观点都在当时曾产生过较大影响,带有一定的范式意义。关于《西游记》学术范式的具体内容,值得专题研究,这里不作赘述。只是需要指出:“五四”前后中国学术的巨大转型,就是从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变革开始的。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寅恪等大师的《西游记》研究正是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遵循不同的学术方法、原则和路径,并以各自的开创性成绩昭示了一种共同的带有革命性和示范性的学术精神、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考察、重温这些“范式”,大师们创获如此辉煌的学术成果,为后人留下如此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借鉴的范本,其神采风韵怎不令人陡生崇敬之心、感激之情!
阿花见我领回一支十来个人的精兵强将来,眼里放出异样的光芒,大声说,我们赢了。后来有个人告诉我他们离开大发厂的真正原因,说大发厂工价跌了,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其二,恪守学术公器理念,培育学人品格。“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人皆不可得而私之。”这一学界古训正是昔日大师们恪守的学术理念,他们以追求学问、探索真理为终极目的,孜孜矻矻,带宽不悔,不结党类,不计私利,不弄虚作假,不汲汲于功名,在《西游记》研究中表现出宽宏的学术胸襟和高尚的学者品格。究其琦言懿行,不胜枚举。
(3)在天然气锅炉中,由于增设冷凝式节能器后,其烟气内的水蒸气得以冷凝而释放出大量汽化潜热,其热量占比可达高位热值的10%左右。并且,在冷凝水侧,烟气内的酸性气体与温室气体直接溶于冷凝水中,降低直接排放至大气中造成的环境影响,可同时达到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作用。
例如:胡适与俞平伯在红学是盟友,共创“新红学”学派,但在《西游记》竟成对手,在《西游记》作者问题上尖锐对立。胡适论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并成一时信论。俞平伯却著《驳〈跋消释真空宝卷〉》一文,反对胡适在《跋》文里重提“吴著”说,成为最早的驳难者和早期“非吴派”的主要代表。胡适于俞平伯有师友之谊,俞平伯秉持的是“学术至大天下为怀”的精神,体现出“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学者风骨。
酯类化合物是构成酱油风味的主体物质,在酱油中起着香甜、浓郁而柔和的基底作用。如表3所示,本试验共检出 12种酯类,其中乙酸乙酯所占比例最高,其相对质量分数高达3.359%,具有强烈的水果香气,能使酱油香味更为醇厚,对酱油的咸味也有一定缓冲作用,还能平衡酱油的风味[31];不同酯类混合能赋予酱油丰厚浓郁的风味,如月桂酸乙酯具有花生香味,棕榈酸乙酯能产生微弱的果香和奶油香气等,与空白组相比其相对质量分数均大幅度提升,对酱油繁杂的风味具有很大贡献。
再如:鲁迅与胡适共同考定《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携手清洗明清“谈禅”“证道”“说儒”一类旧说,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实际开创者。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互通信息,共享文献,不断磋商讨论,并且都以极大的热情引录和推介对方的研究成果。但在孙悟空来源问题上却分持“印度佛经”说和“本土文化”说。且几度论争,十分激烈。对鲁说,胡适明确表示:“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对胡说,鲁迅也针锋相对:“我以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淮河神猴)。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则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我现在还不能说然否的话。”[1,2]可见,在学术上无论是盟军,还是对手,也无论是激赏,还是驳难,大师们总是以坚持真理为指归,直抒真言,从不因私情颜面而作阿谀之相、吞吐之言。
又如:郑振铎是鲁迅晚辈,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版本问题上因坚持王国维“宋刊”说,受到过鲁迅的“严厉”批评,鲁迅对其学问也似乎持有一些不屑的态度[3]176;然而就《西游记》祖本问题,郑振铎以《永乐大典》平话本纠正鲁迅关于阳至和《西游记传》是《西游记》祖本的观点,鲁迅却主动改变己说采纳郑说,不耻下问,向郑振铎虚心认错,并予以盛赞。
20世纪初叶,学界风云际会,大师辈出。他们创立的“范式”是中国学术的宝贵资源,他们高尚的学人品格是后世学者永恒的楷模,连同他们的名字都业已成为后人翘首瞻望的学术现代化的辉煌“地标”。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 胡适.《西游记》考证[M]//吴承恩.西游记.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3] 鲁迅.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M]//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 王力.汉语史稿: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 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J].徐州师院学报,1982(3):22-30.
[6] 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7] 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8] 胡适.《水浒传》考证[M]//胡适.胡适全集·卷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9] 钱文忠.男爵和他的幻想:纪念钢和泰[J].读书,1997(1):49-55.
[10] 曹炳建.《西游记》中所见佛教经目考[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79-82.
[11] 王子舟.陈寅恪读书生涯[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
Paradigm Innovation of Modern Academic Masters :Centering on the Study of Journey to the West
ZHU Hongbo
(Dep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cademic landscape and ecology of the forum of Journey to the West gathered by the great master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y, focusing on the causes, processes, achievements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Wang Guowei, Hu Shi and Chen Yinke to the study of Journey to the West , and reveals the enlightenment and revelation of the academic ideas, academic spirit and personality of the great masters to the current academic circles.
Key words : modern Chinese academy; masters; Journey to the West ; innovation of academic paradigm
中图分类号: G316; I207.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333X( 2019) 08- 0032- 06
收稿日期: 2019- 05- 10;修订日期: 2019- 06- 10
基金项目: 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WY003)
作者简介: 竺洪波(1958-),男,浙江嵊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西游记》学术史方面的研究。
DOI: 10.3969/ j.issn.2095- 333X.2019.08.009
(责任编辑:徐习军 实习编辑:赵 宁)
标签:中国现代学术论文; 大师论文; 《西游记》论文; 学术范式创新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