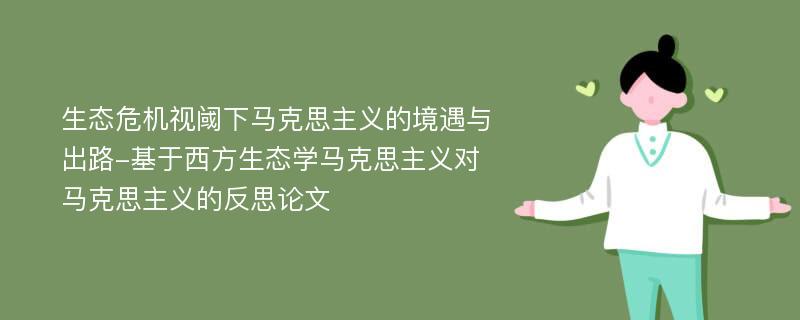
生态危机视阈下马克思主义的境遇与出路
——基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姚晓红
摘要: 在生态危机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经典,在西方现代生态理论研究中备受争议。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生态问题为关切点,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系统反思。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问题,他们或阐释或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形式的诊断,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各具特色的解读;在肯定生态原则与社会主义一致的基础上,他们探索了一系列社会实践方案。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展开的反思既有其合理因素,也有不可忽视的内在缺陷。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思潮对于我们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有效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关注生态问题、批判生态危机、追求生态正义,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共同关注和探讨的焦点。在西方社会繁多复杂、流派纷呈的绿色思潮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思潮,他们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其理论分析的重要前提,对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反思视域宽泛、内容深刻,从哲学到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从批判到建构等不同维度进行了探讨与争论。其中,重点围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具有生态视域,他们或进行了详细阐释,或进行了生态维度的重构;围绕当代资本主义主要危机的表现,他们提出了“危机替代论”、“双重危机并存论”等一系列新理论;围绕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他们在肯定社会主义与生态原则相一致的基础上,围绕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设想。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颇丰,或是重点介绍个别学者的观点,或是分别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某一独立视角进行专门研究。然而,我国学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还相对缺乏更加系统的分析。本文尝试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评析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多角度反思。这一理论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把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正确分析和评价这一思想流派,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国化,特别是对于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反思
在当代西方生态理论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了严厉的生态质疑和批判。其中,特别是针对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承认“自然限制”、技术,物质生产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等问题,西方学者展开了激烈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反驳了西方环境保护主义学者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和质疑,有效地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而且,他们又进一步或阐释或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思想,并将其作为开启自身理论视域的逻辑基础和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理论前提。
初到西点军校的时候,我只有22岁,是系里最年轻的讲师。当时二战已经结束,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场刚开始的盛宴。
一些西方绿色思想家, 如约翰·克拉克 (Jhon Clark)、 维克托·弗金斯 (Victor Ferkiss)、 罗宾·艾克斯利 (Robyn Eckersley)等人,曾经公开指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严重缺乏生态思维,认为生态问题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得以解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也被视为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和“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代言人。比如,克拉克就认为,“在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视野中,……他是一个把自然置于他的自我实现的、不可征服的超自然存在物。……自然无法控制的内在形式和外在自然的威胁形式都必须被征服。”(1) John Clark. Marxs’ Inorganic Body. Environmental Ethic ,Vol.11,No.3,1989,p.258.罗宾·艾克斯利在《环境保护主义与政治理论》中也评论道,马克思彻底沉浸在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信仰之中,并将其作为人类为取胜和征服自然的手段。针对西方绿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批判和指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在其理论阵营内部产生了重大分歧。
然而,与此同时,以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r)、泰德·本顿(Ted Benton)等为代表的少数学者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比较少地或是明显地缺乏生态关照,因此,需要从生态学视角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主义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视域,但却较少地关注生态问题。如其所言,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劳动过程中缺乏一种自然理论,“马克思本人很少对自然界本身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5) 詹姆逊·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在此基础之上,奥康纳从文化和自然双重维度对“生产力” 、“生产关系” 、“劳动”三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进行了全新阐释和界定,继而重构了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其开展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本顿也公开指责马克思主义严重缺乏生态考量。在本顿看来,马克思过度崇尚科技进步和生产发展,片面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因而是典型的生产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者。对此,本顿还将《共产党宣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经典文本视为马克思推崇技术理性主义的重要证据。正如其在反驳保罗·伯克特的文章中所指出的,“至少可以理解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普罗米修斯主义和生产主义的表述和版本已经被规律性地运用作为他们文本的基本原则……这些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读本(《共产党宣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是真实的、证据确凿的文本论据。”(6) Ted Benton. Marx, Malthus and the Greens: A Reply to Paul Burket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8 ,No.1,2001,p.335.另外,本顿特别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展开了严厉的生态指责。在本顿看来,马克思过度强调手工业、工业等生产型劳动,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能动改造而忽视劳动过程对自然条件方面的限制(7) Ted Benton.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 An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New Left Review ,No.178,1989,p.64-65.。进而,本顿将劳动概念区分为“生态规制型劳动”(eco-regulatory labor process)和“生产型劳动”(reductive, transformative labor process)。在此基础上,本顿主张放弃“生产型劳动”、重视“生态规制型劳动”,用“适应自然”的概念取代“支配自然”等,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进行了重构。
休斯在《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也深刻阐释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思想。他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和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是有机统一的,不能因为其强调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而否认人对自然的依赖。并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解读,休斯反驳和批判了相关学者对马克思无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承认“自然限制”等相关指责。同时,休斯还进一步考察了技术发展与生态问题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发展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等问题。在休斯看来,技术发展会带来不同的生态效应,既可以加剧生态问题,也可以减少生态问题。按照休斯的理解,马克思还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新社会发展以及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福祉的必要条件。因此,休斯指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特别是其关于生产力的相关论述,可以看作是对当代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解释(4) 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6页。 。
与福斯特有所不同,格伦德曼详细解读了“支配自然”的积极含义。他强调,否认马克思主义具有生态思维的人实质上并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自然观。这是因为,支配自然不等同于绝对地统治自然,恰恰是由于人们没有合理地支配自然才造成了生态危机。并且,在格伦德曼看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能够合理地调整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因而理性成熟地利用和改造自然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特征,“只有一个能够将其自身活动控制在自然环境中的社会才能够称之为共产主义”(3) Reiner Grundman. Marxism and ecology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11.。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保罗 ·伯克特(Paul Burket)、瑞尼尔·格伦德曼(Rainer Grunndman)、乔纳森· 休斯(Jonathan Hughes)等多数学者肯定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生态意蕴,并从不同视角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原则进行了详细阐释。比如,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不仅承认自然限制、坚持自然本体论,而且注重将自然本体论用于指导人类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而且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福斯特指出,尽管生态危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表现得还不是特别明显,马克思也没有将其作为导致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关于创造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的思考却是稍后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论证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显征。”(2)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对此,福斯特重点研究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根本上导致了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因此,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解,只有通过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能留住食客的味觉记忆,以皮薄、馅丰、汁多、味鲜、形美著称的南翔小笼馒头,在食材与制作技艺方面都很有讲究。小笼皮坯采用多种面粉调和制作而成,每两面粉制作10个小笼包,可见其皮之薄;馅则选用精腿肉,保持肉质之原味,用骨汤熬煮肉皮成冻,拌入馅内,取其鲜美、多汁不油腻的特点。技艺上,采用双杆擀皮,皮子中间厚、四周薄,保证汤水不会流出来,最终小笼馒头呈现宝塔型;每只小笼馒头的收口处打16个以上的褶,小巧精致、玲珑剔透。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争论
众所周知,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其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性的理论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主义危机主要表现为周期性频发的经济危机。马克思重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批判。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系统考察资本的运行过程,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社会原因、主要危害以及如何消除经济危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路径。然而,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特别是无产阶级处境的改善以及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物种濒危等生态问题日益突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否依然奏效?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怎样的地位和影响?以此为背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展开了争论和探讨。
第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偏离。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出发,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生态视角的全新阐释和建构,其争论和探讨进一步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有效地捍卫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应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这一时代课题中的重要价值。特别是在纷繁复杂、流派纷呈的西方绿色社会思潮中,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分析和研究方法,不仅是新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的运用和坚持,并且,这一理论特色又使得其理论分析与生态中心主义等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明显区分开来。他们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多重视角对生态危机进行分析,有效地克服了后者单纯从抽象、空洞的价值论进行分析的理论缺陷,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生态危机的理解。然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又没有彻底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严重的误解和背离。比如,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的文化重构、本顿对马克思“劳动过程”概念的区分,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片面的理解。正如伯克特在批判本顿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本顿对马克思恩格斯详细批判,……依赖于其关于物质/社会的二分法,以及他关于自然条件和限制概念的不恰当的输入。”(24) Paul Burket. Marxism and Natural Limits:a rejoinder. Materilism History , Vol.8,No.1,2001,p.335.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既重视物质的力量又不忽视文化等上层建筑因素。从这一点来看,奥康纳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又与批判现代性思维方式、注重从文化层面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未区分开来。并且,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生产方式等概念的理解是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关系的视角进行的考察和分析,进而赋予社会生产过程,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还是社会主义生产过程,都具有双重特性——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因此,无论是本顿还是奥康纳对马克思的理解,均呈现出明显的机械、片面性特征。这一认识不仅反映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主观分裂的错误传统,实质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背离。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双重危机”并存的时代,其中生态危机占据主要地位。与阿格尔主张的“危机取代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进入20世纪80~9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使得学者们重新意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同时,生态危机的加剧又使得他们重新思考和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奥康纳在其代表作《自然的理由》中,重点围绕“双重危机”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区别、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刻阐述。首先,奥康纳阐述了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由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然而,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由资本主义生产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第二重矛盾”导致的生态危机。在奥康纳看来,正是“第二重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双重危机”并存的基础和前提,而马克思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着重分析了生产关系在经济危机中的重要性,却忽视了生产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虽然马克思对这些生产条件进行了区分,但却没能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10) 詹姆逊·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基于此,奥康纳进一步分析了“第二类矛盾”如何导致生态危机,并详细阐述、对比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分析、危机路径破解等方面的差异。其次,奥康纳详细阐述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充满了危机,其中,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同时并存且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危机导致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不仅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对工人的经济剥削和生理压榨以及成本外化和环境加剧恶化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生态危机又导致经济危机。能源短缺、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条件维护成本的增加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资本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继而容易诱发通货膨胀;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环境保护等新社会运动又可能会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奥康纳指出,伴随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危机。
本·阿格尔(Ben Argurl)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重构,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已经由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在阿格尔看来,首先,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但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却可以发生变化。并且,从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看,资本主义危机是矛盾发生作用的后果,然而,矛盾并不固定的表现为某种特定的危机。阿格尔指出,“我们这样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虽然依然存在,但危机的趋势已大大改变了……虽然这一矛盾依然存在于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其垄断程度如何)之中,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危机的形式只间接与这一矛盾有关。”(8)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18页,第235页。 因此,阿格尔认为,这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理论区分开来,并对其危机理论进行修正。其次,阿格尔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按照阿格尔的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及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化等问题阐述得并不清晰,马克思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趋势,实际上,资本主义危机是可以避免的,资本主义灭亡也不一定是必然的。对此,阿格尔分析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只是指出了危机形成的可能方式而并没有预见资本主义的灭亡,他也不排除资本主义后期出现新的危机形式(9)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18页,第235页。 。最后,阿格尔强调资本主义危机已经由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在阿格尔看来,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等新变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予以关注,因此,重新研究和探讨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形式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路线,就成为阿格尔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总之,正是沿着以上理论逻辑,他们将资本主义危机研究的视角转向了生态危机,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主要危机。
与阿格尔和奥康纳的观点不同,以福斯特和伯克特为代表的学者注重生态危机视阈下人类自身的发展状况。在批判奥康纳双重危机理论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人类发展危机理论。一方面,福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奥康纳致命性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的丰富生态思想,这是奥康纳试图去做马克思在这方面没做成的事情的重要前提。并且,福斯特强调,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详细论述生态问题如何导致经济危机以及如何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但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如何合理地实现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最终力量从来就不在于其经济危机理论,甚至同样也不在于其对阶级斗争的分析,而是更深刻地依赖于其既包括人类史也包括自然史的唯物主义历史观。”(11)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0页,第187页。 因此,福斯特更注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而非经济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在福斯特看来,从根本上来说,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产物,仅仅试图通过经济危机棱镜去考察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只会模糊其本质。另一方面,福斯特否认生态危机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然主要源于奥康纳所谓的“第一类矛盾”。 诚然,资本具有强大的生态破坏力,自然资源的稀缺及相关环境成本的增加确实对资本生产和再生产构成了威胁,但福斯特强调,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资本逐利的本性、不能低估资本即便在生态退化中也具有实现自我积累和再造的能力。因此,生态危机不一定导致经济危机,即生产条件的破坏以及生产成本的上升并不必然将资本推向更可持续的方向。“很少有证据表明,这种成本对当今积累制度整体产生了诸多严重的无法克服的障碍。”(12)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0页,第187页。 在这方面,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也曾指出,资本不仅有着成功解决生态困境的历史,而且,“环境灾难为‘灾难资本体制’创造出获得丰厚利润的大量机会。……资本从来就不畏惧为了逐利而摧毁人类。”(13) 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77页。
三、关于未来社会替代方案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理论,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趋势,系统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并详细阐释了如何依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夺取革命胜利的方法和步骤。然而,这些论断对于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有何意义和价值?生态诉求与社会主义原则是否相一致?如何实现?针对以上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展开了探讨。一方面,他们从生产方式、文化、政治等多维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旗帜鲜明地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他们又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普遍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其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困境的路径选择和理想社会模式。他们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既彰显出一定的共性,又呈现出各自的理论特色。
金安区耕地级别整体较高,主要是因为其属于六安市市辖区,交通发达,路网密布,城镇化较高,地区基础建设完备。全区80%为中壤,土壤黏性不强,耕性较好,可耕种时间长,对肥力与水分的保持功能较好。但是其自然地力等级不高,有机质、氮磷钾、锌铜硼铁等大中微量元素含量不丰。但此次耕地定级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与区位因素。根据特尔斐法专家打分,社会经济因素与区位因素所占的比例远大于自然因素。而这两项正是金安区的优势所在。
然而,关于生态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又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一方面,阿格尔、本顿、奥康纳等学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替代”。由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生态学的空缺或不足,进而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生态视角的重构,因而,其所宣扬的生态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对此,福斯特总结到,以上这些早期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称之为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将生态思想“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以弥补其生态理论的空缺,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被视为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替代。另一方面,福斯特、伯克特等人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不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替代,实质上是后者在生态实践层面的运用。他们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并将生态实践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我们通常都受到误导,认为生态属于社会主义的异常之物;其实远非如此,它从一开始就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7)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0页。 。因此,在他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指的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割裂,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兴。
初诊2型糖尿病是临床常见的内分泌综合征,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或抵抗致病。临床发病率较高,如不及时控制病情,则极易合并肾病、眼病等,严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及生命健康。故科学有效的治疗措施对患者尤为重要。
首先,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主义与生态原则的一致性。长期以来,西方绿色环保主义者将社会主义视为唯技术论或生产力理论,特别是针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导致的生态问题,他们一味宣扬社会主义与生态原则的对立。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予以否认并进行了积极反驳。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在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基础上指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不以获利为目的,它建立在对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因而,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是绿色的(14) 戴维·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7页。 ,能够将生产发展、满足人类需要与自然有机统一起来。奥康纳在其经典著作《自然的理由》中指出,生态原则与社会主义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只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的解释忽视了其“自然的特征”。他通过比较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环境退化的原因指出,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曾经出现严重的生态问题,但二者导致生态问题的原因是不同的,其中,产权和财产关系、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因素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发挥着不同作用。在奥康纳看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体制问题,而非经济体制问题。由此,奥康纳指出,环境退化并非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协调一致的。伯克特也指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对自然条件的占有、支配等都呈现出社会性,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的社会性分离以及这些生产条件与自然之间的分离,从根本上导致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15) Paul Burkett.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dtiv . St. Martin’s Press, 1999,p.11,p.224。。然而,共产主义社会中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将避免这种分离。“马克思勾勒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丰富关系的蓝图,它建立在亲生态和亲人类的系统之上,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变革而实现。”(16) Paul Burkett.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dtiv . St. Martin’s Press, 1999,p.11,p.224。
其次,围绕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理论探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暴力的方式,“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然而,面对当前资本主义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革命理论是否依然奏效?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争论。总体来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不主张诉诸革命暴力手段,但围绕社会变革的重点内容,他们分别从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各持己见。
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Willian Leiss)等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强调消费观念、价值理念等文化变革的作用。他们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消费现象进行批判的传统,强调技术的理性应用以及合理消费价值观的构建。比如,莱斯在《满足的限度》中探讨了需要与商品消费之间的关系,强调过度消费并不能真正满足人的需求,反而导致消费异化。并且,莱斯强调这种高消费又是建立在追求利润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经济制度促使商品消费成为满足人的需求的唯一手段。“这一社会实践的实际形式是我们称之为高强度市场架构的东西,它导致鼓励个人将其需要单一地诠释为对商品的需要的状况。”(19) 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商务印书馆, 2016年,第 115页。 对此,莱斯主张构建一种“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它以较少的生产和需求为主要特征,以此引导人们调整自身的需求观。“如果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目标是降低商品在满足人类需要中的重要性,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均能耗与物质需要,则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总体效果就是易于生存社会的形成。”(20) 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商务印书馆, 2016年,第129页。 高兹则强调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性,倡导变革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经济理性”,树立“够了就行”的“生态理性”。
奥康纳则更强调民主国家在生态实践中的作用。比如,奥康纳认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扬弃传统社会主义生态弊端的有效形式主要依赖于民主国家的建立及其民主化的、有计划性的组织和管理。对此,奥康纳一方面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由中央集权管理模式导致生态危机的弊端,另一方面又批判了西方国家流行的地方自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绿色思潮。奥康纳认为,扬弃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矛盾,从政治上来说就是要克服地方主义(或去中心主义)和中心论之间的矛盾,“即存在于自我决定与生产的全面计划、调节和控制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奥康纳明确指出,地方主义和中心论都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行的应是这样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21) 詹姆逊·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5页。 与此同时,奥康纳还将对生产条件的分析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新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城市运动等)结合起来,并将其视为改善生产条件、建立真正民主国家的主要依靠力量。在奥康纳看来,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新社会运动主要是按照自己的物质利益表达自身的政治愿望与诉求,并最终反映到国家政治层面,然而,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最终只能维护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因此,争取改善生产条件的各种社会运动就表现为追求真正的国家民主所进行的斗争。
另外,佩珀、福斯特等人则主张进行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重点的彻底的社会革命。在佩珀看来,要想改变社会及其与自然的关系,不仅要进行思想观念层面的变革,而且更要注重经济变革(22) 戴维·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与此同时,佩珀还将工人阶级视为社会变革中的关键力量,强调要注重发挥工人阶级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作用。福斯特则将生态革命与社会制度革命统一起来,明确将社会制度变革视为实现生态良好的根本途径。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城乡对立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主要后果,其实质是人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形式,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消除这种断裂关系,消除城乡对立。然而,至于如何实现生态革命,福斯特不是从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中寻找希望,而是侧重于从第三世界寻找革命力量。他指出,当今世界与生态运动有关的主要力量和策略主要集中于外围国家,它们处于与资本主义体系联系较少的薄弱环节(23)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刘仁胜、李晶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
四、正确认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无疑激发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进程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着眼于其产生根源、破解路径、理想社会替代方案选择等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为指导人类生态文明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然而,细究开来,这一理论反思又有其内在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困境。具体来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防汛抗旱,关乎民生,历来是长江委“天大的事”。2013年,面对长江流域先涝后旱的灾害形势,在国家防总的领导下,长江委坚持防汛抗旱并重,及早动员部署,密切监视汛情旱情变化,强化应急值守、滚动会商、应急响应和技术指导,共派出24个工作组和专家组深入流域抗灾一线进行技术指导,加强三峡、丹江口等重要水库应急水量调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生产及生态用水,努力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了流域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误解。针对当代资本主义主要危机的表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积极诊断, 特别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他们各抒己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探讨。这些探讨观点新颖、逻辑论证独特,无疑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角。然而,从实质来看,无论是阿格尔的“取代说”还是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实际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一种严重误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集中表现为社会化的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不仅涵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的矛盾,而且内在地包含了生态矛盾。并且,恰是这一基本矛盾从根本上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危机的爆发。尽管相较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后工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更为凸显,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危机的自行消解。他们对生态矛盾、生态危机理论的过度强调和拔高,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淡化。并且,从实践来看,近些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各国间断性的爆发,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再一次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因此,无论是“取代说”还是“双重危机并存说”已经不攻自破。对此,只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辩证、历史的分析,才能真正把握其理论实质,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危机做出正解。
既然拐角那里就站着一个巡警,警察为什么不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呢?既然苏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直言不讳,为什么对方又不举报他呢?这些看似平淡的事实中却寄寓了语言丰富的意蕴:在苏比看来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在警察那里只不过是一件不屑一顾的小事。因为,警察正忙着去搀扶着另一位“不需要搀扶人”过马路呢。这也就是说,警察不管这些在苏比看来是足以使其进入监狱的“事件”是语句的另一重意蕴。
第三,理想社会方案的虚幻性。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有机联系起来,绘制了一幅生态良好的社会变革方案。然而,从实践来看,尽管他们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美好而具有吸引力,然而,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理想,他们的论证严重脱离社会实践,反而有时又抱幻想于资本主义,因而又表现出明显的空想性、软弱性。一方面,他们有意淡化或否定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他们运用阶级分析法方法不仅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还强调了社会制度变革在生态危机破解中的重要性。然而,在具体实践层面中,他们却又轻视或否认阶级斗争在未来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甚至企图依赖新社会运动力量等来淡化阶级矛盾、化解生态危机。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资本主义国家抱有希望。对于如何构建生态良好的理想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甚至还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奥康纳就特别强调民主国家在解决生态问题中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忽视了国家作为特定社会经济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如果没有彻底的社会经济层面的变革,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不仅暴露出其对资本主义仍然抱有期待,而且更显示了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彻底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缺陷注定了其实践方案的流产和失败。
从图4看出,云南省南部边缘的水、陆稻区,滇南单、双季籼稻区和滇中一季粳、籼稻区的多样性相对其他稻区高。说明,水、陆稻稻区和单双季籼稻区以及粳籼交错稻区是稻苗期耐旱性多样性的富聚区。同时也说明生物多样性的表达必须有环境因素,不稳定的生态环境将诱导生物多样性的产生。
与此同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又对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重要启示。
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归。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归就要坚持全面、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和方法。唯有如此,才能对西方生态思想做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才能有效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在人类普遍追求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只有不唯教条、不唯西方国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我国国情有机结合。当前,无论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状况还是我国社会发展实际来看,我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较,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此,我们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和我国国情有机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才能真正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生态文明治理路径。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的讲话中所强调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25)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我们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解读和引领时代,只有用丰富鲜活的当代中国实践来充实马克思主义,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境界(2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另外,我们还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治理自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生态批判与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结合起来,将生态原则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积极致力于生态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可见,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有实现生态文明的显著优势。对此,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治理的制度、理论、道路、文化自信,又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突出优势,切实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并且,在与西方生态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更要积极掌握话语权,积极宣扬和传播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治理方案和经验。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1世纪以来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批判理论研究”(编号:2019040305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7-25
[作者简介] 姚晓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王云川)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论文; 生态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河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