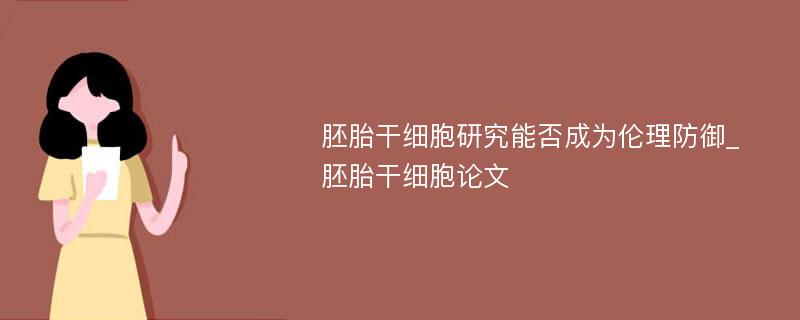
胚胎干细胞研究能否得到伦理辩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干细胞论文,胚胎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5月2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要求政府放宽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改变2001年布什总统关于不允许用联邦经费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做法。但布什总统迅速做出反应,表示将予以否决,不会改变现行政策,并说他的“生命文化”根本没有“多余的胚胎”这回事,认为“为了拯救生命而毁灭生命”是不道德的,强调决不能跨越这条有可能牵涉“摧毁胚胎生命”的“重要的人伦界线”。(注: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5-26。) 联想到2月~3月间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禁止任何形式的克隆人的政治宣言,主要分歧并不在于生殖性克隆而在于治疗性克隆。实际上也就是对胚胎干细胞研究有不同看法。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之争,是当前生命伦理学争论最激烈、最突出的一个领域。
在联合国的讨论中,中国政府一再明确表示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那么,胚胎干细胞研究到底能不能得到伦理的辩护?
一、问题的提出和争论的焦点
1998年10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两项标志胚胎干细胞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大成果。一项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汤姆森(J.Thomson)教授从不孕症夫妇捐赠的辅助生殖多余胚胎中提取胚胎干细胞,建立了人的胚胎干细胞系。另一项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哈特(J.Gearhart)教授从流产胎儿尸体的原始生殖组织中分离出胚胎生殖细胞,建立了多能干细胞系。1999年,这两项成果被《科学》评为1998年十大科技进展之首,并在科学界迅速兴起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热潮。
这种状况,与克隆羊“多利”的问世相当类似。本来,克隆作为无性繁殖,普遍存在于低等生命世界,并不稀罕。蟾蜍等低等动物的克隆也实现了。但科学界普遍相信,高等动物的克隆是不可能的,但“多利”的横空出世却无可争辩地表明:高等哺乳动物的体细胞在一定条件下也能重新编程,并表达出来。于是,科学界为之震惊、兴奋,并迅速兴起“克隆热”。对胚胎干细胞科学界也早有认识,并建立了小鼠等低等动物的胚胎干细胞系。但科学界却普遍以为,人的胚胎干细胞系难以甚至无法建立。一旦成功建立,就好像克隆羊成功一样,一座高山、一条大河被跨越了,科学界怎能不为之震惊、兴奋,并跃跃欲试?
胚胎干细胞最重要也最神奇的是具有“发育全能性”的功能。干细胞是尚未分化的原始细胞,通常分为三类,即全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和专能干细胞。其中,全能干细胞主要就是胚胎干细胞,它能分化成人体200多种细胞类型,形成机体的任何细胞、组织和器官。这多神奇!因此,我曾把它比喻为细胞家族的“神奇小子”。倘能掌握其分化发育的规律,在人工条件下定向分化发育为所需的细胞、组织乃至器官,岂不是可以用来治疗目前还难以或无法治愈的帕金森氏病、早老性痴呆、白血病、糖尿病等顽疾,并且解决十分紧缺的组织和器官移植的来源问题吗?进一步,与克隆技术相结合,运用体细胞核转移技术来得到胚胎干细胞,还能解决细胞治疗以及组织和器官移植的免疫排异难题。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21世纪“再生医学”的曙光,或者说为新的“医学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过,也正像“多利”的降生引发激烈的伦理冲撞一样,人胚干细胞系的建立也带来了新一波的伦理之争。克隆羊的成功意味着“克隆人”在技术上已从不可能变为“现实可能性”,从而不能不触动伦理的敏感神经。人胚干细胞系的建立则意味着干细胞研究将重点转移到人,应用到人的疾病治疗上。这就涉及了敏感而又脆弱的伦理领域。一场尖锐的伦理争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场争论,始终围绕着两个问题而展开:
第一,如何看待胚胎,胚胎干细胞研究是否毁灭生命
胚胎干细胞来自早期胚胎,而从胚胎中提取胚胎干细胞必定会损毁胚胎。胚胎就是生命,就是人,因此,研究胚胎干细胞就是“毁灭生命”,甚至无异于“杀人”。2001年8月,布什总统在梵蒂冈会见教皇保罗二世,教皇一见面就急忙拉着布什的手说:不要资助那些研究胚胎干细胞的人,他们毁灭生命、败坏伦理。此次布什也一再强调,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就是支持“摧毁人类的生命”。
第二,治疗性克隆是否必然滑向生殖性克隆
为了研究胚胎干细胞,充分开发利用其发育全能性的功能,一个重要途径是像克隆羊那样,运用体细胞核转移技术,来得到极早期胚胎,以提取胚胎干细胞。这就是所谓“治疗性克隆”(the rapeutic cloning)。(注:对治疗性克隆这一概念有诸多批评,主要是因为克隆即无性繁殖,克隆一词不可避免地同生殖联系起来,尤其在英语语境中。有人建议按其本义,称为体细胞核转移技术,简称“核移植”。但很深奥,公众难以理解。尤其在中文语境中,核移植之核容易被误解为“核武器”之核。我曾建议称之为“治疗性干细胞研究”。约定俗成,此处从众。我国政府代表在联合国讨论中,也使用“治疗性克隆”一词,其精彩处在于点明了治疗性这一目的。) 可见,治疗性克隆与胚胎干细胞研究密切相关。一些人坚持认为,治疗性克隆必然导致或滑向生殖性克隆(reproductive cloning),因为两者的技术路线是一致的,相差仅一步之遥或一纸之隔。联合国从2001年开始讨论禁止克隆人的国际公约,之所以达不成一致意见,分歧不在于生殖性克隆(都主张禁止),而在于治疗性克隆。美国等国主张同时禁止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认为不同时禁止治疗性克隆就不可能真正禁止生殖性克隆。而禁止治疗性克隆实际上就是要封杀胚胎干细胞研究。
二、对争论分歧的讨论
上述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意见,是十分坚决的。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它直接指向生命伦理学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根据我们的理解,生命伦理学的根本宗旨是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增进人类的健康和幸福。通行的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这四条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既是为了保证这一宗旨的实现,也正体现了生命伦理的根本宗旨。(注:参见沈铭贤主编:《生命伦理学》第一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如果上述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意见成立,那就是说胚胎干细胞研究完全背离了生命伦理学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应该毫不动摇地予以禁止。
我们认为,上述反对意见难以成立,胚胎干细胞研究并不违背生命伦理学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能够得到伦理的辩护。简要讨论如下:
第一,不能简单地把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同于毁灭生命
前面说过,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突破,来自汤姆森和吉尔哈特主持的两项研究。汤姆森的研究对象是辅助生殖多余的冷冻胚胎,而吉尔哈特的研究对象是人工流产下来已经死亡的胚胎。可见,胚胎研究历来就有,并没有被指责为“毁灭生命”。
从1978年7月25日,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布朗在英国呱呱堕地以来,辅助生殖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从第一代试管婴儿到第三代试管婴儿,为上百万不孕夫妇带来了天伦之乐。可是,不管辅助生殖技术如何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多余的胚胎。尽管布什在其讲演中表示,在他的“生命文化”中没有“多余的胚胎”这回事,但事实并不以他的讲话为转移。目前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试管冷冻胚胎。对于这些胚胎,通行的做法是在法定所有人的自主同意下,捐赠出来作科学研究;或者,冷冻五年后经一定程序予以销毁。这些做法已被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所认可,并没有被认为是对生命的摧毁。用作科学研究,还被认为是对人道的贡献。
同样,不管科技如何发达,也不管有些人如何反对,自然或人工流产总难以避免。这些流产的胚胎,多数已经或即将死亡,不会被指责为故意去“毁灭生命”(特别是自然流产)。这些胚胎,在一定前提下(胎龄不超过三个月,知情同意,非商业化等)用作科学研究也是常规,也被认为是有利于人道的好事。
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胚胎干细胞不能研究呢?从发育为胎儿、成人的“潜能”来看,辅助生殖多余的胚胎以及一些人工流产的胚胎,也具有这种“潜能”。从“基因同一性”的角度来看,这些胚胎也继承了其基因提供者双方的基因,与可能发育的胎儿、成人具有“基因同一性”。或曰:胚胎干细胞研究是为了一个生命而毁灭另一个生命。那么,辅助生殖多余的胚胎,是不是为了不孕夫妇而创造一个生命却毁灭了众多生命?为什么辅助生殖对多余胚胎的处理能够得到宽容,而胚胎干细胞研究却得不到宽容呢?
必须指出的是,为了尊重生命、尊重胚胎,现在国际上通常都接受英国沃诺克委员会(Warnock Committee)的建议,即以14天为界限,胚胎发育不得超过14天。根据胚胎学的研究,14天前的胚胎,分裂为8个细胞球后每一个细胞都可能发育为完整个体;14天是形成双胞胎的最后界限,14天前主要形成胚胎外部组织(外胚层)。最为重要的是,“原胚条”(primitive stear)尚未出现。原胚条的出现意味着胚胎细胞开始向多个组织和器官发育分化,表现出各自的特殊性。比如,可以发育为脊椎骨和神经系统等。由此看来,14天前后的胚胎有明显的不同。一般认为,14天前的胚胎还是既无感觉又无知觉的细胞团,尚不构成道德主体,对其进行研究并不侵犯人的尊严,更不是什么“毁灭生命”。当然,必须遵循严格的伦理规范,经过严格的伦理程序。
如果能够反过来再想一想,世界上有那么多帕金森氏病、早老性痴呆、白血病、糖尿病等有生命危险的患者,至今又无根治的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或快或缓地死去。让活着的人感到非常心痛。如今,胚胎干细胞研究为治愈这些长期威胁人类生命的顽疾开拓了一条现实的路,展示了美好的前景。人们怎能不寄以深切的希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等一再呼吁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原因。
要而言之,严格规范下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并没有背离生命伦理学的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恰恰相反,它体现了这一根本宗旨和基本原则,是一项值得支持的人道主义事业。(注:《科学时报》6月17日报道,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接受哥廷根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说:“我们无法逃避解放胚胎干细胞研究这一趋势”,深有同感。我特别赞同“趋势”这一精当的提法。)
第二,治疗性克隆并不必然滑向生殖性克隆
2001年,法国和德国联合向联合国提出,建议制订禁止生殖性克隆的国际公约。联合国为此专门成立特设委员会。2003年10月,第58届联大特设委员会以80票赞成、79票反对、1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将《禁止人的克隆生殖国际公约》推迟至59届联大。2005年2月18日,第59届联大法律委员会以71票赞成、35票反对、4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政治宣言,要求禁止任何形式的克隆人。嗣后,联合国大会也通过这一宣言。
为什么美国等国对禁止生殖性克隆的国际公约投反对票,而坚持主张禁止任何形式的克隆人呢?很明显,美国等国主张不仅要禁止生殖性克隆,而且要禁止治疗性克隆,因为不同时禁止治疗性克隆,就不可能真正禁止生殖性克隆。
应该承认,两者有联系,治疗性克隆从技术上说确有可能导致或滑向生殖性克隆。两者前期的技术路线相同。所谓生殖性克隆,就是将克隆羊多利的技术应用于人,把成人的某一体细胞(如包皮细胞、乳腺细胞等)核注入去核的卵细胞质中,通过特定技术(如电刺激)使其重新编程,分化发育为胚胎,再植入母体子宫,长成与体细胞提供者的遗传基因相同的个体。顾名思义,生殖性克隆就是要借无性生殖(即克隆)技术,实现自我复制。治疗性克隆也要将某一体细胞核注入去核的卵母细胞中,并通过特定技术使其重新编程,分化发育为早期胚胎。但请注意:胚胎不再植入母体子宫,而是从所得到的极早期胚胎(14天前)中提取胚胎干细胞,用于治疗目的。由此可见,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的技术路线,只是在前期相同,而在后期却根本不同:一个要重新植入子宫、发育成人;一个不要。
著名胚胎干细胞研究专家盛慧珍教授在一次学术沙龙活动中对我说过一段话。大致意思是:治疗性克隆从技术上说比生殖性克隆要困难得多。因为生殖性克隆只要把早期胚胎重新植入子宫,而治疗性克隆却要在人工环境下定向培育胚胎干细胞,这种人工环境很复杂、很微秒,有许多未知因素。这实际上也揭示了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后期技术路线的不同是由各自的目的不同所决定的。生殖性克隆是为了生育,当然要将早期胚胎重新植入子宫,而治疗性克隆是为了充分利用和开发胚胎干细胞“发育全能性”的神奇功能,来治疗疾病,移植组织和器官,根本用不着将早期胚胎植入子宫,倒是需要破坏胚胎来提取其干细胞。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还要看到它们的本质区别:目的不同,后期技术路线不同。
如果承认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之间存在本质区别,那就自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只要阻断早期胚胎重新植入子宫,治疗性克隆就不会滑向生殖性克隆。这当然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如果仅仅从技术上考虑和防范,那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伦理法律问题,科学技术工作的理念和目的问题。从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宣布克隆羊“多利”降生以来,已经八年有余了。虽然有些风风雨雨,但总的说来应该增强我们的信心。由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是有理性、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事业,有了相当完备的内部和外部运行机制,从而决定了对其进行伦理法律规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八年多来关于“克隆人”的争论,初步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在治疗性克隆滑向生殖性克隆的可能性面前感到无奈、悲观,甚至夸大这种可能性,主张封杀有利于治病救人的治疗性克隆研究,而是进一步加强相关的伦理法律规范,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国际协作,我相信治疗性克隆并不必然地滑向生殖性克隆。
三、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
在为胚胎干细胞研究作伦理辩护之后,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自然是:为什么胚胎干细胞研究会引起如此激烈如此尖锐的伦理分歧?主要原因是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
2002年6月,在台湾举行的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与法律研讨会上,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H.Engethardt)博士在评论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之争时,用“文化战争”来加以刻画。我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以致我近几年经常引述他的评论。他说:“我们注定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人生命的意义、患病、临终和死亡的认识上,呈现出稳定与痛苦的争议交织出现的世界。文化战争中的战斗在不远的将来将决定生命伦理学的特点。”(注:恩格尔哈特:《道德冲突世界中的生命伦理学:基本争论及干细胞辩论的要点》,《医学与哲学》,2002年第10期。)
生命伦理关注的问题,生命、死亡、健康、疾病以及人的权利和尊严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本身便是文化问题,或者说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因而不能不从文化的角度去考量。这一点,在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之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为什么一些人坚持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是对生命的毁灭呢?为什么布什总统说他的“生命文化”中根本没有“多余的胚胎”这回事呢?根据《圣经》,人是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最后一天(第6天)所创造的,并把男人亚当和女人夏娃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们生儿育女,人的生命从精子和卵子相结合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请看罗马天主教信理部的权威文告《生命祭》:“人类必须得到尊严,即得到作为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是从其存在的第一刻即开始的。”“胚胎必须被当作人一样的受到尊重,他作为一个整体的完整性就必须受到保护。”(注:转引自《维真学刊》(加拿大),2003年第2期,第10-11页。) 按照这种对《圣经》的解读,当然要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甚至加以相当严重的恶名。
这并不是对《圣经》唯一的解读,一些基督教甚至天主教信仰者,并不认为胚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研究。比如具有新教传统的英国,就通过了允许克隆早期胚胎,有条件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律。这里的关键可能是对“位格”(Person)的理解。由于早期胚胎还不是具有“位格”的,因而对其研究并没有侵犯人的尊严,更不是对生命的摧毁。我对此并无专门研究,只是想表明,即便在西方世界,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不同态度,也可以从文化差异中找到原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尊重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早在二三千年前,尧向舜请教世界上什么最为珍贵最有价值,舜毫不犹豫地明确回答:“生(命)最贵”。“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直是中国人民的重要信念。中国人也很早就知道男女结合生儿育儿的道理,所谓“男女構精,万物化生”。虽然也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但并没有像《圣经》那样系统完备的创世故事,更没有像《生命祭》那样对《圣经》的解读。因此,尽管我们的文化同样尊重生命,但不大可能形成研究胚胎干细胞就是“毁灭生命”的理念。相反,认为这是增进人类健康、延长人类寿命的仁爱之举。根据我们对上海、西安8家三级医院250名医师(2003年)的调查,58%的医师认为早期胚胎还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超过70%的医师赞同胚胎干细胞研究,高达94%的医师同意胚胎干细胞研究可为治疗一些“不治之症”提供美好前景。台湾林秀娟教授对61位医师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果。这些调查数据在某些人看来可能难以理解,而我们却认为很自然,也很合理。
人不只是理性的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而且也是文化的动物。人创造了文化,同时又受文化的制约。每一个人无不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背景中,受文化的影响甚至支配。文化传统有巨大力量。这种力量主要通过文化传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表现出来。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会潜移默化地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定势(“文化基因”),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权威性。由此看来,胚胎干细胞研究引发激烈的伦理之争一点也不奇怪。
利益冲突是这场伦理之争更深层的原因。马克思曾指明,人们为之争取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密切相关,都受利益的驱动(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仅从文化差异,很难完满解释美国和英国、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对胚胎干细胞研究会有如此尖锐的分歧。据《洛杉矶时报》报道,此次美国众议院之所以能通过放宽限制干细胞研究的议案,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他们担心,由于国内反堕胎人士和宗教中保守派人士的反对而放弃对这个新兴医学领域的研究,美国很可能就此失去在世界医学研究的领先地位。”“他们不希望因受到道德信仰的束缚,而导致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人才流失,甚至在这一领域被其他国家抛在后面。”① 当前,国际科技正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且这种竞争关系到各国的综合实力,自然不能掉以轻心。胚胎干细胞研究作为新兴领域,各国水平相差并不太大,竞争更趋激烈,谁也不愿意被“抛在后面”。(注:美国众议院表决前,5月19日韩国国立大学黄禹钖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宣布用病人的皮肤细胞克隆出早期胚胎,并成功提取11个胚胎干细胞系。这一重大成果表明,美国有可能被“抛在后面”。)
值得注意的是,据最近盖洛普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0%的美国民众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并不违背道德良知。① 如此之多的公众支持,这在前些年是不可想象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兴起之初(1999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到13000封公众来信,仅300封表示支持。两相对照,变化多么明显!这只能说明,出于种种利益的考量(主要是健康利益和国家利益),美国公众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态度越来越趋于理性。
那么,为什么布什总统依然坚持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立场呢,难道他竟会不考量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宁肯被“抛在后面”吗?非也。一方面,美国拥有2001年8月9日前(即他限制用联邦经费资助前)的78株胚胎干细胞系。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而研究这78株胚胎干细胞系,并不受限制。布什也许以为,研究这些胚胎干细胞,足以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如果全世界都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不许培育新的胚胎干细胞系,那更有利于美国保持领先地位,甚至垄断地位。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在联合国的讨论中,坚持反对“治疗性克隆”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利益是多元的,多种多样的,有健康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利益,政治利益,等等。政治利益中,除了国家利益外,还有个人利益及其所代表的政党、阶层或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布什作为总统,不能不考虑其选民的意向。而支持他的选民,多数比较保守,倾向于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我相信,当布什判断他的选民的意向可能转变时,他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政策也将随之改变,他的“生命文化”也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文化差异不会消除,利益冲突也将继续存在,因此,关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之争也不可能消失。但通过争论和实践,求得一定的共识和妥协是完全可能的。
四、严格伦理规范和伦理程序
为胚胎干细胞研究作伦理辩护,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伦理问题。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胚胎干细胞研究涉及敏感的胚胎问题,并且有可能滑向生殖性克隆,必须十分重视伦理问题,严格伦理规范和伦理程序。我们认为,这是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一个极为必要且十分重要的条件。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严重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对人性的扭曲等。尤其是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对基因进行改造,甚至创造生命,制造人的程度,其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更为尖锐,也更加敏感。如不严格伦理规范,将造成严重的恶果。我们都十分熟悉美国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Sarton)对二战期间,德国某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反人道行为的深刻总结。他说,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技术迷恋症”的受害者。他们是那样深深沉浸在技术问题中,以致于忘记了还有其他的尺度,变得冷漠、麻木,甚至惨无人道、毫无人性。(注:参见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 当今,在科学技术更加强大的条件下,更要谨记历史的教训,决不能让悲剧重演。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缺少沟通和对话,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生命伦理理念和规范却知之甚少,存在诸多误解,甚至认为我们处于伦理“真空地带”,是什么“东方野蛮生物学”。在第59届联大讨论有关克隆问题的决议时,中国投了反对票,属于“少数派”。作为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仅理应分享胚胎干细胞研究带来的福祉,而且希望用我们的聪明才智为全人类、为子孙后代造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胚胎干细胞研究方面可以“为所欲为”,放松伦理规范和管理。恰恰相反,对伦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要严格伦理规范和伦理程序,决不能授人以柄。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有效的措施。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近几年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探讨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规范。早在2001年10月,就提出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则(建议稿)》,共20条。2002年8月,作了进一步修改。上海市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很快接受了这一建议,表示上海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就照这个建议办。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2003年12月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也吸纳了该成果。2004年3月,国际权威刊物美国《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杂志》全文发表了这一建议稿。以下是其主要内容: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项光明的事业,应该支持我国科学家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为保证这一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建立一套既符合国际生命伦理原则,又适合我国国情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和应用的伦理准则”(第4条),这些原则包括:“行善和救人”(第5条)、“尊重和自主”(第6条)、“无害和有利”(第7条)、“知情和同意”(第8条)、“谨慎和保密”(第9条)。具体到胚胎干细胞研究,明确规定:“禁止生殖性克隆”(第10条),并对辅助生殖多余胚胎和流产胚胎用于胚胎干细胞研究作了具体规定。而对于运用体细胞核移植术来进行胚胎干细胞研究更特别明确且细致地规定“必须遵守以下行动规范:(1)卵母细胞必须是辅助生殖多余的,并由不孕夫妇自愿提供;(2)用体细胞核移植术创造的胚胎,只能在体外培养并不能超过14天;(3)禁止将体细胞核移植术所形成的胚胎植入妇女子宫或其他任何物种的子宫;(4)‘人体-动物’细胞融合术,在非临床应用的基础性研究中,如满足上述第(1)、(2)、(3)点要求下可以允许。但在临床应用的治疗性克隆研究中,严格禁止采用‘人体-动物’细胞融合术将人的体细胞与动物卵细胞质相结合的产物用于人类疾病的临床治疗。”(第14条)“要建立和健全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监控和评估机制。生命伦理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应严格审查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计划,并对研究的进程和成果进行伦理评估,务使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符合国际上有关的章程、宣言或准则,符合我国的有关政策法规,利于为人类健康服务。”(第19条)
我们相信,严格伦理规范和伦理程序,胚胎干细胞研究必定会沿着正确的航道有序发展,为“再生医学”开拓美好的前景,惠泽全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