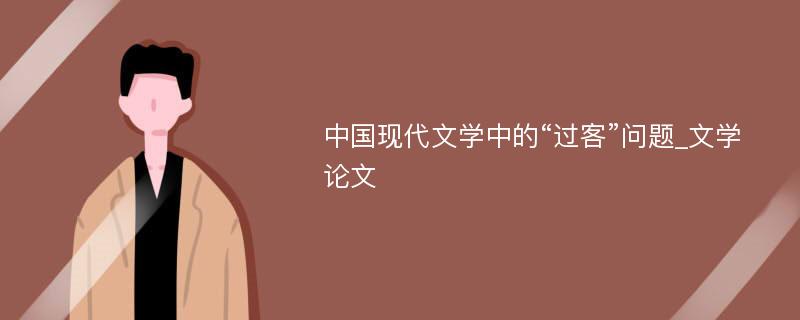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同路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路人论文,中国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路人”的称谓源于苏联,20年代中期传入我国,并长期流行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直至60年代初期,仍有人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沿用“同路人”的称谓。〔1〕相同的政党性质和政治体制, 相同的文艺思想和艺术追求,导致苏联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生产了多方位的直接影响,中苏两国的许多文学现象几乎同步发生。20年代苏联文学出现的“同路人”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并引发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中间状态作家的问题。今天看来,“同路人”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影响问题,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令人深长思之。
一
文学“同种人”作为政治词汇在文学界的移植,最早见于托洛茨基1923年出版的《文学与革命》一书。托洛茨基在该书第二章“革命的文学同路人”中指出:“他们没有从整体上把握革命,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目标也感到陌生。他们程度不同地倾向于越过工人的脑袋满怀希望地望着农夫。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同路人”〔2〕。 根据托洛茨基的论述和“同路人”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实际可以得知,“同路人”作家同情无产阶级革命,但倡导不问政治,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接受革命,却又有保留和不彻底地接受,他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标,因而随时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危险;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处于一种“中间的思想状态”,是处在无产阶级作家与资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
中国左翼文坛对苏联“同路人”问题介绍较全面的是1928年冯雪峰和鲁迅分别译自日文的《苏俄文艺政策》一书,该书展示了苏联文学界在制定文艺政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客观地介绍了苏联文学界高层领导在“同路人”问题上的各种意见和观点。譬如《红色处女地》杂志代表沃隆斯基认为,“同路人”是苏联文学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无产阶级应当与“同路人”合作,并在合作中指出他们的缺点,向他们提出“为工农联盟的利益而工作”的要求。《在岗位上》杂志代表瓦尔金则指出,革命可以“利用”“同路人”,但应当明确“同路人”不可靠,革命不能无限期地与他们保持关系,无产阶级对“同路人”要采取批判的态度,“暴露”他们的“隐约倾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主张对“同路人”采取用文学批评来“吸引”的政策,而不是“用棍棒敲打他们的脑袋”,“掐住他们的脖子使他们喘不进气来”。布哈林批评了“岗位派”提出的苏联只有无产阶级,而没有中间阶层的观点,指出:“难道我们可以因为它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而扼杀它吗?那是一件蠢事”。苏联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坚持他对“同路人”的一贯态度和立场,同时又以新的例证支持他的观点。托洛茨基指出,在革命前受到列宁赞助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新言论》,同颓废派保持过“友好”关系,向他们“提供了很大的篇幅”,原因是当时的颓废派是受迫害的年轻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这种迫害逼得他们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一边,“颓废派虽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毕竟是我们一时的同路人”。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指出,综观这次争论的各种意见,唯一最适当的结论是:“要以一切手段支持我们寄以最大希望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时又决不排斥‘同路人’。”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把非无产阶级和非共产党员的艺术家从我们身边推开”。《苏俄文艺政策》还收入两个对“同路人”立场和态度截然相反的决议,一个是1925年 1月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会议的决议,认为:“同路人不是一个清一色的整体。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尽力地诚实地为革命服务。但同路人中多数的一类人乃是在文学中歪曲革命,常常诽谤革命,……因此完全可以有根据地说,同路人文学在根本上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同路人文学的这种反革命因素必须进行最坚决的斗争”〔3〕。另一个是 1925年6月俄共(布)中央的决议,其中提出党对“同路人”的方针 ,即“周到地和细致地对待他们”,“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通过“耐心地帮助”,“使他们尽可能迅速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 〔4〕译者将两个观点相异的决议放在一起,意在通过读者的对比参照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的文学“同路人”问题出现于20年代末左翼文坛引进苏联文学理论,倡导革命文学之时。由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直接受到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因此,无论是正确的思想还是错误的理论,二三十多年代的苏联文学均给刚刚兴起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以深刻的影响。“同路人”作为20年代苏联文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必然要伴随着中国左翼作家对苏联文学理论的借鉴和模仿而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重现,形成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同路人”问题,并且作为主要因素之一,引发了1928年和1932年关于“革命文学”和“文艺自由”两次文艺论争。
创造社、太阳社在20年代末首倡革命文学,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但由于这些革命的倡导者们尚处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进程中,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缺乏正确与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受到苏联“岗位派”如“拉普”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否定无产阶级作家以外的一切作家,排斥如打击革命文学的“同路人”,使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走了一段曲折的历程。本来,经过2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艺界对苏联“同路人文学”的评介,尤其是俄共(布)中央1925年6 月《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对“同路人”问题做出了正确结论,已使中国广大作家对“同路人文学”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立场与态度有了一定的把握。但是,此后的“拉普”继续执行对“同路人”作家排斥如打击的政策,1931年初,“拉普”更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口号:“没有同路人,只有同盟者或者敌人”〔4〕。 苏联文学界对“同路人”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左翼文坛对当时作家队伍的认识和态度,创造社、太阳社承认中国文坛存在着“同路人”和“同路人文学”,但对这类作家作品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批判的立场。冯乃超在第一篇发难文章《艺术与社会生活》中,分析了文坛上“可以代表五种类”的五位作家,郭沫若是“实有反抗精神”的革命作家,张资平则“没落到反动的阵营里去”了,其余的三位中间型作家:只描写“个人和守旧的封建社会”的叶圣陶,反映“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的鲁迅,表现青年人的“愁苦和贫穷”的郁达夫,都一概表现出“非革命的倾向”,即一种“同路人文学”的特征。
在被左翼文坛点名的中国三个“同路人”作家中,叶圣陶、郁达夫默不作声,鲁迅则以《“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等文章进行论辩,结果一再被戴上“不革命”作家的帽子。李初梨则认为:“鲁迅在这阶级对立间,取一个中立(?)的态度,也‘不革命’,也不‘反革命’。”〔5 〕钱杏邨详尽地分析了鲁迅的性格特点和创作个性,指出:“鲁迅只是任性,一切的行动是没有集体化的,虽然他不反对劳动阶级的革命”。〔6 〕杜荃对鲁迅的论述似乎更像切中了“同路人”作家的要害:“大约他是一位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他对于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已经怀疑,而对于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又没有确实的把握。所以他的态度是中间的,不革命的”。〔7 〕鲁迅被冠以他不应得到的“不革命”作家的头衔,但他仍像以往借用论敌派给他的罪名回击论敌一样,接过了“不革命”的头衔,并常常以此来反讽论敌。然而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是不允许“不革命”的中间作家存在的,他们根据“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逻辑,责令作家在世界形成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两个“战垒”的情况下,“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8 〕他们将资产阶级如小资产阶级作家一律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对立面,提出了“拜金主义的群小是我们当前的敌人”的口号,认为由于作家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太浓重了,所以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是反革命〔9〕。为了打垮这样的反革命作家, 清理出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地基,创造社、太阳社向他们认为的革命文学的最大障碍——鲁迅发动了进攻,咒骂鲁迅是“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和“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10〕
看到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如此激烈的攻击,冯雪峰站出来以《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为鲁迅辩护。冯雪峰认为鲁迅并非如创造社、太阳社所斥责的“反革命”,至多只是“不革命”而已。冯雪峰指出:“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的知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鲁迅不是社会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也“只是一个旁边的说话者”,但从他身上找不出“诋谤”革命的痕迹,相反地在与封建主义斗争中“做工做得最好。”冯雪峰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彻底抛弃了个人主义立场,投向社会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第二类则“也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向往”;第三类是貌以革命,而实际上投机革命的知识分子。冯雪峰将鲁迅划入第二类知识分子,即革命的“同路人”作家范畴。1952年,冯雪峰在回顾他写作该文时的思想动机时指出:“我翻译过苏联的《文艺政策》,我很受这本书的影响……例如我也机械地把鲁迅先生派定为所谓‘同路人’,就是受的当时苏联几个机械论者的理论的影响”〔11〕。冯雪峰出于对鲁迅的辩护,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的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但冯雪峰同创造社、太阳社一样,并未认识鲁迅的革命性,认识鲁迅创作的革命意义。尽管当时的鲁迅尚处在革命民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进程中,仍在创造社、太阳社的“挤兑”下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救正”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将鲁迅视为“同路人”作家并不妥当,当时的鲁迅至少是革命文学的同盟者。
或许是冯雪峰的这篇文章发挥了作用,1928年10月后,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论战的鼓声锐减, 代之而起的是同茅盾的论战。 茅盾早在1925年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中便开始介绍无产阶级文艺,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一度流露出苦闷、悲观情绪,在其第一部作品《蚀》中出现了消极倾向,受到文坛的批评。对此,茅盾在1928年10月发表的文章《从牯岭到东京》中为自己辩解,同时针对革命文学的读者对象问题,提出了革命文学也要面向小资产阶级读者,反映小商人、中小农的生活,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痛苦。茅盾批评了文坛上那种为工农诉苦者为革命作家,替小资产阶级诉苦则“罪同反革命”的倾向,但在强调写小资产阶级中也表现了片面性和偏激情绪,因而招来创造社的批判。他们认为茅盾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与政治上的“中间党派演着同一的任务”,它“处于布尔乔亚与晋罗列塔利亚的两德沃罗基之间”,即一种“同路人文学”。同时指出这种文学实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目的是“替我们的敌人来抹杀蒙蔽混淆晋罗列塔利亚底阶级意识”〔12〕,因此,它“对于无产阶级是根本反对的”〔13〕。总起来看,创造社、太阳社在20年代对“同路人文学”一直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政策,除了棒喝其为“反革命”外,还嘲笑其艺术上的不足。麦克昂在1928年5 月发表的《桌子的跳舞》中曾明确表达了对中国“同路人文学”的轻蔑态度,文章在引用了一段卢那察尔斯基关于允许“同路人文学”存在的论述后,不无讥讽地指出:“但是不革命的作家们哟,你们不要欢喜,以为得了一个护符:须要晓得我们所能听其存在的不革命的作品,那是有限制的,那是要‘艺术的,天才的作品’才行呀,你们要有托尔斯泰或者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天才。而且写的还要是‘天才的小说’!”〔14〕显然,麦克昂并未理解卢那察尔斯基的真意,卢氏明确表示假如这种天才小说是反革命的东西,必须“挥泪扼杀”之,而对于那些”只是不关心政治”,或者“有几分不大好的倾向”的作品则允许它们存在。可见,对于“同路人文学”关键还是看其政治上的表现。比较而言,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对“同路人”问题认识较为正确的是冯雪峰,他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中对“同路人”作家做出了恰当的分析,认为他们“多是极真实的,敏感的人”,虽然“常是消极的,充满着颓废的气氛,但革命是不会受其障害的”。冯雪峰明确提出:“革命也必须欢迎与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一切友方的势力”,无产阶级对“同路人”作家应“尽可以极大的宽大态度对之”,这是20年代左翼文坛在“同路人”问题上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准。
二
尽管左翼文坛错怪了鲁迅和茅盾,他们所做出的鲁迅、茅盾为革命文学“同路人”的结论不能成立,但中国的文学“同路人”问题并未随着革命文学论争的人为结束而解决,1930年左联的《理论纲领》提出反对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外,还特别提出“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便是一个明证。所以,在此后不久开展的“文艺自由”论争中,“同路人”问题自然而然地被再次提了出来。1931年12月,胡秋原在《文化评论》上宣传文艺自由的主张,遭到左翼文坛的批评,谭四海指出:“在一九三一年底,中国阶级斗争紧张到了争取政权的阶段”,胡秋原为首的自由知识阶级提出这样的理论,是“想在严阵激战之中,找第三个‘安身地’,结果是‘为虎作伥’!”〔15〕为此,胡秋原奉劝谭四海读一读译成中文的《苏俄文艺论战》、托洛茨基的《文艺与革命》、冈泽秀虎的《苏俄文学理论》和鲁迅译《苏俄文艺政策》,因为这几部书均有关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论述。胡秋原并明确指出:“布哈林(他当时还没有‘失脚’),也说过文艺要自由竞争,所以也容许同路人活动”,由此在文艺自由论争中引发了“同路人”问题。随后,苏汶以论争双方之外的“第三种人”参加论争,续谈文艺自由的主张。于是,左联把论争的重点转向了“第三种人”,“同路人”问题更突出地显示出来。本来,文艺自由论曾是苏联“同路人”的一个文艺主张,由胡秋原、苏汶引发的文艺自由论争本身即是一个关涉“同路人文学”的问题,但真正切中此题的却是论争中不大为人注意的刘微尘的文章《“第三种人”与“武器文学”》。刘微尘对苏联“同路人文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他根据苏联“同路人”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主张分析了苏汶的“第三种文学”,认为中国的“第三种人”即苏联的“同路人”,而苏汶则是“给中国文坛上奠定了同路人的基地的一个老祖”,指出:“同路人和左翼在文学上的论争,在苏联已是解决了的一件事。但是在中国,似乎尚是老实不欺的苏汶刚来开了一个端倪〔16〕。到了争论的后期,冯雪也认为“同路人”问题已成为这场争论的中心问题,他指出:“放在我们面前的,至少做我们的注意的中心的,应该是革命的和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同路人文学”往往被表达为小资产阶级文学。
左翼文坛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性质有一个认识过程,对其态度前后也有变化。起初,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一出笼,即被左翼文坛斥为在反对普罗文学上,比民族主义文学“站在更前锋”的“狡猾”的敌人〔17〕,苏汶参加论争后,论争的理论性增强了,但认为“第三种人”是“坐在资产阶级的安乐楼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们倡导的“非无产阶级文学,其间接直接有意无意地是会拥护资产阶级的〔18〕。面对浓烈的火药味,陈雪帆出来调停,他指出:“最近胡秋原苏汶两先生的文章,主要点都在对于左翼理论或理论家的不满,我们不应把这对于理论或理论家的不满,扩大作为对于中国左翼文坛的不满,甚至扩大作为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不满”〔19〕。陈雪帆的提醒对左翼文坛正确认识文艺自由论争的焦点如正确对待论争对象具有重要意义,可惜他的意见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论争中,胡秋原诘问左联要不要“同路人”,苏汶也提出马克思也允许海涅这样的“同路人”存在。对此,鲁迅明确回答:“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诱那些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来同走呢。”〔20〕鲁迅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对左翼文坛应当扩大战线早有清醒的认识,但此时以鲁迅也认为文坛不存在“第三种人”。此后的刘微尘则进一步表示,“不是因苏汶是同路人而左翼不要同路人”,而是因为苏汶的文艺自由论“实际上替统治阶级尽了相当的任务”〔21〕。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常委张闻天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斗争》报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对左翼文坛排斥“同路人”的错误提出了批评,指出:“这种关门主义,第一,表现在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张闻天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提醒文艺界领导: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只会使“幼稚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22〕对于左联此时的关门主义,张闻天在1938年延安接受记者采访时更明确指出,左联在坚持斗争方向和培养干部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对于‘同路人’的关系上,还不能吸收更广大的同情者——我们的朋友——参加革命的阵营”。〔23〕
张闻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在左翼文坛产生了积极影响,几天之后,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经过讨论,分别撰写了纠偏文章。在《并非浪费的论争》中,对胡秋原的错误理论继续进行了批评,但明确表示:“我们相信他本人和那些反革命派人也确有多少的不同”。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中,开篇即表明:“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们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文章分析了苏汶文学主张中错误的方面,同是肯定了“苏汶先生们”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文学的立场,表达了与之联合的愿望。可以说,比起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此次的文艺自由论争在“同路人”问题上不是不了了之,而是辩清了一些问题,并在如何对待革命文学的“同路人”问题上得出了比较正确意见。在论争中,胡秋原、苏汶、舒月、刘微尘、鲁迅、张闻天、冯雪峰等都表达了对“同路人”问题的见解,将这些意见综合起来,可以看作当时中国左翼文坛对“同路人”问题所达到的新的认识水准。一、对“同路人文学”的态度。通过论争,左翼文坛端正了对“同路人文学”的态度,表示要“联合一切进步的,为着人类的前进和光明而工作的文学者作家也同走”,即使对于那些只能“同走几步的‘同路人’”也要团结。而排斥和打击“同路人”只能孤立无产阶级文学,削弱同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斗争的力量。二、对“同路人文学”的认识。通过论争,左翼文坛认识到在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之间存在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它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文学。左翼文坛对于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意识、但能揭露社会矛盾、暴露旧世界腐败、描写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作品,“都要利用”,即使对那些于革命没有益处,然而并不帮助反动势力的作家也要团结和帮助。三、对“同路人”的引导。通过论争,左翼作家认识到“同路人”成分较复杂,“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有些“同路人”因与革命距离过远,而“由同路人变为背道者”。“同路人”要成为革命文学之友,必须“有目的地自己不断地矫正脚步,走向无产阶级”,反之则要被“时代扬弃在阴暗的路上”。因此,左翼作家必须积极地引导“同路人”,通过忍耐和细心的工作,使他们发扬革命性,抛弃弱点和缺点,尽快走向革命斗争。
张闻天能够在1932年批评左翼文坛在“同路人”问题上的关门主义错误,一方面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素养和对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苏联纠正“拉普”的错误。1932年4 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散了“拉普”,纠正了其排斥“同路人”作家的左倾思潮和宗派主义错误,以期“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渴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24〕。苏联纠正“拉普”的错误,无疑给半年后张闻天撰文批评中国左翼文坛的关门主义产生了直接的启示和影响。张闻天的文章发表后,及时纠正了中国左翼文坛在对待“同路人”问题上的偏颇和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年经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对此,1933年春的上海反动刊物《社会新闻》上也有所反映,该刊在《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一文中谈到:左翼文艺运动由于“各方面严厉的压迫”和“内部的分裂”而消沉下去了,但在最近的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由此可见,执行正确的联合“同路人”作家的政策对革命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同路人”是中国文坛上一个重要的作家阶层,“同路人文学”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值得认真剖析的问题,其中的诸多教训,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总结。
注释:
〔1〕林默涵:《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 《文艺报》1960年第1期。
〔2〕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2页。
〔3〕《“拉普”资料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9月版,第122、170页。
〔4〕雷成德主编:《苏联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10页。
〔5〕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文化批判》第四期。
〔6〕钱杏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 《我们月刊》创刊号。
〔7〕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创造月刊》二卷一期。
〔8〕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一卷九期。
〔9〕麦克昂:《桌子的跳舞》,一卷十一期。
〔10〕麦克昂:《桌子的跳舞》。
〔11〕冯雪峰:《回忆鲁迅》。
〔12〕李初梨:《对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晋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创造月刊》二卷六期。
〔13〕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创造月刊》二卷五期。
〔14〕麦克昂:《桌子的跳舞》。
〔15〕谭四海:《“自由知识阶级”的“文化”理论》,《中国与世界》第7期。
〔16〕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3月版, 第164页。
〔17〕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
〔18〕舒月:《从第三种人说到左联》,《现代》一卷号。
〔19〕陈雪帆:《关于理论家的速写》,《现代》二卷一期。
〔20〕鲁迅:《论“第三种人”》、《现代》二卷一期。
〔21〕《现代》二卷一期。
〔22〕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8页。
〔23〕程中原:《“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24〕程中原:《党领导左翼文坛运动的重要史料》,《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二期。
标签:文学论文; 冯雪峰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现代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鲁迅论文; 创造社论文; 小资产阶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