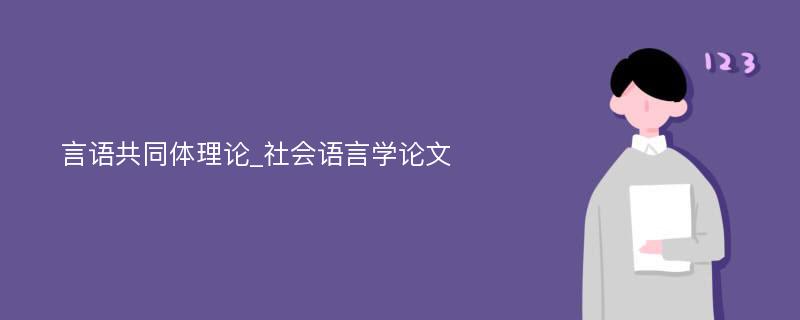
言语社区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言语论文,理论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言语社区理论是当代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参见Patrick 2001)。本文因此探讨言语社区理论的内容、意义和作用,希望对这一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下面第一节讨论言语社区理论对语言学宏观发展方面的意义,第二节指出言语社区理论在语言定义方面的一个重要作用,第三节讨论言语社区的基本要素,第四节介绍一些应用言语社区理论的研究,第五节对言语社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展望。
一 语言学的对立统一
言语社区理论一旦全面、成熟地发展起来,必然成为社会语言学的核心理论,而且会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中取得重要的地位。
上述观点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1)尽管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看社会语言学领域内存在着不同的流派,但是众多社会语言学家的一个共同观点或默契是:言语社区是语言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语言调查的基本单位(参见高海洋2003)。(2)尽管在语言哲学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社会语言学家与许多主要从事形式语法研究的语言学家存在着分歧,在实践上双方却都将言语社区作为语言的描写单位;社会语言学家比较强调言语社区内部结构的复杂性,指出科学抽样方法的必要性;形式语言学家则往往将个别讲话人等同于言语社区的典型代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自觉或不自觉地,所有的语言学家都在研究言语社区;只是有的用比较精密的方法,注重其结构内容;另外一些用比较粗糙、方便的方法,以求迅速获得一个整体印象。
纵览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的研究、语言接触现象的研究,还是言语社区的研究等等,无不是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的方言学以至较新的形式化的音系和句法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进一步研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社会语言学和其他流派的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的基础。以社会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为例,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注重语言的多样化研究,而后者是以同一性的假设来作为语言研究的前提。因此,社会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之间,不是由承认不承认语言的同一性或变异性(或曰差异性)来分别的;而是由对同一性或变异性的重视程度,由研究重心的不同来区分的。
同一性和变异性是对立统一的,语言这一事物包含了这两重性质。社会语言学的特殊作用在于,它弥补了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对言语社区内部变异的忽略。社会语言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研究,立意测量和验证言语社区的同一性,并把它作为研究课题,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一种信念,或者是一张用来回避语言变异现象的盾牌。
关于“言语社区”,最简单的定义可以是:一个讲话人的群体,其内部的某种同一性构成了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而区别于其他类似群体(参见Gumperz 1968)。这一定义可能过于抽象,下文中我们还要补充该定义中忽略了的一些重要内容。但是,这一定义在同一性和差异性方面道出了言语社区的实质:相同是存在于不同之中的,某一方面的相同并不能抹杀其他方面的不同。言语社区理论的特殊作用是,针对语言的同一性和变异性(差异性)来进行研究,使语言的同一性脱离武断的、随意性的判断,使它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科学分析之上。
综上所述,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理论是能够把语言变异的研究与形式语言学的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的。同时,在对语言现象同一性和差异性客观研究的基础上,言语社区理论也有望把社会语言学的各个流派,语言学的各个流派和分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联合起来。
二 克服循环论证
早期的“言语社区”的理念,是指“一个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群”。因此,一种语言对应一个言语社区,一个言语社区对应一种语言(参见Patrick 2001)。但是,这里往往就引起了循环论证,在定义社区的时候用语言(“英语社区由讲英语的人构成”),在定义语言的时候用言语社区(“英语社区使用的语言即是英语”)。那么,到底“社区”是第一位的呢,还是“语言”是第一位的呢?
恰当地定义“言语社区”而又不落上述循环论证窠臼的,当首推布隆菲尔德(Bloomfield 1933)。他指出,言语社区的基础是讲话人之间频繁的交际活动,言语社区的界限是由交际密度的减弱而自然形成的。甘柏兹(Gumperz 1968、1982)进一步发展了布隆菲尔德的交际密度的思想,他指出,言语社区是一个言语互动场所,社区成员不一定都讲同一种语言,社区的“语库”可以包括一种以上的语言代码;但是,每一个言语社区都有一套自己的交际规范,其中包括语码选用的规范。社区成员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他对社区交际规范的熟谙和遵从。拉波夫(Labov 1966、1972、1994)的纽约市英语调查及其随后的语言变异和变化的研究,又将言语社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拉波夫理论上的贡献是,言语社区的同一性主要表现为社区成员言语行为的有序性以及他们对语言变异评价的一致性。拉波夫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将言语社区的研究放到了抽样调查、定量分析的实验性层面来进行。
总结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确定,社区是第一位的,语言是第二位的。语言存在于社区之中。一个言语社区不一定就对应着一种语言;但是频繁的言语互动往往是产生和保持一种语言变体的基本条件。因此,历史悠久的言语社区一般都拥有一个标志性的语言。与此同时,稳定的双语社区也普遍存在。但是,什么样的言语互动群体即可构成一个言语社区,什么样的言语社区条件可以产生一个新的语言变体,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当前的语言研究当中,语言学家往往依据社会上流行的判断。就像形式语言学家依靠本族讲话人的语法判断一样,人类语言学家和方言学家,甚至社会语言学家也往往是一样的。如果当地人说这里有一个社区,有一种什么“话”,我们也就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出发点不应该成为研究的局限,语言学家有自己的工具和标准来分辨语言,也应该有自己的标准来划分言语社区。“社区”可以由社会学的标准来确定,“言语社区”则应该由社会语言学的标准来测定。不但世俗的观念不可盲从,即使是社会学确定的“社区”,也要重新鉴定其在语言方面是否也是一个社区。我们这里关心的是言语社区,是语言方面具有社区特性的一个组织单位。如果要避免按照“语言”来确定“言语社区”的谬误,就必须先确定社区,再确定该社区使用的语言变体。我们对一个语言的承认,在那些历史悠久、有文学传统、有语言规划权威机构的情况下,往往不会出现争议。但是,在一些历史较短的社区中,虽然新的变体可能已经形成,但是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还可能得不到承认。这时,语言学家就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发现和描写这些语言变体。
之所以不能“以语定区”,是因为世俗中所谓“讲同一种语言”是一个难以测定的概念。严格地来讲,没有哪两个人讲话是完全一样的。但是通常人们还是能够确认另外的人是不是在“讲同一种语言”。尽管如此,对于某种语言变体的认同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语言交际能力。对于像汉语这样方言复杂使用广泛的“大”语言来说,人们往往缺乏足够广泛的交际经验以应对可能遭遇的变异。怎样将一般人判断中的客观成分测定出来,而避免流行的偏见,是社会语言学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 言语社区要素
社会学上的“社区”一般包括下列几个要素:在一定地理范围内聚集的人群,这些人之间长期保持着互动关系,并且有一种心理认同。除了这三个最主要的因素之外,社区成员一般还具有相同的生活方式,社区往往还有一些公共的设施(徐晓军2000)。我们发现,这些要素都可以找到语言方面的对应物。因此,“言语社区”是一种符合社会学定义的社区,同时又是一种具有语言特性的社区。此外,聚集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的人群,一般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单位,所有参加有关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员,彼此之间自然也保持着频繁的互动。可以想见,这些互动最主要的就是言语互动。因此,言语社区在很大程度上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产生重合,是意料之中的事。
按照“社区第一、语言第二”的原则,不能简单地“以语定区”,而应该是“区中找语”。对于研究语言结构系统性的语言学家来说,哪些语言事实属于哪个语言系统常常是令人困扰的问题。当一位“本族讲话人”站出来以语感来否定某个语法理论的时候,语言学家不能只是因为它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而不承认对方所指的为“语言事实”,同时也往往苦于没有其他办法来确定所述内容是否为有关的语言事实。这在汉语的语法研究中屡见不鲜,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同来源的语料常常被用来检验一个结构系统。取自不同社区、不同变体的语料并不构成一个紧密的语法系统。有时候,自认为是研究同一现象的语法学家往往是在审视来自不同系统、具有不同系统价值的原始材料。乔姆斯基以“表现错误”来忽略某些语言材料也是迫不得已的,但是哪些是“能力”哪些是“错误”却没有客观、统一的标准。还是索绪尔的“语言/言语”的区分寓意深远;虽然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没有进一步的解说,但是索绪尔指出,“语言是属于社区的,言语是个人现象”(Saussure 1966)。因此,我们要从社区中“发现”语言,同时需要一些科学的“发现程序”。通过这些发现程序而获得的语言事实,才有“语言”(区别于“言语”)的特权地位。依据这些事实发展起来的语法理论才会经得起考验,不必受到语言事实界限不清的弊病的困扰。
从语法研究的需要来看,上述理论具有现实的意义。但是要解决所提出的问题,还要分两步走:首先,用实证的方法来确认一个言语社区;然后再用客观的标准来测量和发现社区中存在的语言变体。言语社区理论的作用就是要列出言语社区和语言变体存现的基本条件,并进一步将其落实为可验证的客观指标。
社会学的“社区要素”,在语言上都有相应的表现;这些表现使言语社区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首先,“在一定区域保持互动的人口”,基本符合社会语言学家对“言语社区”的定义,只不过“言语社区”是言语互动的群体,以区别于以其他方式互动的群体。尽管言语互动是社会互动的主要形式,但是非言语性社会互动的群体也会存在。“非言语性社区”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不能排除的可能。除了“地域”、“人口”、“互动”这三要素之外,“言语社区”还具有其他的社区特性,如“认同和归属意识”。这一点其实是言语社区最重要的特性之一,上文所述甘柏兹和拉波夫有关言语社区心理基础的论断即是它的理论来源。但是,这一特征有时会被无限度地夸大,或者无节制地用来替代其他社区特征。社会语言学家面临的任务是怎样将其客观化、定量化和标准化。对于语言态度的实证性研究可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共同的生活方式”、“共有的社区设施和财产”等社区内容,也可以在语言方面找到对应物。甘柏兹和拉波夫的研究使我们把语言使用的规范、语言变异的分布和言语社区的组织结构联系了起来。共同遵守的语言使用方面的规范,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相似的语言生活,完全可以是“共同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再看“共有的社区财产”:虽然言语社区与居民社区比起来更加抽象,但也不能说它没有公共的设施或财产。首先,语言作为一个音义符号系统,为社区所拥有(上文中索绪尔的论述),可以视为社区的公共财产。一个言语社区往往有一些解决言语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些也可以视为言语社区的公共设施。正像目前城市中小区型社区所拥有的会所等服务设施一样,有关的语言权威机构,语言典籍、成文标准、舆论压力,等等,只要成员都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沿用的途径,自然也就成为言语社区共同的财产和设施。
如果我们确认言语社区具有人口、地域、互动、认同、设施这些要素,那么言语社区的发现和鉴定就要从这些要素入手。
语言鉴定是在社区鉴定基础之上的,我们同样应该建立一些客观性的鉴定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语言学家可能会有一张不同的世界语言地图。从言语社区理论角度来讲,语言是“社区语言”。因此,可以有没有标志性语言的社区,不可以有无社区依托的语言。语言的基本存现单位是言语社区,活的语言都容纳在社区之中。也许语言学家已经到了告别由世人来界定他们研究对象的时候了。对于什么是语言,什么不是语言,以及语言个体之间的切分,语言学需要有自己的明确标准。植物学上对树木的分类与各种自然语言对树木的分类有所不同,为什么语言学家就要沿用自然语言中存在的语言名称呢?名称还不是实质的问题,问题是它掩盖了一系列的概念问题。哪些语言现象被识别出来而冠以名称,哪些又不予识别,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沿用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概念、抑或这些概念的随意组合呢?这样看来,世人所谓“英语”、“汉语”、“阿拉伯语”不过是一些不严格的概念,称作“民族语言”可能更恰如其分。而这些标签,除了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之外,又能从多大程度上告诉我们其通常所标记的语言现象的结构系统的同质性呢?又能从多大程度上告诉我们讲话人之间的交际沟通度呢?语言学家需要的是语言学的分类,虽然类型学家和方言学家已经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其原始材料基本上还受到流行的社会意识的局限。因此,“英语”、“汉语”、“阿拉伯语”这些名称应该是命名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语言学家的术语。作为语言学术语,它们可以叫做语言变体的“显称”或“认称”,它们可以是“民族语言”、“国家语言”、“地理语言”、“政治语言”或“历史范畴语言”,但不是“语言学语言”。“语言学语言”应该是基本上符合索绪尔所描写的自给自足、系统内部结构统一的符号系统。社会语言学已有的一个命题是:上述封闭性系统在语言中并不存在。但是,显然这些系统在心理上是存在的,语言学家近百年来的研究都是在描写和解释这些“心理现实”。社会语言学考虑的另一个命题就是,这种心理现实是否还有一个社会基础?它是否就是某一类社会活动的结果?语言学作为人文学科,着重描写人的感受和民间的文化传统,是无可厚非的。但作为社会科学,将语言作为社会现象来提出因果关系的解释,就不能完全局限在常识和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固有格局之内了。
根据社会语言学几十年的研究,我们目前的假设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后续的形式语言学所描述的封闭性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结构系统将最有可能近似地存在于封闭性的小社区中。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支持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系统的假设。这样一来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更加复杂化了:我们需要回答关于这个开放性系统的开放程度以及开放的方式等一系列问题。只是一味地强调语言是开放或封闭系统、静止或动态系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解决语言系统怎样开放、怎样运动和发展抑或在什么情况下它可以是近似静态的稳定状态乃至稳定到什么程度等问题的时候了。实证性、定量性研究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 言语社区与社区
上文谈到,言语社区可以同其他性质的社区重合,但也不一定重合。新加坡华人社区(简称新加坡华社)是一个民族社区,是否也是一个言语社区呢?曾有该社区是一个双语或多语(下文中“双语”将包含“多语”)社区的说法。如果双语社区是言语社区中的一种类型,该说法即蕴涵着“新加坡华社是一个言语社区”的命题。那么怎样验证上述命题呢?根据言语社区理论,一个言语社区是一个有确定人口和确定活动地点,进行频繁言语互动的社会群体。这一条件,新加坡华社基本符合。新加坡华人是一个确定的人群,他们基本上是在新加坡居住和活动,在方圆六百平方公里的新加坡岛上的近三百万人,日进日出,这些人之间应该是存在频繁的言语互动的。但是,我们发现,建立在社会语言学研究基础上的规范和认同的言语社区的标准却不能得到满足。
根据一项1995年在新加坡华社范围内进行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调查,我们发现,从语言使用规范和语言态度上看,新加坡华社语言方面的整合程度并不高,而且还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趋向。表1列出的是新加坡华人在不同交际场合使用不同语言的情况(引自陈松岑、徐大明、谭慧敏1999:72)。
表1 新加坡华人在不同交际场合使用不同语言的百分比
英语(%) 华语(%) 汉语方言(%)
英语和华语(%)
政府机构
45
31
3
16
购物中心
31
39
4
17
小贩中心 2
50
17
5
巴刹 5
39
24 6
可以看出,除了华语在小贩中心刚刚达到50%的使用率以外,在每一个场合中每一类语言的使用率都低于50%。也就是说,人们使用语言的一致率还达不到50%。
对于双语社会的研究产生了双言制理论(Ferguson 1959)。该理论指出,比较稳定的双语社会中的情况是,社会通用的几种语言变体各有其适用的场合,一般可以分成用于比较高端的社会经济场所的“高变体”,和比较低端的场所的“低变体”,整个社会对此有一致的看法和一致的实践,违反这些惯例将招致非议甚至导致交际活动的失败或停止。这完全符合甘柏兹关于言语社区成员在语言使用方面具有共同规范的理论。但是,新加坡华社的情况显然与典型的双言制不同,并且违反了言语社区的规律。
如果将表1中英语和汉语方言的使用情况单独拿出来看,似乎是一种双言制的格局:英语为“高变体”,汉语方言为“低变体”。高端场合多用英语,低端场合多用汉语方言。(注: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社会曾经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双言制”社会(参见徐大明、李嵬2003)。)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些使用英语或汉语方言的人数比例合计起来并没有构成华社的全部人口,只是在两成到五成之间,见表2。
表2 新加坡华人在不同交际场合使用英语和汉语方言的百分比
英语(%) 汉语方言(%)合计(%)
政府机构
45 3
48
购物中心
31
4
35
小贩中心
2
17 19
巴刹
5
24
29
如果将使用“华语”和“英语”的人列出来,合计人数会多起来,差不多占总人口的五成到七成,但是在“政府机构”、“购物中心”等高端场所却不再出现上面那种比例悬殊的语言选用倾向,而是比例相差不大(76:70),与双言制的情况很不同,见表3。
表3 新加坡华人在政府机构和购物中心使用英语和华语的百分比
英语(%)
华语(%) 合计(%)
政府机构
45
31
76
购物中心
31
39
70
如果把使用“英语和华语”(双语并用)的人数加入合计人数,其对总人口的代表性大大增强,最高达到九成以上。但是上述两类高端场所中英语和华语使用的比例仍然是旗鼓相当:61:47;48:56,不是双言制中一边倒的形势,见表4。
表4 新加坡华人在政府机构和购物中心使用英语和华语的百分比(含双语并用)
英语(%) 华语(%)
合计(%)
政府机构
61(45+16) 47(31+16)92
购物中心
48(31+17) 56(39+17)87
上述情况说明在语言使用方面新加坡华社没有很强的主流趋势,这就使得我们对它是否构成一个言语社区产生了疑问。调查的其他材料也引起了同样的疑问。在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方面,我们也发现了英语与华语比例接近的情况,“从小学会的语言”中,英语为34%,华语为42%;“使用起来最流利的语言”,英语为52%,华语为59%(陈松岑、徐大明、谭慧敏1999:85)。
语言态度的调查进一步提出了问题。表5中列出的是对英语和华语具有不同态度的被调查人的比例,左面一列是认为英语比华语更有用、更有身份、更有权威、更友善、更亲切、更好听的人数比例;右面一列是认为华语比英语更有用、更有身份、更有权威、更友善、更亲切、更好听的人数比例。可以看出,有高达10%的人口与另外10%或更多的人口持截然相反的语言态度。
表5 新加坡华人对英语和华语的语言态度的五项指标(百分比)
英语比华语(%) 华语比英语(%)
合计(%)
更有用
14
19
33
更有身份
32
13
45
更有权威 39
12
51
更友善
10
43
53
更亲切
10
51
61
更好听
12 33
45
必须承认,没有将华语与英语对立起来的人口约在半数左右。但是,参看表5“合计”一项可知,三成到六成的人口对通行在该社会的两种语言持对立的态度。上面列出的前三项指标为对语言的功利性评价,后三项为情感指标,表示的是认同和归属感。有这样高比例的人群具有不同的语言评价意见、不同的语言认同,我们确实不能将该人群等同于一个言语社区。
新加坡的情况可以与其他社会双语的情况来进行比较。海外华人的双语社区很多(参见邹嘉彦、游汝杰2003)。根据甘柏兹的“规范统一”说,言语社区内语言选用的规范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典型的双语社区应该是双言制式的。美国加州的彻丽坞华人社区,虽然包括三类人:只会说汉语的人、只会说英语的人和会(英汉)双语的人,但是社区中几种语言的地位是清楚的,广州话是社区语言,英语是对外语言;四邑话在1965年以前曾经是社区语言,以后则变成只是一部分人的家庭语言(Tsang 1985)。在语言选用方面,主流是十分清楚的,社区中的广州话作为交易语言的使用大约在七成左右,其余三成也主要是用其他汉语方言,只会英语的人在社区中活动是十分困难的(Tsang 1985:430)。从这方面看,该社区是一个合格的言语社区。从语言态度上看,也有相应的特征:无论本人的英语程度如何,被调查的彻丽坞华人全都认为英语比汉语重要(Tsang 1985:430-431)。
当然双言制的情况也不都是百分之百的整齐划一,但至少要有统计上的明显的主流趋势。周庆生(2003)对云南德宏傣族社区的调查发现,傣族双语社区中,汉语为主要的工作语言(七种工作场合中汉语的使用率都在八成左右),而在生活场合中,面对面的交际都是以傣语为主要用语(家庭80%,佛寺80%,等等)。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华社的语言情况从语言使用规范和语言态度方面都与典型的双语社区不同,有了言语社区理论,我们就可以将以种族或民族限定的社区与言语社区区别开来。新加坡的情况是一种不稳定的双语状况(Xu et al.1997),1995年以后的情况还需要继续研究。此外,是否可以将该人群划分成两个言语社区,如果划作两个言语社区,其内部的同一性又如何,其认同的心理基础又是怎样产生的,这些也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参见徐大明等1997,徐大明1999,Xu et al.1998)。我们不认为言语社区的理论已经完善,也不认为七成或八成的一致性就一定是社区语言规范和语言态度一致性的定量标准。目前我们强调的是,规范和态度这两项内容应该成为言语社区的必要内容,而且应该在实证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定量标准。至于这些标准要精确到什么程度,或大致在什么样的数量范围内,这都是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不仅对于双语状况的分析需要言语社区理论,单语社区的确定也需要应用言语社区理论。拉波夫(Labov 1966)的研究说明言语社区的特征之一是其成员对语言变异共有的评价机制,后人一般把它归入语言态度。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多语社会中语言选用的情况作为宏观层次上的语言变异看待(参见徐大明1999)。这样,上述关于语言选用的态度方面的分析就可以直接应用到微观的语言变异上来了。微观的语言变异一般是作为“语言变项”来进行研究的(参见徐大明等1997:100-130),如纽约英语的[r],北京话的儿化(Xu & Gao2001)等。对这些语言变项的社会评价表现出言语社区的同一性。根据拉波夫的纽约调查,虽然各阶层在元音后卷舌发音上的具体表现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语言态度是相同的:较高比例的卷舌发音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北京话的儿化等语音特征,根据1981年(Barale 1982)的调查,是没有明确社会评价的语言特征;2000年的调查(Xu & Gao 2001)却发现较大范围的负面评价,随即发现类似纽约英语[r]变项的语体转移表现。所不同的是,北京赋予不卷舌发音较高的社会价值,而纽约是卷舌具有较高价值(Xu & Gao 2001)。
除了语言使用规范和语言态度的一致性以外,言语社区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内部结构的有序性。既然言语社区不是讲话人的克隆的集合,那么什么是它的同一性呢?除了规范、态度和认同之外,还有没有行为方面的一致性呢?言语社区的异质性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限度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曾经提到,像纽约英语的情形,每一个可能卷舌的机会都卷舌,或讲话中完全没有卷舌,都可能就将你排除在该言语社区之外(徐大明等1997:70)。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参与了卷舌变异机制,你就在这机制中获得了一个象征性的社会地位。言语社区内部是有结构的,每一个社区成员都有他相对于其他成员的地位。社区是一个社会组织,社区成员之间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语言变异的社会分化及其社会评价。与纽约的情况相类似,在北京,如果你一个字也不儿化,你得不到北京人的认同;如果你过度儿化,北京人对你反感。但是,即使在北京人认可的范围内,不同的儿化比例仍然是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的,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至少我们已发现它的语体标记作用(Xu & Gao 2001,彭宗平2003)。
双语社会语言使用的社会分化也可以产生类似纽约英语的社会层化结构(Xu 1996,Xu et al.1998,徐大明1999),单语社区的社会环境不同也会造成其结构类型不同(徐大明2001)。在对包头昆都仑社区的调查研究中,北方话鼻韵尾变异的社会分布说明,在没有显著社会经济阶层化的社会条件下,社区成员主要以社会网络的结构排序。有的语言学家认为言语社区就是社会网络的集合(Gumperz 1997,陈松岑1999)。目前的阶段,排除层化结构模型还为时过早,至少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持(徐大明2001)。
五 研究方向
语言是个复杂事物,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从符号学的角度,可以将语言分成形式和意义两个系统,从形式上还可以分成语音、词汇、语法等子系统。在语言的系统性研究中,迄今最受忽视的是语言使用者的系统。如果对这个系统的研究不深入下去的话,对其他系统的研究必然会受到影响和阻碍,因为语言的各个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的,讲话人这个系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理论是关于语言使用者的组织系统的解释。言语社区是社会化言语互动的产物。人类的社会交际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呈现高度的协调性和组织性。因此,言语社区是可观察、可度量的实体,而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拉伸扭曲的虚拟性分析框架。从定量研究的角度看,一个言语社区,作为一个有形可见的物质性活动范围和一个有社会心理基础的社会群体,可以由一系列定量指标的组合来限定。这些指标,除了上文提到的语言使用规范和语言态度同一性指标之外,还可以包括交际密度指标,沟通度指标(参见徐大明等1997:192-193),相关的内容必然包括社区结构类型(变异的社会分化)和与交际密度联系在一起的交际网络结构(参见Xu 2001)等。这些指标的操作化过程必然又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言语社区理论从社会交际的规模、强度、方式以及效果(质量)几方面来度量和确认言语社区。一个言语社区一旦确定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来判定是否有相应的语言变体产生,以及社区是否区分和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变体。最后一步是对属于这些语言变体的语言现象的界限的确认。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从人出发,发现谁跟谁讲话,谈话的效果如何。
会话是一个合作过程,长期合作造成的一些默契将人们契合在一起。这样一些群体就是言语社区。言语社区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会有自觉的意识,将会命名他们共有的音义符号体系,该符号体系的系统性自然也会随着使用而增强。这一过程在时间上有起点也有终点。事情变得复杂化往往是因为组成新言语社区的人带来了原属言语社区的遗迹。新的言语社区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旧的言语社区有所继承,对别的言语社区有所借鉴。有的时候继承和借鉴都可能继承和借用到语言的名称。由于非语言的原因,讲话人的显性认同可能与其实际使用的变体不同,这时候语言学家就不要盲从。但是要克服社会的压力并不容易,言语社区理论可以为语言学家提供一个科学的工具来完成这一任务。
标签:社会语言学论文; 双语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新加坡华人论文; 新加坡英语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徐大明论文; 语言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