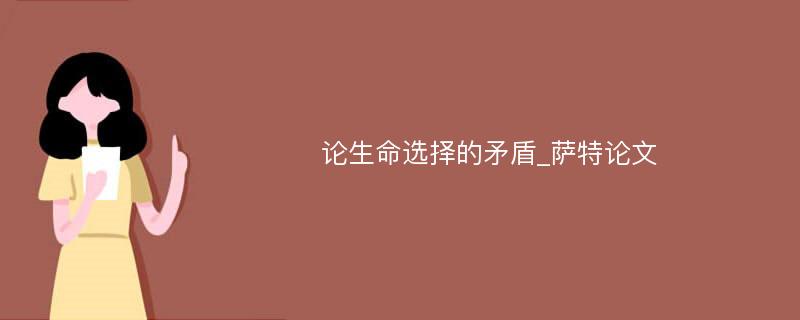
论人生选择的矛盾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性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生道路充满着各种矛盾。解决人生矛盾的过程,实质上是进行人生选择的过程。各种人生冲突都是围绕着价值目标展开的。一个人走什么样的路,确立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树立什么样的理想,都是一种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所谓选择,是指人们根据自身的存在状况、目的需要和价值尺度,对人生过程中各种矛盾关系和事物多种可能性关系所进行的取舍行为。人生选择的内容十分广泛,有对目标、理想的选择,有对人生价值观的选择,有对职业的选择,有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有对现实环境条件的选择,等等。对人生目标和理想的选择,在人生选择中起主导作用。人生中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人生的命运即人生进展。如果选择的方案既符合自己的个性,又具备各种客观条件,便会使自己的命运大为改观;反之,就有可能陷入困境或遭厄运。
一
人生选择与人生自由紧密相联。在哲学上,自由是对必然而言。斯宾诺莎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只有依照理性的人才是自由的。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因为“禽兽没有思想,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所以只有人类——而且就因为它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才有自由”(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人是有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的主体性动物,能按照自身的意愿创造自己的未来。因此,人的自由即人作为主体,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追求和表现出来的一种能动、自主、自为的行为。
人生选择是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人生选择体现了人的自由。人的本质是人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而获得的。人通过对必然性的认识,能够支配和控制客观环境,在社会活动中享有做人的一切权利,并且希望自己主宰自己。人的活动是一种自为的有目的活动,人们总是围绕着自我设定的目标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无论结果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主体都能表现出一定的自由。
自由是分层次的。有国家、民族、阶级的自由,有个人的自由。毫无疑问,国家、民族、阶级的自由是高层次的自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能独立,没有自由,就会成为别的国家的殖民地,成为别的民族的奴隶。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取自由,就会受资产阶级的奴役和剥削。人们都熟知这样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很多革命志士可以抛弃自己的生命和爱情,而选择了为争取国家、民族、阶级的自由而奋斗的道路,因为他们知道,要想个人得到自由,首先必须争取国家、民族、阶级的自由。另一方面,个人的自由也是不能忽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如果每一个人都没有争取自身自由的愿望,国家、民族、阶级的自由就会落空。近代哲学家胡适曾经对青年们说过这样的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设得起来的!”(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这话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如果放弃自由的权利,缺乏主体意识,就有可能成为奴隶,或者成为地主的狗腿子,资本家的奴才,甚至成为卖国贼,为虎作伥。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少青年人就是从争取个人自由走上革命道路的。如有的为了反对封建婚姻,争取婚姻自由,脱离家庭后接受了马列主义;有的不愿受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争取人身自由,逃出牢笼,参加了革命队伍。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连自身的自由都不愿意争取的人,他会为争取国家、民族的自由而奋斗。
在自由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片面倾向。一种是把自由片面理解为社会群体的自由。例如近代学者梁启超就认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人个之自由减。”(注: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他把自由片面理解为国家、团体的自由,他主张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无条件服从团体之法律决议,是自由的前提条件,因而把服从看作是“自由之母”。由于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整体主义价值观和原苏联高度集权模式的影响,我们有很多人在过去也坚持这种主张,人为的把个体与社会抽象地对立起来,不理解自由个性在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中的地位,完全排斥了个体的自由,这是不利于人的发展的。第二种倾向正好相反,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个体的自由。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传统自由观的反思中,有些人把自由理解为个体的绝对自由,理解为可以脱离必然、不受法纪约束、不向社会负任何责任、损害他人权利的为所欲为。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
二
从以上所述我们看到,人生选择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是自由和非自由的统一。
选择的自由性即自主性。人的主体意识、主观能动性以及人的权利、人格价值决定了人们在人生选择中的自主性。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有权利占有劳动资料,享受劳动产品和选择自己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中表现出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这说明人是有权利和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和造就自己的人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生选择的自由性理解为,主体通过认识和利用必然,在实践活动中有目的、有能力、有权利做他应该做的愿意做的事情,从而达到自觉、自为、自主的状态。一般说来,人的命运的好坏、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程度。选择的自主性有利于人的自我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发挥人的潜力,体现人的自由权利。承认和尊重人生选择的自由,是对人的独立人格价值的尊重。
但是,人生选择又是非自由即他主性的。尽管每一个人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和个性进行人生的自由选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进行具体的人生选择时,往往又是不自主的,是被动的。因为人们的选择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人的一切活动必然要受社会关系的制约。事实上,人的行为不单是由个人的意志所决定,“而且由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和标准,由来自外部的异质的压力来决定”。(注:[美]赫舍尔:《人是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选择的自由是人的权利的体现,但权利离不开义务和责任。人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也要负责任。这种责任感对人的选择动机、选择方案和选择的结果都有重大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自由不应是人的权利的宣言,应是人的责任的宣告”。(注:[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此外,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诸如阶级、民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事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分工、道德、宗教、家庭、婚姻等等,都会对人们的选择有所限制。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如地理位置、气候,还有个人的主观条件等,对人们的选择也必然有影响。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人们对工作部门、工作种类、学习专业等的选择。
上述情况说明,人生选择不仅仅是主体自己本身的事情,而且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不是主体的随心所欲,而是自由和责任的统一,权利和义务和统一。
自古以来,人们都向往着自由的人生,但又总摆脱不了某些必然性的束缚。我国战国时代的庄子看到了这一矛盾,他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幻想在精神上能自由自在地逍遥于尘世之外。他不懂得“自由以必然性为前提”(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5、323页。)的道理,只好用消极的逃避的态度对待人生选择的他主性。
强调自由选择,最有名的当数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萨特认为,人的“自由是价值的唯一基础”,人的一切行动都意味着选择,而选择本身就是自由,是完全的自主。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规定性,完全由自己决定,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对自己进行设计、选择和造就自身。他的结论是:“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注: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转引自《存在主义哲学》第342页。 )“自由之为自由却仅仅是因为选择永远是无条件的”。(注: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5页。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碰到具体问题,萨特自己也陷入了选择的困境,显得不“自由”了。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曾举过这样一个事例:
萨特的一个学生,因为下列情形来找他:这个年轻人的父亲与母亲不睦,而且投靠了敌人。他的长兄在1940年的德国侵略战争中牺牲。他想为长兄报仇。他的母亲单独和他住在一起,由于丈夫的叛国和长子的牺牲,她的心境很不安。她看着这孩子,就是她的唯一安慰。这个年轻人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去英国参加自由法国军队,即抛弃母亲不管;或者留下来与母亲在一起,帮助她解愁。他充分明白,母亲只为他而生,他离开(也许他的死亡)会使母亲绝望。至于一切图谋出走和战斗的努力,却是一种不确定的举动,可能触礁搁浅,变为完全无效果。例如,在赴英国作战途中,经过西班牙的时候,可能被无限期地拘留在西班牙集中营内。或者到了英国或阿尔及尔,被安排在办公室内做案头工作。结果,他面临两种很为不同的出路:一是具体而又直接的出路,但却只关系到一个人;另一则关系到一个民族的集体,但这是未定的出路,可能半途而废。这个学生对这二者不得不做出选择。
谁能帮助他选择?萨特认为,没有人能帮助他进行选择,基督教的教理帮不了忙,也没有一种伦理学能告诉他怎样选择。如果这个青年听从了某一劝告者的意见,就无异于自己受那一选择的拘束,就不是自由选择了。所以最后萨特只好对这个学生说:“你自由选择,自由创造罢”。萨特也无法解决这个矛盾。
萨特在这里举的是一个反映家庭伦理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矛盾的事例。当人们面临这样的选择时,往往会陷入二难困境。类似的问题,中国古代早已有人提出。《三国志》《魏书·邴原传》引《原别传》记载:曹丕为太子时,有一天晏会宾客百数十人。他向宾客们提出一个问题:皇帝和父亲同时生了病,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个人的性命,是救皇帝还是救父亲?宾客们有的说救皇帝,有的说救父亲,无法得出统一的答案。皇帝是国家的象征,父亲是家庭的象征。曹丕的问题,是要求人们在国与家、君与臣、忠与孝的矛盾中进行选择。
三
人生选择的矛盾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沈继英、祖嘉会在他们主编的《人生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把人生选择中的冲突归纳为两种:“同一人生价值体系内不同价值原则、价值要求之间的冲突;不同人生价值体系之间原则规范要求之间的冲突。”(注:沈继英、祖嘉会主编:《人生理论与实践》,北大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6—137页。)
上文所述萨特举的例子和曹丕提出的问题,就属于同一人生价值体系内不同价值原则、价值要求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社会心理学称之为“接近——接近型”。这是两种具有积极价值的事物之间的冲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这类矛盾常常碰到,而且比较复杂。它要求人们在“此亦是非,彼亦是非”的情况下进行选择。清代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这样一件事:河北东光县有一条河叫胡苏河,天旱则干涸,下大雨则涨水,给来往行人造成很大麻烦。雍正未年,有一讨饭的年轻媳妇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扶着生病的婆婆涉水过此河。行至中流水深处,婆婆一下子跌倒在水中。媳妇只好把儿子丢弃在水中,努力把婆婆救出水背上岸。谁知上岸后婆婆却大骂媳妇:“我七十老妪,死何害!张氏数世,待此儿延香火,尔胡弃儿以拯我?斩祖宗之祀者尔也!”媳妇不敢回话,只跪着哭泣。留儿子延香火和救婆婆都是符合孝道的,都具有积极的价值意义。但在势不两全的情况下,媳妇选择了弃儿救姑。类似这种选择,在现代生活中也常常发生。据说某新娘为了考验丈夫是否真的爱自己,便向新郎提出一个问题:我和你母亲都掉到河里快淹死了,你先救谁?如果真有其事,丈夫的选择是困难的。这反映的是家庭伦理价值体系中人的选择的矛盾。
至于不同人生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则是指具有积极价值意义和具有消极价值意义的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或同一事物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价值。例如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在信仰、理想、追求方面的冲突,就属于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体系的冲突。这种类型的冲突与前一类型冲突相比,要简单一些,人们在进行选择时,一般来说可以遵循非此即彼的原则。
虽然同一人生价值体系内的选择存在着亦此亦彼的情况,容易使人陷入困境,但并不是没有选择标准的。人的本质决定了人必须把对自己的责任和对社会他人的责任统一起来,即把选择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统一起来。当人们面临同一人生价值体系内的选择时,如面临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矛盾时,社会责任感强的人会牺牲个人或家庭利益,把民族、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作为选择的标准。中国古人把人生的这种选择标准称为“义”。儒家的“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的主张,就是这一标准的具体体现。当然,社会责任感不强的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作出选择。上文萨特的例子中,那个年轻人如果从“自由”的角度讲,他完全有选择的自主性。如果他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他会毫不犹豫地参加自由法国军队,投入到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去。如果他只是一个注重家庭伦理的人,便会选择留在家里照料母亲。这两种选择都符合某种社会价值的评价标准。但二者必居其一,在这种情况下,人生选择是一种痛苦,是一种牺牲。
处于二难困境中的选择一般是不能两全的。那么,把哪一方面作为牺牲的对象呢?在价值观系统中,价值有高低层次之分。在特定条件下,满足社会的需要属于高层次价值观,满足个体需要属于低层次的价值观。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人的本质要求人们舍低求高。孟子把处于两难困境中的选择比喻为鱼和熊掌的关系,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注:《孟子·告子上》。)鱼和熊掌皆美味,但熊掌胜过鱼,如果两者不能并有,只好牺牲鱼而选择熊掌。同样道理,生命和“义”都是有价值的,但“义”即社会价值超过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果两者不能并有,便牺牲个人的生命而选择“义”。儒家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解决人生选择的矛盾仍有积极意义。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那么人生选择的自由性、自主性不就是一句空话吗?不能这么理解。如果把选择的自由性理解为萨特所说的“永远是无条件的”,或理解为“想做什么,便做什么。”那就是一种虚假的选择。选择的自由性是要受必然性的限制的,在一定意义上,没有限制,没有社会责任感,就没有真正的人生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协调,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协调。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发表的《人权宣言》把“自由”规定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的行为的权利”,也说明自由是受限制的。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在进行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是不会回避自己对他人和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如果把这种责任和义务变为自己的自觉信念,个人的选择就是自由的,就会如黑格尔所说的,“在义务中个人毋宁说是获得了解放”,“获得肯定的自由。”(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7、168页。)我国古代的很多民族英雄、爱国志士,民主革命时期的很多革命先烈,在民族、国家需要时,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做到了舍生取义。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中华儿女抛弃家庭和个人利益,选择了抗战救亡道路,很多人为国捐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他们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标准进行自己的人生选择。毫无疑问,这些人的选择是受限制的,但又是自由的。
总之,人生选择既是自由的,又是非自由的,是自主性和他主性的统一。人的一生是在选择的矛盾中渡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