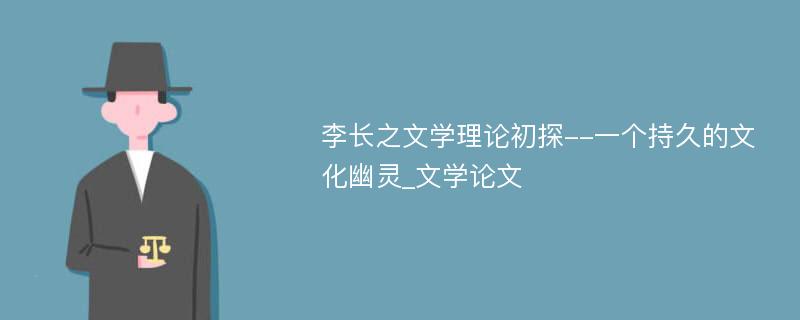
执拗的文化守灵人——李长之文论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执拗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当文学的纯真面孔淹在一片硝烟中,左翼文坛以政治阶级分析为特色的批评话语便理所当然地登上了批评界的盟主地位。然而,在主流话语的轰响中,却还有这样一群批评家,他们怀着对自由独立精神的挚爱来观照人生,聆听艺术,他们或在和平静穆的诗美极境中浅斟低吟,或默默地营造文学的“希腊小庙”,或开着流线型的印象汽车,载灵魂在杰作中探险。他们柔而不弱,寂寞而不孤独,在对纯美艺术的坚执中让生命自由释放,实现人生的艺术化。李长之就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位。
李长之在现代批评史上是作为一个传记批评家奠定他的位置的。《鲁迅批判》与《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便是其代表作。他的传记批评注重“人格与风格互相辉映阐发,感同身受地进入作家的文学世界中吟咏,把创作看作是作家生命的流露,从而深入把握作家的‘独特生命’,把生动的‘人格形相’写下来”(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293页。)。传记批评所以能成就他在现代批评史上的地位,因为背后是有一整套的文学观,批评观,文化观乃至人生观作为支撑。恰如他自己所说,文学的主要内容有三个:“一是文学的美学(Litcrarwisscnschaft),决定文学创作上的一切原理原则,二是文学的美学的应用,便是文学批评(Literarkritik),三是文学批评的应用,乃是文学教育(Litcrarpacdagogik)”(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8页。),而文学内容却“关系于整个文化。我们必须把研究中国文学的事纳入体系的学术的轨迹,从世界性,整个性,窥出那文化价值”(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09页。)。正由于此,才使李长之对我们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他作为一个传记批评的意义,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文学史,批评史,思潮史,文化哲学史等多方面的价值参照暨资源。本文拟对其三、四十年代的文论作一简明勾勒及评估。
一,文学创作:纷纷的回忆雪片的安详飘荡
创作论在李长之的文学观中处于核心地位。文学是什么?他是把文学放在与人生,与社会,与时代,与道德,与科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诸种关系的考察中来回答这一永恒之问的。同时,这也是他针对当时文坛现状的一点严肃认真的思考。而构成这一思考的底色的,当是他对艺术的虔敬与敏感。
在李长之看来,文学是须附丽于人生的。文学表现的对象,就是人生。然而“艺术并不一定表现人生的整个的,也可以表现人生的一方面;艺术并不一定给人生以解答的,也可以把人生的问题单单提出”(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209页。),作家的责任,在于“把了解人类的心胸摆出来”(注:《李长之批评文集》,郜元宝、李书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559页。)。所以,成就一件艺术品的基础,在于作家对人生的情感体验的深度,而不在于作家对社会生活与环境的接触面之广狭。诚然,“赞成唯物史观的人,无疑地首先要分析作者的阶级基础,检定作者的阶级意识,这是应当的”(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82页。),因为“人,无论如何跑不出物质的手掌”(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82页。)。但是,“物质的条件,并不限于阶级的关系”(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82页。),“只把物质条件看作了阶级关系的,那只是片面的看法,直言之,那只是经济学的观点。有同样重要,决定了一个人的造就的,就是天性和教育”(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82页。)。他有一个绝妙的比哈:如果说天性是“如同照相的底板上的影,显像液定像液便是教育。这很显然,如果根本没有影,加甚么材料也是枉然;然而已经有影,不加材料,也自然漫漶消失了去。而一个人的阶级基础,就像作了底板的那块玻璃,有影没有影,加材料不加材料,玻璃总可以作为最踏实的限制着将来的影的根本”(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84页。)。这就是说,包括阶级基础在内的某种宏观的社会生活与时代背景远不如环绕作家役观境遇的教育及作家自身固有的灵气(天性)对创作起的作用更大,更直接。阶级基础在作品中的投影只有通过作家的心理中介。李长之这番话无疑是针对左翼文坛的简单反映论而发生的,当文学仅仅被理解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社会生活又被简化为阶级斗争,文学自由创造本性便遭到了扼杀。即使被左翼视为“离经叛道”的胡风文论来看,当胡风把丰富的人生内容界定为斗争与进步,进而让艺术扮饰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武器角色,而不是像李长之把人生看作是作家的生命体验,进而让艺术保持其独立品格与尊严,其狭隘也是显然的,其思路并未逸出反映论的框架* ,更不要说左翼中的左派了。
不可否认,胡风也像李长之一样重视创作主体的作用,高扬创作中的人格力量,显示了他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的勇气以及艺术的敏锐。但两者对创作主体、人格力量的认识还是有很大区别,胡风认为,人格力量是指“主动地认识并把握客观现实”(注:《批评精神》,李长之著,南方印书馆1942年,327页。),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与游离性就是知识分子的二重人格,这种二重人格当然要体现到作家身上,因此创作过程既是“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注:《胡风评论集》(下),胡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9页。)。很显然,胡风主要是把作家的人格放在与现存秩序之关系即政治格局里来看待的。李长之就不同,他是在本体论层面上来看待作家人格的。他在介绍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对人性的看法时曾说,人性是“一元的呢,还是二元的?倘若是一元的,则只有和外界的斗争而已,受外界的迫害而已,则这种冲突是一时的,一旦社会就了绪,则冲突的形势一定和缓下去。倘若是二元的,那么,即便外界没有迫害,不和外界斗争,那自身的冲突也仍然存在着。……人类自己本身中,也有两个矛盾”,“文艺不必是只源于压抑,还有人类之审美的要求,创作欲望(像小孩子一会提笔就画小人,决不是受了什么压抑),理想的憧憬等等”(注:《胡风评论集》(下),胡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145页。),当然就更不必只是现实战斗的需求了,这样,作家也就不再是政治斗争或宣传的人格符号了。视野的广狭带来了理解的深浅。
正是基于此,李长之十分重视创作主体个性的发挥,重视风格的形成。以单个作家而论,就要写自己最擅长写的东西。他非常敏锐地嗅出鲁迅的悲哀和愤恨、寂寞和倔强、冷观和热情的心理气质对其创作之影响,鲁迅的幽默与老舍的幽默之不同,茅盾则宜于坚实,宜于严肃,宜于沉着;张资平小说艺术的成功在于遵从他擅写的自然主义手法,当他不能素位而行,不安于自然主义时,失败便注定了。以创作方法论,也是如此。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的不同,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的不同,不是源于作家世界观的不同,也不以政治进步与否为衡量标准,而是源于主体个性的不同。李长之从美学与心理学的层面阐述了这种区别,“一部分的诗人的艺术体验是偏于内在性和非直观性的,另一部分诗人则偏于感观的直观性”(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68页。),这是创作个性的不同;此外,诗的对象及诗人体验的内容及文艺的类属也会造成这种不同。这种差异是艺术本身的内在规律,是艺术造型法则,而不是像左翼理论家把现实主义抬到独尊的地位,当作衡量作品的美学尺度乃至政治尺度。
重视创作主体,其精义就是弘扬创作中情感的作用。在作家的主体心理结构中,知,情,意是处于怎样的一种关系和地位呢?李长之说得很明白:“在一个艺术家(文学也在内)是观照人生的态度就必须是审美的而后可,所谓审美,就是正如康德所说是居于知识界与意志界之间,用中国话说,即是既不忘情,又不沉溺的态度”(注:《李长之批评文集》,郜元宝、李书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6页。),“通常说真善美合一,真和二者的关系,我倒觉得远一点,因为真究竟重在客观,究竟人的成分很少,究竟没有价值的问题,美与善则不然,问题都重在主观”(注:《李长之批评文集》,郜元宝、李书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10页。),“都有人的成分,都有价值的问题,其关系之密切,乃是不言而喻的(注:《李长之批评文集》,郜元宝、李书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10页。)”。但是,美与善也有区别。李长之在朱光潜与梁实秋关于文学与道德关系的论战中表明了自己与朱光潜相近的看法;文学是一种纯粹的艺术,道德在文学中可以成为美感观照的对象,但通过美感而来的道德效应,比诉诸理智而来的道德效应大得多。也就是说,一,有两种道德效应,一种是创作中抱着无所为无目的的审美态度而产生的作品的道德效应,它是艺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被情感所浸润的,这是善的极致,也就是美的极致;一种是创作中有意识地抱着功利的道德目的产生的作品的道德效应,如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这时善是超乎美的,游离于艺术作品的有机美感之外。必须注意,李长之对道德的含义的解释,是“爱,生长,创造,反奴性,反残暴,反愚妄”,这就与旧的以忠君为本义的伦理教条截然不同,它是经过现代自由精神洗礼的生命本真。
艺术作品中的情感有两大特色,一是真挚,二是从容。真挚的情感是创作的想象动力,因为“想象动力根源于文艺家的情志即他对人生,世界,历史的总体文化态度或价值评价”(注:《思想实验》,夏中义著,学林出版社1996年,68页。)。真的情感,是活人的情感。现代诗人情感上患了贫血症,对于诗的本质也就只能捉迷藏。李白的可爱,“就在他‘真’得不掩其矛盾。‘真’得不掩其有棱角”,表现在技巧上的“真”,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上虚饰不矫揉,朴实无华,一点人工斧凿痕不能有的光影”(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62页。)。忠实于艺术,就不得有求知的打算,道德的考虑,像茅盾把抽象的外在观念强行注入作品,艺术上必然失真,当张资平附和流行的革命文学观念,放弃自然主义的手法,也就注定了他的失败。情感的从容则关乎想象的规范。所谓想象规范,就是素材的分解和重组,是“文艺家的审美情趣的一种造型法即净化或抽象”(注:《思想实验》,夏中义著,学林出版社1996年,68页。)。鲁迅的《朝花夕拾》为什么比《野草》,比他的杂感在艺术上更美?因为它是对回忆的从容咀嚼,遂绵长有余味。为什么他写农村题材的小说艺术上超过写都市题材的小说?是如冯雪峰所说他是由于敏感到当时革命的问题在于农民是否觉悟和发动起来,这才决定了他的眼光注视农村和农民呢,还是出于天才作家对时代气息的敏感?李长之说得好:“他最初对于取材上,是无所谓的,并没有革命文学的,或平民文学的,普洛文学的企图,他却只是真正有着一些偏不能忘怀的感印,他要写出来以驱散寂寞”(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4页。),“诗人是不知不觉,而作了时代的代表的”(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5页。),诗人是被动的,印象的,情感的。因此,“大凡在某一方面情感极盛,又不得宣泄时,那故作平静,以用以安定了自己的,就是返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逃躲,这便是回忆”(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0页。)。正是回忆隔开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把原初情感的粗糙涤净了。“审美的领域,是在一种绰有余裕,又不太迫切,贴近的心情下才能存在,然而这却正是鲁迅所缺少的”(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9页。)。这是其杂感文情感太烈的缺陷所在。因此,对艺术作品而言,表现情感要有节制。应是“如火焰之只许见其火星的,是如诗人荷马所形容的乌里塞斯的吐字,像雪片一样,虽然纷纷不息,落在地下却是安详的”(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257页。)。而情感表现的从容源于人生态度的从容。想象动力最终决定了想象的规范。
然而,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回忆雪片的飘落姿势未必不重要,这就是文学作品区别于音乐与造型艺术的所在。即“文艺的特质,应该向语言里去寻”(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52页。)。李长之引用一位诗人的诗句表明了他对语言的重视:“字是心灵的影子,/而不是照片;/那里有辛酸也有温暖,/或是我们过去,或是我们眼前”(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60页。),“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的化身,就是一种精神的结构”(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44页。),它对民族的精神内容和思想情感方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从这种观念出发,李长之主张重估文言文的价值,例如文言白话的分别何在,到底是史的先后呢?还是口语同笔写的相异呢?抑是艺术的与实用的差别?……这对我们今天的反思都仍富于启发。
在对文学与社会,时代,人生,道德,科学及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的厘清中,李长之得到了他对文学的比较成熟的看法:“文艺者乃是立于造型艺术与音乐二者之间的字的艺术。造型艺术,主要地是传达直观内容与感觉印象;音乐只在唤起感情与情调,而且无涉于直观内容;至于文艺乃是综合此二者的,而且因为综合二者之故,于是在将外在世界之可把握的直观予吾人之外,又将生命之力或内在生活具体化,换言之,即将这种直观的幻影创造而出。”(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61页。)因此,文学是诉诸情感与想象的语言艺术。李长之对情感,想象,回忆,直观等心理机智与语言表达的关系的思考,可以说与朱光潜对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80年代中国文艺心理学的重建也不无裨益。同时,这也是他推行感情的批评主义的一块基石。
二,文艺批评:激情火焰中的批评主体
文学既然是作家根于生命欲求对情感记忆的一种想象重组,那么,对于批评主体来说,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实行感情的批评主义,在对艺术作品的激情探寻中释放自我的生命感悟。
实施感情的批评主义,有一前提,就是批评家批评精神的高扬。李长之认为,“批评史是一部代表人类理性的自觉的而为理性的自由抗战、奋斗的历史。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批评是武器,换言之,就是人类理性的尊严之自卫”(注:《批评精神》,李长之著,南方印书馆1942年,39页。);“伟大批评家的精神,在不盲从。他何以不盲从?这是学识帮助他,勇气支持他,并且那为真理,为理性,为正义的种种责任主宰他,逼迫他”(注:《批评精神》,李长之著,南方印书馆1942年,39页。),可谓真力弥漫,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批评家的价值自觉与价值自居。正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自觉,李长之在《鲁迅批评》中独辟蹊径,把目光移向鲁迅的著译,从挖掘著者的文艺观来发现鲁迅对艺术的看法,从而寻找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本着艺术自由,批评独立的精神,李长之确也看到了意义。他非常欣赏卢那察尔斯基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看法:“纯粹的政治领域,是狭义。广义上的政治,乃是在国家机能的各部分上,都各有特殊的课题。政治家办理他们所不知道的领域的事的时候,常常有着弄错的危险”(注:《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189页。);“不顾艺术的特殊法则,则提起关于文艺政策的问题,是不成的”(注:《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189页。);因此在李长之看来,“艺术家和政治家的不同,他十分懂得”(注:《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189页。)。艺术家是“依了和政治家工作不同的法则,组织着自己的经验的”(注:《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189页。),倘若勉强,就一定是赝品。这种见地恰恰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针砭。在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国度里,正需要这样清凉的学理的甘露,而就在当时(1935年),胡风还没能从拉普影响的圈子中完全走出来。正是出于把艺术,把批评当作专门的职业同时也是事业来尊重,才使李长之发出了这样激情洋溢的呼告:“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与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统,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
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77页。)因此,在他看来,批评家是为批评而批评的,批评是超实用的,倾听内心的声音而批评,就是批评主体的人格,就是批评的真精神,是感情的批评主义的灵魂。
具体说来,感情的批评主义有三要点,“一是态度方面,一是批评方面,一是理解方面”(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4页。)。李长之这一表述有些含糊,但结合上下文来看,还是有迹可寻的。从批评家的批评态度来看,“该提出似乎和客观相反然而实则相成的态度来,就是感情的好恶。我以为,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亲切。在我爱一个人时,我知道他的长处,在我恨一个人时,我知道他的短处,我所漠不相关的人,必也是我所茫无所知的人”(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0页。),“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1页。)。批评的忠实是基于批评主体真诚的情感体验。在李长之对鲁迅,对屈原,对孔子,对李白,对司马迁的批评中,确实看到他与他们深刻的情感共鸣,即理想与现实冲突产生的寂寞感,以及一种矢志于理想的殉道者般的人格追求。情感的沟通正来源于相近的生命情感。
在注重感情的原则下,要注意两点:“一是在一篇作品中爱憎要各别。惟独如此,才不顾惜,才不求全,也才能够公平”(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1页。)。“爱憎各别”就是说对作品的好坏要褒贬作一分说,要如“老吏断狱,铁面无私;要加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要分析得鲜血淋淳;万不能婆婆妈妈,蜇蜇蝎蝎”(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47页。)。这就需要“理智的硬性”,豆腐渣一样一碰就碎的脑袋是不行的。要避免思想上的“懒”,抄近路,这就要求批评家要有哲学的训练。现代批评家随感寻式的批评,就是思想上的懒惰在作祟。二是“把带有自己个性的情感除开,所用的乃是跳入作者世界里为作者的甘苦所浇灌的客观化了的审美能力”(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1页。)。这就是说,爱憎各别要以对作家作品的切实理解为基础,对作家作品抱同情之了解。这就要求批评家做到:一,了解作家人生体验与感悟的中心观念;二,不但把自己个人的偏见偏好除去,就是他当时的一般人的偏见偏好,也要涤除净尽。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和作者的悲欢同悲欢。即以《鲁迅批判》而论,当时正流行政治阶级分析,就在瞿秋白、冯雪峰竭力挖掘鲁迅杂感中的进步的政治阶级意识时,李长之却以艺术的慧眼看到鲁迅的热切救世之心与从容地酝酿艺术素材的紧张与矛盾。当别人称鲁迅为思想家时,李长之以思想家对理论体系的精心创造的标准发出鲁迅在思想上只止于一个战士的论断,都是与流俗的偏见相悖的,显示出独立思考的勇气。三是要知道作者的社会环境,知人论世,这样才能不仅知道作品中“说的是什么”,还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在李长之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他就系统考察了司马迁生活时代的经济条件、社会风习与心理,时代精神及家学渊源等,从而发掘司马迁“自然主义的浪漫派”之由来。由此,就对批评主体的才气与学识都提出了要求。批评家所需的才气是灼见和审美能力。凭了灼见他迅速地由第一印象即抓到作品的核心;凭了审美能力,他马上尝出作品的高下。天才还须学识与理想的附着。批评家须有人生理想、艺术理想和社会理想,要有哲学训练、美学训练、社会科学的知识和伦理学的知识,有了这些丰厚坚固的知识储备,他才可以飞跃他的幻想力,以深刻的对创作家施以敬意的理解和评衡,完成求真的工作。而批评家“为忠实于艺术,* 忠实于自己,便决不能受了政治的意味的命令,专注意人的转变与否以检定作品的高下。批评家是创造的,不作八股。他更不能滑头,说什么让读者自己去体会的话。艺术家的人格,在用忠实保持艺术的尊严”(43)。正是看到了一些左翼批评家坐着概念的飞机去抢夺思想锦标的浮躁,李长之很推崇归纳法,也看到了鲁迅译书的意义:“有马克思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许多话。”(《三闲集》P140)否则,“解剖刀既未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3页。),都是希望把空洞的论争纳入到真正学术的层面作平心静气的学理探讨。
从作品批评的角度看,实施感情的批评主义,就是把作品中“感情的型”剥离出来。“感情的型”是最好的文艺作品,表现一种可沟通于各方面的感情。李长之从形态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我们看一个作品时,假设一分析它的成分,接受物质限制的大小排列起来,我们会一层层的剥,而发现一种受限制最小的层,这一层就是文艺作品之感情的型。根于某种程度而言,这近乎谈到文学的永久性”(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1-392页。),在接触作品时,我们会有许多物质的限制,如口说还是笔传?写的还是印的?这离作品核心很远。再进一步,如文言还是白话?代表什么思想?这是关于物质环境,即所谓作者的时代,所属的阶级等。可说触着作品的皮了。把这一层剥去,会见由作品情绪惹起的事实问题,如革命,失恋等。这层还可剥去,即到了作品的核心,“只有令人把握的感情,感情的对象却已经抽掉了。这种没有对象的感情,可归纳入两种根本的形式,便是失望和憧憬,我称这为感情的型。在感情的型里,是抽去了对象,有可填入任何的对象的,它已不受时代的限制了,如果文学的表现到了这种境界时,便有了永久性”(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1-392页。)。要注意,所谓抽去对象,其实是忘却了对象,而非真的抽去,欣赏到了令人忘却感情的对象的地步,这是内容与技巧的极致。这是从“外层剥”见到的“感情的型”,从“内层穿”也是这样,“越下等的作品,越使人注意了较外层而不能忘却”(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1-392页。)。
严格说来,李长之关于“感情的型”的论述理论上并非没有可议之处,如他对“情感的型”没有作明确的概念界定,又如他把文艺表现的情感形式归纳为失望与憧慢两种根本形式,这就似乎把文艺表现的丰富的情感形态,诸如恐怖、惊讶、悲悯、疯狂、神秘、激动、愤怒等排斥在情感造型的门外,丰厚的文艺情感也就变得单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他很赞赏孟子对批评标准的理解。个性差异导致批评标准的形态的多样性并不能从根本上否认批评标准的先验普遍的存在。在他看来,批评标准牵涉到审美能力。审美能力是客观的一致的。因此,批评是对这种审美能力的“一种解放”,“一种唤醒”。李长之为“感情的型”的存在提供的四条论据就是从这一角度着眼的:一是从认识方面看,“人有趋于形式的趋向”;二是“就感情的性质讲,原是不问内容的”;三是从审美经验看,鉴赏好的文艺,往往只誉下“感情的型”而忘了今天的对象;四是从文艺批评的往例看,文艺作品的情绪,是“可代以他种内容的”(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3页。)。所以,在李长之看来,艺术永久的魅力在于她表现了一种普遍的恒久的源自人类本笥的精神力量,情感力量,而当作家把这种浸润了自己情感体验的思考(素材)经过想象虚构等形式手段,精心组织加工,使这种原初的粗糙的情感体验从现实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艺术造型时,情感就从材料因转化为形式因;并且,由于这种情感力量饱满充沛,精力弥满,故能“假于艺术的形式而超乎艺术的形式”(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1页。),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达到技巧的极致与当时注重政治阶级分析的主流批评语不同的声音,即他不是指向现实的政治关怀,而是指向对人的精神生命与总体文化态度的。
从对作家的理解方面看,“感情的批评主义之再一点,是本了感情的扩散性,以帮助了解作者”(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4页。)。什么是“感情的扩散性”呢?李长之没有做概念的界定,只简单说“就是和迁怒类似的一切感情作用”(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4页。),如“一个人因为失意于女人,遂绝望于世界”(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4页。),“感情的扩散性,可以容易得到那作家的哭笑的真面目”(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94页。)。推测其意,大约是说由作品中的表现的情感,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以风格释人格的意思吧。在批评实践中,李长之也是这么做的。
这是从批评主体来要求文学批评的。诚然,文学批评的产生,从客观上还需有宽容的土壤。李长之悲愤地说,中国往往太要求“定于一”,太不能容纳不同于自己的立场。“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焚书坑儒的倾向的,只要那书不是自己一派的书,儒不是自己一派的儒”(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75页。),“思想的斗争必须在思想的范围以内去解决”(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76页。),“人类的历史悲剧却往往产生在以思想以外的方法来作思想上的斗争。西洋如此,中国尤甚。中国过去如此,而中国现在更甚。批评必须说真话,如果思想问题和思想以外的事情(例如政治)搅在一起,便很容易做出许多‘违心之论’,这便不会产生真的批评”(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76页。)。洞若观火是因为心有戚戚。他的批评是以血书者。在对文艺批评的生态环境的批判中,在对批评自由空间的拓展中,李长之的批评触角自然而然地伸向了文化哲学领域。同时也可以说,李对创作与批评的思考是有其文化价值观作支撑。
三,文化批评: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
李长之的文化批评是在他对中国当时的文化境遇的深切体验中产生的,因而也赋予了其文化批评以一种饱满激情与实践品格。1937年,他准备去仰幕已久的德国留学,已走到边境了,却接到国民觉通知,须承认“满洲国”,并改从东北绕道出国。他痛恨这种卖国政策,更不能接受必须承认伪满政府才能留学的条件,遂放弃留学。这一事件,在他生命史上当是浓重的一笔。1938年,他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但民族意识的加强并未改变他以文化批评为本位的立场。在他集中表述其文化观点的《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的《序》中,他说明了此书的写作缘起,表现了他在民族危难中的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三八年离开昆明,途中重读《论语》数过,一方面感到‘仁者不扰,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伟大,一方面感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的深切,前者给我鼓励,后者使我戒惧,我同时也便想到许多文化问题”;比如“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这题目便重又跳在我心头了,我深切觉得偏颇的杀人的国防文化害了多少人,中国的读书人都应该勉为文化的长城,负起文化国防的重责,让文化国防是目的,国防文化是手段,本末千万不可倒置,倒置了就会把文明的20世纪又驱入中世纪了。”于是“当我慢慢看到意识到抗战胜利在望,想到战后一切建设,在那百废待举之际,文化建设岂可忽略?在我们这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人,似乎至少应该对文化建设问题贡献一点意见。一个民族政治上压迫解除之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它喝路,于是定书名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鲜明地体现了一个自居为民族文化长城的卫士,要为中国文化把脉的雄才大略,以及一种庄严的使命感,道义感。
需要先澄清一下国防文化与文化国防的概念。所谓国防文化,“就是由国防观点而树立的许多文化事业”(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9-10页。),“是以国防为目的的”(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9-10页。);而文化国防,“就是由文化观点而看到文化价值,而想到必须采用的许多保卫手段和方法。在这许多手段和方法中,国防文化当然不失为非常重要的一种,但是这不是惟一的。凡所谓文化价值,乃是指较为经久的价值的,也是靠本身而存在的价值的,所以这不是只凭坚甲利兵,或飞机大炮所能济事的”(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9-10页。)。所以,国防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民族所以生存的手段,而一个民族的生存,又是一个民族所以实现其文化或精神的手段。国防文化是从民族的生存出发的,文化国防是从民族的文化或精神出发的,二者出发点不同”(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9-10页。)。同时,从性质上看,“国防文化是偏于物质的,是科学的,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问题;文化国防乃是偏于精神的,是思辨的,哲学的,伦理的,价值的,文化的问题”(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9-10页。)。民族的价值,不在于为国防而国防,否则会“蔑视了文化的价值”。“造成人类的罪恶”,“而当为文化价值而战斗”(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9-10页。)。所以,假如说民族主义,则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政治层面上基于爱国情绪的保家卫国意识,一种看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本身的价值,为保卫文化价值而保卫民族的意识,这种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世界主义,是把民族文化当作人类总体文化价值的一分子来看待的,李长之无疑是属于后者。
正是从文化国防的立场出发,李长之考察西洋史,重估“五四”精神文化遗产,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溯源中建立起了浪漫与古典并重,情感与理智和谐发展的文化理想国,在对现阶段的思想建设,舆论建设,精神建设的全方位的文化设计中,期待未来中国文艺复兴的到来。
在李长之看来,“文化是有机的,绝不能截取,文化是延缴的,绝不能和传统中断。但文化也是生长的,它需要外界的营养,正如它需要本国的土壤和水分”(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58页。)。那么,他看到的是怎样一种文化传统呢?
一,“五四”文化运动的评价。李长之是服膺“五四”文化传统的。最大的表现就是对“五四”个性自由信条的坚守。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具现代化色彩的一面。他对国民卑怯根性的批判,也是“五四”国民性批判的某种延续。但是他也看到了“五四”文化运动的不足。他首先否认“五四”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因为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再生,尤其是古代思想方式,人生方式,艺术方式的再生”(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4页。)。文艺复兴探知了希腊古典文化之最内在,最永久的部分,即人性之调和,自然与理性之合而为一,精神与肉体之应当并重,善在美之中,健良,和谐,完善而充实的人文精神,而“五四”不但对于中国自己的古典文化未来得及梳理,对于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没有吃透,它基本上是一个移植的文化运动,截取了西方近代文化运动这一阶段成果,而非全盘吸收,似乎只是让西方思潮史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匆遽重演,因此它在文化上是一个未得自然发育的民族主义运动,因为那时没有民族的自信,也因此,它在文化上最大的成就是自然科学,而对于形上学或人生问题缺乏深挚的吟味,因此它只能算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启蒙运动“乃是在一切人生问题要求明白清楚的一种精神运动”(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6页。)。明白清楚就容易缺少深度,所以“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清浅的理智主义,与之相伴的则是唯物思想和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之最害学术者,则以应用为学术之目的也……功利主义以最大多数为万事之标准,故其论学术之效用,既以多数之享受为衡,其评学术之优劣,既以多数人之意见为断,此亦足以挫真才之气,而阻扼学术之进步也”(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8页。)。归纳法之不精,想象力之薄弱,把一种“客观,体系,思辨,精确”的科学精神理解为机械的科学主义,民主的尊重人权与自由的精义蜕变成众数的意志,学术的堕落,也是国民精神的堕落,这些思考,某种程度上已经与我们今天对“五四”的反思接上了轨。
既然“五四”由于民族缺少自信力导致了精神上的贫瘠,情感上的偏枯,见识上的清浅和鄙近,那么在现在业已走上民主解放之途的情况下,也应该给文化以解放。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是新的文化运动的姿态。那么该怎么做呢?
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之寻根。一方面,李长之主张全面彻底地吸收西洋文化,以填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文化真空,显示出比左翼文坛的精英如胡风等人宽广得多的视野。因为同是服膺近代人文主义的精神,胡风眼里只有高尔基为代表的世界进步文艺,而李长之则在对德国文化的深入研习与浸润中转益多师,由此获得了更宽的眼光与胸襟。另一方面,李又强调要对本民族文化的核心有了解,在继承民族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重建新文化。他非常赞赏冯友兰的两句话,一是在宋明理学的基础上“接着讲”,而非“照着讲”,二是“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可以说,这是他文化批评的座右铭。他正是希望在接着中国本土营养的灌溉,而非照着传统开历史倒车的征途中,让民族文化之根自由伸展,而不愿让民族文化建立在沙滩上。
中国文化的精髓何在?如果说中国有一种根本的立国精神,能够历久不变,能够浸润于全民族的生命之中,又能够表现中华民族之独特的伦理价值的话,李长之认为它在原始儒家孔孟的经典中。儒家的精神好像是以孔孟为人格载体的。孔子的真价值,“在他那刚强,热烈,勤奋,极端积极的性格。这种性格却又有一种极其特殊的面目,即是那强有力的生命力并不是向外侵蚀的却是反射到自身来,变成一种刚强而无害于人,热烈而并非幻想,勤奋而仍然从容,极端积极而丝毫不计成败的伟大雄厚飞魄”(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59页。),也就是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一种古典中的浪漫,把一种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内心的道德律令。而孔子还是一个“收敛了的孟子”。就是说,孟子把孔子的这套道德心性修养推到了极致。李长之非常赞赏孔子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不计成败的精神,在他看来,孔孟正代表了一种勤奋不懈,深厚宏大,“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的刚性文化,一种“不稚弱,不琐碎,不浅薄,不单调,不暂时,不变动不居,不殆滞不前”(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25页。)的玉的德性文化,孔子是这种文化的最好的人格代表。如果说孔子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那么“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的屈原,则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心灵,因为他是浪漫中的古典。两者构成了中国人伦的两要极。
正是对这种反功利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精神的弘扬,使李长之激烈反对老庄的道家思想。“道家终于脱不掉功利色彩,其诱人处不过叫人避苦就乐,如佛家然,他的眼光始终没出乎个人圈儿,没有看到庄严的人类,没看到社会”(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278页。);“道家是虚无主义者,宿命主义者,一切悲观,一切讥讽,他们那里没有光也没有热”(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278页。);道家“空造下数千年来冷淡的人生观,无血色的人生观,短浅的人生观,误以糊涂为奥妙的人生观,对任何‘事不关已’的现象,作一个第三者,没有勇气,永远追随而不能倡导!道家是中国精神上的污点和耻辱,其斫丧中国元气处完全是不可挽赎的罪孽”(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278页。)!极而言之的背后,体现了强烈的用世之心。
不可否认,孔孟原儒中那种自强不息的弘毅之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牺牲精神令人感佩。道家思想中也不乏污秽之处,如讲究阴谋权变的君子两面术,强调“安时顺处”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对人的创造性的束缚,对国民奴性性格的培养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也因此,李长之通过对司马迁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心灵与精神的探寻,提倡反功利,提倡热情,提倡牺牲,以期给情感贫血诗性苍白的国民注射一剂文化的强心计,也便有了意义。他说“司马迁之赞美孔子乃是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立场而渴望着古典精神的”(注:《李长之批评文集》,郜元宝、李书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页。)(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李长之著,商务印书馆1946年,131页。),正体现了他对一种健朗,热情,充实,和谐,坚忍的人格的向往,与对卑劣,猥琐,世故,圆滑,功利的人格的摒弃。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一是道家思想为何能存在两千多年,它与儒家思想仅仅是一种对立关系呢,还是一种补充?如果是一种补充那么其价值何在?二是奴性性格,自私根性仅仅是道家一手制作的呢,还是儒道合谋?
李长之很清楚,怀抱道家浪漫的自然主义的司马迁,他的悲剧在于无限的浪漫精神是“不屈服于任何权威的”,“是没有任何奴隶的烙印的”,而要在汉代一线相承的刻薄的残酷统治中写作如《春秋》一样微言大义的《史记》,想以帝王之师的身份在官家历史的夹缝中赢得一些仁义的呼吸,只能是虚幻的梦;道教徒的诗人李白之悲剧一方面固然在于他是以有限的肉身追求无限的存在,成仙无望,这样的源于生命本身无常之痛苦,另一方面,李白的人间世俗情趣又非常浓厚,把自己的价值生命寄托于现世政伦权力系统,对于一个孤标傲世的诗人来说,当然只能是带来世俗理想的幻灭,从而发出“才高竟何流,寡识冒天刑”的哀叹;而浪漫精神充溢的屈原之悲剧,在于“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正道直行’正是屈原碰壁的根本原因”(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李长之著,三联书店1984年,318页。)。而“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就是中国整个社会上下五千年的总罪状”(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李长之著,三联书店1984年,318页。)!屈原正是以自身生命作了愚妄政治的祭礼。
因此,儒家的个体人格之实现是深深地依附于权力系统之中的。个体价值只能施展于对君王和国家的效忠,也因此,当一个人把集权意志内化凝聚为个体道德命令,道德他律变而为道德自律时,异化的痛苦便不可避免。可以说,道家正是出于对人的本体自由的关怀,在对霸道政治与社会世相的清醒的审视中看到了把个体人格依附于权力的可怕,从而希望在适性逍遥的审美态度中观照人生,重生保身,以期灵魂的安宁与心灵的自由。李长之把儒家思想对个体人格的戕害全然归结到历代统治秩序,强调这是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不是儒家思想本身造成的,是偏颇的,他打比方说:孔子被历代帝王利用了,责任是在历代帝王,不在孔子。就好像:“强盗用火烧房子,火可以说被强盗利用了,难道也是火的过错吗?”(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3页。)然而李长之忘了,火与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有思想。应该说,孔子确实为原始氏族统治开了一剂药方。以理节情,道德自律对个体自我人格与情感的压抑,使思辨力与想象力都不得自由伸展。“乐天知命”,“安贫守道”与道家的“无为无不为”,“安时而顺处”等观念结合起来,共同对逆来顺受、卑劣委琐的奴隶人格起作用。李长之在热烈的赞同儒家的审美教育、道德教育培养的是“全才”,甚至主张以“审美”作为他的“中体西用”文化理想的“体”时,忘了一个大前提,即这种审美教育是依附于传统的伦理教育的,是为培养传统的政论性人格服务的,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意义上的人文人格之培养!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使他对国民性的批判达不到鲁迅的深度和力度。鲁迅是试图在彻底击破传统文化的堡垒时重建新文化,塑造新人的;李长之则频频回首,温情地顾盼传统文化人格塑像,希冀在原儒的经典中发掘道德与美的真谛。这就使他更像一个文化布道者而非启蒙家。
好在李长之是真诚的:“先民之伟大的思想创造,当然会值得发扬,但我们不盲目崇拜,而是发扬需要发扬的方法,这方法是惟有科学的方法(就是需客观,需体系,需思辨,需精确!)可以当之。否则牵入死人的坟墓,这是不发扬古人,却是葬送今人了!”(注:《教道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56页。)是的,守卫传统文化的某种价值,须是将这种萎靡不振的传统格局彻底打破,再将这价值作为文化因子重新整合到新的现代文化格局才可能重新赢得长久的生命力。
最后我想说,真诚源自信仰。李长之的批评激情,与其说是民族文化危机所激发的,不如说是信仰的上帝启悟了他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始终长在独立而坚韧的大树上。如果说对于一个浪漫诗人而言,理想天国的降临,在于他对自身内在诗性与灵感狂潮的全神凝谛与虔诚企盼(因为诗是他真实信仰的上帝),那么,对于一个热情而执拗的文化守灵人来说,伟大的文化精魂永不磨灭的姿势,正是对自由天空的深情凝眸!
标签:文学论文; 温儒敏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文; 文化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鲁迅论文; 读书论文; 胡风论文; 文艺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