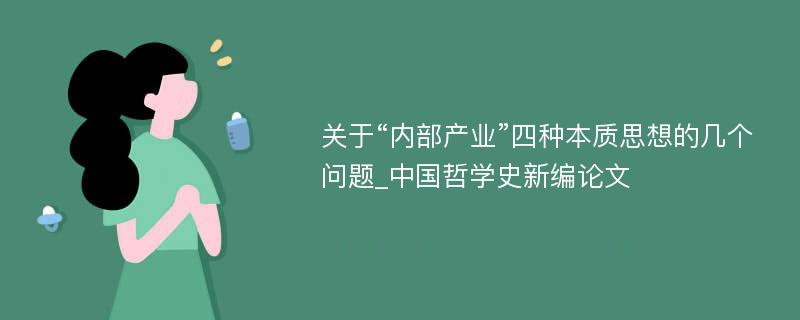
关于《内业》等四篇精气思想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气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数年前,我曾在《管子学刊》发表过两篇关于《内业》等四篇的文章,即《〈内业〉等四篇的写作时间和作者》(1987年创刊号)和《〈内业〉等四篇的精气思想探微》(1989年第2期)。 这两篇文章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有关史料和我的理解,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这两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后来被收入拙著《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作为此书的第四章第一、二节。我深知,关于《内业》等四篇的一些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我的一些观点虽然自审尚属“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不敢自以为确论,只是为学界备一说而已,许多问题是可以通过学者的讨论、辩驳而逐渐趋近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真实的。
在我的两篇拙文发表后,曾拜读过《管子学刊》以及其他刊物发表的有关《内业》等四篇的一些新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与我的观点有同有异,我想这是很正常的事。《管子学刊》1996年第1 期发表《〈管子〉的精气说辨证》一文,此文提出《内业》中的“‘凡物之精,此则为生’并不是指精气结合产生万物”,并且断言“在先秦气论的发展史上还没有自然万物是由精气结合生成的思想”。我对前一点虽不敢苟同但不感到奇怪,而对后一点则未免怀疑作者是否统观或细读了先秦气论的其他史料就作出如此的推断。
近日,又读《管子学刊》1996年第4 期发表的《论〈管子〉‘精’、‘虚’概念的科学与哲学意义——兼探讨是否存在〈管子〉的”‘精气论’及其他》(以下简称《意义》),此文开篇言“有比较才有鉴别”,因而列举了包括我的一篇拙文在内的几篇关于《管子》的精气论的文章。读此文后方了解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即上述《〈管子〉的精气说辨证》(以下简称《辨证》)一文的作者与《管子学刊》1992年第4期发表的《〈管子·内业〉篇新探》一文的作者是同一人。 《意义》一文指出,“同一位作者”在先后两篇文章中“同样引用‘凡物之精’这段话,然而却作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使我愈发感到《内业》等四篇的问题的复杂,作出“相反的结论”并不使我感到奇怪,但同一作者对一同段引文“却作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足以证明《内业》中的文字是多么容易引起异解!而同一位作者在作出相反的结论的时并没有对此前自己的观点作出一定的解释,这除了文风上的欠妥外,也足以说明此前的那种观点是多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或推倒!
然而,更使我关注的是《意义》一文提出:“所谓‘《管子》精气说’是强加的东西,它是作者虚拟的,因此可以任凭作者忽而这样解释,忽而那样解释……”此文的观点比《辨证》一文的观点更进一步,即不仅否认《内业》的“凡物之精”一段话“是指精气结合产生万物”,而且根本否认“凡物之精”是指“精气”,否认“存在《管子》的精气论”。《辨证》一文的作者先后提出两种相反的结论,这似乎成为《意义》一文否认存在《管子》精气说的一种证据。而《意义》一文更强调:“精是精,精气是精气,两者不可混淆,更不可使‘掉包计’。”此文作者发现了《内业》等四篇使用“精气”概念“只有两处”,但在对这两处“精气”概念没有作出任何正面解释的情况下,就断言:“上述所用‘精气’一词,并非视精气为‘产生或构成宇宙万物’的‘精气论’,又非‘把精气看作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本原’的‘精气说’,也非‘以精气为化生世界万物的元素和本原’的‘精气思想’。”这里所提到的“精气论”是针对此文所列举的《管子学刊》1994年第1 期发表的《从〈管子〉的精气论到〈庄子〉气论的形成》,而“精气说”则是针对《〈管子·内业〉篇新探》,至于“精气思想”则显然是针对我的《〈内业〉等四篇的精气思想探微》了。而且,此文还明引了我这篇文章中的两段话,其一即拙文开篇所说“《管子》书中的《内业》、《心术》上下和《白心》等四篇的作者……明确地提出了以‘精气’为化生世界万物的元素和本原的思想”,其二即“‘精气’概念不见于春秋和春秋以前的历史记载和著作,而首见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水地》篇,又见于《易传》等著作”。从时间上说,我的这篇文章是在先的,既然《意义》一文对以上三篇文章的观点都予以否定,而且作者期望“共同研究‘辨证’的辨证”,就此进行“认真讨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内业》等四篇精气思想的几个问题再申明自己的观点,以与《意义》等文的作者共同商榷。
一
我在《管子学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主要是通过《内业》等四篇与《庄子》书有关文字的比照,说明《内业》等四篇作于庄子之后。在我的文章中,有一个《内业》等四篇与《庄子》书有关文字的对照表,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它们或在思想上相承,或在文辞上相袭”;然后我肯定了前人曾作出的“庄子不是抄书的人”的判断,并且试举三例进行分析,证明《内业》等四篇作于庄子之后。第一例是对《白心》篇所谓“为善乎毋提提……”与《庄子》内篇《养生主》中“为善无近名……”的分析;第二便是对《白心》篇与《庄子》外篇《山木》中都有的“功成者堕,名成者亏”两段话的分析;第三例是对《内业》和《心术下》“能抟乎,能一乎……”与《庄子》杂篇《庚桑楚》中“卫生之经……”的分析。这些分析能否成立,有待于其他研究者鉴别。我在此文的注释中还指出了张恒寿先生的《庄子新探》和程宜山同志的《中国古代元气学说》有与本文基本相同的观点。另外,我后来还注意到王博先生在《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发表的《〈黄帝四经〉和〈管子〉四篇》一文中,对我的《管子》四篇作于庄子之后的观点给予了肯定。
然而,《从〈管子〉的精气论到〈庄子〉气论的形成》一文则持与我相反的观点,即认为《管子》的精气论在先,《庄子》的气论在后,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两种不同的观点是可以进行讨论的,但此文在提出这种观点时却没有就二者先后的问题进行任何具体的论证,更没有对我所作的分析进行辩驳。这样,两种不同的观点就无从进行讨论,而只能长期并存了。我对此深感遗憾,这一是因为此问题不解决则影响对战国时期哲学史各个发展环节的理解,二是因为《内业》等四篇的文字较为简奥,有些用语不规范、不统一,易生歧义,如果借助《庄子》书的背景或可在研究上取得进展,而如果《庄子》书在《内业》等四篇之后,则对《内业》等四篇精气思想的理解就会有更多的困难。因此,我希望在对《内业》等四篇的精气思想进行讨论时,能对其与《庄子》书的先后问题有所涉及。
二
《意义》一文否认“凡物之精”是指“精气”,认为“精是精,精气是精气,两者不可混淆”。它在引述我的“‘精气’概念……又见于《易传》等著作”一段话后,接着说“这篇论文并未具体列出《水地》篇哪些地方出现‘精气’这个概念……”而却忽略了我所说“《易传》等著作”的“等”字。我在此话之后紧接着说:“在《水地》篇和《易传》中,‘精气’不是首要的哲学范畴,其意义也不是很明确。”这是我在此处没有具体列出《水地》篇哪些地方出现“精气”概念的原因〔1〕。然而, 我又紧接着说:“在《庄子·在宥》篇中有‘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的说法,在《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中有‘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的说法……”我之所以引述《庄子》等书的史料,是想把《内业》等四篇中的‘精气’概念放在《庄子》等书的背景下,放在春秋战国和秦以后气论发展的过程中去理解。如果像《意义》一文那样,单独分析《内业》和《心术下》中出现的两处“‘精气’这个名词”,那么就较难理解“精气”概念的内涵。《意义》一文在引述了出现“‘精气’一词”的两句话后,只是对“精气”作出了它并非“精气论”、“精气说”和“精气思想”的否定性结论,而正面的解释充其量只有“乃是人的精诚所至抟气如神罢了”。我不知“抟气如神”在作者的语言中当作何解,只以此令人费解或与作者的观点可能相迕的话就否认了《管子》的“精气”概念和精气思想,未免过于轻率!
《意义》一文否认“凡物之精”的“精”是指精气,认为这样就是“偷换概念”。然而,我在具体论述《内业》等四篇的精气思想时首先就指出:“《内业》篇云:‘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这是给予‘精’字一个物质的、‘气’的规定,但对‘精’字本身没有作出解释。”于是,我在后面根据有关史料给出了“与‘精气’概念相联系的‘精’字”有细微、纯粹、神妙和精神四层含义。《意义》一文断然否认存在《管子》的精气说,认为这是:“虚拟的”“强加的东西”,但却丝毫没有涉及“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这句史料。《内业》篇在“谓之圣人”的后面有“是故民(此或名)气……”《意义》一文对此也丝毫没有涉及。我不知作者是有意的回避,还是认为这两句话乃《内业》中的衍文,抑或在读《内业》时没有发现这两处“气”字,抑或在读我的文章时只是读了前面的几行就没有继续往下读?
我在文中还指出:“《心术》下说:‘一气能变曰精’,这是对《内业》‘一物能化谓之神’的解释。”我在综合“精”字的四层意思,指出“‘精气’即细微(……)、纯粹、神妙之气,它进入人的身体可以转化为人的精神”之后,才引述“凡物之精……”一段话,随后作出分析,指出“《内业》等四篇的作者认为,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是‘精气’所生”。再往后,我又一次列举了《内业》的“一物能化谓之神”和《心术》下的“一气能变曰精”,指出“‘一气’也就是‘一物’(《内业》篇‘凡物之精’实也就是‘凡气之精’)。”《意义》一文对这些论述丝毫没有涉及,我不知是作者认为这些论述有误,还是根本就没有读这些论述?如果有幸是第一种可能,那么尚请作者能将我的失误指出一二。
在我看来,《内业》篇的“凡物之精”,就是“凡气之精”,所谓“以‘精气’为化生世界万物的元素和本原的思想”并不存在“偷换概念”的问题或触犯“逻辑学上最大的忌讳”。此问题可以进行正常的学术讨论,但请勿把别人的有关论述有意或无意地抹杀掉;如果对别人的文章未曾卒读就进行批评和否定,这岂不是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的“最大的忌讳”!
三
《意义》一文否定了《管子》的精气论或精气思想,而把“凡物之精”的“精”解释为“一切细微之物”,然后指出:“除了《管子·内业》讲到的由一切细微之物(精)产生五谷……等等以外,《管子·心术上》还讲到:‘无之则与物异矣,异则虚;虚者万物之始也,故曰可以为天下始。’这样,管仲学派以‘精’和‘虚’作为‘万物之始’……我们可以把它和古希腊原子论者的观点作一比较……”这也就是《意义》一文所要论述的“《管子》‘精’‘虚’概念的科学与哲学意义”了。然而,在古希腊原子论者的思想中,“原子”与“虚空”是两个相互对待、不可相离、不可相生的“二元”概念。《意义》一文从《内业》取来“精”,从《心术上》取来“虚”,由此而构成“二元”,这是否有些牵强呢?
《心术上》云:“虚无(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唯圣人得虚道”;“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心术上》所谓“虚”即指“道”而言,其作为“万物之始”的只有“虚”或“道”,而没有其他的概念与“虚”或“道”构成二元的关系。如果《意义》一文的作者沿用现学术界一般认为《内业》与《心术上》的思想属于一个系统的观点,那么在《内业》中有:“夫道者,所以充形也”;“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灵气在心,一来一去,其细无内,其大无外……心能执静,道将自定”。显然,《内业》所谓“道”也就是《心术上》的“道”,而《内业》所谓“道”也就是“灵气”或“精气”。正是因为此,现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内业》等四篇的作者改造了老子或老庄的哲学体系,认为“道”就是“精气”;我在我的文章的开篇也沿用了这一观点。《意义》一文的作者可以不同意这一观点,但认为在《内来》和《心术上》的思想中“精”与“虚”是二元的概念,认为《管子》的“精”“虚”概念与古希腊的原子论“何其相似乃耳”,这是很缺乏史料根据的。
关于中国气论与现代物理学的场论相通,我在我的那篇文章中稍有涉及;而这一点以及对中国气论与西方哲学的原子论和非原子论的比较,我在拙著《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的第六章有较多的论述,学人如有兴趣可参考,或进行讨论、批驳。
四
《辨证》一文的作者对此前他所同意的“《内业》篇把精气看作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本原”的观点进行了“辨证”,提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并不是指精气结合产生万物”,“可以将‘凡物之精,此则为主’注释为:物的精气,有此才使万物得以生”。我觉《辨证》一文所作的“辨证”的确涉及了理解《内业》篇精气思想的一个困难,但由此困难而提出的新说却留下了更大的困难:此说无论从古汉语的注释、现代汉语的翻译,还是从观点与史料的统一上说,都是很难成立的。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的“此”,从语法上说只能是一个动词。因此,认为“此”或为“化”之误,或为“比”(结合)之讹,在语法上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如《辨证》一文注释为“有此”,则“有”字从何来?“增字解经”,古人所忌讳,今人更当避免。“物的精气”,则精气已是物所有:“有此才使万物得以生”,“有”字无着落,“万物得以生”乃是物得之于自己。——古人运思作文恐不至于如此迂曲。
《辨证》一文对《内业》篇的解说还有:“人得到精气则生,失去精气则死;万物得到精气即能生成。”“不是精气的结合而生成人,而是精气使人具有生命和健康。”精气能使万物生成,却不是使人生成。——这种解说也很怪。《辨证》一文实际上是把“此则为生”的“生”解释为生命或活力,但《内业》篇在“此则为生”的后面紧接着就是:“下生五谷,上为列星……”依前后文意,两个“生”字只能解释为产生。《内业》篇云“……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这也只能解释为:使万物得以产生和形成的,称之为道。
《内业》篇较易使人发生疑问的是在“此则为生”的后面提到了“五谷”“列星”“鬼神”和“圣人”,而未及其他。按现代人的划分,“五谷”属于植物或有机物,那么《内业》篇是否认为无机物不是“精气”所生呢?实际上,体察《内业》篇的文意,这不是一篇未带感情色彩的纯粹认知理性的“哲学论文”,而是充满了对“精气”或“道”的褒扬、赞颂甚至神秘化。如果《内业》篇只是想说明“精气”产生有机物,那么比“下生五谷”更规范的表述当为“下生草木”;如果《内业》篇在此根本无意划分有机物和无机物,那么“下生水火”“下生土石”“下生草木”都不如“下生五谷”更带有感情色彩。因此,我认为此处的“五谷”“列星”是代指一切物质现象,这是讲得通的;而如果穿凿文意,认为无机物不是“精气”所生,那么则与后面的“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相矛盾了。古人言“万物”与今人言“万物”意义大致相同,“万物”或有时未包括人,或远处的天体,或宇宙的始基,但从不作有机物(草木等)与无机物(水火等)的区分。
《内业》篇最易把现代读者引向歧途的是这样一句文中很重要的话:“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50、60年代,冯友兰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讲到这句话时说:“照《吕氏春秋》所说的,有精气,有形气……照《内业》篇的意思,天是精气所构成的,地是形气所构成的。从这一方面说,稷下唯物派也许认为精气相当于阳气,形气相当于阴形。无论如何,他们认为人所有的‘精’是从天得来的;人所有的‘形’是从地得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0页)这种表述如果不细读, 很容易使人发生误解。
一种误解是:在《内业》篇中有精气,有形气,因《内业》篇没有讲明形气从何而来,那么精气与形气就是二元的概念。实际上,这种误解是应该排除的。《内业》篇既然已经说精气是:“其大无外”,那么就已经排除了在精气和精气所产生的东西之外还存在任何其他的东西。冯先生在书中还引了《白心》篇的一段话:“道之大如天,其广如地。……一以无贰,是谓知道。”并且指明这里的“道”“也就是‘精气’”(同上书,第284页)。作为万物的始基,精气是“一以无贰”的, 没有任何东西能与精气构成相对待的二元关系,因此我们只能推断如果在《内业》篇中有“形气”概念的话,那么“形气”也只能是精气所产生。在先秦气论的所有史料中,“形气”的概念可能只见于《吕氏春秋·尽数》篇一处;而形、气对举,认为形是气所产生,则在《庄子》等书中有很多的论述。《尽数》篇所谓“形气”,似是指已成为形之气,或气所产生的形;这在秦以后的气论思想中,意义是比较明确的,如王廷相所云“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雅述》上篇),此无须多论。“精气”是细微之气(我在我的文中以及其他论著中曾多次指出,此细微“不是一般的细微,而是‘其细无内’、‘至精无形’”,我窃以为能理解此处的矛盾或奥妙,算是对中国气论的理解达到一个相当的深度)(参见拙文《从两个“迷宫”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哲学研究》1988年第10期), 正如冯友兰先生在其新版《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所说:“既然有‘气之精者’,也必有气之粗者。”(《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4 页)此“气之粗者”构成了与天相对的地,又成为人与万物的“形”的来源。粗气是不是由精气转化而来?这在先秦史料中可能确无明确的论述,但从《老子》开始,天地都是从“一”分化而来,《庄子》甚至说天地是“形之大者”,阴阳是“气之大者”(《庄子·则阳》),天地都是气所生,那么由此推断:构成地的粗气肯定是由无形的气或精气转化而来。可能到了汉初,天地如何从气分化出来才叙述得稍详,如《淮南子·天文训》所云“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至于粗气如何从精气转化而来,可能到朱熹才算是讲得明白,如云:“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朱子语类》卷一)如果期望《内业》篇把朱熹所说的话出能讲出来,那么期望值可谓过高了。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一种很普遍的倾向,即总是把最初的也就是作为宇宙万物始基的东西看得最高、最有价值。老庄哲学是如此,以至后来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也是如此。这一倾向在《内业》等四篇中也表现得极为强烈,这也就是所谓精气“藏于胸中,谓之圣人”等等。《辨证》一文对此曲为之说,认为“有精气‘藏于胸中,谓之圣人’的说法,言下之意,即存在着不藏有精气的人的形体”。那么,这种“不藏有精气的人的形体”当首先是指“圣人”之外的凡人。而“五谷”尚有精气,凡人能没有精气吗?如果不理解精气本身有精粗的变化、有古人所理解的价值层次的高低,把精气与粗气截然对立起来,那么就会得出很荒唐的结论。
冯友兰先生在其新旧两版《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认为《内业》等四篇把精气或气作为唯一的本原,这是很明确的。他在讲到“凡物之精”一段话时说:“总之,从物质现象到精神现象全都是‘气’构成的,一切事物都是气的变化的结果。”(《中国哲学史新编》1962年版279 页,1984年版第203—204页)然而,《辨证》一文却完全陷入这个歧途,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对“天出其精,地出其形”作出了误解。
《辨证》一文的误解,也就是冯友兰先生在讲到这句话时容易使人发生的第二种误解。《辨正》一文在“……合此以为人”之后说:“在这里,精气与形显然为二物,而人是精气与形的结合。”这也就是把“天出其精”的“精”解释为精气,把“地出其形”的“形”解释为与精气相对立的形体或形气。冯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人所有的‘精’是从天得来的;人所有的‘形’是从地得来的。”如果不细读冯先生的解释,而且已经发生了把“精气”与“形气”视为二元的误解,那么冯先生在此说的“精”很容易被人误解为是指“精气”,而“天出其精,地出其形”也就是天出天之精气,地出地之形气,由此而合为人。这样,“存在着与精气相对的形(气),人是精气与形(气)的结合”的观点出就发生了。但是,这种误解实是与冯先生的表述相悖的。冯先生说的是“人所有的‘精’、人所有的‘形’”,显然是把“天出其精,地出其形”的“其”解释为“人所有的”。我认为, “天出其精”的“其精”,或冯先生所说的“人所有的‘精’”,不是指与形气相对立的精气,而是指与人的形体相对待的人的精神。正因如此,我在我的文章中对“凡人之生也……”这句话的解释是:“天出人之精神,地出人之形体,人是天地合气所成。”我在讲这句话之前,已在文中以较多史料证明,在先秦以后的气论思想中,“精气”是有阴阳的,“阳之精气轻清,上浮为天;阴之精气重浊,下沉为地”,因而我所说的“天地合气”丝毫没有精气与形(气)相对立的意思。《辨证》一文的作者如果坚持认为“存在着与精气相对的形,人是精气与形的结合,那么恳请指正我所说之误。
五
《辨证》一文在对《内业》篇本文的解释陷入了歧途之后,接着引用了《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和《吕氏春秋·尽数》“精气之集也……”两段话,问道:“《庄子》的‘聚则为生’之‘聚’是否可解为《吕氏春秋》的‘集’呢?”然后,又引《荀子·王制》和《黄帝内经》的几段话,很粗疏的作了两句说明,便断言:“可见,在先秦气论的发展史上还没有自然万物是由精气结合生成的思想……”这样,作者在《内业》篇陷入的歧途就殃及了整个先秦气论。我想这一殃及未免过于粗疏和轻率了。
实际上,《庄子·知北游》中的“聚”决不可解释为《吕氏春秋·尽数》篇的“集”。“集”必有集合的一个处所或在什么东西内集合的一个地方,这也就是《尽数》篇所谓“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尽数》篇讲的“精气”类似于《内业》篇讲的圣人所“藏于胸中”的精气,这是最具有动能(我曾多次指出中国哲学所谓“气”是matter- energy的统一)和进入人的胸中可使人聪明睿智的精气,它只在运动的主动和被动的问题上与粗气或形气相对,而在宇宙的本原问题上并不与粗气或形气构成二元的关系。《庄子·知北游》所讲的“聚”则是气本身的凝聚,它是产生一个什么东西,而不是在一个什么东西内集合。《知北游》在“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的后面有:“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这里已全然排除了在“一气”和由一气所产生的世界万物之外还存在别的什么东西。《辨证》一文连完整的一段史料中的话都有意或无意的回避了,遑论《庄子》书以及其他书中别的史料了。
说到“聚”与“集”的区别,我想到对《内业》篇“此则为生”之“此”的校释问题。将“此”校改为“比”,释为结合,当然文理上可通。但古人用“比”一般也要有个所“比”的东西,而不是自身与自身相“比”。严格地说,将“此”校改为“比”,文意上也有滞碍。因此,我一直坚持依张佩伦《管子学》将“此”校改为“化”。此校改之正确,在《内业》篇中的内证就是“一物能化谓之神”;因为“一物(气)能化”,所以“化则为生”。“化”也就是《荀子·正名)篇说的“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所谓“实无别”,在《内业》篇中的意义就是“化不易气”。
《辨证》一文在引述了《荀子·王制》篇的一段重要史料后说:“这里并没有认为气的结合而产生出水火、草木、禽兽和人,而只是认为自然万物中都含有气,气是万物中共同具有的东西。”诚然,这段史料是讲万物存在的层次;但《荀子·礼论》所谓“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不是在讲天地合气而万物化生吗?“气是万物中共同具有的东西”,这与作者所谓“存在着不藏有精气的形体”不是矛盾吗?而作者却偏又说“这与《管子》中‘凡物之精,此则为生’,认为万物有了精气才得以生,是一致的”。作者本把“此则为生”的“生”释为生命或生命的活力,而荀子明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这怎么能说是“一致”呢?
《辨证》一文又引述了《黄帝内经》中的三句话,只说明精气内藏于五脏“是对《管子》所谓‘精舍’思想的发挥”,但对其所引“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却未作任何解释。我窃以为,如果作者能对这两处史料有真切的理解,恐不至于失误如此之深。
另外,如果作者能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论述或表述是否在逻辑上自洽,也不致失误至此。作者说:“把《管子》的精气说解为精气是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不解释为精气的结合产生人和万物……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管子·内业》为什么用大量的篇幅论述如何防止失去精气,如何获得精气。”我不明白,“防止失去精气”或获得“精气”就是为了防止失去或获得“存在的物质基础”吗?作者说:“精气与形体是相区别的”,一旦形体与精气区别开,难道形体就不存在了吗?这些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作者还强调:《内业》篇心静得气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今天所谓的‘气功’”。而我在我的文章中则指出:“《内业》等四篇吸收了当时的气功理论”,“气道(导)乃生”、“内静外敬”等等“可以说是对当时气功理论的精彩阐发”。我丝毫没有感觉到,如果把《内业》篇的精气说解释为精气的变化产生人和万物,就会带来理解其气功理论的什么困难。
观人病易,治己病难。以上主要就两篇文章的失误对《内业》等四篇精气思想的几个问题谈了我的理解,而我自己恐陷入误区尚不自知,这就希望其他学者和两篇文章的作者来针砭救治了。
注释:
〔1 〕但我在此文第二节最后一段讲到“精气”概念与阴阳概念紧密相连时还是列出了《水地》篇所云“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