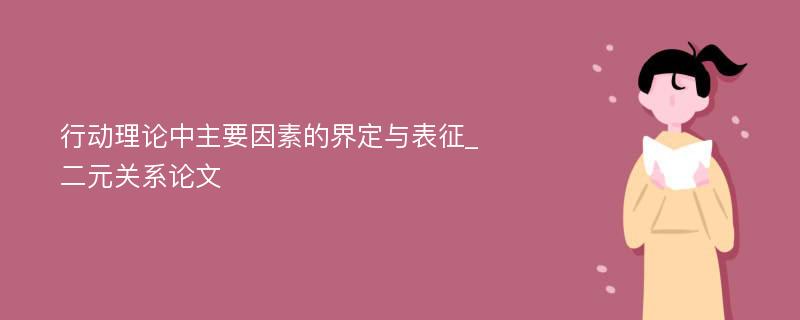
行动理论中主事性因素的界定与刻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3-0081-05
主事性(Agency)是行动理论中一类研究的统称,这类研究都以如何在行动理论的框架内刻画行动者和事件之间的二元关系为其研究对象。因此如果我们将主事性界定为如上的一种二元关系的话,那么不同的主事性理论之间的差别就恰好体现了不同学者对这种二元关系的不同理解。
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行动者(Agent)、行动(Action)、事件(Event)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哲学领域中的传统问题。而行动理论就是以行动为其研究对象,并在刻画、界定行动的过程中体现行动者和事件两者之间这种二元关系,即主事性关系的一种理论。
在刻画行动的时候之所以一定要涉及到主事性问题是因为:第一,当我们谈论行动的时候必然指的是某一或者某些行动者的行动,不涉及行动者因素而能够独立存在的只能是事件而不可能是行动,而行动的做出也必然会对客观世界造成某种改变,即造成某类事件的产生或者消亡,因此我们不可能在研究行动的时候不涉及行动者和事件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伴随着行动的做出必然会出现这种行动者与事件之间的二元关系,即主事性。第二,遵照行动理论的传统,“行动”这一概念被界定为包含主事性因素的事件。在这种界定之下如何借助于主事性将行动从事件中区分出来就是行动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个人的生活中,什么样的事件揭示出了主事性;什么是他的所作所为,什么又是恰好在他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以什么为标尺才能区分出他的行动?”①这些问题成为了行动理论一定要回答的问题。
因此,主事性是一个在行动理论中非常基础的概念,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国内行动理论盛行的环境下,介绍并梳理出国外已有的关于主事性问题的相关研究就更显得重要。
一 主事性与其他哲学概念的区分
主事性作为一种二元关系,体现了行动者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行动者的意向性(intention)因素能够导致这种关联性的出现。因为如果行动者和事件之间会产生这种关联性的话,那这一关联性必然是在行动者的意向性因素支配下产生的,即行动者能够依靠自身的意向性因素选择是否创立这种二元关系。
第二,这种关联性的产生不是必然的。因为如果行动者与事件之间具有的这种关联性是必然的话,那么无论行动者的行动是否做出都会出现这种关联性,这样主事性就不再具有区分行动与事件的功能。
鉴于如上的两个特点,有的学者认为主事性就是意向性,还有学者认为主事性体现的就是行动者与事件之间的因果性,但是通过下文的论述我们将说明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虽然主事性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但是早期的一些理论往往更注重于从语言学的角度区分行动与事件,以说明主事性。因此在区分主事性与意向性、因果性这些相关概念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些早期的理论。由于哲学的语言转向,很多本体论或者认识论上的问题被转变为语言哲学上的问题。伴随着这一转变,很多学者也开始尝试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出发解释主事性问题。因此出现了一批学者认为应该存在或者可以创立一些简单的语法规范来限定主事性在语言中的运用,认为通过某些语法规则可将具备主事性的事件,即行动与其他的事件区分开来。但是因为从没有人发现令人信服的这类语法规则,所以我们虽不能贸然否认这一方法,但是这一方法却从未被证实是确实有效的。
如上这一理论所存在的缺陷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主事性归因于某一主体或者对象,并列出一个表示且仅表示主事性的动词表。但由于反例的不断发现这一观点也被认为是错误的。例如在“他咳嗽”这一例子中,“咳嗽”这一事件的出现如果是由于主体“他”所有意导致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咳嗽”就是一个行动;但是如果“咳嗽”是由于病痛而导致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就不具有主事性,因为“咳嗽”这一事件的出现是主体不能控制的,更不能够体现主体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而“被地毯绊倒”这一事件一般不被认为是一个行动,但是如果这一事件是被主体有意做出的,那么这一事件就是一个行动。鉴于如上两个失败的区分标准,学者们才会转向从意向性或者因果论的角度研究主事性,尝试从心灵哲学的角度阐述主事性问题或者尝试为主事性构建科学基础。其中唐纳德·戴维森(D.Davison)就曾探讨过这两种关于主事性问题的学说,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论。第一,如何利用心灵哲学中的意向性概念来解释主事性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主事性的功能就是区分行动与事件,而要区分行动与事件的话,就要深入探究主事性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以上的区分标准之所以以失败告终,就是因为这些区分标准都只注重于如何在语言使用上区分行动与事件,而没有深入探究主事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当我们认为某一事件具有主事性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行动者在做出这一行动时是有意要创造或者改变自身与事件之间的某种关系,因此行动者才是主事性的构建者。要探寻主事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要了解行动者为什么会要构建主事性。而当行动者打算做出某种行动之前都会首先产生做出这一行动的意向性,在意向性因素的推动下,这一行动才会被做出,主事性才会被构建。因此,该理论认为意向性因素才是产生主事性的关键和基础。
但是戴维森认为这一个标准是不完全的,因为如果可以用意向性来定义主事性的话,那么在意向性和主事性之间应该存在等值蕴涵关系,然而虽然意向性蕴涵主事性,但是反过来却不成立,即主事性并不蕴涵意向性。如果行动者要通过行动建立某种与事件之间的关系,那么其行动做出之前或者当下都会处于行动者意向性的驱使下,也就是说意向性能够蕴涵主事性。但是在“溅出咖啡”这种事件中,如果某一行动者是有意溅出咖啡,那么“溅出咖啡”就是一个具有意向性的行动,然而如果行动者自以为溅出的是咖啡但却是茶的话,那么行动者就没有溅出茶的意向性,这样行动者的同一个行动却既是有某种意向性的又是没有某种意向性的,这就构成一种困境。
因此,戴维森才认为“一个人是某一事件的行动者当且仅当关于他所做行动的描述使得表述他有意所做行动的语句为真。”②而意向性因素本身无法保证这一点。
第二,利用因果性理论解释主事性的学说。因为从意向性理论出发,为主事性因素构建心灵哲学基础的这种尝试的失败使得更多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其他的方法定义主事性。有一种学说就认为主事性强调的是行动者和事件之间的二元关系,因此如果能够借助于因果性理论刻画这种二元关系的话,那就能清楚地定义主事性。
当然因果性理论本身也是哲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学派繁多、观点各异。因此为避免对主事性的研究陷入其他的哲学争论中去,很多学者开始尝试使用物理学哲学中对因果性的描述,为自身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科学基础。早期物理学领域中机械力学的兴盛使得人们认为利用力学的理论可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运动和问题,因此只要拥有对机械力学的充分了解,那么当某人做出某件事后就能利用已有的知识推知其行动会导致的结果。故整个世界就是确定的,没有任何意外可言。但是在这种哲学背景下是无法刻画主事性的,因为在刻板而确定的世界中行动者与事件之间都是确定的联系,只是机械力学所决定的世界中的确定的某部分,行动者只是恰好在那个时间、地点确定地要做出那个行动而已,而那个行动也必然会导致某种结果,在这样的世界中根本没有必要谈论主事性的问题。
而量子力学的出现,特别是量子力学哲学的发展促进了非决定论的发展,即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会因主体的不同选择或者行动而变得不一样。因此在这种哲学背景下才能用主事性来刻画行动者与客观事件之间的这种联系,而要刻画这种不确定性和主事性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分支时间的方法,即在不同的时间分支上给出行动者不同的可能行动或者选择,以便于描述主事性在行动中的作用。
但是利用因果性理论研究主事性的做法也遭到了戴维森等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行动者与行动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而行动者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性更并不是单纯的使用因果性理论就能够刻画的,因为这其中还包含很多不受行动者控制的因素会与行动者的行动一起影响客观的事件。
综上,行动是建立行动者与事件之间联系的唯一桥梁,而行动的做出又都是由于意向性因素的驱使,因此塞尔才认为“‘意向性’正是人类内心与世界之间联结的桥梁。”③,所以,在研究行动者、行动、事件三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意向性因素的重要作用,并将意向性作为主事性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意向性问题本身作为心灵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又涉及到身心问题、意识产生机制等深入且极具争议的话题,因此将主事性规约于意向性的做法不但没有为主事性的研究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反而将主事性建立在更有争议的哲学基础上,使得主事性的理论基础更加不稳固。而通过因果性理论来谈论主事性的研究方法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原本就学派众多的因果性理论很难成为主事性研究的坚实基础,即使将主事性建构在物理学哲学的基础上也很难为其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
二 对主事性的逻辑刻画
由于意向性问题以及因果性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富有争议性,研究主事性问题的学者开始尝试避开这些本身就学说繁多的哲学理论来谈论主事性,正因如此才逐渐形成了主事性的逻辑,即将主事性处理为一种模态算子,借助模态逻辑的手段处理主事性问题的方法。
如果要从逻辑的角度研究主事性,那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逻辑的形式化方法将表示主事性的自然语句形式化。而主事性体现的又是行动,因此如何使用自然语句描述或者刻画行动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戴维森在其1967年发表的论文“行动语句的逻辑形式”(The Logical Form of Action Sentences)中提出了将行动视为一种事件的观点。
这一观点之所以能够让很多的学者都接受是因为如果“将行动处理成为一种事件”③,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于逻辑学中的不同命题变项来表示事件,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刻画主事性的因素以进一步刻画行动。因此,对主事性以及行动的刻画可以建立在已有的逻辑形式化方法的基础上。
我们所要介绍的STIT理论就是以戴维森的这一哲学观点为基础的,所不同的是,戴维森将自己的理论限制在一般性的行动上,但是STIT理论却着眼于个体行动本身。尼尔·贝尔纳普(N.Belnap)认为“以往对行动的研究往往只停留在对行动名称进行研究的阶段,而没有深入研究具体的行动本身。”④例如对“盗窃”这一行动的研究,以往的学者只对被“盗窃”这一名称所涵盖的所有个体行动所构成的行动集感兴趣,即只是对“盗窃”这一名称或者这类“盗窃”行动进行研究,而STIT理论则会将研究的重点放到具体的某种“盗窃”行动上去,深入研究个体行动的特点和构成。
在此基础上,如何通过对个体行动的逻辑刻画以表现行动者和事件之间的二元关系的问题就成为了STIT理论研究的重点。STIT理论借助逻辑学对语形和语义的区别分析,将对主事性的刻画和对主事性这一二元关系的解释分别放在语形和语义两部分中进行阐述。
STIT是英文“sees to it that(即确保、确定)”的缩写,该理论利用语句来表达主事性,而这类语句的构成则包含三部分:首先是行动者,其次是事件,最后则是连接行动者和事件的二元模态算子STIT。如果用“α”表示行动者,“Q”表示表达事件的语句,那么这类语句可表示为:[α STIT:Q],即表示语句“αsees to it that Q”。如“我确定我在跑步”这一语句中,就整个语句本身而言,其刻画的是一个事件,即我确定我在跑步这一事件,但是为了说明这一事件同时也是一个行动,我们就需要在对这一事件的刻画中体现主事性因素,即体现行动者“我”和“我在跑步”这一事件之间的二元关系。如果我们使用STIT,即“确定”这一二元算子以表示行动者与事件之间的二元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使用语句[我STIT我在跑步]这一STIT理论中的形式化表达方法刻画主事性因素。但是由于在逻辑语法中我们不会考虑算子或者语句的真值问题,因此在语法中,我们能够了解的就是主事性的形式化表达方法,至于对这种形式化表达方法的解释则是逻辑语义关心的问题。在这一形式化表达中,我们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α STIT:Q]对于α而言总是具有主事性的。只要具有形如[α STIT:Q]的表达形式,那么这一语句对于行动者α而言就是具有主事性的。如“我确定太阳明天将从东方升起”这一语句,可以形式化为[我STIT:太阳明天将从东方升起],既然这一语句具有[α STIT:Q]这一形式,那么其就是具有主事性的。但是“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一事件是必然的,因此无法体现主事性,这一语句也就只能为假。而语句“我确定我在跑步”,即[我STIT:我在跑步]这一语句则既是具有主事性的,又是真的。
第二,如果语句Q等值于[α STIT:Q],那么Q对于行动者α来说就是具有主事性的。Q对于行动者α来说是具有主事性的,当且仅当语句Q能被成功地形式化为形如[α STIT:Q]的形式。
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STIT理论的语义解释。
STIT理论的框架建立在分支时间框架的基础上。这是因为分支时间理论的哲学基础是非决定论,只有在非决定论的世界中,通过行动者的选择或者行动才能与事件产生某种联系,促成某种结果的发生或者某种事件的转变,以体现主事性。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假定世界是决定论式的,那么一切事件只不过是从行动者的身边经过,行动者本身的行动不会对事件造成任何影响,主事性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说,要刻画主事性首先就要刻画非决定论,正因如此,分支时间框架才成为刻画主事性的基础框架。
通过对形如[α STIT:Q]的语句的不同解释,我们就可以刻画不同的主事性理论。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主事性表示的是行动者已经做出的某一行动能够保证某一事件为真,而且这一为真的事件并不是必然为真的,因为如果这一事件必然为真的话,那在确定为真的事件中就无法刻画主事性;也有学者认为主事性表示行动者当下做出的某一行动能够保证某一不必然为真的语句为真。
针对这些不同的哲学理论,只要构建不同的语义解释就能在已有的语法表达式的基础上构建出体现不同主事性理论的逻辑系统。
哲学上的讨论虽没有为主事性问题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但却让我们对主事性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而建立在这种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不断迈向最终的目标,即精确刻画主事性。而逻辑领域中的构建方法只是为不同的理论构建了不同的语义表达方法,即为不同的理论提供了说明自身明确性的逻辑方法,但却没有指出哪一理论为真,哪一理论为假,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因此,逻辑学领域中的讨论虽然使得我们对很多概念都会有更清楚的了解,但是对主事性问题本身的讨论没有很大的帮助。
①②D.Davison,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Clarendon Press,1980,p.43,p.50.
③约翰·塞尔:《意向性:论心灵哲学》,刘叶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554-557页。
④N.Belnap,M.Perloff,M.Xu,Facing the Future:Agents and Choices in Our Indeterminist Worl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