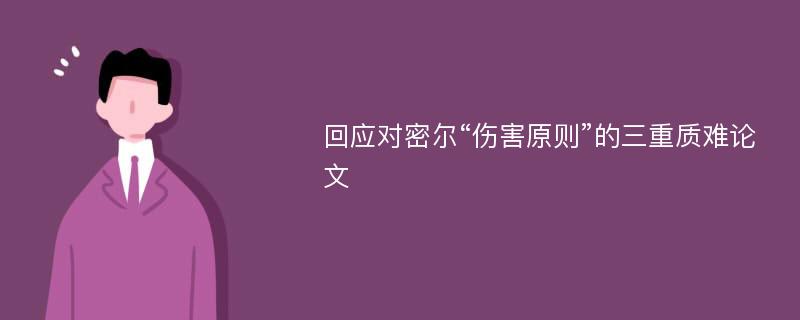
回应对密尔“伤害原则”的三重质难
卢绍辉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提出的“伤害原则”被看作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典范之论,这一原则自其提出便被广泛地批评,其中最主要质难体现在三个方面:“涉己”与“涉他”的区分、“伤害”的含义、“伤害原则”与“功利原则”的关系。本文在厘定前人对三种质疑意见与辩驳内在逻辑的基础上,以密尔文本为依据对这三种质难作出回应,进而为伤害原则正名。
[关键词] 伤害原则;自由;涉己;涉他;伤害;功利
一、问题的提出
“伤害原则”是密尔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与国外学者不同,国内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密尔以“伤害原则”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的现实意义以及带来的自由与社会约束的思考,但是却鲜有人关注在这之前的问题,即“伤害原则”本身的正确性。“伤害原则”在国外一直是自由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于其是否合理的争论一直存在,这就使得我们在关注其现实意义之前,应当将目光放在“伤害原则”本身。
在书中,密尔将“伤害原则”表述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进行自我防卫。”[1]14这一原则意在回答,什么情况下社会有权对个体行为自由进行干涉。答案可以概括为:当且仅当个体的行为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伤害的时候,社会有权对其行动自由进行干涉。
按照密尔的思路,人的行为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只与自己相关的行为,可以称为涉己行为;另一种是同时关涉他人的行为,可以称之为涉他行为。由于对个体自由施加干涉的条件是对他人(社会)构成伤害,所以受此原则约束的行为必定是涉他行为。也即是说,在涉己行为之中,个体享有充分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自由。紧接着,对于涉他行为而言,限制个人自由的正当理由在于对他人(社会)构成伤害。因而,衡量是否有正当理由限制个体自由的检证工作需要分两步进行:一是个体的行为是涉己还是涉他;二是如果是涉他行为,是否对他人构成伤害。这也就为“伤害原则”的展开设置了两重困难:第一,是否存在清晰的标准以区分涉己行为和涉他行为,第二,如何界定伤害。许多学者借由这两重困难,对密尔的伤害原则发起质难。
此外,除了以伤害原则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之外,密尔还以其功利原则而著称于世。如果说伤害原则通过区分涉己行为与涉他行为从而为个体保留了充分自由的话,那么功利原则则对个体的所有行为提出了普遍的道德要求,即要为了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行动。因此一个接踵而至的问题是:来自伤害原则的自由保障与来自功利原则的道德约束之间是否能够达成一致,从这一角度出发,许多学者提出了对密尔伤害原则的第三重质难。
以上三重质难对于伤害原则而言无疑都是致命性的,如果不能提供对这三重质难的合理回应,那么其伤害原则的效力必将大打折扣,也就无从谈及其思想的现实意义了。因此,笔者意图通过分析前人对于密尔伤害原则的批驳与辩护,细致考察这三种质难意见的逻辑结构,从而站在密尔本人的角度,就三重质难所关涉的核心问题一一作出回应。
二、涉己行为与涉他行为
我跟在父亲身后,抬头望天。我的目光越过父亲的背影。我看见晴朗的天空飘来一片乌黑的云,大地顿时灰蒙蒙的,像升起一层雾。
依照密尔在《论自由》最后一章所作的总结,伤害原则可归为以下两条准则:一是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自身以外其他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若为自己的好处着想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进行忠告、指教、劝说以至避而远之,这是社会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不喜或非难时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二是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为,个人则应当负责交待,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认为需要用惩罚来保护他自己的话[2]。
认为两条原则不相容的观点指出,密尔伤害原则事实上会导致(或者说是容许)三种伤害:一是对自己的伤害,例如流浪孤儿自杀的问题;二是对社会造成长远的或间接的伤害,例如个人的饮酒问题或者少数人所担心的肯定同性恋行为而导致的社会人口减少的问题;三是某些自愿行为对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宽泛意义上的伤害),例如看见某人的自残行为而带来的巨大不适感。这三种伤害与功利原则所倡导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显然相去甚远。至少在最直观的意义上, 伤害原则只是限制个人去伤害他人,而允许个人伤害自己,就必定与与功利原则相矛盾[7]。
斯蒂芬的反对理由很简洁直接——不存在完全不影响他人的行为。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构成对密尔伤害原则的直接反驳。因为密尔本人在《论自由》第四章中就明确指出这一点,他提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孤立的存在;一个人若做了什么严重或永久有害于自己的事,其祸害就不可能不至少延及其左右亲人,并往往远及亲人以外的人”[1]95。密尔承认每个人的行为确实会影响周边的人,纯粹只影响自己的行为并不存在。因而斯蒂芬的反驳并没有击中要害,既然不存在只对自身造成影响而不影响他人的行为,那么涉己行为与涉他行为的真正界限又在何处呢?
政治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和胜任力的重要标志。政治领导力强不强,关键看对党和人民的政治忠诚度,这是政治领导力的全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对党忠诚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品格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政治能力的重要标尺。忠诚是人的一种优良品质,对于政党来说,政治忠诚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5]P24
但是,沃尔海姆的辩护仍然存在缺陷。按照沃尔海姆的看法,间接影响从根本上讲不能算作一种影响,可是,密尔显然不会同意这一点。在《功利主义》一书中,密尔明确提出要将间接影响纳入到功利计算之中。二人的分歧可用一个思想试验来凸显[4]。按照密尔的功利主义原则,政府应该强制收容乞丐并且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这样做的理由很明确:遇见乞丐会通过两种方式来降低他人的幸福感,对于富有同情心的人,会让他们产生同情别人的痛苦;对于心肠硬的人,看到乞丐会产生一种厌恶之苦。不管哪一种方式,乞丐对他人的影响都是间接的,但是这种间接影响依然构成了社会采取某些强制行动的正当理由。可以想见,沃尔海姆自然会持反对意见,因为乞丐让别人不快的这种伤害是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只取决于他人对乞丐所持的情感状态,因而乞丐行乞这一行为是关乎乞丐自身的涉己行为,社会无权强制终止这一行为。密尔与沃尔海姆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带来的结果是,即使沃尔海姆的辩护具有效力,密尔本人也不太可能接受这种辩护。
针对密尔总结的那两条准则,里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提出了一种解释,他认为密尔在两条准则中暗含的区分标准是行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标示着涉他行为,而涉己行为只对他人有间接影响。沃尔海姆给出了识别间接影响的两个条件:第一,我的幸福因我实际上参与到他人的生活中而被他人的行为影响;第二,它是一个关于这个行为的道德状态的先在信念的结果。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个行为是不道德的或令人厌恶的,那么这个影响是间接的。因为,这意向并不直接源自行为,而是受影响的客体对这个行为持有特定的信念。以“恐同”为例,如果某人对同性恋持有某种厌恶的情感,那么尽管他并未参与到实际的同性恋行为当中,但其他个体的同性恋行为也会影响到他的幸福,这种影响即是间接影响。沃尔海姆的辩护策略可以概括为:间接影响取决于并且唯一取决于受影响者的主观感知状况,按照这一标准,可以确证涉己行为的确存在。
欧洲公共文化立法探讨及对中国的启示——以英国、比利时及法国公共文化立法为研究对象 … ………………………… 郭玉军,李 伟(3.37)
相较于前面两种质难立足于伤害原则的内部要素,从伤害原则与功利原则的关系入手则是站在伤害原则的外部来进行审思。概括来说,第三重质难认为伤害原则和功利原则相互抵牾。
如同回应第一种质难,密尔的 “伤害他人”应当意味着“损害他人利益”。这种界定方式一方面可以承认个体行为或多或少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保留涉己行为的空间,从而保留伤害原则的有效性。事实上,密尔本人有这样的倾向。在《论自由》中,密尔陈述伤害原则时不断提到“利益”这个概念。这种解释并不依赖于“利益”这个词出现的那一两个孤立的段落的证据,事实上,这个词在文章中至少出现了15次,而且,以利益为关键联结点,能够引发伤害原则与功利原则之间的呼应,这也符合我们对密尔理论体系化的期待。
三、伤害
对于伤害原则的解释显然必须依赖于对“伤害”的解释。在何谓伤害他人这一问题上,密尔给出的回答存在理解上的歧义,进而引发了第二重质难。
密尔在《论自由》中没有直接交代涉己行为与涉他行为的区分,而是将其诉诸于道德直觉,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多少有失严谨。而以区分涉己行为和涉他行为的方式去理解伤害原则又确有必要。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密尔根本没有对这一区分作出合理解释。
质难者认为,密尔的“伤害他人”等同于说“对他人造成了坏的影响”。按照这一标准,他人情感上的痛苦、厌恶等感受的确算是一种“坏的影响”从而构成了一种伤害[6]。那么,某个行为是否对他人产生伤害就仅仅取决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他人的主观状态,那么很多自私的诉求看起来就拥有了正当的理由。这样就陷入了一种困境:如果“他人”是由多个持有完全不同的主观偏好的群体构成,那么对他人伤害与否的问题就转化为不同群体人数的权衡,这种道德判准上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对于一个成熟的道德理论来说显然是致命的。这种界定伤害的方式与前一部分利用影响来区分涉己行为和涉他行为一样蕴含着一种不可避免的风险,那就是消解掉涉己行为存在的可能性从而消解掉个体自由的空间。将个体的主观偏好引入到对伤害的界定中,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个体自由的体现,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容许个体主观偏好在行为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可以说个体拥有行动自由。那么这两重发现走向一个悖论:要么拒斥个体主观偏好而追寻确定性的判断标准从而挤压涉己行为的空间,要么保留个体主观偏好从而保障个体自由。
(2)Macroeconomics,the study of the economy as a whole,attempts to answer these and many related questions.
当然,按照他人的利益来区分涉己行为与涉他行为还需要进一步回答:如何确定他人的利益?密尔本人对此并未给出确定答案。按照密尔推崇的功利原则来推测,哪些东西能够成为个体的利益这一问题存在着某种普遍而确定的标准(例如公正的旁观者的意见),至少不能仅仅根据每一个具体的个体偏好来决定个体自身的利益与否。这样一来,个体自由与个体利益之间就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在判定自身利益的问题上,个体自由需要让位于某种客观标准,那么由此我们也不得不怀疑,密尔为了保护个体自由而提出的伤害原则存在深层次的困难。
但是,正如区分涉己行为与涉他行为时那样,以利益作为最终依据需要面临进一步的追问:如何界定利益?如果利益的定义权在社会的话(假定社会就是那个公正的旁观者),那么就会引出一个悖论:社会无权干涉仅涉及公民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却有权决定什么是公民的利益。
中国农药在全球而言具有相对比较大的优势,是全球农药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蓝天行动、江苏沿海263行动、长江大保护等等都对农药当期生产及长远供应产生深远影响。
四、伤害原则与功利原则
综合上面正反两种观点,区分涉己行为与涉他行为的标准应该是“影响利益”而非“影响”:影响他人和影响他人的利益是不同的,密尔关注的是划分影响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的界限[5]。行为如果未经同意却影响他人的利益,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涉他的;而涉己行为是不影响他人利益的行为。换言之,因为影响他人的行为并不一定影响他人的利益,所以涉己行为可能频繁地甚至伤害性地影响行为者之外的人。在《论自由》中,密尔显然也是以“利益”作为最终定准的,这一点从他多次提到公民利益问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国外学者约翰·C·瑞斯(John C Rees)在《再读密尔的论自由》中稍稍提及:“只有在他人利益被威胁或实际影响的情况下才应施用社会对个人行为的控制。” [5]
这两条准则为理解涉己行为与涉他行为之间的区别提供了某些启示,然而必须说,这种启示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歧义。按照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在《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中的理解,密尔所说的“涉己涉他”行为的区分标准在于行为是否影响他人:如果行为未经他人同意却真实地影响他人,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涉他的;相反,如果行为对他人没有影响,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涉己的。但是,人类社会和人的行为十分复杂,每个个体之间、每个个体与群体之间并不能完全区分开,几乎所有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因而,斯蒂芬进一步认为,“区分涉己行为和涉他的行为的尝试,就好似区分发生在时间中的行为和发生在空间的行为的尝试,每个行为都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发生的,同样我们做的每个行为会或可能影响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区分是完全荒谬和无根据的”[3],简言之,涉及行为和涉他行为之间不存在清晰的界限。
尽管密尔没有像以塞亚·伯林那样直接给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但是密尔的自由思想同时包含了这两种面向。实际上不会导致两种原则相互违背的情况。
总的来说,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是需要我们教师结合不同的教学模式与方法才能获得的,同时他们的主体性得到激发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为此我们数学教师应重视这个过程,并认真反思自身的教学行为,这样学生的主体性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论自由》开篇,密尔首先限定了自己所要探讨的自由概念是一种社会自由。从思想背景来看,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指的是自愿的、不受强制的行动,也就是不受威胁或其他形式的强制、出于自愿选择而做出的行动[8]。他在《论自由》中说:“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合法施用个人的权利的性质和程度。”[1]1“在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1]11这两段文本中就包含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个向度的问题。一方面个人可以通过自我学习和发展实现个人在精神、情感等领域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也是密尔功利主义的前提。但同时,这样的自由并不是放任的、堕落的自由,同样受到“伤害原则”的限制。
通过发掘密尔自由思想所蕴含的消极与积极两个层面的内涵可以发现:积极的自由,即自我发展是个人在接受社会教育和培养后,在社会中追求个体对自身发展的主导,但也是限定在一定的社会制约之下;消极自由则强调在社会强制力之下,为个体留出追求个人幸福的空间。就个体发展而言,消极自由本身是不充分的,它的意义在于为积极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密尔显然意识到了自由概念的复杂结构,而且他也进一步将自我发展了的道德主体作为其功利主义幸福思想的理论基础。
即使密尔的自由概念的确涵盖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面向,这是否就足以说明,伤害原则与功利原则可以达成一致?尽管我们怀着对密尔思想体系化的期待,但是自由概念积极意义的阐发仍然无法消除不相容者的疑虑。如就“社会可以做出何种强制”这一问题进行探索,那么两条原则给出的答案无疑是冲突的,至少在是否允许自甘堕落这一问题上的答案是冲突的。究其原因,在积极意义的层面理解自由概念时,从自由出发所引申出来的各种道德规则充其量只能成为一种倡导,而绝不能成为强制。因为这是所有自由主义理论都难以避免的困境。与此同时,密尔为了调和伤害原则和功利原则之间的冲突也作出了相应的努力,这一点从他在《论自由》第三章极力强调个人发展的积极自由就可以看出。或许可以用一种“宽容”的视角来看待密尔的伤害原则和功利原则:其自由主义体系的构造依托于调和的功利主义思想,而伤害原则本身作为一项道德原则存在于功利原则之中。伤害原则的保守性(仅仅是不伤害)与功利原则的利他性构成互补关系,从而建构起功利主义式的幸福观念:自身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同等重要,理想的道德行为主体是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
五、结语
对密尔伤害原则的三重深层次的质难是:在肯定个体偏好、推崇个体自由与追寻确定标准、维护道德根基这两种倾向中应该作何取舍?全部个体的普遍利益与单个个体的特殊利益之间的鸿沟应该如何消弭?在维护消极自由、容许自我放纵与倡导积极自由、追寻自我完善两种取向之间应该如何平衡?依照密尔的文本分析来看,密尔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这些质难,其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是伤害原则展现出了所有力图绝对和彻底的理论原则都不可避免的张力困境。如何能够走出这种困境,是所有道德理论的永恒追问。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淋巴结转移情况是根据治疗性颈淋巴结清扫术后病理证实的,因此可能造成该队列中的淋巴结转移率的低估。其次,受限于公用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类型,对于SEER数据库中的LLNM患者,我们无法区分其中央区淋巴结的状态,因而限制了后续的预后分析。因此,笔者推荐前瞻性多中心研究和长期随访确定PTMC患者的最佳手术方式。
[参考文献]
[1]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2] MILL J S. On Liberty [M].London:Batoche Books,2001:85.
[3] 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自由平等博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34.
[4]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 张舒.浅析约翰·密尔自由观及其伤害原则的争议[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3(4):86-90.
[6] 叶勤.密尔“不伤害”原则及其对行政权力的道德限定[J].道德与文明,2007(1):55-58.
[7] 杨国晓.由密尔的“伤害原则”引发的若干思考——对“网络追凶”事件的解读[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3):129-133.
[8] 邵爽.密尔的功利主义幸福思想[D].长春:吉林大学,2013:48-65.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5935( 2019) 02- 0071- 04
[收稿日期] 2018-10-18
[作者简介] 卢绍辉(1995—),男,山东东营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doi :10.3969 /j.issn.1673 -5935.2019.02.017
[责任编辑] 谭爱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