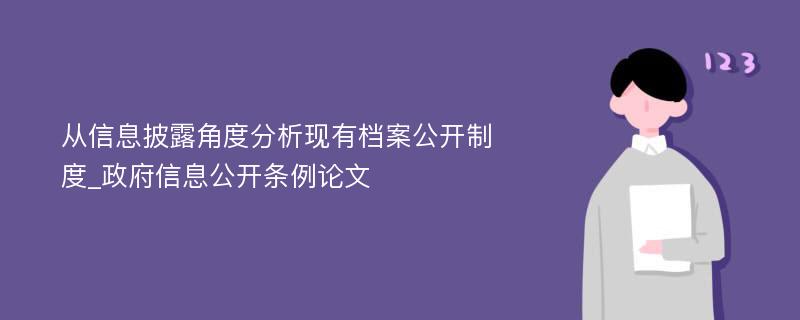
信息公开视角中现有档案开放制度的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制度论文,档案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百多年前,北欧国家瑞典于1766年出台了《出版自由法》,开创了信息公开制度的先河,最早确立了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二十多年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先锋——法国颁布了国家档案馆条例和穑月七日法令,首次提出了国家档案馆向社会开放的原则,赋予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确立了“档案的人权宣言”。两百年后,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文明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取代,使得信息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世界范围内以公众的信息自由权为基石的信息公开制度纷纷确立。公民获取政府现实信息和历史信息的权利诉求不仅推动了信息公开和档案开放,也呼唤着两者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衔接,以及所产生的更大的制度合力。美国、丹麦、瑞典等国直接将档案开放利用纳入信息自由法,实现了信息公开和档案开放的同步发展。我国档案开放的发端(1980年提出“开放历史档案”方针)比信息公开探索早了十多年(信息公开实践源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的政务公开制度)。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与发展态势十分迅速的信息公开相比,档案开放实践仍处处受制,档案开放法规制度略显陈旧。随着信息公开实践先行和国家立法列入日程表①,档案开放与信息公开的种种现实矛盾也进一步暴露和突显。从信息公开的视角剖析现有档案开放制度,既是顺应信息公开之势重新调整档案开放制度的起点,也是保障信息公开进程、协调相关制度的衔接点。
一、信息公开案例中突显的档案开放制度矛盾
曾经轰动一时的“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② 的最大意义在于“提出了中国行政信息公开制度进展过程中一个必须直面的难题:如何处理‘档案’和‘行政信息’的关系。第一次将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制定之后带来的相关制度之间的协调难题,如此直接搁置于公众的关注和相关政府官员的视角之内。”③ 对于档案界而言,这一案例的更大意义在于反映出档案现有开放制度与信息公开之间的“断层”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理论学术的探讨,而是实实在在地遭遇了现实困境。如果房地产登记材料尚未经历文档转化,仍是“非档案”的“政府信息”,那么根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政府信息应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除法律明文规定可以不公开的信息。其余政府信息应该按规定公开。④ 如果房地产登记材料已经转化为“档案”,根据我国的文档管理体制和现有的档案开放制度规定,其开放利用不受《信息公开规定》的约束,不适用“申请公开”、“诉讼救济”等权利保护条款。而由于档案保管部门——房地局确认该档案不适合对外开放,因此董某不但无权查阅该材料,而且没有途径进行申诉和权利救济。同样的信息内容和载体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却适用并不一致的法规制度,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这不得不迫使档案界立足信息公开的客观需要,从保障信息公开有效实施的视角重新审视我国的档案开放制度。
二、现有档案开放制度体系构成
我国的档案开放工作从1980年国家档案局发布《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几点意见》和1982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档案局《关于开放历史档案问题的报告》至今,逐渐形成了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下至各级各类档案馆开放利用规定的制度体系。尽管“档案开放”并没有享受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种单独设立行政规章的待遇,但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立来看,档案开放内容已经渗入国家法律、部门规章、行政规章等各种形式和级别的法规性文件之中,构筑了以《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1988年施行、1996年修改,1990年施行、1999年修改)为根本准绳,《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1991年施行)、《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1992年施行)、《机关档案工作条例》(1983年发布施行)、《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1992年施行)为具体依据的宏观框架,从国家高度建立了“五法一体”的档案开放制度格局。
三、信息公开视角中现有档案开放制度的“衔接断层”
对比我国已经出台的地方信息公开规定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的立法思路、原则和具体条款,笔者发现,目前的档案开放制度在设立原则、开放时间、开放适用范围(主体和客体)三个方面与信息公开存在不协调之处。
首先,信息公开的首要原则是“权利与公开原则”,具体表述为“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获得政府信息,本条例或者法律另有明确限制的除外。”“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⑤ 这一原则不仅在《专家建议稿》总则中列为首要原则,而且体现在立法技术上并不罗列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只将不予公开的七种信息作为“例外”列出,凡不属此列均视为当然开放。而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却将可以提前开放(包括即日开放和随时开放)和满30年开放的档案专门列出,反映的是“一般为满30年开放,提前开放是例外”、“一般不开放,开放是例外”的保守思路。实际上,“在我们长期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对于政府机关所拥有或控制的信息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或习惯,好像不公开是原则,公开反倒是例外或者是一种恩赐。”正因为如此,“为避免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避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各种借口扩大不公开的范围,架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有必要将公开作为原则确立下来”。⑥ 档案开放制度形成于“保密”思想较浓厚的特殊历史时期,脱胎于政府机关内部机构的档案部门仍然残留着不少“机关作风”,这种思维定势下产生的开放原则与信息公开原则必定存在着“断层”。
其次,档案开放与信息公开最明显的脱节体现在开放的“时间断层”上。一方面,信息公开推动下现行文件的即时开放实现了利用的“0时限”;另一方面,政府信息“档案化”后一般要经历30年的“封闭期”才能开放,两者的“时间断层”差距极大。尽管有提前开放的“例外”,但在实际工作中,满30年开放尚无法做到及时鉴定、百分之百开放,更遑论“提前开放”的落实了。此外,从公开传播的时效来看,信息公开时限设置以“工作日”甚至是“小时”为单位计算,档案开放仍然以“几十年”作为时限跨度,即使部分档案信息应该设置必要的相对较长的“封闭期”以补充信息公开的“例外”限制,但这种时间单位差别所体现的时效“断层”显然过大,不利于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因此,档案界也已有学者提出“不设置30年的封闭期,使应该开放的档案开放,应该自由利用的档案自由利用;使应该保密的保密,应该限制利用的限制利用”⑦ 和“缩短档案开放期限,拓宽‘随时开放’范围”的建议。⑧
第三,档案开放的适用范围与信息公开立法思路亦存在“衔接断层”。从档案开放制度适用主体来看,无论是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中提及的档案开放主体,还是《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中的表述,抑或档案开放实际工作的开展,开放一直约定俗成地限定为“国家档案馆”、“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职责,机关档案室并非开放制度适用的主体范围。但是《专家建议稿》将“政府机关”作为公开主体,并界定为“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其他组织”。⑨ 根据此主体适用范围规定,档案局(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和档案馆(提供公共服务)都是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适用的主体,机关档案室作为行政机关的一部分也对政府机关制作、获得或拥有的信息负有提供义务。两种制度在适用主体的“范围断层”将使“文档一体化”后政府电子文件的利用“无所适从”,也会导致目前政府信息服务的“文档断流”,降低了文件形成者与档案保管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换效率。从档案开放制度适用客体范围来看,《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所列出的20条控制使用范围与《专家建议稿》列举的七条“作为例外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在分类上不衔接、表达方式不一,容易造成边界模糊、操作混乱,甚至出现信息公开规定中已公开的文件转为档案则变为控制使用的矛盾。
四、信息公开视角中现有档案开放制度的“权利空档”
结合法国“档案馆开放”的含义和我国当时“开放档案”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档案开放”,从“开放历史档案”、“开放档案”、“档案的开放”逐渐演变而来,在这种语言转换过程中,档案馆开放的精髓——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观念,逐渐被我们的文化和思维惯性淡化了。⑩ 相比之下,“政府信息公开不仅仅只是政府机关的一种办事制度,而是公众的一项法律权利,只有其他法律作出明确规定,才可以限制公众的这项权利”。(11) 以权利原则为导向的信息公开立法十分重视对公众权利的赋予和保护,现有档案开放制度则更多地从档案馆开展工作的角度进行内容设计,忽略了公民对档案的申请开放权、已开放档案的公布权和自由利用权。
目前档案开放制度中设立的档案开放方式均为主动开放方式,如开设阅览室、定期提供开放目录、编研出版史料。对于未开放档案的利用需要,只是“语焉不详”笼统地提及“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规定”(见《档案法》)或“须经保存该档案的档案馆同意,必要时还须经有关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见《档案法实施办法》)。如果有关部门没有相关规定或者不同意,利用者对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既无主动申请的权利,也没有申诉和要求答复不予开放理由的权利。档案部门对于是否开放、对谁开放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公民权利保护的限制,既造成了档案人员畏首畏尾、害怕出错,也为消极应付、不作为导致的不开放提供了庇护。实际上,正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保密过度”使得目前到期档案开放鉴定任务重,压力大,无法在短时期内保证所有无需保密而公众需要的信息都主动开放,因此将主动开放和被动开放相结合,赋予公众申请开放权利,增加依申请开放方式十分必要。
档案公布权一直是档案界存在争议的难点问题,龙潜子女诉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案”最后判决理由落在“已开放档案不能擅自公布”上实在无法以理服人,开放、利用、公布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有待深入探讨。但是,学理上的争鸣并不意味着制度也允许模棱两可。档案开放制度中公民对已开放档案的公布权(12) 和自由利用权的“空缺”使得司法审理和裁定依据不足。《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各级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其公布权属于档案馆以及国家授权的有关单位。利用者摘抄、复制的档案,如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研究著述中引用,但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公布”,在现实社会中因利用与公布、开放与公布的不可分离性而存在悖论和执行上的两难。根据《专家建议稿》中的“自由利用原则”,申请人获得政府信息后,可以对信息进行再加工或者其他形式的开发、利用。国家所有的档案中必然包括这类政府信息,档案开放制度中存在的已开放档案的公布权和自由利用权“空档”应该在信息公开的推动下适时填补。
五、信息公开视角中现有档案开放制度的“保障缺失”
“立法如果不能设置一定的保障措施,再好的条文在实践中也会走形”。(13) 档案开放时间普遍滞后和开放不力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与档案开放制度设计的时限过长、不够细化,边界模糊、范围过窄,权利不明、授权太少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制度实施缺乏社会监督和执行压力,“缺失”了相应的保障条款。任何法规制度都是需要执行者的具体实践和相对人的具体行为才能真正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有力工具。制度基本条款无论设计得如何完备,如果欠缺了相应的辅助规定强化执行,最终都只能流于形式。这种辅助规定一方面来自于相关领域规章制度的外部衔接,一方面则依赖于本身的保障条款进行内部巩固。然而,现有的档案开放制度缺少监督机制对开放的执行施加压力,也缺乏免责机制鼓励档案部门和档案人员提升开放的速度和广度。
首先,现有档案开放制度只是笼统地将开放主体规定为“各级各类档案馆”,至于馆内开放责任具体应该如何落实、哪些人员机构进行协调监督均无规定。其次,虽然设立了四种开放时限和情况,却没有向社会公布各种档案数量及类别,使得具体开放完全是自由裁定、内部操作。社会利用者对具体档案的形成年代或许可以基本判定,但无法了解究竟哪些档案属于“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类且不涉及国家利益”,哪些档案属于“到期不宜开放”,只有当查阅要求被拒绝时才被告知“尚未开放”。这不仅无法由社会对开放工作进行外部监督,也削弱了档案部门向利用者解释的说服力,影响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和社会支持度。此外,尽管档案法也明确规定了“档案馆应该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但档案馆馆藏档案数量和可开放比例并不公开(14),档案馆公布的开放档案目录是否及时全面也无衡量标准。最后,对可以开放但暂未开放档案的利用申请,因为既无明确公开的申请审批程序和依据,也无说明理由制度规定必须答复,常常是不了了之或简单否定,让利用者心有不甘、心生怨气。
《专家建议稿》的立法思路则较为全面地考虑到法规制度的实际执行效果,在具体内容上设计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保障措施”一章,从明确责任主体和协调监督者(如设立首席信息官和信息资源管理机构)、建立登记制度(如要求编制政府信息公开登记簿)、规定不公开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对信息公开施加内外压力、双重监督。在基本条款中也设置了程序公开机制、回应机制(说明理由制度)和救济原则来保障执行。针对档案开放“过度保密”和“泄密责任明确、开放动力不足”的缺陷,开放制度保障条款中还应该借鉴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经验,设立免责条款鼓励积极开放,打破档案部门长期前怕狼后怕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定势。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我国档案开放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冲破了档案利用的封闭思想,强调了档案工作为社会各方面利用服务的思想,促进了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公民知情权的实现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同时,开放与保密始终是档案开放制度建设的难点和重点,我国的档案开放制度兼顾了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9月5日颁布,1989年5月1日实施)的衔接,遗留了原保密法的明显痕迹。2005年,民政部国家秘密中删除了“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国家开始酝酿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的修改,将重新划定保密范围和保密机构、细化解密程序,以保障信息公开的需要(15)。当初《保密法》定秘的标准模糊、程序不严、范围过宽、期限过长,部分影响了档案开放制度与信息公开的一致性和结合力。针对我国现有档案开放制度所出现的“衔接断层”、“权利空档”、“保障缺失”问题,档案立法部门应该从信息公开的促进和需要出发,在国家层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出台之前,关注其立法进程,借鉴其立法经验,从基本内容的增删修改和保障条款的补充完善(16)两个方面来思考档案开放制度的内容设计,以便在年内“条例”出台后占据主动,快速反应,适时修改有关条款。
注释:
① 2006年3月,中国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推进综合司司长徐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被列为国务院2006年一类立法计划,有望今年出台。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03/17/co-ntent_4313521.htm,2006年6月6日
② 案例概要见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508190378.htm,2006年6月5日
③ 刘飞宇:《从档案公开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
④ 这也确实是董某起诉的理由,董某及其律师认为:徐汇区房地局拒绝公开她要求查询的信息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因为该规定确定了任何人可以请求查阅政府信息的请求公开制度
⑤ 周汉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专家建议稿)》,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第1页
⑥ 周汉华:“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信息化建设》,2004年第1—2期
⑦ 吴文革、马仁杰:“论档案开放的原则”,《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4期
⑧ 晋平、耿景和周倩:“论政务公开环境下档案开放范围的重新界定”,《陕西档案》,2004年第6期
⑨ 周汉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专家建议稿)》,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第62页
⑩ 王改娇:“‘档案开放’语词溯源”,《山西档案》,2005年第5期
(11) 周汉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专家建议稿)》,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第48页
(12) 笔者认为,公布与开放不可分离,“已开放档案的公布”自身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实际应表述为“已开放档案的自由利用或传播”。此处仍保留“公布权”概念是基于目前档案法条款和案例的现实存在,以及学界探讨话语一致的考虑
(13) 周汉华:“起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的基本考虑”,《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
(14) 有关各级各类档案馆的馆藏数量等权威性的统计数据均来自《全国档案事业基本情况统计年报》,但此统计资料目前仍然属于内部保密文件,不向社会公开,这与国家自然资源、人口、GDP、环境、贸易、金融等统计数据均提供网上下载和正式出版发行形成较大反差
(15) “我国保密制度重设底线秘密级删灾害死亡数”,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50920/100066.shtml,2006年6月6日
(16) 关于档案开放制度设计的尝试和构想,笔者已另撰文进行阐述,具体思路包括缩短细化档案开放时间、扩大档案开放适用范围、加强公民利用档案权利保护,明确档案开放责任和监督主体、公示档案开放工作、建立档案开放回应登记机制、增设档案开放免责机制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