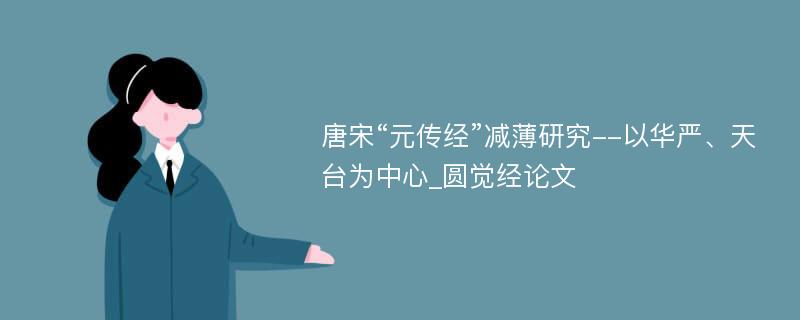
唐宋《圆觉经》疏之研究:以华严、天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台论文,唐宋论文,华严论文,中心论文,圆觉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唐宋《圆觉经》的解经史
《圆觉经》,全名为《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一卷),据称为唐佛陀多罗(觉救)所译。最早记录它的目录——《开元释教录》就已经对该经译出时间不究其详,《开元释教录》卷九中说“此经近出不委何年”。不过,《释教录》并没有因此怀疑此经,反而肯定其思想的意义:“且弘道为怀,务甄诈妄。但真诠不谬,岂假具知年月耶。”①尽管《圆觉经》初期目录所载译时存在着一些疑点,但传统《圆觉经》的解释学者们一般也都遵循《开元释教录》的立场,而肯定该经在佛教义学上的价值。如现存最早的宗密《圆觉》疏在论及《圆觉经》的传译时,就从思想义理而不是历史文献角度来论其真伪:“然入藏诸经或失译主,或无年代者亦多,古来诸德皆但以所诠义宗定其真伪矣。”②可以想见,关于《圆觉经》在唐代的流传中存在一些争议,而宗经者仍然主以所诠宗义作为判定经典之真伪,即以自宗思想的标准来楷定文本的真伪。这种重哲学义理胜于历史文献考订的倾向,在唐宋佛教解经学史上是一个非常主流的观念。
近代学界却颠覆了这一传统解经学方式,重于历史考据,并以此作为判释经教真伪的根据。于是近代日本学界大都把《圆觉》视为中国本土撰述,主流学术也大都接受了这一看法。③我并不想在此细究该经真伪问题,而试着从唐宋解经史去分析《圆觉》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流传和效用。从思想属性方面讲,《圆觉》乃融《起信》《楞严》为一法味,④对于中古以来中国佛教思想的塑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圆觉经》疏的历史看,《圆觉经》最初是在禅门中开始流行,随着禅与华严的融合,特别是经过宗密华严禅的发挥,唐宋华严一家也把《圆觉》思想纳入其思想系统中,而且可以说,唐宋时期华严一系的《圆觉经》疏主宰了圆觉学的主流。天台在中唐以后一直在义学上欲与华严一论高下,如同他们在对待《起信》、《楞严》方面要与华严作不同的发挥,并与之对抗一样,对于《圆觉经》的接受和解释,同样也是因为华严一系注疏的流行而引起台宗的回应。这一点在宋代《圆觉》疏的历史中可以分明辨识出来,让我们意识到唐宋华严、天台两家的解经,不仅为了解释经中奥义,更是要从解经的论述策略上去完成宗派政治意识的需要。
关于《圆觉》疏的历史,日本学者汤次了荣在《圆觉经之研究》一文曾对此作了较完整的阐说,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研究。⑤不过无论从历史材料或是思想史的论述层面,都还有不少内容需要进行新的补充和论议。唐宋时期《圆觉》疏的发展可以宗密《圆觉》疏的出现为分水岭,我们分别从三阶段来看。
1、宗密疏前史。唐代在宗密前所流传的《圆觉》疏家,著名的分别有报国寺惟悫、先天寺悟实、荐福寺坚志和海藏寺道诠四位,他们的疏现在都已经不存在,只有在宗密著作中保留有部分记录和评论。
宗密所指初期《圆觉》疏的四位作者中,其中三位就与初期禅门有关。美国学者格瑞高睿(Peter N.Gregory)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根据7世纪末到8世纪初《楞严》在禅门中的流行,特别在洛阳一带北宗门下的流行情况来推断《圆觉经》不仅流传于南宗门下,也可能流行于北宗门里⑥。格瑞高睿还从柳田圣山关于《圆觉经》的研究中获得进一步的支持。柳田圣山通过将《传法宝记》中发现的“圆觉了义”之语指为《圆觉经》的解释,从而认为《圆觉经》的成立可以追溯到《传法宝记》成立之前。这一解读左右了不少西方学者对《圆觉经》成立的看法。神秀门下所著《传法宝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佛在世时,尝所说法,著乎文字而为经。虽圆觉了义存乎其间,而凡圣不接,离真自远。”
柳田圣山把文中的“圆觉了义”解读为《圆觉经》,这一读法其实是很值得商量的,⑦而马克瑞(John R.McRae)英译《传法宝记》也采用柳田氏的解法而译为经名。⑧格瑞高睿正是根据这一译文来确认《圆觉经》最初在北宗门中的流传。《圆觉经》及其《圆觉》疏与初期禅史的关系,尚可留作进一步的讨论。
2、宗密之《圆觉》疏。宗密有关的资料显示,他接触《圆觉》也是很偶然的机缘。⑨从《圭峰禅师碑铭》、《宋高僧传》到《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记载中,都详略不同地讲到宗密对《圆觉》的契合。如《碑铭》就说:“初在蜀,因斋次受经,得《圆觉》十三章,深达义趣,遂传《圆觉》。”⑩宗密对《圆觉》有感而契,并进行了详密的研究,先后对《圆觉经》作了《大疏》、《大疏钞》、《大疏科文》、《小疏》、《小疏钞》等,一生当中多次而且是如此繁密的疏解《圆觉》,可见《圆觉》成为他一生最重视的经典。宗密疏《圆觉》,有批判地总结前人《圆觉》疏的成果而欲求超胜。在他之前诸家的《圆觉》章疏,禅教之解多是分开的,禅师注经不重经师方寸,而经师论义,又缺乏观心内证。宗密自己是一位兼具禅门与经论师两重传统的人物,《圆觉》给他的兴趣也正是在于,他认为该经体现了他理想中禅教不二的观念。在《圆觉经大疏》序中他这样说:“禅遇南宗,教逢斯典,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一轴之中义天朗耀。”(11)可见他对《圆觉》的认识不仅有义学上的觉解,更有心门禅法上的体会。他不满足于前诸章疏中禅教分置,不能融合的状况,而希望通过重新疏解《圆觉》来会通经教与宗门。宗密在解经和教学上所标举的融合观念,除了当时佛教学内部的要求外,可能还有更深广的社会成因。(12)
在解经的方法方面,宗密并不是简单参照传统《圆觉》疏的成果,而更多地综合佛教各宗经论与南北禅门思想,融会贯通地建构他个人对《圆觉》的理解。他自己就说其疏解《圆觉》乃“采集般若,纶贯华严,提挈毗尼,发明唯识……参详诸论,反复百家,以利其器,方为疏解。冥心圣旨,极思研精,义备性相,禅兼南北等也。”(13)裴休给他的大疏写序时也这样评论道:“禅师既佩南宗密印,受《圆觉》悬记,于是阅大藏经律,通唯识、起信等论,然后顿辔于华严法界,宴坐于圆觉妙场,究一雨之所沾,穷五教之殊致,乃为之疏解,凡《大疏》三卷《大钞》十三卷《略疏》两卷《小钞》六卷。”(14)宗密疏的出现在《圆觉》解经史上成为最为重要的作品,一时间成为后世《圆觉》学之圭臬。如宋代行霆的《圆觉经类解》卷一中就称赞“圭峰之作今古同遵,四海流通,逮今无壅。”(15)一直到清代华严学人通理在他的《圆觉经析义疏悬示》中还这样讲:“目今盛行海内,独步讲筵者,唯我法界第五祖贤宗正三世圭峯大士。所出两疏、两钞为尤著也。如相国裴序赞云:其叙教也圆,其见法也彻。其释义也,端如析薪。其入观也,明若秉烛。其辞也,极于理而已不虗骋。其文也,扶于教而已不苟饰。不以其所长病人,故无排斥之说。不以其未至盖人,故无胸臆之论。乃至云:后世虽有作者,不能过矣。”(16)
宗密的《圆觉》疏名气太大,在佛教史上也引来不少的批评。这一方面有来自于义学的天台学人,而出于宗门的禅师,如宋代的真净克文、大慧禅师等也对宗密《圆觉》疏中改写经文的做法颇有微词。(17)
宗密疏所引出的华严学内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圆觉》与《华严》两经的关系究竟如何?宗密在义学上面追随“华严疏主”澄观,澄观是《华严》大家,最重视和系统诠解的仍然是《华严经》。可以确定地知道,澄观接触过《圆觉经》,并在《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用了“圆觉经”之语;但也可以肯定地说,澄观自己并没有重视到《圆觉》的价值。(18)宗密推崇澄观为宗师,而实际于《华严》的重视则远不如对《圆觉》和《起信》等经论。(19)即使他对《华严》及清凉《华严》疏的解读也要参究到《圆觉》经义上面来核定旨趣,他说“宗密遂研精覃思,竟无疲厌,后因攻《华严》大部清凉《广疏》,穷本究末,……一一对详《圆觉》,以求旨趣。”(20)有学人研究表明,宗密思想虽然源于法藏、澄观以来的华严教学,而恰恰有不少地方是从法藏、澄观那里“转化而产生了自己独立的内容”,特别是他通过对《圆觉》的重视,改变了初期华严教学以《华严经》为至上的传统,而代之“以《圆觉经》为中心的宗密之独立立场出现了”。在宗密的某些论述中,确实含有《圆觉经》教理比《华严》的法门更优秀的证明。(21)
宗密自己经常把《圆觉》提升到《华严》相当的地位,他认为,《圆觉》在义学丰富方面虽然不及《华严》之广大,但却更为简要直入,方便初机:“若约文义富博,诚知不及《华严》;若取指示觉心之体,以投顿悟初机,即不如《圆觉》,故若留心偏愿弘此。”(22)他甚至表示过《圆觉》对《华严》的超越。
“《圆觉》中义与佛所相当,题云了义者。《法华》《涅槃》《华严》不题云了义,应可皆非了义。……《法华》云妙,《涅槃》圆寂,《华严》万行之。《华严》饰法体,《般若》能断烦恼,各从增胜之义,而占一名。不可难云:《法华》之外,余经量皆不妙。《涅槃》之外,余经皆无圆寂之理。《华严》之外,余经皆不说万行及佛。《般若》之外,余经皆便不说智慧断惑等。疏唯此等者,此经决了觉真妄性相,穷须尽底了义之味,偏为增胜,故特标也。”(23)
而在《大疏钞》卷一中有一段文字,宗密则以同属顿教二支来安顿《华严》与《圆觉》的关系。他指出二经所主之义皆为顿教,但一为化仪顿,一为逐机顿。
这些说法是意味深长的,他一面把天台所宗《法华》判为渐教之极,而以《华严》、《圆觉》作为更为殊胜的顿教法门,又以两类顿教来分列《华严》与《圆觉》。《华严经》虽然高据顿教,但只限于上根菩萨成道,性海果分处所说,无法广被随机,而只有《圆觉》的逐机顿教才能够“逐机显体”,更适应时代的需要。在这一新的判教说法中,宗密就做好了以《圆觉经》为中心的判教。在这里宗密做了对法藏以来《华严》为中心判教的完全转变。(24)根据这一说法,宗密把《圆觉》抬到类似《华严》,甚至高于《华严》的地位,而实际上,宗密对这一由《华严》独尊急转到《圆觉》与《华严》并举的论述并没有很好的说明,甚至颇具有独断论的倾向,于是不仅易于引来天台家的反对,就在华严宗内部也埋下了关于《圆觉》与《华严》高下之论的伏笔。宋华严家清远在为宗密《大疏钞》作要解时就特别提出《圆觉》与《华严》哪个更为究竟的问题,而希望回到初期华严学的立场而阐扬《华严》的优越。但宗密《圆觉》疏所隐埋的问题,终于在宋代华严家内部形成一大论争的公案。(25)
3、宋代《圆觉》疏之发展。宋代的《圆觉》疏大致可以分为三系,即华严、天台与禅宗,而以华严、天台两系之《圆觉》疏最为重要。我们以此两系为主来讨论宋代注经家的思想。大致可以这样分判,具有华严倾向注家主要有净源、观复、行霆、清远、如山等,而代表天台一系立场的主要为鄣南、(东阳法师)居式、(竹庵法师)可观、(慈室法师)妙云、元粹、智聪。
先说华严的《圆觉》学。净源(1011-1088年)是宋代华严最重要的学人,被誉为宋代华严学的“中兴教主”,宋代史书把他作为长水子璿的传人,而思想上面他实际上嫡传圭峰宗密的法流。子璿重视的是《楞严》,被称为“楞严大师”,《佛祖统纪》卷二十九说他“以贤首宗旨述《楞严经》。”(26)不过他讲学授徒,是把《楞严》与《起信》、《圆觉》结合在一起开讲的。净源就是他的高足,净源传中说他“听长水《楞严》、《圆觉》、《起信》,时四方宿学推为义龙。”(27)这表示了宋代华严学的门下,虽然宗经的倾向和兴趣有不同的侧重,而对《圆觉》与《楞严》《起信》的关系都是视为相互应承的一脉,应该说,这一现象表示了宋代华严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法流。于是他们也大都是融合《起信》、《楞严》与《圆觉》三经论为中心来开展其思想的论述。
净源很重视《圆觉》,他在《华严原人论发微录》序中,说他就是引宗密之《圆觉经大疏钞》来证义《原人论》的。虽然他没有为《圆觉》疏义,而只有《圆觉经道场略本修证仪》一卷留世,而从该《修证仪》的立场看,他显然都是在延续宗密《圆觉》学的思想。(28)
净源之后,宋代华严学内部关于《圆觉》讨论的最重要的思想事件就是南宋间师会(1102-1166年)一系(师会是净源的三传弟子),主要是在师会的弟子善熹与笑庵观复之间发生的,有关《圆觉》与《华严》的高下之辨。观复有作《圆觉钞辨疑误》两卷(该书现收入在《卍续藏经》第十册中),主要是根据宗密的《大疏钞》来纠正《略疏钞》中的错误,属于一部校对性质的著作。该著并没有讨论到《圆觉》与《华严经》的关系。善熹师承师会的思想,对观复有严厉的批判,其所辨的中心问题涉及到华严判教中“同教”与“别教”的不同理解。善熹批评观复“遂摭所闻,以辨差当,犹不体其本,而未免乎失焉。”(29)虽然这不是专就《圆觉》的判释而论,但从善熹的《斥谬》一文来看,自宗密以来确有一股思潮,把《圆觉》与《华严》一同视为“别教一乘”。
《斥谬》开宗明义就说“近代有人说《圆觉经》乃同《华严》别教一乘,以圭山第十钞云序及玄谈已明言此是别教一乘,非《法华》通教一乘。”善熹认为,如此意见则有损于《华严》独尊的地位。于是他在《斥谬》中布有很多专门讨论《圆觉》的章节,其主要就是针对这一说法而进行驳斥。如他把《圆觉》判为“顿教一乘”而低于《华严》。在善熹看来,只有《华严》为“别教一乘”,《圆觉》在华严祖师的判释传统中只能列为“顿教一乘”。《斥谬》还从性起一义来论《圆觉》之缘起为“同教义”,而认为只有《华严》之性起才是“别教义”,明确表示以《圆觉》去比《华严》十分不相称,“以此经分同华严故不的配”。(30)此外,该文中还分别列举诸条,逐一来说明《华严》高于《圆觉》之义,此不一一详论了。
宋代其它具有华严学倾向的圆觉疏注大体不出宗密疏的范围,或多少只在某些细节方面对宗密疏略加补充而已。如复庵行霆的《圆觉经类解》四卷就是要以宗密疏为旨要,《圆觉经类解》卷一所谓“专用圭山疏要,傍类经子禅语直销文义。”(31)又如清远所著《圆觉疏钞随文要解》十二卷,也是以宗密圆觉疏来判定一切是非,难怪有学人说他“祖述圭峰,用力疏钞,楷定众师之邪正,甄别百氏之是非。”(32)显然这些都是以宗密圆觉学作为典范的。
关于天台一系《圆觉》疏的出现,可以说唐宋以来,天台在义学方面为了与华严宗抗衡,曾经多次借用华严宗所热衷疏解的经论而作出天台教义的疏解与延伸,如他们对《起信》、《楞严》的疏解大都是如此。(33)从唐末以来,天台思想的发展较为衰弱,所谓“台道既微”、“台山坠绪”,其发展只局于江南一隅的吴越一带。天台在思想的创造方面也不像华严学派那么有活力,“讲席教义中断,正统传承不明”。(34)所以天台学人大都疲于应付和被动地为华严宗牵着走,特别在解释《起信》、《圆觉》的方面,多数是由于华严宗作疏的原因才去作出自己的解释与应对。天台对《圆觉经》的意识比华严宗晚很多,代表天台学意识的注疏大多是从宋代才开始的。可以说,宋代天台的圆觉学在天台思想内部并不成为主流,参与注解《圆觉》的天台学人中,名流和重要的人物并不多,甚至有的注家根本不见经传。这样来判断,应该承认天台系的《圆觉》疏注在宋代佛教义学史上还只能说是一伏流。
宋代天台《圆觉》学诸家,如鄣南、(东阳法师)居式、(竹庵法师)可观、(慈室法师)妙云、元粹、智聪等人的作品很多都没有保存下来,如鄣南、(东阳法师)居式、(竹庵法师)可观、(慈室法师)妙云等虽然都有《圆觉》注疏,但均已不存,他们有关《圆觉》的解释,部分保留在元粹的《圆觉经集注》和智聪的《圆觉经心镜》中。(35)说到古云元粹,根据《佛祖统纪》与《释门正统》的排序,其为可观的再传弟子(可观—北峰宗印—元粹),但不见其具体的传记资料。保留下来的作品,除了《圆觉经集注》外,还有一部关于天台的《天台四教仪备释》两卷(收录《卍续藏经》第57册)和注解玄奘所译《心经》的作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解义解要》中收录有他解经的部分内容。(《卍续藏经》第26册)
元粹解经的基本宗趣就是要“传十方天台教观”。(36)《圆觉经集注》不仅以保留天台注家的《圆觉》学为己任,并在此基础上,禀持天台教义来加以引申,以期《圆觉经》思想的天台化。
另外,崇山教寺智聪著《圆觉经心镜》一书,现有保存。有关他的材料都不详,不知道他的法系传承。智聪《心镜》序里虽然说他自己注疏《圆觉》并不采一家之说,而是博采众议,通摄诸家来进行抉择,而实际还是充满了天台教学的宗旨。值得注意的是,他经常应用宋代天台学的教义来进行会解。如其《心镜》卷三即借《起信》“一心二门”而又结合天台性具恶的观念,特别是宋代天台山家所谓“理毒害”的观念来解“圆觉之性”。
又其所论圆修义,颇涉宋天台家之所论:“良由修圆觉者,观性德苦乐,而兴与拔。以即理毒害,为所消伏。”(37)这一理毒消伏的观念,正是宋天台山家山外所论之重要主题之一。(38)
等到天台学人出来疏解《圆觉》时,宗密的疏钞早已成为《圆觉》学典范,于是天台要表示自己的宗义,一面必须广泛应用天台教义来解释经义,同时也针对宗密圆觉学的权威作出直接的批判。这一点在宋代天台的《圆觉》疏中是可以看出来的。虽然天台学还无法对宗密疏进行系统的清算,但也不放过宗密疏在疏解细节方面的问题。可观解经有着强烈的天台宗意识,“南渡已后禀学台宗者,竹庵可观。”(39)元粹《圆觉经集注》卷上引竹庵《圆觉手鉴》解,就根据天台性具观念批评宗密《圆觉》疏妄改经中文字:
“一切众生皆证圆觉,圭峰云:以己证知一切有情无不是觉,译经讹也。应云证诸众生皆有圆觉。噫,圭峰疏序云心本是佛,那得輙改此中经文?亦有引经,一切众生即寂灭相,以证不讹,然终未能了一切如来所修所证皆本性德,若非性德,则名别修别证,非圆顿也。皆证圆觉与夫本来成佛相去几何?圭峰自谓教逢斯典,心开于一言之下,不谓此文偶乖经意。(竹庵)略疏此解,先德皆不取具,如焕疏盖不明性具故尔,学者当依法不依人可也。”(40)
智聪解释《圆觉》受到天台慈室妙云的影响,他对宗密疏钞有过深入研究,但也不一味轻信。他说:
“蚤登台岭,晚会清修。遇慈室每讲斯经,阅圭峯诸家疏记,钩深索隐,各具雌黄。且夫采幽兰者,宁唯于楚泽。求美玉者,奚必于荆山。况摭言辨惑,岂限于宗徒;披砾拣金,何嫌于取舍。”(41)
这段话可圈可点,智聪表面上对天台、华严的《圆觉》学评判平分秋色,而实际暗示了对于宗密圆觉疏独尊状况的不满。所以智聪在《心镜》卷三中也很不密气地批评了宗密的改经手法:
“圭峰云:皆证圆觉者,译师讹也。应云证诸众生,皆有圆觉。可谓聪明人前,有三尺暗。岂不闻上文云:始知众生,本来成佛。成岂非证耶?”(42)
这些批评的内容与宋代禅门真净克文和大慧宗杲对宗密疏的批评是同出一辙的,反映了宋代天台与禅宗门下对作为典范的宗密《圆觉》疏存在着另一类的意见。天台对宗密疏的批判当然是意味深长的,不能够只是从解释的表面来看问题,其背后所隐含的宗派意识还需要作具体的分析。
二、华严与天台解经中的宗派意识
有学者发现,佛教的解经通常同时面对着双重约定,一面必须阐释出经典中的佛陀教义,另一面又必须在解经中说明自身宗派的正统性,以自己的宗派思想作为解经的前提。这两重约定暗含了一种深刻的紧张。(43)如何在经典解释当中去说明自身宗派的正统性与至上性,可以说都含藏于一切解经活动的背后,成为我们讨论解经学所必须去揭示的“解经策略”。
晚唐五代以来,华严与天台两家抗争激烈,表现在他们对经典的诠释当中各立权衡,以自家为至上圆教而贬低对方。唐宋《圆觉》的解经也表现了这样的现象。居简在为天台学人元粹所撰《圆觉经集注》序中就这样明确地评说两家之争:
“圭峯发明此经,造疏数万言,反约于广博浩繁之中,略为别本,由唐至今,广略并行,西南学徒家有其书。于戏盛哉,江淮荆蛮稍若不竞。天台再造于五季糺离之际,鼓行吴越间,作者辈出,巉然见头角。由是二家之言肝胆楚越,咫尺云壤。彼所宗尚,我得排斥;我所宣演,彼得指议异己之。卓识与共堵必羣而咻之,务其说之不售,同己之固陋。远在万里,必引而嗾之,欲其喙之,必信使二家之道不沦于必争之口者几希。”(44)
早在宗密疏注《圆觉》前,他就对天台教说有所不满。在元和六年(811年)给澄观法师信中,他就表示天台“多约止观,美则美矣”但“滋蔓不直”,不能够“示众生自心行相”。(45)在论述策略方面,华严与天台一方面用自家的观念或所宗的经论去会通《圆觉》,使《圆觉》思想华严化或天台化。另外一个手法,即以教相判教的方式去表示自家宗义的圆极至尊。唐宋华严、天台《圆觉》疏中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如宗密以华严“性起”义解《圆觉》,以为性起方是佛教的圆义。《大疏释义钞》卷六中说:
“疏然净缘起下,摄成此门也,(即此经幻尽觉满之门也)亦是释成论中净法不断之义。……言俱融者,迷真起妄,悟真翻妄。离自真性,无别染净。故染与净,即体同真故。云合法界性,故论云无别始觉之异也。起唯性起者,即华严宗中性起门也。”(46)
对照天台的解法,则完全表示了不同的宗趣。智聪的《圆觉经心镜》就以天台“性具”之义来解“圆觉”缘起。《心镜》卷一中云:
“圆觉妙心具足十界,百界千如,三千世间。生佛依正,色心染净诸法,故曰一切。以由圆觉无自性故,遇染则情生。十界俱染,在理则性净。……真如法身德也,菩提般若德也,涅盘解脱德也。此之三德,皆从圆觉生,故云流出。菩萨以此为轨则,故曰教授。众生性具此三德故,一念能感。”
又以天台性恶之义解圆觉,《心镜》卷二说:“若大乘菩萨修圆顿行,以性夺修,名无作行,皆是性恶法门。直指华翳,生死涅拌本如来藏,即大圆觉。”(47)不难判断,华严、天台两之注解《圆觉》,其一项重要的动机就是通过解经活动把《圆觉》经义作宗派性的转化。
我们再从判教来看两家对《圆觉》的疏解策略。隋唐以后,判教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对佛典的思想进行判释和排序,而很大程度上成为宗派自判高下的论述工具。就是说,判教不只是教义的阐释而更多为宗派政治的论述了。(48)所以对中国佛教史上判教的讨论,不能够仅限于思想内部来看,必须意识到其背后所隐喻的宗派意识形态的修辞。
宗密判释《圆觉》就非常鲜明地代表了自宗的立场,并含藏了对天台教义的批判。在《圆觉经大疏》卷一之“藏乘分摄”和“权实对辨”的解说中,他专门讨论了从印度到六朝以来各家判教之旨,表示宗密对《圆觉》的疏解一开始就要安排在他对整体佛教判释的基础上面来进行。他在《大疏释义钞》卷一中先以五时判定一切佛教经义。宗密所谓五时教相与刘宋慧观创倡以来一般所通用之说法,及天台五时教说的判定都不相同。(49)特别是他把天台所宗之《法华经》判为第四时,而且归于渐教的一类,成为“大乘渐教中终极之教”。这一判法明显是在贬斥天台的教义和地位。在宗密的判释中,只有《华严》与《圆觉》属于顿教所摄,所以在思想上优越于一切经教而“不属三时五时”。(50)
宗密认为《圆觉》虽然统摄了天台、华严两宗教义,(51)但他自己在解经的倾向上面还是华严家与禅宗荷泽的立场。他经常以判释教相的方式巧妙地把天台安置于华严之下,其解经中的宗派目的是很明显的。在《大疏释义钞》卷三中,宗密论顿渐修法时,就将天台与禅门北宗列为一类,判为“渐修顿悟者”。在宋代南宗禅一统天下的格局里,把天台与北宗并列暗示了对天台教义的贬弹。宗密就指出,此类渐修顿悟的方法是无从达成圆证的:“天台数年修炼百日加功用行,忽然证得法华三昧旋陀罗尼门,于一切法悉皆通达,即其事也。北宗渐门之教,意见如此。然多入二乘之境,难得圆通证。”难怪清远的《圆觉经随文要解》卷五这样评意味深长地评论宗密的这一说法:“《大疏钞》以北宗之渐禅摄天台止观,《略疏钞》以天台止观摄北宗之渐禅,盖北宗天台皆渐故,行相是同,互举之耳,足见圭山意度深远。”(52)这一点,我们从宗密评论天台止观的说法中更可以鲜明体会出来,《大疏释义钞》卷二中,他甚至将天台禅定列为初禅境地,而提出只有《起信》中之“一行三昧”才是深入的“一性观门”。(53)
宗密在《圆觉》疏的判释决定了宋以后华严诸家园觉学的基本格局。宋华严家清远之《随文要解》就基本沿袭了宗密的教相判释和对天台教义的批判。如其《随文要解》也判《圆觉》为五时教外,宗通别圆,而又有意识地抬高《圆觉》、《华严》于天台所宗《法华》之上。清远在《随文要解》卷四论判教说:
“良由根本法是诸佛师故。然如上所叙,皆疏抄明言,如揭日月矣。……三乘始教属权仪渐中,圆极为能会所会,羣经属五时,五时都不关《圆觉》。蔡祖明言:岂不知此经别,一超通教,宗同圆别……圭峰宁不暗攒眉《般若》、《法华》名共教,菩萨天龙共守之;《圆觉》、《华严》根本法,三世如来亲护持。”(54)
此外,《要解》卷六中还特别批评了天台判教无法包容顿教经论,言下之意即是说,天台教相停留于渐教的宗趣,而顿教之义,超出天台所论,《圆觉》经义乃顿中之极经。
对照来看,天台宗的圆觉学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宋代天台的《圆觉》疏一面从解经的内容上面去贯注天台的教义,批判华严一家之说,如智聪《圆觉经心镜》卷五解释觉性法性关系就明确针对宗密疏:
“圭峯云:若直谈本体,则名觉性;若推穷差别之法皆无自体,同一切性,即名法性。今谓:觉性法性,一体无二,但说果人。所修所显名觉性,因人所迷中修所显者,名法性。法性通一切法也。”(55)
在判教的方面,天台学人解《圆觉》也试图与华严宗一论高低。相对于华严学于教相判释上系统地论述《圆觉》与宗派的关系,天台宗于《圆觉》教学上的判释却显得比较薄弱。其不仅没有系统地建立《圆觉》与天台所宗经论的关系,对于华严一系在判教上排斥异己的手法,也缺乏建设性的批判而只是被动地予以回应。宋天台一系的《圆觉》疏很少从判教方面去专门而细致地讨论《圆觉》教义,但可以看到一些零散的论述。如智聪《圆觉经心镜》中的判释就非常有趣而又意味深长,他不同于华严圆觉学把《圆觉》判为“五时教外”,而指出《圆觉》教义虽为圆宗,在教相上却当归属于方等部。
《心镜》卷一上说“此经乃穷理尽性之书,洁静精微之教。部虽属于方等,教味唯归一圆”。“方等”在天台的五时教义中为第三时,其后方有第四《般若》和第五《法华》、《涅盘》时教。照这样的判释,《圆觉》在教相上面就不是如华严宗人所说,超于《法华》而与《华严》别为顿教的一流,而恰恰远在《法华》之前的阶位。智聪试图以《圆觉》“教味为圆”的说法来打圆场,不过,这里圆教的标准已经不是《华严》,而正是《法华》了。《心镜》卷一就明确以《法华》一经作为圆教之标准,并以此来统摄《圆觉》:
“了义者,《法华》以前,圆教之外,皆不了义,盖权实未融故也。今既闻开显,同《法华》之圆,并为了义,所以事理圆融,因果顿足。佛法之妙,岂复有过于此。”(56)
这一充满了修辞性的判释背后,表示了宋代天台的圆觉学欲维护自家的圆教至尊而不惜与华严系一究高下。可以肯定,华严与天台圆觉解在疏通经义的同时更想完成的是对自宗意识形态的再制造。
三、再论疑伪经论及其诠释:从《起信论》、《楞严经》到《圆觉经》
代表如来藏思想的《起信》、《楞严》与《圆觉》自唐宋以来在中国佛学思想的形成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无论是义学之天台、华严或是禅门宗趣,都相当程度地受到这些经论的影响。有趣的是,这些对中国中古以后佛教思想史的性质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三部经论,却被广泛地认作是疑伪经或所谓中国撰述的经典。吕澂先生就指出,中土伪书由《起信》、《占察》等,而到《圆觉》、《楞严》“一脉相承,无不从此讹传而出”。(57)至于这一系疑伪经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影响究竟是如吕先生所说以讹传讹,造成重大的伤害,或是代表了佛教不同思想的法流,具有正面的意义,这些还需要作新的思想史讨论。
有关佛典中国撰述的问题非常复杂,它不单纯是汉译经典的思想内部或一般经录考订的问题,而同时涉及到更深广的历史脉络,因此需要从中国社会史的角度去加以认识,这里无法细究。(58)不管怎么说,《起信》、《楞严》与《圆觉》——这些所谓中国撰述的经论——其思想之间就存在着很密切的关联和一致性,甚至有学者提出,《圆觉经》的内容乃是基于《首楞严经》,并掺进了《大乘起信论》的教义而在中国被创作出来。(59)更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这些经论所发生的解经学活动中,各经论的解释也通常是互为援引而为经证的。从时间方面看,《起信》与《起信》疏的出现最早,接着《楞严》与《圆觉》及其注疏也交替出现。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唐宋华严、天台两家解释《圆觉》思想中是如何应用《起信》和《楞严》的。
先说《圆觉》疏中的《起信论》。华严宗与《起信》关系自法藏以来就获得充分的发展。(60)法藏很重视《起信》,并参照元晓的《起信论疏》分别作了《起信论义记》和《起信论义记别记》。在《义记》中,他把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论分为大小四宗,其中尤其推重《楞伽》、《起信》等为代表的如来藏缘起宗。宗密的老师澄观也传《起信》,并学习过华严传统中的《起信》疏。《宋高僧传》卷五本传中载:“大历中就瓦棺寺传《起信》、《涅槃》,又于淮南法藏受海东《起信疏义》。”(61)法藏、澄观一面应用《起信》于华严的教学,不过他们学说的重心还是放在《华严经》上面。可以说到了宗密,《起信》才在华严学传统中起到前所未有的应用。
宗密曾经为《起信》作过疏、疏钞和科文,(62)他的整体思想比较彻底地贯彻了《起信》的宗义。他在华严学上的思想系统和论述,基本都是以《起信》为纲骨来建立的。(63)回到他的《圆觉》疏来看,宗密诠解《圆觉》虽然会通了唯识、空论及其它宗义的典论,而最终都是根据如来藏思想“皆本一心而贯诸法,显真体而融事理”,(64)特别是以《起信》思想作为根本而进行的。正如有人评论他疏解《圆觉》乃是“分三重于法界,《华严》之旨现焉;开二门于一心,《起信》之意着矣。”(65)《华严》与《起信》成为他疏通《圆觉》思想的法眼。我们不妨说,《起信》在他的思想论述中起到更为直接和彻底的作用。《圆觉经大疏》卷二讨论《圆觉》宗旨时,就应用《起信》最根本的一心二门、本始二觉来阐明《圆觉》的“宗旨始末”。
其思想体系和概念几乎都是从《起信》中翻抄过来的。
宗密《圆觉》疏中大凡涉及真如一心流转与还灭的解释,其基本论述结构也都是照《起信》真如缘起,本始二觉、三细六粗、真如无明互熏习等理论架构来开展的,类似案例太多,我们无法一一详引。(66)宗密不仅以《起信》作为解释《圆觉》的基本典论,他还经常引述法藏的《起信》疏来进行会解,表示他对《起信》的理解与应用,仍然是在华严学的传统内进行的。如他在《大疏释义钞》卷七解释《圆觉》观门时,就多次引“藏和上《起信论疏》作此释也”。(67)
宋清远在他的《圆觉》疏中也多次引述《起信》为经解。他在《圆觉》疏中,还试图解决由法藏《起信》疏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法藏虽然重视《起信》,但《起信》在法藏判教系统小、始、终、顿、圆五教中却只相当于终教的地位,还不及于顿教。宗密以来,华严学整体的思想更趋向于《起信》,如果《起信》还只是判在终教义门,显然不太合适。清远对《圆觉》的解释中特别要处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他自己的“一家之说”。在《随文要解》卷八“开示二觉”中,他认为法藏判《起信》为终教,是就《起信》生灭门的意义来说,实际上《起信》生灭门是可以通终、顿二教的。他说:
“《华严》、《圆觉》、《起信》皆顿悟渐修故,问:《起信论》贤首判为终教,那得亦具三重因耶?答:贤首唯据《起信》立题及翻对妄染义故(彼疏云兼顿而圭山移注依之),盖取宗经深妙生灭门,宽通终顿,故不妨正终兼顿。”
“彼论虽不判教,释义多约顿门,古今有多异说,或虽然引证,非全同故;或云虽是终教,纔悟性处便属顿教故;或云终教直进人顿悟故,亦名顿教;或云顿渐二机取之不同故,若渐机取之即终教,顿机取之即顿教;或云虽约真如生灭二门分,终教亦大分言之二门,不妨义互通故,生灭门互具顿教义。”(68)
这些解释都意在把《起信》从终教提升会通到顿教,表示《起信》在唐宋华严《圆觉》疏的传统中不断被强化。此外,宋代华严系行霆之《圆觉经类解》也把《圆觉》安放在《起信》、《华严》的关系中来进行论述,《类解》卷一解释经题时,专门讨论了这三经论之间的异同:
“《华严经》说三大,《起信论》说三大,与今经说三大是同是别耶?答:配属三大,约法则同,释义随宗则别。《起信论》就凡上建立三大为宗,《华严经》就玄上及事上建立三大为宗,(凡一字皆具十义)今经就本觉体上建立三大为宗,故不同也。所以《起信》约凡以为心,《圆觉》约佛以标名,《华严》不遂机宜,直显一真法界也。又《起信》大分约因位说,《圆觉》与《华严》大分约果位说。”(69)
《起信》这样流行于华严教学中也逐渐引起了天台学人的重视。唐代天台中兴者湛然为了重兴天台,与华严抗衡,“正破清凉观师,傍破贤首”,(70)就注意到华严一向应用的《起信》,尤其是该论真如随缘不变的思想,并引向天台学的教义,作了与华严学不同的诠解与发挥。到了宋代,天台学内部更是围绕着《起信》而开展了激烈的论辩,可以确定,《起信》在中唐以来,特别是在宋代天台教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71)这一法流在天台《圆觉》疏中也有所表现。
天台学人引证《起信》来解《圆觉》,其中智聪的《圆觉经心镜》就非常有代表性。《心镜》非常多地引《起信》来解《圆觉》。如《心镜》卷一解“圆照”一义,即全引《起信》本始二觉的说法,不过又作了天台“全性起修”观念方向的引申:
“今依马鸣立境体者,所谓本觉;其智体者,所谓始觉。故《起信论》云:所言觉义者,谓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虗空界,无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来常住法身。依此法身,说名本觉。此觉是性,全性起修,名为始觉。论云:始觉者即同本觉。既云离念,岂有思议;既等虗空,无所不遍。岂有一时一尘一心而非本觉及始觉耶。”
接着《心镜》更以天台之心具、理具观念解《起信》本始二觉。《心镜》卷四解《圆觉》中的“圆觉慧”,一面也以《起信》本觉来解,而同时会通到《法华》和天台特有的性恶思想中去作发挥。
接下来讨论下《圆觉》疏与《楞严》的关系。唐宋时期《楞严经》在华严、天台和禅门中都很流行,唐宋有关《圆觉》疏解的历史也同时反映了这一现象。格瑞高睿在《宗密与佛教中国化》一书中,试图讨论《圆觉》为何会在宗密时代受到重视的原因,他提出惟悫是一重要人物。惟悫同时注疏过《楞严》与《圆觉》,宗密《圆觉》疏提到他之前的几位疏家,惟悫是最重要的一位。格瑞高睿认为,从惟悫同时注过《楞严》与《圆觉》这点来看,表示《圆觉》的流行与当时《楞严》的流行有关,由《楞严》的流行而关联到《圆觉》。(72)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是先有宗密疏促成《圆觉》的流行,才连带出佛教界对《楞严经》的重视。日本学人荒木见悟就认为,《楞严》的流行最初起于宗密的《圆觉》疏和五代时期延寿《宗镜录》中广引《楞严》,从而引起学界注目而在宋代以后才加速流行。(73)由于惟悫的《圆觉》与《楞严》疏均已不存,究竟是由《楞严》的流行而引发《圆觉》热,或是因为《圆觉》疏而引起对《楞严》的注意,这些问题还可留作深论。
如果照宋代华严家的说法,则华严学宗经的轨迹应该是先兴《圆觉》而后兴《楞严》的,华严学经历了由唐宗密的注《圆觉》到宋代子璿之传《楞严》的转变。(74)宋华严学人净源就说“若清凉之释大经(华严),圭峰之解《圆觉》,长水之注《楞严》,皆所以抗志一乘,潜神五教。”(75)不管怎样说,这两部思想旨趣较为相近的经典同时流行于当时的华严学中,也表示了唐宋以来华严教学的思想倾向,逐步地走向了由《起信》、《圆觉》和《楞严》所左右的如来藏思想路线,即通过经典解释的方式形成自己的思想传统。宗密疏《圆觉》不仅引到《楞严》为经证,而且还引到惟悫的《楞严》疏。可见,他对唐以来楞严学的传统也有深刻的体会。宗密疏解《圆觉》多次引述《楞严》或《楞严》疏为经证。华严学对《圆觉》的解释不少地方都参照到《楞严》的说法,不过《楞严》在华严学的《圆觉》疏中远不及《起信》那么重要。可以这样说,《圆觉》疏大都是以《起信》思想为宗骨,而在某些具体思想的解释方面才会引述《楞严》以作补充。这一点在宗密所创立的《圆觉》疏的典范中就表现出来。宗密《圆觉》疏钞中引述《楞严》的地方还很多,不过他的《圆觉》疏主旨仍然以《起信》为中心的。最明显的例子如《大疏释义钞》卷四解释经中一心思想时就引述惟悫的《楞严》疏,而最终又融入于《起信》的本觉思想来作会通。唐宋以来天台宗也形成了有天台意识的楞严学法统,特别是经过天台山外学人孤山智圆的《楞严》著述后,天台教学非常重视《楞严》。(76)宋代天台宗的《圆觉》疏很多方面也参酌《楞严》来进行了。
天台引《楞严》注《圆觉》,具有更明显的宗派意识,旨在把《楞严》与《圆觉》的思想天台化。与华严一系不同,天台疏《圆觉》并没有以《起信》思想为纲骨,而形成以《起信》统摄会通《楞严》、《圆觉》的现象。我们仅以智聪的《圆觉经心镜》为例,简要说明天台《圆觉》疏中所述《楞严》的情况。《心镜》卷四在解释《圆觉》“妙觉”概念时,明确以天台三观来解,并指出《楞严》所指亦同天台:
“妙觉,证之极也,亦可云觉者照也。照即是观,即今之所示三观也。妙者,空即假中,假即空中,中即空假,三观互融,故为妙。如《楞严》妙奢摩他亦如此解。今向下正明三观,必其然也。”(77)
如此说来,《圆觉》、天台教观与《楞严》思想形成了三合一的“三位一体”。智聪《心镜》以《楞严》来解《圆觉》,而有意味的是,他于《楞严》的理解所会通的,不仅是传统天台学的教义,更有宋代天台山家知礼和山外学人孤山智圆关于《楞严》的意见,表示宋代天台《圆觉》疏的开展也是与时俱进的。《心镜》卷二以《楞严》“七处征心,八还辨见”来讲一切唯心;其卷三用《楞严》解无始轮回,而接着又以天台四明知礼的思想加以说明:
“《佛顶》云:流爱为种,纳想为胎,交媾发生,吸引同业。以是因缘,故有生死。……今且略陈元始,四明云:良由众生性具染恶,不可变异,其性圆明,名之为佛。性染性恶,全体起作。修染修恶,更无别体。全修是性,故得迷逆之事。无非理佛,即以此理。”
卷四中在讲止观禅法时,一面从天台教史去阐说天台止观本来就与《楞严》、《圆觉》所传禅法一致,接着又引智圆的《楞严》疏加以申说,智聪说:
“天台出时,《楞严》《圆觉》未传中国。天台于止观中云:此三止名,虽未见经论,今影望三观,随义立名。其相云何?体无明颠倒,即是实相之真,名体真止。如此实相,徧一切处。随缘历境,妄心不动,名随缘方便止。生死涅盘,静散休息,名息二边分别止。孤山云:《楞严》阿难虽请于止,以即一而三故。止观亦即平等,三一互融,是以称妙。以由妙故,方曰楞严大定也。”(78)
天台之解《圆觉》,无论是引《起信》还是《楞严》作为经证,都不忘回到自家传统教义上去作会通,在这一方面天台表现更甚于华严一系的作为。这表明宋代天台教学中的《圆觉》疏一流相对华严而言,还处于比较边缘化的境地。天台一直没有出现像宗密《圆觉》疏钞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典范之作,于是他们不断地把《圆觉》,甚至《起信》、《楞严》思想引向到自宗教义而强为之解,正应验了佛尔(Bernard Faure)讨论中国禅宗史宗派论述策略时所说的一个观念:“边缘化的焦虑”(boundary anxiety)。亦即越是处于某种思想边缘化的宗派,越是在论述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中心化和正统化的欲求。(79)
四、结语
从《圆觉经》的成立到唐宋以来《圆觉》疏的发展史,无论是《圆觉》还是对《圆觉》的解经,都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迹。在我们汉文佛教史的书写当中,从《起信》到《楞严》、《圆觉》所形成的思想历史或这一历史中所发生的思想史事件都没有获得充分的重视和理解。正如不了解中国的解经学就无法真正认识中国的思想史或哲学史一样,对中国佛教史,尤其是中古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如果忽略或离开对其中重要的经典制作及其解经史的讨论将是很难想象的。更为有意义的是,从《起信》、《楞严》到《圆觉》,无论是这些经典本身的制作,还是关于他们的注疏历史都直接影响了中古以后中国佛教各宗派的思想发展。这三部被认为思想上“一脉相承”的疑伪经论不仅深刻地塑造了唐宋以来佛教各宗派的思想历史与性格,而且其自身的解经活动之间又互为缠绕,形成了特殊的以伪证伪和以伪解伪的思想传统。这种中国佛教经典诠释中的特殊现象,留给我们重新思考和解读中国佛教思想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向度。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疑伪经或所谓中国撰述的经典还可以进行新的讨论,单一地拘泥于一般历史文献学的考论,我们还无法解释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大量更为复杂的因素和现象,必须挖掘出伪经背后的话语论述。就是说,除了文献本身的考订,还需要对此文献制作、形成的历史世界进行“知识考古”,把这些疑伪经所生产的历史脉络以及在中国佛教史上如何被正典化的过程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如此,我们才能够较全面地洞悉和分析这些疑伪经论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面所具有的思想意义与价值。
注释:
①《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565页上。而其它经录则有不同记录,所以宗密作疏时,这一问题就不清楚,而留待深考了。参见宗密《圆觉经大疏》卷上之二。《卍续藏经》第9册,335页上。
②宗密:《圆觉经大疏》卷上之二,《卍续藏经》第9册,335页上。
③自望月信亨在《仏教經典成立史論》中提出《圆觉经》为中土撰述以来,中日学界大都接受此说,如镰田茂雄就认为,望月之见为确定之论。参考其著《宗密教学の思想史的研究——中国華厳思想史の研究第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五十年版,第102页。柳田圣山也把此作为中国撰述之教典,与望月不同的是,柳田主张《圆觉经》成立于712年以前,而望月说则认为该经成立于开元年间(713-730年)。见柳田聖山《中国撰述経典1円覚経》,仏教経典選13,東京:筑摩書房,1987年版。又,冉云华先生也引望月说,而认为此点“已为大部分学者所承认”,见其所作《宗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234页,注29。
④日本学界基本认为《圆觉经》是以《楞严》思想为基础,而同时融合了《起信》思想而成立。见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玉城康四郎等编集,《仏典解题事典——新仏典解题事典》第二版,春秋社昭和52年版,第104页中《圆觉经》条。又有日本学人提出《圆觉经》的形成是以《首楞严经》为基本思想同时,吸取了当时的《起信论》、华严、天台、禅等的教说而成立的疑经。参考曹潤鎬,“『圓覺經』解明の視點——經典成歷史的觀點から”,出自:インド哲學佛教學研究,第四期,1996年12月。
⑤汤次了荣,“圆觉经之研究”,该文收录于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1册《经典研究论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332页。
⑥见Peter N.Gregory,Tsung—mi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56,57.
⑦参考柳田圣山,《初期の禅史1——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筑摩书房,昭和54年,第408-414页。
⑧JohnM.Mcrae,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6,p.267.
⑨胡适曾经想讨论宗密得《圆觉经》及作疏始末,但只留下一篇读书札记。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68,569页。冉云华教授认为宗密是“无意中读了《圆觉经》”(《宗密》,第12页。),可见,学界对宗密接受《圆觉经》还没有作历史和思想上的具体阐释。
⑩镰田茂雄有详细比较宗密传的各种资料,并对《碑铭》进行了校对,引文见《宗密教学の思想史的研究——中国華厳思想史の研究第二》,第27页。
(11)《卍续藏经》第9册,323页下。
(12)关于宗密《圆觉》疏中之融合禅教,及这一融合观与当时中国社会与佛教状况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小林实玄,“宗密の圓覺の教學について”一文,见《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17卷,第2号,1969年3月。
(13)《大疏释义钞》卷四,《卍续藏经》第9册,538页上。
(14)“大方广圆觉经疏序”,《卍续藏经》第9册,323页上。
(15)《卍续藏经》第10册,12页下。
(16)《卍续藏经》第10册,704页中。
(17)克文与大慧对宗密疏的批评,主要是指出其疏改经中“一切众生,皆证圆觉”为“皆具圆觉”,即“易证为具”,详见冉云华,《宗密》,第237,238页。关于大慧对宗密《圆觉经》疏的批判,还可参考鄭榮植,“《大慧書》における大慧宗杲の宗密理解一《圓覺經》の解释を巡つて”一文,见《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51卷,第2号,2003年3月。
(18)关于此,参考曹潤鎬,“『圓覺經』解明の視點——經典成歷史的觀點から”。
(19)关于此,可以详看宗密的著述目录。这方面,镰田茂雄的《宗密教学の思想史的研究——中国華厳思想史の研究第二》第二章第四节有专门考辨,而在此基础上,冉云华教授的《宗密》更作了深密的考论(见该书第42—54页),可以参考。
(20)《大疏释义钞》卷一,《卍续藏经》第9册,478页上。
(21)吉津宜英著《華厳禅の思想史的研究》,大東出版社、昭和60年初版,第277,282页。这一点,格瑞高睿也发现,宗密几乎有把《圆觉》看作高于《华严》的倾向,他甚至认为,宗密的圆觉疏标志着华严教学史上解经学的一大重要转变。Peter N.Gregory,What Happened to the "Perfect Teaching"?Another Look at Hua—yen Buddhist Hermeneutics,Donald S.Lopez Ed.,Buddhist Hermeneutics,p.216,218.
(22)《大疏释义钞》卷一,《卍续藏经》第9册,481页上。
(23)《大疏释义钞》卷六,《卍续藏经》第9册,540页下。
(24)吉津宜英:《華厳禅の思想史的研究》,第276页。又格瑞高睿也发现,比较宗密与法藏不同的判教思想,可以反映晚唐华严学“变化中的历史情境”。Peter N.Gregory,Tsung—mi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p.134.
(25)其《随文要解》卷二载:“问:《圆觉》既称圆,别与《华严》有何优劣邪?”清远自己维持《华严》卓越的地位,他接着上面问题这样说“答:圆顿合论,顿圆无别。如上所举,理义昭然。今疏抄中比比皆尔,若或拣之,不妨有异。如云性起之义,分同《华严》;三观亦云分具圆义。又云此分摄圆教者,此经不明显说诸佛身相国土自在无碍,尘沙大用及诸法法尔互相即入,重重融摄等义,不得全名圆教所拣之义。如云何尝相滥邪?问根本法轮,唯《华严》也,故云开渐之本《圆觉》亦属别教。”见清远《随文要解》卷二,《卍续藏经》第10册,33页下。
(26)《佛祖统纪》卷二十九,《大正藏》第49册,293页下。
(27)《佛祖统纪》卷二十九,《大正藏》第49册,294页上。
(28)他在《修证仪》“总叙缘起”中说:“有唐中吾祖圭峰禅师追弥天之余烈,贯智者之遗韵,备述《圆觉》礼忏禅观,凡一十八卷,包并劝修,揆叙证相。故道场法事之门有七,而礼佛忏仪之门有八。其所伸引冲邃澣漫(多用佛名文及华严经等意),葢被三期限内修证耳。余以像法之末遇兹遗训,缅怀净业其亦有年,繇是略彼广本为此别行,法类相从。”《卍续藏经》第74册,512页下。
(29)善熹,“注同教问答”,《卍续藏经》第58册,574页上。
(30)均见善熹,“斥谬”,《卍续藏经》第58册,589,590页上。
(31)《圆觉经类解》卷一,《卍续藏经》第10册,168页上。
(32)道恕:《圆觉经随文要解》序,《卍续藏经》第10册,12页上。
(33)关于此问题,分别参考拙文“北宋天台宗对《大乘起信论》与《十不二门》的诠释与论争”,《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宋明楞严学与中国佛教的正统性——以华严、天台《楞严经》疏为中心”,《中国哲学史》2008年第3期。
(34)分别见《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中“草蓭纪通法师舍利事”一文,《大正藏》第46册,930页下;《释门正统》卷二,《卍续藏经》第75册,279页上;项示元,《浙江佛教志—天台宗》。
(35)关于鄣南,不见传记材料,他的圆觉疏不存,另外他还写作过天神传的作品,《重编诸天传》序中就说天台—系诸天传的写作是由他而发明的:“斯文草创于鄣南,功成于镜庵。”见《卍续藏经》第88册,421页上。(东阳法师)居式的《圆觉》注也部分保留在元粹的《圆觉经集注》内,天台史书将其列为山家一系的传承,应属四明智礼的三传弟子(智礼—浮石崇矩—景云温其—东阳居式)。《佛祖统记》卷十四(《大正藏》第49册,224页中)虽列有他的传,但本纪的内容已经遗失,只说他撰《圆觉》疏四卷;又,《翻译名义集》(宋代法云编)中有部分转引居式的《圆觉》疏内容,并批评他的解经有违于天台止观,如说:“居式《圆觉疏》云:空如来藏,即无住本;不空如来藏,即所立法。此二释违南岳止观。(《大正藏》第54册,1127页下)”(竹庵法师)可观(1092-1182):宋代台宗史书把他作为智礼下南屏一系的传人(南屏下四世:知礼—南屏梵臻—从谏—择卿—竹庵可观)。《佛祖统纪》卷十五,《释门正统》卷七有其传;其著作包括了对《圆觉》《楞严》的研究,有《楞严说题集解补注》、《圆觉手鉴》等。(慈室法师)妙云:南宋天台慧觉玉法师的弟子,他的传承应该是这样:知礼—南屏梵臻—从谏—慧觉齐玉—清修法久—慈室妙云,与竹庵可观同属于南屏系下的不同传承,《佛祖统纪》卷十六本传说他“淳熙初(1174)迁慈溪永明,以所得悟意,述《圆觉直解》。”《统纪》卷二十五“山家教典志”记录其《直解》为三卷,可惜这本著作已经不存,部分注文保留在元粹的《集注》和智聪的《圆觉经心镜》中。
(36)《释氏稽古略》)卷四“高宗”,《大正藏》第49册,890页下。
(37)引文均见《圆觉经心镜》卷三,卷一,《卍续藏经》第10册,404页下,384页中。
(38)此见山家知礼与山外智圆所争论的理毒性恶,消伏三用之义。此争论见智圆,“请观音经疏阐义钞”,《大正藏》第39册;知礼,“释请观音疏消伏三用”、“对《阐义钞》十九问”,《大正藏》第46册。
(39)钱谦益,《楞严经解蒙钞》卷首,《卍续藏经》第13册,504页上。
(40)《圆觉经集注》卷上,《卍续藏经》第10册,458页上。
(41)《圆觉经心镜》序,《卍续藏经》第10册,378页上。
(42)《圆觉经心镜》卷三,《卍续藏经》第10册,403页上。
(43)Donald S.Lopez,JR.,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hayana Sutra,Donald S.Lopez Ed.,Buddhist Hermeneutic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8,p.52.
(44)《卍续藏经》第10册,437页中。
(45)宗密,“圭峰定慧禅师遥禀清凉国师书”,文引自镰田茂雄《宗密教学の思想史的研究——中国華厳思想史の研究第二》,第46页。该书写作时间考,见冉云华,《宗密》一书所附“年表”,见该书第277页。
(46)《卍续藏经》第9册,591页中。
(47)引文均见《圆觉经心镜》卷一、二,《卍续藏经》第10册,382页上,396页下。
(48)Kogen Mizuno提出隋唐以来,判教“堕落”为对思想高下的价值性判断,而成为宗派性的论述。参考其著,Buddhist Sutras:Origin,Development,Transmission,Tokyo:Kosei Publishing,1982,p.138.
(49)关于刘宋以来及天台所判五时教相,可以详见中村元著,林光明编译《广说佛教语大辞典》上卷,台北:嘉丰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230页。
(50)《大疏钞》卷一,《卍续藏经》第9册,473页中。
(51)《大疏释义钞》卷二说“然天台四教,賢首五教,皆攝一切經。今經義具,故是廣也。”《卍续藏经》第9册,489页下。
(52)《卍续藏经》第9册,43页上。
(53)《大疏释义钞》卷二说:“言诸家禅定者,说一向安心息念门户,色四空四者,四禅四空也。六度中禅门,亦只约四禅等辨其行相。……天台广明甚深禅定,亦只约四禅八定而为修习之门。二显深也。真如三昧者,论云:若修止者,住于静处,端坐正意,不依气息形色,不依于空地水火风见闻觉知,乃至依如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谓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当知真如是三昧根本。若人修行,渐渐能生无量三昧。释曰:此一段上门,有始有终,简魔简伪,显能显益,义意门户一切周圆。故异诸教,诸教但说义也。”《卍续藏经》第9册,490页上,490页中。
(54)《卍续藏经》第10册,33页下。
(55)《卍续藏经》第10册,416页上。
(56)分别见《卍续藏经》第10册,378页下,379页上。
(57)吕澂,“与熊十力书(1943年4月12日)”,收入《中国哲学》第11辑,“辩佛学根本问题——吕澂、熊十力往复函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页。
(58)牧田谛亮,《疑經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昭和51年版,116,117页。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北美学界如鲍斯威尔(Robert E.Buswell)就疑伪经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就展示了重要的成果。参考Robert E.Buswell,Ed.,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
(59)参见“『圓覺經』解明の視點——經典成歷史的觀點から”一文。
(60)法藏与《起信论》的深入关联,可以参考吉津宜英“法蔵の『大乗起信論義記』の成立と展開”,该文收入平川彰編:《如来蔵と大乗起信論》,株式会社春秋社,1990年6月版,第377—410页。
(61)《宋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737页上。
(62)关于此详见冉云华,《宗密》第47,48页。
(63)关于从法藏、澄观到宗密对《起信》的应用,可以具体参考拙著《大乘起信论与佛学中国化》第七章,“《大乘起信论》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台湾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出版,2001年,第374—379页。
(64)《宋高僧传》卷六,《大正藏》第50册,741页下。
(65)“大方广圆觉经大钞序”,《卍续藏经》第9册,459页上。
(66)如宗密《大疏释义钞》卷六上中所述圆觉妙心流转还灭义,基本内容就出自《起信》,“明如来藏为总为源,染净为别为末,亦具如《楞伽》、《起信》。”又如,他疏解《圆觉》“法义”宗趣也完全照《起信》的一心、体相用三大和本始二觉来开展:“故论中欲显大乘深隐性相道理,先开此二论,云:摩诃衍者略有二种,一者法,二者义。法指一心义开三大,正同此也。心是如来藏心,即圆觉在缠之名义,谓体、相、用。”均见《卍续藏经》第9册,587、335页中。
(67)《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卍续藏经》第9册,616页中。
(68)分别见《随文要解》卷八,《卍续藏经》第10册,100页下。
(69)《圆觉经类解》卷一,《卍续藏经》第10册,168页上。
(70)湛然:《止观义例纂要》卷三,《大正藏》第56册,第47页上。
(71)关于宋代天台与《起信》的关系,可以参考拙文“北宋天台宗对《大乘起信论》与《十不二门》的诠释与论争”。另外,宋天台与《起信》关系,还可以参考木村清孝“北宋仏教における『大乗起信論』——長水子璿と四明知礼”;池田魯参“天台教学と『大乗起信論』——知礼の判釈と引用態度”,此二文分别收入平川彰編:《如来蔵と大乗起信論》第411—432页,第433—470页。
(72)Tsung—mi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p.56.镰田茂雄认为,宗密的《圆觉》疏引用《楞严》,但他并没有为《楞严》作解,很可能是他太倾向于《圆觉》疏而无暇为《楞严》作疏了。参考镰田茂雄《宗密教学の思想史的研究——中国華厳思想史の研究第二》,第110,111页。
(73)此见荒木见悟《陽明学の開展と仏教》“明代における楞厳経の流行”,东京:研文出版,1984年版,第247页。
(74)关于子璿与《楞严》疏问题,可以参考拙作“宋明楞严学与中国佛教的正统性——以华严、天台《楞严经》疏为中心”。此外,我在这篇文章中还考察了唐宋以来楞严疏的发展史,可资参考。
(75)净源:《教义分齐章重校序》,该文收录于《圆宗文类》卷二十二,《卍续藏经》第58册,561页下;又宋代华严学人令观也谈到当时学界由宗《圆觉》而转向宗《楞严》的情况,《补续高僧传》卷二本传中载“世徒传当年《圆觉》之圭峰,何知不有今日《楞严》之我耶?”,见《卍续藏经》第77册,379页下。
(76)详见拙作“宋明楞严学与中国佛教的正统性——以华严、天台《楞严经》疏为中心”。
(77)分别见《圆觉经心镜》卷四,《卍续藏经》第10册,408页下。
(78)《卍续藏经》第10册,392页中,399页下,410页上。
(79)Bernard Faure,the Will to Orthodoxy:A Critical Genealogy of Northern Chan Buddhi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9,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