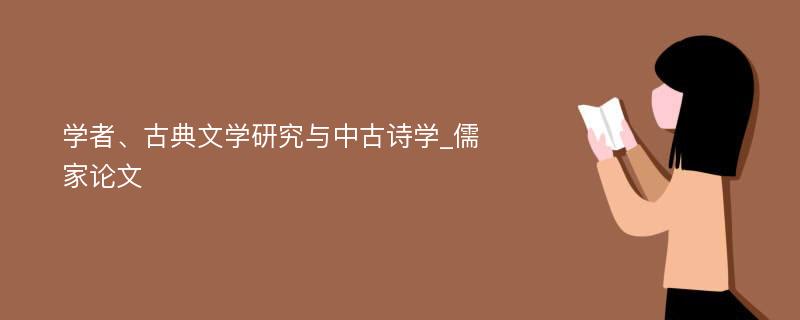
士族、古文经学与中古诗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经学论文,中古论文,古文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魏晋南朝时期,中国的诗歌理论有突破性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诗论名著。当代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儒学衰微和玄学兴盛所致。本文认为这是与士族地主的兴起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起主导作用相关联。士族地主不同于汉代宗族地主,他们是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强大的宗族,以世积文儒、位居清要,性尚通脱、重视自我及侈情奢华为特征。玄学的兴起和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都是缘于士族的习性及其对思想文化的新好尚。中古诗论家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的诗论体系都是以儒家诗学为主导,兼收了玄学及其他有益的思想成分,是儒体玄用而非玄体儒用。
关键词 士族 古文经学 玄学 中古诗论 儒体玄用
中古文学的自觉与诗学的兴盛、诗论的发展,是与门阀士族的兴起与影响分不开的。在政治、经济领域内居统治地位的士族,也使文化思想领域内发生相应的变化,古文经学的行时和玄学的风行,就是这种变化的表现。士族文士由生活习性而形成的审美趣味,更是直接投射到诗学。本文拟从士族和古文经学的统治地位,论述儒家诗学体系在中古诗论中的主导位置。玄学也是士族的派生物,在诗论中所起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文中附带论及,不作专题系统论述。
士族与中古的政治和思想文化
中国的门阀士族,萌生于东汉末期,形成发展于魏晋南朝,至隋唐而逐渐衰落,有明显的时代属性。在中古时代,他们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主宰者和支配者。
门阀士族作为中古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殊阶层,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以姓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和形成为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很强大的宗族。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十分特殊:一方面高踞于平民以至于一般庶族地主之上,在地主阶级中出现“士庶天隔”这种异常情况;另一方面对所属王朝似乎也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和高贵的地位,并不完全是依从关系。改朝换代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仍不变,一个士族官僚可以在几个朝代延续任高职,无忠贞死节的道德可言,这和汉代的宗族地主的情况大不相同。由于这种政治经济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
第二,世积文儒,位居清要。这是士族门阀最重要的外在特征。前者是指书香门第,文化传家;后者是言官居清要的文职,祖先位至三公、九卿者则门第更为显赫。以武功居高位者则不在其列。构成士族称谓的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士族,又称世族,世胄等。以“士”冠族、是以文人学士自诩并以此为贵;世族、世胄,则是文官清职,代代相继,这就是所谓“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就王、谢两大士族言、据《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琅邪王氏有文集者二十人,陈郡谢氏有文集者十二人,这是隋唐间集录的数字,在当时行世的远不止此数。《南史·王筠传》载其“与诸儿书论家门集云”:“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沈少傅约常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沈约属吴兴沈氏士族一系,又是齐、梁时政要和文坛上领袖,他赞扬琅邪王氏文才之盛是一种舆论导向。王筠引其言以自重,并劝勉子弟继续努力,也是风气使然。中古时期的士族文士是独领风骚的,既是文化思想的占有者,也是文化思想的创造者和主导者。寒庶文士,虽才富文艳,学积五车,也只能作为华胄的附庸。
所谓“世积文儒”“人人有集”,所写是包括诗赋及经学、玄学、史学、子书等各类著作。玄学的兴起与风行是这一时期最特出的现象,正始玄学的创始人王弼、何晏等都有专著、专论面世,如王的《周易注》、《老子注》,何的《论语集解》、《道德论》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士族文士远非一边倒于玄学,注解儒家的经典,也是一大热门,象东海王朗、王肃父子,都是以经学名家,王朗“皓首穷经”,王肃的古文经学,在魏晋南朝时称显学。玄学的兴盛对诗歌创作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并不都是积极的,统治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就是失败的记录。玄学对促进诗歌理论批评的发展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玄学形成了一代的论辩风气,从而开拓了诗论家的思路,增进了理论兴趣,提高了思辨的能力。但玄学家们并未建立起相应的诗论体系,自成一家之说,而玄学的有些论题,如言不尽意论,反被儒家诗论所吸收,从而促进了儒家诗论的发展,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主宰中古诗学论坛的,仍是儒家的诗论体系。
第三,性尚通脱,重视自我。这是某些士族文士习性上的特征。通脱有率真旷达的含意,既表现在行为上,也表现在思想上。就行为言,他们任性而为,兴尽则止,嗜酒吃药,放荡不羁,不拘于常礼。《世说新语》中《任诞》、《简傲》诸篇记载的事例很多,阮籍居丧无礼,刘伶病酒诳妻都是其例。正始名士蔑视礼教放浪形骸的某些极端的表现,固然包含有对司马氏政权用礼教诛除异己行为的一种抗争,但同时也可视为士人人格意识的觉醒。性尚通脱是魏晋文士较为普遍的风尚,为尔后许多文士所乐道,所效尤。所以这不是一时的策略行为,而是一种习性的表现。士族文士重视个人的价值,不愿过多地接受常规礼教的约束,这与士族地主的庄园经济实力强大和政治上相对独立于中央王朝有关。所谓魏晋时代人性的自觉,实质上是士族文士人格意识的觉醒和独立意识的增强,这与汉代儒家章句之学规范下的文士习性是大不相同的。《世说新语·品藻》篇云:“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桓温与殷浩同为东晋大士族,后都出将入相,风云一时,年少时同有令名,但各不相服。殷的才干实不如桓,但殷重视和突出“自我”这番话,时人引以为美谈。由此可见其时士人人格意识的增强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重视表现自我,这是文学自觉的重要内涵。
通脱表现在思想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经学思想的变化和玄学的风行,就是士族文士思想通脱的结果,学术文化以及诗学上呈现异采也得益于这思想通脱。当然,士族地主思想上的通脱,也只是一定程度摆脱汉代士人对章句经学和常规礼仪的拘泥,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孔教,孔教的核心点是纲常名教和礼乐刑政,这是建筑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士族门阀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也必须依赖名教来维系统治。他们的异端思想不过是将道、释等思想引入孔教之中,或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阐释孔教,新的经学是如此,玄学的本质亦复如此。
第四,侈情与奢华。这也是士族文士习性上的特征,并进而形成特有的审美情趣。侈情是在情感上的率性任真,是通脱在情感领域内的表现。圣人是有情还是无情,曾是玄学的论题,谈家的口实。何晏主圣人无情,王弼主圣人有情。王弼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何邵《王弼传》),所谓“应物而无累于物”,汤用彤解释说:“无累于物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亦可谓应物而不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哀乐不淫不伤,适得中和。这就是说,圣人有情,但不侈情。这是玄学家的理想人格所要求的。但其时很多士族文士,不但主有情,而且倡侈情,把自己和圣人区别开来。《世说新语·伤逝》篇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正反映一些士族文士率情任真较为普遍的心态。这与后汉士人矫情和伪饰大不相同,发而为诗,就有“长于情理”与“以气质为体”的区别。重视率情、钟情和侈情,是中古诗学变革的内在动因。
奢华主要表现在士族地主的奢侈豪华的生活上,养成了一种习性,进而形成了特定的审美心态和审美定势,并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上层,绝大多数都是奢华的。但相对而言,汉代的士大夫还是比较朴实,特别是在他们中间提倡俭朴廉洁。汉代的察举制度之一是举孝廉,即孝亲和廉朴才能被荐举为官,俭朴廉洁也就成为社会时尚。魏晋以来情况不大相同,高门士族竞相斗富比奢,炫耀市朝。石崇与王恺争富,晋武帝乃王恺之甥,暗中助恺,在当时也成为美谈。下及南朝,其风不衰,大诗人同时也是大士族官僚谢灵运,也是“性奢侈,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宋书·谢灵运传》)“世共宗之”,其影响就不仅在士族上层了。士族地主这种被服华艳的生活习性,同时也形成了重视华丽之美和秀丽之美的审美心态,由物及人,由人及文,似乎是这种审美趣味发展、演进和相依、相存的环链。士族文士品鉴人物,除重视人格美外,同时也非常重视形态美。这是这个时代重视形式美的另一种表现。对男人评头论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是极少见的,但在魏晋南朝时却是一种风尚。《世说新语·容止》篇对此有大量的记载,如称美男子卫玠为“璧人”,赞裴楷为“玉人”。晋简文帝司马昱“轩轩如朝霞举”,王恭“濯濯如春月柳”。“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还有掷果潘安,看杀卫玠,都传为美谈。士人对容颜美的鉴赏,甚至置礼仪于不顾。如王濛仪容修好,“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濛父王讷字)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世说新语·容止》注引《语林》)礼重讳言父祖之名,王濛自我欣赏,真呼其父名字,时人不以为非礼,还以为“达”,爱美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更有甚者,身犯重典,只因风姿秀美就可免受诛戮。东晋苏峻之乱,朝廷几被倾覆,事平陶侃说:“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但大士族官僚庾亮兄弟“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世说新语·容止》)竟因此免罪。陶侃系东晋一代名臣,谢安曾称赞说:“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晋书·陶侃传》)这个“法外意”,大概是包括审美趣味的投入吧!中古时代骈文、诗歌和辞赋非常重视词采的声色之美,正是士族文士爱好形式美在文学领域内的表现。
缘情与饰采是中古诗学的两大特征,两大成就,都与士族文士重情与豪华的习性所形成的审美心态和审美趣味相关联,而不是玄学或经学的直接派生物。
古文经学与中古诗论
经学、玄学、钟情与饰采,是构成中古诗学思想和艺术特征的四要素,都缘于门阀士族的思想和艺术的好尚,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经学。在玄学风行的年代里,儒家经学确有所削弱,但这是相对于两汉“独尊儒术”,经学处于一统天下的情况而说的。经学作为统治阶级的主要统治思想,其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在文化思想领域内也是如此。玄学的挑战,成为经学思想变化的一种推动力量,加速了古文经学代替今文经学的过程;玄学的论争与发展,如名教与自然之争,崇有与贵无之辩,经学往往是制衡的因素。中古文化思想发展史表明:是经学融合并代替了玄学,而非相反。
经学和经学思想是有区别的。所谓经学,主要是指《诗》、《书》、《易》、《礼》、《春秋》及《论语》等儒家经典所宣扬的纲常名教之学。这是支撑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贯穿并渗透在封建制度的机体之中并与之相终始,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但阐释儒家经典的经学思想,却发生了数次大的更换。从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到东汉的谶纬之学,是统治汉代的经学思想,属今文经学,到魏晋时则为古文经学所取代。经学今古文之分本是所依据的文本不同、书体有异而别名,前者是隶体书写的秦汉时流行本,后者是西汉时出土用大篆体书写实为先秦时古本。但经学今古文最重要的区分还是解说的思想和方法有别,古文经学是以通训诂、举大义为研究经书的主要方法,反对今文经学谶纬迷信和繁琐解说。古文经学之所以能取代今文经学,是由于其时上层统治失序,统治基础削弱,促使士族文人对前此的经学思想进行反思的结果,同时也说明迷信虚妄已经维持不了原有的皇权统治,而破碎章句也不足以禁锢士人思想。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新的经学思想来维系统治,古文经学应运一跃而占住主导地位,并在学术争鸣中又分化为两大学派:即活跃在南方荆州的宋衷、王肃学派和在中原地区居统治地位的马融、郑玄学派。郑玄能融合经学古今文的研究成果而集其成,王肃学派宗马(融)反郑(玄),时出新意。他们都发展了两汉的古文经学,是一种新的经学思想。王肃学派凭借其政治势力(王是司马昭的岳父)在魏末及西晋时代占统治地位,而郑玄新经学在东晋南北朝时代则更为风行,后经孔颖达的解说在唐代处于独尊的地位。郑、王新经学共同点之一是都能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和一师之说。一部经学可以有多种义疏和讲疏,学术思想较为自由,这是士族文士所追求的学术风气;另一共同点是宗奉儒家经典所阐释的礼乐刑政和纲常名教,为当政皇朝制礼作乐典章法度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规范。这是维系士族地主统治的生命线,是一刻不能偏离的。把一种经学思想的衰落说成是经学的衰落,把今文经学的衰弱当成儒学的衰弱,这是较为流行的观点。但这是很不准确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经学与玄学在中国诗论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每位诗论家的论著中表现情况都不一样,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全部囊括的。作为决定事物性质的主导思想倾向看,几乎都是尊奉、沿用和发扬儒家诗学的风、雅体制,很少见到例外。而风、雅体制,是《毛诗序》中所确立的儒家诗学本体论中一重要问题。今之论者,在评述这一时期的重要诗论著作时,常常使用“体”与“用”、“内”与“外”等范畴来概括撮要玄学的主导地位,本文也想加以借用,不过持论恰与之相反。
“体”与“用”原是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运用于政治和诗论中,含意是不一样的,不能混同。哲学的本体论是探讨宇宙的本源,玄学的“无”,古文经学家王充所言的“气”即属此。政治学领域内的“体”,应是政治体制,晚清保皇党人所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此意。《毛诗序》所建立起来的风雅体制,就是后代许多诗论家所遵循的“体”,它与功用论密切不可分,且往往体现在功用论上。唐孔颖达本《毛诗序》说区分诗的“六义”(风、雅、颂和赋、比、兴)为“三体”、“三用”(《毛诗正义》),宋朱熹界划“六义”为“三经”、“三纬”(《诗集传》),元杨载别“六义”为“三体”、“三法”,并言:“此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诗法家数》)都是对儒家诗学体用观的阐发。以此来检验中古的文论和诗论。并未发现有大的背离。曹丕所言“夫文本同而末异”、“本”即“体”、“末”即“用”,他重视“末”,也强调“本”。同理,陆机的创作理论是“用”,崇风雅,言文用则是“体”,虽然他重在言“用”兼及于“体”,但“用”受“体”制约并服务于“体”。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诸篇,在阐明“体”,而文体论、创作论等数十篇则在明“用”。钟嵘评诗,探源《风》、《骚》,在尊“体”,具体品评则是“用”。中古诗论家在“用”上有重大的丰富、发展、变化和创新,于“体”当然也有相应的丰富和发展,如把风雅体制升华而成美学风格和审美境界,但其基本核心点并未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古诗论的基本性质。玄学的“言不尽意”、舍形求神、清通简要的文风等,如同缘情、饰采一样,都属于“用”或应用于“用”,儒体玄用(部分也非全体)的诗论著作,是不能说以玄学为主导的。和汉人诗论相较,其异同处也可称之为“本同而末异”的。我们不能把“本”、“体”(风雅体制和精神)视为“外”,把“末”、“用”(艺术特色、技巧等)当成“内”,冠之为“内玄外儒”,而恰应视为“内儒外玄”,更何况“末”“用”只有部分直接来之于玄学呢?
本着诗学的这种体用观,以下侧重例举摄要评述古文经学对中古诗论在本体论上的巨大影响和决定性的作用,玄学的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是以明“体”为前提。
开中古文学自觉新时代的曹丕的文学体用观,集中体现在“夫文本同而末异”这句话上。“本”是什么?《典论·论文》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前者用以治国,后者借以成名,后者是有赖于前者,这是功用论也就是本体论上的共同点。其他才性异区、文体区分、风格有别等等都属于“末异”。曹丕在“本”、“末”论述上都作出了贡献,他非常重视“末”,充分论述“末异”,但丝毫未忽视“本”,“末”是服务于“本”,受到“本”的制约,从“本”“末”区分可见。就“本同”说,文章不朽也就是立言不朽,曹丕的《与王朗书》有更完整的表述:“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立德扬名”即立德立功,“著篇籍”就是立言,这三者都可不朽。“三不朽”原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属古文经学的,在两汉受到今文经学家的排斥,不得立博士,古文经学行时后才受到尊奉。上引这段话见于鲁叔孙豹与晋范宣子的答问。范氏世代执晋国柄,而晋又是中原霸主,范宣子认为范氏这种世代显赫的权位,是可称谓“死而不朽”的。叔孙豹回答说:“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臧文仲立言,见诸《左传》的主要是政治外交辞令。其学识渊博,见解深刻。一百多年后叔孙豹称赞他身虽死而言立,所以不朽。从《左传》这段记述看,叔孙豹虽然提出前代的“三不朽”格言,但着重强调立言不朽。《典论·论文》所言文章不朽,也是侧重于立言的。曹丕把“立言”延伸为“文章”“篇籍”,并把诗、赋等文学体裁也囊括在内,这是他的新见,对提高文学的地位和促进文学的发展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不过我们也应正视,曹丕所说的“文章”是包括四科八体的。诗、赋两体列在最后。他是更为重视经学和政论文章的。《论文》中例举立言不朽的事例是西伯演《易》和周旦制《礼》。建安七子中能得到立言不朽美誉的是徐干,因为徐“著《中论》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与吴质书》)曹丕对自己的著作最为重视的是《典论》而不是诗、赋,是书五卷二十篇,《论文》只是其中一篇,而多数篇章是总结前代政治得失的。此书被刻石立于太学门前并亲自给太学生讲授,足见曹丕是想以《典论》传世不朽的。缘起于《左传》的立言不朽是曹氏兄弟、陆机兄弟及刘勰等发愤著书的精神动力。立言之所以不朽,就是因为文章有益于治国,而“文章经国之大业”云云,是缘于古文经学《毛诗序》的,《诗序》认为诗是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用之帮国”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这不就是治国之大业吗?当然,曹丕的文章治国论内涵要丰富得多,但无实质的变化。汤用彤说:“盖于文有两种不同之观点:一言‘文以载道’,一言文以寄兴,而此两种观点均认为‘文’为生活所必需。前者为实用的,两汉多持此论,即曹丕《典论·论文》亦未脱离此种观点之影响,故他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而后韩愈更唱此论也。”(《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曹丕所论“末异”,其中“文气”说可能与名家的才性说有一定联系,而与他们去世十余年后才产生的正始玄学是无涉的。
陆机是江东大士族,父祖显宦,经学传家。其《文赋》所论,集中地反映了魏晋士族文士的审美好尚。从体用关系看,是以儒家诗学为主导,也少量吸收玄学的思想资料,尽管他在学术观点上是反对玄学的。
《文赋》的中心论题是研究创作的用心。“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是全文力图解决的理论命题,并非申言“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观物是意称物之始,“伫中区以玄览”,就是对所写事物要深观明察。《文选》李善注引《老子》“涤除玄览”释其意,不一定符合原意。陆机曾作《羽扇赋》,赋中也用过“玄览”一词:“昔武王玄览,造扇于前……”《羽扇赋》以主客问答式虚拟宋玉和诸侯的对话,宋玉使用了与众不同的羽扇,遭到众诸侯的嘲笑和责难。上引即诸侯之言,认为不符合周武王造扇的古制。这显然是言武王圣哲,能深观明察,后人的智慧是不能超越的,其“玄览”意与《文赋》所用同。唐武则天召文士编类书百卷,也以“玄览”名书,这与《羽扇赋》所言“武王玄览”意同,都是深观明察意,与畅玄体无没有关系。“玄览”有多释,依李善释将陆机的创作命题引入玄学之中,不一定是得当的。
《文赋》在论述“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时,引用了《庄子》轮扁语斤的寓言:“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但这仅限于“随手之变”部分,不是创作论的主体,更不是指整体。就主体说,他详尽地研究和阐明了以文逮意的理论,是言能尽意论者;就有限部分说,他吸收和运用了《庄子》的“言不尽意”的资料,说明创作中诸如“丰约之裁,俯仰之形”等在理论上是无法说清也不能悉说的问题,创作者要善于“因宜适变”,才能曲尽其妙。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据此而认定陆机是“言不尽意”论者。
陆机主要生活在西晋元康之世,他在政治和学术活动中,是站在崇有派裴頠一边,反对正始玄学的虚诞之弊。《三国志·裴潜传》注引陆机《惠帝起居注》:“頠雅有远量,当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頠理具渊博,著《崇有》《贵无》二论,以矫虚诞之弊。文词精当,为世名论。”裴的《崇有论》说:“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晋书·裴頠传》引)“制事必由于心”,不可“谓心为无”,与陆机的“意称物”和称灵感为“兹物”的观点完全一致,也可以说陆论是以裴论为哲学依据。又,陆机的《七征》及《演连珠》五十首中多首都直接对玄学加以责难和批评。
陆机是以“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晋书》本传)著称,但在创作论中又吸收了庄玄的思想成果,这既可见其理论思维比较开阔,不拘泥于一家之说;也说明当时儒、玄论争中,既有互相对立、排斥的见解,又有互相吸收和融合的一面。面对这较为复杂的现象,要全面考察,分辨主次,把握主体,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尊奉儒家诗学的风雅体制,发扬风雅精神,在《文赋》中有很鲜明的体现。这既集中表现在文用论上,也贯穿在文体论中,同时也制约着创作论。“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处理好文与质的关系,是创作论中的大问题。创作论中的物一意一文的关系,“意”是中心的一环,而“意”是以情理为内核的。陆机认为“理”是文章的主干,“文”则是干上生长的枝叶花朵,是依附于树干的。理与文的关系,是文论中“体”与“用”的关系的一种体现,一切创作构思和表现技巧都是为了表现理的。情也必须受理的制约,悲而不雅是必须克服的文病。所以《文赋》的中心论题是创作构思,而归结点则是文用。从“体”、“用”关系说,“用”要服从于“体”,服务于强调政治功用的儒家诗学的风雅体制:“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途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沾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作为文章的内质同时也借助文章表达的“众理”,就是儒家创始人所宣扬的周公文武之道和古文经学家所强调的诗的教化讽谕。《论语·子张》:“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子贡认为孔子所学习所力行的文武之道,是人心所向,无所不在。陆机则进而要求通过文章使文武之道永不中断,诗的教化讽喻永不泯灭,这不就是经国之大业吗?在陆机看来,文章要服从并服务于政体的,是经国大业中不可代替的组成部分。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囊括万物,间入毛发,变化莫测,润物无声,“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文章的作用有其特殊性和不可代替性,它不同于经学、哲学和政治学,文学的自觉意义就在此。一切包括言不尽意的创作构思,缘情和词采的声色之美,文体的多样性和风格的特殊性及美学要求等等,都从这里生发出来。陆机在创作构思论上有重大的创新和贡献,在文用论上也有重大的发展。由于他很自觉地尊奉儒家诗学的风雅体制,这就决定了他的诗论的性质。
以“体”制“用”,也贯穿在文体论中。《文赋》在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及赋、颂等十体文章各有不同的特色后归纳说:“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这是对十体文章的共同规范。“理举”即前文所言“文、武之道”和诗教的内容,“禁邪制放”就是要严禁、制止“放辟邪侈”。此言出于《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这段话另见于《孟子·滕文公上》,都是说治民之道,不能使民走上不守封建礼义以至于犯罪的道路。“放辟邪侈”,王力解释说:“放,放荡。辟,同僻,指行为不正。邪,和辟同义,侈,和放同义。这里‘放辟邪侈’是泛指一切不守封建社会‘规矩’的行为。”(《古代汉语》上册第一分册)陆机以“邪”兼“辟”,取“放”合“侈”。“禁邪制放”即禁、制“放辟邪侈”,陆机要求包括诗、赋在内的十体文章“亦禁邪而制放”,也就是要止乎礼义,设了礼义的大防。“诗缘情而绮靡”与“亦禁邪而制放”是互相衔接的完整的命题,比起《毛诗序》所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命题,有了重要的丰富和发展,但无本质意义上的区别。“诗缘情而绮靡”,反映了新时代多数士族文士对诗歌的共同的审美要求,突出了诗歌最重要的美学特征,并且第一次铸成新语。“亦禁邪而制放”是化用孟子的旧语,以此来规范和制约前者。孟子的话比《毛诗序》是更有权威性的。不能充分评估他铸成的新语的价值,是属无识;无视他承袭儒家的旧话,信奉儒家诗学的风雅体制,也不能正确估量陆机。那种认为陆机是“发乎情,不必止乎礼义”的倡导者的见解,无论是前人因此加罪抑或是今人因此加冕,都非知言。
成书于齐梁间的《文心雕龙》和《诗品》,虽在不同程度上受玄学观念及其思辨方式的影响,但以风、雅体制作为其立论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而刘书尤盛。我们甚至可以说,刘勰是集中古以前儒学论文的大成,是中国古代儒学论文的一个杰出的代表。刘氏以儒学为论文立论的基点,在其书《序志》篇有详尽的说明:“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段自白至少包含三点内容:第一、他是服膺儒术的,对孔子和经书五体投地,认为对儒学阐述最精的是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家,他的使命就是用古文经学家的观点来评述文章,立言传世。第二,文章是经典的支条,本源于儒学,其作用巨大,“五礼”“六典”是治国之本,要靠它阐明才能施行;君臣政绩赖以炳焕,军国大事赖以昭明,是不可或缺的。这就直接从体用关系上说明宗经的必要性。明文用,首在宗经。第三,认为现在一些文章,背离了本源,越出了正轨,在本体论上出了大问题——“离本弥甚”,导致文风浮诡、讹滥。他要本着孔子的攻乎异端的教诲来批判当前的文风,依从《尚书》所言作文的原则申言写作要义,从而“正末归本”,是倡明文章。刘勰宗儒的文艺观,在他的申言中是如此清晰而无一点含糊不清之处。验之于所著,亦复如此。列为全书“文之枢纽”诸篇,集中阐明文学与儒学的依存关系和以经驭文的论文原则,并由此而概括和提炼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对各体文章都普遍适用的六项审美要求。《原道》篇把文学的起源和生成囊括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两句话内,构成“道—圣—文”和“圣—文—道”互相依存的两个公式。“道”既是出发点,又是归结点;“圣”(周公孔子)是中介,能体道而为文(经书),又能因文(经书)以明道,这个“道”当然是儒家之道;为圣人所作能体道明道的“文”(经书),是至高无上的,既是后世各体文章的源头,又是后世为文的典范。从而构成了文原于道,为文要“征圣”、“宗经”的儒家文论的理论模式,这就是《原道》、《征圣》、《宗经》三篇的主要内容。《正纬》篇是疾谶纬之虚妄,是集中批判今文经学的,表明他对古文经学的信奉;《辨骚》篇是辨析《楚辞》与经书的异同,是倚《雅》、《颂》以驭楚篇的。以上诸篇,是全书的“纲”,也在阐明其“体”。刘勰抓住这个“纲”,突出这个“体”,居高临下,对历代作家各种文体的创作分体分题进行总结和评价。从中提炼和升华出一系列的理论命题、理论范畴和审美原则。譬如列在文体论之首的《明诗》篇,开宗明义即引用《尚书·尧典》、《毛诗序》、《论语》等经书有关论述来界定诗义。其中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之说,以“持”释诗,是出自《诗纬·含神雾》(见孔颖达《郑玄诗谱序正义》引),但刘氏作了“持人情性”的新解说,诗是用以修养人们的情性,规范人们的行为的,这是对《毛诗序》所言诗的教化作用的一种具体阐释,是很有意义的。此例既可见刘勰论诗是本着儒家诗学的,还可见刘勰和郑玄一样立足于古文经学,兼收今文经学的一些有益的见解。至于文体论各篇所褒贬的历代作家各种文体之作,也都是立足于宗经,以“体有六义”那六项审美要求相权衡的。譬如《乐府》篇中批评“魏之三祖”某些乐府诗是“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刘勰对曹氏父子的诗作是包含贬意的。所以《风骨》篇所列范作是潘勖的《策魏公九锡文》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而不是建安代表作家三曹七子之作。在刘勰看来,潘文“思摹经典”、“典雅逸群”;相如赋志在讽谏,命意高雅。两文都能“熔铸经典之范”,“确乎正式”,所以“风清骨峻”。今人析风骨,往往回避上述两文,而与建安之作直接联系起来,这是不符合刘勰原意的,是无视于刘氏宗经的文艺思想的结果。且“风骨”的提出,原是包含情意和辞义两方面的审美要求,这也是立足于诗教和书教,并用以针砭时弊的。《风骨》篇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风即情意,重化感;骨即文辞,尚体要。风骨的本意即原于儒学。在界定和阐述风骨的内涵和形成过程时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峻爽,则文风清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这就进而赋予其审美内涵了。“风骨”作为刘勰论文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实际上也是《宗经》篇所言“体有六义”那六项审美要求的提炼和延伸,是儒家诗学一项重要成果。上引可见,刘勰论文的指导思想是宗儒的,他的成功与不足都与此有密切联系。范文澜先生说:“刘勰撰《文心雕龙》,立论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王元化先生说:“刘勰撰《文心雕龙》,基本上是站在儒学古文派的立场上。”(《文心雕龙创作论》)范、王二位在他们的专著里对此结论都有很精辟的论述。前此的论者,也都持此说。今之论者,有少从玄学和佛学思想主导立论而生新说,并颇受青睐。刘勰生于玄、佛盛行之际,他确实吸取了玄、佛某些思想资料和词语,如《神思》篇所言“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就有言不尽意的内容,其他如《比兴》篇对兴体的界定,《隐秀》篇对隐体的分析,也包含有对言不尽意的生发,但都纳入了他的儒学诗论体系之中,是充实“用”而非明“体”。对玄、佛的理论体系则是采取拒绝的态度。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对此有精到的阐释。现有的新说在点与“末”上深入了,但似有以点代面以“末”代“本”以偏概全之嫌,是不足以取代原有结论的。
钟嵘的诗论,虽未标宗经,但受儒学的影响也很明显,宗奉风雅体制贯穿前后。《诗品序》所言诗缘于心物感应并受“气”的主宰,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即来自荀子的《乐论》和汉人所作的《乐记》及《毛诗序》。荀子和东汉古文经学家王充以“气”为物质基因的宇宙构成论,成为钟氏诗歌起源论的理论依据。溯流别是《诗品》理论结构的特点之一,借以“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全书把汉魏至齐梁众多的五言诗人,分属于《国风》、《小雅》和《楚辞》三个源头(《风》《雅》同属《诗经》,实为《风》《骚》两系)。清代的章学诚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称之为能“深从六艺,溯流别”,是“思深而意远”的表现。“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文史通义·诗话》)章氏所言“古人之大体”,就是宗经的体制。论文论诗“深从六艺”,“探源经籍”,是汉魏至南朝宗儒的文论家普遍使用的方法,挚虞的《文章流别志》和刘勰的《文心雕龙》评述各种文体,都归源于经书,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文心雕龙·宗经》)钟嵘评诗,溯源《风》《骚》,也是宗经思想的表现。刘勰以儒学的审美要求评价历代各体文章的高下优劣,钟嵘亦复如此。《诗品》奉《国风》一系为正宗,对《楚辞》一系的名家颇多贬抑,评价偏低。《国风》一系最杰出的诗人是“建安之杰”曹植,他在诗国的地位是“譬人伦之有周、孔”。钟氏赞美其诗是“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文质彬彬”本是孔门的君子风范,被钟氏移植为对诗体的美学规范和审美要求。“情兼雅怨”即“怨而不怒”,含蓄深致,这是风人之旨,也是诗教的要义,钟氏评诗最高的审美范畴——建安风力,即以此为内核。风力与丹采相结合的评诗标准,是《毛诗序》所言“主文而谲谏”的丰富、发展和升华。其中赏爱“词采华茂”,体现了其时许多士族文士共同的审美好尚。钟氏评诗,崇尚渊雅,以雅正与否界别《风》《骚》。他有感于齐梁诗坛上《国风》一系后继无人,被时人所嗟讽的名家鲍照、谢脁、沈约等都是“颇伤清雅之调”的《楚辞》一系的诗人,钟嵘将他们一律放在中品,以表明其对风雅精神的重视和想扭转齐梁诗风的写作意图。
《诗品》从溯流别,评风格到定品第,无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所尊奉的风雅体制的制约。钟嵘甚至将他那个时代文士所特别赏好的润饰丹采,归之于《国风》的传统,把明显受到玄学影响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阮籍诗,则系之于《小雅》,称之为“洋洋乎会于风雅”,钟嵘诗论体系的归属,还能作其他判别吗?
综上所述,中古诗论,从曹、陆到刘、钟,以得风人之致为旨归,是一脉相承的。风雅精神不但集中体现在功用论上,而且被升华为崇高的风格美。曹植在《前录自序》中说:“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皓皓,与雅颂争流可也。”曹植是钟嵘称之为孔氏之门用诗已入室的最杰出的诗人,在诗国中的地位如同人伦中的周公、孔子,他的贡献就在于把风雅精神熔铸而成诗歌风格和意境美上有辉煌的成绩和突破,并在诗赋论中加以总结,从而与汉人纯功用诗论划界,与经学分途。尔后陆机及刘、钟等正是继承这个传统加以发扬光大,那种认为儒家诗论只与政治功用论结亲而美学绝缘是不确切的。但儒家诗歌美学是受“体”制约的“用”,不能背离“体”,也不能游离于“体”之外而自行其是。拿曾被称为“三用”的“六义”中的兴、比、赋“三义”说,刘、钟的“比兴之义”,都吸收了玄学的言不尽意论,加进“文已尽而意有余”和“情在词外”等内涵,从而构成了实际上已包含有“味外味”诗的特有美感,即诗的滋味。但他们仍沿着“主文而谲谏”“温柔敦厚”的路子,要求“讽兼比、兴”,使诗“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取小象以明大义,从而能得“讽谕之致”。这个“用”是与“体”合一的。以“体”为主,体用结合,以《毛诗序》为代表的汉人诗论是如此,以曹、陆、刘、钟为代表的中古诗论亦复如此。虽然在“体”与“用”特别在“用”的内涵上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如抒情成分浓厚了,审美意识增强了,艺术表现形式也多样化了,其中包括吸收了玄学等思想养分,但以风雅体制为核心这一本质特点并未异化,所以仍属儒家诗论体系的范围。从总体上看,中古诗论的主体都可作如是观。
“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杜甫在《偶题》中自言其从小就殚精锐思于儒家诗法。当然,这也是从诗的体制立论所作出的概括。所以在这首诗中,他把“汉道”、“骚人”及“邺中奇”、“江左逸”都囊括在他所致力学习的儒家诗歌美学传统之内。今之论者,常把诗歌美学排斥在儒家诗学之外,把儒学衰微作为中古诗学兴盛和诗论大发展的前提,这符合中古诗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吗?
标签:儒家论文; 世说新语·容止论文; 典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古文论文; 玄学论文; 毛诗序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