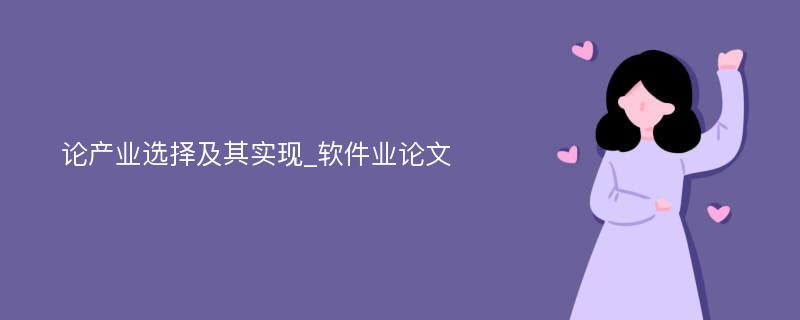
论产业选择及其实现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途径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与此相适应,各种对策研究纷纷见诸报刊。但是,有些研究或者忽视了市场的基础作用,或者过于强调产业结构的自然演进而忽视了政府的能动性,特别是,它们往往回避了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机制。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政府能否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自己的目标产业选择?如果能,其实现的途径是什么?
一、产业选择的基础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进化是渐近的……它的前进运动绝不是突然的……它是以部分自觉与不自觉的习惯为基础的。”这一认识同样适用于产业结构的形成与演进。产业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企业的形成又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合约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要素所有者依据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模式选择合约的对象从而形成企业。因此,不是别的因素,而是由消费者偏好决定的产品价格和由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决定的产品成本共同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形成与演进。这一判断隐含的结论是:市场(通过价格的决定)是影响产业结构的主要因素,且市场化水平越高(即价格的扭曲程度较弱),产业结构的综合素质就越高。
一些数据证实了这一判断。卢中原的分析表明:(1 )大部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综合素质较低;(2)近年来,陕西、新疆、 宁夏等省的产业结构综合素质有所提高(卢中原,2002)。这与市场化指数的变迁是一致的。1999年,西部地区市场化平均指数为3.90,低于全国平均数5.26;而1997~1999年,陕西、新疆、宁夏等省的市场化指数有显著提高(樊纲等,2001)。
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都支持市场对决定产业结构所起的基础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产业政策是无效的。不过,因为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尚未确立,特别是占国土2/3和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还很低,各种价格,其中主要是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较高,所以,我国自然演进的产业结构便不可避免地有较高程度的扭曲,呈现“低效,重复”的特征。故此,我们认为:市场是产业选择的基础,最基本的产业政策就是加快市场化趋向的体制改革。
承认市场对产业选择的基础作用,并不排斥政府的产业政策干预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即使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各种产品或要素相对价格仍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扭曲,从而导致低效产业结构的产生。这些因素便是广为人知的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等市场缺陷的存在。所以,小宫隆太郎明白地将产业政策的核心理解为“在价格机制下,针对资源分配方面出现的市场性而进行的政策干预。”可见,必要的产业政策干预是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需求。
政策干预的目标是:政府试图纠正扭曲的,由市场自发形成的产业结构,使之达到“合意的”产业结构。这涉及到两个问题:(1 )合意产业结构的确立;(2)实现的途径。关于前者, 我们的答案是:由于政府目标的多元性,而在其选择行为中体现出不同于个体选择行为的结果,由此形成了合意产业结构与自然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政府目标多元性可能来自于动态比较利益等基于效率的判断,也可能来自于国家利益等非效率的价值判断。至于后者,我们将以克鲁格曼的精彩分析为起点寻找这一途径,自然,我们的途径要求是以市场为基础的。
二、产业选择的实现途径:以规模经济为例
以下分析是以规模经济的存在为假设条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以其他因素(如结构转换、技术开发等)作为分析的基础。之所以选择规模经济,仅仅是因为作者的偏好。
1.初始状态。首先我们假定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资本丰裕型的“外国”,一个是劳动丰裕型的“本国”。一种产业,是具有规模经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某种原因,外国首先进入该产业,从而扩大了生产规模,降低了平均成本,即存在“先动优势”。这意味着,虽然外国由于资源禀赋的劣势,从而在每一产量水平上,其平均成本都高于本国的平均成本,但是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外国可能以低于本国平均成本(对应于较小规模)的实际成本提供较大的数量。而与此相反,如果本国企业试图进入该产业,受初始规模的制约,只能以高于外国平均成本(对应于较大的规模)的实际成本提供较小规模的供给。二者对比的结果是本国企业在竞争中失败,本国在资源禀赋中的优势不能转化为胜势。
2.市场失败。如何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答案似乎非常简单。如果资源禀赋具有优势,即使失去先发优势,从而在短期内企业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但就长期而言,企业仍然可能凭借其资源优势在竞争中胜出。问题是,市场自发的演进不能支持这一判断。
显然,如果要获得动态的比较利益,(1)在短期, 企业必须支付高昂的初始成本;(2)在长期, 企业并不能限制相似资源禀赋的国家进入,企业面临的可能是更具资源禀赋优势的他国的竞争。多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会降低企业的预期值,从而减少该企业相关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收益。这就意味着,对这类生产要素的需求下降。在此预期下,如果这类要素的供给弹性足够大,那么,其供给会相应减少。
事态会进一步恶化。低水平的要素供给反馈到生产者,生产者预期其扩大生产规模的努力会在长期遭遇到该生产要素的瓶颈制约,从而使其利用规模优势凸现动态比较优势在经济上不可能,企业会进一步降低企业预期值,从而要素的边际产品收益也继续下降……,反复博奕的结果形成了低价格,低数量的均衡模式。受要素供给制约本国企业生产规模不能达到在长期胜出的供给规模。因此,市场的自发演进过程不能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
3.干预及其途径。假定政府基于不同的理由,试图充分利用本国的劳动力优势而进入该产业,即形成了所谓的目标产业选择。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实现其目标产业选择?
政府可以选择直接进入,凭借其国家信用承担较高的生产成本。这也是改革前我国实现其产业选择的基本途径,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不过,这种途径有其固有缺陷。市场化改革以来,这一途径的基础地位逐渐丧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政府更多的采用财政、货币政策手段,通过税收优惠等市场化方式实现其产业选择。但是,这类政策作用过于间接,各国政府实现其产业选择的结果优次不一,有得有失。因此如何有效地实现政府目标产业选择仍有探讨的必要。
市场之所以不能自发地选择该目标产业,是因为该产业相关生产要素可能陷入低水平的均衡之中。因此推动市场实现目标产业选择,关键在于打破这一均衡。
政府可以选择的途径有二。其一是直接向该产业提供补贴,以增加企业的预期值,提升要素边际产品收益预期,从而使要素需求上升。其实质在于政府向企业所有者提供某种程度的保险,以降低企业所有者基于不确定性而对企业预期值做出的折扣,最终令企业预期值与政府目标产业选择所要求的预期值相等。
这一途径的问题在于非市场化的政府补贴,会弱化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由此可能会呈现出政府直接进入企业的一系列缺陷。另外,供给曲线如果在短期内缺乏足够弹性,要素价格大幅上升,反而可能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
第二种选择则是直接补贴要素所有者,从而降低生产要素的供给成本。一方面,在每一价格水平上,生产者会增加要素供给量;另一方面,面对要素的潜在供给,企业确信不会受到要素的瓶颈制约,因而其对企业预期值评价也相对较高。这意味着,企业对要素的需求也相应上升。
这一途径的结果是要素价格下降,而均衡数量达到合意的要求。对生产者而言,进一步降低了平均成本,同时避免了要素的瓶颈制约,因此生产者可能获得竞争优势;对要素供给者而言,由于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生产成本,因此他有扩大供给的愿望;至于政府,虽然支付了部分要素成本,但政府达到了实现其产业选择的目标。这是一个典型的多赢结果。途径二的核心在于通过政策干预,影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以降低目标产业的预期成本,从而促使具有动态比较利益的企业走向成熟。这也是政府推动市场完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途径。
4.干预的对象。上述分析是以规模经济的存在为假定条件的,但这只是为了简化分析过程,这里的结论并不以规模经济为必要条件。分析核心在于市场所认同的边际收益产品曲线低于长期的边际收益产品曲线,而后者被假定与政府合意的产业结构相适应。直观地说,市场低估了该生产要素的生产力,致使生产要素供给数量过低,而这是政府干预的直接原因。作为干预的对象,该生产要素具有下述特征:(1)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评价与社会评价具有了差异。(2)长期供给弹性较大而短期供给弹性较小,这样市场需求的变化在短期内不会导致均衡数量的变化,而更多地反映在价格的变化上;而在长期,政府具有干预空间。(3)生产中的主导性,因为其实现途径首先依赖于降低生产者的生产成本。
如果说,前两个特征保证了干预的必要性,那么后一个特征则保证了干预的有效性。因此,适应于不同的目标产业选择,所选择的调控对象也有所不同。而政府干预的途径应当是:降低该调控对象的生产成本,增加供给以达到合意的均衡数量。
三、实证分析:中印软件业比较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与印度相继将软件业作为其目标产业选择。为此,政府选择了多种政策手段:(1)税收减免;(2)财政补贴;(3)政府支持进入等。那么,这类政策的具体效果如何呢?
1991年两国软件业难分伯仲,且两国资源禀赋情况类似。但是,两国软件业的发展轨迹却有很大差异。2000~2001年,印度软件业总收入高达130亿美元,其中出口收入为95亿美元, 而同期中国软件业产值只约2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软件出口值的1/5。
显然,与政府目标相一致,我国软件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与我们的理论分析相吻合。一系列政策手段提高了企业的预期值(途径一),因此,其有效性可以预期。但是,与印度相比较,我国软件业的发展只能说相对滞后。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滞后发生于我国GDP 增长值远高于印度的背景之下。这一背景的显著作用在于:各产业的协调发展更有可能向软件业提供需求。资料显示,我国国内软件市场容量要远大于印度。这意味着,不考虑国际贸易,我国软件企业的预期值要高于印度。因此,我国软件企业有可能比印度软件产业启动得更早。考虑到两国相同的资源禀赋,相近的产业选择意愿,我国在软件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令人费解。我们的推断是:我国在软件产业的弱势地位,是我国产业政策的必然结果。因为,这类政策没有涉及到产业的主导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的供给,特别是,它们不能降低人力资本供给的成本。而我们的分析表明,后者(途径二)是更为有效的产业选择实现途径。
乍一看,多数数据表明我们的推断可能是错误的。因为,(1 )从人才存量上来看,两国软件人才数量均在30~40万之间,并无显著差别;(2)从增量来看,印度400多所大专院校每年培养1万多专业人才, 而我国计算机专业每年毕业生高达3.5万人,然而, 除了依靠高等院校培养高级人才以外,印度还有各种民办软件人才培训机构1000多家,它们每年培训各种中初级软件人才15~18万人。不可否认,为实现其产业选择的目标,我国政府并没有忽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但与印度相比,我国政府相对忽视了软件蓝领工人的培养,而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到高级人才的培养上。
蓝领工人缺乏会出现高级人才向低级职位的流动,即所谓的“高能低就”。这一倾向的问题有二:(1)高级人才培养成本较高, “高能低就”会直接增加企业成本;(2)高级人才培养周期较长, “高能低就”会造成高级人才虚热,需求上升,工资相应上升,进一步推动企业成本上升。这两个问题反映在两国软件业中:印度软件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不足8万元,而我国软件从业人员总费用高达15万元。 正是这一成本差异,成为两国软件业不同发展轨迹的基础。而这一成本差异,显然是两国政府不同的人力资源政策的结果。
四、结论与启示:适用于我国的现实选择
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都支持我们的认识:(1 )市场的自然演进是产业选择的基础;(2)政府要实现其目标产业选择, 应当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来完成;(3 )降低目标产业主导生产要素供给成本是有效途径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高科技产业已成为许多国家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竞争力的战略性选择。不仅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转向高技术产业,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把发展高技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也相应地选择了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目标产业结构模式。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又是什么呢?
一般认为,高科技产业是以人力资源为主导生产要素的产业。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就生产性而言,高技术产业以创新为企业之灵魂,而人是创新的主体;就经济效果而言,为人力资源所支付的费用在企业成本中占绝对比例。因此,依据上述逻辑,我们认为:为实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目标选择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应当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源本身。我国要实现高技术产业的目标选择,就必须推进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其中,加大对相关产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是目前的现实选择。这一判断也可以解释近年来各国纷纷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的现象。
适应我国的产业政策,我们以高科技产业的实现途径为基础说明了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但并不局限于此。事实上,随着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推进,物质资本稀缺性被人力资本稀缺性所代替,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越来越得到加强(冯子标),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主要产业政策手段必是一个加强的趋势。
标签:软件业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供给价格弹性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目标成本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优势分析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