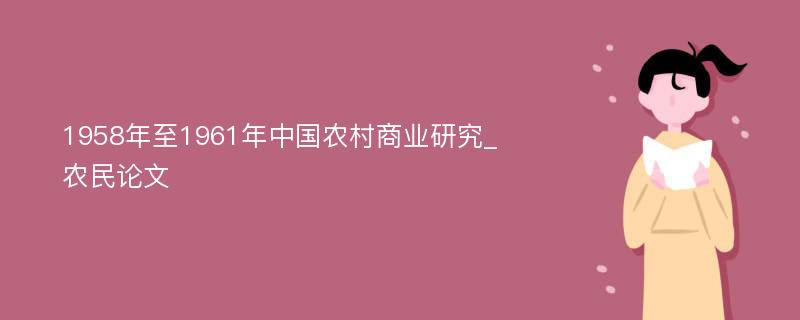
论1958-1961年的中国农村商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村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3)03-0217-05
1957年以前,我国共有三条商品流通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集市贸易,同时,个体小商小贩依旧存在。但是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兴起,我国的商业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集体性质的供销合作社被合并到国营商业里面,集市贸易被关闭,小商小贩不允许存在,只剩下国营商业一条商品流通渠道。但是这位群众生活的“管家人”并没有起到服务人民生活、促进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三年大跃进期间,我国的商业陷于停滞状态,商品市场极为紧张,日用工业品和粮食、副食品等倍感短缺。
面对粮食、肉禽蛋、食用油、棉花、蔬菜、日用工业品等生活资料的匮乏局面,从1961年初开始,毛泽东多次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以便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进而制定正确的调整农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生产队和社员家庭,对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其中,胡耀邦、李先念、邓子恢对农村商业状况的调查颇有历史价值,因为他们在调研中发现了大跃进期间农村商业的弊端,并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
一、胡耀邦:青年魁首来到白山黑水之间
1961年3月广州会议以后,胡耀邦率领工作组到辽宁进行调查研究,回京以后于1961年5月5日向毛泽东递交了几份调查材料,其中一份名为《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的材料,其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点:
(一)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商业搞得很糟
1.在农副产品的收购方面
胡耀邦发现国营商业对农副产品采取了“统光购净”的做法。
当时国家将农副产品分为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对第一类农副产品如粮食、棉花、油料等实行计划收购,对第二类农副产品如烟叶、麻类、生猪等实行统一收购。同时规定在对第一、二类农副产品进行收购时,要给农民留下自用的部分,但是基层商业部门往往把收购计划指标定得太高,给农民留的太少,不够农民自食自用的。
对种类繁多的第三类农副产品如扫帚、苇席、瓜子、小手工业品、小家禽、新鲜水果、粉条等,国家的政策本来“放”得很宽,允许公社、生产队、社员之间自由交换,但是基层商业部门却不准对第三类农副产品进行自由购销,统统由它来统一收购。由此出现了将第三类物资提为第二类物资,第二类物资提为第一类物资的现象,最终造成对农副产品“一购而光”的局面。对此农民很有意见,“他们说,种花生的吃不到花生,种麻的没有绳子用,种烟的没有烟吸,种果树的没有水果吃,养蚕的不光穿不到绸子,还吃不到蚕蛹。”[1](P179)对农副产品以较低的价格“统光购净”的错误做法,严重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村副业生产的积极性,使我国的农副业生产大幅度下滑。
2.在对农村的商品供应方面
对农村的商品销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供应农业生产资料;二是供应农民生活资料。
就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而言,大跃进期间,国家不允许城乡间、地区间、公社间、大队间互相进行直接交换,统统由县商业局和基层商业管理所(简称商管所)负责统一平衡、统一分配、统一经营。结果造成生产资料供应不及时,不仅影响农副业生产,也造成商业企业的商品大量积压,影响资金周转,增加企业亏损。对此,胡耀邦指出,“有些商品,由于盲目地追求统一调拨,统一加工,而造成极大的浪费。刘二堡公社农民说:供销社(农民的习惯性称谓,官方称谓是商管所)加工的套包子,‘狗戴太大,马戴太小’。供销社把山区用的镐头调到平原,因为不适用,农民说它是‘减产镐’。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1](P180)
就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而言,商业部门做得就更不好了,许多日用轻工业品和副食品根本供应不到农民手里,“据我了解,某些商品的大部分是从‘后门’分配的,农民根本买不到。”[2](P538)对于商品分配中的“走后门”现象和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广大农民很不满意。
(二)向中央提出了改进农村商业工作的建议
鉴于农村商业的不良状况,胡耀邦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恢复供销合作社,二是改变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政策和工业品的供应政策,三是恢复农村自由贸易。
1.恢复供销合作社
在供销社的恢复上,胡耀邦提出从上到下建立供销合作社的各级组织,将其由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并且恰当处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分工问题,分工的原则是能够更好地刺激农村商品生产、活跃农村市场和便利群众购销。
2.改变对农村的商品购销政策
首先,胡耀邦提出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要定低定死,几年不变,要给农民留下足够的自用部分,要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不论是生产队还是农民出售粮食、油料、猪禽蛋、烟叶、棉花等,都要奖励适量的工业品和返销粮;其次,他指出在向农民销售商品时,要对农村的产妇、婴幼儿、病人、老人等实行特需供应,要在农村恢复农民生活必需的“四坊”(油坊、粉坊、酒坊、豆腐坊),改变那种将大米、小麦、大豆、油料等原料由农村运到城市进行加工,然后再运回农村,造成迂回运输,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现象,让农村就地取材,就地加工,自给自足。
3.恢复农村自由贸易
胡耀邦建议在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基础上,允许公社、生产队、手工业单位、社员为了生产和生活需要,直接交换自己的产品,特别“对于第三类物资要允许公社和农民个人,在一定范围内自由采购,自由推销,恢复旧有的购销关系”[1](P180)。总之,只有允许地区之间、集体之间、个人之间互通有无,自订合同,自由议价,才能刺激生产,便利消费。
二、李先念:财贸“总管”论粮食
1961年3月广州会议以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财贸工作的李先念,组织了五个调查组,由财贸系统各部委的党组书记、部长率领,分赴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调查,他本人则坐镇北京,听取各组汇报,并亲自到石家庄及其附近各县进行调研。经过对调查材料的周密分析,他于1961年5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他对粮食问题的看法:
(一)粮食问题是城乡矛盾的焦点
1961年3月广州会议确定1961年到1962年度全国粮食的征购“盘子”是八百八十亿斤,但是各省向各县下达统购任务时却遇到了困难,许多基层干部和社员认为征购任务太大,要求减少任务,顶了几天牛,任务还是分不下去。李先念举了河北藁城县作为例子。
藁城县是河北省一个有名的余粮县,产棉花也产粮食。从1957年到1960年该县粮食产量基本上是逐年增加的,但是粮食的征购数量远远超过了粮食的增产数量,一九五七年调出一千七百万斤,一九五八年一下子增加到五千万斤,一九五九年再增加到八千三百万斤,一九六零年仍然调出六千七百万斤。粮食的过度征购和调出,给该县造成了不良影响,“农民的口粮,一九五七年是三百七十九斤原粮,到一九六零年只有三百斤了。这几年,猪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牲口减少了一半多,棉田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一,花生种植面积减少了将近一半,最后仍然影响到粮食生产,去年冬麦种得不好。这种情况,是同我们几年来征购任务过大的缺点分不开的。”[3](P257)
不仅藁城如此,全国余粮省几乎都要求减少粮食调出量。李先念细算了一下,八百八十亿斤的征购任务至多只能征到八百四十亿斤,很可能八百四十亿斤也征不到;同时重灾省(1959年至1961年我国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缺粮省则要求调入更多的粮食,有些粮食自给省也要求调入粮食,这两项加在一起需要多调入粮食四十亿斤。
经过多方权衡,李先念向毛泽东建议将1961年至1962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由八百八十亿斤减少到八百四十亿斤。这样本来广州会议确定的征购八百八十亿斤的征购任务就留有七十亿斤的亏空,现在加上要求减购的四十亿斤,要求增调的四十亿斤,亏空扩大到一百五十亿斤左右。如果亏空不解决,那么一亿三千四百万城市人口就得不到最低的粮食供应标准。但是再也不能挤农民了,农民人均口粮仅有二百八十多斤,于是粮食问题成了城乡矛盾的焦点。
(二)减少城市人口弥补粮食亏空
如何弥补一百五十亿斤的粮食亏空,他建议采取两条措施:一条是进口粮食,另一条是减少城市人口。他建议尽最大努力进口粮食一百亿斤,但是不能再多了,原因一是国外货源不可靠,二是外汇不够,三是船只运载和港口吞吐都有困难。这样一来一百五十亿斤的亏空,还有五十亿斤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想来想去,认为只有减少城市人口一条途径,他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城市人口过多,商品粮需要量大,农村难以负担。如果把城市人口减下来,把征购任务降下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把农业搞上去,有了粮食,有了原料,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只要农业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3](P262)况且当时我国农村人弱、耕畜少,要想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起来,需要增加大量的劳动力。
由于李先念的分析精辟入理,他的建议被毛泽东接受,随后我国1961年和1962年连续两年减少了粮食征购量,并先后精简城市人口两千多万。
三、邓子恢:农民利益代言人情系农村商业
1961年至1962年之间,邓子恢率领工作组到福建、黑龙江、广西、湖南、河南等省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议,其中有关农村商业的论述也颇具价值。
(一)农村商业弊端很多
1.对农民生活用品的供应工作没有搞好
邓子恢指出,“目前的情况是,在农村和城市里,商业部门除了布匹百货以外,一切副食品,如油、豆酱、酱油、咸鱼、海带和红白糖等,都成批地卖给食堂或生产队,再由食堂或生产队配售给社员……食堂或生产队的好干部,时常因为不会配售,弄得自己赔账,不好的人则从中揩油克扣,弊端百出,群众怨言很多。另外,商业部门又实行一种‘现金责任制’,只需完成卖钱的现金任务,不管商品收付,不管真卖假卖,更不管卖给谁,因此许多市场上缺乏的物资,可以大开后门,私相授受,而一般农民、市民则很难买到。”[4](P538)
邓子恢对农村商业部门在生活资料供应方面的论述可谓切中肯綮,不仅他的家乡福建龙岩地区如此,全国亦如此。当时的商业部门是财大气粗,全国人民的生活资料供应都由它负责,独家垄断,没有个体和私营商业,也没有供销社。大跃进期间商业部门的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废除,商品的采购、仓储、调拨、分配、供应、销售等环节十分混乱,致使商业员工的买空卖空、外购外销、商品“走后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行为频出。其中的商品“走后门”现象最为群众所不齿,“群众不满的说:‘手里拿着一把钱,不如认识一个营业员’,也有群众反映说:‘现在有四等人:头等人送上门;二等人开后门;三等人人拖人;四等人没有门。’”[5]
2.对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做得很糟
主要表现是对以粮食、棉花、油料、猪禽蛋为主的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过低,甚至出现了坑害农民的现象。1961年5月邓子恢在家乡龙岩调查时,一位农民反映“他队里前几天将一头牛,照规定送到商业采购部门去卖,采购部门将牛杀了之后,把牛皮、牛头、牛腿、牛骨、牛肚通通不算,只按所杀牛肉二百斤,每斤四点二角计价,得款八十四元,而该队买那头牛是花了一千二百多元,结果赔本一千一百多元。”[4](P535)邓子恢认为这是违反社会主义等价交换原则的,要求商业部门迅速改正。
(二)提出了改进农村商业的措施
1.对农副产品的收购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
邓子恢指出“等价交换与按劳分配同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则,这两条法则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不实行等价交换,就不可能按劳分配。”[4](P597)
为此,一方面要把国家对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任务定低定死,几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如果国家还想在计划以外收购更多的农副产品,可以委托供销社与生产队或农户进行议价,充分实行等价交换。
另一方面,对统购、派购都要实行物物交换,尽量做到等价交换,具体来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综合换购,你卖给国家粮食、棉花、鸡、猪,国家卖给你布、糖、盐、酒等。比如一百块钱的农产品,国家给六十块到七十块钱的工业品,老百姓很欢迎。另外一种是单项换购,比如一斤棉花给你三斤粮食,一百斤棉花给三百斤粮食。”[6](P586)邓子恢倡导的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实行综合换购和单项换购的方法,堪称真知灼见,后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接受。其核心是国家以“计划价格”收购农副产品,也以“计划价格”向农民供应工业品。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说的一斤棉花给你三斤粮食,是为了鼓励经济作物区(主要生产经济作物,从事副业生产,不产粮食或少产粮食,以吃“返销粮”为主的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三斤粮食也要钱,只不过“低价”卖给“棉农”而已。
换购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都很匮乏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妥善地解决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等价交换问题。
2.加大集市贸易的开放力度
1959年9月,中共中央虽然要求各地有领导有秩序地开放大跃进初期被关闭的集市贸易,但是各地都谨小慎微,生怕被指为“右倾”,对集市贸易“管”得多,“放”得少。对此,邓子恢认为集市贸易要进一步开放,他说:“两年来的实践证明,在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的现阶段,集市贸易是不能关死的。现在有两种地区:两广的集市贸易比较灵活,小杂粮熟食业允许自由上市;另一些地区则控制较严,杂粮完全禁止上市。据我看前一种地区比较好,对农业生产起促进作用,对城市人民生活也比较方便。后一种地区则相反,实际上后一种地区粮食还是有私人买卖,只是不敢公开,而转入黑市交易,可见这是一种不能用人为办法加以改变的客观规律。”[4](P598)
后来,邓子恢明确提出第三类农副产品完全允许进入自由市场(集市贸易),第一和第二类农副产品在完成统购和派购任务以后,也可进入自由市场。集市贸易的放开,为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提供了原料和产品的购销渠道,在当时农业“集体生产”只能获取口粮和其他少量实物的情况下,集市贸易成了社员获得“零花钱”的第一途径。
3.恢复供销合作社
只有恢复了供销合作社,才能改变农村商业的“官办”现象,在当时物资缺少的情况下,使供销社这个农民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在力主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同时,邓子恢还对即将恢复的供销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指出“供销社系统恢复后,必须建立严格的会计制度,建立‘物品账’和‘现金账’,改变‘现金责任制’。上级社对下级社和代销处,不仅要查对现金出纳,而且要查对物品收付,因为目前国家牌价与市价相差很大,如果只查对现金,而不查对货物,其中贪污舞弊将很难查清。”[4](P539)
在1961年至1962年之间,胡耀邦、李先念和邓子恢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改善农村商业的建议,主要包括把国家对农副产品的收购数量定低定死,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在收购农副产品时实行“换购”制度,恢复供销合作社,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开放集市贸易等,这些建议都被中共中央接受。
正是在他们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对农村商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商业部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1961年6月19日)、《商业工作条例》(1961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1962年9月27日)等三个重要文件,制定了如下调整商业工作的政策措施:
(一)恢复1957年以前的商业制度
包括恢复供销合作社;开放农村自由市场,默许城市自由市场;恢复社员的家庭副业经营权和副业产品自产自销权;恢复城乡手工业合作社及其与供销合作社的业务关系;承认私商的合法地位,并对新生的私商实行有限的发证政策;放弃大跃进期间推行的错误的“大购大销”方针,反对进行盲目的大购大销,反对高估产、高征购;在稳定市场物价的基础上,实行两个市场、两种价格;恢复1957年以前的商品分配原则,即实行“工业品优先供应农村,农副产品优先供应城市”的商品分配原则,成立商品分配委员会、商品分配小组、消费者代表会、商店监督委员会等有普通农民社员、市民、职工参加的民主监督检查组织,坚决杜绝商品“走后门”现象。
(二)实行以商惠农战略
1.恢复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和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经济建设方针
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支援农业,工业部门要加快生产适合农村需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商业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服务正常的农业生产需要、农村生产救灾(1959年至1961年我国灾情严重)需要、农民生活需要上来。不论是农业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凡是适合生产队和农民需要的,商业部门就要优先供应农村。
2.抛弃对农副产品“一购而光”的做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商业部门在收购农副产品时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正确运用价值规律,贯彻多产多购多留原则。对一类、二类、三类农副产品分别采取统购、派购和议购,但不论实行哪种收购形式,都必须与生产队或农户签订合同,特别是统购、派购任务要本着“定低定死”的原则,一定三年,增产不增购,减产酌情减购,在收购农副产品时要尽量实行换购、奖售制度,拿工业品和返销粮换农民的农副产品,力争使卖了钱的农民能够买到必需的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
在上述一系列调整商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我国城乡市场终于走出了大跃进造成的低谷状态,再现繁荣。
标签:农民论文; 商业论文; 生产队论文; 农村论文; 农业论文; 三农论文; 供销合作社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工业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