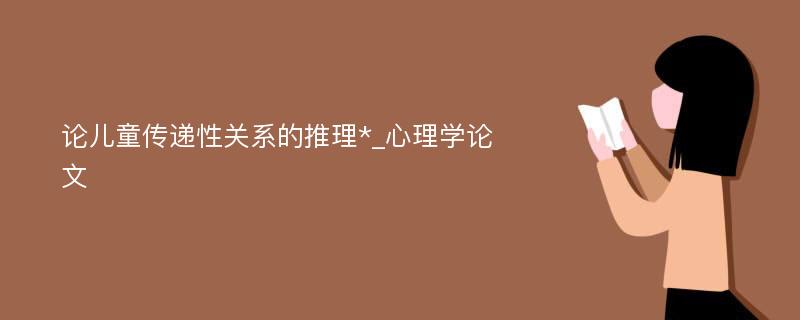
论儿童的传递性关系推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关系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传递性关系推理是一种间接的关系逻辑推理。已有研究认为,儿童解决传递性关系推理的能力是一种具体运算思维能力或其以上发展阶段的思维能力。本文认为,儿童的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能力,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具体运算阶段的成就,其发展在儿童认知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即依靠感知动作实现的传递性关系推理、依靠形象进行的传递性关系推理和依靠符号进行的传递性关系推理。据此,对目前该领域的几个热门课题,如儿童何时能够进行传递性关系推理、加工策略问题以及推理与记忆的关系等问题,都应重新估量。
关键词 儿童 传递性关系推理 加工策略
一、传递性关系推理研究概述
传递性关系推理(transitive inference)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传递性关系的判断构成的推理,是一种间接的关系推理。根据“小张高于小李”和“小李高于小王”,能推出“小张高于小王”的结论,这就是传递性关系推理。根据逻辑项的个数,可以将传递性关系推理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即三项系列问题和N项系列问题。三项系列问题由三个逻辑项组成,是传递性关系推理的一种基本形式,即线性三段论推理(Iinear syllogistic reasoning),N项系列问题由四个及四个以上的逻辑项组成,如A>B,B>C,C>D,问谁最大或谁最小。
一般地说,心理学所研究的传递性关系推理是不可逆的传递性关系推理。心理学对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本世纪初到二十年代
心理测量学和能力心理学最早研究了传递性关系推理。1919年,Burt就认为传递性关系推理是了解儿童智力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并把它作为儿童智力测验的一个分测验。[①]这一阶段确定了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也是儿童智力发展中的重要成分,但没有对儿童传递性关系推理的性质和心理机制加以研究。
第二阶段: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
Piaget在研究儿童思维的起源和发展时认识到传递性关系推理在儿童思维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把传递性关系推理作为具体运算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阶段主要探讨了儿童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的性质问题,儿童能够完成几种不同任务的传递性关系推理的年龄问题等。但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广泛重视,研究也不深入。
第三阶段:本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
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逐渐受到国际心理学界重视,传递性关系推理逐渐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中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Piaget的观点作出的批评和修正,主要研究了传递性关系推理年龄问题[①],推理与记忆的关系问题[③][④][⑤],加工策略问题[⑥],心理模型问题等[⑦][④]。认知心理学兴起后,对传递性关系推理作了大量研究,探讨了推理策略和推理的心理模型,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⑧][⑨]。
第四阶段:本世纪七十年初到九十年代中期
Bryant和Trabasso在七十年代初重新对Piaget的研究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与Piaget的结果完全不同的结论,引发了研究者们的热情和争论,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探讨,其中特别是关于推理与记忆的关系问题[⑤][⑩][11][12]和儿童何时能进行传递性关系推理的年龄界限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对认知发展颇有影响的模糊痕迹(Fuzzy-trace)理论和区辩性模型理论(Discriminal model)。
目前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几个问题:传递性关系推理的实质、传递性关系推理的最初出现年龄、心理模型、加工策略、推理失败与记忆的关系。除“儿童进行传递性关系推理的心理模型”问题笔者已经另文探讨外[13],本文将对其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二、传递性关系推理的实质
1.前人的研究结论
传递性关系理能力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Piaget在研究儿童的序列(Seriation)发展时,认为传递性关系推理是一种“演绎合成形成”,是儿童具体运算思维的重要成就和标志之一[②]。Piaget学派的心理学家也常常将传递性任务作为测量儿童是否能够进行具体运算思维的工具之一[①]。
Flavell把它作为形成运算思维的例证[①],是演绎推理的特殊形式。根据Piaget的理论,形式运算思维是思维发展的高级水平,比具体运算思维水平更高,指采用符号、语词进行的命题运算。这与Piaget的观点是不同的。
Sternberg把它看作特殊形式的三段论,即线性三段论推理,是演绎推理(deductivereasoning)的特殊形式[⑨]。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把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作为一种与形式运算思维相似的、抽象的逻辑思维看待。
可见,在传统的心理学研究中,传递性关系推理是一种具体运算思维或其以上的一种思维能力。也就是说,儿童至少要到7—8岁才能开始掌握这种能力。这种观点引起了后来一系列的研究兴趣和争论。
2.关于传递性关系推理研究的理论构思
对于上述观点,我们不能苟同。就其它的研究来看,儿童表现出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的年龄不是在7—8岁,而是3岁或4岁[③][11];从我们的研究来看,2.5岁的幼儿在解决了比较句式的理解和前提记忆问题后,就能进行推理[15][16]。可见,不能简单地把传递性关系推理作为具体运算阶段的思维成就。它在前运算阶段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但为什么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主要与研究中采用的方法和任务的改善有关。Piaget等的研究采用具体形象的语言形式作为刺激,而Bryant和Trabsaao等则采用实物来作刺激。可以说,他们研究了传递性关系推理的不同形式。前者研究的是语言形式的传递性关系推理,后者则研究的是实物动作形式的传递性关系推理。
Bruner的认知发展理论表明,儿童的认知发展有三种再现表象形式:即动作式再现表象、肖像式再现表象和符号式再现表象。[17]这体现了儿童思维发展的一般趋势,即从直觉行动思维到具体形象思维、再到抽象概念思维的发展过程。我们设想,与儿童的思维发展水平相适应,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即与直觉行动思维相适应,是通过对具体实物的感知运动操作而实现的传递性关系推理(动作思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与具体形象思维相适应,是通过对物体的表象操作而实现的传递性关系推理(形象思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而与形式运算思维相适应,是通过对抽象符号的操作而实现的传递性关系推理(抽象概念或抽象符号思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因此,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能力,它的发展也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趋势一样,体现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动作——肖像——符号。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采用不同抽象水平的任务作为实验刺激,可以得到不同水平的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
根据我们的观点,Piaget、Flavell、Sternberg等人所研究的并不是同一水平的传递性关系推理。Piaget、Sternberg等人研究的是具体形象思维的传递关系推理,Flavell研究的是符号思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而Bryant和Trabasso等研究的是介乎于动作思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和具体形象思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之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因此,他们的结论不一致不足为怪。
三、儿童进行传递性关系推理的最早年龄问题
Piaget指出,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才开始具有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即儿童要到7岁左右能进行长度和大小的传递性关系推理,在9岁时能进行重量方面的传递性关系推理,而要到11、12岁时才能进行容积方面的传递性关系推理。但这一结论受到了怀疑。
Braine指出,在对前提作过度学习的情况下,儿童所表现出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的年龄比Piaget所报告的年龄提前了2岁。Bryant和Trabasso指出,如果对儿童加以适当的训练,使他们在推理之前记住赖以进行推理的前提,那么,4岁儿童就能表现出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③]Halford和Kelly研究了3—7岁儿童学习传递性关系推理问题的能力发展问题,结果表明,3—4岁的儿童并不具备学习传递性关系推理问题的能力[14]。然而,魏华忠、宋世龙的研究却又表明,在解决了记忆问题之后,甚至是3岁儿童也开始具备了传递性关系推理的能力。[11]我们自己的研究表明,2.5岁的幼儿在解决了比较句式的理解和对前提的记忆问题之后,就能够解决实物形式的传递性关系推理问题[15][16]。
我们认为,关于“儿童在何时开始具有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的问题,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第一、不同形式的传递性关系推理可能有不同的出现年龄,而不同的研究者所研究的是不同形式的传递性关系推理,所以不能认为某研究的结论必然更加正确,而其它的研究就不可靠。Piaget、Sternberg等人研究的是具体形象思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Flavell研究的是符号思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而Bryant和Trabasso等则研究的是介乎于动作思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和具体形象思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之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我们自己则研究了动作思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所以,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不相一致是合理的。第二、即使是同一种形式的传递性关系推理,也可能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出现年龄,例如对于具体形象的思维的传递性关系推理,采用语言刺激和实物刺激得出的结论就显著不同。第三、是否对儿童的传递性关系推理能力进行训练也影响研究结果。Piaget的研究没有采用训练程序,他的结论是儿童在自然状态下传递性关系推理的表现情况。而Bryant和Trabasso以及后来的许多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某种训练程序,他们的结论是儿童在训练之后的传递性关系推理的表现情况。
四、儿童传递性关系推理中的策略问题
这个问题目前主要涉及了两个方面:第一、人们采用视觉加工方式或是采用语词加工方式来解决该问题?例如,对于“比尔矮于阿伦,比尔高于查尔斯,谁最高?”的问题,如果儿童在解决时形成了心理形象,所采用的就是视觉加工模式。如果没有形成心理形象,则采用的是语词加工方式。第二、人们是将不同的前提整合到统一的信息表征之中或是个别地加工每一前提?如果被试报告说形成了单一的空间排列,那么,被试所采用的就是将前提信息整合到统一的表征中去的策略,简称为整合加工策略(integrated strategy)。反之,则是个别地加工前提中的信息,简称为分离加工策略(separate strategy)。[⑥]
1.视觉加工与语言加工
视觉加工和语言加工的争论实际上是传递性关系推理的空间模型和语言模型的争论。
Desoto和Huttenlocher的空间模型强调视觉加工,并提出了两条原则[⑨]。一是评价性排序(evaluative ordering)原则,即按照“从好到坏”的顺序(better-to-worse)排序比按照混合顺序(mixed-ordering)排序的加工效果好,“从坏到好”(worse-to-better)加工效果最差。二是端点锚定(end-anchoring)原则,即端点项(end item)在前、接着出现中项(middle item)的前提,比中项在前、然后出现端点项的前提更容易加工,即被试宁愿“从端点项到中项”(ends-to-middle)地加工,而不愿按照“从中项到端点项”(middle-to-ends)的方式加工。
Clark的语言模型强调前提的语义加工,有三条加工原则[⑨]。第一、机能关系优先(the primacy of functional relations)原则,即推理中信息加工是按照前提中的逻辑关系(或机能关系)来存储信息,而不是按语法关系存储信息,就是说,是按照语言的深层结构存储信息。第二、字词标志原则(lexical markings),即前提中是否使用有标志的形容词(marked adjective)将直接影响加工的难度。第三、一致性原则(congruence),即前提表述与问题表述的一致性有助于信息加工。
Sternberg和Weil研究了儿童解决三项系列问题时的策略问题,结果发现,不同能力类型的被试所采用的策略不同,空间加工方式与其空间能力有关,而与语言能力无关;语言策略与其语言能力有关,而与空间能力无关;空间——语言混合策略则既与空间能力有关,又与语言能力有关。这说明在空间和语言两类基本策略之外还存在着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策略。根据Sternberg和Weil的观点,并不存在某种普遍适用于所有被试的策略,策略只是相对于不同类型的被试而言的[⑨]。
Maryer认为,这两种信息加工方式都是存在的,只是它们所适应的问题形式有所不同。对于有些传递性任务,可以用空间加工方式解释,而对另外一些问题,则应该由语言加工方式来解释。因此,Mayer归纳了三种加工效应。第一、方向效应或者标志关系效应(directional effect/marked relation effect),即按“从好到坏”(better-to-worse)方式表述的前提,比按“从坏到好”(worse-to-better)的方式进行的前提更加容易加工。第二、端点锚定效应(end-an-choringeffect),即以端点项作为前提的主语,比以中项作为前提的主语更容易加工。第三、转换效应(translation effect),即在不需要将问题表述转换成为与前提表述相一致的形式的问题中,信息加工比较容易[⑥]。
2.整合加工与分离加工
Potts曾以距离效应来说明整合加工策略。他通过故事的方式来呈现问题,若被试在阅读故事时形成了诸如“A>B>C>D”的空间排列,那么在回答“谁最大或谁最小”时,相邻项之间的比较就将比不相邻项之间的比较更困难。若被试没形成这种空间排列,而是单独地记忆每个逻辑项,就不存在距离效应[⑧]。Humphreys的研究指出,被试以标签(tags)来单个地存储每个逻辑项,然后根据每个逻辑项的存储频率来确定其在传递性关系中的位置,并据此来回答问题。这是分离加工策略的研究[⑥]。而Mayer的研究表明,这两种策略都是存在的。他将被试分为两组,一组接受人工的、或抽象的问题,例如,“A>B>C”,另一组则接受较具体、较熟悉的问题,例如,“比尔比戴维高”。结果表明,使用抽象问题的一组倾向于单个地记住前提,然后再解决问题,即没有出现Potts所描述的距离效应。而使用具体问题的一组则采用整合策略,被试也出现了较强的距离效应[⑥]。Egan和Grimes-Farrow的研究也同样支持两种策略并存的结论[⑥]。
不同类型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将采用不同的加工策略,这可能是对传递性关系推理策略的最佳概括。然而,我们所需要弄清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被试将采用何种策略,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才是最佳策略。这是先前研究所没有回答的。
五、儿童传递性关系推理与记忆
据Piaget学派的观点,传递性关系推理乃是演绎推理,对前提的精确回忆是解决传递性任务的必要条件。因此,幼儿推理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前提记忆的失败,不是逻辑能力不足。Braine采用“过度学习技术”(overlearming technique),证明儿童的推理的确依赖于对前提的记忆。Smedslund认为,Braine的研究引入了无关因素,因为在过度学习中,前提“A>B”中的A总是被编码为“长”,而B总是被编码为“短”;而在前提“B>C”中的B总是被编码为“长”,C总是被编码为“短”。久而久之,A总是与“长”联系起来,而C则总是与“短”联系起来。这样,依据记忆中A和C的标签就能回答问题[⑨]。这就导致了传递性关系推理与记忆关系的争论。
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1.儿童的推理必须依赖记能力,这被称为“推理——记忆依赖效应”(reasoning-remembering dependance effect);2.儿童的推理与记忆能力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性,它们是相互独立的两种能力,这被称为“记忆独立效应”(memory independence effect);3.推理成绩与记忆之间有某种关系,但不是第一种观点所指出的那样密切,推理成绩对记忆的依赖只是一种模糊的记忆痕迹,这被称为“模糊痕迹理论”(fuzzy-rtace theory)。
Bryant和Trabasso(1971)支持传递性关系推理依赖于记忆的观点,为了检验这种观点,他们先对儿童进行前提记忆训练,在能记住前提后,才呈现推理任务。结果表明,4岁儿童就能解决Piaget研究中7—8岁儿童才能解决的问题[③]。Halford、Galloway和Russell的研究表明,儿童推理失败的原因不能单独归因为记忆缺乏,可能还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又有研究表明,儿童在解决传递性关系推理问题时,没有必要象Bryant和Trabasso指出的那样,必须清晰地记住前提的一切细节,只要能够对前提信息产生一种模糊的记忆痕迹就能够解决问题[⑩]。我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三项系列问题或五项系列问题的传递性关系推理,前提记忆都是影响推理成败的重要因素,然而,前提记忆不是单独地对推理的成败发生影响,前提的记忆、儿童成熟水平、儿童对汉语比较句式的理解三者对儿童的推理成败具有复杂的交互作用。对三项系列问题的研究来说,在总测验中,不能记住推理的前提影响2.5—4岁的推理成绩。在“比长”中,记忆训练对2.5—3岁组推理成绩有显著影响,对4岁以上均无显著影响;在“比短”中,记忆训练对所有实验年龄组都有显著影响。对五项系列问题的研究来说,前提记忆的训练效果也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且在“比长”句式中的训练成绩明显优于“比短”句式的训练效果。[15][16]
* 本文得到林崇德、黄希庭教授的悉心指导,特致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