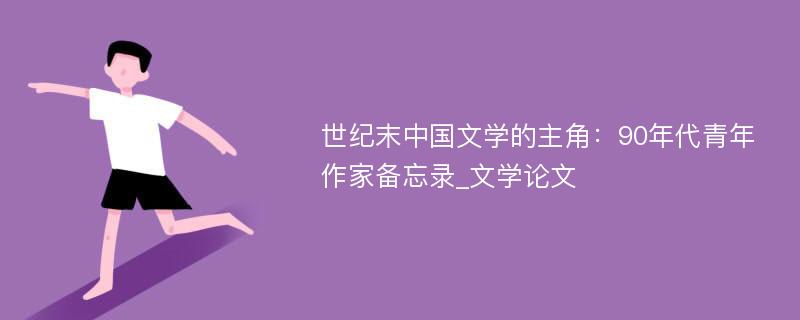
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主角——关于90年代青年作家的一份备忘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世纪末论文,备忘录论文,中国论文,主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批作家力图告别那种将思想理念作为创作起点也成为创作终点的小说观念,他们很少急切地呼应现实的强势话语,也不直接模仿流行文化
●他们介入现实的方式,多半不是正面碰撞现实的坚硬结构而是留连于那些底层的幽暗面,率先捕捉精英知识分子不屑解释的市民社会新的价值生长点
●在他们中间确实还看不到未来大师的身影,可也并非均系庸常之辈
这篇零星的印象记涉及的一些青年作家,大多在50—60年代出生,60—70年代启蒙,70—80年代接受中学大学教育,80—90年代进入世纪末的文学潮汐而有以自立。他们用不同于父兄辈作家的方式讲述一个世纪的往事,也从不同渠道切入当下精神世界。这个新的小说群体将横贯下一个世纪,成为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主角。
1
他们首先透露出小说观念甚至整个文学观念的某种深刻转化。李庆西、李杭育兄弟在80年代中期就惊呼小说领域发生了一场“哗变”。当时的解释偏于现象学与叙述学理论,似乎小说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西方某种哲学观念和叙述技巧的输入。后来,由于小说随着现实生活节拍进一步“哗变”,它的大幅度自由化、松散化和世俗化推进,很快扭转了这种纯粹经院式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变动的小说景观与90年代生活样式的对应关系。近来一些刊物热烈讨论的意识形态分析和市民社会、民间世界话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
十八世纪以降,其他艺术品类相继式微,小说后来居上,一枝独秀,由“致远恐泥”的“道听途说”,上升为与正史平行关乎社稷兴衰的“伟大叙述”。二十世纪的小说已不再是原初那种自由、松散、充分世俗化的民间叙述形式,而几欲取代诗歌戏剧散文,扮演人类存在命定的语言。它也因此日趋沉重和精致化,像十八世纪或更早时期中西方小说一致表现出来的与市民生活息息相通的那股粗犷活泼的生命力已逐渐退化。它总是力求靠近某种超越的思想,阐释某个绝对理念。即使贴近世俗的作品,也免不了包裹着这样那样坚硬的理念内核。小说长期居于金字塔的顶端,充当政治意识形态与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传感器、而疏离民间世界的清新空气,其逼仄、僵硬、沉重、枯槁,就不可避免了。
80—90年代崭露头角的一批青年作家力图告别这种绝对化的小说观念,有意躲避超越世俗生活的种种形而上的需求和规范,重返松散、自由状态,融入平民的生活空间。它首先是生活的艺术,而不是真理的话语。“我们拥有艺术,以免亡于真理”(尼采)。90年代中国小说的“哗变”,和二十世纪这种普遍反对形而上学预设而回归生活大地的精神是相通的。现在有人拿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形而上”标准来指责小说家们过于“形而下”,确实匪夷所思。
市民社会生活信息爆炸,民间世界价值体系崛起,开始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理想并立,应该是这场“哗变”的社会学基础。哗变即还俗,也就是从天上落到地面。多元化取向也由此而来。6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年龄经历彼此接近,但很少全方位的相同和重合。已往那种可以用年龄段划分的清一色作家群体不见了,正是“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况味。
2
他们很少急切地呼应意识形态强势话语,也不直接模仿流行文化(那是变相呼应意识形态或制造新意识形态即大众文化霸权)。他们潜入了飞扬的人生的底层,沉缅于故事的迷宫,编织扑朔迷离的情节,好像和现实的历史指向背道而弛(格非、李冯、刁斗、朱文),或者陶醉于语言的雕刻,在词语的浪花中随波逐流(孙甘露),又或者听任想象的翅膀穿越现实的天空,翱翔于往事的原野,在尘封的史籍、杳不可寻的古战场或早已倾废的帝王后宫,选择停息的枝头(苏童、须兰、吕新)。他们刚刚步入而立之年,却显得过于老成,旧事重提成了拿手好戏(苏童、余华、张旻、韩东)。俗则俗得彻底(王朔、何顿),雅又雅得“须仰视才见”(北村、鲁羊)。有乡村生活的素描(迟子建),也有城市的“环境戏剧人”(邱华栋)。走向现实的道路与通往自我的曲径时相交错(张欣、迟子建、陈染、林白)。
多向度的格局实难一概而论。有评论家把他们归入“先锋派”或“后现代主义”,这多半只是平面的文化借喻。事实上,他们的写作,总是和一代人共同的“过去”难舍难分,很难扯上“先锋”或“后现代”。比如许多青年作家都喜欢倾诉“早年”经历,匮乏的童年与少年成了叙述的无尽资源,现在进行时的生活反被一再冷落。苏童《离婚指南》、《城北地带》,余华《呼喊与细雨》,韩东《同窗共读》、《下放地》,张旻《校园情结》、《情幻》,何顿《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刁斗《纯情岁月》,包括王朔的《动物凶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种倾向。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在经济大潮面前手足无措,内心空空荡荡,生活全部乱了套,或者在极端务实的商品时代坚守古典主义情感原则,结果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他们对正在兴起的商业社会似乎心存疑惧(张欣或许是个例外,她在小康前后的两个世界游刃有余),对正在消逝的“前商业”、“前小康”社会极度贫困的生活景观则情有独钟。他们多半可以说是前小康社会(主要是70年代)的凭吊者。
3
凭吊往昔的感伤情怀使乱世才女张爱玲再度走红。这种后向性写作,似乎和回归世俗的精神并不统一。但是且不说张氏本人的文学雅俗难分,90年代大陆青年作家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当然也不排斥单纯的模仿和抄袭),决非没落贵族情调的虚拟化表达,而是80—90年代商业化进程在社会底层搅动的变革时代常有的那种怀旧情绪。张爱玲不迟不早在此时此景引起青年作家的追慕,这一现象本身就颇能说明问题。形式上的退避与逃逸,恰恰是进入现实的一种美学策略,只是少了张氏叹息繁华已谢的苍凉,而有更多的苦涩与荒涎。
也有从正面迎向现实而且惊世骇俗的。90年代青年作家介入现实的方式,多半不是正面碰撞现实的坚硬结构,而是留连于那些底层的幽暗面,率先捕捉精英知识分子不屑解释的市民社会新的价值生长点,特别是破译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蓬勃发展的各种欲望形式。刁斗的《捕蝉》,格非的《欲望旗帜》,就是旨在窥破现实的欲望化本质。类似的作品比如像作家陈村的《张副教授》,在80年代还是孤立现象,现在就不足为奇了。许多场面描写很容易调合商业文化的种种恶趣,实则是反商业的。描写欲望不等于认同欲望。他们之所以喜欢用“窥视者”身分揭露现实的欲望化本质,正显示出他们和欲望化现实的距离。他们也并不简单把人的欲望漫画化,更多是对这种被解放的原始人性的泛滥保持一种真诚的惊愕。
直面人的原始欲望,大概算不上“终极关怀”。不过,既然生活的常态往往就是欲望的不断延耽和掩盖,那么挑明这种躲躲闪闪的本质,也会把精神逼到一个死角,即厌倦和拒绝欲望的重复。这样的死角或许就是诗情或圣情的发生地(陈村和北村就是最好的例子)。无论优美凄凉地凭吊往事,还是对这个生猛时代投去窥视者充满疑惑的目光,其中都不乏文学性的剥离与审视。
我不知道凭吊往昔与窥视现在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但我发现这确实是90年代文学的两种精神症候。凭吊者和窥视者都表现出存在的某种疏离感。无可否认,这代作家大多数正经受着痛苦的自我认同的危机。他们总是在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遥遥无期的现实感。他们和现实的关系一言难尽,甚至多少有点暧昧。他们无疑是软弱无力的,缺乏一代人共同的企慕与抗议。如果有人制成一面统一的旗帜,在他们中间肯定找不出合作的旗手。
4
所以我们很少看到高调陈述。“先锋”作家格非的长篇新作《欲望的旗帜》,仿戴维·洛奇《小世界》的构思,竟然大肆嘲弄94年提倡“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学术氛围。这里没有理想道德的空洞承诺,也找不到足以支撑小说结构的坚硬理念内核,只是对种种以学术思想名义出现的原始欲望进行冷静机敏的破译。一贯追求精神乌托邦的王安忆,近著《长恨歌》也毫无高调可言。这部长篇采用的“详述体”,富有弹性,大包大揽,本应该处理成宏大题材,实际上陈述的却是一个感伤的怀旧故事,目的只是为回避了历史飞扬的一面,探索所谓“做人的芯子里的事情”,一目了然的张爱玲味不可避免地消解了任何思想积淀与理念综合的企图。格非、王安忆这两部准低调长篇,似乎都故意要反一反知识界真假唐·吉诃德们的高调。
普遍的“低调”使兄长辈的张承志、张炜等人成了名符其实的精神孤岛。一些评论者拿“二张现象”批评青年作家的低调,更有专以骂人为业的文坛慷慨党与天理家指责他们的作品“苍白贫血”,“霉味扑鼻”,“瞒和骗”,“千篇一律”,“根本没有灵魂”,“从鼻腔里淌出来”。如此激烈乃至恶毒的批评话语,促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坚持理想和信仰的“二张”与更多低调作家的关系。我们始终缺乏从时代深处爆发出来的精神火花,也一直期待着能够说出现时代生活秘密的作者。在这方面,90年代许多青年作家确实令人失望。与此同时,“二张”说出了许多极精彩的思想,但也有未尽人意处。张承志拿伊斯兰宗教文化越俎代疱,从外面抨击汉族社会,彻底弃绝被他宣布为毫无希望的“人粥”世界,甚至干脆以奉献自由的宗教代替寻求自由的文学。张炜则把农业文明和商业技术文化绝然对立起来,以不容分说的拒斥取消可能的沟通与理解。“二张”的抗议模式带着他们各自的生命印迹,具有个人文化选择的合理性与很难仿效的精神魅力,然而他们的选择毕竟不能涵盖一切。“二张”的存在为更年轻的作者树立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参照,但他们无意事实上也并没有为90年代文学构筑或指示一条必由之路。
有些文学上的“假唐·吉诃德”,整天“道德”个不够,“理想”个不够,“崇高”个不够,“关怀”个不够,动不动拿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教训同时代作者。他们飘飞在时代上空,当然崇高得很,可惜和地面上的众生无关。青年作家确有枯萎软弱之病,但医治的良方决非他们的“战歌”与“长剑”。现在要紧的不是指责青年作家缺乏道德、理想和崇高精神,而是设身处地,在我们共同的文化时空中,为这些难以立足的肯定性价值,开掘可以赓续的不竭长流,寻找可以“着陆”的坚实地面。文学和语言的道路伸展在贴近大地的俗世与沉静平实的情思中,与半天空急切的呼唤无关,与严厉的呵斥也无关。
青年作家也并不一味地软弱低调自我封闭,他们仍然保持关向社会现实开放的广阔扇面。北村的作品就让我们感到平凡人生蕴涵着强烈的宗教情绪,它联系着80—90年代中国民间的某种宗教生活。北村的宗教当然有对现实的批判,但他并不是把宗教从现实中生硬地剥离出来,而是顺着现实生活的肌理自然而然推导出信仰之路。这和张承志用宗教批判现实特别是用一个民族的宗教从整体上评判另一个民族的世俗生活,是有区别的。像张欣、何顿、张旻、吴滨、唐颖、邱华栋、徐坤以及王朔的大量作品,则浮现出一个小康社群的影子,现代都市新市民是他们主要关注的对象。他们的叙述谈不上高调,但也不是什么低调,而是平实地叙说“做人的芯子里的事情”。刘震云、刘醒龙、常捍江等人的小说,更多暴露现实社会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能让梁晓声觉得吾道不孤。但这种现实关怀,一般只是普通平民乃至“草民”的讽世或慨世。现代人或者也不止于现代人的平常心,代替了寻求终极解决的启蒙意志,更没有梁晓声那样浪漫的社会理想与英雄情绪。这或许是理想主义抗议文学之外另一种批评模式。
看来,这个仅仅由年龄界线构成的作家群体,并没有整齐划一的价值标准与艺术主张,“不统一”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精神特征。他们彼此之间不统一,自己和自己也不追求绝对的统一。不消说,这多少折射出世纪末普遍的观望、随机与两可心理,映现着90年代芜杂诡谲的文化布景。然而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中,我们目睹了长久统治小说的某种非此即彼的绝对之物的崩溃。统一的小说发生了根本性的裂变。他们只是想在裂变所提供的缝隙中争取生存与写作的新空间。在这种似乎“无名”的两可状态,确实看不到未来大师的身影,可也并非均是庸常之辈。
199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