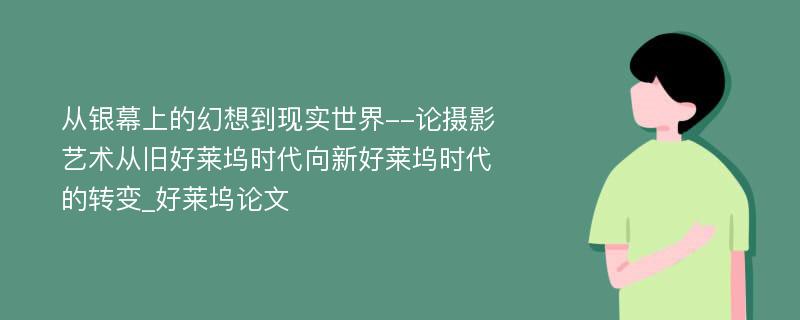
从银幕上的幻梦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谈摄影艺术从旧好莱坞时代到新好莱坞时代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好莱坞论文,时代论文,摄影艺术论文,幻梦论文,银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少年来,沐浴在南加州和煦阳光中的好莱坞,用那台沙沙作响的神秘盒子挽留了消逝的时光,保存下难得的历史印象,也纪录了一个电影帝国的起起落落。而更多的,则是它见证了整个电影艺术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段时间里所经历的一场漫长而又深刻的观念变革。这场变革彻底改变了电影的创作实践,并连接了好莱坞电影最重要的两段历史:被称为旧好莱坞的好莱坞黄金时代;被称为新好莱坞的当代美国电影。在这篇文字当中,我们试图通过对好莱坞电影的这两个不同的历史片段,特别是作为电影艺术最终实现的摄影艺术的探讨,来管窥这场变革带给世界电影的深刻变化,以及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历史环境,以及商业化电影工业体系,意识形态企图三者对电影艺术的牵制和推动。
充满假定性的银幕幻影
——旧好莱坞时代的电影摄影艺术
旧好莱坞在长期的创作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整套完整、严密的电影工业体系。它包括了严密的组织分工、制片人制度、明星制度,并在此之上,逐渐形成了它的类型电影创作观念。而摄影艺术针对不同的类型,在“用光”、“构图”、“运动”这三个最基本的摄影元素上,形成了它相应的影像创作方法和艺术特征:
用光——充满假定性和修饰性的戏剧式用光。
构图——深受古典西洋绘画的影响,讲究均衡和黄金分割率的应用。
运动——沉稳、平滑的运动,更多的是全景呈现式的使用,而很少内在含义。
这些艺术特征反映了旧好莱坞时代在摄影艺术创作上形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和教条。今天,当我们重温那些由亨弗莱·鲍嘉、克拉克·盖博、丽达·海华斯、英格丽·褒曼等天皇巨星主演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影像似乎有着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即便是像约瑟夫·沃克尔(Joseph Walker)、约翰·F·塞茨(John F Seitz)、阿瑟·安德森(Arthur Edeson)(注:约瑟夫·沃克尔、约翰·F·塞茨、阿瑟·安德森,都是旧好莱坞时代的著名摄影师。)这些杰出的黑白电影摄影艺术家,也很难绝对逃脱这种窠臼。
比如说在用光方式上,所谓的假定性和修饰性反映在场景布光和人物造型光两个方面。我们拿大家非常熟悉的影片《北非谍影》(Casablanca)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我们在《北非谍影》第一段里克咖啡馆的戏中,看到的就是典型的旧好莱坞时代的内景环境布光方式。整个环境晶莹剔透、辉煌浮华,人物光影差距微乎其微。实际上,在一个人工照明的空间里,处于不同位置,影调效果是决然不同的。正是这种差异,才是内景环境照明最有味道的地方,也是最能呈现场景特征的地方。而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影像却与我们自己在酒吧、咖啡馆得到的影调体验完全不同。这正是旧好莱坞时代布光假定性的特征:忽略真实的环境和时空特征,主观、人为地创造影调结构、控制照明均衡,从而为剧情和构图服务。
另一方面,所谓用光的修饰性,则主要表现在人物造型光中。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它形成了以“五大光”为基础的创作手法。每一个人物形象的镜头,特别是那些特写镜头完全按照主光、副光、轮廓光、修饰光、眼神光五种基本光线以及它们之间特定的光比来创作完成。我们在《北非谍影》当中看到的亨弗莱·鲍嘉和英格丽·褒曼的镜头,大多是按照这一方式完成的。最典型的,在莉莎和里克重逢的段落里,莉莎本来是坐在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里,她实际上应该处于照明环境中比较暗的地方,不会有太好的影调效果,亨弗莱·鲍嘉的表演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她所处的这种位置(里克一抬头,才发现了坐在角落里的莉莎)。然而,当我们看到她的特写镜头的时候,还是发现她似乎正处在一个绝好的布光环境中,一切都是那么精致、华丽,不可思议,当然也难以忘怀。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古典时期的好莱坞电影形成了它独特的用光方式,那就是一种脱胎于舞台布光经验的戏剧光效体系,非常讲究影片影像风格上的主观创造,从而达成一种戏剧性。这样的用光方式首先受到了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比如说早期的黑白胶片还不能很好表现影像中灰色的区域,这就必须依赖从舞台照明中借鉴过来的直射照明,即把聚光灯的光线直接投射到人物身上、环境当中,这样才能比较好地将人物轮廓从背景中区分出来,或者在一个大的环境中划分不同的区域。这种光线非常的“硬”,完全不像经过漫反射的日光那样柔和,因而也必然表现出强烈的人为痕迹。另一方面,这也是好莱坞商业电影制度导致的必然。好莱坞电影是一种戏剧式的电影,说白了就是“讲故事”的电影,它所要表现的不是一个朴素的客观世界,而是故事的核心——人物(也就是明星)。只有这些具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明星才是这一行业赖以生存的基础,那么也就必然导致一切工作围绕明星展开。能否成功塑造明星的形象,成了衡量好莱坞摄影师的准绳。有的摄影师因为在一部影片中的成功,得到明星和大制片人的青睐,从而职业生涯一路扶摇直上;有的摄影师则因为没能将明星拍得像《Life》周刊上那样好看而失去工作。
实际上,旧好莱坞在艺术创作上是比较保守的,创新很少,即便出现了创新,也很快被消化、整合成新的创作传统和教条。为了迎合最大的观众群体——城市平民阶层的欣赏口味,它讲求的是一种绝对化(或者说庸俗化)的美感,一种非常古老和传统的美学观念。这在构图上和摄影机运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同样以《北非谍影》作为例子,我们发现旧好莱坞时代的摄影构图有着强烈的趋向古典西洋绘画的意识,非常讲究画面内视觉元素布局的均衡以及黄金分割率的应用。在里克咖啡馆的那场戏当中,运动的镜头很少,大多数都是固定的单人、双人、多人镜头。这些镜头,单个的个人总是被放置在黄金分割的位置上,双人以上的镜头则总是遵循或前或后、或高或低,要么干脆并列平置的均衡布局方式,以达成整体视觉上的赏心悦目。在这种创作方式的指导下,始终以人物为核心,尽量避免画面中不安的视觉元素,从而防止对观众的观赏心理造成干扰,影响对影片内容和思想意识的默认。简单地说,就是阻止影像的节外生枝造成叙事流的中断。
片中的运动摄影,更多的是在跟拍主人公的同时,作为展现奢华内景的一种手段。当里克穿过喧哗的大厅,来到钢琴旁制止山姆演唱的时候,摄影机的运动只是呈现了里克走过大厅的动作,除了视觉上的舒适之外,基本上也没什么更多的含义,如果换成一个平摇镜头也可以完成镜头在叙事上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摄影机只是作为“上帝的眼睛”存在,无所不知,无处不在,冷漠的旁观摄影机前发生的一切,却缺乏一种对待影像——现实世界的态度。仅就“态度”的缺乏这一层面来说,这也曾是旧好莱坞摄影艺术与新好莱坞摄影艺术之间一个根本的区别。平稳、含蓄是它最大的特征,与此同时,在起幅、落幅间寻求达成重新构图的种种可能,继续完成叙事的动作。
从客观上来说,造成这样一种状态的基本原因同旧好莱坞的戏剧式用光原则一样,是受到当时电影摄影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例如,当时的摄影机并不是一种“解放”了的摄影机。被普遍使用的米歇尔摄影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操作系统,沉重笨拙,难以移动,取得灵活的视角或者自如的运动对它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而当时用来拍摄《乱世佳人》的由伊斯曼·柯达公司和特艺色公司合作开发的基于“三色印染法”技术的彩色摄影机一次就要安装三条胶片,其庞大的规模更是可想而知。1927年声音引入电影以后,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摄影机的机械噪音。当时的摄影机被放置在一种被称为Icebox的隔音间内,只能隔着一层玻璃进行拍摄,以免对录音工作造成影响。这些原因,都使得电影的拍摄必然被限制在一个狭窄,同时也充满了假定性的空间——摄影棚之内。摄影艺术,这种当时进行在一个设备庞杂的“照相馆”内的活动,被斩断了一门艺术与它所依附的生活之间必要的联系,从而失去了其称之为“血源”的现实生活。
这种电影技术上的桎梏,在不久之后有了种种的突破:1934年装有消声装置的米歇尔NBC摄影机上市,摄影机离开了隔音间。然而,这些电影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给好莱坞摄影艺术带来更多、更深层次的改变。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摄影技术、摄影师与好莱坞工业体系之间的内在关系。
以商业利益为核心的好莱坞大制片厂制度,构成了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面,出于对商品(电影)质量的高度重视,好莱坞向来都是热衷于电影技术的进步,推动技术进步是它的一个根本传统。而我们所要探讨的摄影师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艺术,则是好莱坞工业当中的一个结点,一道工序。在好莱坞这个分工明确的体系内,除了极少数大师级的人物可以去开创新的手法、新的表现方式外,绝大多数摄影师的责任更多的是保证每一个镜头的曝光准确,每一个明星的美仑美奂,很难在影片叙事、视听风格上提出自己的建议,制片厂也根本不可能给他们那样的权力。制片厂花钱雇佣他们,只是使用他们的摄影技术,高质量地完成拍摄工作。创作空间较狭窄的他们,与其说是电影摄影,不如说是图片照相,只好逡巡于摄影技术这一“过于简单”的层面,并形成了好莱坞电影摄影艺术独有的技术美学、技术流派,而对于造成这一切的好莱坞制片体系则是颇多微词,一些有才华的摄影师更是在一些公开场合袒露了对“明星制”等众多体制的不满。
另一方面,当时好莱坞电影的创作观念,以及意识形态也不可能为摄影师提供除了拍摄漂亮的画面以外更多的创作空间。在旧好莱坞时代,类型电影创作的主导观念一方面在叙事上采用了戏剧性的模式,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一方面在视听语言上基于大卫·格里菲斯、爱森斯坦等电影先驱所开创的蒙太奇理论。这种戏剧模式从银幕上的反映,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独立的空间里展开的三分钟一场的情节短剧,高度依赖场面调度和人物表演。而影片的蒙太奇结构实际上是将蒙太奇理论简单化、极端化,只是完成着时空上一种封闭的线性因果关系。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当时通用的所谓“三镜头”法。在遵循180度拍摄轴线的基础上,由一个人物关系镜头、两个人物近景或是特写构成一个镜头组,然后再由一个又一个的镜头组一环扣一环地彼此衔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视听“流”。这个“流”客观上是由后期制作的剪辑工作完成的,因此,摄影艺术也就只能褪减为在拍摄期完成一个又一个镜头的收取。衡量摄影工作的好坏,是能否精准地完成底片的曝光,保持每个镜头影调的华丽和细腻,而非对视觉语言更深层次的建设性贡献。
这种建立在戏剧性叙事模式上封闭的视听流,是旧好莱坞电影强烈追求电影商业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的目的不是呈现现实生活的真相,而是创造一个90分钟的银幕幻梦,完成对每一个电影观众的精神抚摩。人们必须在这条封闭的只有一条出口的视听流的结尾处,得到一个“生活是美好的”、“人生应该是有意义的”或者诸如此类的思想结论。众所周知,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产生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经济的大萧条时代,失落的人们纷纷涌入影院,寻找心灵的慰藉。作为梦幻工厂的好莱坞从那个时代开始就一直呈现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企图,主观上是供求关系使然,客观上,则是作为美国文化精神领域的支柱性产业不能回避的责任。
类型化的商业艺术观念,强烈的意识形态企图,以及这一切所依靠的对技术演进的热衷,使好莱坞电影在它的黄金时代呈现了一种“零风格”的状态,其中摄影艺术的境况也就可想而知。在养成注重影片技术质量、推动技术应用的工作传统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强硬地封闭在一个僵死的框框当中。摄影师们的工作几乎只是按照既有的教条和方案来实施,而丧失了摄影艺术原本应有的创造性。高度发达的专业化技术优势与僵化陈腐的艺术气质并存,几乎是它发展到后期一个必然的宿命。
摄影艺术在战争以及战后时代的改变
是战争改变了好莱坞。
就像战争总是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诱因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动摇了好莱坞所创造的一切,促使它顺应时代的潮流,开始改变,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艺术观念上。
战争首先改变的是人们对影像的一贯印象。电影院里,每天都在上映的新闻纪录片晃动不安,充满了战壕里惊心动魄的气息。这样的影像推翻了以往旧好莱坞经典电影中四平八稳的世界景象。这些肩扛手提,用生命换来的镜头蕴涵着一种摄影棚里无论怎么精心都打造不出来的真实感,人们意识到,这才是“现实”。
由于大量的16毫米摄影机、8毫米摄影机(尽管这个时候还无法实现同期录音,只是摄录单一的影像画面)出现,为电影工业介入到战地采访、军事情报等方面工作提供了技术条件。同时,美国军方与好莱坞的大范围合作,使得为数众多的好莱坞电影工作者加入到战况新闻片、军事宣传片等纪录类型影片的拍摄工作中。这使得他们获得了以往在摄影棚当中无法获得的工作经验。
这些人当中,不乏约翰·福特、约翰·休斯顿、威廉·惠勒这样一些大导演。在他们以后的创作中,不同程度地都体现出了战争经历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利用隐藏的摄影机去记录军人们……讲述他们的绝望、失掉战友的悲伤、失眠、梦魇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注:[美]理查德·M·巴萨姆(Richard M.Barsam)《纪录与真实——世界非剧情片批评史》,王亚维翻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39页,原文是对约翰·休斯顿拍摄的二战纪录片《把这里点亮》的评论。),这在以往的好莱坞电影创作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后,一些具有社会意识的电影工作者融合了纪录片的写实主义和传统影片中的戏剧性叙事手法,开创了一种被称为“半纪录片”(Semidocumentary)的新类型电影。虽然这种类型昙花一现,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仍然对很多影片的影像处理方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像约翰·休斯顿的《夜阑人未静》、伊利亚·卡赞的《码头风云》以及希区柯克的《伸冤记》等影片都是在这一新“类型”的影响下出现的佳作。其影像风格和拍摄手法表现出明显的向纪录片靠拢的趋向。
实际上,这种“真实”对“虚假”的冲击,不光是在电影领域,而是在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的领域。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人类长期以来所相信的那样一个美丽的神话世界陷落了。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才是生活的真实境况?
在电影领域,这种反思具体表现为战后一次次改变电影历史、彻底更新电影创作观念的电影运动。4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50年代后期发轫的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都是以反对虚假的传统电影为最初的纲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所反对的“白色电话片”,法国新浪潮反对的精致的法国传统电影,都是一种与旧好莱坞电影相似的“片场”电影。于是,意大利人“将摄影机扛到了大街上”,法国人则抛出了“作者论”。这些电影运动对旧电影传统的改变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因为他们不仅颠覆了传统的电影制作方式,更改变了电影的语言,改变了电影的影像构成。他们倡导影片的纪实性,倡导“长镜头理论”,力求镜头的时空完整,反对滥用蒙太奇剪接,讲求镜头内部已有的故事性,意即生活本身所蕴涵的意味。他们尊重并追求对生活中具体的个体存在的重视,反对制造虚假的梦幻。
年轻影人的创作和主张得到了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持。更轻、更灵活也更精巧的摄影机(注:1947年由法国爱克勒尔(é clair)公司设计生产的卡米弗莱克斯(Cameflex)型摄影机以其重量轻、精度高、使用灵活的特点在欧洲、拉丁美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在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中发挥了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出现了,特别是在50年代末期便于携带的新型磁带录音机——纳格拉的应用,使得电影创作者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庞大复杂的技术设备对电影艺术的桎梏,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机动灵活地从事电影艺术的创作。这些进步大大拓展了电影语言的革新,以及新的思想内涵的产生。《偷自行车的人》当中,摄影机所摄取的战后意大利贫瘠的城市景象;《精疲力尽》当中充满主人公内心情感的主观视像,可以说,新电影观念带给观众的感受丰富多彩,具有意想不到的张力。实景拍摄、自然光照明、灵活的摄影机运动、多全景少特写等全新的摄影艺术创作主张使新电影呈现了更多对生命个体的关怀,少了虚假的刻意,从而形成战后电影时代最进步的影像力量。
从前卫的欧洲发起的这一系列电影运动,很自然地波及到了大洋彼岸的好莱坞。然而,在那里,却没有像在欧洲大陆那样迅速掀起新电影的浪潮。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好莱坞商业电影体系的坚固。这种电影形态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已经深深同娱乐市场、社会文化融合在一起,很难轻易颠覆。面对新电影观念的冲击,它表现出了欧洲同行不曾具有的耐力。
即便这样,旧好莱坞的商业体系还是遇到了巨大的冲击。电视的普及使得电影业面临大规模的观众流失;反垄断法案对大制片厂的发展提出了诸多限制,观众群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看电影、电视长大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逐渐取代文化水平不高、经济拮据的失业贫民,成为最大的观影群体。特别是电视台播出的大量来自欧洲的电影作品,使他们深受战后欧洲进步电影观念的熏染。他们对电影更懂行,要求更多,口味更高,古典时期的那种好莱坞电影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面对这些,好莱坞秉承了一贯的思维方式,首先想到的是利用电影技术的进步、投资成本的加大来维持日渐缩小的电影市场,而没有对电影体制、电影观念做任何的改进。这一时期,新型的彩色胶片、宽银幕电影设备、立体电影、汽车影院纷纷出台,笼络年轻的电影观众。从战后一直到60年代新好莱坞电影的兴起这段时间,摄影艺术除了这些必然的技术进步,其他的,实在是乏善可陈。
这个中的原因,恐怕我们依然要回到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上来。战后的美国,作为战争最大的赢家,在文化上,僵化保守,50年代好莱坞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就是最好的例证。面对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它非常担心自身也出现类似的社会变革和欧洲式的精神危机,从而努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自己的固有传统和一贯的美国神话。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它非常在乎好莱坞这样一个意识形态阵地的纯化。在这种背景下,要求好莱坞迅速响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召唤,开始一场电影艺术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经过10多年的压抑,直到60年代美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文化冲突,一切才开始有了巨大的改变。
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
——新好莱坞电影中的摄影艺术
历史行进到60年代,过去10多年里费尽心机的粉饰和压抑,已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社会深层的矛盾,一时间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动荡。经历了罗斯福新政和二次世界大战的老一代美国人与电视机前长大的年轻一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新好莱坞电影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很自然,其中必然蕴涵着强烈的反传统电影的意味。它不仅冲击了传统的电影体制,更改变了电影创作的观念。60年代的最后几年,被称为是美国历史自独立战争以来最黑暗的时代,然而,也是在这几年,出现了自40年代末以来某些最独创的美国电影。(注:转引自[美]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周传基、周欢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1967年新好莱坞的开山之作《邦尼和克莱德》(导演:阿瑟·潘,摄影:伯纳特·加菲)问世,使美国观众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随之而来的《毕业生》(1967年,导演:麦克·尼克尔斯,摄影:罗伯特·L·舒尔蒂)、《午夜牛郎》(1969年,导演:约翰·施莱辛格,摄影:阿德姆·霍兰德)、《逍遥骑士》(1969年,导演:丹尼斯·霍泊,摄影:拉兹洛·柯华克)等一系列影片也是深受好评。这些影片带给观众全新的视听感受,针对题材和手法的不同,它们的摄影艺术明显向来自欧洲的新的创作观念靠拢,更清新、自然,也更个人化。
自然光照明在这些电影中被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主流,摄影机也更加灵活。尽管像伯纳特·加菲、罗伯特·L·舒尔蒂这样的人是来自旧好莱坞时代的摄影师,但由于新一代的导演们摆脱了大制片厂的束缚,有着明确的艺术要求和个人倾向,对影片拍摄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控制能力和控制欲望,所以他们还是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创作状态。而对于《午夜牛郎》和《逍遥骑士》的摄影师来说,则根本就是与新导演们一拍即合,因为他们大多有着相似的背景或艺术观念。
这一代年轻的摄影师,把握着“解放”了的摄影机,徘徊在城市的深处,游荡在公路上、乡村中。摄影机就像他们的眼睛,当他们凝视生活的时候,呈现出的是对待生活真挚的诚意和那个时代年轻人特有的浪漫。正是由于摄影机的“解放”,使得这一时期的摄影艺术在用光上、构图上产生了同旧好莱坞时代摄影艺术的根本不同,完成了由“戏剧光效”向“自然光效”,从“摄影构图”到“运动取景”的转变。
完成于1969年的《逍遥骑士》,被认为是新旧好莱坞电影创作的分水岭,带来了美国电影的深刻变化,同时也突出地表现为电影摄影艺术观念在上述两个方面的转变。这其中,摄影师拉兹洛·柯华克功不可没。这位1956年从匈牙利事件中逃出祖国的艺术家受过良好的电影教育,有着丰富的拍摄纪录电影的工作经验,并深受战后欧洲电影的浸染。他为影片提供了一种轻松、随意、青春的影像风格,大量公路上自然光效的运动镜头,真实地再现了60年代崇尚自然、渴望回归的嬉皮精神。
自然光效的创作观念可以说与戏剧式用光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它讲求真实再现客观环境的光影效果和时空特性,强调光源的合理性,特别是光线在色调、强弱、形态、质感等方面的真实。人物造型上,自然光效追求真实反映现场环境中人物的影调状态,力求朴实自然,不露痕迹,反对刻意的修饰和突出。影片《逍遥骑士》的绝大多数场景是在公路上,摄影师将大自然的壮丽景观以及丰富的光影变化尽收眼底,充分表达了自然光效的魅力。影片的影调构成非常简单,就是两个骑车人漫无边际地在公路上行走着,他们身上、脸上的光影变化完全取决于自然的变化。最有意义的是,我们在这些镜头中看到:摄影师对这种光影变化的捕捉蕴涵着主动的心理意念,它能动地表达出对自由的赞美。
正是这种主观的意念,使摄影师得以摆脱旧好莱坞时代类似技术员的尴尬境地,而真正参与到影像的创作活动中。旧好莱坞时代,摄影艺术所遵循的构图上的均衡、运动的平稳,特别是面对现实生活的“零”态度,在这里也被完全打破。当摄影机在《逍遥骑士》中大量跟拍两个主人公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参与其中的感觉,仿佛也是其中的一员,在永不到头的公路漫无目的地闲逛。画面和核心不再是影片的人物——明星,而是呈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许多镜头中,影片的主人公只是浩瀚的自然景观里两个很小的点,传统创作中对构图的刻意经营变为真实环境下对人物状态的纪录。没有了古典意义上的构图,只有运动中的取景。由于影片的创作不再按照视听“流”的方式,而是采用了更开放、更随意的处理方式,镜头随意、自由地组接,甚至摄影车与演员所驾驶的摩托车之间一次简单的换位,就轻松地改变了轴线的方向,传统影像上180度轴线的限制形同虚设,这也使摄影机获得了另一个层面上的解放。这种“解放”不仅是摄影技术的进步(轻型摄影机的应用、同期录音的可能,以及高感胶片的发明)带来的,更建立在对电影本体的重新认识之上。对电影本体的回归,构成了战后新电影变革的理论核心和观念基础,也最终使得现代电影的影像构成显现成今天的这个样子。而新好莱坞的电影青年们是美国电影中最早也是最主动的实验者/实践者。
实际上,与《逍遥骑士》的摄影师拉兹洛·柯华克有着类似的背景,特别是纪录片工作背景的新一代电影工作者很多,这也是他们的一大特色。很显然,这使他们的素质与那些在旧好莱坞时代片场里成长起来的摄影师迥然不同。他们有的来自欧洲,有的参加过学生运动,拍过纪录片。他们当中有导演,也有摄影师,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像后来非常著名的摄影师戈登·威利斯(弗朗西斯·F·科波拉的摄影师,凭借《教父》一片广受赞誉)、维蒙·齐格蒙(1956年同拉兹洛·柯华克一起离开匈牙利来到美国,拍摄过《猎鹿人》、《第三类接触》等著名影片)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纪录片的创作。而马丁·斯科塞斯更是为“直接电影”运动的重要作品——纪录片《沃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担任剪接师,并曾于1970年和他纽约大学的师生们共同拍摄过反映学生运动的纪录片《街道》。他于1973年拍摄的《穷街陋巷》(摄影:肯特·沃克福德),不仅主动寻求自然光照明,还大量使用肩扛手提摄影机的纪录电影拍摄方法,与直接电影的影像风格如出一辙,充分表现了生活在贫民区的人们的生活现状,真实感人。除此之外,到了70年代,像西班牙的阿尔芒都等一些在欧洲已经颇具盛名的摄影师也来到好莱坞,为电影创作带来了欧洲更前卫的摄影理念。他们更大胆地运用自然光源、有出处的可信光源,使用更小巧的照明设备、高感胶片。比如阿尔芒都在影片《天堂岁月》当中创造了著名的magic time,将自然光效的运用推向了极致;又在其他作品中使用手电、家用照明等设备,为影片营造真实可感的生活现实。这些创作实践,也深深影响了好莱坞后起的摄影新秀。
新好莱坞?旧好莱坞?或者仅仅是好莱坞?
无论年轻的导演们如何在投资、制作等环节成功地摆脱了好莱坞大公司的控制,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很好地解决一个问题:影片发行。只要他们希望成功,渴望被更多的观众认可,就无法回避大制片厂强大的发行放映能力。好莱坞很快抓住了新电影的这个弱点,开始将有前途的电影新人笼络到自己的门下。于是,在最早发起运动的群体中,除了个别幸运者,或是善于妥协的人,大多数新好莱坞的发起者都渐渐淡出了。70年代迅速崛起的电影小子(注:指以乔治·卢卡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弗朗西斯·F·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等人为代表的由电影艺术专业学校毕业,进入电影行业的电影工作者。)们,则几乎从一开始就抱着被好莱坞承认,并最终为大制片公司工作的目的。毕竟,商业系统能够带来的好处太诱人了。
六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冲突,以及漫长的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社会开始沉静下来。当年踊跃的投身电影变革的电影小子们也在好莱坞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新的传统。摄影艺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真实的光源 + 主观的创造”这一观念。在尊重生活真实的同时,强调艺术化的处理,纯粹的自然主义退出了舞台。不可否认,这确实是摄影艺术的进步,但另一个层面上,似乎也预示了某种危险。在随后的日子里,当新好莱坞在影像上的创新、在叙事语言上的拓展被吸收、消化、改变以后,对电影技术的苛求再度浮出水面。更具技术意味的斯坦尼康(Steadicam)取代了原本的肩扛手提,在保持摄影机自由运动的同时,回归了旧好莱坞讲究影像质量、追求技术美感的传统。更新、更好的胶片、摄影机、光学镜头、照明灯具纷纷出现,它们在方便摄影工作的同时,也形成着日益繁复、庞大的技术体系。新兴的计算机CG技术和数码影像技术,在电影小子们掀起的科幻片热潮中迅速发展,成为更新一代处理影像的技术,并将彻底改变自电影诞生以来的影像观念。
短小精悍的青年摄影组不见了,好莱坞的新宠儿们坐在椅子上指挥着他们终于庞大起来的班底,开始打造属于他们这一代的银幕神话和黄金时代。一切都仿佛历史的一场玩笑,当新好莱坞电影革命渐渐平息的时候,时间似乎又回到了它开始的地方。关照今天的好莱坞摄影艺术,新的传统和教条已经被确立起来,在任何一部所谓的大片当中都可以找到。相反,作为电影艺术赖以维生的根本性艺术元素——摄影艺术,在语言上的进展甚微。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种与黄金时代的好莱坞非常类似的情形。当初造反的快感,在商业化电影工业体系巨大的胃口中溶解、消化。当美国走出整个社会冲突的阴影,再度成为全世界的某种楷模、某种梦想的时候,好莱坞电影又一次幻化成表现美国精神、美国文化优越性的窗口。它的形象可以不再是西部片、歌舞片,但可以是动作片、科幻片。它提供的不仅可以是抚慰,还可以是鼓动和勾引。在电影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里,并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就能够说明问题。摄影技术的进步只能为摄影艺术的发展创造条件,却不能根本性地决定艺术本身的拓展。在这里,更多的是体现了科学技术、历史发展与意识形态企图这三者之间的牵制与互动。摄影从它应用到电影工业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工业和艺术的结合体,体现着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里的追求,这是这门艺术先天的矛盾,也是它的宿命。
标签:好莱坞论文; 摄影艺术论文; 摄影论文; 观念摄影论文; 摄影镜头论文; 运动镜头论文; 逍遥骑士论文; 北非谍影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