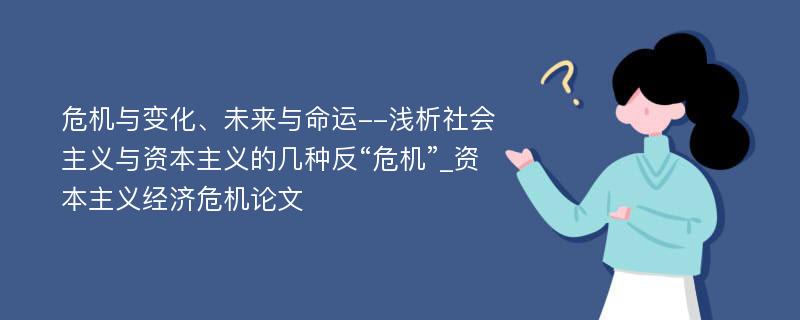
危机与变革,前途与命运——简析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几次反“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几次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前途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0)01-0071-06
始于2008年下半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成为考验各类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的试金石。这次金融危机的广泛性、深刻性和冲击性,引发出人们在历史与现实层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以及在两种制度主导下不同发展模式所遭遇的几次“危机”与“变革”方向的思考。深层次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反“危机”导向及其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调整、变革与发展规律,进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的认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罗斯福“新政”:资本主义反“危机”的成功案例
1929年发生的“大萧条”是“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首次经济危机。它以华尔街股市大崩溃为先导,随之出现大量银行倒闭,千百万人的积蓄付诸东流,数千人跳楼自杀。美国随之步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生产出现严重过剩,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销毁过剩产品,86000家企业破产,失业率高达25%。危机很快从美国扩展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从金融危机转变成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场危机被史学家称之为惊天动地的大灾难,世人惊呼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1](p.683)何处去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政治发展前途问题:德国走向纳粹主义,日本走上军国主义,二战一触即发,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
具有戏剧性历史意义的是,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时正是苏联崛起之时。在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时,苏联经济却“安然无恙”,成为“一枝独秀”。1921年,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1927年逐步取消新经济政策实行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政策。1928年是苏联开始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从1929年始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增加了3倍,1938年,苏联经济总量在全球所占比例,已从1929年的5%跃升为18%。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在对比五年计划和大萧条时指出:“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大增。在西方经济确实是一团糟的同时,……苏联从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它们一者衬托着另一者”[1](p.683)。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敏锐地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现象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中。
目睹苏联计划经济成就和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当时出现了一个“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的特殊现象:1930—1935年间,西方著名的政界、经济界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一时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计划经济“转变为模仿”。
正是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参照系。借鉴其成功经验,资本主义起死回生。1932年,美国民主党人罗斯福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职,他上台即担当重振乾坤、为民请命重任,实施“新政”。1933年,罗斯福按照苏联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作法,设置联邦计划机构。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新政”首次大规模尝试实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反“危机”的方法,它摒弃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原则,在宏观层次上运用国家政权干预经济;在微观层面上较大地调整产权关系、生产方式和生产受理体制。英国学者帕克在《超级大国——美苏对比》一书中承认,苏联的全面计划经济,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了自由派资本主义的救星,在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年代,促使西方社会放弃对传统派自由市场学说的信仰。
受惠于苏联计划经济的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实践,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的成熟,推动了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新政”是一场包围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帮助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渡过了空前大灾难。
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社会主义反“危机”的惨败案例
罗斯福“新政”之后约50年,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敏锐地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以说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很相似。两大方案都是为应付令人痛苦的危机——美国胡佛时期的大萧条和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而设计的。两大方案都是由不是来自下层、而是上层、来自国家上层的领导人进行的。”[2](p.774)他说,对罗斯福来说“是幸运的”,“新政”成功“结束了大萧条噩梦”,挽救了资本主义;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则“是不幸的”,他造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
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创了一种国家制度和经济运行模式,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制度的探索具有划时代意义。该模式一开始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它帮助苏联创造了经济奇迹,改变了苏联的面貌,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和军事强国。斯大林去世时,丘吉尔曾这样公正地评价过他:斯大林接收苏联的时候,苏联是一个扶着木犁的国家,在他告别人世的时候,苏联却成了一等强国。
诚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资本主义大萧条之际显示了巨大的优势,然而,任何优势又是相对的。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摩根索曾说过,当一个国家发现它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处于力量巅峰时,特别容易忘记这一点,那就是一切力量都只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应该明白,那种曾经拥有的力量优势很可能由于自身的愚蠢和疏忽而丧失掉。很不幸的是,后来苏共历届领导人,真的不懂得过去“曾经拥有的力量优势”仅是“相对而言”的道理,他们把过去曾经取得巨大成就的计划经济模式不合时宜地、不顾时空条件地推到极端,将之视为普遍真理而不加以改革,致使该模式高度集中,计划无所不包,所有制单一,两个平行市场封闭,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与世界市场割裂。造成管理落后,经济体制活力衰退,资源配置不合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优势耗尽,逐步进入“停滞的年代”,经济严重下滑,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1950年至1970年的5%至6%下降到1971年至1975年间的3.7%,进而又下降到1976年至1980年的2.7%。日本超过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他上台时,苏联遭遇了至少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危机,戈尔巴乔夫“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推行“新思维”。关于戈尔巴乔夫其人其事及反“危机”的功过是非,迄今为止,唯有基辛格评价最为全面、深刻而透彻。基辛格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是自列宁一脉相传下来的第七任苏联领袖,与历代苏联领导人不同,戈尔巴乔夫属于另一代人,他缺乏前人的强悍作风,不足以担负化解苏联危机的角色。他虽然能发现问题所在,却缺乏创意与技巧去打破根深蒂固的僵硬局面。他仿佛是关在完全透明,却打不破的玻璃窗内的人,戈尔巴乔夫可以清楚地观察外面的世界,却受到室内条件的局限,没办法确切了解他所见到的景象。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找到答案,他命中注定要替这个帝国送终。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届代表大会上,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摒弃。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已经远超过调整苏联既定政策符合新现实的步调,完全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列宁主义正统以及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不仅使苏联失去历史上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也让苏联局势中固有的困难加剧。戈尔巴乔夫押赌注自由化,必然失败。戈尔巴乔夫不明白这则等式,叶利钦则了然于心。戈尔巴乔夫要求苏联进行做不到的改革,加速推动了他代表的制度的灭亡。他的改革是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改革,他摧毁了共产党,推动了把他送上权力宝座那种制度的覆亡。然后,数个世纪辛苦建立的帝国,也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瓦解。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造成了苏联帝国崩溃之速度甚至快过当年崛起之势。作为一个西方著名的政治家,基辛格无不惋惜地评价道:“不到十年,东欧附属卫星国家解体,苏维埃帝国土崩瓦解,几乎把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侵吞之所有权益,全部吐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3](p.706)
三、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反“危机”的卓越案例
如同世界上任何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及其发展模式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中国模式”,也是在中国面临危机、寻求变革中产生的。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向何处去?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事”盛行,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徘徊;与此同时,面对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严重滞后的国际形势,中国与世界潮流的“时差”日益扩大。面对上述严峻形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卓越的政治大智慧,力挽狂澜,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发展方向上作出重大的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邓小平告诫全党和人民:“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p.150)“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p.370)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实力提升最强的纪录,“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国家成就的篇章”。[6](p.10)历史表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从危机中奋起、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国道路”是在不断反“危机”中形成的。在新世纪进入第十个年头之际,让我们回望过去30年发生在世界与中国的几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就不难发现,反“危机”贯穿整个“中国道路”前进的历程:1989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中东欧轰然崩溃,执政的共产党下台,而早在中东欧剧变的11年前,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果断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使中国命运实现了伟大的转折。1991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解体。1992年,面对国际浊浪、西方制裁并欲改变中国的图谋,以及国内针对改革的争论、质疑之声,邓小平就世界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这些谈话是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奠基之声。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成为“中国模式”最后超越“苏联模式”的重要标志。2008年秋,国际金融危机开始肆虐全球,中国共产党人以卓越的政治大智慧化解危机,中国在反金融危机中巍然挺立,赢得世界称道。
四、当前全球反“危机”导向
从表面看,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严重弊端所致,实质上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经济周期性折磨”、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模式误导的结果。当前,全球反“危机”尚在继续,新一轮资本主义改革方向有待继续观察,有几种倾向值得关注:
(一)罗斯福“新政”回归,凯恩斯主义复活,国家干预重新回潮
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纷纷对金融机构实行国有化,政府直接介入金融系统,加强监管力度,刺激经济增长。英国《泰晤士报》称,曾经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最资本主义化的政府,已经决定铲除这个国家最大、最重要的私人金融企业老板,以政府任命的官僚取代之。强烈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里根过去曾说,政府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现在美国人却说,市场是个问题,政府是解决之道。30年来,一向高举新自由主义大旗的美国政府终于对市场伸出了“看得见的手”。美国《新闻周刊》撰文说,全球资本主义开始进入更多管制的新时代。
(二)“社会主义”一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危机”给西方世界带来思想上的强烈震撼。各国反“危机”导向,引起世界经济学家、金融家、政治家的评论如潮。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说,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迎来美式社会主义。欧元太平洋资本总裁施夫说,美国救市行动代表着这个国家迈向社会主义最大的步伐,标志着美国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自由市场的终结。前德意志银行高官罗杰·依伦伯格评论说,美国政府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历史性反应将我们置于一个几代人也没有看清的一个位置:我们已经正式地跨越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红线。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发表这样的评论:正如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一样,美国也在建立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三)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重视
饶有兴趣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再次走红。德国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克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马克思理论的某些内容并非是错误的。《泰晤士报》报道,这次金融危机,资本主义摔得“灰头土脸”,反倒是倡导共产主义的马克思重新引起世人的重视,而他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也再度走俏。在西方,《资本论》变成了畅销书,许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遭受损失的投资人,想从《资本论》中找到资本主义失败的根源。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受到高度关注
美国有经济专家指出,这场危机明显地损害了美国一直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金融危机促成英美模式与中国模式势力消长。牛津大学教授阿什在英国《卫报》撰文说,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正被乌云笼罩,与此同时,中国实行的中央控制经济加市场经济的混合模式看来前途更为光明。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蒂·哈拉比最近指出,中国对世界经济发挥着“稳定器”作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不是一种偶然或无法解释的现象,而是更多得益于其缜密的经济和社会规划,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保证了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资本主义却还不停地对环境和资源进行破坏。法国《论坛报》撰文指出,社会主义救了中国。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重大举措投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并给予积极评价。
五、启示与思考:若干重大政治判断与思考
“千古兴亡鉴青史”。回顾、观察、对比20世纪和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先后出现的若干重大“危机”与反“危机”,不难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特定阶段出现的各类“危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危”与“机”并存,关键是在危机中,能否把握住正确的航向,方向维系其前途和命运。
(一)资本主义反“危机”始终坚定地捍卫着资本主义制度
第一,罗斯福“新政”是坚守资本主义阵地、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新政”在资本主义经济肌体内部进行了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突破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标志着资本主义脱离了19世纪传统的自由放任形态,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次重大转型。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表明资本主义实现了从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转折。第二,始于2008年下半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并将继续对“冷战”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自身缺陷与利弊进行重新审视、反思。资本主义将面临新一轮重大改革,将获得新的变革与调整。资本主义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反思与纠正。就像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改革后一样,资本主义将以一种新形式继续生存下来。第三,资本主义在反“危机”中,程度不同地借鉴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对其自身制度的根本否定。罗斯福“新政”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意味着美国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目的是为巩固、完善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此次反“危机”中,“社会主义机制”,国家干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受到重视,也不表明西方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为了更加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发展模式。
(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教训沉痛而深刻
如果说罗斯福“新政”是留给历史的一次成功的资本主义反“危机”案例,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留给世界社会主义的一次失败的反“危机”案例。戈尔巴乔夫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其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方向的政治改革造成苏联局势全面动荡,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一个对世界政治经济、世界格局和西方资本主义产生过重大而积极影响与作用的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有着79年历经磨练、具有世界影响的政党顷刻崩溃,令人扼腕长叹。从基辛格对戈尔巴乔夫所谓改革与反“危机”的精辟分析与惋惜之情中,不难解读出基辛格这位资深政治家的弦外之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可以改革的。历史永远不能改写,但戈尔巴乔夫反“危机”失败的沉痛教训值得世人永远铭记。
(三)在全球视野中回顾与瞭望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坚定捍卫其基本制度进行改革的卓越范例。面对“中国模式”、“中国奇迹”,近年来国外一大批致力于“读懂中国”的“中国观察家”悄然涌现,他们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反“危机”与改革的精辟观点。第一,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同于苏联,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沈大伟、牛津大学教授亚当·罗伯茨、美国学者布鲁斯·吉利、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陈有为、日本《产经新闻》驻中国局长伊藤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弗里德曼等认为,为中国指引前进方向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仔细研究并总结了苏联瓦解的经验,中国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而是提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二,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政治稳定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前提。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和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联邦议会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卡特·冯·克登等认为,对中国来说,经济和社会转型必须保持政治稳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起着特殊作用,它为推行有效的经济改革确保了稳定的政治基础。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中认为,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上的,“两者的合力”既促进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政治稳定。第三,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使中国获得成功。法国前驻华大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康拉·德赛茨和新加坡学者认为,中国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能够平安地与资本主义市场这只“狼”共舞,并创造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使全球惊讶与羡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又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长处;既以博大的胸襟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既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又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有一个“聪明而又富于实践精神的政府”和“坚强的领导层”,政府“可以促进市场经济机制的完善”,这个特征已经为“成功指导中国经济转型的政府记录所证明”。
(四)一部人类历史是战胜各类“危机”的历史,反“危机”的方向维系其前途与命运
“危机”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与变革的前提。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都要历经反“危机”、调整、改革和完善;任何一种改革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反“危机”没有终点。第一,试图将一种制度与模式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推向全球是行不通的。斯塔夫里阿诺认为,世界历史的趋势是向全球多样化而不是同一化,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会模式。他说:“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幸运的是,世界历史的趋势是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1](p.907)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苏联解体让美国感到自己是个“胜利者”并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世界”。现在大家明白,这个规则并不起作用。第二,维系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所有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没有一个尽善尽美。一部人类文明史充满着繁荣与危机交替的场景,历史证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都要经历改革、调整与完善,并接受历史的检验与考验。第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及其主导下的发展模式都会遭遇曲折甚至危机,都要历经调整与变革,但改革的方向却维系其前途与命运。罗斯福“新政”是完善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当前资本主义反“危机”中,程度不同地借鉴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对其自身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的根本否定,而是为了更加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发展模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与方向的改革,其教训沉痛而深刻;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维护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卓越范例。“中国模式”历经考验,但并非完美无缺。“中国模式”的生命力永远表现其具有变革、发展和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
标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美国金融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全球金融危机论文; 美国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罗斯福新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