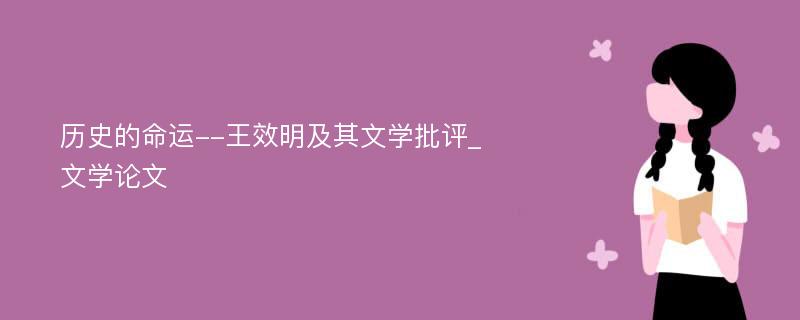
历史的宿命——王晓明与他的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宿命论文,历史论文,王晓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批评家并不比作家简单,如果是一位出色的批评家的话。赵园就曾为文学批评做过一种描绘:“批评也是一种对世界的发现,对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尤其对于艺术世界自身规律的理论发现,——丝毫没有什么卑微。批评与创作在从事精神创造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这是那些有分量的批评家对世界的一种坦城的独白,在理论思辨的世界里,对世界的描述,对艺术与人生的理解,西洋人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诸多风格,且对文坛影响深远。与之相比,中国的大多数批评家们,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我们一向缺少思想深邃的批评家,从五四到今天,影响文坛的批评文字,主要还是出自风靡文坛的作家之手。鲁迅、茅盾、胡风、刘西渭乃至当代的王蒙等,其批评文字有着鲜活的价值。如果要写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你会惊奇地发现,至少在本世纪上半叶,优秀的批评文字,很少来自高校的学人,而恰恰是来自那些集作家学者于一身的人们。中国的批评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还十分弱小,文人们的智慧大多留在艺术形式中,很少驻足于思辨的形式里。批评的光辉被五光十色的文学景观遮掩着,许多年来,世人一直把它置于一种属于“他在”的领域。理解批评并不容易,直到今天,这种蔑视批评的观念依然残存在国人的认识中。
批评的如此艰难,倒使那些恪守批评圣地的人们多了几份悲壮。十几年来,我一直注视着批评的团体,注视着那些始终如一的堂吉诃德式的斗士们在文学世界留下的足迹。我看到了王晓明,这位与我同龄的青年学者,他的闪光的文字和忧郁的篇章,一直给我带来亲切而复杂的情感。我觉得他是当代批评家中少有的具有个性意识和精神信念的人。王晓明或许是一位不带有思辨理性意义的批评家,但却是一位值得品味的学人。他本身的崇高感与复杂的矛盾心绪,他的敏锐的、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给我们的文坛带来了不少的话题。实际上,他已成了近十年来学院派批评家的有代表性人物之一。无论你接受还是拒绝,他至少让我们感到了一种精神锐气,你必须正视他的存在,那平静得几乎没有声音但却蕴着巨大的情感潮汐的理性,使我们的作家遇到了一种不再轻松的拷问。他的颇为细腻的艺术感觉和近于苛刻求疵的神志,使批评的分量,在他的手中变得沉重了。
我最初注意到他的文章,是那篇《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在此之前,还没有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那样使我激动过。王晓明论述作家的角度是独特的,他慢条斯理的自语式的,不带华丽辞藻和理性演绎的文体的背后,常常却有着逼人的气息在突奔着。描写鲁迅心理个性的地方,在理性的层面上,他几乎没有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发现,这一点他远不及钱理群、王富仁、王得后诸人。但是他的文章却释放着一般学人少有的情感,他把人们阅读作品时的感受,颇有分寸地传达出来。这种感受并不单一地停留在自我的直观的接受过程上,而是透着理性的穿透力。他把作者的心态与自我的觉态联接起来,文章通篇弥漫着心灵感应诱人的氛围。随后读到他的《在俯瞰陈家村之前》、《所罗门的瓶子》,进一步感到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尤其是《所罗门的瓶子》,那里的层层剖析对象世界的话语方式,不仅在感知的细腻上让人赞叹不已,更主要的是灵魂解析过程的那份严峻和冷静,很是让我震惊。中国的新文学诞生以来,从来没有过这一类心理分析式的批评文字,它既不同于心理学上的感知透视,也不属于社会学式的展示。王晓明注重的是人的意识结构和心灵的结构特征。他并不过分在意艺术形式的问题,对他而言,透过艺术的生成过程,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比其它问题更为重要。他的良好的艺术理解能力,本应在解析小说文本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可意识习惯却使他把精力主要投入到作家心态的分析上。这是一条新奇的研究思路,在精神的层面,这一思路更接近于思想的批评而非文本的批评。王晓明承认自己对文学中的非文学因素的注意,超过了对艺术形式自身的分析。我猜想,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多半与他的知识结构,个性爱好,以及思想的背景有关吧?应当说,他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过程的把握是充满灵性且有力度的。当人们习惯于以先验的理性方式解析艺术世界的时候,王晓明却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从直观的感受出发,自下而上地阐释文学的现象。他的充满真诚的文字,使人对他的价值态度产生了一种亲切感。重要的不在于他展示了什么观念,而是读解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读者与文本间的奇妙的关联,被他精彩地勾勒出来。注重作家的心理个性,注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弱点,这使王晓明的学术风格转向了更切实的精神思考之中。他写鲁迅、茅盾、沈从文、张天翼等人的精神冲突,写张贤亮、高晓声、张辛欣等人的精神缺陷,在许多方面是令人信服的。从心理分析的方式切入到作家作品之中,它激活了人们感知艺术世界新的兴奋点,这似乎比生硬地搬用洋人的批评方式,更适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我从王晓明众多的批评文字中,深切地体味到他找到了自我精神表达式的快意。《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所罗门的瓶子》、《在俯瞰陈家村之前》等的问世,标志着作为心理批评家的王晓明的诞生。他的这一方法的出现,我以为是对八十年代以来批评界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贡献。
王晓明的成名之作,实际上是那本论述沙汀、艾芜的论著《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那时他已在书中显示了心理透视的某些特点。我近日翻看这本十年前的旧作,依然有新鲜之感。他的智慧不是闪现在一种理论的归纳和精神的抽象上,《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的诱人之处,在于读出了作品的个性与作家的个性的联系。他写沙汀的现实情感与价值取向,写艾芜的某些乐天精神,是准确的。他凭着自己的天赋,读出了作家世界复杂的一面,这种读解的过程,自然而然地消解了传统文艺理论某些教条的东西,使你不由得对他的书产生了一种认可的态度。尽管此书在许多方面还带有旧的认知习惯,可他却在文学批评方式的尝试上,为后来心理分析方法的出现,奠定了实践基础。我不知道他起初何以选择了这两位四川作家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两位并不复杂的作家,使他一开始运笔的时候,就显得较为自如,这大概建立了他后来文学批评生涯过程中的某种自信。他在作家作品面前,从未显出“须仰视可见”的神态,即使写鲁迅这样的人物,精神上依然显得从容。王晓明后来渐渐养成了自高处俯视众生的习惯,尽管他也承认自己的矛盾与困惑,可他批评现当代作家的那种毫不温吞的态度,如果不是建立在一种坚强的信念和自重的基础上,恐怕是不会产生的。我注意到他一再引用的鲁迅的那句话:“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的知识阶层”。这句话所生成的信念直到今天依然顽强地矗立在他的批评世界里。他后来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退化历程”的描述,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观点,差不多一直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以富于责任感的态度来看待本世纪的文学,给他的批评文学带来了十分庄重的情感。我几乎未见过他随意应酬的文字,十几年来,他的文章,差不多一直保持着这一个性。
然而王晓明给文坛提供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的东西。我觉得他对现代文学的读解,更主要是从历史主义的道德意识出发的。他在鲁迅、茅盾、沈从文、张贤亮、高晓声等几代人那里看到的,大多是“异化”的问题,是环境对人的自由心灵的压迫。他正是从外在环境如何异化人的主体世界这一角度,来考察作家的心灵困苦。例如他写茅盾的先验精神对创作的窒息,写沈从文后来独特文体的消失,写张贤亮自上鬼魂的影子,很有说服力。在这样的时候,他往往从艺术感受中走出来,回到思想、意识的解析之中。这里可以看出传统批评思维方式对他的制约。读他众多的文章,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以文学为话题,在陈述着思想史的内容。但他不像一个庸俗的社会学批评家那样机械地演绎文学,他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至少那种认真读解与不盲从的精神,让人对他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如果你读一读他写张天翼世界的文字,你会惊异于他细腻的感悟。那篇关于张贤亮的长文,语气的沉重与理性的明晰,让你对作者的雄辩的气魄顿生敬意。他的迷人的文字不在于感受艺术时的那种呼应,而在于他的批评的文体,为作家的心灵画像。那篇写高晓声的文字,其诱人之处在于勾勒了作者的精神形象,《所罗门的瓶子》在曲折多变的陈述中,为我们描述的不是艺术的图景,而恰恰是作家心灵的图景。这使他的批评文字产生了一种散文效应。他是以理论家的思维方式,完成了散文家式的雕塑人物的过程。这种从理论的角度刻画作家个性的方式,在更高的层次上,其思维方式与传统批评的感悟特征是有着深刻的联系的。王晓明把这种联系,进一步地个性化了。
王晓明的治学过程,近来越发被焦虑的沉重感包围着。无论是写现代作家还是当代作家,他常常以挑剔的目光审视对象,以致使文章透出了一股冷峻。即使是对鲁迅这样的作家,他的笔,依然不免苛刻。他对中国文人的要求也许过于求全,在他的思想深处,似乎一直渴望着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和独立品格的知识者群体的出现。这种理想主义的观念,成为他文学批评的一个参照。《潜流与漩涡》一书,就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一步步地退化着。他用一种纯而又纯的尺度要求作家,结论中的失望语气,就不言而喻了。在论及艾芜时,他曾提出了“艺术正是生根在对生活的肯定和追求当中”的观点,但他在中国文人那里,看到的健全的心态还是太少了。人文精神的变形与扭曲,处处充塞着本世纪的文学。王晓明差不多在所有杰出的作家那里,都看到了这一残酷的事实。这使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中国作家心理障碍的关注上。他过于看重人的心理冲突,对许多貌似理想的文学创作口号,保持着冷静的觉态。有些批评,也颇见功力。例如他说韩少功犯了“以意为之”的毛病,是看到了作者的弱点的。“寻根文学”缺少深思熟虑,是作家灵感式的冲动产物的结论,也很精辟。我注意到他批评张辛欣、刘索拉和残雪的文字,其中对作家弱点的估计,很有分量:“当悲观的情感过于沉重的时候,作家会不会干脆‘看穿一切’,用理智地撤回人生诺言的方式,把自己从失信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当阴郁的心境过于强烈的时候,作家会不会干脆转过身去,听凭下意识的愉悦本能,把自己引向快乐的语言游戏?张辛欣、刘索拉和残雪的小说,似乎就证实了这种可能。或是早已经看破一切而心灰意冷,或是终因为无力‘自啮’而渐趋肤浅,她们不都在有意无意地抑制和躲避自己的痛苦吗?而且,又何止是她们三个,就在其他不少作家身上,不也分明可以看到同样的抑制和躲避,同样的或者更加严重的空虚和做作吗?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灵的疲惫,一种似乎是先天性的精神的孱弱,它们足以打破一切有关文学新时代的热烈期望,我当然要深深地震惊了。”从这样沉重的语气中,多少可以看出王晓明的严峻。这严峻的背后,则是扯不断的焦虑、失望之情。几乎所有的作家,在他眼里都充满了个性的冲突和非正常情态。鲁迅、茅盾、沈从文等人的心绪的复杂因素,使他对二十世纪人文精神的变化深为忧戚。他发现了几代文人共有的心理障碍,并且在这种障碍中寻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特有规律。这样的挑剔式的视角,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启示显然不可小视。但过于看重心理障碍,而不从这种障碍生成的艺术作品中寻找人类创造精神文明的新奇精神,显然失之于偏颇。世上本没有纯粹,没有一致性。障碍是人类生存的正常的东西。人类心智活动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障碍生成与障碍克服的历史。障碍也可以产生智慧。当王晓明过分强调障碍对人的不利因素时,他实际上就开始疏远与艺术自身的距离了。不能用“泛人格化”的尺度去看艺术,艺术其实与人的心灵有着复杂的、非线性因果的联系。如,谈论张贤亮的时候,如果单纯地把作家某种心态的畸形与艺术的畸形等同起来,在方法论上就显得简单化。尽管他是从作品出来总结人的心态,但忽略心理障碍对艺术积极的影响,那至少犯了一元论的错误。人从未有过自在自为的精神状态,人们所以要创造艺术,乃因为现实有着太多的矛盾,庄子的潇洒,莎士比亚的博大,其内在因由,我想也是与内心矛盾和精神的渴望有关吧?鲁迅、周作人在苦难中的思索,那种咀嚼苦涩之果的方式,不也是生存智慧的选择?当代文学尽管在某些方面不及五四时期的文学,但在整体上表现的情态,是从五四那里延伸出来的。仅仅站在人文科学的单纯的角度去声明中国人在退化,显得过于武断,这必然走向悲观主义。历史毕竟进化了,科学哲学对当代文人的影响,人们生存空间的改变,仅仅用前工业文明中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必然出现视觉的错位。如果我们看不到王蒙、汪曾祺、史铁生、刘恒等几代人的生存智慧与对待苦难的正常态度,就看不到当代文人的某些与过去不同的优势,王晓明的文学批评中的焦虑情感,一方面给他的文字带来深沉的使命感和人格力量,但又因囿于单值的价值判断,而显得狭窄与不通达。他大约不善于从宽泛的视野中,换一种方式探讨客体,这限制了他走向博大的可能。但又因其十几年来坚守心灵的圣地,表现出顽强的个性主义情操,他的文字也因此迸放出在许多批评家那里少有的光芒。至少在对精神价值的体味的深刻性方面,他是当代批评家中较出类拔萃的一位。
他的这种个性,在鲁迅研究方面显得尤为突出。《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是迄今为止他最有分量的一部著作。他多年形成的认知习惯,感知个性,乃至哲学品味,在此书中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四十年代末出现第一部鲁迅传记以来,国内有关鲁迅的传记已有十几本之多了。但王晓明的著作,却是很有个性的一部。几十年来,我们的学者太习惯于从既定的模式出发去理解鲁迅,众多的传记中均留下了先验理念的影子。人们要么从神的角度去描摹他,要么类似郑学稼、苏雪林那样全面诋毁他。除了曹聚仁等少数作者外,传记令人失望的地方太多。王晓明着手写鲁迅的时候,中国学术界已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生活也与先前大不相同。我读他的这部传记作品时,感到其内心正经历着人生的困难时期。他比先前更具有孤独和偏执的一面。鲁迅的存在与现存生活诸多矛盾的存在,使他的精神天空布满了层层云霭。他对鲁迅的咀嚼太沉重了,已看不到多少纯学人式的静观。他陷得过深,把自己也燃烧在里面。《鲁迅传》的重要之处不在于展示了新的理念,而是他对对象世界心理冲突的详尽分析。在王晓明笔下,鲁迅的神圣的一面被更多的阴郁与悲壮代替了。他几乎撇开了鲁迅身上所有的明朗的东西,一意地钻到他内心的困苦之地。应当说,就人物精神的总体把握而言,他的感觉有许多地方是准确的,且弥漫着更深沉的心灵感应的气息。鲁迅时代的苦难与鲁迅自身的苦难,在王晓明痛楚的笔下被复原了。我感到深深的刺激,他那么残酷地经受着鲁迅曾经历的精神历程,使你感到,王晓明在对象世界的精神过程中,找到了一种深切的呼应。我记得赵园说过,她那代人的学术研究,有着太多的自我情感,他们发现了自己与现代史上那几代知识者的精神感应。王晓明这一代人,何尝不是如此?他在《鲁迅传·跋》中写道:
鲁迅的痛苦是极为深刻的,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正是那愤世嫉俗的忿懑之情,对像我这样几乎是读着他的著作成长起来的人,他的思想本来就特别有震撼力,偏偏我自己的心绪又是如此,他的忿懑就更会强烈地感染我。我当然是在描述他的痛苦,但这痛苦也是我能够深切体会,甚至是自觉得正在承担的,你想想,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写作状态中,就是思路再慢,也克制不住地会要疾书起来吧。
这样的太多的自我情感的参与,显然使作品的客观性受到了影响。虽然人们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过于囿于自我的价值偏爱,而忽略客体确实曾存在的另一方面,是不是有些过于武断?我十分欣赏他对鲁迅矛盾内心的颇有张力的描述,但他因过于相信心理障碍对人生经历的影响,而忽略了传主的精神结构与知识结构。鲁迅世界的确切性的一面,不幸被王晓明一笔抹掉了。《鲁迅传》的根本弱点在于,作者把先生的思考统统让位于那些非理性的悸动。他对鲁迅精神不确切性因素的偏爱,超过了对那些确切性因素的冷静观察。我至今也相信,如果了解鲁迅,倘不懂得他对科学哲学的偏爱,是不全面的。鲁迅的藏书中有大量的自然科学著作,他早期人生观的形成,一多半来自于他对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解。不仅社会观如此,历史观也多有这些因素的投影。请看他早期写下的《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等,其锐利之处,是一般同代人不及的。这形成了他认识论的牢固的根基。他相信理性可以穷极对象世界。回国后,他大量地购买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矿物学、生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及医学卫生等类书籍,表明他对科学理性是看重的。他晚年对植物学、生物学的念念不忘,表明他在认识论上,并不完全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你才可以理解他的杂文何以具有常人少有的理性力量,他对愚昧的抨击,对复古主义的审视,都是建立在对科学理性信仰的基础上的。他晚年购置大量的社会学著作,其中也隐含着一种理性的渴求吧?理性世界的确切性是一回事,情感体验的非理性因素又是一回事。倘仅仅看到后者而漠视前者,在我看来,至少是残缺的。王晓明在后者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亦有惊人的、颇为启示性的发现,但当他滑向灰暗的精神之谷后,是否会感到自己在偏激的路上越走越远?一味地审视作家心理障碍的一面,并不能窥见其全豹,《鲁迅传》的偏颇,恰恰体现在这一点上。我感觉到,作者在这里把自我精神情趣摧向了极致,他的情感的位移,至多不过表达了一种阅读的再度体验,却难以在理性的层面上复原传主的全貌。王晓明的众多批评文字,是不是常有这种弱点?
尽管这样,我依然喜欢这部充满激情的著作。我许久没有读过这样一部敢于直面作者弱点的书籍了。记得只有曹聚仁,曾在《鲁迅评传》中说过类似的话,但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细究。王晓明却抓住了鲁迅困惑的一隅不放,大胆地走下去,至少在一个角度上,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鲁迅的视角。全书气韵生动,一气呵成,在文字和结构上均显示出作者的才气。比起论沙汀、艾芜时的王晓明来说,这里的作者已判若两人了。我想,在这里,他的心理批评的模式,达到了透彻的地步。如果说写沙汀、艾芜时还有些拘谨,那么到了鲁迅这里,他把更为复杂的人生体验,与民族的历史,更深刻地融汇到一起。他无法扯断历史的脐带,内心的苦楚像潮水般地涌现出来。他似乎不再像审视沈从文、茅盾时那么自信,心头还有着理想主义的光环。现在的王晓明,有了更多的困惑,更多的焦灼。当他直面鲁迅的时候,除了与作者的苦难的共鸣外,那种明晰的理性之光正在慢慢消失。写作家心理的障碍,是不是自己也有太多的这种障碍?如果是这样,他的研究视角,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还失之于单纯。学术研究如果不会将自我与对象世界适当疏离,也许缺少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吧?五四以来,中国最有成就的是史学,史学比文学理论与批评,更少受主观因素的任意控制,虽然历史学也无法避免主观的色彩,但至少史学中的距离感,使我们对它的客观性抱有一种亲近的态度。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在这一点上如不注意校正自我,要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是很难的。
我丝毫不是抱怨我们的批评家。但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批评中的这一“死门”。如果不将其克服,并且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理性蓝图,悖论是不可避免的。王晓明和他的友人们近来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证明了旧有的思路的弱点。我想,王晓明等人提出的“人文精神”的话题,是他多年思想的必然结果。应当说,这个讨论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国文坛趋于沉寂、缺少凝固力的今天,能试图用一种理性去正视现实的浮躁,对当代人来说,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提示。他们对道德感丧失的忧虑,是充满责任感的。只有抱有理想主义的人,只有在五四人文精神中沐浴过的人,才会具有如此深切的忧患意识。我初读他与几位学者的对话时,深深地被他们的忧患精神所打动。坦率地讲,我并不苟同他们的许多观点,在我的认识中,王晓明等人的思路,有“泛人格化”倾向。一味地把当代文坛看成人文精神的失落之处,在价值尺度的运用上,是缺少充分依据的。他似乎也承认自我在寻找道路时的茫然心境。回首历史,自然有空空荡荡的感觉;看看现实,商业化袭扰使传统话语场失去效应,未来呢,似乎已没有了明晰性……“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正是在这种历史的转型期提出来的。在价值失范、权威理性弱化的今天,中国的不同文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精神信念,均旨在拯救民族进入现代社会时的精神失态。“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们从消解意义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价值取向,而“新儒学”者们则以狭隘的民族保守主义观点来重觅乌托邦之梦。在诸多主义粉墨登场的时候,王晓明等一代批评家们采取的是一种更为切实的态度。他们不可能走向传统,又不像“后现代主义”的提倡者们那样对现实采取一种朦胧的态度。王晓明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中。他不仅遇到了急剧变化的、不可思议的工业化社会的挑战,也开始面临着知识结构的挑战。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置身于鲁迅所言的“无物之阵”的痛苦。我想,他后来潜心进入到鲁迅的世界中去,且那么深沉地呼应鲁迅内心复杂的情感,这与他自身的处境,大概不无关系。他对当代文学表现出深切的失望与不满,但又找不到一种理性的力量去拯救现实。因此,当他和自己的同伴们呼喊去建立新的精神秩序时,就多少显得有些茫然和空泛。除了呼喊之外,在这种悲壮的声音里,几乎看不到多少清晰的理性画图,他这样地描写过自己的心态:
从必得要有一个希望在前面引路,到看不清希望也要勉力往前走,这就是我五六年来大致的思想过程。我是比先前更不愿意谈论将来了,但我的心境却相当平和。我似乎有可能看清楚周围的环境,我更觉得有能力把握住自己。我开始知道了什么是我该做的事,我应该大致往什么方面去努力。而正是从这努力和该做的事情上面,我获得了某种生命的意义,即便我也知道,这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意义。这样的平和与稳定,究竟是不是面对现实所适宜采取的姿态呢?或许它很快又会被新的刺激所打破?但我又觉得,经过了这几年,我大概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跌回原先的绝望了。也就因为这一点,虽然明知道自己正陷在“穷途”之中,几年来的思想和言行,都不过是一种“刺丛”中的徘徊,我却愿意引用鲁迅曾经引用的《离骚》中的名句,将这些都称作是“求索”了。
——《刺丛里的求索·序》
王晓明的陈述与鲁迅在《呐喊》序言中的话,在韵律上是相近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地贴近鲁迅,理解了鲁迅。如果不是曾有一个理性的力量支撑着自我,而又遇到了现实的重创,也许不会有这种失望中的追求吧?
这也恰恰以王晓明自身的经历,证明了鲁迅那代人,精神上并非全部笼罩着虚无。它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障碍过程,并不仅仅只是精神上的退化过程。在诸多心灵冲突里,亦具有某种超越旧我的历史进化之类。历史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准上,单纯地用进化与退化来形容历史过程,并不能准确地描绘历史。我以为王晓明的重要地方不在于他怎样地解释过去,而在于他那种解释世界的道德激情。他直面人生的真诚勇气,比闭着眼睛说着昏话的人,要可爱多了。这使人们对他的任性,表示出了一种谅解。不回避自我的缺陷,在批评的世界里敢于大胆袒露自我的局限,这使他的学术活动,增添了诱人的光彩。他形容自己像鲁迅那样在刺丛里求索,这不是一句漂亮的形容词。的确,在中国的今天,我们注定超越不了鲁迅,在为民族与人生出路思索的时候,鲁迅所感受到的那一切,被我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王晓明能跳出这一精神的循环么?他的多年的学术活动,这样深地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困顿交织在一起,使其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大大超出了文学自身的范畴。这是批评的不幸还是它的荣耀?这种单一地求索可以真正丰富批评自身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么?王晓明也许并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一问题,坦率地讲,我们这一代人,对此均有着相似的精神觉态。当冷静地去正视批评的历史时,我们又被同样的历史一同地卷入到精神的黑洞之中。在这个漫长的精神洞穴里,我们不自觉地成了当年所批评的对象。这种历史的宿命,不仅适用于五四时的那代人,同样也适用于今天的许多文人。王晓明的存在,是不是使我们更看清了这一点?
1995年7月31日深夜于北京
标签:文学论文; 王晓明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鲁迅传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