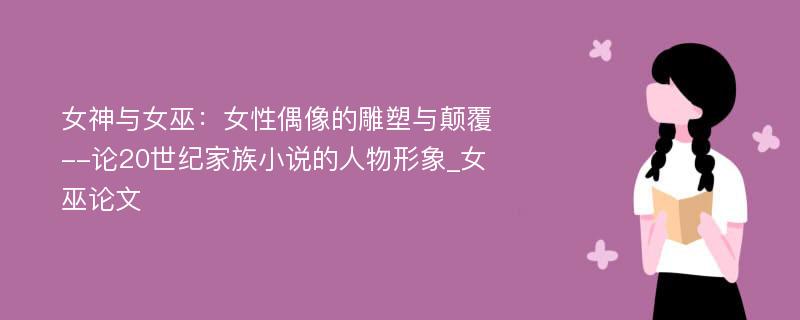
女神与女巫:女性偶像的雕塑与颠覆——20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巫论文,雕塑论文,女神论文,偶像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1)02-0076-07
女性向来为小说的重要形象,她是构成人生内容和意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文学史上,一部分作家就是因为擅长描绘女性形象而著称文坛的。20世纪中国小说不仅创造出了许多丰满动人的女性形象,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女性形象,有的人物甚至代表着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和水平。在男权家族社会,女性往往被人划分为两种身份类型:或是传统美德的化身(女神),或是家族罪恶的使者(女巫)。这种分类的标准十分简单,仅看她对男权尊奉与否。因此,从民间(家族)文化的角度去审视这些女性形象,就有了新的审美文化意义。不仅具有忍、柔、美传统美德的妇女为人赞美,而且那些突破家(“枷”)的桎梏,追寻自由理想的女性亦被人接受。而作家们对人物的审美态度与价值取向,既反映了他们对女性的评判心理,亦成为作家身份的一种判别。
女神:家族女性的偶像
对女性的尊爱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文化现象。世界各国都创造对遍施母爱、拯救人类、繁衍后代、播撒爱美于人间的“女神”。同西方古老神话中的维纳斯、缪斯女神一样,中国也有着神化母爱的圣母文化传统,她虽然历经了不同的社会时代,却潜隐地影响着中国人对女性“美”的标定,制导着作家的审美创作。
中国虽然曾有过女娲创世的神话,有过母系氏族社会,女性作为氏族社会的主要成员也拥有超过男子的特权,生殖女神崇拜亦被视作全民性行为广为传承,而且沉积为一种心意原型,潜隐于心。但是,进入父系宗法社会后,随着女权易位于男权,妇女的话语权旋即丧失,妇女成为男子的附庸,女性的美善标准亦由妇权视界转为男权尺度。从此,女性在家庭中的养育作用就成为传统文化规范女性的基础,三从四德
像一道索链,将女子捆绑在男权家礼之下。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端庄淑静的仪态,“惟务清贞”的节操(注:《女语论》:“女子……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转引自李晓京:《中国封建家礼》,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孝亲持家的劳务,就这样成为女子走向妇人的身前美德。而低眉顺眼的事夫,孀居终身的守节,甚或死作夫鬼的殉身,又规定了妻子柔顺屈从的身份!
当然,尽管中国宗法文化对女性的自然天性有过许多的束缚和压抑,致使后世社会发生了许多为伦理不容的“淫欲”之事,但是,母爱及其牺牲精神又滋养出传统文化特别是家族文化的崇母倾向。端庄、阴柔、和谐等女性特征对男权世界也产生了潜在而持久的影响。因为“母亲以她全力塑造的儿子为中介,将她的威严、慈爱、性格、情感、心态、趣味灌注到男人世界的‘灵魂’里,使之在人格理想、思维方式、人生智慧、性情气质等许多方面都打上了‘女性化’的烙印。”[1]正是在母性对男子的滋养影响和男权对女性的设计规范的双重作用下,才生发了中国文艺审美的女神化倾向。
本文所说的“女神”形象,专指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范畴,中国古代文学的“女神”内涵与此有着明显的差异。无论20世纪曾有过多少次文学运动呼唤或改变了对女性审美的态度,但对女神的塑造与向往却没有大的变化。忍、柔、美几乎可以概括女性美的全部内涵。我们可以从沈从文的《边城》中的翠翠、许地山《春桃》中的春桃、贾平凹《天狗》中的师娘和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娘四个女性形象比较来看。这四个女性的共同之处是一女择嫁“二夫”。尽管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是个苗族姑娘,生活在“茶峒”山城,但是她美丽、温柔、善良,一如汉族文化中的女性。她孝敬体贴爷爷,善待每一个渡客,为了不伤害顺顺船总家大老二老的感情,为了方便行人过河,她情愿呆在渡口摆渡。她的身上,鲜明地突现着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中的女神的柔美特征。许地山的“春桃”在生活中也遇到一女择二夫的两难困境。这位勤劳、坚韧的女性,以其忍和柔不仅解决了令难友刘向高和残疾了的丈夫李茂为难的两夫一妻的尴尬问题,而且以“三人开公司”的办法,把苦难人生达观地维持下去。在春桃身上,同样体现出男权社会家庭主妇具有的忍辱负重一心为家的至善美德。《天狗》中的师娘朴素而柔情,面对瘫病在床的丈夫,她坚韧地操持着家务。天狗的“入盟”,更让她的“温顺”焕发出美丽的光彩。山人的“野情”,让她多了一份女性的自然欲望,因而也更能感化天狗和丈夫的心。
综观翠翠,春桃、师娘的形象,可以发现她们具有相同的家族文化结构“现代”理想女性的内涵。在外观上,她们美丽、温柔、贤慧、吃苦耐劳。在性格上,她们坚韧持家,富有献身精神。和传统女性相比,她们少一份逆来顺受,俯首低眉的家奴相,增强了自主持家的家庭主妇的主体意识。正是她们身上的母性的慈爱,感化了男权把持的生存空间中的男子,使每一个家庭都显露出了生机和希望。她们的每一个关爱的眼神,轻声的问候,都使男人焕发出战胜苦难的信心和力量。因此,从持家的角度可以说,女神第一次成为与男子对等的家庭主人,成为社会男人喜爱的“女人”。
《为奴隶的母亲》属于女神的反例。作家虽然不是为了塑造女神形象而描述春宝娘和秋宝娘的故事,但在原夫与被典“丈夫”的抉择间,春宝娘却以母性的牺牲与博爱成全了两个无耻的丈夫。她的悲苦命运与其说是社会黑暗、阶级压迫造成的,不如说是男权之下妇女无力抗争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春宝娘是宗法社会的传统女性的代表,她身上典型地体现出宗法家族女性的附庸身份及其现实存在。
“女神”的塑造与地域文化中民俗美的魅力密切相关。作家在刻画这些女性形象时,无不依循地域民欲的“伟力”以突现“女神”的性格特征。翠翠生活在民风“纯正”的传统民间文化氛围中,每一种民俗事象都似原生民俗一样古朴,较少变异。浓重的民间文化信仰——民间诗歌、童话、寓言、谚语、俗语以及自然崇拜等构成一个地域民族的梦想与企盼,培育着民族的地方的民众的生活习惯,维系着他们与自然、传统的联系。正是在端午节的祭奠与戏水等一系列文化语境中,翠翠纯真的自然天性和柔美特征才呈现出来,为人们所喜爱。《春桃》和《天狗》缘自同一“招夫养夫”婚俗惯制。虽然这两篇小说的时代背景相距50年,但如果我们不仅仅拘泥于阶级斗争的主题阐释,就会从民间文化视角发现小说的新的母题意义。人生的悲苦虽然与社会时代有很大关联,但同一悲剧却完全可能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中。民间大众日常的悲苦往往具有这种“恒常”性。李茂的残疾和“师傅”的瘫痪虽然发生在两个时代,但他们都使女主人公在家庭中充当了招夫养夫的角色。丈夫的生死和家庭破败的危困现实逼迫她们做出了有违人伦传统的抉择:牺牲自己,成全家族。因而使主人公成为消解性别意义,献身家族的“女神”。从这个意义上去透视春宝娘的不幸遭际,就可以理解,她无从选择的选择只能是为男权生子繁衍,只能使自己付出的母爱在两个孩子(春宝与秋宝)间割舍亲情关联。她的卑贱的付出,实际上成全了两个男人家庭,使女性又一次在生存现象中证实了“女神”亦不过是男权创造的“神话”的主人公,是“典妻婚”的牺牲品。因为“在由父子相似性和占主导地位的男性逻辑构成的一个心理语言世界里,女人是匮乏或缄默,销声匿迹和默默无闻的性别。”[2]
女神是悬浮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神,她一方面以自己的坚韧、勤劳、贤慧的母爱哺育着每一个男人,另一方面又被迫按照男权主义设定的规范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是在这种个体与家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悖论中,她们才建构起了属于男性的神话世界,并作为这个世界中的女神,感染和影响着每一个男人。青年评论家闫建滨曾有一段精当的评述,可以做为女神形象的总结。她们“都有美丽而博大、神圣而苦难、平凡而难以企及的特征,是男主人公生命为之奋斗的动力和苦难遭遇的避风港。”[3]她们不属于现实生活中凡常而又丰实的女性。她们较少女性意识,她们的爱欲实现的渴求总是与男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很少有付出后的索取和回报。她们名分上虽然是女主人,其实她们只是男权视觉中的美丽影像,依然是为实现家族血脉传承的生殖机器,是伺候丈夫、公婆的贤妻、贤媳。和古代妇女相比,她们只是不再被任意打骂和娶辞。勤劳、坚韧、朴实、柔顺、贤慧、美丽,这些十分动听的褒义词句正反映了男权主义实现后的恩赐和不平等。这也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马克·赫特尔所指出的,“表面上看,缠足是被幻想成为女性的美的标志,实质上在中国它是妇女顺从角色的象征。”[4]“女神”的奉献没有对等的“男神”的付出,也证明了女神是理想与受难者形象的内涵。正因此,她们给读者的审美印象是优美的,绝少冲突,绝少压抑,欣赏者从文本形象中唤起的是和谐、圆融的生命价值感觉,她们从而获得了优美、“可敬”的女神的评价。
人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人在同自然压力进行殊死搏争之后发展到今天,成为具有充分的感性能力和清醒的理性思维的智者。超越了宗法家族阶段的男人,需要的是具有七情六欲活生生的女性,而不是美丽梦幻般的女神。贾平凹《浮躁》中,金狗就曾对“女神”做过一番辨析抉择:
“英英对着镜子收拾好了头发,说夜不早了,她该回去了。金狗便将她送出门去,看着她一步步走进溶溶的月色中去,金狗心身全清醒了,脑子里出现了小水和英英两个形象,小水是菩萨,英英是小兽啊,人敬菩萨,人爱小兽,正是小兽的媚爱将金狗陷进了不该陷的泥淖中了。”
这里金狗将小水比做菩萨,也就是女神,认为女神是尘世男子爱不可及的,只能供奉敬重,而充满爱欲的小兽(凡常女性)才是男人所渴求的。所以,金狗对小水的爱,只是一种对女神的爱慕,缺少两性相融合一的情感爱欲基础。
纵览20世纪中国小说,“女神”形象的塑造呈现着不断更新和扩展的态势。时限愈推近当代,“女神”愈多,形象越鲜丽,思想愈近现代性。巴金笔下的瑞珏、梅,老舍笔下的韵梅,与翠翠、春桃、师娘等虽都类属“女神”,但前者更接近古代宗法家族中的贤淑女像,后者更多一分自然气息和现代女性的生命意志。与20世纪前期的女神形象相比,新时期小说中的女神不仅思想更开化,个性意识有所增强,而且她所包容的文化象征意味和作家的文化个性更为鲜明突出。张承志的索米娅(《黑骏马》)是自然之神及其母爱——祖国(中国)、母语(汉语)、民族(回族)等诸多因素相整合的“女神”;贾平凹的小月(《小月前本》)、小水、师娘则是作家从小深居商州山野,倾听祖母的民间故事,渴望和谐圆融的生命价值感觉的心理反映;而路遥笔下的女性形象,如巧珍(《人生》)、田润叶(《平凡的世界》)则是传统伦理和共产主义理想结合的产物。
有必要指出,20世纪的小说园地中,女神在女性形象中只占少数,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的嬗变,更多的女性形象在步入“女人”和“女巫”的角色。虽然从自我意识和爱欲要求及社会伦理规范去看,她们(尤其是“女巫)给社会伦理秩序以一定的冲击,带来了道德的“滑坡”,但从人性与审美的角度说,这正是社会进步、思想观念变革的正常变化,是值得庆幸和肯定的。
女巫:女性偶像的颠覆与重写
女巫,原指施行巫术的女性,后渐转贬意,多指装神弄鬼欺诈作假的女性。本文的女巫则专指在男权社会爱欲遭受压抑心理畸变的女性。美国女学者吉尔伯特曾指出,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命运不是发疯就是成为玩物。20世纪家族中的女性在传统家礼的桎梏下,呈现出的亦是这两种悲剧性命运。无数个冤屈变态的巫姐形象,好似一个个阴魂指控倾诉着男权主义的传统伦理(家礼)的罪恶。她们作为对“女神”的反叛,即对传统伦理规范下的女性偶像的颠覆性重写,具有深刻的文化反思意义和独异的审美价值。
人类的生存空间固定着不变的性别关系,男女、公母、雄雌构成了生物的最基本的两元对立。然而,在这些两性对等的关系中,惟有男女具有文化服膺的关系。随着父权家族的确立,男性的强大和女性的柔弱像一条生理法则被固定和传递下来,长久持存的男人中心、女人附庸的二元对立,逐渐形成了民间文化中习以为常的各种惯制、礼仪和禁忌。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对女性的最大束缚是个性自由。从穿衣戴饰、女红、(注:女红:指女子必备的技艺,包括缝补、机织、做衣、纳鞋、刺绣等。)缠足、轻声柔气,到“惟务清贞”、孀居守节、为夫殉身,家礼为女性设定的所有规范,无不指向男权中心,无不服从宗法家族的利益和男子的玩赏。“文明社会通过贬抑女性为祸害、灾难、淫乱而肯定男性的正面权威和价值,所有的善和优秀品质都属于男人;而低劣、邪恶、罪孽则是女人的天性。”[5]正因此,民间社会才建立起一整套伦理规范,数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男尊女卑的不变法则,从而实现长幼、尊卑的等级社会控制。当女性像子女恭孝父辈一样服帖男性时,她就被戴以贤慧、柔顺、善良的神冠,成为贞女、烈女、孝妇;当她冲破男权制定的家族伦理规范,追寻自我理想与爱欲时,就会被视为淫妇、荡妇、泼妇。正是在这种封建伦理的压抑和束缚下,女性的爱欲需要才逐渐萎顿以至扭曲变态。所以,当现代作家将女巫形象带到审美的视界,无论这种写作是否带有男权的偏见和女权主义的执著,都是对“五·四”运动力图颠覆而未能彻底颠覆的传统男权文化价值的解构,是对现代女性生存图景与心理图景的一次认知,具有重要的审美开启意义。它使女巫形象第一次成为小说的主人公,且承载了丰厚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撮要而论,20世纪小说中的女巫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扭曲变态的寡妇型。她们因为守寡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爱欲指向而致使心理畸变,所以转而寻求施放爱欲的替代物,或通过虐待替代物而宣泄久积在胸的爱欲潜能。另一种是“自甘堕落”的妓女型。传统家礼的洗礼,使她们把自己的爱欲与自由实现的期望挂系在男人的腰带上,为在献媚男人的竞争中获得主动而不惜自虐和戕害他人,自我迷失的结果,终受被抛的打击。妓女型同样类同于寡女型的扭曲畸形心理,她的变态的欲望的被满足同寡妇的无法满足一样,都不可能实现爱欲和获得人格的独立与自由。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巴金《寒夜》中的汪母、王蒙《活动变人形》中的倪母、叶兆言《半边营》中的华太太,是20世纪不同年代中创作的寡妇——女巫的典型。苏童《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米》中的织云,贾平凹的《废都》中的唐婉儿、柳月,以及李锐的《厚土》系列中的部分女性则为妓女型女巫的代表。
寡妇门前是非多,寡妇型女巫是中国家族文化的独特产物。宗法家族礼仪对女性的束缚,往往使一旦守寡的女性从此失去再嫁和与男人亲密交往的可能。正值盛年的寡妇由此处在被爱欲煎熬的“绝境”。向儿子间接地释放爱欲,与儿媳竞争儿子(男性)的欢心,对子女宣泄久抑在胸的火气(性欲潜能),便成为中国家族颓败时期寡妇——家长的独异特征。汪母独守文宣一子,无论是占有还是宣泄,她面对的只有儿子和儿媳。对儿子的娇爱和对儿媳的尖刻,使汪家没有一天安静的日子。像所有长子恭敬孝顺一样,文宣对母亲的唯命是从一方面纵容了汪母的守旧与骄横,另一方面又拉大了与妻子的心理距离。作为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曾树生,决不容忍丈夫的无能和婆婆的无端责骂,出走,就成了她的唯一选择,而汪母也只能以白发人“送”黑发人终结家族的破败。与汪母笼络儿子的方法不同,倪母是用大烟加媳妇拴住年仅17岁的倪吾诚的自由的。亲自教授儿子吸大烟,无异于亲手杀死儿子,然则为了倪家“独苗”成活为符合传统家礼的孝子,倪母不惜制导了吸毒与娶亲两件大事,从此导致倪家数十载争吵不安。
如果把寡妇家族做个统计,会发现作家们共同有意无意地创造了一个“女巫”之下无壮男尽孝子的家族悲剧。同文宣多病致死、倪吾诚“神经”不正常常发奇想一样,阿米亦是一个体弱无傲骨的独子。无论华太太怎样刁蛮任性,甚至扼杀了儿媳葆兰,他都守孝在家,决不出家另谋出路。家族的颓败和“女巫”的骄横,使“长子”后继无人,“幼子”出走无望矣!
本欲持家育子,反倒促发子“亡”妻“离”的结果,寡妇们的苦心缘何落得如此下场?这与宗法家族结构关系的制导有关。在长子未成“人”即尚未达到传统宗法文化规定的修身、立命之本以前,父亲以家长的身份辖制着妻子与长子。同被管束与训导的关系,使妻子与长子具有较为亲密的关系,父亲的威严使长子对母爱怀有深情的渴望与依赖。同样,妻子作为伺奉公婆和丈夫的家庭主妇,虽然可以得到丈夫的性爱,却摆脱不掉“小女子”的身份与地位。只有当长子进身为父亲和家长,长孙继位为长子时,母亲才摆脱了小女子的身份,作为“婆婆”行使长辈权力。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家族身份结构中,一旦丈夫遇难夭折,尚在青壮年的妻子即被推到家长的地位。守寡的煎熬,小女子的软弱,长子幼小不足以治家,都使寡妇陷入悲困之中。因此,皱眉强撑起的治理家族的重任,就迫使寡妇在日后漫长的人生途中,既要清心寡欲甘做贞女孝妇,又要淫威母爱并施操持家务。爱欲的持久压抑和家长威严的号施,终必促其重觅施放爱欲的对象,不是充当“淫妇”,便是做“恶婆”——欺压儿媳,霸占儿子,导演出一幕幕寡妇的悲剧。汪母、倪母和华太太也因此成为寡妇形象的代表,承载着无以言表的女巫的悲苦。
综观现代文学中的寡妇型女巫形象,曹七巧最具有典型性。老年的曹七巧阴毒、刁钻,施展出一身本事,将儿子和女儿“囚禁”在身边,陪她虚度青春光阴,她以超过年龄的兴趣逼问儿子婚后的床第之事,又有意抖落给众人,折磨死儿媳芝寿。她一反母爱地逼引儿子、女儿吸毒,却又故意将女儿的大烟瘾暗示给未婚女婿,拆散了一对有情人。她的这种扭曲变态的母爱心理,反映了宗法家族颓败的结构图景。30年前,年轻貌美的七巧同所有新娘一样憧憬着美的生活,然而贪财的父母却把她嫁给了虽有钱却身患骨痨病的姜家二少爷。面对着失去性功能的丈夫和风流成性的小叔子季泽的爱恋式挑逗,她伴随着孤月经受了压抑爱欲(主要是性欲)的煎熬和渴盼施放爱欲的冲动。如果说性欲的无法排遣使其愈发紧张与焦虑的话,那么,财富和金钱的积聚与挥霍又间接释放了她的“力比多”及其紧张感。大家族内部的虚伪与狡诈,也使她逐渐变得凶狠和算计起来。当她的爱欲失抑完全锁闭了她的青春和希望后,破坏(近于死亡)本能便成为其日后报复性行为的心理驱力。因此,无论对于儿子、女儿婚姻幸福的妒嫉和破坏,还是对于小叔子老来的再次亲密性表示的冷漠,都表现出她扭曲变态的女巫性格的定型。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巫在男主人公欺辱下畸变不同,张爱玲采取追忆的方法,让女性充当主人公,将男性搁置一旁,成为陪衬,并以审美批判的冷峻之笔,不仅揭示了爱欲迷失对人的压抑和折磨,而且鞭挞了传统家族文化对女性自由的束缚与践踏。曹七巧的一生,象征地表现出旧家族中从孝女到孝媳再到“上房”婆婆循环转换的身份结构,形象地转喻出“长幼有序”的家族制度的虚伪与罪恶,从而成为以女巫形象颠覆旧礼教旧制度的扛鼎之作。
妓女本指被迫卖淫的女人。本文所谓妓女型女巫主要指那些勾引男性,将自身价值与爱欲实现寄托于男子的家族女性。对于向来注重伦理道德的中国家族,女人“献身”于男子,其中既有“嫁鸡随鸡”的夫为妻纲的纲常规范,亦有以“色”谋“利”,换取生存权益的复杂成分,至于为取悦于男人而不择手段的互相争斗,更内涵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因而使妓女型女巫形象成为反思家族文化,颠覆女神偶像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女大学生颂莲可谓妓女型女巫的代表。她虽然文墨满腹,也不乏理想欲望,但传统家礼的熏陶使得她一旦身处生存竞争之地,便施展开“文明”的所有手段:为了争得糟老头丈夫陈佐千的宠爱,她与其他三房太太明争暗斗,争风吃醋。她并不是为了爱欲的得失才不择手段加害他人却最终自己发疯的,相反,在老得可以当她父亲的陈佐千身上她厌腻这所谓的性爱。她所追寻的只是对男人的依附和虚荣,全没有个人的人格理想。她在学校中学来的文化知识,不仅没有使她变得文明和友善,相反,当她一旦悟得陈家大宅的生存“奥秘”之后,生存意志和虚荣心反倒促使她将文化智谋全部用在与人争宠与争斗上。正因此,互相倾轧的结果,只能是她的人格失落、精神失常和走向死亡。
与颂莲的争宠献媚的动机多有不同,织云对男性的勾引与献身更多地是爱欲(主要是性欲)的失抑和靡烂。虽然她对吕丕基(六爷)死心踏地的追嫁具有炫耀自己的虚荣成分,但从吕丕基对她的打骂和五龙对她的性暴力上,却又分明显示出她强烈的爱欲与自虐狂心理特征。一个并不缺吃少穿的富户人家的长女,竟然无视金钱与家规,一心为满足自己的爱欲而不惧“堕落”,表现出家族女性背叛家族伦理渴望个体自由的内涵。虽然织云仍难脱“淫乱”之责,但她的“可悲”的结局毕竟给家族的颓败因由追记了有力的一笔!
如果说倾莲和织云的“堕落”主要是爱慕虚荣,追求性欲的话,那么,李锐的《厚土》系列中的女性则是以出卖肉体换取生存的典型,其内涵更令人忧思。《驮炭》中那个健壮的农妇,她在与领牲口的汉子的打情骂俏的挑逗中,隐藏着极现实的交易;为换得一块好炭不惜以身相许!还有《假婚》中的那个女人,为了生存,“情愿”先给队长“过了一水”,再“嫁”给一个“临时”丈夫。李锐笔下,吕梁山的女人并非为爱欲而献身,出卖肉体的目的只是为了换得家人的生存必需品。从表面上看,她们是为克服贫困所经受的“基本压抑”,具有某种无可奈何的“合理性”,而实际上,她们是男权家族为维护其文化统治所施加的“额外压抑”的牺牲品。她们活似牲口,毫无个性自由和权益可言,为了家族的利益,可以随意被男人交换。她们生为家族之属,死为家族之鬼。无足轻重的女人只在死后的陪葬中方显出其在家族中的卑微地位。吕梁山的妇女们淳朴得令人生发悲悯的“主动卖淫”现象,虽然仍为社会道德所不耻,但它的深刻的文化反思与审美批判意义却不可低估。是什么原因使男权家族势利横亘20世纪?无疑,读者对“新家族”内蕴的探问追寻,将会促发小说更大的文化审美空间。
女巫是对女神文化的一次反叛与形象重铸。无论是寡妇型女巫,还是妓女型女巫,不管“寡妇”因丧失爱欲(尤其是青春性欲)实现的对象,还是“妓女”为过度淫迷丧失自我追寻的价值对象,她们都因违背传统家礼规范和因为人格迷失而沦为审美批判的对象。曹七巧、倪母、华太太、汪母为宣泄个人扭曲的爱欲而不惜向儿女“施暴”的现象,潜隐地显示出寡妇“复仇”的心理。儿女是父亲血脉传延的象征,对儿女的恨,就是对亡夫的记恨和复仇,因为丈夫的早逝造成寡妇青春的被毁,爱欲(尤其是性欲)抑失。寡妇沉缅于对儿女的折磨及其所促成的不幸,象征性地暗示着对父系男根的铲断。因此,华太太对于儿媳难产死去和孙子的夭折,曹七巧对于儿媳患病的早逝,所表现出来的漠然态度,甚至是兴灾乐祸的神情,都表明了她们对男权血脉中断的快感。这种血亲间令人发指的残忍克杀,正是寡妇女巫释放心理潜能的鲜明特征。她们比之贤贞不屈的节烈之妇(女神),更近于现实人生的真实状态。她们使家族走向败落,令家族血脉无以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女巫”正是作家用以解构父权文化的形象手段,是对女神形象的反叛与重写。
妓女型女巫也具有解构男权、重写女性形象的审美意义。家族“妓女”是男权文化的产物。在家族小说(扩而言之,也是所有小说)中,女性的勾心斗角,妻妾间的争风吃醋,无不是为了男权这个中心。虽然家族礼仪为女性制定了女子的行为规范,但是恰恰就是这些旨在要女子为男权奉献的家教、家礼、家法,束缚了女性正常的身心发育,压抑了女性爱欲的正常泄导,扭曲了女性的审美心理,因此,一旦得到释放心理潜能的机遇,女性的久抑失衡的爱欲(尤其是性欲)便摧促女性不惜突破人伦家礼禁忌,去为生存而“献身”,为欲望而冒险,为争宠而相斗。其结果,自然是淫迷无度,人伦尽失,自由全丧,人格畸变,成为人们诅咒的女巫。贾平凹的《废都》之所以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就与他笔下的几位淫迷无度的女巫有关。无论是来自县城的唐婉儿,还是来自陕北农乡的柳月,一旦拥向庄之蝶,一旦为作家名人的男权所诱引,久抑失衡的欲望便倾泄而出,伦理、礼仪、规范、人格全抛脑后,感性欲望成为生活的全部意义。在她们身上,人们不难看到从颓败的家族女性延续下去的依赖男权、丧失自我的可悲人格。因此,对女巫批判与呈现,就是对男权主义的批判与颠覆,对“女神”走向人生现实的一次启唤与解救。
有必要指出,在对女巫的形象的塑造暨男权家族文化的颠覆性描写中,作家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一部分男性作家潜意识中有着男权主义的阴影,他们对女性(尤其是对女巫)的描写有着玩赏性的成分,解构多于重写。除了贾平凹在《废都》中对女性的过滥的性描写外,苏童对于卓云、梅珊、颂莲等姨太太的性心理的描写亦近于生理的欲望,缺少女巫被男权家族扼杀的心理铺垫与叙述转换,使读者对她们的人生悲剧的理解多怜悯、同情,少文化批判和艺术超越。李锐在《无凤之树》中对暖玉的性作用的“过高”评价也是一种阅读误导。既然创作女巫形象的目的是为了颠覆女性审美的误区,重写女性形象,那么,把女性的爱欲渴望和对男性的诱引作为愉悦读者的调料,在文本中反复渲染和描写,就难免偏失创作意旨,陷入男权主义玩赏的泥淖。同样,对女巫的抒写仅仅停留在家族颓败的历史主题上,仅仅展示宗法文化是怎样束缚和扭曲了女性的爱欲心理,还不足以颠覆男权文化秩序,实现重写女性形象的目的。因此,如何以现代审美文化精神和人类意识烛照和洞穿宗法家族阴暗的礼法,消解女性的心理束缚,建构出现代审美人格,是所有作家们的责任和义务。
收稿日期:2000-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