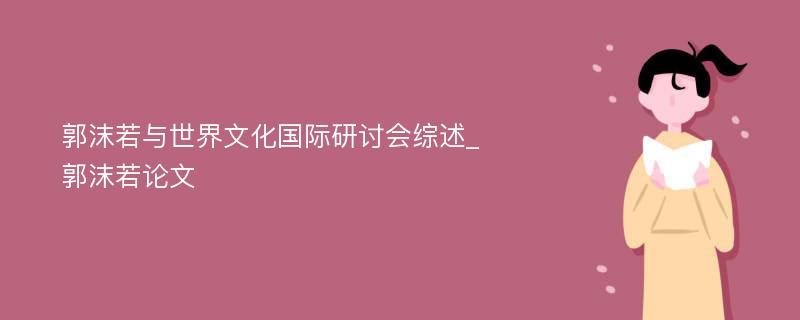
“郭沫若与世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世界文化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学会、四川联合大学中文系、成都石室中学联合主办的“郭沫若与世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29日至30日在成都四川联合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西安、济南、青岛、成都、乐山及美、日、俄、越等国的高校、科研及新闻出版部门从事郭沫若研究的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了会议。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析综、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饶用虞、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胡继先、四川联合大学副校长周宗华等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由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四川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锦厚教授和北京郭沫若纪念馆馆长王骏骥研究员、四川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唐明中副教授轮流主持,采用了圆桌讨论、自由发言的形式。代表们主要围绕会议中心议题,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研讨。
一、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
郭沫若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巨人,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名人,他的文化观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状态,但总体上是一种世界文化观。
谢保成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郭沫若的文化教养是浸染于儒家经典,寝馈于传统文化的,从小便从感情的喜好出发接受了传统文化积极、浪漫的方面,《诗品》、《庄子》、《楚辞》、《文选》等侧重于抒发主观情愫,张扬自我的一类传统影响郭沫若思想中浪漫主义的形成,但浪漫、叛逆的个性又使郭沫若对旧学中的消极面产生极大的反感,使他转而向西方思潮中寻找同调,留学日本使他有了这样的机遇。这样吞吐中外学说,瞩目异族优秀文化,使他在中外文化的对比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文化观,把世界文化划分成中国、印度、希伯来、希腊四种派别,而以中国的固有精神与希腊思想同为入世,即动态而非静观,主张以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弥补传统文化的缺陷,旨在恢复民族固有的精神。
黄侯兴研究员(北京郭沫若纪念馆):郭沫若和本世纪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提出既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又要“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融汇在哲学上的契合点,而这是以泛神论为媒介的。郭沫若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大胆告白他是“崇拜孔子”的,而其孔子观是参证外国哲学,用泛神论去探究孔子得来的,称孔子是一个泛神论者,“与斯宾诺莎 Spinoza的泛神论异趣”,在此一点上使孔子“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力的巨人”,从而为中西文化找到了哲学上的契合点,使“五四”时期大规模无选择输入的外国文化形成对传统文化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发展动力。
孙开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世界文化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泛神论、无神论,用泛神论思想为武器,对上古三代的神鬼迷信进行批判,认为三代是“黑暗时代”,而春秋战国则是对于三代进行思想革命的“文艺复兴”时期;以泛神论的思想解释孔门儒学,认为孔子与歌德都是十分完美的伟人,把中西文化在共同的一点上联系起来。二是对墨子及其宗教的批判。郭沫若把墨子学说放在整个世界文化的背景上,对印度和希伯来文化的宗教思想持批判态度,指出墨子是中国的马丁路德,乃至耶稣,是顽固的守旧派,甚至把墨子和纳粹法西斯者流相提并论。这样,从他的世界文化观出发,完成了对墨子的认识。三是重视发掘中国与西方相对应的自然科学思想。他重视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思想,在研究先秦诸子时,竭力发掘与希腊文明相对应的自然科学家,最突出的是找到了提出了原子说和地圆说的惠施,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自然科学方面亦可与希腊文明媲美,其所论证的世界文化总体观也有了有力的证据。
二、郭沫若对中外文化的创造性吸收
作为文化巨人,郭沫若涉猎十分广博,但他的贡献是他创造性吸收中外文化的结果。与会者从多个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
谭继和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郭沫若的作品表明他受过西方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二是客观缜密的分析。但他对自然主义又有较大的改造,其笔下所反映出来的自然主义已是改头换面,他并不是照相似的记录,而是纠正了自然主义不重精神的不足,用儒、道的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无为而治”,和自然主义积极的一面结合,展开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但郭沫若在创作历史剧时主张必先研究历史的态度,仍是自然主义科学态度的表现。
姚锡佩研究员(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和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都受到德国文化的影响,但鲁迅偏重于理智,受海涅影响较深,而郭沫若则更多受歌德影响,一方面和歌德的浪漫个性相类似而引以为正调,另一方面在此后郭沫若和歌德又有类似的心路历程。
阎嘉副教授(四川联合大学中文系):在郭沫若早期所受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始终贯穿着的主旋律是现代生命哲学。早期郭沫若艺术上的浪漫主义与哲学上生命哲学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其哲学观中的主调是现代生命哲学,其在哲学上所推崇的一些思想,几乎都与现代生命哲学有密切联系。
首先,
早期郭沫若极力推崇“生命力”和“Energy”,“Energy”应该理解为“活力”、“精力”,在其《生命底文学》中,几乎是叔本华和尼采的观点的中文版。二是郭沫若和现代生命哲学的倡导者一样大多推崇和具有强烈的挑战与反抗意识;三是郭沫若与现代生命哲学家一样推崇天才;四是在死亡观上,早期郭沫若曾一度把死亡看作是对生命的解脱,而叔本华已有类似的观点。而把早期郭沫若的生命论哲学观与他所推崇的浪漫主义文艺观联系在一起的,是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所说:“我想诗人与哲学家底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透视万物底核心为天职。”
三、世界文化背景下郭沫若的思想“转换”
一般认为,郭沫若的思想和精神世界经历了由传统到西方个性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一些与会者指出其“转化”过程必须具体研究。
王骏骥研究员(北京郭沫若纪念馆):如果把郭沫若思想转变的过程简单化,是不能对郭沫若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的。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的主潮中,郭沫若反道而行,明确张扬起尊孔崇儒的旗帜,这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感情至深有很大关系。纵观郭沫若一生思想多所变化,而尊孔崇儒却执而不弃,不是独树一帜的理性使然,而是融汇着他经过深沉思考的对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追求。留学日本的郭沫若从《王文成公全集》中彻悟了一个奇异的世界,顿悟了中国儒道哲学的“道”和“化”,并因此由王阳明导引到庄子、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度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欧洲大陆布鲁诺、斯宾诺莎等哲学家。于是他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这就是一种“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超越有限,达到无限,超越自我,达到永恒的“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体悟之深切见之于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创作以及《屈原》、《高渐离》等剧作。不仅如此,1935年写的长篇学术论文《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先秦天人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学术考察,表明郭沫若已超越了“五四”前后对“天人合一”形而上哲学的体认和感性的泛神论,由感情的拥抱变成了理性的选择。又如郭沫若对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影响也只是表面现象,“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的思想证明他的泛神论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有本质区别,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道家的“天人合一”只有人生哲学意义,儒家的“天人合一”则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郭沫若对自由的体认更接近老庄哲学,而价值体认则接近儒家思想,表现为儒家的人本主义伦理观。这从1925年郭沫若的思想中可见一斑,他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以争回大众的个性与自由!”在郭沫若这里,个性自由不是不可度让的个人权力,它是可以也应该屈从于大众的。
魏建教授(山东师范大学):一谈到思想转变就首先说是世界观转变,未免有简单化之嫌。实际情况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没有被多少中国人掌握,即使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只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部分学说。进入二十年代后,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兴趣的主要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的一种新文化模式与社会理想。郭沫若也不例外。他向往新生的苏俄社会,在《巨炮的教训》里充满激情地赞扬了列宁,在1921年写的《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一文中,更是“觉得便是马克思与列宁的人格之高洁不输于孔子与王阳明。”进一步分析后,他得出结论说,1924年前,郭沫若思想一步一步发生“转换”的过程与其说是一步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一步一步接受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过程。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就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思想转换的阶段性成果。这种“转换”时期,郭沫若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三十年代后的历史研究中才完成了这一“转换”,即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掌握。
李晓虹博士(北京郭沫若纪念馆):郭沫若早期主要是以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但也曾经直接面对并认真探讨诗人的问题,正面描述理想人格的蓝图,甚至这种人格观成为其艺术观的统领,建构于诗论之上,在人与做诗的关系上,提出“人之不成,诗于何有”的先做人、再做诗的主张。这和儒家文化的修身思想不无联系。郭沫若早期追求的人格理想的突出表现是欣赏全面发展的“完满”天才,在内在丰富性的开发上体现人性的深度,主张理想艺术与理想人生的和谐统一。但是这种人格观在二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思想的急剧变化也突然发生变化,个体意识迅速向群体意识皈依,由“球形发展”的人到“标语式”、“口号人”,从不做“留声机”到做“留声机”。这种转变,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秦川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党伯教授(武汉大学中文系)、龚翰熊教授(四川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博士(美国威斯利恩大学)、邓牛顿教授(上海大学中文系)、李继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泉明教授(武汉大学中文系)、陈漱渝研究员(北京鲁迅博物馆)、税海模教授(乐山师专中文系)及特级教师徐敦忠(成都石室中学)等都在会上发了言,并就进一步深入研究郭沫若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由郭沫若题写馆名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和郭沫若的母校成都石室中学。
注:本文发言摘要根据提供的论文及大会发言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