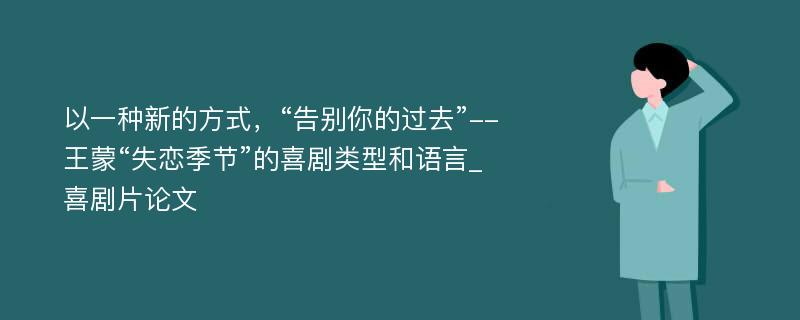
以新的方式“和自己的过去诀别”——王蒙《失恋的季节》的喜剧类型和语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自己的论文,以新论文,喜剧论文,季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特别评价
一
假若换一个作家,《失恋的季节》的题材可能被处理成悲剧性的作品。由于王蒙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杜勃罗留波夫语)和艺术才华的特点,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喜剧作品,而且是作者的第一部大型喜剧作品。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面,始终回荡着笑声,其中的人物几乎从头到尾都在笑。我相信,读者大约也和我一样,整个阅读过程自始至终伴随着自己的忍俊不禁的笑声。这是一部洋溢着强烈的讽刺和幽默的激情的小说,作者卓越的喜剧才能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而生动的艺术呈现。
谈到喜剧,我们常常想起马克思的那段名言,“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就是喜剧。……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①《失恋的季节》确是这样一部“和自己的过去诀别”的作品,但是作者在同自己的过去诀别的时候,心情决不仅仅是轻松愉快的。因此,“愉快的和自己的过去诀别”,恐怕不能精确地概括这部小说的喜剧特色。我以为,王蒙在这部长篇作品中创造了不同于一般传统喜剧的新的喜剧风格,作者的讽刺的和幽默的激情具有现代喜剧的性质。可以说,《失恋的季节》是一部具有现代喜剧风格的长篇小说。
别林斯基指出:“喜剧的内容是缺乏合理的必然性的偶然事件”,“喜剧的主人公是离开了自己精神天性的本性基础的人们”,“喜剧的实质是生活的现象同生活的实质和使命之间的矛盾”。②《失恋的季节》主要描写了一批从青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在国家机关工作的青年职业政治工作者,在反右运动中大都被定为右派,随后到京郊劳动改造,最终摘掉右派帽子的经历。作品的喜剧性内容所反映的,恰恰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缺乏合理的必然性的偶然事件”,其喜剧性便在于失去本身内容的虚假的生活形式同真实的生活内容的矛盾,生活的现象同生活的实质和使命之间的矛盾,即人物的生存形式同生存内容的矛盾。隐入这一矛盾之中的主人公们,恰恰是离开了自己的精神天性的本体基础的人们。
产生这一喜剧性矛盾的主要根源是:把主人公们定为右派并集中到郊区劳改的理论依据,是以代表和体现国家与人民利益的神圣、庄严面目出现的政治权力话语,而实际上这种做法却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主人公们划为右派并集中到郊区劳改的光明正大的理由,是教育、改造和挽救他们,以不使其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道路”上走得更远,而结果却伤害了、毁损了、扭曲了他们的感情、精神和灵魂。作品的主要喜剧载体是被划为右派的青年职业政治工作者。这些人物的喜剧性在于:他们是被权力机构按照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权力话语划成右派的,显然,这种话语是与他们的权利、愿望、感情和追求相对立的,但他们却不知不觉、甚至是自觉自愿地服庸、信从和膜拜这种敌视他们的政治权力话语;被以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权力话语划为右派的人们,无疑是这种话语的受害者和牺牲者,但他们也同样运用自如地以这种话语为武器,裁定他人的“右派言论”,批判他人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参与对他人的伤害,并把伤害当作是帮助、教育和挽救;主人公们很小就参加了革命,本来是“革人家的命”的,是把革命等同于自己的人生的“天生革命家”,但在反右运动中却大都“被人家革了命”,成为革命的对象和“反革命”。这些人物之所以是喜剧性的、可笑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支配他们命运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权力话语,是盲目的、蒙昧的和迷信的。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的喜剧性、可笑性源于他们自身,源于他们缺乏摆脱这种愚蒙状态的强烈愿望、自觉性和主体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的喜剧性、可笑性,从根本上又反映和折射出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权力话语由于脱离实际与违背社会历史规律而呈现出的谬误和可笑性质。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指出,喜剧中的“人物只有在自己并不严肃地对待严肃的目的和意志时,才把自己表现为可笑的人物。”③黑格尔这里说的基本上是传统喜剧的特征。而现代喜剧的特点是,喜剧中的人物对貌似严肃而实则荒谬的目的和意志,采取不严肃的态度。一般说来,传统喜剧所讥讽和嘲笑的对象是明确的、单一的,所引起的笑声里透露出优越感和轻松感,其艺术色调是明朗的;而在现代喜剧中,讥刺和嘲弄的对象变得含混、复杂起来,既讥刺他人又嘲弄自己,所引起的笑声里透露出的是无力感和无奈感,其艺术色调是晦暗的。我们在美国黑色幽默文学中看到的,正是这类喜剧。《失恋的季节》是接近于这种喜剧类型的。
二
英国作家华波尔说过,“在那些爱思索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喜剧,在那些重感情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悲剧。”④当王蒙以清醒的理性意识反顾和追思历史,观照和透视他笔下人物的思想与精神状态的时候,他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俯瞰他们,发现了他们的“可笑的本质”和他们的“不一致”,洞见了“这一思想和那一思想的脱节,这一感情和那一感情的相互排挤”;⑤他以“历史的幽默感”(王蒙语)理性的优越感和智慧,调整和嘲笑他们,这些人物的被否定的喜剧性格便艺术化地显示出来。而另一方面,王蒙所描写的那段历史过程,又是他曾亲身经历的,他与那段历史有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在历史往事中埋藏着他的难以忘怀的青春、理想、热情和泪水。在审视消逝已久的历史事件时,他是无法把自己排除在外的。回首往事,他在重温以往的“刻骨铭心的经验”(王蒙语)时,心中势必再次鼓荡起昔日的激情。钱文、郑仿、杜冲、萧连甲、费可犁、周碧云等人物的某种“可笑的本质”,在他身上也曾存在过。在他们的身上,都可以发现作者的影子。在这里,作者与他笔下人物之间的历史距离消失了,他和他们站在同一历史地平线上。他发现了他们的狂热中的真诚、盲目中的信仰、奴性中的卑微、愚妄中的可怜、荒唐中的可悲,看到了他们思想和精神状态的某种“历史必然性”。所以,他又怀着温情、仁慈和博大的爱的情愫,悲悯、体谅和宽恕他们。于是,喜与悲,讽刺和幽默,辛辣的嘲弄与无奈的自嘲,激情难抑的倾诉和痛快淋漓的宣泄,执著的痛苦与超脱的轻松,便在《失恋的季节》中错综复杂地纠缠、交织在一起。
事后许多年,时过境迁,恩消怨泯,重叠使记忆模糊,现实使往事冲淡,新的喜怒早已打磨掉了悲欢的陈迹,往日的忧虑在新的可能面前更像是一次幕间的谐谑插曲。所有这些当年觉得惊心动魄觉得千回百转觉得鲜血淋漓觉得天塌地陷的经验,都变成了不足与人道却又荒诞不经,有趣却又不无伤感的故事。
第三章开头的这段叙事者的议论,似乎道出了作者对他所描述的这段历史和人物的复杂的情感态度。
这部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这种叙事角度的客观性间离性和超脱性的特征,有利于作者在一定的历史距离中,以理性的观察和冷静的剖析,对历史及人物进行喜剧性的洞照和审视。但如前所述,由于作者与这段历史的深切联系,由于作者温和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由于作者的诗人气质与难以自制的主观抒发和情感表达的意愿,又使他在叙事中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削弱第三人称叙事的客观性,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强化着作品叙事的主观色彩。在小说的开篇部分作者的叙述语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快乐,我们的悲哀,我们在地球上的胡作非为,我们的罪恶和忏悔的泪水,也只有在许多许多万年以后,在除了极少数极少数考古学家再没有任何地球人关心我们知道我们乃知相信我们当真这样生活过激动过哭过的时候,才能被那个辽远的星球上的智能人所觉察”。在我看来,这时原“我们”,显然与小说里的“他们”具有同一性;作为“我们”中的“我”的叙事者,显然实际上是“他们”中的一员。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大量采用没有引号和引导语的“自由直接话语”,⑥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的相互转换极为灵活而自由,二者的界限甚至也变得模糊和难以确定起来,人物语言的客体性因而被削弱了,作品的整体的主观性加强了。
三
莱辛曾指出,喜剧的功用“在于训练我们的才能去发现滑稽可笑的事物。”⑧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充分表现了王蒙作为喜剧大师的杰出才能。他是多么敏锐而深刻地发现和揭示了历史生活中异常丰富多样的喜剧的、笑剧的与闹剧的现象啊!
在小说中,主人公们对于指引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政治理论话语的崇拜和信念,本来是自愿的、真诚的和圣洁的。但是,当革命取得胜利,政治理论话语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政治权力话语的时候,他们的崇信就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对于政治理论话语的崇信了,而是已经包含和掺杂了对于政治权力的服从、甚至屈从的因素了。第十章描写钱文按照组长徐大进的吩咐,回到住处不睡觉先写揭发批判杜冲的材料。他虽然感到为难,但还是得写,“不管怎么说大进也算是领导”。他是这样想的:
我是抗拒不了组织的。我的胆子早就吓破了。我胆小。谁愿意嘲笑我就随他嘲笑去吧。除了乖乖的,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又敢做什么呢?要知道这一切是我自己的组织、我自己的党、我自己的革命、我自己的事业所要求于我的呀!要知道这就是真理的化身呀!……除了听领导的,我还能听谁的呢?难道我能听我自己的?难道我愿意自取灭亡?在党和人民面前,我愿意承认我只是一个渺小的可怜虫,也许我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我的惧怕和畏缩上呢。
在这种情况下,钱文们的认真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积极揭发别人批判别人,便具有了喜剧性和可笑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真理”即政治权力话语的信从中,具有一种盲目的、自欺的,甚至是怯弱的、奴性的东西。在他们的“低头认罪”和“疯狂劳动”的“真”中,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了“假”的东西。这种真与假的悖逆和不协调,不能不在他们的身上涂抹上喜剧的和笑剧的油彩,他们的言行也因此具有一种做戏的、表演的性质。⑨钱文的妻子叶东菊大约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她茬弱而不卑怯;虽然她远未达到自觉程度,但是,在她身上的奴性最小。尽管她被开除了工职,但她“硬是一个字也不检讨,一个字也不揭发!”
作为热情地追随革命、拥抱革命、献身革命,真诚地崇拜和信仰指导革命赢得胜利的政治理论话语,坚决地服从革命和人民利益的职业政治工作者,钱文、郑仿、萧连甲、费可犁等人对以革命、人民和真理的名义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对右派实行劳动改选的措施,是努力地去认同、理解、响应和参与的,不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怀疑和困惑。然而,作为能够从实际生活中获得正常感觉和常识性判断的有血有肉的个体的人,他们不可能不直接地、真切地、具体地和经常地感到种种别扭、反常、荒唐的可笑,甚至在潜意识里产生反感和憎恶。下乡劳改以后,钱文觉得自己“长大一点”,郑仿则“似乎更加惶惑了”。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他们尚不可能把自己从生活获得的这种零碎的、片断的感觉,上升到完整的、有机的理性认识的高度。于是,在他们身上,理性和感性发生了断裂,职业政治工作者和普通人产生了分离。在理性认识方面,他们对于反右斗争是无条件地拥护和由衷地赞成的;但在自我感觉中,他们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在这样一种情境当中,他们的言行和形象不能不令人多多少少地感到别扭、乖戾不和谐、不自然,并因而具有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喜剧色彩。在这些人物的形象塑造上,体现了作者的讽刺的和幽默的激情至相交融的特点。钱文、郑仿们发出的笑常常是自嘲性的,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心理内容和释放、净化与升华等审美效应。
在小说结尾,劳改右派即将摘帽回城、重新安排工作的前夕,领导决定由郑仿负责护秋——看青。在凉风徐来,暑意全消,大地更加迷茫、天空更加朦胧的夜晚,郑仿独自一个人,不由得想起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荒唐、尴尬的一生:在反右斗争中,他从“儿童文学刊物的主编”像“高天上的风筝一样地一个倒栽葱、嘴啃泥,跌入了臭屎坑烂泥塘。”
然后是一个每月十八大吊的准罪犯,一个堂舅家的食客,一个被分析得一塌糊涂又能随时把一切人分析个体无完肤的口舌如刀的改造者,一个改造的“上游”,一个大跃进民歌的作者,一个犯了错误才发掘出诗才的新生活的歌者,一个像大蒜的罪犯,一个被赦免的流氓,一个小寡妇的未婚夫,一个墓地上的逍遥客,一个猫头鹰的知音,一个初夏夜的田园风光的领略者了。真是有趣呀。真是如梦如儿戏如逗弄如小说如神话如不可思议如胡闹乱弹琴呀!
然而,这一切过去之后,他还是他。过去的一切又是显得多么可笑、多么徒劳、多么无事生非、多么过眼烟云和了无痕迹呀!想到这儿,郑仿“躺在墓地上哈哈大笑起来!笑出了许多眼泪。”他的笑,具有无奈的自嘲和酣畅的宣泄成分,既是对生活的谬误和命运的荒诞的嘲讽,又是对在这样的生活和命运中自己的被动性与“自己的局限性”的揶揄。诚如作者所说,在这里,“喜的基础是超越”,这里的“喜是悲的升华,是悲的超度,是悲的极致”,这里的喜是悲中来的喜,“是有深度的喜”。⑩
对于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他人的命运的人物,如陆浩生、曲风旺、洪嘉、徐大进、苏二进,以及带有极度夸张的疯狂的喜剧色彩的闹剧化人物章婉婉,作者的讽刺的笑胜过了幽默的笑,尖刻犀利的“冷”嘲多于慈悲宽厚的“热”讽。
四
《失恋的季节》的喜剧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品的语言艺术,甚至可以说,没有作者风格独特的语言,就没有这部作品的独具一格的喜剧性。喜剧大师和语言大师,在王蒙身上是统一的。
美国当代语言哲学家约翰·西尔勒认为,“我们怎样去领悟我们所经验的世界,是受到我们的反映系统影响的。……世界是按照我们划分它的方式而划分的,而我们把事物划分开的主要方式是运用语言。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的语言范畴”。(11)王蒙笔下的主人公们便是按照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话语,去领悟他们所经验的世界和认识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他们感受和认识现实生活的特点,就是这种话语感受和认识现实生活的特点。这种话语是他们唯一能够运用、能够言说的具有合法性的话语。甚至可以说,运用和言说这种话语是他们唯一的存在方式。他们的语言因而失去了个人性、独特性,以至于他们说话的时候,听上去好像是政治话语的独白。因此,要表现这些职业政治工作者的经历、命运、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是离不开当时的政治话语的。这恐怕是王蒙描写五、六十年代生活的小说中频繁出现当时的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主人公们在言说政治话语的时候,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郑重的和真诚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这又是正常的、不带任何喜剧色彩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反差和语境的相异,立足于九十年代的作者在对此进行具体的心灵感受、情绪体验和文学表达的时候,上述一切的荒谬可笑的喜剧性便鲜活而真切地凸现出来。我们读者在《失恋的季节》中感受到的喜剧性,正是作者在被情绪记忆激活了、唤醒了的历史生活中,感受到、体验到和意欲表现的喜剧性。正像西方学者施皮策尔所说,当人们在重复别人的话语时,“仅仅由于换了说话的人,不可避免地定要引起语调的变化:‘他人’的话经过我们的嘴说出来,听起来总像是异体物,时常带着讥刺、夸张、挖苦的语调。”(12)政治性话语,经过作者的遴选和艺术的排列组合之后,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之中的时候,其语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候,政治话语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话语了,已不是原生态的政治话语了,而是一种变了调的政治话语。这种变了调的艺术化的政治话语,是直接服务于作者的艺术目的和审美意旨的。不论是在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中,只要出现了政治性话语,我们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语境和氛围中,从语调和语气的细微变化中,分辨出语言的真正含义,体察出人物的实际意图,乃至作者的倾向和情感态度。这种情形导致了双声语的产生:“一种语言竟含有两种不同的语义指向,含有两种声音”。(13)在《失恋的季节》中,这种双声语主要表现为三个类型:仿格体、讽拟体和游戏体。
仿格体即模仿他人风格的语体。这种语体通过仿效他人风格,使他人指物述事的意旨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亦即服务于自己的新的意图(14)例如,小说第十三章,劳改右派们在汇报回城休假的见闻和思想时,发觉组长徐大进和杜冲说话的“调子”完全不同,但他们对这种矛盾不想去深究,因为他们觉得,“辩证法嘛,这么讲也是对的,那么讲也是对的,二者而且是不矛盾的,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对你态度好是为了鼓励你改造,所以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感人的;对你态度不好,也是为了敦促你的改造,所以这种态度也是正确的和尤其是感人的。”显然,这是对当时出现在政治性话语中的某种伪辩证法的带有讽刺意味的模仿。小说第九章,每天晚上连续的、拖得很晚的批判会终于结束后,对此很反感而又困倦不堪的钱文甚至于想说,“枪毙也得先让我睡一觉呀!他想有时候人的需要就是这样的简单,困倦到极点的时候,好好地睡一觉就是幸福就是上游就是天堂就是共产主义;而明明困倦极了却硬是不让睡觉这就是痛苦就是地狱就是下流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对于动辄进行政治定性、乱扣帽子的政治性话语,这里进行了极度夸张的挖苦模仿。第十三章写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劳改右派们不得不以稀代干、以粥代饭,天天喝糁子粥,但仍填不饱肚子,“这些人便在扩大肚腹容积上狠下功夫”。这里是对政治话语中的个别词语的仿效。把常常出现在政治性话语中的词语“狠下功夫”仿用在这里,明显地含有讽刺意味。第九章写在一次批判费可犁的会议上,费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认为大家谈得非常之好。这么好那么好这个好那个好实在是太好太好”。这种变了形的模枋,是针对政治性话语中泛滥的空话、套话和假话的。作者在第十章描写了钱文对于在劳改右派中评出上、中、下游和排列名次的想法,他“虽然是中游的倒数第二,比起费可犁来毕竟名次在前,这就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喽!徐大进苏二进分别列为改造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自然是天经地义,众望所归;就是郑仿列为第三名,这也是根据曲风旺同志的直接指示,当然是正确的喽,你得不到曲风旺同志的直接指示,你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起码他没有像钱文那样吃西餐与喝酒,又没有像费可犁那样甚至引起了农民的讨厌。领导总是正确的噢!”这里讽刺性模仿的对象,我以为是有些领导干部讲话时装腔作势的话气腔调。
和仿格体一样,讽拟体也是借他人语言说话;而与仿格体不同的是,作者要赋予他人语言一种同原来的意向完全相反的意向。隐匿在他人语言中的第二个声音,在里面同原来的主人相抵牾,发生了冲突,并迫使他人语言服务于完全相反的目的。”(15)这部作品中的讽拟体语言大多是杜冲的“专利”。同样是右派,同样到郊区劳改,杜冲的心态,逻辑与别人完全不同,他不痛苦,不反省,不分析,不耿耿于怀”,他“不相信崇高的革命,所以也不相信危险的反革命”,“不相信神圣的原则,也不相信可耻的叛变。”他似乎是一个局外人,虽置身其中却又能超脱事外、冷眼旁观,因此比别人多了一份清醒、一份透彻。对自己周围的一切,他常常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所以,当他说起话来“话里有话”时,他的话便是讽拟体语言。如:“我是反动透顶愚蠢透顶头上长疮脚底下流脓的坏种的了。啊,真好,真好啊,清除了那么多坏人,多伟大呀!真是英明呀光荣呀正确呀有意思呀……瞧,大跃进时搞得多么轰轰烈烈!不把右派揪出来,能有大跃进吗?”“专门让最不好的人干最好的事,也就希望我们这些最不好的人变成最好的人,也就是对于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太伟大了,太温暖了!”“戴个帽子(指右派帽子——引者)是多么好呀!只要有了帽子,什么思想问题都好解决,什么私心杂念都好克服,消食化气,降火灭瘟,安神补脑,调阴理阳,四季平安,长命百岁!”“是啊是啊,洪嘉同志真好喽!我们的女同志的觉悟真是一个又比一个高喽!好喽,好喽!好喽!太好啦,太好啦,……”这些具有讽拟体风格的语言,或是对当时流行的政治批判词语的讽刺性摹拟,或是为讽刺而摹拟当时通用的歌颂性词语;其讽刺的锋芒既有对准所摹拟的政治话语的风格的,也有瞄向所摹拟的政治话语的思维逻辑的。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说话者的意旨与被讽拟对象的意旨都是截然相反的。
五
除了模仿风格体和调整摹拟体语言之外,《失恋的季节》大量而频繁运用的是游戏体语言。作者创造游戏体语言的方法是丰富多彩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构造新词。如:“欢秋”。“毒物”。“右友”。“叹为闻止”。“脏不忍睹。”“有吃无类”。“闻斗起舞”。“豪言巧语”。“倚左卖左”。“人精人英”。“弥天大错。”“有呼无应”。“穷饿潦倒”。“东郭女士。”“眼比天高。”
二是活用词语。如:“我也右派了”。“马列主义了半天。”“让我们资产阶级一下吧。”“做什么还是集体一点好。”“改过来造过去”。“老态虽不龙钟却也歪歪斜斜。”“任虽未必重,道那倒是确实很远很远的。”“什么叫痛快呢?先痛后快嘛。”“革命中的革命,天上的天,比太阳还要太阳的太阳呀!”
三是运用语气词。这种情形多见于领导干部的讲话。陆浩生、曲风旺、洪嘉等人讲话时,“嘛,吧、呀、喽、啊、哟、奥、吗、呢、啦”等语气词,使用频繁,语言因此而显得游戏化了,具有了做戏和表演的味道。最典型的则是下面两段:|戴花要戴大红花啊——哈,|骑马要骑千里马啊——哈|唱歌要噢唱跃进歌,|听话啊要听党的话!|共产党昂来领翁导噢,|把山安治日呀,|人嗯民的力依量昂,|大啊无唔边安。|蟠龙翁山安上昂,|锁哦蟠安龙翁啊|……
这两段歌词,特别是后一段歌词,由于超量地超常规地嵌入了语气词,十分明显地带上了游戏的诙谐的、调侃的意味。
四是采用比喻、借代、回文、顶针、错综等多种修辞方法。如:郑仿在他的“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革命罪行”被揭露后,对他斗争规模非常大。开一次会,一会儿揪上台来一会儿轰下台,“斗了个不亦乐乎。斗了两个多月——用他自己的话——才算炖熟了的”。朱可发的“右派言论”被揭发出来批判,“当群众问他认不认罪的时候每次他总是回答:‘我认了这壶酒钱了’。”曲风旺在批判萧连甲时说:“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你会把屁股放到哪一面呢?……要害就在屁股问题上!屁股屁股屁股!!听见了吗?我说的是屁股!”萧连甲投海自杀后,劳改右派在学习毛主席的《介绍一个合作社》,联系实际、联系萧连甲自杀事件谈体会时,大家纷纷表态,“自己绝对不做花岗岩”,声称自己“绝对没有做花岗岩的意思更没有做花岩的胆量”。杜冲声明:“我们不是花岗岩,我们宁愿做‘糁子粥’。”政治批判、政治学习、政治表态,本来都是很严肃、很庄重的事情,但在语言文字的表述上采用了这些修辞方法后,严肃的庄重的内容与游戏化的近乎玩笑的形式之间产生了不协调。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势必给人以滑稽可笑之感。
事实正是如此。朱可发在大唱他的听党的话认酒钱的论调时,听者的脸上出现了“一抹浅笑”;对“自己是糁子粥而不是花岗岩”的“妙喻”,右派们“人人咀嚼,个个温习,不断重复,笑声连连”。萧连甲投海自杀,人们喝糁子粥填不饱肚皮,这本来是悲剧性的事件和境遇;但是,经过作者采用游戏体的语言文字,进行了喜剧化的艺术处理之后,萧连甲的不幸和人们的痛苦,也变成了开玩笑的对象,变成了调侃的对象。喜剧艺术大师卓别林认为,幽默是对于痛苦的戏弄,每一个玩笑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出悲剧。(16)《失恋的季节》拿痛苦和不幸开玩笑的幽默当中,也具有一种刻毒和残酷的意味。正像作者所写的那样,“他们颇不忠厚地拿着糁子粥自嘲,他们的嘲弄中流溅着毒汁”。如前所述,正是在这一点上,这部作品的幽默,接近了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黑色幽默。
小说结尾写到,二十几年以后,钱文们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只有闵秀梅哭了个死去活来,因为领导告诉她,她不需要改正,她压根就没有被定成右派。“但不知为什么,人们还是一直拿她,尤其她自己拿自己硬是当右派对待。”命运和闵秀梅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啊!面对这荒诞的存在、残酷的命运和不可理喻的人生,面对着“头发秃得一塌糊涂”的闵秀梅,我们无论如何也笑不出声来了。掩卷之后,笑声过后,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部喜剧作品所深含着的悲剧性质。在喜剧化的形式、风格和外壳下面潜藏着的,是深刻的、令人震悚和沉思的社会历史悲剧和人的悲剧。
游戏体语言和具有游戏化外观的仿格体、讽拟体语言,有效地构成了这部大型喜剧作品的不可或缺的语言基础,出色地完成了它所担负的艺术使命。从语言格调、情绪氛围、语气系统、审美感受、艺术效应方面来看,仿格体、讽拟体和游戏体语言给作品带来了滑稽、调侃、嘲弄、笑谑的喜剧色彩,引起了冷潮热讽、谐谑刻毒、尖酸刻薄的笑声;从作品的意蕴、内涵、倾向等方面来看,仿格体、讽拟体和游戏语言,非常契合地适应了作者对于具有“文字游戏”(17)文化传统的“瞒和骗”(18)的话语游戏的巨大泥沼的精神逃离和文化突围的艺术需要。作者采用了以游戏反抗游戏的以毒攻毒的文学策略和语言技巧,现实世界话语游戏在游戏化的文学表达中被艺术地颠覆和瓦解了。历史和存在的矛盾、荒谬、不合情理和不可理喻,在笑声中遭到了尖锐而彻底的否定。作者以拟游戏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游戏化的语言风格,巧妙地隐含着并鲜明地显示了否定的、批判的反游戏的情感态度,并由此达到了对话语游戏的文化、历史与现实的艺术解构和审美超越,(19)实现了以新的喜剧艺术形式“和自己的过去诀别”的意图。
《失恋的季节》作为一部大型喜剧作品是独树一帜的。由于作品主人公所置身其中的“广阔的语言和超语言行为的环境”(20),以及他们与这一语言和超语言环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部作品的喜剧风格和语言风格也是具有独创性的。这种艺术独创性所隐含着的,是特殊的文化性格。
这部作品是作者正在创作的“系列长篇”的第二部。我感到,作者尚有更深广的苦闷、更强烈的愤懑,有待于宣泄和抒发。我们期待着。
注释:
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别林斯基《诗的分类》,《西方文论选》下卷第38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③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316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④转引自陈瘦竹、沈蔚德《论悲剧》第4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⑤赫斯列特《英国的喜剧作家》,《西方文论选》下卷第40页。
⑥参见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⑧莱辛《汉堡剧评》第二十九篇,《西方文论选》上卷第426页。
⑨笔者在《话说游戏:沉隐与逃离》(载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2期)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请参阅。
⑩王蒙《漫谈喜剧》,《风格散记》第80、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麦基编《思想家》第267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
(12)转引自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267-268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13)(14)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260页。
(15)巴赫金《陀思妥耶夫基诗学问题》第266页。
(16)转引自陈焜《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第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7)(18)鲁迅语,参见《且介亭杂文二集·迩名》、《坟·论睁了眼看》。
(19)详见拙文《话语游戏:沉陷与逃离》。
(20)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第574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