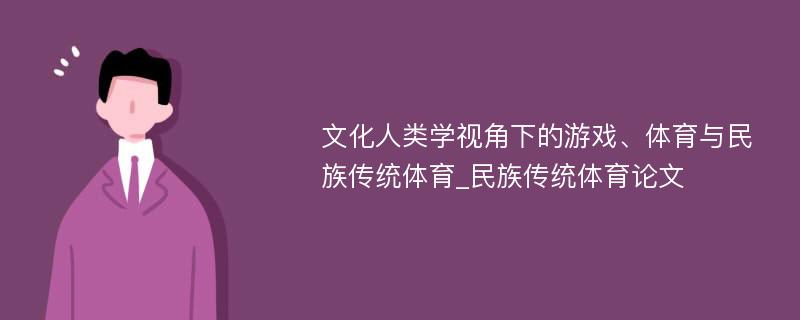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游戏、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育论文,人类学论文,视野论文,民族传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1-0033-04
游戏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其中不但残存有人类历史的初始景象,而且也绵延着人类对教育、伦理、礼仪、社会规则、美学和哲学等诸多方面的实践和思考。
1 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下游戏的本质:自由
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游戏之说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席勒、斯宾塞,再到现代心理学的弗洛伊德、皮亚杰,文化人类学的泰勒,阐释学的伽达默尔,以及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人,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游戏现象进行了研究与阐述。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有言:游戏是休息,然后导致工作效率提高。这是第一次明确游戏和工作的关系,也是人类第一次明确指明游戏的目的。其后,古罗马文论家马佐尼讨论诗的模仿性质时,进一步指出了游戏的目的:诗和游戏一样,他们的目的就是娱乐。
从理论的高度对游戏进行研究的第一人是伊曼努尔·康德,他用游戏来分析美学问题时,提到游戏和艺术有两个共通点:都是令人愉快的;没有目的,不关心实际利益的获得和理性的参与。更为重要的是,康德从游戏和艺术共同的愉快情感出发,进而推到游戏和艺术的本质是自由。康德的主张深刻影响了后来研究游戏的学者。弗里德里希·席勒认为:统一于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游戏冲动是以自由为其精髓的。同时,席勒把游戏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完全的人。深受席勒影响的谷鲁斯(Karl Groos)撰写了《动物的游戏》(1898)和《人类的游戏》(1901),其后的赫伯特·斯宾塞、弗洛伊德、赫伊津哈和伽达默尔等人都对游戏有一定的研究。其中,伽达默尔和赫伊津哈对游戏的研究更为厚实和深刻。伽达默尔提出了三种游戏概念:作为自我表现活动的一般游戏概念;作为理解游戏的特定游戏概念,主体意识间互相参与融合,从而导致具有再创造性的精神交流活动;作为复合性理解活动的艺术游戏概念,艺术是感性与非感性相结合的复合意识的表现与接受活动。
历史上,把游戏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第一人是赫伊津哈。赫伊津哈把游戏分为三个层次:广义的游戏泛指活动者以活动自身为内在目的的虚拟活动(包括个体游戏和群体游戏);中义的游戏指群体游戏,某个群体在特定的休闲时空中按特定规则进行的社会性游戏;狭义的游戏仅指竞争游戏,参与者的目的在于满足追求优越及其他相关心理需求的具有竞争性的群体游戏。
对人类而言,游戏如此相亲相近,使得许多哲人都试图把它形而上。对于体育人类学来说,游戏在体育人类学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给游戏下一个可以被多种文化接受的定义也是十分有必要的。然而,游戏概念如此纷繁,欲一统它几乎不可能。但是,从康德到赫伊津哈,这些研究游戏的知名学者都把自由作为游戏的本质,这种自由是思想和活动在摆脱生存羁绊下而获得的愉悦状态。这也是本文对游戏研究的出发点。同时,根据前人研究的成果,对游戏有如下总结:工作是游戏最佳参照活动之一,非劳作是理解和诠释游戏的核心成分之一;娱乐和习得是游戏的主要功能;竞技性是游戏的显著特征。至此,不妨把人类社会中的游戏界定为:为了获得习得和娱乐,在非劳作前提下而从事竞技性活动所获得自由状态的活动。事实上,游戏与节日、宗教祭祀、嬉戏活动、文艺活动等都是在人类在闲暇时间里的活动。
2 游戏的分化、创新与融合
游戏行为在动物中普遍存在,人类的游戏行为早在人类文明之前业已存在。在仰韶考古发掘中,发掘出了石球、陶球、陶制陀螺等器物。公元前15世纪创作的浅浮雕,已刻画了划船手比赛和追逐战车飞奔的战士。公元前1360年的赫梯文本也反映出当时古印度已有了高超的赛马术。同时,人类学家也记载了许多游戏活动,如彝族的“别尔”、“老虎护子”,爱斯基摩人的“耳朵负重跑”、“飞行”等。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加深,尤其是文化意识的出现,不但改变了人类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游戏。作为人类在生存和生理时间之后,在闲暇时间所获得的一种自由体验的游戏,逐步在进行着分化、创新和融合。
2.1 游戏的分化
人类文化意识的出现,复杂了人类本身,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尤其是人类的生存物质有了富裕之后,人类自身也逐步分化成了高低贵贱之别。伴随着人类阶层的出现,尤其是凡勃仑所言的有闲阶层出现后,游戏从最初的有别于生存手段的劳作和生理作息活动,逐步在分化,在复杂化,也在丰满化。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游戏的功能性分化;游戏参与主体的分化;游戏本体的分化。
2.1.1 游戏的功能性分化
游戏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环节,在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功用。随着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游戏的功能进行分化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游戏的主体功能越来越突出。用作学习生存手段(或娱乐手段)的跑跳投等游戏活动,逐步分化为:教育(社会化)、军事、娱乐等范畴下的游戏,拟或几个主要功能交叉并存的游戏。一些游戏逐步专门为教育或军事服务,如射箭、摔跤、标枪、弈棋等,而一些游戏活动则专门为了娱乐而独立发展起来,如斗鸡、斗鸟、马球游戏等等。在我国古代游戏活动中,“射”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不但具有习得生存手段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明显的教育、礼仪和娱乐性功能。类似此种游戏在人类社会中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如摔跤、御车赛等。
2.1.2 游戏参与主体的分化
随着人类物质的富裕,导致人类在度过生存时间和生理时间之后有一定的闲暇时间用来支配,尤其是所谓的有闲阶层产生之后,对闲暇时间如何消耗成为人类社会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全人类有着大同小异的共性:成人用游戏、节日、宗教祭祀、嬉戏活动、文艺活动等活动来使他们的闲暇时间更加社会化。在绝大部分民族志作品中,对游戏的描述比较少。一般而言,零散地对游戏的描述多与儿童行为或教育有关;或存在于节庆、祭祀等活动。从笔者对黔东南独木龙舟的田野调研可知,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游戏正从仪式中剥离出来,逐步成为成人游戏的一个项目。随着人类物质文化愈发达,成人从其他活动中剥离或者完善游戏的愿望和行动也越来越明显。一般而言,途径有如下三种。一是用于儿童的游戏逐步成人化,成为成人打发闲暇时间的手段;二是在节日、舞蹈、宗教祭祀等活动中的具有游戏性质的一部分开始脱离它的母体,逐步独立出来并被成人所使用(有时也用于儿童间的游戏活动);三是用于劳作、战争等活动中的一部分,转变成成人闲暇时间中的游戏项目。
2.1.3 游戏本体的分化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文明化,以及成人逐步成为游戏的主要参与者,游戏本身也在进行着分化。游戏本体的分化一般存在两方面:一是游戏的种类在逐步细化;二是游戏的构成在分化。划分标准的不同,游戏也被分化为不同的类别。从身体运动的角度而言,游戏可以分为运动类游戏和非运动类游戏。运动类游戏如朝鲜族的秋千、彝族的爬油杆、仡佬族打篾鸡蛋等;非运动类游戏如我国古代历史上的斗诗、赛歌、棋牌类游戏等。由于使用标准的不一,对游戏的分化种类的归类也不尽相同,在此不一一列举。游戏的构成分化主要是指在游戏规则逐步规范化的过程中,作为游戏整体中的参与者和观看者逐步变得成泾渭分明。带有竞技成分的游戏,随着有闲阶层的逐步扩大以及交通技术的进步,参与者和观看者逐步被分化为不同的人群,专业性的游戏表演者和观赏者逐步形成。
游戏的分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在这个过程中,游戏的创新也在不断出现。
2.2 游戏的创新
创新是人类的文化能力之一,作为人类文化的游戏同样也在不断地被创新。一般而言,人类的仪式、节日都来源于古代人类与自然斗争或感恩行为,有的因战胜自然而定为节日,有的因屈服和敬畏自然而定为节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仪式和节日都是人类的创造成果之一。不管是作为节日的环节之一,还是作为人类闲暇时间的活动之一,游戏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成果之一。德格鲁特在他的《厦门的节庆》中指出:古代中国的登山节导致了赛风筝的出现;仡佬人的打篾鸡蛋、苗族的斗牛赛等游戏都是由于故事或传说而被创造出来的游戏活动。类似的情况比较普遍。
仪式、故事、传说或神话等创造除了游戏,游戏(或具有游戏性质的活动)一旦出现,犹如伽达默尔所言:游戏不是从属于人的活动,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游戏犹如具有生命一样,它在不断地进行创新。一般而言,游戏的创新主要存在于对规则、器具、场地、时间、奖励、选手、服饰、仪式等环节。游戏创新的宏观背景主要是物质生活的丰富以及文化的濡化和涵化现象,尤其是文化的涵化对游戏的创新影响明显。海南黎族苗族“三月三”节的活动内容不但继承了昔日的对歌、射箭、摔跤、荡秋千、跳打柴舞、粉枪射击等传统的内容,而且还增加了其他民族的游戏项目。类似这种情况的涵化现象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是普遍。
2.3 游戏的融合
游戏作为人类活动之一,它不断地从仪式、祭祀、节日等活动中被剥离出来,也不断地被仪式、祭祀、节日等活动融合。我国正月十五元宵节早在汉武帝业已存在,不过,真正作为民俗节日是到唐宋时期才发展起来的。据如今文献资料可知,在唐宋时,元宵节上就开始出现游戏活动。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正月十五日元宵……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歌舞百戏,粼粼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游戏融入节日、仪式和祭祀中的情景,在现代社会更加普遍和突出。很多现代节日都加入了现代的游戏活动,如传乒乓球、合力吹气球、瞎子背瘸子等等。
游戏被融合到民间节日活动中,是一个自然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游戏不断地被分化和创新,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各异的活动集合体。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时代,游戏的自生自灭虽然十分缓慢地,但是它的变异却是十分庞杂。一村一寨的同一游戏项目存在差异的情景十分普遍,形成了差异万千的游戏形式,然而,伴随着人类进入工业时代,这种情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3 从游戏到民族传统体育
从游戏到民族传统体育的变迁,经过了两个阶段:从游戏到体育;从体育到民族传统体育。二者相依相成,不可分割。
3.1 从游戏到体育
在文艺复兴的滋润下,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中叶开始逐步席卷了全球。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不但造成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极大提高,而且也在重新塑造着人类的生活、工作、习俗、宗教等等方方面面。尤为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带来新的理念——标准和以人为本。肌体劳作方式的陡然改变,使得人类的肌体不能快速地进化到与之相适应的程度,造成了很多身体问题;以人为本的理念取代以神为本,使得人类开始重视人类身体在生理层次上的满足和锻炼。这些,促使民间广泛存在的游戏逐步被工业化,即部分游戏开始标准化。
游戏的标准化为游戏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一村一寨各不相同的游戏被逐步标准化,制定规则、形成组织,组织大规模比赛等,游戏逐步和工业时代的一个新兴名词——体育(Physical Education/Sports/Competition等)变得不可分割。游戏正在被体育化。伴随着“日不落”帝国的形成,英国在逐步统一一些游戏规则的同时,也把这种与游戏具有不同性质和文化内涵的变种——体育传遍了整个世界。
1850年以后,体育已走向全球。英国规则下的足球、棒球、羽毛球、乒乓球、越野赛马、一些田径项目等等逐步成为全球规则。欧洲大陆于1875年在布达佩斯首次举办了按英国规则组织的田径比赛,欧洲人为自行车公路赛和赛车场赛的热烈场面所吸引,越野赛马、射箭、滑冰竞赛日渐风行。现代游泳诞生于17世纪60年代英国的约克郡地区,1837年成立世界上第一个游泳协会。类似的情况也在西欧和北美地区出现:统一本国游戏规则,推广本国体育项目和规则,成立体育组织,组织比赛。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把游戏的体育化推向了一个高潮,推向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正规化道路。在体育这种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不发达国家的游戏在迅速地经历着代换、附加、综摄、创造、抗拒等文化涵化的过程。至此,体育逐步开始替代游戏的部分地位,世人眼中的体育俨然业已成为游戏的上位概念。事实上,用体育一词完全取代游戏,是工业文化的内在要求:任何事物标准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全球统一化,去其差异性。然而,虽然游戏有藏匿于体育之后表象,但是它和体育截然不同的特征还是保持着,也将永远保存下来。
3.2 从体育到民族传统体育
在游戏体育化的过程中,不是任何游戏项目都能被体育化的。游戏最初被体育化的多是所谓有闲阶级认可的活动,并且对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员身份有着诸多限制,如田径项目、击剑、板球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低层次的、流传广泛的游戏活动才逐步被社会广泛认可,如足球、拳击等。然而,如繁星之多的游戏活动,能被体育化毕竟是少数。只有那些具有高对抗、有悬念、显身份、显个性、新奇变化等特点的游戏能被体育化,因为游戏这些特点符合工业文化(或后工业文化)的要求。即使在游戏中没有符合这些要求的,那么就创造和改造一个体育活动使之适应之。然而,游戏中的绝大部分不具有这些特点,在世人眼中仅有体育而无游戏的背景下,非体育化的游戏就有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称谓:民族传统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是工业社会中对游戏进行表面体育化的称谓。众多的游戏活动,不具有被体育化的特点,也就意味无法在工业文化体系下长久地传承下来,自灭看似是它们的唯一归宿。同时,体育对这些游戏也造成了革命性的冲击,体育文化迅速地植入到这些游戏中,成为它们理所当然的文化内涵,从表面上看,这些游戏也被体育化了。它们仅仅是移植了体育文化的逻辑思路是:以体育文化的核心之一——标准化来改造这些游戏,使得它们成为具有统一规则的游戏;从形式上借鉴体育推广的手段,组织比赛,游说企业和媒体,扩大影响,吸引眼球,再扩大比赛规模,一如企业所追求的规模经济一样。在这样的体育文化和体育推广模式影响下,世界各国涌现出了许多所谓民族传统体育比赛赛事,和时下提倡的休闲文化充分结合,轰轰烈烈,大有比肩体育赛事的趋势。
然而,民族传统体育毕竟不是体育,用人类学的眼光审视它们,二者之间有着明显地区别。
4 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
人类学多关注非工业文化下的人类的文化、行为、社会等,与社会学关注工业化国家中的种种问题不同。可以说,一个用涓涓细流般的长时间观察来思考人类社会和文化;一个用急风暴雨般的选定问题、设计问卷、发问卷、统计问卷、分析问卷、提出对策等手段来痛思人类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提出应对措施。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出发点,造成了两个学科不同的研究风格。用文化相对论、整体论、普同论的研究视角来整理、分析、诠释涓涓细流堆积起来的小样本量考察成果,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然而,它对解读和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则最为恰当,因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根源来源于非工业的文化形态,它虽被冠以“体育”,但它却不是工业文化内涵下的体育。
用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所谓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体育项目所依存的文化土壤不是工业文化中的标准化、分工化、利己主义、消费化等内涵,而是非工业文化(拟或是农耕文化、游猎文化、原始文化等文化形态)的随意、自给、无欲等文化沉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数依存于一定的节日、祭祀、礼仪习俗下,有着极为清晰和深厚的传说、神话故事、宗教和习俗传承,而体育项目的这些业已模糊和淡化,有着的多是功利性的诉求,如金钱、健康、荣誉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所依存的人群多是没有工业文化观念或是工业文化观念不深的、较为闭塞的族群,这和体育所依存的在工业文化濡化下的具有全球观念和视野的人群截然不同。虽然,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了体育的一些表面特征,甚至是核心内涵,但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体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根本不是规则的统一、比赛次数和规模、参与者和观众的多寡和赞助金额的数量,而是它所依存的空间、文化以及具有这种文化的人群。具体体现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人(参与者和观看者)的服饰、器具、言辞、食物、行为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即所在地的气候、地貌、植被、动物、工具、建筑等方面的状况;民族传统体育背后所具有的深层文化,即仪式、禁忌、目的、心智特点等等。然而,国内有多少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者能对这些关注呢?人类学的研究十分艰苦,尤其是出成果要漫长的时间,这在眼下追求短平快的研究氛围下有点突兀。毕竟,有多少年轻的学者愿意做十年磨一剑的等待呢?然而,跳过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根本,而去研究和它无关联的体育特征,分析、论证和阐述“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种种不足和经验,从而提出洋洋洒洒万言的应对措施和建议,这是研究的误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5 总结
游戏的本质是自由,它标准化之后的形态——体育的本质也是如此。游戏是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的根源;而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脱离体育的源头和它所依存的文化内涵而解读体育,从而想当然地阐述民族传统体育,显然是不合适的。欲纠正这种研究习惯,必须从人类学的视野来重新思考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条理它们内在的逻辑,以求能把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建立在牢固的研究基础上,形成逻辑清晰、推理缜密、资料扎实的研究成果,形成真正的体育学科的范式!而不是凭一言、一个事例或一个观点来演绎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窃以为,这应是体育工作急需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
